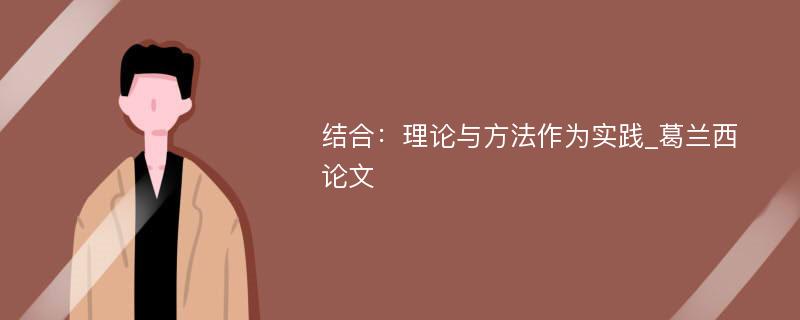
接合:作为实践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以下简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不复存在。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从率先将其学科化的伯明翰大学消失,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与方法,它已播散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地,内化为人文及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近十几年来,中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态度从1990年代中期的激烈反应与争鸣,转变为理性、冷静与细致的学术探讨,“接合理论”(the theory of articulation)也因此受到了学人们的关注。受发轫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一文的启发,①诸多学人选择了接合理论研究作为新的兴趣点,积极加以评介和阐释。但不难发现,在过去十多年问,接合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种显在的“在异之同”现象:既有的接合理论研究大多止于评析接合理论的内容、特点、意义,未能很好地把握其本质——作为培养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实践的理论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既有的接合理论研究可谓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文化研究的理路,因为研究者没有充分探讨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发展,很少考察接合理论被形塑的情势,忽视了借鉴与反思的双重视角。本文将分析文化研究的范式转移,追溯文化研究对接合理论的选择与形塑,探讨接合理论的内涵与贡献,考察接合理论的运用与实践,以揭示接合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误区与盲点,寻求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现实的接合或者说耦合之道。
一、走向接合理论
约翰·菲斯克指出,“对那些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属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来说”,接合概念遍布其著述。②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接合概念的拥抱与它为“表征平等的空间”而坚持的意识形态传统息息相关,③“意识形态始终为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范畴”④。1960年代末与1970年代初,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进入理论时代,其意识形态认识的核心从阶级转向霸权(hegemony,又译领导权),关注焦点也从英国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转移至媒介研究的微观政治经济学,其支配性研究范式由文化主义过渡为结构主义。原本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选择“第三条道路”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受罗兰·巴特与路易·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的启发,开始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对还原论与本质论的反思:
到1970年代,文化理论家毫不含糊地参与了批评“经典的”或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对彼此关联的两种还原论的依赖: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前者依赖的是对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概念的有限阅读,后者依赖的是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有限阅读。⑤
简言之,经济还原论抑或决定论认为,生产方式(基础)控制、决定社会的其他一切(上层建筑),社会的一切可以还原为相应生产方式的运作,而且唯有通过生产方式才能得到解释;阶级还原论则认为,政治与意识形态实践、冲突等非经济因素与阶级有着必然的对应关系。早在文化主义时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便开始了对还原论的批评,一如其精神领袖斯图亚特·霍尔所言:“虽然文化主义经常肯定不同实践的特殊性——‘文化’不能被吸纳入‘经济’,但它缺乏一种从理论上证明这种特殊性的恰当方法。”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文化主义的支配下,往往求助于别样的经济或阶级还原论,就像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在文化研究奠基作《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面观》中那样,把战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仅仅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到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对还原论提出了自己的‘内部’批评,即还原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支配与从属机制的解释并不恰当”(“Theory”:116)。也就是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已无力解释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这样一些文化现实:新的社会形构、阶级内部显在的个体差异、工人阶级的非革命文化、非经济因素(性别、种族、亚文化)何以进入复杂的支配与从属关系等。于是,霍尔等文化理论家启用巴特、阿尔都塞等欧陆左翼理论家的理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经济还原论、阶级还原论等发起新一轮质疑与批评,实施一种基于解构的理论建构。
这一过程的发生源自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登临英国左翼思想阵地。为了重新激活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赋予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安德森主持的《新左评论》引进了诸多关乎意识形态的欧陆理论,比如巴特对“今日神话”的分析、雅克·拉康对主体性形塑的论述、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米歇尔·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它们先后成为了范式转型中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理论资源,但最终是安东尼奥·葛兰西与恩斯特·拉克劳的理论促成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完成范式转型这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思想转型和战略调整”⑦。1959年,威尔士历史学家格温·阿尔夫·威廉斯向英国人“举荐”了葛兰西,但直到1960年代中期,葛兰西才开始受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严肃对待,或者被独立地解读,或者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并与其他理论家比如阿尔都塞、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巴特相联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葛兰西理论体系中的霸权、有机知识分子、霸权与反霸权斗争、接合等概念渐次显影,结构性地影响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各种关系的阐释,尤其是青少年文化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⑧、政治话语(比如英国性、种族主义、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⑨、都市身份形成经验之间的关系⑩,等等。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首先引起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注意。葛兰西认为,根据其社会职能的不同,知识分子可以大致分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新知识分子即有机知识分子:“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只是要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11)所以,非知识分子并不存在,但我们可以基于知识分子是否与大众相结合、其理论与实践是否相统一,将他们进行新与旧、传统与有机的区分。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观念对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但葛兰西对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其霸权概念。在利用马克思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观点阐释“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时,葛兰西提出了他著名的霸权概念——霸权是控制社会冲突的一种文化及意识形态手段,一系列两相认可的观念或思想,既源自阶级与其他社会矛盾,也为形塑阶级与其他社会矛盾服务: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2)
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某一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通过成功获取从属集团在道德、政治及文化价值等方面的“认同”,建立一种将支配集团与从属集团融为一体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认同,从而确保支配集团的社会及文化领导地位,维护支配集团的支配抑或统治地位。不同于武力制服或高压控制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霸权视领导权为不可或缺的,抑或说领导权是霸权的关键。一如保罗·兰塞姆所言:
葛兰西使用霸权概念来描述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可以援用的各种社会控制方式。他区隔出高压控制和认同控制,前者显现于直接的武力或武力威胁,后者产生于个人“心甘情愿地”或“自愿地”吸纳支配集团的世界观或霸权;一种使该集团具有霸权的吸纳。(13)霸权表现为从属集团对支配集团的话语权威的认同,即从属集团之所以认同和接受支配集团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非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某种身体或心理诱惑,或者意识形态灌输,而是自有理由。比如,从属集团对支配集团的认同可能是因为支配集团的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并以某种方式体现着从属阶级的利益。葛兰西说:
毋庸置疑,霸权的事实事先假定考虑被施行霸权的集团的利益与趋向、达成某种折中平衡——换言之,领导集团应该做出某种经济公司式的牺牲。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牺牲与这样的妥协不会触及本质;因为尽管霸权是伦理-政治的,但它必然是经济的,必然基于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关键内核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14)
说这番话的葛兰西很可能给人以经济还原论者之嫌,因为他似乎在暗示,支配集团必须做出经济妥协或让步才能达成作为霸权基础的折中平衡。但事实上,“葛兰西试图找寻的是机制,当一种制度显在地基于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时,使这种制度得以维持其控制的机制。霸权是葛兰西给出的答案。这种形式的权力并非是由经济或政治支配所简单支撑的”(15)。既然霸权关乎从属集团对支配集团的道德、思想及价值观的认同,支配集团所做出的妥协与让步也就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是必然也关涉到文化及思想等领域。换言之,关乎霸权的认同是一种特殊的认同,是某一社会集团依靠“智识与道德领导权”把自身的特殊利益呈现为整体的社会普遍利益而获得的认同;某一社会集团依靠变特殊利益为普遍利益、变潜在对立为简单差异的手段而获得霸权。正如拉克劳所指出的:
与其说一个阶级的霸权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向社会中的其他人强加某种一致的世界观,不如说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这样一种方式阐释不同的世界观,使它们间的潜在对立得到缓和。英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转化为霸权阶级,所借助的并非是向其他阶级强加某种一致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消除不同于自己霸权事业的各种意识形态间的对立性,成功地阐释它们的程度。(16)
因此,葛兰西所谓的认同无异于谈判;支配集团必须与从属集团就“智识与道德领导权”进行谈判,最终被认同的只可能是支配集团智识与道德的某种“谈判版本”。一如罗伯特·格雷所言:
阶级霸权是一种动态的、变动不居的社会从属关系,它朝着两个方向运动。从属阶级的行为与意识的某些面向可能复制出某种版本的统治阶级价值。但价值系统在为适应种种存在条件做出必要调整的过程中被修订了;从属阶级因此遵循统治阶级的一种“谈判版本”。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霸权的结构改变和吸收不同的价值观,以便有效地阻止它们充分实现其内涵。(17)
支配集团通过实施“智识与道德领导权”而建构的认同、获取的霸权始终“变动不居”;霸权必然随支配集团与从属集团的持续谈判不断更新,呈现为一系列不断变化的话语与实践。换言之,霸权是一种由持续形成与替代过程所构成的非稳定均势,一方为支配集团的利益,另一方为从属集团的利益;尽管在均势中获胜与流行的总是支配集团的利益,但支配集团并不能因此便为所欲为。葛兰西认为,享有霸权的支配集团必须时刻警惕从属集团结成反霸权联盟、进行反霸权斗争;反霸权联盟的反霸权斗争能否成功取决于由家庭、教会、学校、大众媒介、大众文化等“私人”组织总合而成的市民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两个阶层之一,市民社会承担霸权的生产、再生产及转化的功能;唯有得势于市民社会的集团方有能问鼎上层建筑的另一“阶层”——“政治社会”或“国家”。上层建筑的两个阶层分工明确:政治社会或国家实行高压、市民社会行使霸权。霸权可以借市民社会的机构渗透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中,使大众媒介与大众文化服务于霸权的生产、再生产与转化,一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服务于支配性意识形态。所以,“市民社会是葛兰西确定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位置的途径,而霸权则是他理解它们如何发挥作用的途径。基于一种葛兰西式视野来看,对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理解与解释必须依赖霸权概念”(18)。
正是在这里,为范式转型带来的“理论谜题”所困的霍尔看到了希望:“尽管我读过很多更精致和复杂的论述,但葛兰西的论述在我看来,似乎最能表达我们想要做的事情。”(19)受葛兰西的启发,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学人采取了重新理论化还原论过程这一“绕道”策略,于其间发现了曾经被还原论遮蔽、现在急需填补的理论空间:“1970年代与1980年代初,文化理论家的工作,尤其是斯图亚特·霍尔的工作,通过关注还原论概念令其费解之物打开了那个空间。好像出现了一个理论空白,一个勉力被填补的空间。”(“Theory”:117)霍尔不但为此设计了“生产模型”、“关系组合”等概念,至关重要的是,他在向葛兰西的转向中发现了拉克劳,促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走向接合理论。
二、形塑接合理论
文化主义流行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时候,接合一词仅仅是“一个避免还原论的符号”;从其未能成为文化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的“关键词”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何为接合、接合如何运作等问题并未得到当时文化理论家的重视。首先把接合作为一个概念理论化的,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虽然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思想家都曾对其有过开掘。比如马克思在论述生产方式时,曾经使用过“结合”、“总和”等概念: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20)
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还原论,尤其是阶级还原论,已然同时在理论与政治上失效,无力解释阶级话语中的实际变化;发展一种能够代替还原论的理论已然成为一种必须:
如今,欧洲工人阶级影响日盛,并且在他们注定要将其斗争越来越构想为对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与政治霸权的争夺之际,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发展出一种消除阶级还原论的最后残迹的意识形态实践的严格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Politics:142)在批判性地吸收尼科斯·普兰查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有效地挪用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的基础上,拉克劳提出了自己的接合系谱学。拉克劳认为,接合概念古已有之,“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在历史上第一次包含了接合理论”,它深植于欧洲哲学传统,但需要重构,一如他对柏拉图洞穴隐喻的解读: “常识话语,即意见(doxa),呈现为一个误导性接合的体系,概念于其间似乎并不是由内在逻辑关系所联系,而是仅仅被习俗与意见已在它们之间确立的内涵的(connotative)或引发共鸣的(evocative)联系绑在一起。”(Politics:7)接合即是“概念之间的联系”。(Politics:7)洞穴隐喻意在“解接合”(disarticulate)(误导性的)联系,“再接合”(re-articulate)它们真实的(必然的)联系,即是说,摆脱意见走向知识的过程即是切断原有的接合重建真正接合的过程;从“解接合”到“再接合”的双重运动关系着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范式。作为一种“重构”,他把这一范式修订如下:
第一,并不是每一个概念都与其他概念有必然性联系,仅仅从一种关系出发构建一个体系的总体性是不可能的……第二,在不同的概念结构间不可能建立必然的关系,而只能构造出接合的可能性条件。第三,因此,任何对具体的接近都以更复杂的概念接合为前提条件,而不仅仅是对简单的概念全体逻辑特性的揭示。(Politics:10)
所以,对任何具体情势或现象的分析都必须探究复杂的、多重的、理论上抽象的非必然性联系;一如拉克劳对支配阶级的霸权行使过程的分析所证明的,获得支配地位的阶级总能将非阶级矛盾的话语接合进自己的话语,因而总能吸纳从属阶级的话语内容。即是说,虽然没有任何话语有着一种本质性的阶级内涵,但不同的话语总是在内涵上联系着不同的阶级利益与特征。就197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而言,其内涵可以由革命性的反抗、对剥削阶级的仇恨组成,但也可能接合进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享受与革命热情的消退(Politics:161)。
不难发现,拉克劳的接合概念体现的是一种非还原论或本质论的阶级观,对实践与意识形态元素之非必然对应关系的主张,对作为冲突性意识形态结构的常识的批评,以及对霸权乃一种话语接合过程的坚持(“Theory”:120)。正因如此,虽然拉克劳对接合概念的使用多少有些实验性,“意识形态要素的阶级决定,作为诸要素的复合的具体的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的阶级因素的收编或接合而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变形——这一探讨方法有何值得批评之处呢?”(Politics:97)拉克劳依然成为了霍尔形塑接合理论时的首选资源:
一如我对它的使用,接合理论是由恩斯特·拉克劳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其间他的观点是,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内涵并无必然的归属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不同实践之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要素之间、构成一次社会运动的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等等——偶然的、非必然的连接。他用接合概念来与夹杂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中的必然论和还原论逻辑决裂。(21)
“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内涵并无必然的归属性”所暗示的,是意识形态要素并非一定具有阶级属性,其中的一些要素是非阶级的或中性的;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并非是由主体在生产关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所给定的,而是取决于意识形态各要素的连接方式——接合。换言之,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非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为意识形态要素的接合所建构的;接合在打造由多种要素组成的意识形态同一性的同时,赋予意识形态“自治”。这无疑是拉克劳对马克思主义还原论的一种颠覆,而霍尔正是从这里受到了启发,一如他在讨论意识形态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时所言:
它[意识形态]不可能是一种历史或政治力量被简单地还原为一个一致的阶级……事实上,唯有通过作为一致化的意识形态内的集体主题的形构,它才成为一种一致的力量。直到它开始拥有某种解释一种共享的集体情势的心智形式(form of intelligibility),它才变为一个阶级或一种一致的社会力量。即使到这时,决定其地位与同一性的东西也绝非我们可以还原为我们过去常常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所意指的术语。(“Postmodernism”:144)
然而,霍尔对拉克劳的有些观点也不乏拒绝,一如他在谈到拉克劳与尚塔尔·墨菲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时所言:
我依然偏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当时他[拉克劳]正在艰难地摆脱还原论,开始以话语模式重新概念化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在新作中,元素之间为什么可以或者不可以潜在地接合的理由并不存在。很显然,还原论批判已然导致社会乃一个完全开放的话语场域这一概念。(“Postmodernism”:146)
霍尔“依然偏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是因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集中在那些乍一看来是被赋予特权的许多危机方面凝聚点的话语范畴上,以及在多样折射的各个层面上解释可能的历史意义。所有话语折中主义和摇摆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22)。霍尔认为,由于拉克劳坚持“在这一讨论的环境之中,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连接[接合],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连接实践的结果。来自连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23),他从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滑向了单纯的话语境地。霍尔指出,按照“实践皆话语”的逻辑,难免会出现“将所有实践概念化为仅仅是话语而已,将所有历史行动者概念化为话语建构的主体性,大谈位置性却绝口不提社会实际位置,仅仅看到具体个体被询唤到不同主体位置性的方式”(“Postmodernism”:146)。在这里,霍尔看到了他和拉克劳与墨菲的分歧:他们认为“世界、社会实践是语言,而我想说社会像语言一样运作。虽然语言之喻是重新思考很多基本问题的最佳方式,但存在着一种从承认其效用与力量到认为它实际如此的滑动”,直言不讳地对他们提出了批评:
从逻辑上讲,一旦你已然开启门扉,穿过它去看看世界的另一面是什么模样便是合情合理的。但在我看来,这经常变为它自己版本的还原论。我想说,彻底的话语立场是一种向上的还原论,而不是像经济主义那样是向下的还原论。情况似乎是,在反对一种幼稚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X像Y一样运作的比喻被化约为了X=Y。(“Postmodernism”:146)
当然,就对“实践皆话语”的批评而言,拉克劳与墨菲并非霍尔仅有的批评对象;阿尔都塞同样遭遇了他一针见血的批评。讨论意义、表征与实践的关系时,霍尔虽然承认一切实践及其意义密切联系着其表征与话语,但拒绝把一切实践还原或化约为话语:
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一切实践都带有意识形态的痕迹,或者被意识形态铭写,一切实践便仅仅是意识形态。那些以制造意识形态表征为主要目标的实践是有特殊性的。它们有别于那些……制造其他商品的实践。从事媒体工作的那些人在生产、再生产与改变意识形态表征领域本身。就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言,他们有别于生产、再生产物质商品世界的那些人,然而,物质商品同样被意识形态铭写。(24)在他对还原论、“实践皆话语”等观点的批评中,对实践特殊性的强调中,霍尔开始了其接合理论形塑之旅。在发表于1980年的《支配结构中的种族、接合与社会》一文中,霍尔第一次对作为一个概念的接合做出了阐释:
这种联合或接合所形成的同一性始终、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万物一如通过相似性那样通过差异性,彼此相关。这就要求连接不同特征的机制显现出来——因为没有“必然的对应”或者表达上的类似可以被视为“给定的”。这也意味着因为联合是一种结构(一个接合的联合),而并非是一种随意的组合[association,又译串联],它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被结构的关系,即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因此,借用阿尔都塞的模棱两可的术语来讲,联合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支配结构”。(25)霍尔在这里对接合概念的阐释仅仅揭示了接合理论的部分内涵。(26)经过数年的持续努力,在1985年发表的《意指、表征、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论争》一文中,他对接合概念的系统理论化与阐释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我用“接合”一词来表示一种连接或者联系,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未必是给定的……而是要求出现在特定存在情势之中。它必须通过特定过程积极地维系,也并非是“永恒的”,而是必须被不断更新;它在某些环境下可能消失或被瓦解,导致旧的联系被消解、新的联系——再接合——被打造。同样重要的是,不同实践之间的接合并非意味着它们会变得相同或一种实践消解到另一种之中。每一种实践都保持其独特的限定因素与存在条件。然而,接合一旦形成,两种实践就会共同作用,并非是作为一种“即刻的认同”……而是作为“同一性中的区隔”。(27)
霍尔对接合概念的最详尽阐释,见诸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人在1985年对他的访谈:
在英国,这一术语具有微妙的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e”表示发出声音、说出来、发音清晰等。它带有用语言表达、表达等意味。但我们也说“铰接式”卡车(货车):一种前体(驾驶室)和后体(拖车)可以但不一定必须彼此连接的卡车。两个部分相互连接,但要借助一个可以断开的特殊环扣。因此,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让两个不同的元素统一起来。环扣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必需的。你不得不追问,在什么情势下可以打造或产生出一种关联?因此,一种话语的所谓“同一性”实际上是不同的、独特的元素接合,这些元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接合,因为它们丝毫没有必然的“归属性”。至关重要的“同一性”是被接合的话语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一种环扣,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但不一定必须借助被接合的话语与社会力量连接起来。因此,接合理论既是理解意识形态元素何以在一定情势下逐渐连接在某一话语之内的方式,也是追问它们何以在某一关键时刻(conjuncture)与特定政治主体接合或不接合的方式。(28)(“Postmodernism”:141-142)这里霍尔不但阐释了接合概念的丰富内涵,比如接合、解接合、再接合、环扣、意识形态、要素、一定条件、遇合、差异性、同一性,等等,而且以接合-解接合-再接合的动态发展视角,揭示了接合的非必然性、非持久性、暂时性、动态性、未完成性等特征,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促成了接合概念的理论地位,即著名的“接合理论”。当然,霍尔之所以能成功地形塑接合理论,原因并非仅仅在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传统、对还原论与本质论的持续批评,同时与霍尔对“关键时刻”的把握息息相关,霍尔勉力建构或形塑接合理论可谓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关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当政以降已然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英国社会文化现实对理论阐释的渴求。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的福利制度改革显然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为何却赢得了后者的认同与支持?霍尔发现,撒切尔夫人成功的秘诀在于一种独特形式的领导权——“威权平民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它强调“对一种基于法律、秩序和家庭价值的新的平民道德的需求”,并且“通过将受欢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界定为包含所有人,它也变成了一种道德力量”。(29)撒切尔夫人时常与工人阶级一起抱怨官僚政府,不断重复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为富人服务,而且也为普通人服务,即普通人同样能够成为股东与投资人,“在公司里不要跟我谈什么‘他们’和‘我们’”,“大家在公司里都是‘我们’。你活下去就是公司活下去,你成功就是公司成功——大家齐心。未来在于合作而不是对抗”(30),等等。在与左派的斗争中,撒切尔夫人图谋借助赢得大众的认同而重建“新右”政权。通过这样的一种威权平民主义实践,“其中平民被威权化即综合和超越,而威权被平民化即被普遍化、道德化、常识化和自然化”,威权平民主义便成为了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性意识形态的实践,抑或威廉斯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不再关乎经济的枯荣。(31)
面对撒切尔主义的胜利、右翼势力的复兴、广泛的保守政策的回归、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衰退、声誉正隆的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颠覆,尤其是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的质疑,霍尔主张左派从撒切尔主义的胜利中吸取教训,放弃过时的还原论、本质论。为此,霍尔“解接合”了撒切尔夫人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再接合”了作为一个概念的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修订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第一,意识形态不是专属于或者天然地联系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第二,在复合型社会里,意识形态计划……可以发挥出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可以改变社会……第三,这种改变并不必然地受制于或者紧密地相关于经济力量而发生。(32)
同时,我们还须知道,就接合理论的理论资源而言,俄罗斯理论家瓦连京·沃洛希诺夫亦可谓至关重要,尤其是他针对同源论(homology theory)提出的“阶级并不与符号社区相一致”、“符号是阶级斗争的战场”等观念。(33)一方面,“一些意指结构比另一些意指结构更为容易地与某一团体的利益相连接”,另一方面,“当两个或者多个相异的元素被用于暗示、象征或召唤彼此的时候”,它们可以建立起“非常牢固的接合关系”(34)。一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音乐所证明的,青少年的反叛、工人阶级的质朴、族裔之根等元素被接合在一起,彼此召唤。与此相联系的是沃洛希诺夫的复调、多声部等概念。文化文本可能发出的不同“腔调”注定了文化文本的意义始终为社会产品;同一文化文本可以被归附上迥然不同的意义决定了文化文本的意义始终为斗争和谈判之场域。所以,文化领域充满了为特定意识形态和特定社会利益而接合、解接合和再接合文化文本的斗争;文化文本并非意义之源,而是可以为了特定的、也许是对抗性的社会利益在特定语境下生产出各种各样意义的场域。霍尔说:
大众文化是这场支持和反对支配者文化的斗争进行于其间的场域之一……它是认同与抵制的竞技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霸权出现的地方以及霸权被获得的地方。它并非社会主义,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被简单地“表达”的场域。但它是社会主义可以被建构的场域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大众文化”重要的原因。(35)
三、评说接合理论
如前所述,“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让两个不同的元素统一起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接合理论旨在建立差异中的同一性,“接合即在差异性中产生同一性,在碎片中产生统一,在实践中产生结构。接合将这个实践与那个效果联系起来,将这个文本与那个意义联系起来,将这个经验与那些政治联系起来。而这些关联本身则被接合为更大的结构”(36)。其次,接合理论的关键词包括差异、动态同一性、接合、解接合、再接合、非必然性、一定条件等,它们暗示了接合、接合理论的理论化的未完成状态,从而决定了接合理论必然以反本质主义、摒弃还原论和决定论为特征。所以,詹妮弗·达里尔·斯莱克认为,霍尔对接合理论有如下贡献:
第一,他拒绝阶级、生产方式、结构还原论的诱惑,拒绝文化主义把文化还原为“经验”的倾向。第二,他提升将话语与其他社会力量相接合的重要性,“悬崖勒马”没有把一切都变为话语。第三,霍尔致力于接合的策略性特征,凸显了文化研究的介入主义承诺。第四,霍尔对接合的讨论是最为持久、最易操作的。(“Theory”:121)
接合的各个要素内部及其之间呈现出接合与被接合的双重动态的辩证关系,即接合-解接合-再接合的过程体现出一种动态、流动的关系,所以,任何要素的接合都是暂时的、松散的,并没有固定或者必然的本质。一如葛兰西的霸权与反霸权,一切都在运动中,在历史中接合、发展、变异,“接合因此并非仅仅是一种结果(并非仅仅是一种连结),而是一个创造连结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一如霸权并非支配,而是创造与维持认同或者协调利益的过程”(“Theory”:114)。但是,接合的非必然性并非意味着接合是任意的,而是需要“一定条件”,一方面是接合者的意图,另一方面是历史条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非必然的接合,也都需要一定条件,否则接合就会像霍尔坚决反对的那样,趋向任意的、无目的的流动:
我并不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彼此接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有时被称作“完全话语的”立场前突然停止。所有话语都有“存在的条件”,虽然这些条件不可能固定或者确保特定的结果,但它们可能限定或限制接合过程本身。历史形构由先前的但强有力地被打造的接合构成,不可能被某一抽象的历史法则确保处于恰当的位置,但它们是非常抵制变化的,并且确实确立了趋向与边界之线,这些趋向与边界之线给予政治与意识形态场域一种形构的“开放结构”,而非简单地滑入一种无休止的、无尽头的多元性之中。(37)
霍尔对“存在的条件”的强调意在反对拉克劳与墨菲的激进或极端话语理论,即把一切条件还原为话语条件,否定社会主体的实践能动性。这一点得到了格罗斯伯格的呼应与支持:“接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为活跃的关于决定概念的认识……接合总是复杂的:不仅是原因有效果,而且效果自身也影响原因,二者本身由大量别的关系所决定。接合从来不是单纯和单一的,它们不能抽离于相互连接的语境。”(38)
可以说,接合理论既是霍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贡献,更是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贡献,代表了新葛兰西派文化研究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努力。更加具体地讲,接合理论模糊了进步的大众文化与反动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区隔,代表了霍尔等文化研究学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一种理性思考与选择,暗示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别样”态度:既不是阿多诺与利维斯主义者的“批判”,也不是本雅明和萨特的“利用”,而是一种与“俯视”无关的“理解”。(39)或者一如托尼·本尼特所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以“理解”大众文化代替了原来的“声讨”。(40)如是,接合理论可以让人看到文化形式与实践——葛兰西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权力的社会-经济结构并不决定它们,而是与它们相联系。
接合理论认识到了文化领域的复杂性。它不但坚持文化与意识形态元素的相对自主性……而且强调那些被实实在在地建构的组合模式(combinatory pattern)确乎调和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的、客观存在的模式,以及调和开展于斗争之中:为了以特定方式接合文化领域的元素,以便它们的组织基于由某一阶级在现有生产方法中的地位和利益所决定的原则和价值体系,各阶级相互斗争。(41)
现实文化与阶级地位等经济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总是成问题的、不完整的,是意识形态运作与斗争的对象,“文化关系与文化变化并非是预先决定的;相反,它们是协商、强加、抵制、变化等的产物……因此,特定的文化形式与实践不能被机械地或者根据范式附加于特定阶级;对某一种形式与实践的阐释、评价与用途同样不能”(42)。借用霍尔的话来讲:“这样的完全不相关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即它们在历史不变性的关系中,根据范式附加于特定的‘所有’阶级”(43)。虽然文化诸元素并非直接地、永远地或者唯一地关联着阶级地位等特定经济决定因素,但它们是受这些因素最终左右的,通过直接联系着阶级地位的接合原则(articulating principle),要么将现有元素组合为新模式,要么赋予它们以新内涵。
接合理论的另一理论意义在于它可以在促成人们重新思考大众文化政治的同时,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大众文化概念本身。一方面,大众文化是霸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关键场域,其间充满了支配集团和从属集团利益的斗争和谈判,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既不是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文化产业强加的文化,而是葛兰西意义上的一种折中平衡,一个底层力量和上层力量的矛盾混合体,既是商业性的,也是本真的,既有抵制,也有融合,既是结构,也是能动性。此外,接合理论无疑还可以推动文化消费的研究。首先,从理论上讲,了解文化文本被赋予意义的方式需要考虑文化消费。这将把我们带离对文本意义的兴趣,转而去关注文本使之成为可能的意义的范围。文化研究从未真正感兴趣于单个文化文本的意义,作为基本的、被铭写的、被保证的某个东西。文化研究始终更加关注诸多文本的意义,它们的社会意义,它们在实践中被挪用和被使用的方式:作为归附而非作为铭写的意义。基于接合理论的文化研究可能有时会导致对普通人的活生生的文化的赞美,但这种赞美始终是在这样的全面认知中完成的,即一种语境下的“抵制”,可以很容易地在另一种语境下变为“融合”。其次,从政治上讲,基于接合理论的文化研究承认文化产业确乎是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主要场所,但它拒绝认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是“文化盲从者”,“人世间新式鸦片”的受害者,而是主张消费者“在使用中生产”。(44)当然,“在使用中生产”并非意味着文化消费始终具有授权性、抵制性;否认文化消费的被动性并非是否认文化消费的偶尔被动,否认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为文化盲从者并非是否认文化产业的操控意图。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所要否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是一幅堕落的商业和意识形态操控景观,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产品旨在牟取利润和取得社会控制。生产与消费问的关系并不能靠精英主义的一瞥或高人一筹的嘲笑一劳永逸地决定;解读文化产品的意义、愉悦、意识形态效果并不能依赖于生产的时刻,而是“在使用中生产”。
四、实践接合理论
接合理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所以,接合理论自诞生以降,不断被大西洋两岸的文化研究学人挪用,行之有效地服务于他们对身份认同、差异政治、族裔流散等问题的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实践之一是迪克·赫布迪格完成的,他考察了二战以降的英国青少年亚文化中的“反叛的情形及意义、作为一种拒斥形式的风格的含义、犯罪升华为艺术”(45)。一如《亚文化:风格的意义》所告诉我们的,赫布迪格考察了“太保少年”(teddy boy)(46)、摩登族、摇滚族、光头族、庞克族等从属群体的表现形式及仪式,以期证明“由具有双重意义的寻常之物构成的”风格不但是亚文化的集中体现(Subculture:3),而且浸淫了抵制与融合、接合与解接合。赫布迪格发现,青少年所把玩的寻常之物,比如保险针、尖头皮鞋、唱片、滑板车等,往往因他们的把玩行为与人们对把玩行为的反应间的矛盾、支配集团与从属集团在亚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张力,获得了象征维度,构成了一种耻辱或自我强加的流放形式。一方面,作为一种“差异的在场”,青少年的把玩保险针、尖头皮鞋、唱片、滑板车等行为往往给人一种“邪恶在场”之感,招来含混不清的怀疑、心神不安的笑声、“苍白沉默的愤怒”;另一方面,对那些把保险针、尖头皮鞋、唱片、滑板车等建构为圣像、视它们为誓约与咒语的人而言,这些寻常之物成为了被禁止身份的符号、价值的源泉。这样的一个始于“不合常理”或异常的行为,止于风格的建构、挑衅或蔑视的姿态、微笑或嘲笑的过程,表征的是一种具有丰富社会意涵的拒斥,“这样的拒斥是值得进行的,这些姿态有意义,微笑及嘲笑有某种颠覆价值,即使它们在最终的分析中……只不过是种种规则的更加阴暗的一面,正如囚室墙上的涂鸦”(Subculture:3)。
赫布迪格在考察中发现,青少年亚文化团体在战后英国的出现以一种蔚然壮观的形式反映了一致性价值观的崩溃,虽然“亚文化所代表的挑战霸权并非是由它们直截了当地表示。恰恰相反,它间接地体现于风格之中”(Subculture:17);青少年亚文化对支配性文化的反对或挑战置身于、显现于各种现象的意味无穷的表层之中,即符号的层面。受“接合旨在建立差异中的同一性”这一观点的启发,赫布迪格认识到意识形态中的不同话语、不同定义及意义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表意实践内的斗争,即对符号拥有的争夺(Subculture:17)。被赫布迪格作为例子使用的保险针,其意义始终摇摆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保险针等寻常之物“可以被变戏法般挪用,即被‘从属群体’盗用去传递种种‘秘密’含义,这些含义通过符码表示对极可能使他们继续处于从属地位的秩序的一种反抗”(Subculture:18)。从这个意义上讲,“亚文化的风格蕴含着意义。它的种种变换‘违背自然’,扰乱‘正常化’的过程。因此,它们是趋近于言语的姿态和运动;这些姿态和运动冒犯‘沉默的多数’、挑战团结与连贯原则、否认一致神话”(Subculture:17)。
另外,赫布迪格还发现,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风格与西印度群岛黑人文化关系密切,比如庞克在深层次上关乎与“雷鬼”(reggae)相联系的英国黑人亚文化。炎热的1976年夏天,庞克正式在英国音乐报刊登台亮相,最大限度地容纳了所有主要的战后英国亚文化;摇滚、雷鬼无不在作为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文化代表的庞克中留下了自己清晰可辨的“身影”。所以,赫布迪格建议,从理解雷鬼及作为庞克前身的英国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内部构成与意义入手,去理解庞克与英国黑人亚文化之间的对话:“首先,必须追溯雷鬼在西印度群岛的根源;其次,必须把战后的英国青年亚文化重新阐释为对1950年代以降的黑人移民在英国的出现的连续级差反应。”(Subculture:29)这一指导思想使赫布迪格将自己的关注视野从学校、警察、媒体与母文化等传统领域,转移到了种族及种族关系等长期被人忽视的维度上,因此得出了语惊四座的结论,即在二战后的英国,尽管白人青年与黑人青年一样热衷于林林总总的亚文化,但黑人文化明显在青年亚文化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耶鲁大学教授迈克尔·丹宁(Michael Denning)对19世纪美国廉价小说的分析也堪称接合理论的完美实践。(47)廉价小说是对商业性的、批量生产的19世纪美国情感小说的通称,旨在制造一种令人兴奋、无伤大雅的“屏障记忆”,内容主要关乎西部冒险、白手起家、学童趣事等。廉价小说有三种版式:故事报(story paper)、廉价小说(dime novel)、廉价图书馆(cheap library);它们无论在历史还是内容上都有重叠,但确乎代表了19世纪廉价小说出版的三个不同时刻。通常情况下,很多故事首先在故事报上连载,然后作为廉价小说以单行本发行,最后在廉价图书馆上重印。尽管版式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读者、出版商及故事本身却具有连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为这类故事贴上“廉价小说”的标签可谓是合情合理的,以示它与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高雅文学的区别。
据丹宁的考察,廉价小说的出现与流行与以蒸汽式滚筒印刷机为代表的出版技术的发展、由铁路和运河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以及工匠、技师等新阅读大众的出现有直接关系,而廉价小说的消失则主要关乎图书托拉斯的建立、廉价杂志的出现以及国际版权协议的签订。在廉价小说由盛及衰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故事逐渐从早期西部故事、拓荒者故事、印第安战斗故事等演变或“堕落”为亡命徒故事、都市生活故事、侦探故事等。另外,廉价小说通常被视为男童和男人的图书,而定位于女性的罗曼司则鲜有读者。所以,尽管评价廉价小说在19世纪美国工人阶级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丹宁接受了廉价小说乃文化产业产品这一观点,但他并未因此认为其间仅有融合或抵制在发挥作用。相反,丹宁坚持认为,这类小说既非欺骗、操控的形式,也非反对和抵制支配性文化的表达,而是一个充满竞争与冲突的场域,其间的符号呈现出矛盾的伪装,发出不同甚至对立的腔调;一如支配性文化的符号可以用人民的腔调进行接合,工人阶级文化的符号也可以用多种手段进行放逐。
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美国学者罗伯特·S.汉斯佐(Robert S.Hanczor)对备受指责的电视节目《纽约重案组》(NYPD Blue)的考察。(48)我们知道,每当公共利益问题经媒体曝光时,分析出现在认同赢得过程中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便成为一种必须。对此,传统做法是以议题设定、政治经济与修辞等为视角,但在考察1993年《纽约重案组》争议的过程中,汉斯佐选择了霍尔的接合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期发现参与争议的个人与团体之间的授权性关联以及流行于其间的意识形态社会力量。基于对出现于该次争论之中的非必须的、冲突性的关系的观察,汉斯佐发现,貌似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往往密切联系着更大的社会-政治运动,证实了接合理论不失为探究经过大众发酵的公共争议问题的性质的一种新视角。
以上的接合理论实践表明,接合是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或多种不同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方式,体现为在差异化的要素中建构同一性的一种关联实践。接合是一种建构,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绝对的,而是语境化的产物;它是各种“相异原素”在“关键时刻”相连接的某种方式,这种方式形成某种新的机制或连接后获得某种新的意义。在一些评论家看来,接合理论似乎有时候适合于事件,有时候适合于关于事件的话语,其原则到底是经验的还是逻辑的让人难以捉摸。(49)但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实践策略,接合理论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解读具有独特而深刻的阐释功能,尤其是在关于文化与政治、话语与传播、族裔散居与身份认同的解构与建构的解读实践中,体现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连贯性。
格罗斯伯格曾经指出,“文化研究已从批评性阐释的实践移离至接合的实践”,批评计划“必须超越压迫模式……走向接合模式”。(50)于是,如何进行“接合的实践”、如何“走向接合模式”等问题俨然凸显在了我们面前,而回答或解决问题的前提,便是我们必须对何为接合理论有着清晰的认识。如前所述,接合旨在通过不同要素的结合,形成新的历史集团干预现实、变革现实;接合本身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所以,接合不仅是一种理论或者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作为实践的理论与方法。唯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将其贯穿于我们的研究实践,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仅仅充当西方文化理论的脚注者:
接合概念或许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力的概念之一……接合已获得理论的地位,一如在“接合理论”中。从理论上讲,接合可以被理解为在描述一种社会形态的特征时为避免落入还原论和本质论的双重陷阱所采用的一种方式……但接合也可被视为文化分析中所使用的一种方法。一方面,接合为理解文化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提供一种方法论构架;另一方面,它为进行文化研究提供策略,一种将分析对象“语境化”的方法。(“Theory”:112)
对当下文化研究的现实而言,接合理论倡导充分发挥接合的策略作用,在文化与经济脱钩之处重建关联;面对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时,以接合思维致力于探讨共享差异平等与差异自由的生存方式;在分析与批评资本主义文化时,坚持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为此,我们的接合理论研究必须以实践为核心,以社会介入为目标。一如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布鲁诺·拉图尔在《潘多拉的希望:科学研究的现实论集》中所言:“就像翻译一样,这个术语占据由客体—主体或者外在世界—内心之间的二分所留下的位置。接合不是人类语言的属性,而是宇宙的本体论属性。问题不再是陈述是否关涉事态,而是命题是否得到充分表达。”(51)为了“超越压迫模式”,走向“接合模式”,我们的接合研究应当聚焦于谁在接合,谁/什么在被接合,什么在被遮蔽或被抹除。换言之,面对文学/文化文本时,我们必须基于政治-历史(外部批评)与审美-形式(内部批评)的接合抑或耦合,分析有特定利益的个人或团体何以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设法与其他个人、团体、经济组织等相连接,分析这样的个人或团体何以设法促成各不相同的对象像一个团体一样行动,或者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团体。
注释:
①《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载《思想文综》第4辑,饶芃子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4-231页;原文见Lawrence Grossberg,ed.,"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986,10(2),pp.45-60,以及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2003,pp.131-150。
②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③Nick Couldry,Inside Culture-Re-imagin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2000,p.2.
④Graeme 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167.
⑤Jennifer Daryl Slack,"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2003,p.116.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文名称首词,不另作注。
⑥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in John Storey,ed.,What Is Cultural Studies:A Reader,London:Arnold,1996,p.44.
⑦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⑧See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London:Hutchinson,1976.
⑨See Stuart Hall,et al,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le and Law and Order,London:Hutchinson,1978; 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New Times: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a the 1990s,London:Verso,1989.
⑩See James Donald and Ali Rattansi,eds.,Race,Culture and Difference,London:Sage,1992.
(11)Antony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9.
(12)Antony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p.57-58.
(13)Paul Ransome,Antonio Gramsci:An Introduction,New York:Harvester/Wheatsheaf,1992,p.150.
(14)Antony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161.
(15)Dani Cavallaro,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Thematic Variation,London and New Brunswick,NJ:The Athlone Press,2001,p.78.
(16)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LB,1977,pp.161-16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17)Robert Gray,The Labour Aristocracy in Victorian Edinburgh,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6.
(18)Dominic Strinati,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1996,p.169.
(19)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in 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 and Paula A.Treichler,eds.,Cultural Studie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2,p.281.
(20)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3页。
(21)Lawrence Grossberg,ed.,"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2003,p.142.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作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22)恩斯特·拉克劳、查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金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23)恩斯特·拉克劳、查塔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第114页。
(24)Stuart Hall,"Signification,Representation,Ideology: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i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vol.2(No.2,1985),pp.103-104.
(25)Stuart Hall,"Race,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in Sociological Theories:Race and Colonialism,Paris:UNESCO,1980,p.325.
(26)邹威华《斯图亚特·霍尔的“接合理论”研究》,载《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1期,第44页。
(27)Stuart Hall,"Signification,Representation,Ideology: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pp.113-114.
(28)基于霍尔在此间对“articulate”的阐释,笔者建议将其译为“耦合”,以突出接合理论的未完成性、偶然性、暂时性。另外,关于“conjuncture”的翻译,参见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刘康《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75-81页。
(29)Angela McRobbie,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p.24.
(30)Stuart Hall,The Hard Road to Renewal: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8,p.49.
(31)详见金惠敏《霍尔的文章,麦克罗比的眼睛——霍尔文化研究三大主题的评议》,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第233页。
(32)Angela McRobbie,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p.26.
(33)Valentin Volosinov,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New York:Seminar Press,1973,p.23.
(34)Valentin Volosinov,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pp.9-10.
(35)Stuart Hall,"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in Raphael Samuel,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1,p.239.
(36)Lawrence Grossberg,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2.p.54.
(37)Stuart Hall,The Hard Road to Renewal: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p.10.
(38)Lawrence Grossberg,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p.56.
(39)赵勇认为,大致地讲,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采取了四种姿态:批判、利用、理解与欣赏(详见赵勇《批判·利用·理解·欣赏——知识分子面对大众文化的四种姿态》,载《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期,第68-74页)。
(40)See Graeme 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47.
(41)Richard Middleton,Studying Popular Music,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1990] 2000,p.9.
(42)Richard Middleton,Studying Popular Music,p.8.
(43)Stuart Hall,"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in Raphael Samuel,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1,p.238.
(44)详见约翰·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徐德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7-110页。
(45)Dick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9] 1997,p.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46)“teddy boy”(太保少年)一词出现于1960年代的英国,表示“行为放荡不羁的青少年”之意。这些放荡不羁的青少年他们喜欢穿爱德华七世年代的服装,而Teddy是爱德华七世的爱称。
(47)See Michael Denning,Mechanic Accents:Dime Novels and Working Class Culture in America,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7.
(48)See Robert S.Hanczor,"Articulation Theory and Public Controversy:Taking Sides over NYPD Blue",i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vol.14(No.1,1997),pp.1-30.
(49)See Chris Rojek,Ways of Escape:Modern Transformations in Leisure and Travel,London:Macmillan,1993.
(50)Qtd.in Kevin DeLuca,"Articulation Theory:A Discursive Grounding for Rhetorical Practice",i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vol.32(No.4,1999),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p.334.
(51)Bruno Latour,Pandora's Hope: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303.
标签:葛兰西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还原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