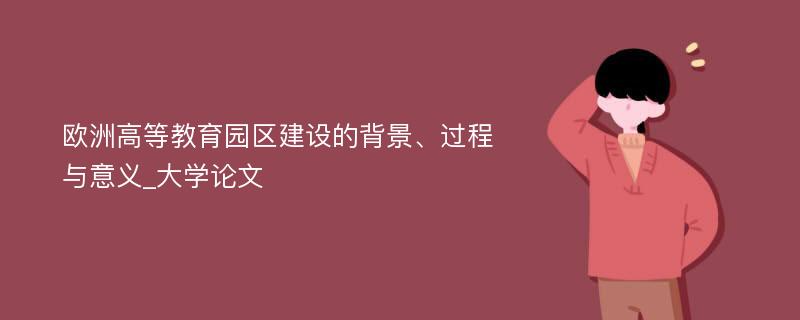
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背景、进程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高等教育论文,进程论文,意义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3)07-0009-13
继1998年5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四国教育部长联合发布《梭尔邦宣言》,呼吁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为建设一个开放的欧洲高等教育区而努力之后,欧盟国家的教育部长们频繁聚首,于1999年6月在意大利波隆那签署了《波隆那宣言》,2001年5月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联合发表了《布拉格公报》。通过这些宣言和公报的逐步阐释,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轮廓便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本文拟对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背景、过程及其意义进行分析,以期对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本质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背景
在世纪之交欧盟国家的教育部长们提出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设想,并通过一系列的《宣言》与《公报》对在新世纪初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部署;这一号召不仅得到了欧盟国家的认可,还得到了其它一些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应该说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提出是有着其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的。
首先,从整个欧洲社会大环境来说,在全球化浪潮下,欧洲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里的联系日益紧密,迫切需要在文化教育上,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加强合作,一方面培养适应欧洲经济联盟要求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期望通过高等教育间的合作与交流来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增强欧洲联盟内部的凝聚力,提高整个欧洲的国际竞争力。
从20世纪50年代初欧共体的第一个联盟雏形——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到1992年在欧洲联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欧洲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及其它社会领域里的合作与联系日益紧密,一个以经济为基础向各领域不断渗透的全方位联合的欧洲联盟正在形成。这一联盟从广度上来讲已超出了目前欧盟15国的地域范围,逐步向中欧、东欧发展;从其深度上来说,欧洲多国家、多民族组成的特性也要求欧盟间的联系必须从经济间的合作深入到文化层面上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并藉此进一步促进经济间的联系与合作。因此在90年代,“欧洲人身份(European Identity)”[1]或“公民的欧洲(Europe of the Citizen)”的概念成为欧洲联盟建设的主要议题之一。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明确指出了在建设“欧洲公民”或“欧洲人身份”的过程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欧洲国家联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欧洲区域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并且具有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能提供更多更好工作岗位的经济联盟,而这一经济联盟又必须以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不同种族、文化间相互融合的社会文化联盟为基石。这两者都必须依托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因此,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在此过程中具有两重任务:一是通过高水平的教育、训练和研究,帮助增强欧洲的国际竞争力。二是,由于欧洲国家间的频繁交流所带来的必然挑战,如人员的流动性、语言技能、不同种族间民族间所需要的宽容,以及未知世界对欧洲公民的挑战等都将逐步增加,大学必须在帮助欧洲公民面对这些挑战、通过公开讨论社会冲突的根源、消除偏见和仇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等方面起积极的、主要的作用。
其次,就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及吸引力而言,欧洲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已失去了中世纪的风采,其高等教育系统的吸引力为后起之秀的美国、加拿大甚至澳大利亚等国所超越。欧洲是近代大学的发源地,是世界学术的中心,曾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学生和学者,尤其是在中世纪和近代。二战以后虽然学术中心开始向美国转移,但是,欧洲的高等教育仍然以其高质量而著称于世。到了90年代,由于语言和高等教育系统本身等因素的影响,其高等教育的吸引力,正受到来自其他非欧洲英语国家的威胁。例如,1996/1997学年度留学英国的国际学生为198,839名,占其总学生人数的10.5%;德国为165,977名,占其总学生人数的7.8%;留学意大利的占24,858名,占其总学生人数的1.3%;法国为138,191名(1995/1996);而1995/1996学年度,留学美国的国际学生则达到453,785名,占其总学生数的3.2%;1997年留学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为102,284名,占学生总人数的9.8%,同年留学新西兰的人数为6,415名,占学生总人数的3.8%。[2]从国际学生人数上看,美国位居第一,其后依次为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但是,若从国际学生的来源地来看,欧洲国家国际学生的生源主要以欧盟国家为主。若从以上国家对亚洲学生的吸引力来进行比较,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的情况不容乐观。例如,1995/1996年,在留学美国的453,785名留学生中,亚洲学生占64.1%;在新西兰的6,415名留学生中,亚洲学生占70.8%;而在留学法国的学生中亚洲学生仅占13.4%,在留学德国的165,977名学生中,亚洲学生占36.2%,在留学意大利的学生中亚洲学生占12.1%,留学英国的学生中亚洲学生占34.2%。[3]可见,90年代中期,对亚洲学生吸引力最大的不是欧洲,而是以美国为首的非欧洲英语国家。再如,从世界上主要英语国家留学生总人数来看,1996/1997年,共有602,000名留学生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四国学习,其中在英国学习的占17%,在美国的占68%,在澳大利亚的占10%,在加拿大学习的占5%。[4]显而易见,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相比,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在20世纪90年代有减少的趋势。
再次,从欧洲高等教育系统本身来看,自6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对高等教育系统所进行的改革均以失败告终。欧洲国家的教育首脑们希望藉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为契机,对高等教育进行新一轮的改革。
20世纪后半叶欧洲高等教育主要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规模扩大及所带来的多样化和大众化;二是政府资金投入减少所造成的经费紧张。在60、7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经济迅速增长、科技革命必然导致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同时,社会需求理论则认为应满足大部分人增加教育机会的愿望,两者迭加,成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因。当时,人们认识到高等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高等教育逐步被看作是公益事业。当时的社会政策目标包括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提供多样性的项目,促进机构间的多样化,促进高等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等。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预算也有所提高,大部分国家都取消了学费,政府资助系统十分慷慨。这一时期欧洲国家处于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大规模需求的局面,而没有从根本上对其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改革。[5]到了80、90年代,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形成了自己的动力系统,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一直维持在相当的水平上,有些国家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已不再是社会公共责任或个人权利,而被认为是可带来个人收益的个人责任。经济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人们转变了高等教育观念,即高等教育从公益事业转变为具有个人收益回报的个人投资,结果导致一些国家开始引进收取学费政策。90年代,由于公共预算的紧缩改变了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欧洲国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变得疏远了,国家通过有关法律和协议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宏观管理,政府逐步解除对高等教育细节的控制。传统上政府导向机制的基础受到了削弱或动摇。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高等教育机构自治,从外部争取更多的财源,促进高校的非国营化。总之,自6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对高等教育系统所进行的改革均以减少耗损为目的,欧洲国家松散的学习系统由于学习时间过长和淘汰率高仍然倍受指责。
最后,欧盟及欧洲国家间已有的教育合作已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设作了铺垫。
欧洲国家间的教育合作始于“学位资格的互认”。在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条约中,与欧洲学术认可有关的法律政策有:1953年《欧洲相互承认大学学位的条例》及《条例议定书》(1964);1956年《欧洲大学学习期限的换算条例》;1959年《欧洲大学资格的学术互认条例》;1979年《欧洲地区国家有关高等教育的学位、学位文凭、学习研究的互认条例》;1990年《欧洲大学学习时间的换算条例》等。在1997年这些条例均被纳入《里斯本条约——欧洲高等教育资格互认的协定》的框架之中。[6]在条例、条约的具体实施方面,1975年第一份规章公布,它针对在医学和健康领域的学位证书相互承认,随后于1978年颁布牙科和兽医的相互承认文件,1985年颁布药学和建筑学互认规章。这些规章都与“协调规章”相随,“协调规章”对国家学习计划进行协调,对不同学习程度国家的教育政策进行限制。
同时,欧洲国家高校间人员流动项目也早已开始。最有影响的项目是欧共体大学生流动行动计划,简称为“伊拉斯姆斯计划”(ERASMUS)。该项目于1987年正式启动,其目的是支持在大学间建立网络、为欧洲国家学生流动项目提供资助。到2002年9月参加此项目的学生超过了100万人,参与国从1987年的欧盟11国扩展到现在的30个欧洲国家。[7]从1995年到2000年,伊拉斯姆斯计划被纳入一个范围更广的计划“苏格拉底”(Socrates)框架之下。其它教育合作与交流项目还有很多,如ECTS,TEMPUS等等。这些教育合作项目无疑为欧洲高等教育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进程
1、《梭尔邦宣言》:提出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设想
1998年5月25日,在庆祝巴黎—梭尔邦大学建校800周年的纪念会上,法、英、德、意四国教育部长联合发布了题为“建设和谐的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之联合宣言”,即《梭尔邦宣言》。内容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呼吁建设一个开放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域以加强学生间的流动和学校间的密切合作;二是提出通过国家间学位的相互承认来增强欧洲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宣言指出应建设一个具有国际比较性和相互承认的体系,包括两个主要循环系统(本科和研究生)。宣言明确指出在本科阶段,要有多样化的项目交流,每个项目必须引向一个相应的资格水平;在研究生阶段,重点必须放在研究和独立工作上;提出适当缩短攻读硕士学位的时间并延长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以便有可能在国家之间进行流动。这四位部长承诺他们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可相互参照的共同框架,以提高外部承认和促进学生流动和职业能力为目标”并“努力创设一个欧洲高等教育区域”。[8]
应该说,《梭尔邦宣言》是在仓促中起草的,也因此而留下了足够的解释空间。但其意义在于它最先明确提出了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概念。虽然欧洲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早已开展并不断频繁,但是,以往的交流与合作均缺乏一个长远的、通盘的规划和明确的目标,而欧洲高等教育区概念的提出则为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发展设立了一个明确而宏伟的目标。同时,由于欧洲高等教育区这一设想符合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需要,也符合欧洲高等教育机构决心重振欧洲高等教育雄风的愿望,因而深得广大欧洲高等教育机构的赞同与响应。
2、《波隆那宣言》:界定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概念
《梭尔邦宣言》公布不到一年,即1999年6月欧洲29个国家负责高等教育的教育部长聚集意大利波隆那,签署了《波隆那宣言》(全称为《欧洲高等教育区域:欧洲教育部长在波隆那集会的联合宣言》)。该宣言提出了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的七个目标:第一,采用可比较的和易读的学位系统,通过学位辅助系统完成;第二,采用两个主要的循环系统,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统,本科阶段至少三年时间,毕业后既可进入相应的欧洲劳动力市场,也可继续进一步攻读学位;研究生阶段应通向硕士和博士学位;第三,设立学分系统,如ECTS,促进学生流动;第四,克服其他障碍使学生与教师有效地流动;第五,促进欧洲区域内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方面的合作;第六,进一步发展必要的欧洲高等教育特性;第七,在尊重文化、语言和国家教育系统多样性以及大学自治的基础上,宣言提出通过政府间合作和在欧洲高等教育方面有资格的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以巩固欧洲高等教育区域。
与《梭尔邦宣言》相比,《波隆那宣言》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的欧洲区域的具体构想,它对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内涵本质进行了阐释与明确,并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和后续工作计划,将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由概念框架落实到具体的工作日程之中。另外《波隆那宣言》的意义还在于它扩大了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范围,参加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意向国由4国发展为29国。
3、《布拉格公报》:政策的后续保障
在波隆那会议举行一年之后由扩大小组的国家代表提交了第一份《波隆那宣言》实施进展报告,包括学位结构的调整等。为配合高等教育区建设,欧洲委员会也资助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学位辅助系统、学分累计和互换系统、欧洲教育质量保障网络、跨国教育、欧洲教育结构的和谐等。
为了对所开展的工作进行评估,并对今后几年高等教育区建设与发展制定方向和优先方案,欧洲分管高等教育的教育部长会议于2001年5月18、19日再次于布拉格举行。会议讨论了布拉格教育部长会议决议——《形成欧洲高等教育区域》(Shaping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欧洲高等教育机构萨拉曼卡会议决议”、“哥德堡会议决议”等文件,签署了《布拉格公报》。会上高等教育机构代表和政府代表讨论三个主题:高等教育两个主要循环系统中的课程问题,加强流动性问题以及质量保障和确认问题。部长们希望将布拉格会议作为欧洲区域扩大的标志。与《梭尔邦宣言》和《波隆那宣言》相比,《布拉格公报》明确提出了欧洲委员会和它的“建设性支持”。《公报》还对《波隆那宣言》中所设立的目标逐项进行了评估,指出了仍需努力之处。在质量保证认证方面在区域层面上安排了新的活动。会议决定将于2003年聚会柏林,对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过程进行监控并对此间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讨论。
三、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意义
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设为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发展设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并因此而成为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
第一,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设将引起欧洲国家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变化。围绕着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这一总目标,参与国都在对本国的有关高等教育政策或法律进行检讨、调整和修订。一个十分明显且重要的变化是一些欧洲国家的学位制度将会有很大改变,例如,荷兰政府重新修订了自1993年以来一直适用管理和调整其高等教育的法律《高等教育和研究法案》,已于2002年9月颁布了新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法案》。在学位结构方面,新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法案》规定从2002/2003学年起,启用新的学位制度等。
第二,必将促进欧洲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增强欧洲高等教育机构的吸引力。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将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契机,欧洲各国高等教育将向着更加具有开放性、国际化以及相互间学位、学制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同时,人员流动与知识交流也必将对欧洲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带来机遇与挑战。
第三,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将对欧洲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始于经济上的合作,并以经济为基础向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不断扩展、深入。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欧洲国家间、民族间的矛盾、冲突在人们的心里曾投下过深深的阴影,有些阴影至今抹之不去,影响着整个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将通过文化、教育方面的密切交流,增强“欧洲人身份(European Identity)”或“公民的欧洲(Europe of the Citizen)”的概念,对于促进不同种族、不同文化间的社会凝聚力,消除国家间、民族间的隔阂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将通过高水平的教育、训练和研究,帮助增强欧洲的国际竞争力。
当然,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设也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在欧洲高等教育趋同过程中,如何保持欧洲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特性?如何确保欧洲高等教育质量?等等。这些问题均有待于在建设过程中不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