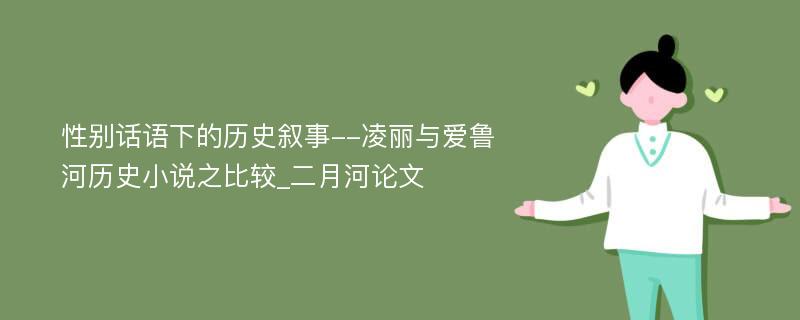
性别话语下的历史叙述——凌力、二月河历史小说创作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小说论文,话语论文,性别论文,历史论文,二月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5-0077-04
中国一向以“信史”为传统,即使是历史文学创作,也是以尊重历史为指归。凌力和二月河也均称尊重历史,前者认为历史小说“必须是文学,有历史感。强调文学,是要求它有艺术感染力,有形象,有审美价值;强调历史感,便是历史小说之所以区别于现实题材小说的基本属性”[1](P697)。后者称,“没有人改写历史,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的真实面目”[2]。二人同是表现清代生活,但由于是两个不同的创作主体,尤其是性别的差异,必然造成他们对同一历史题材的不同叙述,本文拟就凌力的《暮鼓晨钟——少年康熙》和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夺宫》为例,来分析二人的历史小说创作。
一、“中华民族”观念及“仁爱”思想
历史小说创作需要熟悉历史,要有小说家的写作技巧,更需要有在广阔的社会阅历和深刻的人生感悟中形成的对史实的判断,以及对历史的总体把握与深层理解,也就是史识。两位作家均有见解独到而精湛的历史观,重点表现在“中华民族”观与“仁爱”思想上。
两位作家均写清代帝王系列小说,一曰“百年辉煌”,一曰“落霞”系列,都肯定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一方面,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夷狄”对“华夏”的统治,是游牧文化对农业文化的改造,民族、文明之间的差异、对比、冲突比较突出,而另一方面,清代又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的王朝。因此,表现这样一个王朝,更能体现作家的政治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在两个作家的创作中,均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观念,抛弃了大汉族主义思想,写出了满族也是中华民族之一员,而清王朝在封建统治中也比较有成就,出现了几代明君,如康乾盛世等。
二月河认为,“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兴盛的时期,又是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个特点是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不具备的。”[3],而凌力也指出,“康熙皇帝玄烨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伟大的君主,他的一生用‘辉煌’来形容,也许并不过分”[4](P889)。
两位作家均描写康熙的才能与远见卓识。但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清朝初年,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如“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而这两位作家对此现象均有表现,但态度不同,凌力强化这种对立,而二月河却淡而处之。凌力提到了“哭庙案”、“奏销案”、“通海案”,重点描述了“明史案”。满族统治者认为,江南“哭庙案”、“奏销案”、“通海案”等十宗大案下来,杀一小批,整肃一大批,狠狠煞住了南蛮子的气焰,一平他们胸中长期积蓄的委屈和怨愤。如今又来了个明史案,那些桀骜不驯的蛮子文人,还敢不夹住尾巴、老老实实地听喝吗?几个不足驯服的汉臣何足道!……他们对汉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作家凸现了满汉冲突,这无疑体现满汉差别,以及中心与边缘、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这是历史或现实中的性别冲突造成了作家对差异的敏感。
满汉之争体现了作家性别之争的观念。“等级制建立在男女两性自然关系的理解基础之上。……从男女两性关系的立场出发,就十分容易理解主权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要使战争合法化,常见方式就是鼓吹男子汉气质(保护弱小的妇女儿童),宣扬对上级、父辈、国王的忠贞,将男子汉气质与民族强大混为一谈。”[5]因为作家的女性身份,使其对女性与男性的差别、弱势地位的女性的被压迫处境深有体会,从而对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特别敏感而至深恶痛绝。从而大量描写了满清贵族对汉人的压迫与屠杀,反映了被征服者的悲哀与悲愤。
凌力在对满文化的批判时,也对汉文明有所批判。她写到了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如“天算案”便是争夺文化霸权的表现。而在叙述此事件中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如对杨光先的阴险、奸诈、尖刻的描写无疑是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儒家文化是一种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孔子曾声称“唯小人与女子难养矣”。这种区别也显示了作家的矛盾,一方面作家对满人对汉人的残酷统治(诛杀)深恶痛绝,鞭挞淋漓——而满人之所以这样做,是要谶越正统文化,是边缘对中心的占领,是处于边缘状态的满清占有者对以“正统”、“华夏”、“中心”自居的汉人的一种驱逐或报复,使其处于边缘状态,并得以臣服。而女性的处境何尝不是一种边缘状态,而作家描写正是要把埋没于历史尘埃中的杰出女性挖掘出来,使其重放异彩。另一方面,也隐藏着作家的良苦用心,满汉冲突是强权对弱者、对理性的野蛮摧残和残酷绞杀;而这正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真正作用的抹杀。“天算案”更是理性与野蛮的冲突,是膨胀的政治野心对客观存在的抹杀。性别的差异造成对一切差异的敏感与关注。
任何一个王朝都是统治人的,而儒家思想则是政治统治的精华。尽管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实行儒家的“仁政”。“仁者,爱人”。二月河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孔孟以来的中国文化传统是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的,是任何力量打不倒的”[3]而凌力也认为康熙、雍正、乾隆“他们祖孙三代皇帝,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座右铭,医治战争浩劫遗留的创伤,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提倡和颂扬的仁政,给中国平民百姓带来了一人半世纪的和平与繁荣”。[4](P890-891)
但是凌力在提倡仁政的前提下加入了基督教思想,即“博爱、平等、自由”。仁政是讲帝王之术,是如何驭民的,是帝王与平民、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以等级为基础;而基督教思想是讲人与人的关系的,是平等的。她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对战争对平民的迫害深恶痛绝。所以在她的作品里一再出现传教士汤若望,他是顺治的师父,是孝庄皇太后的义父,很多华人成为他的信徒。且不说作家抛弃了传统的对传教士的误解、恢复了传教士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作家把传教士当作一个为了正义、信仰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并且用自己的仁爱思想来影响统治者。在二月河的作品里提到了汤若望,但没有重点描写他,对他的信仰也没有提及,而重点通过伍次友的“帝师”作用,重塑了儒家学说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前者体现了女作家的慈善心肠,后者体现了男作家的出将入相的“入世”心态。
二、宫廷情趣与朝廷斗争
历史是由一系列事件、场景组成的,而政治斗争为其主要成分。而对男女作家来说,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同,女性比较关注家庭内部,而男性则相对关注外面的社会,因此,凌力着重关注宫廷生活与宫廷情趣,而二月河则着重关注朝廷斗争。
凌力着重写后宫生活:写祖孙、兄弟、夫妻等的日常生活及伦理关系,着重反映一种柔情。通过家庭、婚姻、爱情、友谊来渲染历史人物的成长环境。太皇太后的生日、公主的结婚典礼以及皇帝的完婚,写得隆重而雍容华贵,既显示了皇家的高贵与典雅,同时也显示了帝王之家也与普通人一样,也有天伦之乐与缠绵亲情。也写了少年们的嬉戏,体现了少年人的率真与童年情趣;同时表现了少年男女的友谊与朦胧的爱情。从而强化了家庭对主人公的作用,使背景变为前景。关注家庭解构了后宫为祸水的传统观念,宫闱也由神秘、绮靡、淫荡变得世俗化、生活化。
而二月河大量描写朝廷及外面的世界。如伍次友煮酒论功名、倭赫父子受戮、三臣联折被杀、苏克哈萨喋血、康亲王杰书倒戈、白云观、池心楼弑君与救驾……件件事紧密锣鼓、风云而至;件件事扣人心弦、波谲云诡。而这多为权力与野心使然。
二人的描写重点可以通过对主人公康熙的表现即见端的。凌力笔下是一个平民式的少年康熙,而二月河笔下是一个天子式的少年康熙。
康熙8岁登基,是一个娃娃皇帝。在凌力的笔下,也写到他的为政之道,如天算案中假扮太监登台观察、学习天文、历法,与鳌拜斗智斗勇,但更能震动人心的则是他的家庭生活。他虽然年幼,却具佛心,笃于亲情友于弟妹,是仁爱之君。同时也暗示了女作家的良苦用心——希望男人即使贵为天子,也要多一点对女性的关怀,对男子汉、白马王子满怀顾盼。
但他毕竟是一个皇帝,他的行为必然要与政治发生关系,始终与权势相伴。因为自己的少年贪玩,而使倭赫四侍卫被杀;皇位也时时拘束着自己的行为:不能与两小无猜的冰月结合。在选择贵人时也要与政治相权衡。因为是孩子,尚未定型,有时率性而发,显得怪僻与不合身份。其实他的一些行为是天性使然。他的行为总是充满孩子的天性,即使与权臣周旋也是以孩子的天性(好奇、懵懂、贪玩等)来迷惑他们。
作家也写到了康熙与权臣的周旋以及官场行为,这显示了官场对人性的扭曲与压抑,他只能委曲求全、虚与委蛇,这与后宫的率真天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作家通过孩子的眼睛描写了朝廷斗争,如倭赫四侍卫被杀、天算案、明史案、圈地案、苏中堂被杀以及鳌拜被擒等。通过孩子的眼睛,或稀释了紧张,或置于幕后,使重点突出。
作家不仅写到了宫廷的天伦之乐,还写到了平民的生活。如同春与梦姑的久经磨难、不改初衷的恋情,感动了要杀他们的人,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他们二人的爱情又引出了王爷对梦姑的痴迷、福晋对同春的迷恋,但同春、梦姑二人均不被富贵、权势所动。而玛尔赛对鳌拜的感情则显示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纯真爱情,即使鳌拜被囚也愿同囚,以示爱情之真诚与纯洁。
大量写爱情,这一方面体现了女性作家比较关注感情生活的特点,另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对历史的看法,历史不仅有事件,而且有人物;不仅有大事,而且有小事;同时也表现了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历史的进程中,爱情、家庭起着润滑乃至生死攸关的作用,而爱情的一极——女性则是至关重要的。太宗皇帝(皇太极)因敏惠元妃的仙去而忧郁而死,造成了顺治的少年登基;而董鄂妃乌云珠的去世则使顺治出家,造成了康熙的8岁就做了小孩皇帝。
凌力抹去了历史的神秘面纱,加入了自己的合理想象,实现了历史与本文的对话。不再拘泥于历史事实,因为历史本文和文学本文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6](P4)通过对历史的阐释与虚构,显示了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而二月河作品里的对皇宫的生活描写不多,对皇室的爱情、友谊、亲情几乎没有着墨,而苏嘛喇姑与伍次友的恋情、胡宫山与李云娘(翠姑)、翠姑与明珠之间的关系的表现重点不是表现爱情,而是体现了传统的士大夫情绪:郎才女貌、英雄救美等思维模式。
康熙也几乎不见童年的情趣、孩子的天性,一出场便是少年老成,学习帝王之术。二月河重点在朝廷的斗争中塑造了康熙这个少年皇帝的复杂个性。作者倾力于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宫廷纷争、权谋机变中,艺术地展现帝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非凡才干和历史功绩。8岁即位的康熙,从师伍次友,努力学习;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与权高势大的辅政大臣鳌拜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与较量;鳌拜逼迫康熙杀掉建议禁止圈地的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大臣之后,又逼迫他杀掉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甚至气势汹汹要弑主篡位,形势有一触即发的危险。康熙估计当时的形势,还难以除掉鳌拜,因而隐忍不发,作暂时妥协。待到一切部署就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除掉这个势力盘根错节的集团——15岁“庙谟独运”智擒鳌拜,表现了康熙的胆识和智谋。
在表现康熙体恤民情,网络人才,明朗豁达的同时,又表现他性格中多疑猜忌,阴险狡诈,手段高明的一面。他重用九门提督吴六一,把军权交给他的同时,又给魏东亭一道密诏,“以防变中之变”。而对魏东亭也不放心,派人装作魏东亭的看门人,潜伏在魏东亭身边五年,魏竟没能察觉,而且把魏东亭的母亲(康熙的乳母)留在身边,以控制魏东亭。苏麻喇姑想到:这个情理通达、爽朗可亲的少年天子,猜疑之心竟如此之重,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作家表现了一个少年老成、深懂权术的小皇帝,而少了儿童的天性和少年情趣。
后宫的人性化和朝廷的兽性相对比,女人的柔情与男人的无义成对比——家庭与政治做对比,显示了男女作家的关注重点与思维方式的差异。
三、帝王之师:女性与士大夫
两位作家均写少年康熙如何获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过程。少年人必定有一个受教育的成长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外人起着重要的作用。两位作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截然不同。
凌力表现的帝王之师为庄太后。庄太后是科尔沁草原的少女,并没有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她既有普通女性的悲欢离合,又有太后的雄才大略;既有慈母的菩萨心肠,又有母后的权谋与威严。自顺治17年秋天起,不幸就固执地缠住了她。她最喜爱的干女儿兼儿媳妇董鄂贵妃病故,揭开了灾难的序幕。五个月后,儿子顺治帝去世,犹如摘去了她的心肝。皇家的灾星不退,刚入康熙二年,皇帝的生母,进徽号为慈和皇太后的康妃又去世了!太皇太后已经欲哭无泪,心被悲哀折磨得近于麻木。沉郁和悲凉始终像两条绳索捆绑着太皇太后的心,不得解脱。又为了皇室的稳定与利益,不顾正义与臣子的生命。借辅臣之刀杀出天子威仪皇上尊严,值得!只是委屈了四名侍卫及受株连的费扬古等人,何况四辅臣执政以来,深得八旗之心,专横跋扈形迹未显,驳回他们,很容易使自己处于违逆众心的不利地位。她认为,当年太祖太宗皇帝开创江山,杀人如草。因怨望和大不敬而杀却的大臣不也不在少数,算不上失德……显示了为政者的残酷。
老鹤飞不动了,小鹤还不会飞。辅臣权重,危极社稷,但她又不能轻易动作。只能委曲求全,暗中操作,藏而不露,旁敲侧击,使她的心思权臣摸不透。长期以来,太皇太后不预外事。但江山社稷是她爱新觉罗家的,她岂能不管?在天算案中,她对官吏的任命与调度及对公主出嫁的安排,则显示出她从来就不曾真正“不预政事”。朝廷内外的人和事,她全都不若指掌、成局在胸。这根本不是个坐享晚年之福的老祖母,她仍然和30年前、20年前一样,内秉风雷之气,外持静怡之容,一位杰出的女人。她的一番布置,举重若轻,不着痕迹,有多么精巧!为政精到,常人是万万不能及的。给未成年的玄烨大婚,也是一举两得:既表示了归政的要求,又笼络住辅臣,不至于伤他们的心。但是她毕竟势单力薄,有时显得力不从心,与康熙成了相依为命的祖孙俩,只有精心培养康熙的帝王之才:官场斗争、权术之争。她对康熙的成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家强化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作用,而庄太后无疑是凌力的贡献。她忍辱负重,周旋于满汉、朝廷与贵族之间,她为两代统治之母,顺治、康熙她起重要的作用,显示了她的非凡才能。康熙的智擒鳌拜,就是她精心调教的结果。
而苏嘛喇姑、孔四贞也是非常有亮色的女性。苏嘛喇姑扶持康熙、帮助治理后宫起着很大的作用。四贞以少女而开军府、袭封爵,掌定南王事,遥制广西,维系定南王旧部,与平西、靖南、平南三藩成犄角之势。作家把尘封于历史中的女性发掘出来,闪现出璀璨的光芒。
二月河的作品中有亮色的女性也不少,但这些女性重点表现在儿女情长上,并未显示出有多少政治才能。苏嘛喇姑比较独特,政治、官场、宫廷均有作用,但她是作为伍次友的陪衬出现的,作家重点表现男人的丰功伟绩。伍次友在不知康熙(龙儿)身份之前,给他讲解经、史,从历史经验中给康熙极大启发。伍次友等是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身上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出将入相,为帝师是他们人生的最高理想,体现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但他们又都是汉族知识分子,在满洲贵族当权的时代,他们处在被怀疑、被疑忌的地位,时常有“伴君如伴虎”的危机感,因此,当他们感到危机迫近时;或在生活上、政治上失意时,就采取道释文化中消极“出世”的态度。伍次友先浪迹江湖,后归入空门。他虽然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都不可能实现人生理想,能保善终就很幸运了。他们的命运给人以迷惘、悲凉之感。在他们身上概括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庄太后以女性给康熙以影响,伍次友以传统士大夫给康熙以影响。作家性别不同,就表现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英雄也不同。
人们现在一般认为,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人类本质,人类的主体性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界定和确定我们的地位的文化符码(culture codes)来产生。也不存在“客观性”,我们是在语言中体验“世界”,我们所有对世界的表现,对于本文和过去(the past)的阅读,决定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地位,决定于寓于其中的价值和政治。[7](P90)历史是被人叙述的,在叙述的过程中,也叙述着叙述者自身。凌力、二月河通过对同一历史的不同叙述,显示了自己的文化身分,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
标签:二月河论文; 康熙论文; 凌力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伍次友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作家论文; 鳌拜论文; 魏东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