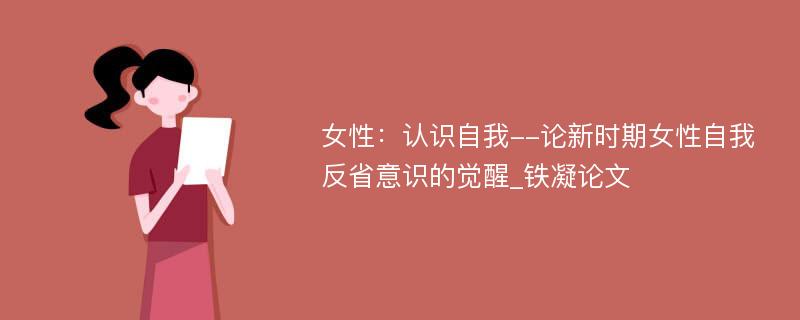
女性:认识你自己——论新时期女性自审意识的觉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你自己论文,新时期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未经批判的生命是无价值的。”
——苏格拉底
新时期之初,女性文学最早从追寻理想爱情之命题崛起,很快,转向对女性作为社会人自我价值的寻求。作为披荆斩棘的先驱者,张洁们在“女人不是月亮”这一抗争性的命题内完成了昔日的辉煌;继之,年轻的刘西鸿则以崭新的特区女性风貌,亮出了“女人也是太阳”的自豪,她们以新时代女性的潇洒风采,完成了几代妇女为之奋斗的理性超越,使张洁们求索的沉重找到了炼狱的出口。
然而,时代发展的不平衡,使这炼狱的出口仿佛只属于得天独厚的新一代特区女性。
那么,“拯救”绝大多数女性的“方舟”在哪里?
拯救女性的方舟必得女性自己营造。
外部探索的极限亦有局限,展示了另一条探索之路的必要,即女性自审意识的觉醒。
新时期女性文学自审意识的觉醒,经历了由并非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经历了由表层揭示——即女性人生的自省与女性命运的反思,到深层挖掘——即女性灵魂的审视与生命本体的透视这样一个过程。质言之,即由“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过程。
至此,新时期女性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将目光和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女性自身,开始落落大方地追寻刻在古罗马阿波罗神庙里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一)“批判的武器”
“批判的武器”是指女性文学将女性弱点的揭示作为批判十年浩劫封建余毒和极“左”路线的武器来使用。
我们知道,女性生活在变动不居川流不息的大千世界里,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并确立自我的人格与价值,既不能靠天赐,也不能指望别人给予;不仅必须靠自我奋斗来实现,还须靠自我批判来激励。张洁曾经这样阐述过她对女性人格的看法:“妇女自身存在的缺陷很多。必须将自己弄好了,才能要求别人尊重你,自己如不争气——愿意当花瓶和贱货,那则是无可救药。”①这一段话措词不无激烈之处,但的确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女性自省的必要和重要。女性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那就不能不彻底改变旧有的心理结构,就不能不通过对新东西的认同、吸收和改造,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批判,自我整和,以提高女性自我的质量,乃至重铸女性自我的灵魂。女性只有经过自我批判与自我奋斗的双重努力,方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自己营造的“方舟”。由此,女性文学中关于女性人物对外部环境愤激抗争的命题,最终——或迟或早都会转向对女性自身的审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文学中自省意识的觉醒,是女性文学寻找自我价值命题的延展。
张洁等女作家对于女性解放道路的求索,所具有的先驱意义和启蒙精神,一直贯穿在女性文学的追寻之中,其功不可没。然而,女性文学发展求索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后继者总是以她们独特的思考超越先行者。因此,当王安忆和铁凝自觉开启女性自审之路后,回望先前女性文学寻找自我的路程,披荆斩棘中的自省,左冲右突中的反思,均必较朦胧。那时的自省是不自觉的,或者说,不完全是自觉的。因此,女性文学在追寻女性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女性人生的自省与女性命运的反思基本是社会的、情感的、心理的层面问题。严格地说,这是女性文学自省意识的觉醒,还不能说具有了自审的意义。自省与自审,二者有着表里、深浅、轻重之区别。
如果从新时期女性文学命题潮头的演进划分,无论是《心祭》《七巧板》还是《人到中年》,都可以包括在揭露极左路线酿成的“伤痕”“反思”文学中,或者是广义的“问题小说”中。如前所述,当整个民族处在一个拔乱反正的特定历史时期,女性文学对女性自身弱点的反省,是新时期女性文学所表现的历史郁积的情感和思考的一个分支。它无疑是属于全民的。女作家们此时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注。或者说,她们对女性自身弱点的揭示,尚未进入完全自觉的状态。无论是《心祭》中女儿们的追悔,还是《七巧板》中金乃文的奴性,抑或是《人到中年》中所塑造的仰仗特权的“藤”等等,女作家的主旨均不在于或不完全在于对女性自身弱点的揭示,不在于以女性自身弱点的反省为目的,而在于通过对女性可悲命运的揭示,鞭挞那个肆虐的年代;而在于从把女人当作人的角度去鞭笞把女人不当人的十年浩劫;或在于从女人应把自己当作人的角度去挖掘造成女人不把女人当作人的社会、政治、历史的动因。因此,这些作品对女性弱点的揭示,是将其作为历史的解剖刀,揭开历史的疮疤,剜割历史的毒瘤;是将其作为文学批判的一种武器,暴露非人性反人道的东西对女性心灵情感的压抑、禁锢和毒害。女性文学对批判武器的选择,即批判历史、批判社会是完全自觉的;而自省意识的开启,则或许是一种不自觉的选择。
然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批判的武器”,还停留在较浅的层面,停留在社会学、心理学意义的层面,还未深入到女性灵魂、生命的深层。完成“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过度的,是谌容的《错!错!错!》。
其价值在于,它避开了通常所描述的人们也十分熟悉的造成婚姻的那些政治、社会、经济及伦理道理因素。它所审视的不是婚姻的外部之风而是夫妻内部浊浪迭起的缘由,尤其是女性心理误区性格悲剧的缘由。婚姻破裂的悲剧,在全球,在中国,无时无刻不在一家又一家重演着,姑且不论政治、经济、伦理的因素,单就人性和心理误区导致的婚姻悲剧,西方与东方还少吗?反之,如果《错!》中将失败的爱情故事灌注政治内容而不是心理性格的悲剧内涵,如果它一旦向社会悲剧靠拢,那就不是《错!》现在的视角和思想题旨了。因此,《错!》这类女性小说,标志着女性文学自省视角的一种推移。它并没有否定社会、伦理、文化的传统角度,但它的焦点逐渐移向女性内部。
是的,女性常常能够战胜和超越外部世界的艰难险阻,却难以战胜和超越女性自身的弱点,所以,女性清醒地认识自己,勇敢地审视自己,是女性由传统型转为现代人的心理与精神建设的前提。
(二)“武器的批判”
“武器的批判”,是指女性对自身弱点的批判。是以批判自身弱点为目的或主要目的。是女性自审意识的觉醒。其之于女性文学,应以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与铁凝的《玫瑰门》始。
王安忆和铁凝冲破单一的社会批判、心理误区的揭示及一般意义悲剧性格的批判,开启了一个女性自审的时代;一个女性毫不留情地、严峻的自我批判的时代;一个对女性灵魂进行拷问、对女性生命本体进行探索认识的时代。
王安忆和铁凝揭开了千百年来那些别有用心的道学家和作茧自缚的世俗观念强加在女性身上神秘的面纱,不仅铁面无私地冷峻拷问女性的灵魂,审视女性生命本体,而且同时高扬起女性生命的蓬勃。她们关注影响女性命运的内在根由,关注女性多姿多彩的生命之流,她们不回避女性的七情六欲。她们懂得,只有通过七情六欲的深刻揭示,才能撼动女性最隐秘的灵魂暗弦。“三恋”和《玫瑰门》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同时也包括男性形象),不再仅仅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而且作为“文化的人”,“有生命有生有死的人”而存在;②不再作为表象化的寄托和偶然的“这一个”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某种抽象意味的整体性的符号隐喻而存在。
“三恋”在女性文学中,第一次揭示了生命现象的内在冲突。女人的痛苦,女人的悲剧,在王安忆的笔下给予了特别的关怀。无论《小城之恋》中的“她”,还是《荒山之恋》中大提琴手的妻子以及金谷巷的女孩儿,她们都不能把握自己的性别,因而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无论忘记自己是一位女性,还是太知道自己是一个女人,都是女性的悲哀——女性性别态度的悲哀。即使是《岗上的世纪》那样被评论界认为是颠覆男性的女性主义的作品,王安忆依然揭示出了女主人公无力战胜心中恶魔的人性的陷井。“也就是使她以性为手段转成目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性的迷狂。由此作品展现出在现代社会对性的原始冲动采取认可态度的同时,现代女性心灵有可能陷入的不清醒状态”。③王安忆在这些作品中表现了对这种极不清醒的女性态度的否定,从而从生命本体的角度完成了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刻透视。
如果仅仅剔出了“三恋”的自审意识,对其的解读还失之简陋,失之肤浅。“三恋”之深意在于,女性自审意识是与女性生命意识一起苏醒的。王安忆以鲜明的女性生命意识,写出了女性生命的形态,女性生命的欲望,女性生命的流程。正是对亘古不变、与生俱来、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奥秘的探索,淘洗出了潜在深层的污垢和泥沙。使之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为女性从生命的角度认识自己,提供了一个文本。
同样,铁凝在女性自审的探寻中亦进步得惊人。从《麦秸垛》到《玫瑰门》,从道德的“性意识”到人性的“女性意识”,铁凝对各类不同女性的生命展示与女性复杂的灵魂审视,都是新时期作家中鲜有的。铁凝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嘈杂的女性世界的“玫瑰门”。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们曾用玫瑰色的语言赞美女性。但铁凝笔下的女性灵魂,女性生存状态,却完全失却了玫瑰般的美丽。“玫瑰门里不玫瑰,这是铁凝的一个大胆的发现和勇敢的揭发。这不仅是艺术中女性形象描写的拓展和衍进,而且对于人类社会学和女性人类学的研究,也是不无参考意义的。”④铁凝在审出“玫瑰门”里女性丑恶灵魂的同时,还写出了女性因受压抑、摧残的痛苦、绝望、挣扎、疯狂,以及在挣扎反抗中燃烧着的女性活生生的欲望和蓬勃非凡的生命力。这不仅不能视为一种“女性的自赏意识”⑤而恰恰是女作家对真实的女性灵魂不加掩饰的披露。司漪文无“德”却有着不能泯灭的“欲”,她不能像正面女性那样,让人们在完美的操守面前肃然起敬;也不像反派女子,生来就烂透坏透。司漪文曾有过“池水般的清澈”,有过“睡莲般的纯洁”,甚至到老都有一张容光焕发的脸,一片对初恋情人真挚的情。因此,笔者认为,司漪文这一女性的出现,为新时期女性文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一个灵魂自审的领域;一个女性自我认识的领域;一个相对自然而非简单分明的道德评判角度描写的女性世界。在这里,女人第一次走出社会的道德界定;第一次表现了不以男性中心世界的意志为意志的女性的主观意志;也第一次袒露了道德无法判定善恶的女性的情欲与血肉之驱。因而,你可以认定司漪文丑恶,但她决不愚昧;你可以认定司漪文疯狂,但她活得决不窝囊。透过表面膨胀到疯狂的邪恶、私欲,司漪文在骨子里显示了比以往女性要多得多的对生命的觉悟。铁凝就是这样打开了一扇女性世界的玫瑰门。从纯然女性的视角,从性心理的深层,去揭示人性的复杂及其脉动,审视丑恶的灵魂,也审出丑恶后面燃烧的生命力。为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玫瑰门》是少有的女性认识自己的一面透视镜,一面女性灵魂的透视镜。
残雪的作品在审视女性灵魂的丑恶方面,或许走得最远。在她的《苍老的浮云》、《山上小屋》等一系列作品中,传统小说中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温柔俏丽形象不见了,也读不到男女之间贯常有的温情脉脉的关系。在残雪表现的梦幻世界里,只有男性对女性的各种迫害和女性的心理仇恨。然而残雪在颠覆男性自我形象的同时,也“将女性圣洁的偶象击得片甲不留。”“而且在抨击人性的丑恶,人类阴暗性的一面时,残雪对女性并不比对男性宽容,几乎是女性对自我的一次摧毁。”⑥残雪以自己的方式,在一个特殊的领域,提供了人认识自己的方式;在一个特殊的领域,提供了女性认识自己的文本。
(三)追根与溯源
从人性的角度,生命本体的角度看,女性的弱点乃至丑恶是怎样形成的?它或许有遗传基因和人体的密码,但如果将它与社会历史环境完全割断了联系,视它为孤立的,那么人就变成了纯粹的生物学意义的人了。这当然是荒谬的,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生命是由血肉铸成的。作为自然界最高形式的人的生命,具有基本的自然性。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进化,它除了自然性外,又积淀了深厚的社会性文化性。正如王蒙所说:“什么是人,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是有生命有生有死的人。”⑦值得称道的是,王安忆和铁凝并未陷入“生物学”的沼泽。她们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探索人的本能的。是在广褒的大文化背景上揭示人性奥秘的。
诚然,“三恋”中有意淡化了人的社会性。这里没有浓笔重彩的背景描写,也没有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纠葛,主人公同周围的环境与他人的关系是十分淡漠的。人物的感情,心理,行动,基本是受一种自然欲望和冲动的支配。小说的整体构架是围绕生命的流程营造的。但是,透过人物感情,心理活动,你可以感受到一种大文化的氛围。《小城之恋》中的两个年青人,互相拒绝着,躲避着,拼命想挣出那泥潭,可没有文化理智没有教养的他们,是那样软弱无力。他们无力无“文化”支配自己的生命。王安忆把这样的生命形态放在一个古老落后的小县城的自然环境中,置于“文化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是颇有意味的。距离现代文明还很遥远的古老土地,却人为地要“革”一切“文化”的命,其结果只能是制造无数个愚昧、贫困的灵魂,助长各种原始本能的滋长。反转来,这种愚昧贫困的灵魂,对那场民族劫难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王安忆稍有不同的是,铁凝在《玫瑰门》中并未淡化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司漪文的典型性格,是在长达七十年的典型环境中形成的。铁凝在司漪文形象中,不仅汇聚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上某种历史风涛的剪影,而且几乎是汇聚了整个“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极为真实的市民心态及生态景观。曾被社会一再拒绝,排斥打击的旧世家出身的家庭妇女司漪文,在“文革”对尊荣人物的亵渎和摧毁中,突然发现了自己获得生存价值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在用“文革”精神“严格要求自己”的种种“拟态”的表现和表演之后,她依然遭到拒斥打击,而且是更加冷酷的拒斥和打击。于是绝望中的她露出了报复的丑恶灵魂。那是不能被掩抑的真实的女性灵魂。那是被历史的重负和现实的压力纵横挤压得扭曲变形的女性的灵魂。以司漪文为中心的响勺胡同诸女性之间相互猜疑互相窥视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女性健康的性心理和性生活得不到尊重和发展的畸型病态的性文化阴影中形成滋长的。铁凝揭示了一个异常严肃的关于女性生存方式与女性的本质被异化的悲剧命题。它的深刻性体现在人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文化即人的本质。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渗透使人与文化的关系变得十分牢固和久远;人创造了文化却又被自己创造的文化所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对自我的审视与认识,带有本体论的意义。
(四)继承与超越
严格地说,女性文学自审意识的觉醒,并非始于新时期。早在五四时代,与冰心、庐隐、冯沅君齐名的,被鲁迅誉为表现了“高门巨族精魂”的凌叔华,即是最早开拓女性自省的女作家之一。当“五四”女性文学中的“新女性”们,高举个性解放的旗帜,高喊着“我是我自己的”,冲破封建家庭牢笼,汇入时代洪流中时,凌叔华,则撩开“闭锁在深闺、隐居在高宅”的旧式女性和“解放”了女性的绣楼帷幕的一角,透过她们安逸的生活,深刻地呈现了女性深层意识的陈旧落后,道出她们生命的停滞,人性的枯竭,精神的窒息和个性的泯灭来。
后来,将凌叔华的自省意识继承并加以非凡深化的,是四十年代的张爱玲。她从女性角色的历史深处去审视女性灵魂,一部《传奇》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页。无论是新派、旧派,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无不心履斑斑,创伤累累,生命在黄金与报复,虚荣与庸俗的牢笼里,一点一点地枯死。张爱玲从女性本体出发,揭示那个时代女性无意识的种种表象;展露出女性深层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女性不幸的根源。使女性文学中的自审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新时期女性文学从自省的开启到自审的掘进,与现代女性文学由自省(凌叔华)到自审(张爱玲)的发展轨迹大致相同。大多是对女性本体的观照和价值判断。然而时代的变迁,社会精神风貌的更新,使得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自审有不同的审美风格和心理内容。张爱玲的自审“呈现了女性深层意识中传统的积淀,从而引起女性‘人’的抗争,其目的在于批判和破坏女性沉囿了几千年的非‘人’的精神牢笼。”⑧但是这种自审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破不立。张爱玲在作品中流露出对女性的态度更多的是居高临下的悲悯和痛惜;笼罩在她作品中的是一种茫茫无边的苍凉和彻骨的凄冷;自审的契机并非是完全自觉的。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自审则是完全自觉的。女性作家以成熟,强健的心灵,对女性自身做彼举性的审视;女性作家在对女性自身的“剖析与自责中,认识女性内在的尊严和价值,其意义在于建设一个新的女性尊严和人格。”⑨我们从王安忆和铁凝的作品中感受到的,是女作家对人、对女性的那种深广的爱,对人尤其是对女性文明的渴望。可以说,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自审意识,尤如一条暗河,在汨汨地流淌着,那是一条源自历史,流到现在,通向未来的暗河。
女性文学自审意识的开启,如同女性文学哲学意识的觉醒一样,并非企望它可以为女性指明一条在精神上彻底解放的平坦大道;亦并非是在更高层面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批判以期完善。而是力求通过对女性心灵积垢的挖掘,对女性生命的感悟,以期达到对生命之谜,人之奥秘的认识;以期达到对女性自己的全面认识。其对女性自身的意义即在于,形成对女性世界的透视能力和批判眼光;提高女性主体的精神素质;探寻女性心灵的强健之路。难以想象,背负沉重的精神枷锁,带着一颗扭曲的灵魂,女性能够达到解放自身的目的。新时期女性文学自审命题的开启标志着觉醒的女作家从本质上有了一种足以与男性中心文化相抗衡的内力。
注释:
①《张洁答香港记者问:谈女权问题与“女性文学”》原文载香港报刊,转引自《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9.12。
②王蒙《文学三元》,《文学评论》1987.1
③董之琳《妇女文学:女权观念烛照下的视角选择》,《艺术广角》1992.2
④曾镇南《评长篇小说〈玫瑰门〉》,《人民日报》1989.3.28
⑤于青《走出“玫瑰门”》,《文艺争鸣》1991.1
⑥董之琳《妇女文学:女权观念烛照下的视角选择》,《艺术广角》1992.2
⑦王蒙《文学三元》1987.1
⑧⑨于青《苦难的升华》,《当代文艺思潮》19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