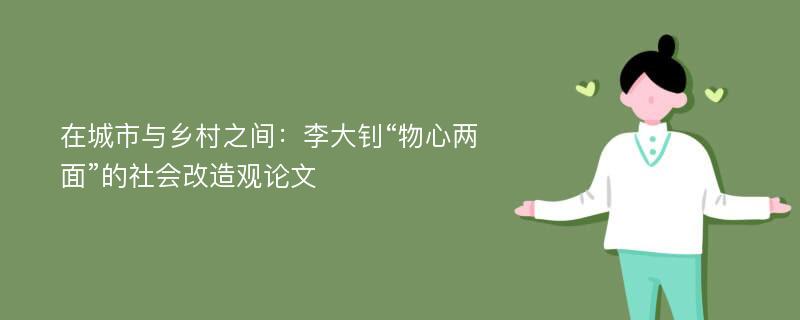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李大钊“物心两面”的社会改造观
马学军
[摘 要] 李大钊是中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灵肉一致”和“物心两面”的社会改造观。早期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主张道德革命和精神改造,号召青年发扬劳动主义,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也主张物质改造运动,但他认为物质改造和阶级斗争仅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达到互助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目标。李大钊后来虽也提出“工人政治”的表述,也领导了中共的工人运动,但随着都市工人运动的失败,他较早提出中国革命应依靠农民、应到农村开展农村革命。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李大钊;道德革命;物质改造;社会改造;到农村去
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革命历程,形成“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方针,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俄国先占领城市、后占领农村的革命道路,对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说作了重要发展。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其革命重心何以会从城市转向农村呢?
“农村人口众多说”和“地主农民矛盾激烈说”两种观点,是长期以来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主流观点,二者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农村人口众多说”而言,某一群体的数量多少,并不能完全决定该群体的力量大小。马克思就认为,法国小农人数众多、生活相似,但并没有共同的经历,还带有保守性和私有性的特点,并不具有工人阶级那样的觉悟性和革命性①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中,认为“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任何的共同体,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合,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因此,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只能让别人来代表他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17页。 。就“地主农民矛盾激烈说”而言,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益集中的严重趋势,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也并非那样尖锐[1-3]。这提醒我们,对于中共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理解,需要在以往这两种主流观点之外,寻求另一种解释的思路。而本文试图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以李大钊社会改造的思想为切入点,来尝试理解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后来转向农村革命的思想缘由。
李大钊,最早热情拥护俄国十月革命,最先发表《Bolshevl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人们会认为,李大钊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纲领,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为工具,来改造社会、开展革命。可是,“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却表现出多重性和复杂性,即使在他接受和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思想和观念仍然是多重性的,而非单一性的。李泽厚洞见性地指出,“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代表。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和最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在于他的这种接受和传播,从一开始便具有某种‘中国化’的特色。这特色使他不同于陈独秀,而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倒有一脉相通之处”[4]162-163。李泽厚进而指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两点最值得注意,即民粹主义的色彩和和道德主义的色彩。不独李泽厚,国外研究李大钊思想的迈斯纳,也尤其指出李大钊思想中的民粹主义色彩和互助论色彩。令迈斯纳惊奇的是,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青年与老人》《新的!旧的!》等文中,对劳资问题、青年与老人关系、中西方文化问题等,并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而是从合作、互助和调和的角度来理解和阐发[5]45。
1.1 对象 2009年8月—2011年11月在我院实施鼻内镜手术患者120例。采用PVF海绵进行术腔止血者60例,其中男32例,女28例,年龄20~42岁;采用凡士林油纱条止血者60例,男31例,女29例,年龄为18~40岁,均排除因其他器质性原因导致术后胀痛及出血等情况。
当我们细读李大钊热情拥护俄国十月革命、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文献时,确会发现李大钊表述了诸多如互助、合作和人道的观点。李大钊在1919年那篇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结尾处,明确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6]35。而在同年更早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演讲中,李大钊开篇即说“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改造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6]11-12。
李大钊所主张的“物心两面的改造”,尤其能表明这一时期他思想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这一点[7-8]。如果把“物心两面的改造”视为“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的核心表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心”的改造,是在李大钊热情拥护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早有的思想,而“物”的改造是他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五四”时期新近形成的思想,以此就出现了他称之为“物心两面的改造”的主张。而本文比较关心的是,李大钊早期“心”的改造思想如何形成以及为何要倡导“到民间去”?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后,如何处理“物的改造”和“心的改造”二者的关系,如何处理城市革命和农村革命之间的关系呢?
一、“心的改造”与“到民间去”
在李大钊思想早期的形成过程中,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其影响极大。吴汉全指出李大钊吸收托尔斯泰的悔改即革命说,倡导非暴力主张,强调道德的自我完善,主张个人的忏悔达到人心变动;继承托尔斯泰的“博爱”观,提倡人道主义;还接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注重知识分子的劳动问题和劳动者的教育问题[9]。本研究更为关注的是,李大钊在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影响下,如何形成自己“道德革命”和“劳动主义”观念的?这种观念又如何影响李大钊“到民间去”的观念?
(一)道德革命与“心的改造”
1906年李大钊到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受学校日文教员吉野作造与今井嘉幸的影响,开始接触并译介托尔斯泰的作品[10]42。吉野作造与今井嘉幸是日本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时期的重要发起人。此二人执教北洋法政学校时,向学生介绍和传播日本的民主思潮,提供日文期刊和书籍,与李大钊结成了密切的师生和友谊关系。李大钊毕业后,与二人保持密切的书信和活动往来,还一直阅读并翻译二人的文章和著作。
随着李大钊对马克思著作的了解和加深,他也在进一步思考如何理解物质变动和道德变动之间的关联。在1919年12月《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他认为道德的起源是物质,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风俗、习惯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6]117。李大钊在1920年相继写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和《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也是在进一步阐释经济变动和物质基础的观点。
《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这篇文章,是李大钊翻译日本人中里弭之助的《托翁言行录》,综合托翁学说结晶而成,以“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为题名发表的。中里弭之助,又名中里介山,信奉基督教,参与教会活动,同时着手社会主义研究,宣传托尔斯泰主义思想,是日本大众文学的创始人之一[12]158。李大钊在文中,条列八条纲领来简要介绍托尔斯泰的思想,其中第1至4条,阐述了托尔斯泰批判现代虚伪的文明论、忏悔论、道德革命论和善恶论,第5至8条阐述托尔斯泰的劳动观。
关于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英语教学的思考 ……………………………………………………………………… 卢丽媛(5/70)
李大钊在五四时期主张“灵肉一致”“物心两面的改造”的观点,并不认为互助论、人道主义和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矛盾之处。如果是按物质和经济改造的要求,社会改造要在都市从劳工运动来入手,而如果从精神改造出发,自然是像托尔斯泰那样躬耕于乡野,到农村开展运动。那么两方面改造如何协调、从何着手呢?
可见,托尔斯泰的革命论,其立论基点是针对“心”而发生的。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罪恶根本在于人们“心”的堕落,以此才出现“虚伪之文明”。“革命”不是针对外在的事物,而首先是针对内在“心”的革命,是“去旧恶新善之心”的变化。“心”发生变化了,其外在的世界也就发生变化了;“革命”的方式,不是暴力,也是不是其他,而惟有忏悔。托尔斯泰提出“勿以暴力抗恶”的道德观念,认为只有通过“道德自我修养”,才能摆脱罪恶实行“爱”的目的,使人类达到“最后的幸福”。这即是托尔斯泰的“道德革命”论,也是被称为成熟的“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观点[14]。
1913年底,李大钊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16年5月回国,同年8月他撰写《介绍哲人托尔斯泰(Leo Tolstoy)》一文,介绍托尔斯泰生平和他的思想,强调他生于专制国,倡导博爱、扶弱摧强,以劳动为神圣;1917年2月作《日本之托尔斯泰大热》,介绍了日本的托尔斯泰研究,慨叹本民族的文学介绍与民族兴亡的关系;1917年3月又著文《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认为人道主义的革命文学的鼓吹是俄国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1917年4月李大钊发表《罪恶与忏悔》这篇极具有托尔斯泰“道德革命”色彩的文章。文章开篇即以托尔斯泰的“道德革命”观点来痛斥吾国革命不知忏悔之义而发生的浩劫: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6]11-12。
从图5中可以看出,带载无转向工况下,最大行进阻力约为480N(图2中X与Z向的合力,下同),至多两人即可操作;但增加2°/s的转向角速度后,行进阻力峰值增至约1 450N,已超过3个人的操作上限。因此在带载工况下,利用梯形机构实现转向操作较为费力,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1919年2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这篇文章中,非常鲜明地提出青年应到农村中去。他说:
中国革命如此,世界革命也同样如此。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就认为法俄革命,不是法国或俄国一国人心的变动,而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15]228。李大钊在1918年12月发表的那篇著名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同样表达了完全相同的观点:“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国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15]263。
以此可见,李大钊思想在“五四”之前,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道德革命论的影响很深,注重“心”的忏悔和改造,以期实现个人、国家以及人类文明的复兴。如何能践行这种“心”的忏悔和改造?李大钊进一步发扬了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号召青年不仅要力行节俭,还要“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而不应成为都市游民。
(二)泛劳动主义与“到民间去”
1916年8月李大钊发表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Leo Tolstoy)》一文,介绍托尔斯泰的思想,认为其思想中一方面是倡导博爱主义,扶弱摧强,传布爱之福音于天下,另一方面是亲自躬行,倡导泛劳动主义,提倡“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11]174。李大钊早期的《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文,前4条阐述了托尔斯泰的忏悔论、道德革命论和善恶论,后4条都在阐述托尔斯泰的劳动观。我们已经分析了托尔斯泰的道德革命论,接下来我们就看在道德革命论下,李大钊是如何进一步提倡劳动主义和“到民间去”的。
“道德革命”论,以“心”为立足点,以“忏悔”为唯一方式,以实现去旧恶、从新善的道德革命目的。“善”是什么,最大的“善”又是什么,又何以能达到呢?李大钊条例的第四条纲领解释说,“善”就是“人间本然之理性与良心之权威是也”[13]408。最大最初的“善”就是“劳动”。《纲领》中言,“无劳动则不能生活,即离劳动无人生”[13]408。劳动是人生最大的义务,从而也是人生最大的“善”。劳动既然是人最基本的义务,也是最大最初的“善”,但为什么很多劳动的人反而是痛苦的,不劳动的人却是不痛苦的呢?其原因是,存在掠夺劳动者这样不合理的制度。《纲领》最后说,理想的世界就是人人半日劳动可满足基本的衣食住需要,同时可半日消遣得“灵性之慰安与向上”的美好世界。这样的“劳动”,即能健康人类心身,还能健康体魄,使得疾病绝迹于社会。
李大钊不仅只是译介和阐发托尔斯泰的观点,还以道德革命论来解释现实的自杀问题和革命问题,同时以泛劳动主义来解释当时的劳动问题,并号召青年“到民间去”。李大钊于1917年2月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一文,认为人力车夫在北京最可伶,“夫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11]]264。此时俄国十月革命还并未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并未结束。李大钊并不是受俄国十月革命,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人力车夫的命运,而更多是以人道主义的视角,认为人力车夫终日在马路尘土中穿行,风吹日晒,最易吸入尘土,是有悖于人道主义的。
1917年4月22日,李大钊发表《简易生活之必要》这篇极具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的文章。在文中李大钊指出,“盖今世之生活,泰半倚于过度……于是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种罪恶,皆因此过度之生活以丛滋矣”[15]118。今人衣食、交友、利禄等,处处呈现“过度”现象,各种罪恶也相伴而生。因此,李大钊提出惟有节俭生活,提倡简易之生活,方能救赎[15]118。李大钊最后期望,“苟能变今日繁华之社会、奢靡之风俗而致之简易,则社会所生之罪恶,必不若今日之多且重。然则简易生活者,实罪恶社会之福音也”[15]119。李大钊在文末指出简易生活与忏悔的关系,“余既于本报示忏悔之义,而忏悔之义,即当以实行简易生活为其第一步。吾人而欲自拔于罪恶也,尚其于此加之意焉”[15]119。
此处李大钊所痛心的“浩劫”,指前一年发生的袁世凯称帝事件。托尔斯泰的“道德革命”论,直指人心的忏悔和改造问题,可国人历经多次革命,尚未知革命应有的“忏悔”之义。何日能脱幽暗而向光明,犹未可知,这正是李大钊一直忧虑的问题。李大钊认为社会动乱是社会之罪恶造成,因此社会中之各个分子都应承担忏悔之责。人人忏悔,弃旧恶、就新善、涤秽暗,全体社会之人心才能发生变化,光明也才会复归[15]117。
可见,李大钊在“五四”之前即受俄国“到民间去”的思潮影响,较早号召青年到农村中去,认为农民也是劳工阶级的一部分,也较早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同年3月,李大钊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提出》中提出了“尊劳主义”,认为青年人的苦痛可由劳动来解脱。“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斥他,解脱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就叫作尊劳主义”[15]319。李大钊认为,现在的社会,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而且社会组织不良,少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被大多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五四”运动爆发几个月后,在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演讲,认为青年到农村不仅是改造农村,尤其重在青年自身的改造。李大钊在文中说:
“我们中国今日的情况,虽然与当年的俄罗斯大不相同,可是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15]304。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对工程进行准确有效的造价评估也是极为重要,是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主要是因为工程造价评估触及的方面较多,容易出现问题,从而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因此,一定要建立严谨的造价评估管理制度,对造价评估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与管理,确保在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的前提下,减小与实际费用的误差,减少成本的投入,保障水利工程建设能够正常的进行。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里,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智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厥,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6]12-13。
以此可见,李大钊受托尔斯泰道德革命和泛劳动主义影响,主张“心”的改造,认为当时中国人人应忏悔、劳动、过简易生活,社会上的贪婪和虚伪的罪恶才能消除,个人和社会也才能救赎。广大青年,尤其不应该在都市里漂泊,而应该到乡村去,与辛苦劳动的农民为伍;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农村几乎是隔绝的,是两个世界,因此更需要青年到乡村里。
我家有四个孩子,还有年迈的奶奶,一家七口人就靠父亲一人工作养活全家。在八十年代初,像我们这样的七口之家想要拥有一台缝纫机是很难的。在我要上小学时,隔壁的一位上海知青要离开连队,因为感谢母亲救了她落水的孩子,最后把这台压脚有问题的飞人牌缝纫机送给了母亲,母亲花钱找人修理了一下,从此,我家那小小的房间里就经常传出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
例如,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8]”
二、“物心两面”的改造观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但在国内并未立即产生很大影响。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一直关注并思考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1918年7月,他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认为法国革命代表19世纪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俄国革命代表20世纪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十月革命具有世界意义。此后,他陆续发表《Bolshevlsm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在国内较早阐发并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早期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李大钊,当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其思想也同样表现出多重性。
(一)道德改造与物质改造
在1918年11月纪念一战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指出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是社会的。李大钊认为政治上的结果,是“大……主义”的失败,民主主义的胜利。民主主义的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15]254-255。在社会的结果,表现为:“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15]255。李大钊在文后,提出了人人是劳工,人人都应赶快劳动的口号。他并没有特别突出和强调从阶级斗争的意义理解劳工问题,而是从合作、互助和联合的角度强调人人劳动的重要意义。
可见,李大钊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是把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Bolshevism混同起来看的,认为一战协约国的胜利都是这些主义的证明,这些主义都有其共同性。那么,如何理解人道主义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的关系?如何理解托尔斯泰的道德革命论和马克思物质改造两者的矛盾性呢?李大钊在1919年7月6日的《阶级竞争和互助》中说: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方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15]356。
对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李大钊补充说,“他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他是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启。他是确信继人类历史的前史,应该辟一个真历史的新纪元”[15]356。以此可见,李大钊在五四时期虽然接受了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也接受了其中物质改造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但他认为阶级斗争还仅仅是手段,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符合或达到互助论的信条和人道主义精神,并不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
在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演讲,对“五四”青年提出的理想目标是创造一个“少年中国”,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就是“少年运动”。“少年运动”包含两种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精神改造的运动和物质改造的运动是双向的,不可分开的。他在文中明确阐述了他的“物心两面”的改造观:
“俄国大哲托尔斯泰诠释革命之意义,谓惟有忏悔一语足以当之。今吾国历更革命已经三度,而于忏悔之义犹未尽喻。似此造劫之人心,尚未知何日始能脱幽暗而向光明。瞻念前途,浩劫未己,廉耻扫地,滋可痛矣!”[15]116
这段话无疑是最直接、最明确表述李大钊“物心两面的改造”的观点了。“精神改造”的运动,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这其中能看到李大钊既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影响,也受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物质改造”的运动,李大钊言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的经济制度,把劳工从旧制度解放出来。这是受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主张从经济基础入手。这两种运动之间的关系,李大钊说“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6]12。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求学这几年,正值晚清民国政治急剧变动的时期。历经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又经民国初建后的党派斗争和军阀干政,人们期望的共和政治和民主民权却久久不能实现。李大钊1913年4月发表《大哀篇》,副标题即为“哀吾民之失所也”,其中言“则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今者一专制都督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则所谓民权、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11]11-12。1913年4月1日,北洋法政学会所创办的政治评论与理论性刊物《言治》月刊正式出版,李大钊任编辑部长[10]129。李大钊在《言治》创刊号第1期,即发表《大哀篇》《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等文章。
不过,他并没有因为接受物质变动和经济基础的观点,就否定之前人道主义和互助主义的精神和信条。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和生活发生变化,道德也要发生变化。而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阶级的道德、私营和占据的道德,而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6]117。在某种程度上,李大钊用经济变动来解释一战人道主义、大同主义兴起的原因,如他说互助论和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一样。
(二)工人政治与农村革命
托尔斯泰认为现代文明是少数阶级之淫乐与虚荣的虚伪文明,而多数人却陷入贫穷、饥饿和死亡,因此需要革命。“人生真实也,不堪虚伪。今之文明虚伪也,则革命必不得不至”[13]407。什么是革命?“革命者,人类共同之思想感情,遇真正觉醒之时机,而一念兴起,欲去旧恶新善之心的变化,发现于外部之谓也。然悔改一语外,断无可表示革命意义之语”[13]407。革命如何进行?“无悔改而欲入于道,未可以想像也”[13]407。“悔改”既是个人,也是社会和国家摆脱罪恶,实现革新的唯一方式。因此,李大钊在文中断然地说,“然悔改一语外,断无可表示革命意义之语”[13]407。
侍酒师团队的扩大,意味着教育行业也在不断进步,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很多挑战。Joao Pires MS 认为:“挑战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世界主要葡萄酒产区,如果一个人不去实地考察,与葡萄园亲密接触或者和酿酒师学习,那么对想要进步的侍酒师来说很难。但侍酒师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新的职业,有无限的可能。而且已经有一位中国的侍酒师大师诞生,意味着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亚洲MS到来。”在张聪心目中:“教育发展已经逐渐和欧美同步,需要的只是时间与付出,如同那句话‘酿造一款优秀的酒,其实很简单,只要坚持300年’中国的侍酒师行业也同样如此,没有弯道超车,只有努力追赶!”
总而言之,国内人造金红石制备过程中总体呈现出以下问题:产品粉化严重;盐酸再生回收利用困难;设备腐蚀严重。
1.2.1 表现不典型:疾病表现不典型时诊断就有困难了。疾病可以发生在并不常见的部位、并不常见的人群、并不常见的地区,尤其是出现并不常见的临床表现。例如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应当表现为在左前胸压榨样持续性疼痛,但不典型者可以表现为咽喉痛、左肩痛甚至腹痛。有1例急腹症患者,外科收住院准备做剖腹探查手术。在术前准备插胃管时突然心跳停止。尸检证实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又如1例呼吸衰竭患者,两肺闻及广泛哮鸣音。开始诊断为哮喘,经过治疗毫无改善。摄胸片发现左侧气胸,胸腔抽气后,哮鸣音消失。原来该患者有慢阻肺史,肺功能较差,一旦发生气胸就可以出现哮喘样表现。
随着李大钊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肯定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又进步提出“工人政治”的表述。在1921年12月他发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演讲,认为平民政治,亦即德谟克拉西,是近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是反对强权和不平等的。而社会主义的精神,也是平民政治的一种,与德谟克拉西是同一源流。不过,他认为社会主义目前仅仅注重经济方面,还需要拓展在社会、政治各方面追求。李大钊认为后德谟克拉西而起者,为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是俄国革命实践和开创的,可译为“工人政治”,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16]3。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随后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产业工会。李大钊是中共重要的发起人之一,此后也是中共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在全国第一波工人运动高潮中,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范围最广、势力最大、影响也最大。不过,随着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中共工人运动遭受很大挫折,有关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方向问题此后成为党内反复争论的问题。尽管共产国际和中共后来决议同国民党进行合作、开展国民革命,尽管李大钊也参与了国民党事务,但他对革命的出路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李大钊较早提出国民革命更多要依靠农民,要到农村去发动农民革命。
在1924年9月发表的《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一文中,李大钊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他们绝大部分是半赤贫的小农;外来工业的冲击,更带来了流离失所的农民,中国革命要重视这一重要的力量[13]31。1925年至1926年,李大钊在北京党组织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发表《土地与农民》这篇极为重要的文章。迈斯纳称,这是李大钊第一次试图把农民革命的力量看作是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基础[5]254。在文中,李大钊认为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而目前,“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国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13]76。他在文中提及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广东的农民运动非常有成效。最后他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13]85。
李大钊在1926年8月8日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文章,认为山东、河南、陕西一带兴起的红枪会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力量。他说,“这个现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将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13]128。当然,在农民中也存在狭隘的村落主义和乡土主义。他号召农村中有觉悟的青年、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尽快加入红枪会,去帮助他们,、推动农民运动。
有老太医运筹帷幄,有金叶子耀武扬威,还有什么秘密查不出?于是,风云八虎,还有八虎身后的德公公,逐渐浮出水面。
三、结论
张灏先生指出,“五四”思想表现出明显的两歧性:表面是一个强调启蒙,推崇科学的理性主义时代,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又含有很强烈的浪漫主义;表面是一个理性与怀疑,破除一切偶像的时代,但其也是一个强烈寻求信仰的时代[17]4。在张灏看来,“五四”知识分子,要面对政治秩序和“取向秩序”的双重危机。在这种双重危机的压力之下,他们急切地追求新的价值观和宇宙观、新的信仰。而“五四”时期的思想和信仰形形色色,纷然杂陈,“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理想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这些信仰,内容虽是庞杂,却有两个共同的倾向: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乌托邦主义;另一个,无以名之,名之曰:人本主义的‘新宗教’”[17]10。张灏进而指出,不仅是信奉新村主义的周作人,包括服膺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胡适、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五四”时期都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
如本文分析所言,近代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中共重要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的李大钊,即使在接受和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思想仍带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早期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主张道德革命和人心的改造,提倡简易生活来实现这种忏悔和心的改造,主张像托尔斯泰一样亲自躬行,发扬劳动主义,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认为阶级斗争还仅仅是手段,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达到互助论的信条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因此倡导“灵肉一致”“物心两面”的改造观,认为“精神改造”运动,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而“物质改造”运动,改造现代的经济制度,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纳入的样本量不够大;其次,本研究为自身对照研究,并没有设计安慰剂对照组;另外,由于对门诊患者进行长期的随访较困难,导致难以评估患者的长期疗效。
尽管李大钊后来也提出“工人政治”的表述,也领导中共北方工人运动,但随着都市工人运动的失败,以及国共合作的分歧,他较早提出国民革命更多要依靠农民,要到农村发动农民革命。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现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2]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学(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饶伟新.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121-128
[4]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9
[5] 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6]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吕明灼.“道德革命”与“心的改造”——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8] 後藤延子.日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後藤延子,王青,等编译.李大钊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
[9] 吴汉全.托尔斯泰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影响.学术交流,1993(6):125-130
[10] 朱成甲.李大钊传(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1]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 谭晶华.日本文学辞典·作家与作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 刘倩.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哲学思想.国外文学,1990(Z1):35-47
[15]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6]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7] 许纪霖.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Li Dazhao's View of Social Bilingual Remolding of Spirit and M aterial
MA Xuejun
Abstract Li Dazhao was the firstMarxistof the CCP,he advocated amovement of bilingual remolding of spiritand material.In the early days,hewas influenced by Tolstoy's humanitarianism and pan-laborism,alleged themoral revolution and spiritual reform,called upon the youth to carry forward laborism and go to join with peasant.Although after accepting Marxism,he advocated material reform movement,he still believed material reform and class struggle were justmeanswhile the ultimate goalwas to realizemutual aids and humanitarianism.He put forward “worker politics” and actually led workers'movements,butwith the failure of the urban workers'movement,he believed Chinese revolution relied more on peasants and needed peasant revolutions in the countryside.An in-depth study on LiDazhao's thoughtswill promo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CP which based on the proletariat but turned to the rural revolution lastly.
Keywords Li Dazhao;Moral revolution;Material reform;Social reform;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收稿日期] 2019 05 21
[基金项目] 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兴衰史研究及其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借鉴意义”(19YJC840031)。
[作者简介] 马学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讲师,邮编:100083。
标签:李大钊论文; 道德革命论文; 物质改造论文; 社会改造论文; 到农村去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