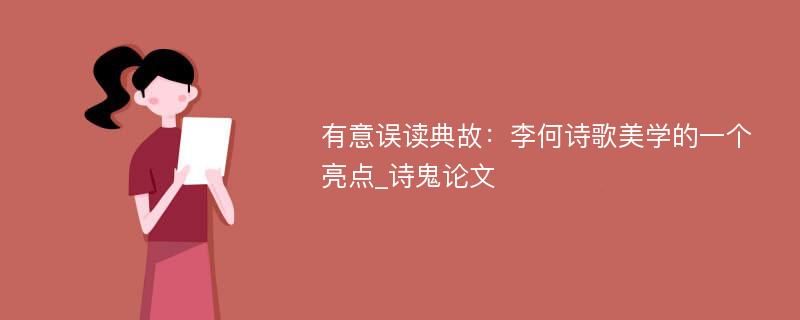
“典故的有意误读”——李贺诗歌美学的一大亮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读论文,一大论文,典故论文,美学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8)03-0010-05
在唐代乃至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李贺堪称一个十分别致的人物。他是个命运悲惨的小人物,但同时他又是个满怀痛苦激情的大诗人。他的诗,不仅风格冷艳、意象奇诡,而且在章法、用韵、用典等方面也十分奇特。单就用典方面而言,李贺常常撇开典故的原有意义,在具体诗歌情境中对典故进行“有意误读”,赋予它另外一种意义,甚至相反的意义。这样,典故的原义与语境义之间便构成对话与冲突,诗意由此变得十分复杂。李贺诗中典故的“有意误读”很多,如《苦昼短》中的“任公子骑白驴”典故、《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三》中的“千金买骨”典故、《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魏明帝青龙九年”典故、《南园十三首·其十二》中的“虞卿”典故,等等。这些“有意误读”的典故,决不只是为了在诗风上的争奇斗险,而是更多地与他的悲剧的命运、深切的痛苦、狂热的理想、尴尬的身份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通过对这些典故意义生成的特殊方式的具体解读,我们可以窥见李贺隐秘的文心。
一、“任公子骑白驴”
“任公子骑白驴”出自李贺的名篇《苦昼短》: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1](p.221)
诗中共三次发问。第一问:“神君何在,太一安有?”第二问:“何为服黄金,吞白玉?”第三问:“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
这三次发问由一个总题引起:“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李贺面临一个问题:天道有常,流化无情。世间万物,在时光流化面前,显得那样无奈和渺小,因此他发问道:“神君何在,太一安有?”
回答是:“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日出处有神木,日落处有神龙衔烛。
对此,李贺有一个愤激的想象:“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天不怕,地不怕,将神龙肉体消灭,斩草除根,一了百了。这是一种最坚决、最强烈、最愤激的主体抗争姿态,虽然,这是一种莽汉式的抗争。
这正是对第二问的回答:“何为服黄金,吞白玉?”用不着再服金吞玉,炼丹修道了,再也用不着学着神仙的样子,在造化面前辛苦挣扎了。看来,这个想象的解决是最简单有效的了。
前两次发问,都得到了回答。那么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呢?决不是的。不可能、也不应该让问题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因为那不是李贺。愤激的抗争或辛苦的挣扎,他对这两种态度全都不满意,全都怀着深度的怀疑。
这种深度怀疑通过第三问得到全面表达:“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这是典故的“有意误读”。“任公子骑白驴”涉及两个典故:
1.“任公子”。见《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
任公子典故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任国公子做了个大鱼钩,系上粗绳,用50头牛做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把钓竿投向东海,终于有大鱼食吞鱼饵,白浪如山,声震鬼神。任公子把大鱼剖开制成鱼干,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的人都得饱食。——这是一种气吞万物的大境界。而那些目光短浅的浅薄之士,见到任公子之举后吃惊地奔走相告。他们也举着钓竿丝绳,奔跑在山沟小渠旁,守候小鱼上钩。——这是执于小节的小境界。
2.“白驴”:神仙常骑乘之,著名的“骑白驴”者有张果(即张果老)、张洪崖、邹和尚,另外还有一个汉灵帝:
张果尝乘一白驴,一日行百里,夜则叠之置箱中,乃纸耳。[3](p.7)
张果常乘一白驴,休则叠之如纸,贮箱中,以水噀之,复成驴矣。[4](p.25)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唐有张氲,亦号洪崖先生。……十六年,洪州大疫。氲至施药,病者立愈。……跨白驴,从者负六角扇、垂云笠、铁如意,往来市间,人莫知其岁耳。[5](p.36)
洪崖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姓张名蕴,字藏真。……每述金丹华池之事,易形炼丹之术,人莫究其微妙焉。……白驴曰雪精,日行千里。[6](p.7)
唐大历间有僧,号邹和尚,不知所从来。跨白驴,登伞山,结茅以居。须盐米薪菜之属,即书寸纸,系钱缗,遣驴负至市区。人知为邹也,取平直,挂物于鞍,纵驴归。……邹末年北走通泉县灵鹫山龛中,其徒追及之,但见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驴者,狮子也。[7](p.15)
后汉灵帝于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以为之乐。公卿贵戚转相仿效。[8](p.33)
这些骑白驴的先生们大多有些煞有介事的小家子气。张果应该是最“神”的一个了,能玩纸驴子变活驴子的把戏;张洪崖显得“专业”一些,精通“金丹华池之事,易形炼丹之术”;邹和尚来头不小,是文殊菩萨变的;驴子也不简单,狮子变的,它负责下山买东西,同时传播“作人要诚信”的道理。汉灵帝最没出息,他骑白驴纯粹是为了玩,也难怪,他不是神仙。
任公子,《庄子》事也;骑白驴(张果老、张洪崖、邹和尚),道教、佛教事也。显然,“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是“谁是任公子,海中钓大鱼”和“谁是张果老(张洪崖、邹和尚),云中骑白驴”两个问句的合并,这两个疑问表达了李贺的双重怀疑。怀疑之一:“谁是张果老(张洪崖、邹和尚),云中骑白驴?”——这一问,问的是后世那些求仙修道者(包括秦皇汉武)。张果老(张洪崖、邹和尚)飞升而去,后人枉自学他们“服黄金,吞白玉”,不过徒劳而已。怀疑之二:“谁是任公子,海中钓大鱼?”——这一问,问的不是别人,正是“云中骑白驴”的张果老们。这些成仙飞升的修道“成功人士”,和任公子比起来,也不过是小儿科,小境界。他们充其量比“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的“辁才讽说之徒”略强一些而已。
李贺令任公子骑白驴,把两事合并成一事,强行拼接出一个荒诞意象,驴身而马面。任公子的大境界因为骑白驴的张果们的闯入而变得有些荒诞和虚妄;而张果们骑的白驴由于换了主人,也变得不伦不类。这样,“任公子”和“白驴”便互为解构因素,互相削弱、互相虚化、互相淡化,钓大鱼的任公子少了气吞万物的大气,骑白驴的张果们少了炼丹使气的仙气,神圣耀眼的光环暗淡了。结果是,“骑白驴的任公子”走下神坛,由神圣的使者变成了滑稽可爱的“圣诞老人”。只可惜这位“圣诞老人”往人们袜子里放的不是甜美的糖果,而是一响而散的爆竹。爆竹炸响后,所有美丽辉煌的梦幻像微尘一样迸散,只剩下一缕彻底怀疑的思绪。
这第三问对前面的第一问、第二问及其回答也构成了彻底的解构。“任公子骑白驴”这个荒诞意象再度刷新了“神君何在?太一安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张果等众神仙在任公子的冲击之下已经失去了神秘和神性的光环,众神所归的“神君”、“太一”的合法性也就出现了危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同样,第三问也对第二问构成了彻底的解构。第二次发问以及回答分别显示了对待时光流化的两种对立态度:一种是“斩龙足,嚼龙肉”的大胆抗争,一种是“服黄金,吞白玉”的辛苦经营。这两种态度在第三次诘问面前轰然崩塌了。“服黄金,吞白玉”已经被李贺用一个“何为”否定掉了,但这还不算完,李贺对它进行了穷追猛打。任公子典故显示了两种境界:一种是任公子“大钩巨缁”、“扬波东海”的大境界,一种是“辁才讽说之徒”“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的小境界。不难看出,这两种境界和对待时光流化的两种态度是对应的。而且,骑白驴飞升的神仙们尚且如此,后人的“服黄金,吞白玉”也就更难得什么善果了。
扩大一步说,求仙修道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它同时还具有一个观念体系。粗略来看,求仙修道呈现为一种三级体系:神君、太一——道士(包括飞升成仙的道士)——俗人(包括秦皇、汉武)。“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这个荒诞意象,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它的怀疑能量辐射到整个诗篇,整个求仙修道观念体系因之崩解。首先是对神君、太一的怀疑,其次是对“骑白驴”的道士神仙们的怀疑,最后是对俗人求仙修道的怀疑:“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那么,“斩龙足,嚼龙肉”式的愤激抗争的态度应属大境界,李贺是不是肯定了这种境界呢?也不是。任公子没有去钓大鱼,而是骑上了白驴。钓大鱼出身的任公子刚刚要作出一付“伟大”姿态,白驴却没有配合,一声空幻的驴鸣,把他刚刚上演的“崇高”瞬间变成了“滑稽”。“斩龙足,嚼龙肉”式的豪壮也因之散作微尘。
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只剩下两种东西:自然的永恒流化,人的绝对怀疑。人在不断的挫败面前,可能会产生两种怀疑:怀疑自己,或怀疑命运。李贺没有怀疑自己,他一直自负于自己卓异的诗才和“诸王孙”的出身。但他卓异的诗才并没有使他科举及第,而是由于荒谬的“家讳”被排斥于科场外;后来(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他在韩愈引荐下才作了一个无聊的小官奉礼郎,两年后病归昌谷饱受饥寒;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他在无情命运面前做了最后一次挣扎:到潞州投军,但次年又是无功而返。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一直在不停地挣扎,但是,除了早年通过河南府试,他几乎从来没有顺利过;除了新婚之喜,他几乎从来没有快乐过。他怀疑命运,他愤怒、悲哀于命运对他的不公,现实世界对他的无情捉弄。激情之余,他能为自己的人生状态提供的最终解释是:命运的无常与人生的空幻。
二、“虞卿”
“虞卿”也是被“有意误读”的典故。在历史上,虞卿是“发愤著书”的典范,但李贺在《南园十三首·其十二》中却让他裁制了一件道袍:
松溪黑水新龙卵,桂洞生硝旧马牙。
谁遣虞卿裁道帔,轻绡一匹染朝霞。[1](p.92)
这首诗作于李贺乡居昌谷时。前两句充满了道教神异色彩。松溪桂洞,黑水龙卵,自是清幽之处,而且有一种神异氛围。王琦注:“松溪桂洞即其所居之地,龙亦卵生,凡水深而色沉黑者,必有龙潜焉。松溪之中或者传有龙居之,故云。又山涧中所产蜥蜴,土人往往称之曰龙。龙卵或是蜥蜴之卵,亦未可知。”[1](p.92) 生硝马牙,则是十足的修炼药饵。但是第三句中“虞卿”的出现,使这种道教神异氛围变得不安起来。
此诗中的“虞卿”典故见于《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跻檐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9](p.1859)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9](p.1862)
虞卿被司马迁视为身具纵横捭阖之才、失意则“发愤著书”的典范,在后世典籍中也总是以这种面貌出现的。他与道教或道士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李贺在此诗中却让他披上了艳如朝霞的大红道袍:“谁遣虞卿裁道帔,轻绡一匹染朝霞”。这是为什么呢?
王琦对此二句的理解是:“《史记》称虞卿,游说之士也。……与长吉生平无一相似,无庸取以自比,且与全首文意亦了不相干,何以忽入此古人姓名?意者昌谷中人有潜光隐曜,道服而幽居者,与长吉往来交好,其人虞姓,故以虞卿比之。如称贾至为贾生,孟浩然为孟夫子,唐人诗中类多有之。”[1](p.92) 王琦之说粗看似有理,但细考具体诗篇,却不尽然。“贾生”在《全唐诗》中共出现66次,明指贾至或类似其他贾姓实名者只有二首,即独孤及《送陈兼应辟兼寄高适、贾至》“贾生去洛阳,焜耀琳琅姿”[10](p.622),以及刘长卿《送贾三北游》“贾生未达犹窘迫,身驰匹马邯郸陌”[10](p.358),其余诸诗中的“贾生”皆指贾谊。“孟夫子”出现5次,都明确与孟浩然或孟郊有关,即李白《赠孟浩然》、元结《送孟校书往南海》、刘叉《答孟东野》、《与孟东野》、韩愈《远游联句》。这些诗句中“孟夫子”或“贾生”的指代,都在诗题或正文中有明显交代或暗示。然而,李贺此诗中的“虞卿”,不论是在这首诗中,还是在全集其他各篇中都没有任何暗示。所以,推断此诗中的“虞卿”指代昌谷中一位道服幽居之人,固然有此可能性,但是很牵强。而且以“贾生”喻贾至和以“虞卿”喻“昌谷中道服幽居之人”的差别是很大的。贾至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乙亥科状元及第,著名诗人,一生仕宦,历任中书舍人、尚书左丞、京兆尹、右散骑常侍等官职,与汉代贾谊自有可比之处;但“虞卿”与“昌谷中道服幽居之人”几乎毫无可比之处。由此可以推断,李贺此诗中的“虞卿”指的就是《史记》中所记述的那个“发愤著书”的“虞卿”。
王琦的目的很明确:他发现了“谁遣虞卿裁道帔”一句中的意义裂隙,但他总想努力弭平这种裂隙。弭平是一种遮蔽。我们的态度和他恰恰相反:我们决不试图弭平这种裂隙,而是要彰显这种裂隙,更要沿着这种裂隙深究下去,因为这个裂隙正是李贺文心的幽微之处。那么,李贺让“发愤著书”的虞卿来裁制道帔,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其用心处何在?确确实实是不相及的,确确实实是一种强行的嫁接,这正是李贺此诗的隐秘所在。这是李贺心目中两种隐居生存方式的强行嫁接:一种是隐居著书名世,一种是修道养生。这两种生存方式在李贺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著书名世是李贺最不愿接受的一种退路,他在《南园十三首·其六》中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对“寻章摘句老雕虫”[1](p.88) 式生活的厌倦,到第十首中,则明确地说:“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1](p.90) 所以,在这首诗中,他才会让以发愤著书名于后世的虞卿去裁制一件道帔。“谁遣虞卿裁道帔,轻绡一匹染朝霞”,这是一很滑稽的画面。游说得志、官拜上卿、失意后发愤著书的虞卿,一生为显身扬名辛苦经营的虞卿,现在却以一匹朝霞色的轻绡,裁了一件道袍,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极不和谐。而且这两种不和谐因素并列一处,每个方面都成为对方的一种解构因素。虞卿一生为显身扬名而操劳,他那火热而沉重的激情,在“轻绡一匹染朝霞”的道袍之下变得轻飘飘起来,在松溪桂洞、生硝马牙、黑水龙卵的阴气熏染之下也变得冷清了起来;同时,松溪桂洞、生硝马牙、黑水龙卵、轻绡道帔的“仙气”由于“虞卿”这个冒失鬼的闯入也变得不纯了,虚静超脱的“仙气”中掺进了世俗躁动的杂质。
滑稽的背后是李贺深深的苦涩。他不会去发愤著书,也不会去山居修道。著作与修道,他只不过是想想罢了,这两件事情在他的心中,根本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神圣。也难怪,人们常说的是“归隐”或“退隐”,青年李贺还没有“出去”,还没有半点功业可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1](p.87) 的激情梦想还在召唤着他,何言“归”,何言“退”呢?所以他在昌谷也呆不长,不久(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他就离开昌谷,到潞州(今山西长治)投奔去了。
三、“骏骨送襄王”
提起马,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韩愈的《马说》。《马说》揭示了一个由“千里马—伯乐—饲马者”所构成的关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骏马”是渴望为主人效力的“人才”;“饲马者”作为马的主人,掌控着对骏马是否任用、如何任用的权力;“伯乐”则是作为“饲马者”的智囊,他有发现骏马的智慧,拥有对饲马者的“建议权”,但骏马的“待遇”是否“落实”,那不是他的事情,饲马者完全可以不理伯乐的意见。事实也正是如此,伯乐的“建议权”常常是被架空了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11](p.20) 实际上,不仅骏马难遇伯乐,伯乐更难遇明主——有眼光、有魄力的“饲马者”更是少之又少。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位伯乐,一位“堆金买骏骨”的少年。
宝玦谁家子,长闻侠骨香。堆金买骏骨,将送楚襄王。(《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三》)[1](p.105)
这个身佩宝块的少年周身弥漫着一种英雄豪气。“侠骨香”一词体现出人们对豪侠之士任侠使气、蔑视法度、重义轻生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极度赞赏。张华《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其一:“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其二:“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12](p.5) 李白《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10](p.385) 这样一位少侠却做了一件让人十分费解的事情:“堆金买骏骨,将送楚襄王”。
关于“骏骨”,历来有两种解释。
一是认为“骏骨”即是《战国策·燕策》中著名的“千金买骨”典故。燕昭王即位之初,想要招贤报仇,向郭隈问计。郭隈建议燕昭王,效法传说中以500金购买千里马尸骨的古代君王,厚待他郭隈来招揽贤士。燕昭王听从了他的建议,“为隈筑宫而师之”,果然不久以后,“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战国策·燕策》)[13](pp.15-16)
“千金买骏骨”典故在唐诗中也是反复出现的。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骤耳空腾骧。”[10](p.400) 杜甫《昔游》:“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有能市骏骨,莫恨少龙媒。”[10](p.534) 诗中总是用昔日燕王“千金买骏骨”的魄力来反衬今世人主对贤才的漠视。李贺诗中的“骏骨”有如此意义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是认为“骏骨”指的是“骨相奇骏之马”。在唐诗中,“骏骨”作此解者也不乏其例,如李世民《临洛水》“春搜驰骏骨,总辔俯长河”[10](p.22)、《咏饮马》“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10](p.24)、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骏骨黄金买,英髦绛帐延”[10](p.1006),还有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其九“夜来霜压栈,骏骨折西风”[1](p.102)。
楚襄王即楚顷襄王,楚怀王之子。顷襄王既不好骏马,又不好贤才。他有两件事最著名,但都不太光彩:一是他好女色。宋玉《神女赋》:“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14](p.8)。二是他放逐屈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9](p.1935)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9](p.1936) 不论是骏马,还是骏马之骨,这个少年堆金买来送给好色恶才的顷襄王做什么?
又是“典故的有意误读”。“买骏骨当送燕昭,反而送楚者,所谓北首而南辕也,用意深妙。”[1](p.512) 清代阙名《李长吉诗集》:“寓尽明珠暗投之苦。却送楚襄王,趣极。”[15](p.112) 多数注家均持此解。但细想来,这个“长闻侠骨香”的少年,有任侠使气、重义轻生、纵横六合的豪情,不大可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愚忠腐儒。所以,与其说他是“明珠投暗”,还不如说他是故意送错了人。正因为顷襄王好女色、近小人,少侠才偏要送骏骨给他,以此来刺激他一下,让他反躬自省,广招贤才,重振国威。这个少年所要表达的不仅有无奈,更有他的愤怒。虽然侠肝义胆可鉴,但他的一份苦心却是白费了。那么诗人李贺借这个有意误读的典故所要表达的,便不仅是无奈与愤怒,更是深刻的失望与虚无了。李贺以骏马自况,然而,在《马诗二十三首》中,骏马们没有几个好下场的,有的“蒺藜衔”(其二)、有的“骨查牙”(其六)、有的“无人用”(其八)、有的“折西风”(其九)、有的“溘风尘”(其十一),而庸马、劣马们则是“银鞯刺麒麟”(其十一)、“白铁锉青禾”(其十七),待遇好得很。骏马无依,明主安在?李贺借这个典故的有意误读,充当了一回无可奈何、又有点气急败坏的伯乐,堆金买来骏骨,往楚襄王面前一站:“你看着办吧!”
四、“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
李贺是一个诗人,他带着他的诗来到这个世界。诗,是他最重要的财产;诗人,是他最切实的身份。当然,他还有一个“诸王孙”的身份。他有一个遥远的祖上作过“郑王”,于是,这个“郑王记忆”支撑了他全部的“诸王孙”想象。而且这两个身份在李贺心目中的地位不是等同的。他非常在乎这个“诸王孙”身份,在他的身份想象中,他是陇西那个荣耀的“诸王孙”,而不是家住昌谷的这个窝窝囊囊的书客。“诸王孙”是他的一个“心结”,是他心中最强有力的召唤。他的“蛇作龙”的梦想、“噪礼乐”的大志,都是这个“心结”的辐射。他以“诸王孙”的“想象身份”,“想象地”加入帝王的伟业。《金铜仙人辞汉歌》序文中明言自己以“诸王孙”身份为魏明帝写作咏歌:
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1](p.94)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序文中,李贺把“魏明帝迁徙金铜仙人”这个典故进行了“有意误读”,虚构了一个“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的事件发生时间[事实上,魏明帝青龙五年·(公元233年)即改元“景初”]。注家对此众说纷纭。笔者以为,对于这个“有意误读”的案例进行孤立的“史事钩沉”未必是有效的,更应该注意的是诗人在他自己本文中透露出来的微妙信息:首先最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虚构了“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的事件发生时间,又特别明言自己的“诸王孙”身份;其次,要明确一个重要原则:他“误读”了什么,同时就是在提醒着什么;他掩盖着什么,同时就是在彰显着什么。单就典故误读而言,李贺并非有意将全部“真事隐去”,只是更动了时间,是一种“有意误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首先是让人注意时间问题。注意时间的什么呢?诗歌首联即明确交代:“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时间的无情流化。这正是他的“时间焦虑”;其次,淡化事件真实,意在强化情感真实。联系诗歌正文可以看出,对此典故,李贺最想说的是仙人被迁时的“潸然泪下”,全在一个“情”字。这是解读的第一步。
下一步,我们把“魏明帝迁徙金铜仙人”这个典故的“有限误读”与同一段文字中“诸王孙”身份的明示作互文性解读。既然明言自己的“诸王孙”身份,同时诗的表达重在一个“情”字,那么,本诗的隐含旨意一定不是对帝王的“讽刺”或“揭露”(虽然这种断语非常符合中国的意识形态解读习惯)。典故的“有限误读”表明,他承认事件的基本真实性,同时又表明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想象性参与”。这样,“诸王孙”身份的明示也就非常重要了:他以“诸王孙”身份对“魏明帝迁徙金铜仙人”事件进行了“想象性参与”——对方是帝王,“我李贺”是“诸王孙”,俨然一副“自家人管自家事”的姿态。所以,这个典故的“有意误读”,与其说是对帝王的揭露与讽刺,还不如说是他“诸王孙”身份的有意宣示和“诸王孙”行为的“想象性实施”。
李贺抑制不住这种冲动。他的《公莫舞歌》把“刺豹淋血盛银罂”[1](p.138) 之类恐怖的血光剑影场面尽情渲染一番之后,作为观众的诗人李贺借樊哙之口讲了一通“大道理”:
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人赤龙子。芒砀云端抱天回,咸阳王气清如水。
铁枢铁楗重束关,大旗五丈撞双环。汉王今日须秦印,绝膑刳肠臣不论。[1](p.138)
钱钟书以此诗为证,说明李贺诗专在修辞设色上用力,缺乏世道人心之感[16](p.47)。李贺所牵肠挂肚的当然不是世道人心,而是他的“诸王孙”身份。这通“大道理”正是他以“诸王孙”身份对刘邦这个“天授”帝王的倾情维护。
在用典上,很少有哪位诗人像李贺这样大胆。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对典故的有意误读,他在诗句中有意构造一种语义裂隙。这道隐隐约约的裂隙,像一个神秘的黑洞,它招引着人们去探寻,去领悟隐藏在裂隙深处的隐秘文思。这无疑是李贺诗歌美学的一大亮点。
[收稿日期]2008-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