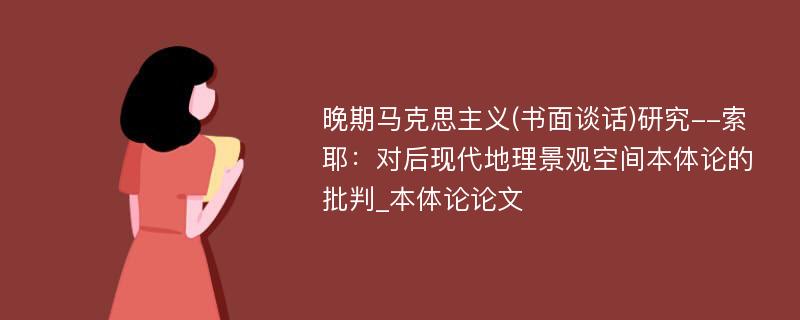
晚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笔谈)——索亚:后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本体论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笔谈论文,后现代论文,晚期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5-0005-21
黑格尔说过,哲学像是一只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所谓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就 是后现代话语挑战中姗姗来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如詹姆逊所反思的:形形色色 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联袂演出的“马克思主义终结论”,逼着马克思主义 者发展出一种“更加现代的”(实际上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它试图对传统的研 究客体,即资本主义本身所呈现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维度”,即“后现代状况”加以理 论化[1](p.310)。由此,晚期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得出一个近似的结论:后现代主义 与其基础即晚期资本主义具有着互为表里、彼此辩护的现实同谋关系!而达成如此共识 的理论前提是,认为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性哲学话语,在后现代语境下完全 可以被激活而决不可以将其瓦解;但这种历史决定论必须被重新主题化为一种“空间化 的辩证法”。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是“量” 的扩大再生产,还不是同质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再生产过程。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工业化社会生产过程的制约,但他实际上已 经隐约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但是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 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止,而实现的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发展到 后现代,它的主导生产方式就是“空间的生产”,而不是物的或社会的生产。所谓的后 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症状,是与资本主义的流动化空间化全球化发展过程——“时空的压 缩”、“共时性对历时性的胜利”等无意识地相一致的空间化体验形式[2](p.149,251) 。
当然,晚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空间化”激活的角度 还是各不相同的。如詹姆逊是以后现代文化的空间图绘为经络,德里克则是以全球化与 地方化的空间互动为视野,而戴维·哈维以及本文要重点评析的爱德华·W·索亚(亦译 作苏贾,Edward W.Soja),则以地理学为空间化的隐喻原型。所以,他们心目中的晚期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后现代化”和“历史地理的唯物主义”[3](p.98 )。
索亚在其扬名之作《后现代地理学》(1988)及其他著作中,首先以地理学为本位,突 出地显化了19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城市地理学、区域研究、世界体系论与晚 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包含的空间问题讨论成果,指出要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摆脱理 论与实践危机,就必须实现社会批判的空间化转向;其次越出地理学边界,吸收综合存 在主义(萨特与海德格尔)与结构主义(阿尔都塞、濮兰查斯),特别是列斐伏尔、福柯、 詹姆逊、吉登斯等人的空间辩证法思想,而提出了所谓空间、社会与历史三位一体,辩 证互动的三元辩证法(trialectis)[4](pp.53-82),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社会批判理论哲 学基础的空间本体论;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批判被转换成一种后现代地理 景观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学说被转译为一种社会时空重构化理论。最后,他 以空间本体论为指导,并通过后福特主义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的概念中介, 将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实证化为一种具有鲜明地理学特色的“批判性的区域研究”方案 。
1.一场矫枉过正的范式变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化重构
索亚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法空间化解释的突破口,是要解除马克思主义的“ 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紧箍咒。他认为这实际上也戳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软肋。他通过给 地理环境决定论“平反昭雪”,通过把社会历史的“地理环境”过度诠释为社会的“空 间”,进而把社会关系生产从具体物质生产过程中提升出来,抽象化为空间的生产,这 就为其雄心勃勃的主张铺平了道路。他有意无意地置马克思与普列汉诺夫的许多论述于 不顾,而坚持认为,从马克思开始便具有排斥地理空间的倾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具有根 深蒂固的“反空间主义”传统[3](p.192),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患有顽固的“空间短视 症”[3](p.186)。马克思发表的著作,基本上是“无空间和封闭性体系”的理论阐述, 其中的资本主义“像天使般站在针尖上”[3](p.130)。
马克思主义的反空间传统,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是它与地理学长期处于隔绝状态。而 传统的地理学本身也是反空间的。与传统的地理学将空间视为僵死不变的地域——“一 个被动和可以丈量的世界,而不是具有行动和意义的世界”[3](p.57)——相似,资本 主义、欧洲、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那里,便有了一种坚不可摧的历 史决定论式的先验的本质统一逻辑。
索亚认为,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是预先规定好的、同质化的历史目的与历史必 然性自我展开与实现的过程,而是对具体的时间与地理的重构过程。于是马克思的历史 决定论可读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地理,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 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生产的 历史地理的条件下创造了历史与地理”[3](p.196)。马克思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看到地 理空间性(如城乡)的客观外表掩盖着生产的各种基本的社会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存在着一种不发达不自觉的空间问题意识与空间问题框架,这种含糊状态需要清晰自 觉。
在索亚眼里,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各种历史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 。地理学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一重任——彻底解开这种神秘化的空间外套。但问题是 ,在它眼里只有自然的地理环境,而没有空间想象。正像是“在所有补鞋匠的眼里看到 的就只有皮革”[3](p.104)。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关心的不是表面上的地理,而是隐藏于 其后的资本主义对地理的空间性政治控制与利用。而“对隐藏于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 发展背后的各种更一般的更多层的过程进行概念化并在经验上加以检视”,这需要一种 后现代的地理学想象(即哈维所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才行[3](p.175)。
索亚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与商榷的观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开空间的生 产这个主导结构,而仍然还原论地强调物质生产决定论,这就牺牲掉了“一切历史和地 理的具体性”[3](p.151)。这恰恰是“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教条主义。这种历史— 地理唯物主义,本意是要解构那种以牺牲历史地理具体性为代价的宏大历史叙事霸权的 ,但结果却是以牺牲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阶级分析这样的核心本质批判逻辑为代价 的。在他看来,阶级关系概念无法解读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流动的、区域化发展的趋势 与现实:区域并不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也不是阶级性的直接表现,而是各种基本的 生产关系等级性构建的各种社会过程。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 合起来”的本质主义理想宣言,是无法反抗更加隐蔽而流动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统治 方式的。所以,社会批判理论离开了空间的控制与地理学的分析只能是抽象的、大而无 当的“屠龙之术”。[3](p.177)
2.一个过度诠释的主题与贡献:空间化本体论
索亚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空间化解释,其第二个步骤是要让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决定 论的这个“无边佛法”中解脱出来,而这是以非常过度地挖掘与夸张地解释马克思社会 生产概念中所潜在的隐存的“空间本体论”内涵为基础的。他自称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 及所谓的后期现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具有分裂性的内爆”[3](p.111)中生发出一种 后现代性批判人文地理学。“这种地理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性理论中继续不断地 吸取灵感,但已经不再局限于其原有的界限。”[3](p.112)它“力求对在历史和历史唯 物主义中的空间意义和意蕴进行重新的登记与定位。”[3](p.113)“正在崛起的是一种 辩证的唯物主义,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与空间的唯物主义”[3](p.120)。
但实际上,索亚并没有直接从马克思文本中读出多少空间本体论思想。他主要还是借 用福柯、伯杰、詹姆逊、特别是列斐伏尔的观点,来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 。试图使传统的历史叙事空间化。这种“空间化转向”不是语言学的或者说地理学的学 科性质上的,而是全面地、本体论化地建构。他甚至因此含蓄地指责哈维,说他天真地 以为,只要在历史的唯物主义中再加上一个形容词“地理的”,就能创立历史地理唯物 主义[3](p.115)。与“存在论”构成一种优先的本质联系的,不是历史性,也不是自然 的地理性,而是空间性。问题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存在与空间”。
索亚心目中的“马克思”,其实是他的老师——晚年的列斐伏尔。列斐伏尔的两个著 名论断,为索亚走向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空间本体论化解释,开了方便之门:一是认 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空间的生产”时代,资本主义何以长盛不衰,关键就是它利用 空间而不断地生产出自己的空间来。二是认为生产关系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存在,其具 体化方式只能是空间的存在。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社会存在,但惟有它们的存 在具有空间性时才会如此。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 于空间。否则它们就会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
索亚的另外一个“马克思”,是把社会生产关系共时性结构性特征本体论化的结构主 义者濮兰查斯。在濮兰查斯看来,空间是社会的母体(matrix),是一种基本的物质框架 (经济基础)而不是单纯的表征方式(上层建筑)。空间与时间的母体创造与转换建立了一 种基本的物质框架,即社会生产的真正来源。他据此进一步发挥说:空间性是一种实体 化了的、并可以辨识的社会产物,是“第二自然”的一部分,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共 存性与具体化,是马克思所谓的商品物化作为抽象社会关系的神秘化的另一种表现。作 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 结果;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具体化/产物,又是社会活动的手段/预先假定/生产者[3]( p.197)。
显而易见,《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不满足于发展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地理理论, 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空间化或都市化,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重心从历 史化转向空间化。索亚不满足于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理论。也反 对轻率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出路在于,既要超越那种排斥 历史唯物主义所有洞察力的过于简单的反马克思主义,又要超越历史决定论的教条主义 。必须大力发展一种新的认知图绘,这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看穿反动的现代主义和 后期现代历史决定论毫无存在必要的面纱,以建立一种政治化的空间意识和一种激进的 空间实践”[3](p.115)。
索亚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是自然—社会—空间本体论三位一体,马克思的社会 再生产理论最终极的本体论框架,是一种先验的空间性时间性与社会性三位一体。但与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照,他肯定是过分突出了生产概念中的空间维度,而牺牲了其更根 本的历史性内涵;只聚焦于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暂时性特征,而有意地模糊了永恒 的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
3.后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本体论批判:批判性区域研究
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及其晚期马克思主义实质,其价值与意义在于,它是对西方马克 思主义后期成果的突破提升,也是对其必然终结的逻辑命运的一种深刻反省。在他看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必然导致一种地理学性质的,即都市化空间化 解释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空间化转向起源于六七十年代城市社会学、区域 研究与世界体系理论之间的争论与融合,并经过了这样一个不自觉的范式转换过程:即 从“对都市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式分析”到“对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的都市化改造”[5]( p.87),从空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6](p.104)。
索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地理学融合所导致的一项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资 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已经引发了‘各种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形成和革新’”[3](p.241)。 而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理论 ,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和哈维的时空压缩与弹性生产理论,是形成后现代地理景 观(geographical landscape)理论的重要里程碑——他称马克思、列宁与曼德尔是“最 敏锐的学者”[3](p.278)。
对于索亚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空间化转向的第一个决定性环节是曼德尔。他发 现:“关键一点是,资本主义……内在地建基于区域或空间的各种不均等,这是资本主 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段。资本主义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的支撑性存 在和极其重要的工具性为先决条件的。”[3](p.162)整个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 的生产能力的等级性结构,而这种等级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是由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所造成 的。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标志是区域不平衡发展(它始终是超额利润的生成与榨取的重 要基础),转变为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格 局,导致新的流动性的国际分工与产业重组。
其次,从哈维的《资本之诸种局限》(1982)一书开始,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更为 广深的发展。哈维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终于发现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人造的自然环境不断 建立与转换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历史、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危机与重建的历史、积 累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均表现为一种地方性的地理景观的历史地理学[3](p.155)。哈维 模仿马克思的语言说,资本主义始终不渝地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一种社会和物质 景观,但由于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到头来只是毫无疑问地在日后某一时刻必须亲手 毁灭掉这个景观。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就是一幕无休止的地理景观舞蹈。
不过,在索亚看来,今天我们所面临着的灵活复杂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控制的 现实,是传统的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的阶级关系概念所无法捕捉与理解的。即使1970年代 的传统城市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亦无 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把握这种神秘莫测的当代城市化重构过程。能够透视晚期资本主义 地理景观变幻之谜的,则是处于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历史决定论三大思潮交汇 点上的“批判性的区域研究”方法[3](p.287)。
由这个新角度看,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呈现如下新的地理景观:金融资本不受地域 限止、更加全球化流动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首次发生于一系列的边缘性国家和 区域,而许多核心国家已经历了广泛的区域性工业衰退。工业与资本的加速的地理流动 性引起了各国政府之间的投资的地域性竞争。各国内区域的劳动分工正相应地发生着剧 变。随之导致高工资/高技术工人与低工资/低技术工人之间的愈益明显的职业两极化, 这加剧了劳工内部的竞争与矛盾。而职业、种族、民族、移民身份、收入、生活方式和 其他与就业相关的可变因素,正在制造愈益严重的区隔现象[3](p.280)。
上述表明,索亚的确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看透了后现代地理景观的资本主 义经济基础,而没有陶醉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激情造反。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化 统治本质及其神秘化的地理构造的批判是深刻的,他对以洛杉矶为象征的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的超级都市空间群体的“中观图绘”方法,是相当精致且有充分说服力的。但他还 是没有挡住后现代诗性想象的诱惑:出于过分强烈地反对历史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需要 ,而生硬地拼凑出的所谓“第三种空间”,正像他承认的,是“亦真亦幻”的、却无具 体的历史地理居所的“云中漫步”。
黑格尔在约200年前曾意味深长地说,现代性辩证法的精髓就是“使固定的思想取得流 动性”,这比“感性存在变成流动的要困难得多”!今天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可谓深谙此 道,但有“以指为月”、“以用为体”之过!他们经常抓住了流动的思想却丢掉了固定 的现实。
收稿日期:2004-06-10
标签:本体论论文; 地理学论文; 决定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马克思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地理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