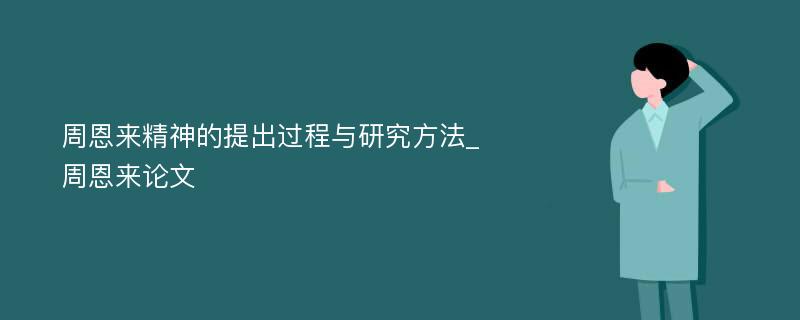
“周恩来精神”的提出过程与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过程论文,精神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精神”研究正在成为周恩来研究的热点。但是,“周恩来精神”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它的含义如何由众说纷纭到达成共识,科学研究“周恩来精神”的方法论原则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还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却对深化“周恩来精神”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一、“周恩来精神”的提出过程
“周恩来精神”的提出经历了由群众自发到学界自觉、由少数人观点到多数人认同的发展过程。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哀痛,有组织或自发性的哀悼活动持续不断,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那种发自内心的哀痛之强烈甚至胜过痛失亲人之悲。人民所悲痛的一是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人物,二是怀念周恩来的伟大人格。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致的悼词,充分肯定了他的高尚品质,认为“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这一评价为提出“周恩来精神”提供了最初的依据。
从周恩来去世到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第一次全国周恩来研究学术研讨会召开前,这一时期主要以缅怀和回忆周恩来的生平、业绩为主,在这些数量惊人的纪念文章中,大多数都涉及对周恩来高尚的人格、风范和品德的赞美。在一些文章中、甚至在群众中开始出现“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说不尽的周恩来,研究不完的毛泽东”等说法。“周恩来精神”由群众自发到学界自觉以及由具体上升到抽象概括的端倪开始出现。
从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第一次全国周恩来研究学术研讨会起,由感性的怀念文章开始向理性研究升华,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周恩来人格风范个别方面的赞誉,而是感到周恩来身上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强烈地吸引着人们。从我们占有的资料看,最早提出“周恩来精神”的是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刘济生,他在《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3期发表了《论周恩来精神》一文,在2001年出版的《解读周恩来》一书中还单独辟一篇论述周恩来精神。1992年,石仲泉的《周恩来的卓越贡献》一书在对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比较研究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各位老一辈革命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相对而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影响更大一些,如果拿这两位伟人相比较,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其思想,周恩来影响最大的是其精神。他在其稍后的著述中将“周恩来的精神”直接简化为“周恩来精神”(当然,学界有人认为“周恩来的精神”与“周恩来精神”两个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前者主要是指周恩来个人独有的精神,后者主要侧重于以周恩来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精神。这种区别实质上是为了强调“周恩来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精神的联系,强调其普遍性。),并将“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八个方面:无我精神、求是精神、创新精神、民主精神、廉洁精神、严细精神、守纪精神和牺牲精神。应当说,如果从影响角度看,石仲泉的观点影响更大。与此同时,国内还有不少学者也不约而同地提出“周恩来精神”的概念,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概括。
对周恩来的怀念与研究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冷,反而越来越热,到了1998年周恩来百年诞辰的时候,周恩来研究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而这一新高潮的突出理论成果就是“周恩来精神”之说被人们普遍接受。如果说1998年之前关于“周恩来精神”的概念还只是少数学者坚持的观点,那么,到了周恩来百年诞辰的时候,它最终成为人们的共识。“周恩来精神”研究的高潮和形成共识的重要标志是梁衡1998年在《职工天地》发表的长文《大无大有周恩来: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他虽然没有用“周恩来精神”一词,但通篇的主线就是“周恩来精神”。因为周恩来的“六无”(一无是死不留灰,二无是生而无后,三无是官而不显,四无是党而不私,五无是劳而无怨,六无是去不留言)的核心是“无私”。他甚至认为,正是周恩来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称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养护者”。对周恩来作“大无大有”的概括,引起了人们情感的强烈共鸣,该文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民众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重庆中共党史学会联合在重庆举行了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收集了7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直接或间接论述“周恩来精神”的文章达50余篇。另外,周恩来故乡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还专门开辟了“周恩来精神”研究栏目,上述文集和专栏成为研究“周恩来精神”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和阵地。
1998年,江泽民在周恩来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作了讲话,他不仅回顾了周恩来一生的伟大贡献,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周恩来的精神”这一概念,并对这一精神的源泉和深远意义作了深刻分析。
二、“周恩来精神”的含义
学界在提出“周恩来精神”之初,并没有在“周恩来精神”的内涵上深究,主要侧重于描述性地概括“周恩来精神”的具体内容,即便有些论著涉及“周恩来精神”的内涵,也主要偏重于道德人格方面,如有学者认为:“人们把周恩来身上充分展示的以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道德风范亲切地称为周恩来精神。”[1](p.243)这一理解既具有代表性,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们感到,古今中外伟人并不少见,可为什么只有周恩来能得到人民那样最真诚的敬仰和深切的怀念?这不仅是因为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是因为他具有连他的政敌都不得不敬仰的高尚的品德,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的楷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是中华传统美德的范型。“周恩来精神”正是对周恩来这些特殊贡献的恰当概括。即使不太赞成把“周恩来精神”作纯粹道德化理解的石仲泉很多时候也还是从道德角度来理解“周恩来精神”,他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周恩来精神’是共产党人党性的道德精华和民族性的道德精华的高度统一。”[1](p.24)
随着对“周恩来精神”内涵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认识到,“周恩来精神”不仅有道德品格方面的内容,还有智慧、个性、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内容。甚至有人从主体角度来考察,将“周恩来精神”扩展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革命精神的总和,不完全局限在从周恩来一人独有的视角来研究“周恩来精神”。这种理解主要是为了避免把周恩来神化和偶像化,以利于研究和宣传“周恩来精神”。为此,在重庆举行的“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讨会上,出现了“周恩来精神”与“周恩来的精神”的不同概念之争。一种意见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和高尚道德的结晶,是集体精神风范的产物,由于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精神的化身和楷模,所以,用周恩来的名字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就叫“周恩来精神”。而“周恩来的精神”则是指周恩来个人的,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光辉形象典范的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2]另一种意见不赞成这种区分,认为没有必要在“周恩来精神”与“周恩来的精神”之间抠字眼,不能过于强调“周恩来精神”的集体性,否则就没有办法具体研究“周恩来精神”,即使概括出其具体内容,也失去了其个性魅力和感染力,不利于人们学习周恩来的精神品质。因此,“周恩来精神”应当特指周恩来个人的精神品质。后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笔者也赞成把“周恩来精神”作狭义的理解,突出强调周恩来这一特殊的主体。
对“周恩来精神”理解的扩展和深化,为“周恩来精神”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促使人们思考,要真正准确科学地理解和界定“周恩来精神”,首先必须准确地把握“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其次还必须将“精神”定位于一个实在的主体,即周恩来,如果完全离开了周恩来这一具体的主体,所谓的“周恩来精神”就变得虚化了,也丧失了其感染力和吸引力。假如为了避免把周恩来神化,强调“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精神的结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周恩来精神”这一概念的内涵来看,必须把它定格在周恩来这一特殊的主体上。
“精神”与人格和风范有着一定的关系,所以,人们常常是将这三个概念混用,但细究其含义,这三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和不同。风范与风度、气派同义,是指具体而美好的行为举止。人格广义上是指人的性格、气质和能力等特征的总和,狭义上是指人的道德品质。风范是人格的外在表现,人格是风范的内在根据。所以,应当通过周恩来的风范表现来揭示其人格特征和魅力。
关于“精神”,有一种观点认为,精神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总体性哲学范畴,它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认知”,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在“知”的过程中沉淀出人的智慧,建立起人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二是“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特别是对人的态度,其目标是“爱”。“情感”造就出人的高尚情操。三是“意志”,是人们改造外部世界和改造人自己的决断和志趣,体现为为某种目标奋斗的顽强意志力。因此,“精神”是理智、情感和意志三者的辩证统一。因此有学者将“周恩来精神”界定为:周恩来在理想和智慧、情感和品德、意志和操守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美好品质的总和。它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是以为人民服务价值原则为核心的热爱人民、团结同志、真诚待人的人文精神:三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为目标,努力奋斗、严于律己的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3]
上述对“精神”的理解虽不无道理,但笔者以为,这里的“精神”主要不是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广义概念,而是狭义的价值范畴。生活中有许多特有的精神,如延安精神、雷锋精神和长征精神等,这里的精神是指一种价值观、价值理念或价值理想。“周恩来精神”与这些精神是同类的范畴。精神以其价值属性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值得人们去追求与学习。从宏观层面看,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对一个政党来说,它是由政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从微观层面看,精神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政治立场、方法论以及意志品德等诸多因素经提炼后的综合反映。
基于对精神的这一理解,有学者将“周恩来精神”定义为:周恩来在其奋斗的事业和社会生活及个人言行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想、思想、道德、意志、品格和作风的精髓之总和,是他深邃思想、坚强党性、过人智慧、高尚人格、优良作风之集大成。“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类似的总体性范畴。”[4]还有学者认为,“周恩来精神”“是指带有周恩来个人鲜明色彩的,区别于其他一般领袖的,在他的伟大实践中、日常生活和言论著作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风采,一种在他身上始终体现出来的风范,一种能催人向上的魅力,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5]对“周恩来精神”的这两种理解是深刻的,但不够简洁,也未能点出其实质。另有学者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统一,是共产党人理想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永恒的价值。”[6]严格地说,这也不是对“周恩来精神”的定义,而是对其源泉和价值所作的较为准确的判断。
综上述理解之所长,笔者认为,可以对“周恩来精神”作如下界定:“周恩来精神”是由周恩来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理想追求、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和工作作风等所体现出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崇高价值理念和信仰。“周恩来精神”的具体内容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渐丰富,但“周恩来精神”作为概念,如果外延过窄将流于片面,但若外延过宽又容易泛化,显示不出其特点。“周恩来精神”不同于周恩来的某一品质或观念,而是统摄其一生言行的价值理念和最高信仰,这种崇高的价值信仰又具体而生动地体现在周恩来的理想追求、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和工作作风上。
即便学术界对什么是“周恩来精神”的具体理解有所不同,但在对其实质和核心的理解上却非常一致,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去世所佩戴的胸章就是“为人民服务”,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苦撑危局时也曾说过,他的一生只有八个大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最高的价值信仰,是“周恩来精神”的真谛。在周恩来诞辰105周年之际,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委和淮阴师范学院联合召开了以“周恩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楷模”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并将与会论文汇编出版,即《周恩来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楷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对“周恩来精神”研究的又一次升华,该论文集产生了较大影响。周恩来一生之所以能不折不扣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宗旨,是基于以下两个朴素的真理性认识:一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民是党的力量之源泉这一伟大真理:二是他认为唯有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在周恩来看来,当好人民的勤务员、任劳任怨地辛勤工作是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途径。
三、“周恩来精神”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的确立是研究任何问题的前提条件,不同的研究对象应当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周恩来精神”必须要解决好方法论问题,这一点学界关注不够,这也是“周恩来精神”所涉及的具体内容难以形成共识的重要原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但仅有这一方法论原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在这一前提下选择具体的方法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体系有所侧重和细化。笔者认为,以下两种具体方法是研究“周恩来精神”的主要方法:
(一)实践和思想相结合的方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周恩来精神”主要应当从周恩来本人的实践中来研究,如果以言论为主来研究,那是纯思想研究,而不是精神研究,侧重于言论研究就容易研究出假精神来。[7](p.120)从一般意义讲,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思想与行动是有差距的,一个人未必时时都能做到言为心声、言行一致。只要我们能够从总体上把握一个人的人格品质,再根据具体历史背景分析某一言行的原因,就不难分清言行的真假来。况且,从一个人的一生来看,其思想与行动是基本一致或统一的。
选择研究方法还要因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周恩来这样一位伟人——有人称其为“中华高德伟人”、“中华千年一巨人”等,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实践和思想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不能单一地依赖周恩来的实践(简称实践研究法)或周恩来的思想(简称思想研究法)。这主要是因为,周恩来是言行一致的模范。周恩来是具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实事求是、说真话、做实事、身体力行和言行一致的精神是人们公认的。诚然,精神作为价值范畴主要体现于实践中,因此,特别要关注周恩来的实践活动,从中提炼出周恩来的精神是研究“周恩来精神”的根本途径。大凡与周恩来交往过或听过他讲话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他的讲话实在而真诚、亲切而温暖,决无让人烦心的大话空话,言为心声,人们想听,有感触受启发。基于周恩来始终能够保持言行一致的可贵品质,我们在研究“周恩来精神”时,就必须同时关注其思想,不能忽视对其言论与思想的研究,否则就是不全面的。由于我们是以其思想来佐证和提升其行为,因而,注重其思想不会将“周恩来精神”研究变成周恩来思想研究。这些年来,人们普遍感到,有许多周恩来研究(包括“周恩来精神”研究)的文章没有足够的“研究”色彩,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过于关注和停留在个别性的具体事例中,这使得“周恩来精神”研究常常变成了事例的简单重复,既缺乏历史的生动,又缺乏理性的深刻。实践和事例虽然具有生动的特点,但它毕竟是感性的具体,是个别的和不全面的现象,必须通过理性抽象才能上升到理性具体,从而把握其本质。周恩来的大多数言论是有准备的、理性的和深思熟虑的,代表了他本人的真实思想,因此,它更深刻而全面。换言之,从人的一生来看,其言与行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不应以周恩来的只言片语否定其精神品格的伟大。总之,立足于周恩来的实践,结合其思想观念,是研究“周恩来精神”的重要方法。
(二)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
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要求我们在研究“周恩来精神”时,一要关注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如此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在周恩来一人身上,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应当避免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或一叶障目或以偏概全。二要注意抓住“周恩来精神”的重点、实质或核心内容。正是由于“周恩来精神”的内容是宏大的体系,就必须要理出其中的红线和最主要的东西,抓住突出的特点,不能把它搞成大杂烩和大拼盘,不分主次地将什么内容都纳入其中,如果这样,就显现不出“周恩来精神”的特色。在分析周恩来身上的多重性格、个性时,在把握其优缺点时,都要看其占主导性的方面。例如,他偶尔的雷霆之怒不能否定其温文尔雅的个性:他偶尔说过一些违心话、办过一些错事,但不能否定其一生品格的伟大。总之,从实践和思想相结合并以实践为主把握周恩来的精神,从整体中把握周恩来精神的体系性,从主导方面把握周恩来的精神品格,这是研究“周恩来精神”应当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