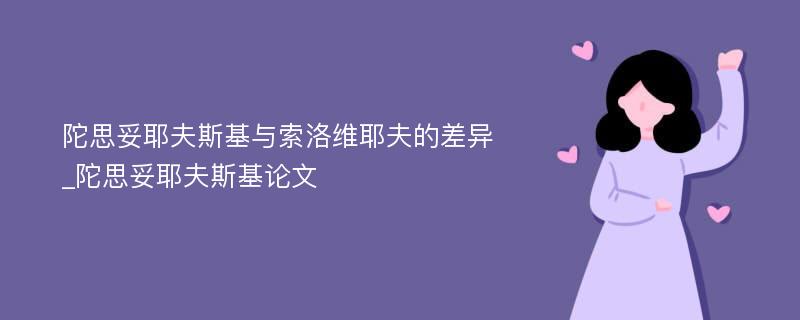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的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基论文,分歧论文,耶夫论文,洛维论文,陀思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离世,曾经在精神上有点儿从属于他的弗·索洛维约夫① 就迅速地、坚决地与他分道扬镳。从这位已故哲学家《文集》第三卷中的几篇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这次分道的最初几步。他的基本的动机是什么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最优秀、最辉煌的篇章中,向读者吹来了一些美梦——全宇宙的和谐、人与人是兄弟、各民族是兄弟、大地上的居民同供养他的大地与天空的和谐;《荒唐人的梦》(见《作家日记》)和长篇小说《少年》中的某些地方,让人们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那颗心,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触摸到了这些和谐的奥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荣誉一半就建筑在这些光辉的篇章上,另一半奠基于他那著名的“心理分析”上,——《罪与罚》为此提供了即使不是最好也是最著名的例证。对一个直率的、简短的问题:“为什么您那么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俄罗斯如此尊敬他?”任何人都会简短地、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这是俄罗斯最富有洞察力的人,也是最慈爱的人。”慈爱和睿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顶桂冠,伴着它们却留下了更多的疑问。
这种狂热的慈爱的表白,一处是在《群魔》中,他说:“我为一切祈祷;那里是一个蜘蛛在墙上爬——我也为它祈祷。”蜘蛛,这是某种丑恶的东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源于他自身的慈爱的力量,克服了丑恶本身,以川流不息的心理之光驱散了所有的黑暗,而且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太阳,高处于恶与善之上”,他也打碎了善与恶的藩篱,重新感觉到大自然和世界是无罪的,即使在它们最丑恶之处。在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这种“和谐”的瞬间,“和谐”——罪恶从世界上抹去,而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赎罪的世界的奥秘,关于这个世界我们说了很多空洞无味的废话,实质上却丝毫不知道也不理解对世界而言究竟什么是“赎罪的”。这种“赎罪性”的形而上的秘密,我们只是口头上知道,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了,或至少是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敞开了一会儿。在那些敞开了这一秘密、构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面名声的篇章,他提出了自己的“正题”,而另外的、常常是很阴暗的篇章则培养了他乃至一般人类心灵的现代文化的很多“反题”(《地下室手记》、《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
构成“黑暗陀思妥耶夫斯基”中“一线白光”的,差不多跟我们熟知的普通“白光”的构成一样复杂。首先包括“基督形象”。还在少年时期他就像对待不容争辩的天堂美景一般对待这一形象,以此检查所有可疑的、世俗的东西。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中的基督,掺入了他个人的独特的杂质;也许,他对基督的感觉,与我们大家、与东正教的普通的神甫略微有点儿别样;正是因为他比我们更切近生活,不像我们那样不切实际和书生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谐”的第二部分是他的俄罗斯民族感情,几乎是平民的感情(《作家日记》中的《农夫马列伊》、《百岁老妪》以及该处的某些议论)。在他生命的终点,他对普希金和我国有教养阶层的最好部分连同他们的“宇宙的同情心和再体现能力”的态度与这种感情汇流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民族的这种感受与上文提到的已经极端生活化了基督的感受,不可分割地汇合在一起。“我们(且只有我们)的民族——接受了基督——因此它就”,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式和经常的解释。对他而言,“东正教”、“基督”、“俄罗斯民族”汇合得如此紧密,以致可以运用一个名词代替另外的名词;且这不是以公开说出的形式,而是以神秘的方式。如众所知,在俄罗斯民间存在着一个教派,除了被本丢·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外,还承认许多体现在大地上的“基督”和“圣母”,满怀敬仰地对待他们,就像对待那一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俄罗斯的“民族-上帝”(《群魔》)的奇妙的、富有表现力的篇章中,我们几乎得到了这种民间神话信仰的一个天才的、知识分子的变体。同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及其富有预见力的、热情洋溢的创作中,差不多给了我们一把破解这个黑暗的俄罗斯教派的心理学钥匙。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光”的第三部分存在着泛神论,但这不是客观的、艺术的泛神论(如歌德那样),而是主观-宗教的、精神-道德的泛神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说“我欣赏蜘蛛”、“我从它身上观察大自然的智慧并且研究它”,而是简短和更加有力的“我为它祈祷”。这大概既是科学,也是欣赏,但它们隐在后面并被遗忘了,而表面上的则是甜蜜的祈祷,狂热。他创办的《作家日记》以《论大熊星座》这样一篇评论开头,对于政论家有点儿奇怪,对于记者则过分高调。这是鞭身教特色的腔调,因为我们的鞭身派尽管有其“精神本性”并坚定地向着基督迈进,传教士们还是跟前基督教的多神教紧密联系着。这里就是根据。我们已经指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佐西马长老身上,星星比修道院的章程、森林的完善、“恶者和善者都呼吸着”的清晨空气的仁慈,起着更多的作用。我们一般并不识别自己身上的宗教性动机,而一旦弄清了它们,追踪了甚至是伟大苦修者的心灵,你就会一层层地深入发现几乎一整卷“宗教故事”,有最古老的,也有最新的。谁能向我解释,为什么阿西西的方济各② 和他那类型的人,只能在荒漠、山岩、洞穴、百年古松之间生长,苦修者一旦进入城市,就开始残酷、严肃、简短、兴奋地行动和说话。穿着阿西西的方济各穿过这些法衣,我们在托克维玛德③面前战战兢兢。聚集在森林、加利利的古老的“圣林”中以及比利牛斯、亚平宁、阿陀斯④ 等荒山上的修道院,塑造了整个基督教、它的全部的精神和气味。城市则导致职级间口角、权力、律法和令人厌倦的学究式争吵。这就是尼康⑤ 和谢尔基·拉多涅什斯基⑥ 之间、阿西西的方济各和英诺森三世⑦ 之间、梵蒂冈和诸如森林中的罗斯之间的界限。
索洛维约夫思想(和感情)上完全深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和谐”,未分辨其中我们已指出的这些复杂因素;把它作为真正的历史上的基督教的表现和使命接受下来,要求(可以说)偿清它的巨额期票。在其以后全部神学家-政论家的活动中,他就像一个不很受欢迎的法警一样,手拿文件夹绕着富人的住宅奔走忙碌,但怎么也没能让人们打开小窗子,扔给他一块新鲜出炉的面包。
“从远处还可以爱邻人,但从近处——绝不!永远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处地方(《卡拉马佐夫兄弟》)喊叫道。在这可悲的自白中说出了自己乃至其创作的深刻界限和局限性。他的光辉篇章被编入了他的无限昏暗的卷帙之中。他“为蜘蛛祈祷”。 看他怎样对待蜘蛛的吧。即使不是蜘蛛,而是哪怕波兰人,——毕竟不是蜘蛛式的民族。尽管这是发展不够充分的人的类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从他们——酒鬼和骗子列别德金大尉(《群魔》)和格鲁申卡、米坚卡·卡拉马佐夫身上找到了无罪的人的特征。最好是抛开民族身份,那样就只有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因而性格变态的人,最好是抛开他本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讲得如此精彩的那个拯救和坦白的“洋葱头”。但就连“洋葱头”他也没有抛开。他抛出了两个波兰人身份的赌棍和面首(《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没有多说什么,就扭头而去。瞧,又是天主教在作怪。我不能不在此作为最需要的片段来引述两三句话,那是真正善良的、即使在近处也善良的斯特拉霍夫⑧ 富有远见地扔给我的。我在一篇长篇论文中比较了三种宗教,我们的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结束文章时描述了我们外省一个普通教堂里的彻夜祈祷,一些老头和老太太来到教堂祷告,带着那种真正信仰的天真烂漫和热情,“这信仰在西方都已丧失了”。首先我描写的是我亲身了解的东西。是呀,所有的俄罗斯人在谈到自己的信仰相对于其他信仰的优越性时,都会坚决地、直截了当地回答:
“我们的信仰是真正的信仰,其中没有道德的戏谑,也没有智慧的滥用,只有对待上帝的淳朴的、恭顺的态度。我们的祈祷是热情的,而期望是牢不可破的。”总之,谁仔细观察了“俄罗斯信仰的实质”,发现了或将会发现它跟“信仰的俄罗斯的实质”不可分割,发现或将会发现,正是俄罗斯人的恭顺的身影而非教条,构成了“东正教信仰区别于其他信仰的优点”。实质上,“关于教会分别”的神学议论包含着跟“种族分别”差不多的道德激情,每个民族都就其“根本特征”无限地赞美自己的民族。俄罗斯民族的、“从而也就是东正教”的根本特征,就是恭顺。读了这篇文章也就明白了,在这里引用的地方蕴含着我为自己的信仰骄傲并且蔑视其他信仰的首要的根据。斯特拉霍夫向我指了出来,并摇着头说:
“哎,瓦·瓦,这些恭顺的、带着这样的热情和淳朴、完全沉浸在祈祷中的老太太,——难道您认为,在新教和天主教中她们就不存在吗?到施瓦茨瓦尔德⑨、到提罗尔⑩ 去看看吧;那就……”,于是他挥了一下手。这几句话,开头我是机械地听着的,但实质上,其中包含着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也正是从此出发,最好应该开始关于“教会合一”的讨论,将教条的差别和等级的竞争撇在一边。如果有一天人们断定基督教世界应该合并,那么它将会是出自人民大众的合并,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合并的基础就是斯特拉霍夫的那条简单的真理(我们将接着巩固这一荣誉)——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东正教徒同样地对待基督,同样为基督而感动,同样向基督祈祷。因而,祈祷也就是每个俄罗斯人拥护每个波兰人、通常的天主教徒,拥护每个德国人和路德派新教徒的基础和土壤。各民族的心灵世界或早或晚被引到了集体和等级,宗教信条也是如此;宗教信条引起了如何对待最基础方面的差别、其实也就是如何对待宗教哲学的问题,恰如对待存在于信仰的仪式、传统、习俗中的差别。不需要汇合、一致。在《启示录》中,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站着并祈祷的,不是一种动物,而是四种动物——鹰、狮子、牛、人。为什么这不是指点、不是“启示”呢?上帝不需要一致的祈祷,上帝本身想看到各民族的人们穿着各种花样的、五彩缤纷的服装走向他,用无数的语言和无数种逻辑对他说话。在信仰差别和语言差别的基础上,建立了民族学的差别。而信仰就是那种大自然的色彩,不可消灭的species fidei[真实的外貌],正如任何一种口音一样。如果在基督中,所有的欧洲人此时已经和解了,那么将来,在伸展于“善恶之上”的天父之中,欧洲人也该和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和解,他们跟我们一样在“太阳西沉”的时刻,对着“夜晚之光”祈祷,带着恐惧向上帝祈祷。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基于血缘和心理上的差别很难理解和“内心里接受”罗马的司祭或博学的新教牧师,那么我们就更难——几乎不可能——明白叙利亚人、阿拉伯人身上的任何东西。但这是我们作为西纽斯、特鲁沃尔、留里克(11) 的后裔的界限,而不是人类——亚当的后裔的界限。
在那个时期——90年代中期的争论中,我不得不参与了跟索洛维约夫的论战。
当时我感觉到(这差不多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印象),东正教是一个古老的、安静的老太太,失去了力量、青春和美貌,但拥有伟大的过去,而主要的是她从未伤害过什么人;这不,从她身边走过来几个养得肥肥胖胖的、为当日的新鲜空气而幸福的绅士们,诸如恰达耶夫、索洛维约夫和我们所有的自由主义者,碰到了她,用胳膊肘稍稍撞伤了她,不仅不是出于无心,而且甚至是恶意的。对我而言,“东正教”一词总是简单地意味着“圣餐时教民的教堂”;我爱她,那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在此受到侮辱的独一无二的、唯一的地方。我常常去看教会场所,总是站在那儿,思考:“到处都有人们的分别,到处都有聪慧与恶意、高贵与卑贱、知识与蒙昧,而且到处都有人受辱:门徒被师傅、农夫被地主、官员被上司羞辱。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受了侮辱的人来到这里,他就不会再感觉自己是个受侮辱者,而且谁也不会那样看待他,而他就像跟天使和上帝在一起,高于并远离自己的侮辱者。”教堂作为“没有侮辱”的地方,是我许多年来的幻觉(现在我这样想)、灵感、精神振奋的源泉。
与此同时,索洛维约夫(据我观察)却根本没去过教堂,他所注意的是“历史性的事件”,正如他常常表白的那样。在此情形下,我感觉到自己的行动就像一个背着背包的士兵,而他则是军事家和统帅,满脑子战略地形。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即使没有什么现实的理由,也足以导致争吵和意见分歧。被“世界和谐”的理念所激动的索洛维约夫,领导了宗教的、教会的问题,但首先,他是把它作为联合的问题而非和解的问题,其次,他期望这种联合来自吵翻了的教派(职位等级),是自上而下的,贵族式的。他幻想着唯一的(统一的)基督教组织(“一种动物在上帝的宝座前”,《启示录》),而不是把基督教作为信仰的果园。在这里他作了很多发明,把很多新的世界观挤入了对象,但在总体上他却遭受了失败,并以在他的“和谐”范围内“持不同思想者”的激动气愤和例外而结束,——其中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者在所有非俄罗斯民族(波兰人、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身上看到了滑稽可笑或犯罪。他开始于“为蜘蛛祈祷”,结束于怀疑和中伤,似乎天主教屈服于撒旦,是“撒旦反对基督的阴谋”(《宗教大法官传奇》),结尾是一篇非常阴郁的坦白,——“不可能避开这样的阴谋”(《传奇》的结尾,基督亲吻了宗教大法官)。索洛维约夫没有像基督这样宽宥任何人,至少在他生前,天主教与东正教世界的关系大概也未必没有尖锐化到像围绕教会合并而斗争的时代那样紧张激烈,而这(教会合并)正是有赖于他的努力。但是从索洛维约夫的著作中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后果:他动摇了我们的status quo[某种状况],克服了霍米亚科夫(12) 的寂静主义学派。他将我们的宗教界本身引向了沉思、自我分析,使我们丧失了过度自信和宁静。他发现了——这是他的重要功勋——对教会的永恒的道德革新而言最严肃的道德动机。可以认为,霍米亚科夫学派和一般旧的斯拉夫分子被索洛维约夫摧毁和消灭了,索洛维约夫依据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因,指出了西方的那个真理:它1)思考,2)痛苦,3)探索,而东方只是4)睡觉。但这个梦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教条主义的美德。问题在于,被列入西方的“傲慢和自大”恰恰出现在富人中间的东方老太太口袋里,她像古代的第欧根尼的追随者一样,炫耀着自己衣裙上的破洞。譬如我们的分裂,譬如我们的其他弊端,它们是那么明显,明显得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我们简直没有做任何努力以消除它们。我们是历史性的懒人。而这种懒惰被抬高成为教条,几乎被认作黄金的东方区别于锡制的西方的主要特征。活跃、刚毅、孜孜不倦的,永远在睿智地耕耘着的索洛维约夫,终止了这种懒惰。这是他的伟大的历史性功勋,是他的八卷著作、他的“opera omnia”[全部优秀著作]的“辩护”(他写了《善的辩护》一书)。
遗憾的是,索洛维约夫向着人类心理的所有伟大的混合——实质上也是人类历史的混合——走去,走得过分简单和无足轻重,就像一个拿着执行单的法警。他直截了当地、明确地传唤“能够在一切方面再变形”的俄罗斯,——顺便说说,哪怕一下子变形成为天主教徒。他被报以残酷的讥笑和弃绝。由此甚至开始减少了他的荣誉,降低了他的威望。但不得不承认,他身上所拥有的东西,也是斯特拉霍夫所拥有的东西,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根本没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擅于以“天使之爱”爱邻人,如果这个邻人站在无限遥远的远方的话;而斯特拉霍夫却知道对站在近处的邻人的小爱的奥秘,索洛维约夫也知道这一奥秘并且据此支付了期票(这是主要的)。在其最悲惨的时期,当他被在自己“心里与全世界和解”的“再变形者”(这是得到斯拉夫分子赞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念)的箭矢彻底伤害的时候,他不是深刻地、热烈地、天才地,然而却是真诚地与天主教和天主教徒、新教和新教徒和解了。在生命的终点,当弥留之际,他说他放弃在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和解的尝试,作为一个忠诚的东正教徒而死去。因此,他的具有强烈的天主教色彩的嫌疑就自动消失了。他没有承担好基督教教会统帅的角色。但他第一个完成了纯粹基督徒的伟大事业他从自己的内心挤出了“信仰分裂”的黑色血滴,主观上期望不与任何人分裂而与全人类和解。
全部这个时期在俄罗斯文学中一闪而过,而现在看来,我们只能回忆他,而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始的事业的现实后果中研究他。索洛维约夫的最优秀的特点是他的真正美好的愿望;他在自己的文学活动中也试图实现某些善良的心愿,但却极其不成功。我们从他身上丝毫看不到对恰达耶夫的重复。将他与恰达耶夫混为一谈,在他生前是经常的,而且看来对他极为有害。但恰达耶夫是个骄傲的、傲慢的智者,在表现能力尤其是文学表现力方面有惊人的天才,却属于空虚的人(据有关他的某些回忆录判断)。索洛维约夫与他的做作的、优雅的、昙花一现的形象很少有共同之处,而是确确实实为了伟大的使命辛勤劳作、持之以恒、从不退缩的人,而且其优雅的文学形式也少得多。总之,上帝没有给他力量,但给了他善良的心愿。我们再回到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回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个哲学家站在神秘主义小说家旁边,就像芦苇站在橡树旁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自己感染人,而不供养人。这种感染人的、迷人的力量,是索洛维约夫完全没有的(除了所谓天真质朴方面),他过分的理性化,朴实,内在的平庸乏味(与外表的诗意相矛盾)。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感染人”,但这并非责备他、评判他身上的不好的东西。在他的理念中,在他的独特的语言中,在他辉煌的篇章中,散发着香味,还是香味,但却没有面包,必需的、适宜的、合用的。出自他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可以利用的。要是有人深入了他所发现的“赫斯珀里得斯的果园(13)”,尽情呼吸非本土的、非俄罗斯的芬芳气息,一旦走出来回到俄罗斯现实的场所,将只会带着头痛,带着一颗饱受折磨的心。在他那儿,一切都从伟大的和解开始;但它们沿着弯曲的抛物线前进,一切都以伟大的隔绝结束。向所有的人张开怀抱,结果却是把所有的人都推了出去。始于无限的广阔——终于无限窒闷的狭小;终于某个卡别尔纳乌莫夫家(《罪与罚》)的盲目狂热迷恋,在这个家里,“他本人口吃,而且他的九个孩子都口吃,就连他的小姨子也口吃”,——不知怎么的,这一切不仅很好,而且还差不多非常适合向全世界展览。我们的片面性,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还从佐西马长老、从阿辽沙·卡拉马佐夫身上为自己找到很多解释。索洛维约夫召唤我们从睡梦中真正的苏醒过来,直接侮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请回忆一下,他由于列文(《安娜·卡列尼娜》)在寻觅、在为之激动不安的东西,是怎样地激动起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抛物线”的次要的、否定的这一半,表现得多么强有力,正像它的第一半、像他的“正题”一样有力。索洛维约夫更朴实、更理性、更乏味。他身上没有任何麻醉,他也没有呼吸任何“非人间的百合花”。但在他的心里,确实活跃着一些善良的感情,非常适用、极为可行的正确的愿望。他不是天才,但却是俄罗斯大地上的一个好的工作者,在最高的程度上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的理想,对待自己的故土。通常关于他的意见差不多都是与真实相矛盾的;在他身上存在着某种恶魔的、“非凡的”、狡猾的同时也是强有力的东西。一切完全相反。
注释:
①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哲学家,诗人,政论家,主张东西方教会整合统一。——译者注
② 阿西西的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1182-1226),天主教圣徒,天主教托钵修会圣方济各会的创立者。——译者注
③ 托克维玛德(Tomás de 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宗教裁判制度的奠基人,首位宗教大法官。——译者注
④ 阿陀斯山(Athos),基督教历史上的圣山,在希腊东北部。——译者注
⑤ 尼康(1605-1681),俄国人,1652年起任东正教莫斯科牧首。——译者注
⑥ 谢尔基·拉多涅什斯基(1314-1392),莫斯科东正教会修士,莫斯科三一修道院的创立者。1452年封圣。——译者注
⑦ 英诺森三世(Innocentius PP.Ⅲ,1161-1216),俗名罗塔里奥,生于意大利,1198-1216年为罗马教皇。——译者注
⑧ 斯特拉霍夫(1828-1896),俄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⑨ 施瓦茨瓦尔德(Schwarzwald),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巴登——威登堡州。——译者注
⑩ 提罗尔(Tirol),中欧的历史地名,位于阿尔卑斯山东部地区,中世纪曾为独立的伯国伯爵领地,包括现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等地区。——译者注
(11) 传说中俄罗斯国家的创立者。据编年史,862年留里克成为统治诺夫哥罗德的公爵,他的两个兄弟西纽斯和特鲁沃尔分别统治白湖和伊兹波尔斯克,两年后二人去世,留里克成为唯一的统治者。——译者注
(12) 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哲学家,斯拉夫主义者。——译者注
(13) 古希腊神话:地母盖亚将金苹果送给了赫拉和宙斯作为结婚礼物,赫斯珀里得斯(Hesperides)姊妹是看守金苹果的仙女。——译者注
标签: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 东正教论文; 基督教论文; 索洛维约夫论文; 俄罗斯民族论文; 罪与罚论文; 群魔论文; 耶稣论文; 天主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