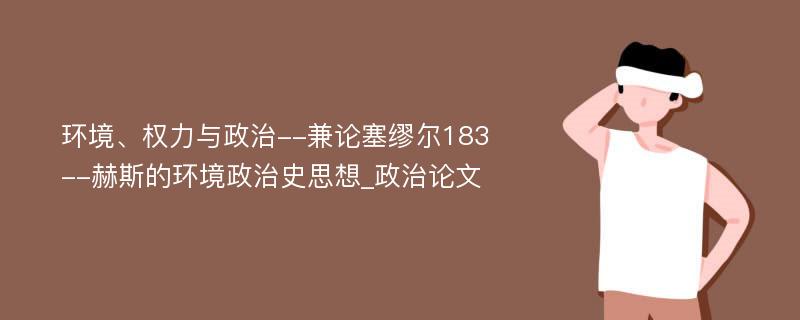
环境、权力与政治——论塞缪尔#183;黑斯的环境政治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环境论文,权力论文,思想论文,塞缪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3-0144-06
环境问题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内部包含着诸多环境主体及相关因素,这就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入其学术界域提供了前提。从环境史的研究成果看,也确实如此,研究者们结合自身的兴趣,在各自问题意识的指导下,从不同的维度和层级展开了相关理论的构建和实证研究。笔者认为环境史和政治史的研究同样可以公度,塞缪尔·黑斯的环境政治史研究为二者的结合展示了深厚的史学渊源,从史学演进的角度为环境政治史研究提供了合法性证明。本文将在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其有关环境政治史研究的理论思考,以更好地指导我们相关学者的研究。
一、黑斯的生平与治学经历
塞缪尔·黑斯(Samuel P.Hays),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杰出贡献教授(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他在城市史、社会史、政治史和环境史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不仅涉及面广,而且著述丰厚。比较而言,其建树最大的当属环境政治史研究。可以说,黑斯是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为环境政治史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而且与其实证研究相比,其理论构建的意义更大。以下将在梳理他的人生经历和治学历程的基础上,勾勒其理论观点,以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史学史基础。
塞缪尔·黑斯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小镇科利顿(Corydon)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自小就与土地、森林和河流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拥有360英亩的格恩西奶牛农场(Guernsey dairy farm),他自己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自然保护区。基于农场的经历,黑斯接触的第一个政府机构是土壤保护局(the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SCS)。20世纪40年代初他短暂供职于西俄勒冈地区的一个森林管理机构,同时还参加了两次贵格会劳动夏令营(Quaker work camp),这使得他对田纳西流域和密西西比河有了初步的了解。1943-1946年他供职于俄勒冈和加州再生土地管理局(the Oregon and California Revested Lands Administration)。
与此同时,黑斯开始注重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并渐渐对学术产生了兴趣。他通过阅读林业局(the U.S.Forest Service)的大量文献,写成了一系列有关林业管理的文章,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他新近出版的著作《森林中的战争》①。在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求学期间,他先后学习过哲学、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派强调感知在理解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对他日后的研究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1943年春,丹尼尔·布尔斯汀(Daniel Boorstin)教授的《现代欧洲史》课程将他引入历史学的殿堂,特别是布尔斯汀教授对独立思考精神的提倡,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术旨趣。考虑到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专长,他在该学院教师弗雷德·托勒斯(Fred Tolles)的鼓励下,来到哈佛大学,师从弗里德里克·默克(Frederick Merk)教授,于1948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②。
在黑斯确定其博士论文的选题时,西奥多·罗斯福纪念协会(Theodore Roosevelt Memorial Association)提供了一笔研究基金(fellowship),唯一的要求是论文要与其生活的某个方面相关。默克认为他的资源保护政策是一个好的选题,黑斯欣然接受导师的建议,在1951-1953年间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并在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人们熟知的《资源保护和效率的福音》(Conservation and the Gospel of Efficiency:The Progressive Conservation Movement,1890-1920)。该书从资源保护的角度研究进步主义改革,挑战了传统上所持有的进步时期的改革为“善良之人和恶的利益之间的道德冲突”(a moral struggle between the virtuous‘people’and the evil‘interests’)的看法,强调了资源保护政策“自上而下”(top down)的特点③,认为它事实上是将科学规划引入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之中,以求更大的效率。这一著作将对环境的关注与美国的政治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视为环境政治史的开山之作,以致理查德·怀特在追述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做出了如下判断:1960年代后期环境史的出现源于政治史和思想史,这个领域的成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部著作,即塞缪尔·黑斯的《资源保护和效率的福音》和罗德里克·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1](P297-335)。单就前者而言,“它将进步运动的重新阐释置人了黑斯和其他政治史家的中心”[1](P298)。
此书出版之后大约12-15年时间里,黑斯的研究重点转入了社会史和政治史,其间他发表了大量论文,代表性的如《1880-1920年美国政治史的社会分析》、《社会和政治:政治和社会》、《美国社会和政治史中新作的理论意蕴》等④,以相关论文为基础结集成的著作《作为社会分析的美国政治史》⑤,是他十多年来社会史和政治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该书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政治史,在政治史的领域内关注草根阶层,试图把大众的普遍价值、感知(perception)和上层政治整合起来,为政治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气息,很大程度上是新政治史的组成部分。这种思想在他后来的环境政治史研究中得到了发扬,以致有人评价道:“无论对于信徒还是怀疑者,黑斯在政治史思考方式的革新上都是施洗者约翰,他的思想迅速成长并充斥于其著作之中,促成了该领域全新文本的产生。”⑥此外,他对城市史也有所涉及⑦。
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黑斯并没有忘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这期间,《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出台、地球日的诞生、环境保护局的设立,加之他自己参与环境运动的经历——作为塞拉俱乐部宾夕法尼亚分部(Pennsylvania charter of the Sierra Club)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新的事件使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逐渐回到了早期对环境问题的兴趣上来。并且受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思路的影响,他在环境史领域开启了一条“独特的旅程”⑧,这就是其环境政治史研究。
至此,黑斯的研究跨越了政治史、社会史、城市史和环境史四个领域。在他看来,这四个领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关联的焦点是权力、价值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和制度,是引发渐变和突变的社会动力[2](Introduction,vii)。他也因为在学术界的重大贡献而获得多项殊荣:1982年获森林史学会西奥多·布勒冈奖(the Theodore C.Blegan Award of the Forest History Society),1991年获宾夕法尼亚人文学科杰出贡献州长奖(the Pennsylvania Governor'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he Humanities),1993年获宾夕法尼亚历史协会史学著作人奖(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estern Pennsylvania History Makers Award),1997年获美国环境史学会颁发的第一个环境史终身学术成就奖(Career Achievement Award for Lifetime Contributions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
二、三重结构分析模式的形成
黑斯环境政治史研究思想的核心是三重结构分析模式。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本重要的论著中:《美丽、健康和持久:1955-1985年的美国环境政治》、《环境史中的探究》和《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⑨。仔细研读这些著作,可以认清其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感受其环境政治史研究由感性到理性、由分析到综合、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其中既不乏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影子,又不失其自己的研究特点。正如威廉·克罗农所说:“20世纪在影响我们对环境政治的理解方面,没人能与黑斯媲美。”[2](Foreword,xi)
前已述及,《资源保护和效率的福音》是黑斯环境政治史研究的起点,不过此时的研究仍在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范畴之内。及至《美丽、健康和持久:1955-1985年的美国环境政治》一书,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但他结合对城市环境、荒地、有毒环境、人口资源和增长的极限、里根的反环境革命等具体问题的分析,突破了自上而下的视角,已涉及与环境政治相关的各种因素。例如,环保势力(the environmental impulse)、反环保势力(the environmental opposition)、中间阵营(the middle ground)的管理者对各种力量的调和;地方、州和联邦在环境政治中的关系;立法、行政和司法在环境问题处理中的作用;科学、技术和经济等因素在环境政治中的作用等。对这些不同的主体和因素,黑斯有着详细的阐释。首先是环保势力,他认为各种环境组织、国家环境政策、公民环境行为、公共舆论导向等都是构成环保推动者的元素。美国社会的环境动力和对环境保护的兴趣因时因地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动力模型(pattern)。根据资源保护选民联盟(the 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LCV)对选民投票情况的统计,他将全国分为环保动力强弱两类地区,认为环保动力的强弱从三个方面显示了其内在逻辑:第一,环保兴趣的强弱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旨在强调环境运动来自高级工业和消费社会人们的价值观的变化。第二,新老人口团体、新旧城市、新旧地区在价值观和态度方面有着重大的不同,中大西洋和中西部各州的老工业地带的环境兴趣要低于西部甚至南部有着新价值观人群的各州。第三,环境价值的积极表达和自然景观本身的状况也密切相关[3](P51-52)。
环境的反对者在黑斯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此他运用分层研究的方法把视角从上层延伸至与环境治理直接相关的利益主体。在他看来,环境主义者对农业、劳工和商业团体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尽管这些团体有时迫于压力不断改善自己的环境目标,但其总体的政治策略即最大程度的抵抗、最小程度的退却(maximum feasible resistance and minimum feasible retreat)[3](P287-288)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农民作为环境反对者是与其自身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首先,他们反对城市休闲者,反对野生动物保护,因为许多农民本身是猎人。其次,他们反对环境主义者对农业耕种方式的批评。在他们看来,环境政策可能限制水资源、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新泽西和俄勒冈州的农民运用燃烧的方式清理田野,产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但农民反对政府和环境主义者努力限制这些行为的企图。不过农民反对环境的强弱有着自己的变化规律:越是乡村地区,反对越强烈。在更多以乡村为主的南部和西部,立法者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情绪。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州,反对的声音更多来自该州的乡村部分。然而,在遭受大规模工业发展和废弃物威胁的乡村地区,立法者表现出与城市同样的环境兴趣[3](P296-297)。
工人对环境问题的态度与工人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态势密切相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比较复杂,既可以是环境支持者,也可以是环境反对者,常常成为工、商业团体和环境主义者共同争取的对象。总之,因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在有些情况下,工业成功地赢得了工人,另外的时候,环境主义者和工人形成了同盟[3](P298)。例如,在空气污染问题上牵涉到煤炭的运用,因此煤矿与工业界联合起来谴责限制二氧化硫排放的行为,继而又阻止应对酸雨的行为。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甚至支持工业界要求放松汽车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的企图。然而又因为将原子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反核问题上成了环境的支持者。在职业健康问题上,他们也与环境主义者站到了同一个阵营之中。
对环境目标最强烈的反应来自商业和工业团体。他们的力量分布于大众媒体、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他们不仅单独反对环境目标,而且还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协会和研究所。例如1960年代,随着对空气污染关注度的日益增强,国家煤炭工业协会抵制对煤炭使用的限制;1966年,美国石油研究所(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组建了专门的空气和水资源保护委员会(Committee for Air and Water Conservation),它的目标是“设计帮助指导公共政策的原则,发布信息和研究结果”,以应对美国公共卫生署建立的燃料中硫含量的标准[3](P309)。此外,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他们还形成了一整套反对策略,如制度控制策略和技术革新控制等。
对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的环境态度所做的这些分析,是黑斯环境政治史研究的特色,它明显地受到了其先前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也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巨大难度。与此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传统政治史研究的领域,如总统对环境的态度、民主党、共和党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差异、国会制定环境法律的历程、法院对环境诉讼的判决、环境管理机构的成立、行政机关对环境管理章程的制定和实施等。这些方面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取向受到经济形势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并随着不同社会阶层对环境问题支持度的变化而变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状况。
除去有着明显主体性的因素外,黑斯还十分注重对环境政治中经济、科学、技术和信息等因素的分析。这些因素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是中立性的,但在他看来却不然。它们隶属于不同的环境主体,因交织着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争论而变得不再中立,成为了政治问题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才有他所谓“科学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cience)、“经济分析和规划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lanning)之说⑩。这种非政治因素政治化的倾向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得以反复强化。
在经济问题上,黑斯认为传统经济学关心生产和利润问题,不考虑环境的成本和价值,二者是对立的。但环境主义者从提高消费水平的角度,认为环境和新型消费经济是统一的,需要把环境的无形价值纳入经济分析中,计算成本和利益。于是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围绕环境的无形价值,经济学家产生了分歧。传统的经济学家受自己职业传统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不考虑环境的价值,而环境政治本身又受经济因素的制约,于是“经济分析事实上成为了政治选择,经济统计方式的变化就是政治策略的改变。经济分析的细节决定了政治选择,也使得选择复杂化而难以把握”[3](P376)。例如,商业领导者强调环境规划带来的成本,在政策制定上引发无数的经济争论。面对这样的形势,卡特政府期间,环境保护局(EPA)和环境质量委员会(CEQ)也展开同样的分析,与代表商业利益的研究中心——国家经济研究协会(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Association)展开斗争。
在科学问题上,黑斯认为“1960、70年代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的观念被扩展至每个雇员之中。科学家很难不表达自己雇主的利益,商业、工业或政府发展机构雇佣的科学家不值得信赖,因为对问题的科学判断中有他们雇主的利益”[3](P356)。事实上,环境科学的研究结果作为公共政策的基础,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它能否为政治决策提供证据。于是在公共政策出台的过程中,代表不同利益的科学家就科学的标准问题产生了不同的争论。把有利于自己主张的科学称之为“好科学”,不利于自己利益的科学称之为“坏科学”,极端的情况下称之为“垃圾科学(junk science)”[4](P149)。正因为如此,被管制的企业通常努力限制新的科学知识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实用性。例如,1967年春,二氧化硫基准文件受到工业界的强烈反对,煤炭、钢铁、石油和汽车工业的科学家对公共卫生署的科学评估产生了强烈的异议,最终导致对初始标准的成功修改。
污染治理中,技术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黑斯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环境政治史的研究中,他认为技术的使用涉及成本和利益问题,因此也就存在大量的对技术革新的抵制者,存在技术问题政治化的趋势。环境支持者希望发展清洁的技术,不过“基于新技术的可行性或成本过高的问题,抵制者经常把技术的革新者诽谤为“反技术”[2](Introduction,xxxi)。1977年的《清洁空气法》大量限制聚乙烯橡胶工业生产的气体排放,这因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引发了工业界的大力反对,但当工业界发现回收技术不仅能够利用废物而且能降低原材料成本时,他们的态度就缓和得多[4](P183)。
如前所述,商业团体作为环境反对者,专门发明了技术革新控制策略(the contro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许多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所使用技术的合理性,还建立私人实验室,例如杜邦公司(Dupont Corporation)的哈斯科尔实验室(Haskell Laboratory)、密歇根州米德兰市道尔化学实验室(Dow Chemical Lab)都是很好的例子[4](P326)。
环境治理中对相关信息的占有和获取,存在同样的道理。环境决策经常与科学技术的细节、历史记录和经济分析的详情密切相关,因此执行有效信息策略的能力在不同环境主体的较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型组织占有更多的信息,对信息产生和流通的控制是他们的主要政治策略。他们要么把具体信息据为己有,要么阻止关键信息为竞争者所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高级工业社会,‘新政治不平等’就是获取科学和技术信息的不平等。”[2](P328)在获取环境信息的竞争上,环境主义者掌握信息细节的能力取决于掌握政府资料的能力,而在这方面反对者占据巨大的优势,他们经常寻求与政府的合作,以限制公众的环境信息量。因此,信息政治(the polities of information)与政府机构不断转化的角色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2](P373)。
以上涉及的与环境问题相关的诸多因素,从身处底层的平民大众到美国政治的最高点,从具有实在利益关系的环境推动者、反对者到经济、科学、技术和信息等因素在利益较量过程中的政治化,是黑斯环境政治史框架的基本元素。不过此时他仅仅分别陈述和剖析了这些纷繁复杂的因素,它们并列在其思想的蓝图之中,尚无内在的逻辑关联。
在《美丽、健康和持久》一书出版后的十多年里,黑斯以这些因素为基础,结合二战之后的环境政治,开始考虑环境政治史研究的结构问题,即如何把分散的元素综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此,他发表了大量文章,最终集结成《环境史的探究》一书。在这本书的导论中,他初步建立了不同因素之间的逻辑关联,即通过潜藏在环境事务中三种主要的政治动力,形成了三重(tripartite)结构分析模式:(1)把环境目标置入公共领域,并以持续渐进的方式关注这些公共价值的推动力;(2)推动力量的反对者,它们试图限制推动者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3)专家、行政部门、立法机构和法院构成的中间阵营(the middle ground),它们关注政策的执行,对反对者和支持者进行调节,以实现双方的协调和妥协[2](Introduction,xxii)。此书中无论实证的个案研究还是有关环境政治史的理论构建,都围绕着这个分析模式展开,既把各种因素纳入其中,又有利于揭示问题的本质。
在这个结构中,他明确了所应分析的三种力量,但尚不十分精炼,而且对每种具体力量如何分析、它们各自的作用机制如何等问题,还未有详细的阐释。不过这一切在《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中得到了补充和完善。该书是从理论角度对过去思想的总结和提升(11)。在此,他把三种力量简化为:致力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个体和团体;环境的反对者;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制度。对其中每种力量,都分析了它们的起源、思维和行动的方向及功能[4](P2)。这就为从微观的角度剖析每种力量提供了指导。
这三种力量是否有共同的作用焦点和相互作用的界面呢?答案是肯定的。黑斯认为,它们在“公共政策目标,由立法到具体规章的转化,日常的规章实施,科学、经济和技术的作用,政策制定过程中行政、立法、管理和司法手段的选择,地方、州和联邦的作用”[4](P2)等方面,有着相通之处。这意味着研究这些细节,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三种力量的有机联系和互动关系。至此,三重结构分析模式成为了黑斯环境政治史研究的核心,也标志着其研究思想的成熟。该模式有助于把单个问题的阐释置入整个框架之中,使人们更加容易认识环境问题的本质和牵涉因素的复杂性,而不至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三、黑斯环境政治史研究的意义
首先,从历史学的发展来看,史学关注环境问题有着充分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既是史学的‘实用’或经世传统的一种发展,又是现代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新世纪史学工作者的一种社会担当”[5](P60),彰显出史学的现实功用。更值得重视的是,这种研究将环境因素、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引入政治史领域,可以说是新政治史研究的继续(12)。它不仅接续着新的研究视角,而且会对传统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产生新的考量,这有助于更新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式。由于政治史虽然不再是历史的骨干,但依然是历史的核心[6](P355),笔者认为,解剖环境问题中的政治现象和权力关系并把二者结合起来,也就是使环境史和政治史相结合,这将从一个方面大大推进历史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环境史研究的深入来看,从何种路径进入其研究范畴并完善其学科体系,是20世纪60、70年代环境史诞生至今仍为大家所讨论的重点问题。从美国环境史研究来看,沃斯特曾发展出物质环境-社会经济与环境-环境思想的三层次(three levels)分析模式(13);约翰·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有三个维度(varieties):物质环境史(Material Environmental History)、环境文化/思想史(Cultural/Intellectual)、环境政治史(Political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7](P6);威廉·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可以包括三个研究范围: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部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8](P1122-1131)。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环境政治史的研究至少可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亚领域,而塞缪尔·黑斯则在环境政治史的理论构建和方法论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来说,以此为指导、以具体的环境问题为原点开展环境政治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增添新的主题,而且不失为加强环境史学科体系建设的一种有益探索。
其次,从现实着眼,黑斯对环境问题中经济、科技和草根阶层等因素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解构诸如阶段论、技术万能论和代价论等不当的环境论调,从而有利于认识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本质。事实上,环境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环境出了问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满足于认识到环境被污染、被破坏。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形而下层面、治标不治本,将无法取得根本性成效。当我们认清这一本质、正视诸多利益矛盾的交织时,方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解构阶段论。因为在黑斯的理念中,环境和经济发展并不存在截然的对立关系,二者可以共存共荣,关键是必须处理好环保势力和反环保势力在成本-利益计算上的标准问题。我们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对技术万能论而言,我们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固然离不开技术,但技术绝不是万能的,它发生作用是有条件的,而且当技术混之以其他问题时,可能引发新的成本、代价问题,甚至成为反环保势力的助手。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一书的分析逻辑为我们展示了同样的观点(14)。就代价论而言,我们必须解构宏大叙事范式下的论断:环境问题是人类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论断屏蔽了污染者、受益者和代价承受者的区别。我们必须追问谁在污染、为何污染,而又是谁在污染中获利、谁在承受污染的代价。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这显然离不开环境政治史对各个阶层的正名,只有恢复作为代价承受者的“小人物”的真正面目,倾听他们的呼声,才能保障其环境权,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最后,认清环境问题的本质,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黑斯环境政治史的研究有利于指导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将环境治理定性为一个政治问题,这自然就规定了解决问题的落脚点和突破口:维护大自然的权利和公民环境权,进而在环境正义的基础上实现环境史研究倡导的真正的人本主义。这在根本上符合环境史对人的存在及意义的探究,即环境史的创见主要在于更新了认识人及其活动的视角,因而突破了“人类惟一”的狭隘意识以及“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环境史不仅不反人类,相反,它倡导和实践的是一种更宽泛、更真实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既关注抽象的人类,也关注具体的人群和个人,还关注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9](P125)。如果这种人道主义是环境史和政治生态伦理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环境政治史的研究将以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对问题的回答作为完成其使命的积极践行者,这既彰显了环境政治史的社会功用,也与历史学作为“人”学的主张不谋而合。
收稿日期:2009-08-10
注释:
① Samuel P.Hays,Wars in the woods:the rise of ecological forestry in America,Pittsburgh,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7.
② 《环境史》杂志于2007年4月对黑斯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黑斯详细讲述了自己的学术经历,见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2,No.3(Jul),2007,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eh/12.3/hays.html.
③ Ibid.
④ Samuel Hays,“The Social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1880-1920”,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80,No.3 (Sep.,1965),PP.373 -394.“Society and Politics:Politics and Society”,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5,No.3 (Winter,1985 ) ,P481-499.“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Recen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Politics”,History and Theory,Vol.26,No.1 (Feb.,1987 ),pp.15-31.
⑤ Samuel P.Hays,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s Social Analysis:Essays,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0.
⑥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eh/12.3/hays,html.
⑦ Samuel Hays,“From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to the History of the Urbanized Societ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Vol.19,No.4 ( Aug.,1993),pp.3-25.还可参见姜芃:《西方城市史学初探》,《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⑧ 塞缪尔·黑斯把自己在环境史领域的研究称之为“独特的旅程”(A distinctive journey in the field),此说参见Samuel Hays,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8,Introduction,xiii.
⑨ Samuel Hays,Beauty,Health and Permanenc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55-198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since 1945,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0.
⑩ 参见Samuel Hays,Beauty,Health and Permanence: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55-1985,vii.
(11) 在接受《环境史》杂志的采访中,他专门谈及了《美丽、健康和持久:1955-1985年的美国环境政治》和《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的关系,认为前者太长,思路尚不十分明确,不易阅读,后者是对前者的浓缩和精炼。见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eh/12.3/hays.html.
(12) 参见菲力普·R·范德米尔:《新政治史:进步与展望》,载伊格尔斯著:《历史研究国际手册》,陈宏海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40页。
(13) 详情参见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ed.),The Ends of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293.
(14) 康芒纳著:《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惠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