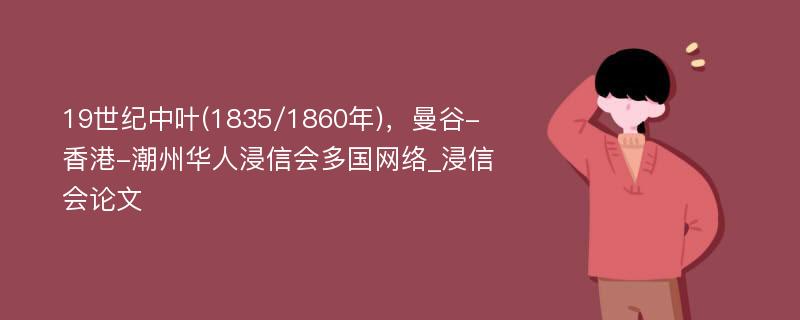
19世纪中期(1835-1860)华人浸信会教民的曼谷—香港—潮州跨国网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曼谷论文,潮州论文,教民论文,香港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2)01-0042-08
从18世纪中期至1860年,基督教在中国被视为异教,此间不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游历布道。当时新教差会要向中国传教的唯一选择是在东南亚使海外华人皈依基督教,然后靠他们把基督教带到中国传播。本文调查了19世纪期间美国浸信会面向中国的传教活动,研究焦点落在华人浸信会跨国网络在中国南海出现的过程,提出海外华人基督教徒沿着所建立起来的沿海网络,由暹罗到香港,再向广东东北部潮州方言区发展。因为在英国人打赢鸦片战争(1839-1842)之前,中国沿海地区禁止基督教的传播,所以归国的华人基督教徒面临着相当的个人生命危险。尽管环境不利,但他们成功地利用亲缘关系、村落与印刷的网络,发展信众并修筑教堂。在没有基督教传教士总领的情况下,他们使基督教思想本土化,并布道实践,因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做出了贡献。
浸信会在曼谷的早期传教活动
浸信会在海外华人社区中是如何开始传教的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因为这涉及到19世纪初有一个有争议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Gutzlaff,1803-1851)。1826年,郭士立首先由荷兰传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派到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Indies)的海外华人中工作。但在1828年他忽略了原来的工作而与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捷科布·汤姆林(Jacob Tomlin)以及在新加坡和暹罗的三个中国助手一同工作。从1828年到1831年,郭士立使一群讲方言的华人皈依基督教,在人数上是最多的。在潮州的华人居住在暹罗南岸大多数的城镇和乡村。他们与中国做生意,收益颇丰,此外还积极参与商团的种植工作,比如甘蔗、胡椒与烟草(注:G·威廉·斯金纳(G.William skinner):《泰国华人社团的历史分析》(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An Analytical History),艾思卡(Ithaca)、纽约,1957,83-84。)。在曼谷,郭士立指导几个基督教问道者并在1830年至1831年间使一个潮州移民皈依,叫庞太(音译,原名不可考,英文名Boon Tee,译者注)(又,Bun Tai;Bunty,原文注)。皈依后,此人为郭士立在移民中布道传福音。他甚至计划去前法属印度支那,在潮州社区中传教,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前法属印度支那正在与暹罗开战(注:郭士立1831年4月1文:《关于暹罗的翻译工作,收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图书馆世界传道会档案》(C.W.M.)《1830-1839的华南》1号档B箱3号夹。)。关于庞太的背景与传道办法,郭士立没有多少叙述。庞太很可能从曼谷的家人与朋友入手,利用当地的网络使其他的华人皈依。
不管庞太使用什么样的办法,他是一个出色的传道人,不负郭士立的期望。他独立布道的能力使郭士立确信:海外华人基督教徒经过指导,在得到支持的前提下可以在自己的民众中传道。曼谷的潮州社区是一个传教的希望之土。郭士立在1844年建立了汉学会(Chinese Union),雇佣在西方传教士指导下的当地传道人。此举是否是郭士立受了庞太介入传教一事鼓舞所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潮州传道人在19世纪40年代汉学会的传教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叫“明”的人在1847年担任汉学会会长(注:胡德(George A.Hood):《未完成的使命?英伦长老会在华南岭南的传教史》(Mission Accomplished?The English Prebyterian Mission in Lingtung,South China),福郎霍特(Frankfurt),1986年版第22页。)。我们只能猜测:由于郭士立与庞太在曼谷共事的早期经历,郭氏可能对潮州基督徒有了良好的印象,于是乐于请他们做助手。
1831年,郭士立抱怨欧洲新教组织对他的工作支持不足(注:郭士立1831年4月1文:《关于暹罗的翻译工作,收入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图书馆世界传道会档案》(C.W.M.)《1830-1839的华南》1号档B箱3号夹。)。于是他向美国的教会求助,要求向暹罗派送更多的传教士并给予其他帮助(注:翟斯·G·露茨(Jessie G.Lutz):《不小的错误观念:郭士立与19世纪美国赴华差会的兴起》("The Grand Illusion:Karl Gutzlaff and Popularization of China 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ttitudes during the1830s"),辑入帕特里西亚·尼尔斯(Patricia Neils)《美国对华态度与政策》(United States and Policies toward China),阿曼克(Armonk)、纽约,1990年版第46-77页。)。美国浸信会对此请求作出反应,在1832年将庄约翰(JohnTaylor Jones)由缅甸调往曼谷,在1835年又派璘为仁(William Dean)(注:卡尔·E·布兰德佛德(Carl E.Blanford):《泰国的华人教会》(Chinese Churches in Thailand),曼谷,1962年版第32-34页。)来。在庄约翰到达之后,郭士立决定离开曼谷去中国南部沿海的澳门。1832年10月,他在查顿与孖地信的洋行所属的鸦片船“塞尔夫”号(Sylph)上做翻译。从那个时候到1839年鸦片战争期间,他多次作为鸦片商船翻译和情报员到中国沿海地带。鸦片战争期间。他为英军充当翻译和情报员。1842年夏季,他在中英签定《中英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也颇为活跃(注:阿瑟·威利(Arthur Waley):《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伦敦,1958年版第222-224页。)。郭士立与鸦片商的联系与他传教士以及和平使者的身份相矛盾。郭士立的例子表明了一些早期传教活动是顺着由东南亚到中国的鸦片贸易路径而来。美国浸信会也是如此。
庄约翰与璘为仁的到来标志着美国浸信会在暹罗潮州社区传教工作的开始。庄约翰在庞太成功的基础上,于1835年在曼谷创建了中国浸信会。由于浸信会的教义强调洗礼的时候要完全浸入水中方为有效,庄约翰对庞太进行再次洗礼以正式纳入教会(注:施其乐(Carl T·Smith):《中国新教教徒受洗名录,1831-1842》("A Register of Baptized Protestant Chinese,1831-1842"),见《崇基学报》(Chung chi Bulletin)第49期(1970),第24页。)。洗礼之后,庄约翰指派庞太管理中国教民并劝戒问道者。这个立即指派的任务表明庞太在郭士立那里接受了相当的传道训练,可以管理当地的教堂。他一直为美浸信会工作到1836年,因为与上司璘为仁工作关系欠佳而退出浸信会。但1843年璘为仁一离开不久,他就回到了教会。庞太最后的宗教生涯体现了内地传教的争端,中国助手由于没有独立的资源支持,在雇佣他们的传教士面前经常没有商议的余地。
庞太的离开对美国浸信会造成什么的程度上损失尚无从知道。璘为仁继续在曼谷的潮州社区传福音。到1842年,总共已经有18个华人浸信会教民(见附录1)(注:施其乐(Carl T·Smith):《中国新教教徒受洗名录,1831-1842》("A Register of Baptized Protestant Chinese,1831-1842"),见《崇基学报》(Chung chi Bulletin)第49期(1970),第26页。)。其中有四个年长的基督教徒在19世纪40年代回到了潮州老家(注:美国浸信会传道会微型胶片(下称FM),FM71-7:约翰臣(Johm W·Johnson),1860年7月14日;1860年6月;FM69-2;璘为仁,1852年5月17日;FM71-7;约翰臣,1860年10月11日,及天竺传教会,1860-1861,3-4;)。他们类似于大多数潮州移民,到东南亚去赚钱后归乡养老,回家后传播华人在暹罗皈依浸信会的消息。关于他们与美国传教士的个人接触与皈依的经历有助于在他们自己的社交圈传播基督教。
发展到香港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不久,璘为仁决定把浸信会总部由曼谷迁往香港。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利用英国人在香港的有利条件来进行传教工作。迁居香港是美国浸信会向广东潮州东北部潮州地带发展的第一步。在19世纪,香港是不断发展的鸦片贸易以及暹罗与华南之间苦力贸易的中心。也有很多人经过香港由潮州向东南亚移民。著名中国作家赖连三(Lai Liansan)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观察到这点,当时潮州华商垄断了中国与暹罗之间的贸易,在殖民地经营大量的生意(注:赖连三(LaiLiansan):《香港杂录》(Xianggang Jilu),广东,1997年版第56页。)。他注意到在殖民地销售由暹罗到新加坡船票的代办多达百家(注:赖连三(LaiLiansan):《香港杂录》(Xianggang Jilu),广东,1997年版第66页。)。赖连三的记录清楚地表明了大量潮州人经由香港来来往往。
虽然潮州华人分散在东南亚的不同国家,但他们通过血缘与老乡关系与家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种乡土联系表现了一种强烈的乡土感。如陈达的著作中,这些联系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关系,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作为有效的支持网络(注:陈达(Chen Ta):《华南移民社区》(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上海:Kelly and Walsh,1939年版。)。因为有了这么大的流动人口,浸信会得依赖这些跨国福音传播网络进行传教。由于考虑到这点,也考虑到英人在香港的有利条件,美国浸信会离开曼谷迁香港,在那里的潮州社区建立新的传教地。
在香港岛英皇道浸信会教堂的广东浸信会帮助下,璘为仁在1843年5月建立了第一个讲潮州话的浸信会教会。当时在市区里已有两个华人新教集会(注:施其乐((Carl T.Smith):《历史感:香港社会与城市历史研究》(A Sense of History: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香港,1995年版第288页。)。约翰臣(John W.Johnson)与耶士摩(William Ashmore)后来加入了璘为仁的工作。他们都热切地要在潮州开始传教工作。璘为仁从曼谷带来了两个助手陈雅(音译,原名不可考,英文发音Chen Ya或Chek Yet,译者注)与洪赫(音译,原名不可考,英文发音Hong Hek,译者注)。1848年4月,就是在教会建立的前一个月(注:施其乐(Carl T·Smith):《中国新教教徒受洗名录,1831-1842》("A Register of Baptized Protestant Chinese,1831-1842"),见《崇基学报》(Chung chi Bulletin)第49期(1970),第25-26页。),陈雅在试图去解决一个争吵的时候被杀。在洪赫的帮助下,璘为仁于1843年至1859年间为12个信徒施洗,其中男女各占一半(见附录2)。他们显然是顺着长期以来的家庭与家乡网络皈依的。
陈孙(英文发音Chen Sun,A Sun)和李恩(英文Li En,A Ee;另,Ee似应为En,但原文如此,译者注)两人的例子可以表现出家庭作为改宗信教机制的作用,属于丈夫把宗教信仰传给妻子与孩子的典型情况。陈孙是澄海县南阳村当地人,他使他的妻子、女儿和岳母皈依。李恩是潮阳县达濠市场的本地人,他把妻子带到了教堂。这两个家庭在香港浸信会12名教徒中占了一半。在这些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小辈理应跟着长辈上教堂。
当地网络是潮州称民改宗信教的又一个重要机制。1843年,普宁县光南村人陈兑(英文发音:Chen Dui,Tang Tui,A Tui)是香港第一个问道受洗者。他是当时英属香港政府的包工头,手下有不少人手,其中很多可能是光南村的老乡(注:施其乐(Carl T·Smith):《中国新教教徒受洗名录,1831-1842》("A Register of Baptized Protestant Chinese,1831-1842"),见《崇基学报》(Chung chi Bulletin)第49期(1970),第26页。)。他们到香港的原因是英国人的到来使得市场对苦力、切石工与木工的需求量增加了。1842年至1843年,来自广东各处的苦力到了英国殖民地,一个月可以赚五元钱(注:施其乐((Carl T.Smith):《历史感:香港社会与城市历史研究》(A Sense of History: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of Hong Kong),香港,1995年版第40页。)。如同殖民地大多数的华人一样,这些苦力来自广东、客家与潮州话区。可以推测,讲同一种方言的苦力有其老乡关系与村落联系。尽管他们的属系不同,他们都有一点共同之处:他们让妻子留在家里料理家务,自己来香港。他们形成了一个阶层,与殖民地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认同感。英国人把他们当作“下等人”对待,住在社区边缘(注:施其乐((Carl T.Smith):《历史感:香港社会与城市历史研究》(A Sense of History: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of Hong Kong),香港,1995年版第287-288页。)。低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于基督教传教活动所提供的支持更易顺从(注:施其乐(Carl T.Smith):《香港早期教会与中国传统家庭模式》("The Early Hong Kong Church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pattenms")见《景风》,20:1(1977),第52-60页。)。在香港一些潮州移民心中,浸信会的信仰能够扎根,正是顺应这一背景的。
就像其他的称民劳工男子一样,陈兑与他的手下在香港只是谋生而已,想赚一笔钱回家。但是常年不在家使他们没有亲友的情感支持。在一个离家好似流亡的社会里,潮州浸信会是一个可供选择的社区生活中心。陈兑上教堂的时候可以与其他的潮州人交往,有团结感与归属感。这种聚会生活对陈兑与其他潮州移民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受洗过后,陈兑把他的三个老乡带到教会来。其中一个男子,叫陈都,另外两个是女性,叫李兰、吴龙卵。我们不知道陈都是否陈兑的手下。如果是的话,说明陈兑善于把老乡关系与权力关系结合起来以使同事皈依。
总体来说,在曼谷与香港的潮州浸信会聚会由移民劳工所组成,有未婚和已婚的,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依赖家庭、同乡的网络交往。这些社会网络是中国南海无形的沿海高速公路。因为这些网络不在清政府的监视之下,便提供了一种稳定而有效的宗教传输渠道,因此便利于浸信会由边沿向中国内地发展。费正清(John King Faribank)很好地总结了海外华人社区与基督教传教活动之间的关系:“新教传教活动通过东南亚移居海外的华人社区这个薄弱环节展开了侧翼进攻”(注:苏珊娜·威尔逊·巴尼特(Suzanne Wilson Bamett)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书面材料》(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剑桥、马省,1985,13。)。费正清引起了人们极大地关切新教早期跨中国南海的传教活动。美国浸信会开始进入潮州社区传教正是这幅宽阔的画面中的一部分。
浸信会流动性的传教活动并非独一无二,应该放到当时新教在东南亚传教活动的大背景中去理解。美国浸信会并不是唯一在东南亚使海外华人皈依的差会,也不是第一个利用华人跨国,乡土与家庭网络进行传教的。《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前,华南沿海与外商、传教士就有紧密的联系,当时新教早期的差会在中国的边缘必须得以立身。他们请海外华人做传道人,所依赖就是使在海外的华人信教,然后回国传教的模式。巧合的是,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开始想在中国南海扩张,这对新教差会是有利的。恒河外方传道会(MS.Ultra-Ganges mission)的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斯(Walter H.Medhurst),美国浸信会的璘为仁(William Dean)、约翰臣(John W.Johnson)使曼谷的海外华人皈依,《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又回到香港。
香港潮州浸信会教会建立后很需要助理事工。璘为仁雇佣了三个教徒做助手,陈兑、陈孙与李恩,均出生在19世纪头10年,在1844年均30出头。他们形成一个年轻、精力旺盛的布道团,在当时还属新安县的九龙、新界使一些潮州人皈依,这两个地方一直到1860年与1898年才割让给英国。在他们的帮助下,璘为仁于1860年在长洲岛(即广东通常所说的长洲)建立了第二个潮州浸信会礼拜会。长洲浸信会的教堂位于东湾岛北部。根据蔡志祥的研究,19世纪,来自汕尾、海丰与陆丰的这些潮州话区的渔民在东湾居住了下来(注:蔡志祥(Choi Chi-cheung):《加固种族渊源:长洲的角节》(Reinforcing Ethnicity;The Jiao Festival in Cheung Chou),辑入大卫·福里(David Faure)、海伦·F·休(Hele n F.Siu):《脚踏实地:华南疆域的禁锢》,(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South China),斯坦福(Stanford),1995年版第250页,尾注23。)。这些渔民成了岛上最早的皈依者。1860年,陈兑成了第一个被派送去料理教堂的人。据报,他在教务管理方面颇为娴熟,赢得了外国差会与当地礼拜会的尊敬(注:美国浸信会传道会微型胶片(下称FM),FM71-7:约翰臣(Johm W·Johnson),1860年7月14日;1860年6月;FM69-2;璘为仁,1852年5月17日;FM71-7;约翰臣,1860年10月11日,及天竺传教会,1860-1861,3-4;)。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长洲浸信会教堂今仍在,但香港皇道的第一个潮州浸信会教堂却在1861年差会撤离汕尾的时候关闭了。这种发展表明香港两个最早的潮州浸信会礼拜会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前者是由长洲的渔民构成,后者的成员有许多的无定居处,找临时工作的流动劳工,他们并不想在香港定居。更重要的是长洲教堂是由陈兑和当地华人管理,而市区的教堂由美国的差会作为传教站来使用。在长洲教堂,中国人直接介入领导也许是该教堂比香港皇道的教堂能够存在更久的原因。遗憾的是长洲教堂并没有保留1910年以前的任何文字材料,而1860年之后的发展也很少有书面材料。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该教堂归属了香港的广东浸信会教会,逐渐形成了讲广东话的礼拜会(注:刘粤声:《香港基督教会史》,香港,1941年版,1997重印,第161-162页。)。
海外华人传播福音
当璘为仁在香港建立临时基地并培养助手的时候,巴色会(Basel Mission)的黎力基(Rudolf Lecheler)于1847年到达香港。黎力基是巴色会直接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他的第一个传教地是广东东北部的潮州县。黎力基在潮州沿海居住五年,此间郭士立的汉学会成员帮助他在汕头东北22英里的盐灶村中制盐、捕鱼社区里传教。由于当地官府的敌意,也由于公众对福音没有热情,黎力基在村子里呆不下去。1852年他回到香港与同仁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一起在客家方言区这个更有希望之处共事(注:汲约翰(John Campbell Gibson):《华南地区的传教问题与方法》(Mission Problems and Mission Methods in South China),爱丁堡、伦敦,1901年版第144-149页。)。1856年,英国长老会的宝为邻在他的第一次假期之间驻足于香港,想到要在此开辟新的传教地。美国浸信会根据在曼谷与香港的工作经历,认为在海外华人基督教徒的家乡,还有很多家庭与乡土关系,还可以施洗不少人(注:美国浸信会传道会微型胶片(下称FM),FM71-7:约翰臣(Johm W·Johnson),1860年7月14日;1860年6月;FM69-2;璘为仁,1852年5月17日;FM71-7;约翰臣,1860年10月11日,及天竺传教会,1860-1861,3-4;)。1855年,就是璘为仁与潮州的黎力基分开三年的时候,璘为仁从香港派陈兑到他的老家传道三个月。1856年8月约翰臣派陈孙与李恩到潮州执行同样的任务,他们发现亲友还是可以接受基督教的。当中国内地还是对西方封锁的时候,传教唯一的策略是使海外华人基督教徒的亲友皈依。
当陈孙与李恩去潮州的时候,英伦长老会的宝为邻刚好在汕头学方言。宝为邻抓住这个机会与这两个能干的浸信会事工一起工作,陪同他们到家乡村子里传教。在他们的帮助下,宝为邻很快熟悉了当地的环境。陈、李与张林市场的郑戴、郑兴建立起联系,他们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基督教徒,在19世纪40年代由璘为仁在曼谷施洗。但是,当浸信会事工到达,在户外传道的时候被当地长官逮捕并关押四个月,一放出来他们就回到香港的浸信会。他们离开之后,宝为邻就到了福建的厦门,那是条约里规定的开放城市,也是长老会的传教地。宝为邻离开并不意味着要结束长老会开始在汕头传教的计划。一个月后,施饶理(GeorgeSmith)从厦门而至,要在那儿建一个传教站。1859年,他给陈开霖施洗,他是汕头的第一个长老会教民。在1882年,他成了长老会第一个被授予牧师职的人(注:汲约翰(John Campbell Gibson):《华南地区的传教问题与方法》(Mission Problems and Mission Methods in South China),爱丁堡、伦敦,1901年版第172-173页。)。
从条约签定前在潮州的美国浸信会与英国长老会的福音传播策略上可以看出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涉及到福音传播中的华人社交网络。1835年,美国的浸信会为在曼谷的潮州移民施洗,1842年就到了曼谷香港潮州方言人群中运作。总部由曼谷移到香港的决定部分原因是可以利用英国人在那里的有利条件,也因为可以利用以前存在的福音传播社会网络。浸信会到了香港以后,顺着教徒的血缘和乡土关系直往潮州发展。这些社会网络为基督教徒在不同的地方受洗提供了主要的途径,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促成浸信会的传教活动。
第二个特点涉及到早期浸信会皈依者加入美国差会并为之做事工的动机。璘为仁与约翰臣请了五个潮州皈依者做助理,包括在暹罗的陈雅与洪赫,在香港的陈兑、陈孙与李恩。除了陈孙以外,其他人都直接从美国差会领取固定的薪金(注:美国浸信会传道会微型胶片(下称FM),FM71-7:约翰臣(Johm W·Johnson),1860年7月14日;1860年6月;FM69-2;璘为仁,1852年5月17日;FM71-7;约翰臣,1860年10月11日,及天竺传教会,1860-1861,3-4;)。他们很快被提拔做了传道人。但是我们无从知道传教士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事工,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圣经》训练。对这些事工个人背景的考察表现出传教士喜欢什么样的人选以及他们以什么样的动机归属教会。19世纪40年代早期,就是这些人受雇的时候,他们至少都是二十大几或三十出头的人。虽然他们并非来自名门贵显,但他们识字,能够领会有关浸信会教义的丰富知识。他们皈依之后,利用血缘和老乡关系把亲朋好友带到教会。既然他们在文字上过关,在信仰上有传教责任,璘为仁就招这些年轻人并训练他们成为传道人,这是符合逻辑的决定。
至于他们的动机,对于这些加入美国差会的年轻人来说,此事似乎有很强的物质刺激。他们移民到暹罗与香港首先是纯经济方面的原因。差会所提供的雇佣机会在经济上是长期有保障的。他们为差会做事有所得,不会亏。虽然环境的证据提示了经济利益与宗教归属之间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尚不能解释为什么潮州移民中只有少数人加入差会,以及为什么他们后来离开香港去汕头,在反洋危机中还继续为差会工作。
除了物质上的刺激。我们还应考虑到社会和文化的因素。由于与浸信会的联系,这些年轻人可以摆脱劳工阶层,转向众多的文人活动,包括翻译《圣经》,撰写宗教册子,户外讲道与教堂的牧师工作。通过这些传播福音与《圣经》的活动,中国事工可以学会教学和组织的技巧,他们没有其他的机会来学这种技巧。当时在中国,有文化是权利与地位的象征,被美国浸信会所雇佣对这些移民劳工来说当然是具有吸引力的差事。有文化,有领导能力保证了向上层社会流动,在社交圈赢得尊重。人们可能作出这样假设:这些年轻人认为向上层流动与经济效益一样重要。但不管初衷如何,他们抓住了美国浸信会所给予的机会。虽然差会结构使他们与璘为仁、约翰臣形成主雇关系,但他们仍得以允许,建立起同样强大,同一水平线上的网络。
结论
根据近来的研究,基督教正成为全球性的宗教,近来中国大陆基督教社区的发展引起人们对中国福音传播者及其社会网络的重视。本文跟踪几个海外华人基督教徒的生平,讨论了他们对于美国浸信会传道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海外华人皈依者做了传福音者,语言引导者与地方教堂的创立者。他们的传教责任,基督教徒生活方式以及与亲友分享浸信会信仰的意愿特别表现了他们作为东西方十字路口文化使者的作用。在《中英南京条约》签定以前,当基督教还是作为异教的时候,如果没有当地传道人的帮助,美国浸信会要使任何华人皈依都是十分困难的。
本文除了将浸信会早期使海外华人皈依的成功归功于几个海外华人皈依者之外,也强调当时他们运作环境的复杂性。郭士立与璘为仁的经历提示了新教早期的传教活动是沿着从东南亚到南亚的鸦片贸易路径而来。与鸦片贸易紧紧相关的是食物、资金、资源、人员与思想通过中国南海在流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早期的浸信会传教活动融入了中国亲缘的、乡土和跨国的网络。这样的网络把浸信会的信仰传入了中国百姓心中,为在华南最早的浸信会礼拜会打下了基础。
虽然文章只讲述了为数不多的华人基督教徒,但提出了研究中国人皈依的新方式。使中国人加入浸信会的不是哲学上的关切,而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对海外华人基督教徒而言,美国浸信会提供了工作,解决了每日劳苦尚入不敷出的问题。从他们的皈依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信教缓慢但递增。他们的经历引起人们注意基督教与中国当地社会颇为复杂的关系。比如,海外华人皈依者不止属于一个社交圈。比如,他们在国外工作的时候,靠乡土关系获得支持。回乡之后,他们在一个长久的亲友网络里运作。新、老皈依者中经常有交叉关系。只有研究这些易被忽略的基督教徒我们才能更好地在基层面上理解基督教的动态。
附录1 1835年至1842年在曼谷受洗的海外华人①
受洗年姓名② 个人细节①
1830-庞太(Bun Tai)
郭士立施洗过,1833年12月8日庄1831/1833
约翰再次施洗。1836年离开暹罗
浸信会,1843-1844年间回到教会。
1835 陈涵(Chek Han)
40岁,1843年6月去世。
1835 陈奕弟(Chek Ete) 60岁,商人。
1835 裴春(Pay-chun)
70岁,园丁,1844年5月19日去世。
1838 凯诚(Kiok Cheng) 无资料。
1838 陈华
无资料。
1838 陈括(Chek Kok)
无资料。
1839 陈雅(Chek Yet)
1843年与璘为仁来香港。
1843年在调解一次争端中遇难。
1838 洪赫(Hong Hek)
1843年与璘为仁来香港,
是璘为仁在香港的潮州浸
信会教会的创始人之一。
1839 一个新成员无资料。
1840 四个新成员1840年5月13日受洗。
1840 两个新成员1840年10月11日受洗。
1842 陈逖门(Chek Team) 1842年1月受洗。
1842 陈荪(Chir Sun)
1842年4月16日受洗。
1842 陈秦(Chek Chin)
1842年8月7日受洗。
①见施其乐(Carl T.Smith):《中国新教教徒受洗史名录,1831-1842》(A Register of Baptized Protestant Chinese,1831-1842),见《崇基学报》(Chung Chi Bulletin)49(1970),第24-26页。
②因原名不可考,姓名均采用音译,译者注。
附录2.1843年至1859年潮洲浸信会教会教徒①
受洗年姓名性别受洗年龄祖籍
1843 陈兑男
37普宁县光南村
1844 胡得男
20
不详
1844 陈孙男
20澄海县南阳村
1844 陈都男
28普宁县光南村
1844 李恩男
32潮阳县达濠乡
1844 陈向荣
男
45潮阳县达濠乡
1848 张金女
30
不详
1851 李兰女
22普宁县光南村
1854 徐月凤
女
21潮阳县达濠乡
1854 谭桂女
25
不详
1859 吴龙卵
女
17
不详
1859 陈遂心
女
18
不详
汕头市档案馆,民国档案,案卷号C184。《岭东佳音:岭东浸信会历史特刊》。《岭东浸信会初期会友芳名录》,第十一、十二期合刊,1936年12月20日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