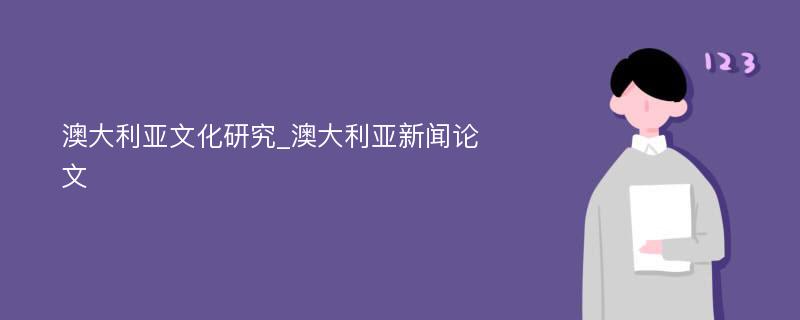
被屏/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文化论文,被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范式与知识领域之一,文化研究已然稳稳地在学术机构内获得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炫目地引发了言人人殊的“文化转向”。这一过程的发生直接联系着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美国文化研究,联袂建立“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由此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实现全球播散,但一些学人有所不知,作为其间不可或缺的中继站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被遮蔽状态之中。直到文化研究史书写热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现,尤其是其间的“去中心化”趋势的出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方被屏显或者敞明在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之中。但我们不难发现,此间的屏显直接联系着有关学人集体无意识地聚焦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因而导致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再次被遮蔽,尤其是它独特的生成脉络与内部复杂性。鉴于文化研究于新时期之初带着美国的学院体制化包装来到中国时,诸多中国学人虚妄地把原产于英国、经过美国过滤的文化理论视为“元理论”,继而绘制以英美文化研究为主部的世界拼图。今天“做”文化研究于文化研究后发之地的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与审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从而更新、丰富与完善我们的相关知识谱系。
一、虚假的“英国性”
1997年,从英国移民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家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撰文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患有历史健忘症而无力提供关于自身发展历程的权威叙述,①其结果是它既不如作为文化研究源头的英国文化研究频繁被人论及,也不如作为文化理论输出地的美国文化研究时常被人言说,尽管正是因为它的中继站作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才得以建立。米尔纳的观察可谓不无道理,因为之前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乎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致力于建构令人信服、条理清晰的起源神话,“像一个25岁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忙于写自传”,②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不同视野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塑叙事正悄然显影: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从历史、文学研究、电影理论的角度,彼得·古多尔(Peter Goodall)从传播与媒体研究的角度,詹妮·克雷克(Jenny Craik)从期刊文化的角度,约翰·弗劳(John Frow)与墨美姬(Meaghan Morris)从工人教育协会与左翼实践的角度,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与佐伊·索菲亚(Zoe Sofia)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法国哲学的角度,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与吉姆·戴维森(Jim Davidson)从文化史书写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研究。③从这个意义上讲,米尔纳的批评无疑是片面或不准确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不但开始了建构自身发展历程的叙述,而且因此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中获得了与英国、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当的能见度;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受邀担任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与《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等国际知名刊物的编委,频繁地穿梭于、驻扎在先前被英美文化理论家支配的“现场”。
直接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能见度或被屏显的,是出现在文化研究史书写中的一种“去中心化”趋势,它源自具有实体性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新时期的消失。1988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变为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以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系与社会学系合并的1992年以降,“许多文化研究理论家一直在试图挑战联系着本领域的某些系谱学叙述”,含蓄地指责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视为文化研究唯一源头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其结果是“关于文化研究及其形塑的很多修正主义解释已然出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外的文化研究现场随之获得了能见度:“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场,在过去的十年里,在跨国文化研究共同体中,一种独特风格的文化研究已然于其间获得了显著的能见度。”④除前文提及的特纳等人的著述以外,瓦尔达·布伦德尔(Valda Blundell)、约翰·谢泼德(John Shepherd)与伊恩·泰勒(Ian Taylor)的编著《重新定位文化研究:理论与研究的发展》,⑤汉德尔·K.赖特(Handel K.Wright)的论文“我们胆敢不以伯明翰为中心吗?”,⑥也都旨在消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动摇文化研究的传统空间政治。
然而,这一去中心化过程却不无悖论地钩沉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鉴于在文化研究浮出澳大利亚地表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无力提供文化研究培训,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移师澳大利亚,加之第一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大多曾求学于英国,有人甚至还得到过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的耳提面命。一些文化研究史专家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首先是作为英国文化理论家全球流动的产物而存在的,毕竟多数文化理论家都是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⑦在这些学者看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几乎可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殖民地”,显在地具有“英国性”(Englishness)。
由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与英国文化研究全球播散的时间巧合,上述观念颇为流行。众所周知,1964年,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d)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是便有了筚路蓝缕、影响深远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以及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don)所谓的“文化兴趣的复兴”,⑧英国文化研究经历了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所谓的从“作为政治的一种学术实践”到“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的演变,⑨继而开始全球播散,费斯克、特纳等人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程随之出现。他们于其间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包括举办文化研究课程、创办文化研究刊物、出版或发表文化研究著述,⑩不仅为澳大利亚学人提供了文化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普及了文化研究基本教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在我们看来,承认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活力与重要性似乎为一大进步”,促成了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观——“大众的全部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与仪式、他们的娱乐与消遣,不但包括艺术,而且包括体育与海滨度假等实践”——根植于澳大利亚土壤。(11)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替英国是否在这个领域具有霸权地位背书”,(12)但一如费斯克与人合著的《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特纳独著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等著作所证明的,费斯克等人确乎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深深地打上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烙印。
费斯克等人能够成功“殖民”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前提: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澳大利亚智识文化的发展依旧主要受英国而不是美国智识潮流的影响。一如米尔纳在讨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成时所言,澳大利亚新左派博采众长,不断从《竞技场》(Arena)等本土马克思主义期刊到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毛主义(Maoism)等政治运动获取资源,但在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英国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13)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至少就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而言,似乎有一条驿马快递专线将巴黎与《新左派评论》联系起来,将《新左派评论》与墨尔本及悉尼联系起来。”(14)这一前提不但保证了费斯克等人的成功,而且导致“英国性”一直幽灵般徘徊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上空。历史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尝试,如苏珊·德莫迪(Susan Dermody)、约翰·多克(John Docker)与德鲁希拉·莫德耶斯卡(Drusilla Modjeska)合编的《内莉·梅尔芭、金杰·梅格斯与朋友:澳大利亚文化史论文集》,(15)约翰·辛克莱与吉姆·戴维森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等于伯明翰加本土》,(16)几乎都借助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模式,而古多尔与米尔纳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著述,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为基线。
正因如此,诸多文化理论家往往集体无意识地建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贴上“英国性”的标签予以屏显,虽然殊不知的是,此间的“英国性”不无虚假成分。受历史与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刺激,澳大利亚智识生活从一开始就受英国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必然是后者的翻版;就文化研究的内部发展而言,英国与澳大利亚两地的研究传统从一开始便不尽相同。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主张英国文化研究以学术性为主,假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实践性见长——或者倘若它是英国文化研究,它就没有理解何为澳大利亚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最具创新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作……一直更感兴趣于阐述象征行为的特定形式的含义、文化实践的特定时刻的影响,而不是参照更为古旧的文化理论去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17)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能提供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参考,更能致力于公共话题的论争。一如本尼特的“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所表征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直主要致力于研究——因此凸显——日常生活文化。然而,或许让这一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美国同行的,是它与实用主义文化政治的联系、与智识实践的特定参与形式的联系。”(18)
随着安巴拉瓦纳·斯瓦兰登(Ambalavaner Sivannandan)所谓的“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语词”的视野转移,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文化研究理论时代的“理论实践者”时常因难以履行自我宣称的有机知识分子职责进退维谷;(19)面对英美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即国家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限制文化准入时,诸多文化理论家既未能提供应有的洞见,也无力进行必要而有效的干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移居澳大利亚的本尼特以自己创办的格里菲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所为大本营,致力于文化与媒体政策研究这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未竟事业,以期实现对文化的营救抑或“重释”。考虑到英国文化研究彼时所遭遇的范式危机,本尼特呼吁启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其“治理性”(governmentalization)与“监视”(police)观念,从理论、实践、体制等维度“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从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的纠缠去考察文化实践。(20)本尼特意在实现的并非是凸显政策考量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或者悬置文化研究,而是与地方及全国性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或者顾问关系,通过组织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等活动,切实参与关涉澳大利亚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与教育政策的政策制定。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社会运动现实,约翰·福莱士(John Flaus)、墨美姬、海伦·格瑞斯(Helen Grace)、司图亚特·康宁汉姆(Stuart Cunningham)、汤姆·奥里根及哈特利等人纷纷对本尼特的工程做出呼应,分别以评论家、独立电影制作人、产业理论家等身份加入其中,阐释政策研究与理解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媒体与文化产业、新闻及相应规章制度的关联。
最终,本尼特等人合力终结了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造就了处于“日本人所谓的蓬勃发展状态之中”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21)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此作为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凸显在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之中,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成立之后。一如弗劳所言:“两个时刻记录了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终结: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在1992年的形成、格雷姆·特纳的《民族、文化、文本》与我及墨美姬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在1993年的出版。”(22)所以,本尼特等人所实践的这样一种以“实践性”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即使不能否定,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评论家们所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屏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无异于进行错位的表征。此间更具意味的与其说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毋宁说是屏显这样一种虚假“英国性”的原因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之所在。
二、遮蔽下的复杂性
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大放异彩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理论家乔恩·斯特拉顿(Jon Stratton)与洪美恩(Ien Ang)多次告诫同道中人,作为一个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表征的是一种误导性的同质性。首先,它割裂了澳大利亚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次,它忽视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世界性;再次,它遮蔽了澳大利亚的内部差异性。(23)因此,在基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建构一种同质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其铁板一块的“英国性”的时候,人们很可能造成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再次遮蔽;不同于之前作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被遮蔽,此间被遮蔽的是其独特的形成机制与内部复杂性。这首先是因为系谱学考察本身可能具有片面性;无论是考察个人行为还是开展智识工作,作为方法的系谱学都可能具有欺骗性。一如特纳所指出的,在关于文化研究系谱的英美叙述中,“几乎没有认识到北/南分歧、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差异(更不必说第三世界的任何叙述),或者文化研究知识的新帝国主义运作——完全吻合生产它们的国家的政治史的运作”,(24)而非英美世界的叙述则明显缺乏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意识。
基于系谱学考察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这一术语首先遮蔽的,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复杂纠缠。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形塑动力,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澳大利亚人的“经济问题需要‘文化’解决办法”这一20世纪80年代共识,以及围绕澳大利民族身份的媒体论争,(25)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曾受到过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甚至可能具有某种“英国性”,毕竟“在文化研究学术层面上,‘英国’具有相当领导力”。(26)另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如英国文化研究,首先被孕育于成人教育运动之中: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人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工人教育协会),同时滋养与保持了关于自学成才与业余实践的一种强大但不正式的智识文化,这种文化形塑了后来因教育系统扩张而成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很多人的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自己与一种“文化与社会”方法的首次遭遇并非来自阅读雷蒙德·威廉斯,而是来自参加约翰·福莱士举办于悉尼新港滩(Newport Beach)的工人教育协会电影暑假学校。(27)
20世纪70年代末,媒体研究在澳大利亚的职业化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严肃学术力量的登陆,导致了以福莱士为代表的成人教育讲师被遮蔽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历史之中,尽管1953年以降,福莱士一直以教师、评论家、演员的身份活跃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之中,穿梭在期刊与从实验电影到电视剧及商业片的诸多媒体之间,“为文化研究工程培养一批支持者,以及培养一代电影及媒体评论家”。(28)墨美姬之得以成长为文化理论家、电影评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她从福莱士的1969年与1970年电影暑假班获得了正规大学教育无法提供的灵感源泉:“福莱士所介绍给墨美姬的,是主要存在于学界之外的一种批评性思考的文化,在独特的澳大利亚脉络文化理论的早期发展中起形构作用的一种文化。”(29)
所以,特纳虽然坚称“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起源的神话……不同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并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因之而起的核心机构。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依旧是多重碎片化的”,(30)但同时断然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诞生“在电影与媒体研究等更为成熟的学科的边缘,在文学研究、艺术与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内,或者学术之外,女性主义之内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作为结构文化政策发展与批评之内争辩的手段”。(31)
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显影过程中,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学人一如他们的英国同行,往往协同作战,团结在某一期刊或研究中心的周围,或者借用彼此所教授的某一课程,如费斯克、特纳与米莱克合力创办刊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费斯克与特纳在科研中并肩战斗。然而,澳大利亚学人的合作通常很短暂;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即使两位学者曾在同一家机构任职,也未必是在同一时间。
其次,作为一个同质性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遮蔽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多重耦合。(32)弗劳与墨美姬在追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系谱时发现,就其形塑力量而言,“或许比其他任何单一智识影响更重要、更持久的,是女性主义与对日常生活及‘个人’生活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33)他们所意指的女性主义是澳大利亚学院智识与社会运动的产物、本土力量与跨国影响的结晶,包括“女权主义官僚运动”(femocrat/femocracy movement)与“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迫于“妇女选举团”(Women's Electoral Lobby)的压力任命了一位总理妇女顾问,“女权主义官僚运动”随之开始,诸多女权主义者,尤其是来自高等教育行业的女权主义者因此获得了公职。20世纪80年代,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阵营的罗斯玛丽·普林格尔(Rosemary Pringle)与索菲·沃森(Sophie Watson)等学院派女权主义者基于福柯的权力模式,视政府为“一组竞技场”,而安娜·耶特曼(Anna Yeatman)则勉力耦合互不兼容的政策与后现代主义话语,干预政府政策。虽然鉴于“澳大利亚社会理论化的实用性”,(34)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出现于澳大利亚丝毫不让人吃惊,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将法国理论应用于国家政策领域的方式却是非同寻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必须被视为在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铺平道路,尤其是为伊恩·亨特(Ian Hunter)与托尼·本尼特等人受福柯启发、定位于政策的著述铺平道路。”(35)
“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即费尔斯基与索菲亚所谓的“身体女性主义之澳大利亚‘流派’”,源自1970年代以降的国际智识引入,以及本土期刊与出版业积极参与理论建构。(36)集“女性主义修辞、拉康心理分析与巴特符号学”于一体,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澳大利亚后结构女性主义工作,对国际智识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比如通过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合编的沃索出版社(Verso)“女性主义问题”系列——在把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引入说英语的知识分子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地,很多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为了把法国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置入英美学术界,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37)
不难发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无论是女权主义官僚运动还是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致力于本土与国际智识与政治轨迹之间的交汇。一如苏珊·谢里登(Susan Sheridan)所言:
总是在为“国际”(美国与英国,后来是法国)女性主义的移植提供着肥沃土壤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有着某些本土特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它将其它的那些特征与自身的发展相嫁接而且不时地培养出新品种的能力。一如澳大利亚小说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 Stead)对这个大陆本身的表征,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可以被想象为并非一个孤立的殖民前哨,而是位处世界贸易路线的交叉口,而且矛盾的是,被天生为旅行家的殖民者占据着。(38)
然而,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所曾“嫁接”抑或与之处于“一种双向交流关系”的,既有深刻影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女性主义,也包括由米歇尔·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亨利·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罗兰·巴特等人所代表的有关日常生活的当代法国理论。(39)一如墨美姬所证明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始终基于自己的本土性、澳大利亚的民族性、法国理论的跨国性,与法国理论保持一定的临界距离:“20世纪70年代以降被引入澳大利亚的一批批思想并非是被写到了一张白纸上,而是遭遇与进入了流行于彼时本土模式的激进文化批评的对话之中。”(40)在接触与译介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弗里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等人著述的过程中,墨美姬有意识地参照自己成长于其间的落后乡镇的情感结构、“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智识传统的需要,耦合本土、民族、跨国元素,因而有效地证明了智识的跨国流动何以促成以民族为基础的智识形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基于动荡的、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生所驱动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智识文化促成了理论运动在澳大利亚的学术合法化。1980年的“第一届澳大利亚传播与文化研究大会”,以及1981年的“外国身体大会:澳大利亚的符号学/符号学与澳大利亚”,标志着法国理论开始被体制化于澳大利亚学界,因而大大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发展,虽然我们必须知道,直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创刊,“文化理论才自觉地假借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获得中心位置”。(41)
1983年,费斯克、弗劳、特纳合力创办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旨在凝聚人才,同时,通过发表定位于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卓有成效地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国际舞台。费斯克等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与“品牌化”,不但催生了一个众所周知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的出现,而且刺激了英美学界对澳大利亚文化理论的兴趣。1987年,美国梅图恩(Methuen)出版公司收购《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之为基础打造出了名为《文化研究》的国际刊物。1990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厄温海曼公司(Unwin Hyman)为特纳出版了专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在成就特纳为主要文化理论家的同时,有效地帮助了美国学生及其他读者衔接基本素材与概念背景之间的鸿沟,获得文化研究的基本教养。继20世纪90年代应邀赴美教学与科研之后,2000年底,墨美姬受聘担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她通过与陈光兴、酒井直树(Naoki Sakai)等亚裔文化研究学者的合作,着实推进了陈光兴所谓的“新全球地方主义”(new internationalist localism),有力地促成了亚洲文化研究与英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所以,倘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导论》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走出被遮蔽状态屏显于世界的媒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无疑是“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不折不扣的中继站。
新时期以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固然获得了久盼的屏显,但从本质上讲,此间的屏显是与遮蔽相伴生的,在屏显一种虚假的“英国性”的同时,遮蔽其独特性与复杂性。就曾深刻影响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资源而言,鲜有机会获得能见度或被屏显的,至少还有马克思主义,(42)以及“社会成分混杂但高度家庭化的都市亚文化与维系它的小小期刊网络”(43)——它们中多数都未直接定位于文化研究,但大多又都以左翼立场参与政治与文化论争,先后向文化研究敞开了大门。或被屏显或被遮蔽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多种多样,既有关涉利奥塔、鲍德里亚及福柯等理论家的“欧洲理论”,也包括:
美国人类学、澳大利亚研究课程中所使用的“区域”研究方法、英国对异常行为与报刊的社会学研究、《银幕》理论、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编码/解码电视研究)、感兴趣于政策与民族身份建构的一种本土媒体研究、后韩礼德社会符号学,以及澳大利亚历史的女性主义重写。(44)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难以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成与发展追溯到某一特定的现场或中心,尤其是在屏显与遮蔽相生相克、共存一体的情势之下;无论是在地理的意义上还是在体制的意义上,它的发展都是散播的。
注释:
①Andrew Milner,"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Hegemony",in Arena Journal,Vol.9,1997,p.137.
②Martin Baker and Anne Beezer,Reading into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3.
③Graeme Turner,"It works for me':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Australian film",in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A Reader,ed.John Storey(London:Arnold,1996),pp.322—335.
④(18)(29)(35)(37)(39)(40)(41)Tania Lewis,"Meaghan Morris and the Formation of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A Narrative of Intellectual Exchange and Located Transnationalism",in Cultural Studies,Vol.4,2004,pp.46-7,p.46,p.51,p.58,p.57,p.46,p.52,p.59.
⑤Valda Blundell,John Shepherd and Ian Taylor eds.,Relocating Cultural Studies: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Research(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⑥Handel K.Wright,"Dare We De-centre Birmingham? Troubling the 'Origin' and Trajectories of Cultural Studies",in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1),1998,pp.33-56.
⑦John Fiske,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ix.
⑧其主要内容为:“在80年代,对于把文化视为一种解释变量的兴趣开始复兴”;详见Samuel E.Huntington,"Forward",in Culture Matters: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eds.Lawrence E.Harrison and Samuel E.Huntington(New York:Basic Books,2000),xiv 页。
⑨详见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作为政治的一种学术实践》,载约翰·斯道雷:《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徐德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07-117页。
⑩费斯克等人首先在西澳大利亚科技学院(后来的科廷科技大学)设置了文化研究专业,然后创办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国际权威刊物《文化研究》的前身),出版了《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Myths of Oz:Reading Australian Popular Culture)等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具有发轫性作用的著作。
(11)John Fiske,Bob Hodge and Graeme Turner,Myths of Oz:Reading Australian Popular Culture(St.Leonards,Australia:Allen & Unwin,1987),p.viii.
(12)(26)Graeme Turner:《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亚太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vi,vi页。
(13)Andrew Milner,"Literature,Culture and Society:The Politics of Australian Cultural Theory",in Representation,Discourse and Desire:Contemporary Australian Culture and Critical Theory,ed.Patrick Fuery(Melbourne:Longman Cheshire,1994),pp.35-69.
(14)Peter Beilharz,"Social theory in Australia:A roadmap for tourists",in Thesis Eleven,Vol.43,1995,p.127.
(15)Susan Dermody,John Docker and Drusilla Modjeska,"Introduction: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Problems and Dilemmas",in Nellie Melba,Ginger Meggs and Friends:Essays in Australian Cultural History,eds.Susan Dermody,John Docker and Drusilla(Malmsbury,Australia:Kibble,1992).
(16)John Sinclair and Jim Davidson,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Birmingham+Meanjin :An Occasional Paper in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Melbourne:Footscra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84).
(17)(25)(27)(28)(33)John Frow and Meaghan Morris,"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in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A Reader,ed.John Storey(London:Arnold,1996),p.351,p.344,p.361,p.361,p.363.
(19)Ambalavaner Sivanandan,Communities of Resistance:Writings on Black Struggles for Socialism(London:Verso,1990),p.49.
(20)Tony Bennett,"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in Cultural Studies,eds.Lawrence Grossberg,Cary Nelson and Paula A.Treichler(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1992),p.23.
(21)(22)John Frow,"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Theory,Story,History",http://www.australianhumanitiesreview.org/archive/Issue-December-2005/frow.html,Sept.18,2011.
(23)Jon Stratton and Ien Ang,"On the Impossibility of a Global Cultural Studies:'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in 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eds.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London:Routeldge,1996),pp.361-91.
(24)Graeme Turner,"Of rocks and hard places:The colonized,the national and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in Cultural Studies,Vol.6,1992,pp.424-432.
(30)(31)(44)Graeme Turner,"Introduction:Moving the Margins:Theory,Practice and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in Nation,Culture,Text:Australia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ed.Graeme Turner(London:Routledge,1993),pp.4-5,p.5,p.6.
(32)Tony Bennett,"Cultural Studies:A reluctant discipline",in Cultural Studies,Vol.12,1998,pp.528-545.
(34)Peter Beilharz,"Social Theory in Australia:A Roadmap for Tourists",in Thesis Eleven,Vol.43,1995,p.129.
(36)Rita Felski and Zoe Sofia,"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n Feminism",in Cultural Studies,Vol.10,1996,p.386.
(38)Susan Sheridan ed.,Grafts:Feminist Cultural Criticism(London:Verso,1988),p.1.
(42)马克思主义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墨美姬受其父亲的影响,在1969年加入了澳大利亚共产党(1972年退党)。
(43)John Frow and Meaghan Morris,"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in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A Reader,ed.John Storey(London:Arnold,1996),361页;主要期刊包括:Meanjin(《本土》)、Arena(《竞技场》)、Australian Journal of Screen Theory(《澳大利亚银幕理论》)、Art and Text(《艺术与文本》)、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前身)、UTS Review(《悉尼科技大学评论》,2002年更名为Cultural Studies Review《文化研究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