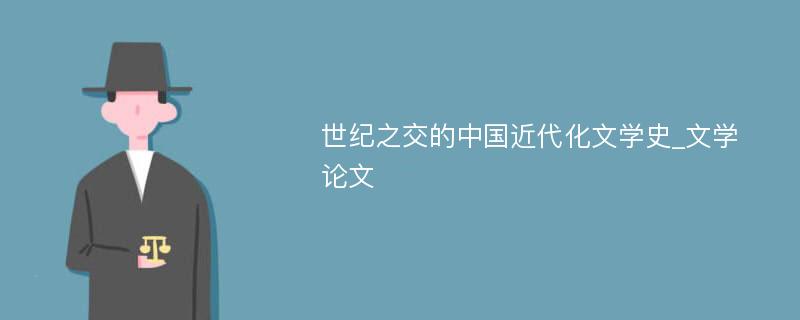
世纪之交话偏至——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现代主义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话偏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书是在朱寿桐教授主持下,积数位研究者多年心血结撰而成。应该说,它不仅在主编者个人学术史上标志着由创造社研究、新月派研究到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三级跳”的实现,更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史上有其集大成的意义。
80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已经卓见成效,从比较文学角度和“影响”论上所进行的各种基础性研究工作更是硕果累累。但缺少的却是切合中国新文学史实际的整体价值评估和纳入清醒史学视野的细致周密的“散点透视”。对于一些基本症结性问题,诸如:现代主义在中国新文学中究竟是否具有思潮性意义还是只有具体的方法论意义?既然它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同被视为中国新文学的三种基本创作方法,为什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直受到普遍褒扬而唯独现代主义受到贬斥?现代主义及其所包含的各种文学形态从本世纪初相继传入中国,它们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情状和命运究竟如何?应如何看待它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它的中国化进程及其所包含的文学史意义究应如何评价并予以有效定位?……等等,往往缺乏突破性见解。然而,这些却是该书编纂者以其宏阔的史学视野,第一次给予有效探讨的系统性命题。
诚如该书“导论”开宗明义:现代主义是“中国新文学的一脉传统”。首先,它在“五四”新文学中是有着明确定位的。20年代,当现代主义被沈雁冰等人以“新浪漫主义”的名目加以绍介时,它就被视为较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更新进的文学潮流。但同时,绍介者面对这样一朵似乎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奇葩,发出的乃是一片叹惋之声:“新浪漫主义在理论上或许在现在是圆满的,但是给未经自然主义洗礼,也叨不到浪漫主义余光的中国现代文坛,简直是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这似乎便预示了它在中国的未来命运。
从艳羡到排拒,这不啻是一种历史逻辑推演出来的必然结果。因此,现代主义初入国门就呈现出一种在观念上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传统文学形态所不容的态势。这就决定了它作为独立文学形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微妙而艰难的生存处境及发展的有限性。具体地说,在实际文学史进程中,它较多地呈现出创作方法上的特征而较少整体上的思潮意义。这是它作为“中国新文学一脉传统”的特殊性所在。该书编纂者充分注意到这一历史情状,在史著结撰中突破惯例,并非一般性地按思潮、流派史规程清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史实脉络,而“注重的只是处于传统化话语中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因而能在一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处支配地位的文学史语境中正确厘定出现代主义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生存发展的三大基本特性:第一是概念上的“假定性”,即不确定性。这最早从新文学倡导者们对“新浪漫主义”及其内涵莫衷一是的界定中呈现出来。第二是与现实主义的趋同性。现代主义的各种形态,在新文学倡导者们看来,都应该为现实主义的丰富和完善服务。不仅沈雁冰认为,“新浪漫主义”的提倡是为“写实的文学”作“进一步之预备”,胡适也说:“梅特林克等的新浪漫主义经过写实主义的‘洗礼’,故没有了‘空虚的坏处’”。以史证之,20年代李金发的自省,30年代戴望舒的转向,现代派文学的短暂欣荣等,都证明“几乎所有形态的现代主义艺术的最后归宿大都是现实主义这一大本营。”第三是“工具性”。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确乎无处不在,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借鉴象征主义开始,各种作为艺术手法的现代主义几成为每一位有成就的新文学作家艺术上克敌制胜的法宝。刻板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新文学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代主义在创作方法上给现实主义以极大的丰富。因此,“现代主义的全部魅力都在其技术性和功能性方面”,而“现代主义文学思维的意象化”代表着其“艺术表现方法的精髓和灵魂”。
基于这三大特征,不难认定“五四”时期头绪纷繁的现代主义文学形态(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唯美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就不可能从其本来意义上去把握,而基本上只具有创作方法上的意义。正由于此,编纂者对于20年代头绪繁复的现代主义文学形态才未作繁琐的考证,而是站在一定历史高度给予了恰当的忽略和应有的简化,清理出三种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支柱性形态: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和表现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存在主义等则是作为最普泛的哲学意蕴渗入这些文学形态成为其精神支柱。由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诸种形态在中国新文学中的呈现方式主要是内潜式而非外显式,它们在创作方法及文体意识上对于新文学的渗透就常常大于其哲学意蕴的流布,只是“在艺术一方面对于作家的创造性给予极端的鼓励。”著者认为鲁迅历史小说《故事新编》文体性质上的独创性即得益于表现主义艺术精神的鼓舞。其中时常插入的现代“油滑”现象打破了小说营造的历史气氛,进而毁弃了小说规定情境的同一性。这种有别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规程的创作方法,正是对表现主义“艺术变形”手法的绝妙运用——“突破既定的文体规范,使得小说文体发生变形以适应主体意象表现的需要。”
洞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情状,紧密追踪文学史现象的内在逻辑,有效地引导着编纂者从文学史意义上对于各类具体文学史实展开细致周密的“散点透视”,在过去一些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所舍弃或无法合理理解的文学问题上贡献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若非这样的“散点透视”,就不会注重二三十年代之交现代主义对新文学理论的极大丰富及其艺术上的刻意探求,就不会认识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对新诗理论的独特贡献,就有可能像传统新文学史著那样,把从李金发到闻一多、徐志摩、穆木天,以及冯至、戴望舒等人饱含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激情的诗作无一例外地送上传统现实主义并非宽容的理论魔床,并不会对施蛰存、穆木天、梁宗岱等人的文学新论和朱光潜的文艺美学理论给予某种历史性的珍视。同样,不明了40年代现代主义理性化的历史进程,就难以对张爱玲、徐訏、钱钟书等的创作作出有效的价值评估,给予应有的历史定位。另外,若非编纂者们苦心“挖掘”,于赓虞、袁犀等无名作家断不会那样理直气壮地步入中国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可见,明晰精致的“散点透视”每每带给编纂者以“发现”的快慰。同时也极大地开拓了编纂者的认识视野,增强了其史识的穿透力。书中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秩序”所作的归纳尤显得力透纸背,这则是:“在显性意义上向主流位置和中心地位突破的屡遭败北,与在隐性意义上向主流文学和文化中心渗透的渐趋成功,构成了现代主义的中国秩序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这更使人清楚地看到,扎根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体而现代主义为用”的中国新文学土壤,现代主义不得不以施展自己的技术魅力而委曲求全,安于其文学支流地位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蜷曲”,在不断地渐变中化归于现实主义主流。这不啻映证出一切外来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并驾齐驱的历史潮头。一是以启蒙主义为中心,具有“近代”文学特征的文学潮头,它一般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体而被视为主流文学潮头。“五四”文学是这一潮头的渊源。高张反传统的思想革命,遵循科学和民主的价值取向是这一文学潮头的理性选择和基本价值定位。同时,这也是由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要求所决定的。另一是带有后启蒙性质,孕育于现代西方工业化社会,感性色彩浓郁的现代主义文学潮头。它强调感兴,追新逐异,讲求声色之美,体现“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带有强烈的非理性化色彩。这两股文学潮头都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应运而生,因而给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带来两难选择:一则为完成启蒙主义的历史任务要求文学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一则为使文学合于世界文学大势摆脱各种社会意识的束缚寻求彻底的独立自由。然而,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决定了社会革命是中国社会的生存主题,而启蒙运动及其思想革命的呼声与社会革命的历史要求紧密相连。这就决定了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潮头始终处于社会意识的中心,而追求一己的绝对自由的现代主义文学只有置身边缘领受那份生存的惶恐。这样,它本有的“先锋性”便消弭了,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无奈地扮演起了“非先锋性的角色”。这两个潮头此消彼长,最终未能真正合一,从而造成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两难处境。
然而,现代主义毕竟带来了中国新文学在文学意义上的高度自觉,这体现了它与启蒙运动中个性解放要求相契合的一面,因而它又与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开放意识的获得相表里。它在创作方法和思想意识上对中国新文学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表现力,加速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进程。40年代以后,它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已不是表层的,而是深层的。正如《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一书揭示,它一则在创作方法和艺术形态上丰富着现实主义的文学内涵,一则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与通俗化的市民文学相渗透,显示出巨大的思想包容性和艺术活力。40年代徐訏和张爱玲的创作就是明显的例证。进入当代,它更与中国新文学发展繁荣的各个历史时期结下不解之缘。从五六十年代的台港文学到八九十年代的大陆文学,各种中国样式的现代主义文学粉墨登场,现代主义文学意识,甚至后现代主义文学意识广泛渗透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各个领域,进而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中国人的文学观。这表明,现代主义正以其汹汹之势加速着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文学领域的“先锋”地位已渐次获得当今文学界的指认,其自身历史进程中的“非经典化”、非主流化秩序,正改变着当今中国文学的发展态势。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一书正是站在这一世纪性的历史高度,对现代主义文学作出总体价值评估的。在对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前途的认识上,主编者坦言: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面临的“只是一个新的更有生气的发展时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倡导的后现代主义其实还是中国现代主义的另一番批评形态。”这不啻是发人深省的论断。
在史学意义上说,宏阔的文学史构架之外,要算是该书编纂体例的特异。它摒弃了以往文学史著按社会政治史和社会革命史的发展逻辑划分文学史阶段的陈套旧习,而是追寻现代主义文学史的自身逻辑剔析其发展演进的轨迹,从而使全书更显得是一部较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史。在时段的划分上,主编者恰当地援引了西方文学史家有关“文化地震学”的概念:以“十进制”的历史划分法体现文学史的“一个恰当的周期”。从本世纪开端至40年代末,将“一个个十年期视为现代主义发生、发展的‘生理节率’”。以“史前发萌期”(10 年代)、 “普遍尝试期”(20年代)、“感性表现期”(30年代)、“理性深化期”(40年代)归结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本世纪前40年现代主义文学的不同发展周期。而第五编“‘偏隅’发展期”和第六编“恢复繁荣期”既以体现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历史的非常性演进,又分别呈现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港和大陆的不同发展态势。这样,既便于史实的横向梳理,又凸现历史向纵深发展的系统格局。
阐释和描述相结合,是该书编纂方法上的又一大特色。以往的文学史著,描述性强而阐释性则弱。史家贡献于学术史的真知灼见常常湮灭于多重语境的非统一性论证,和那些看似明白晓畅实则琐碎絮叨的描述性语句中为人忽略。重史实,轻理论不啻是传统文学史著的通病。该书在尝试理论阐释与史实描述的结合上为未来文学史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书中理论探讨部分的相对独立性,显示出编纂者有效地排除了社会政治史等因素的干扰,保持了文学史语境的基本统一。其理论性的亮色尤其映现在第二编“普遍尝试期”之中。在论述“中国现代主义的原初模式”上,主编者认为,20年代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并没有压制住作家探求现代主义精神情怀的激情。那种“世纪末”的情绪所带来的精神迟暮感和幻灭的悲哀,虽然离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还很遥远,但敏感的新文学作家们仍被激起了一缕缕不绝于耳的精神共鸣。但精神世界与现实环境的分离终究造成了新文学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一种模式化的接受方式,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诸多原初模式:象征主义中的艾略特“荒原模式”,波特莱尔“恶之花模式”,唯美主义中的王尔德“莎乐美模式”,表现主义中的奥尼尔“琼斯王模式”等。这无疑是较为精当的概括。
标签:文学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