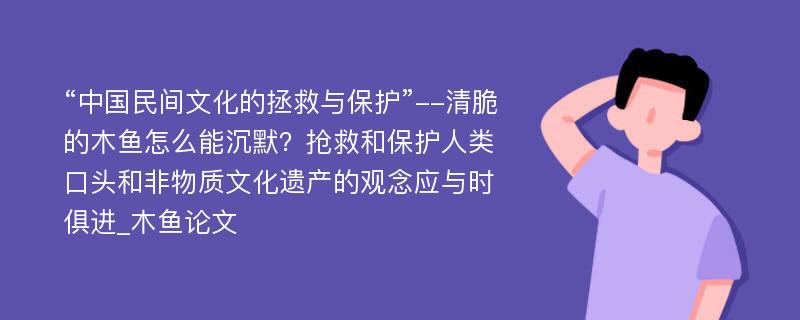
“中国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笔谈——清脆木鱼怎无声?——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应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木鱼论文,与时俱进论文,清脆论文,文化遗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3-0007-03
说起木鱼书,我首先想起的是寺庙里清脆的卜卜声,尽管学术界对这一名称的来历多有争议,我还是怀念这种沉积已久的文化记忆。读大学时听我的民间文学教师说,美国有人把研究木鱼书作为博士论文,我还以为他危言耸听;后来从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中知道,广东流行的木鱼书,在民间有极大的影响力,民间多有不知“红楼”、“西厢”,只知“花笺”、“二荷”者。珠江三角洲还有句俗谚:“想傻,读二荷;想颠,读花笺;想哭,读金叶菊。”可见其影响之大。郑振铎自己“所得的不下三四百本,但还不过是存十一于千百而已,其中负盛名的有《花笺记》、有《二荷花史》”[1](P381)。德国著名作家歌德读后亦为之激动,写下了《中德四季与黄昏合咏》十四首诗,就此传为佳话。我那位老师大概也为此情所动,在广州的地摊里搜罗了一些木鱼书和潮州歌册之类的文献,那是我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回到当年就学的母校任教时才知道的。在系资料室的墙角里堆着一包包发黄的旧报纸裹着的发霉的线装书,资料员告诉我:这是你那位老师“下放”资料室时买回来的。打开一看,每本封面上都写着“批判”二字,确实是那位老师的手笔,这也许是为了避免残酷斗争的一种认罪手段,也许是巧妙保存这些资料的一种方法。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曾出现过一阵木鱼书研究热,先后有美、英、法、俄、日等国汉学家加入了这一行列,出版过许多专著。较有影响的如日本波多野太郎的《道情弹词木鱼书》、《木鱼与南音——中国民间音乐文学研究》,美国艾伯华教授的《广东唱本提要》,英国龙彼德教授的《泽田穗瑞所藏广州唱本简目》,美籍华人梁培炽的《香港大学木鱼书叙录与研究》,以及三位日本学者(稻叶明子、金京文、渡浩司)合编的《广东说唱文学研究——木鱼书目录》。[2]其后还有一些新加坡和香港学者,按图索骥,请求我们代查并复印海外只见目录、没有刻本的原文,无奈保存单位或不让复印孤本,或要收取高额的损耗费,致使对方五万港元的课题费还不足以应付,只好望而却步。联想起我们最近为编印《中山大学经典民俗丛书总汇》,在踏破铁鞋觅不全的情况下,日本传来了佳音,找到我们所缺的一本——《孩子们的歌声》的下落。但在复印时,日方提出,只能复印一半,显然他们已意识到此资料的珍贵,怀疑我们在“盗宝”。我们只好想方设法,在台湾出版的另一个版本中补印了另一半。
最近听到国家有关部门为抢救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成立了专门机构,一项巨大的工程即将启动,报刊也加大了宣传力度,呼唤各方的文化自觉意识,争取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创建的“世界记忆工程名录”。我于是感慨万千,诉诸同仁。
一是如何增强独特文化的自觉意识,不要见宝不识宝,反视宝为草。去年,我国的昆曲和日本的能乐同时被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日本举国欢腾,而我国则反应淡漠,笔者也是在参与宁波“梁祝文化”申报评议时才知道的。类似的遗产我们可以数出一大堆,仅口头文学就有如《格萨尔》、《玛纳斯》、《黑暗传》、《盘古歌》、木鱼书、潮州歌册等等。在广东木鱼书中就有被誉为第八才子书的《花笺记》和第九才子书的《二荷花史》,“花笺”作者故里的乡亲也有感于名曲绝唱,呼吁抢救。[3]潮州籍学者薛汕、马风辛辛苦苦搜集200种歌册,也苦于无力出版。堂堂的中山大学,也把这些宝贝丢在废纸堆里,等待“批判”处理。就连当年自己独家出版的丛书,居然也要到日本、台湾才能配齐,我们的独特文化的自觉意识到哪里去了?作为今日中山大学的一员,我亦深感内疚。
须知,此类遗产是一种无形的、不可重复的文化现象,它来无影,去无踪,随着时代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遗产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有的已濒临消亡,如巫术、傩戏、古琴乐、神秘游戏、某些宗教仪式等。这些无形的遗产承载着我们民族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而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是很容易被忽视和忘却的。海南琼山有种风俗叫“闹军坡”,据说是为了纪念南北朝时期高凉俚族首领冼夫人出兵海南、平定叛乱、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缘起的,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每届冼夫人出兵的日子(农历二月初六至十二),民间便有模仿当日出征的“装军”活动,并展示当年冼夫人奖励农耕的五种作物:地瓜、芋头、韭葱(荞)、桑叶和桔叶,当地民众视之为吉祥之物。这些积淀了千百年的民族情感,若不及时唤醒,便会失忆。如今已有不少年轻人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视一些祭祀冼夫人的纪念活动为封建迷信,这和我们把木鱼书、潮州歌册扔进废纸堆一样可悲。幸好前年江泽民同志到高州“三讲”,视察了冼夫人庙,称之为“我辈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这一活动才得以正名。
二是要更新抢救的概念。有人以为抢救的提法不妥。社会发展了,文学艺术以及一切民俗事象也和生物界一样,适者生存。恐龙已灭绝多年,人类社会照样发展;被誉为动植物界活化石的鲎和苏铁存留至今,于人类社会亦补益无多,故此不必刻意为之,让它们自然淘汰。新的社会生活不需要旧的民俗,即便是演示以恢复人们的记忆也没有必要。更“因为旧俗很少是真正意义上的旧俗,它是千百年来经历过多次‘新变’后传承下来的,所以民俗是层积的,民俗在吐故纳新中传承,并非陈陈相因。新旧俗的更迭和盛衰消长是非常自然的。抢救所谓民俗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旧民俗,抢救在文化研究中是个非常天真的字眼,感情色彩较浓。”[4]我们认为,民俗文化虽不断更迭,但其精神内核心是相对稳定的,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民族的“根”,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因和内在动力,文化创新的高度往往就取决于对传统文化遗产发掘的深度。抢救和保护这些传统文化,不是要复旧,要让这些故旧的东西在现代生活中重演,而是要弘扬一种精神,培养一种基因,打造一个更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环境,推动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事业向纵深发展。
目前,许多单位都在打文化牌,想搞文化产业,提出什么“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之类的口号。可是由于开发者的无知,打出的文化牌往往没有一点文化味,甚至于不伦不类。有的楼盘标榜的是“岭南庭院”,用的却是罗马柱和中世纪的古堡。一些房地产老板想“名盘办名校”,请来几位名校退休的老师,挂起名校的招牌,以为就办起了名校。殊不知在一片荒山野岭的文化沙漠中连一根萱草都长不出,人才如何成长?!于是一个个翻身落马,还不足以为戒?有些单位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办这个节那个节,什么大蒜节、辣椒节、豆腐节、鸭梨节、葡萄节、荔枝节等。仅广东办过荔枝节的就有深圳、增城、高州、博罗、横沥等地许多单位,有的宣布寿终正寝,有的不告而终,也有的成功了。这其中成败的原因,主要就看其文化底蕴。增城挂绿与八仙之一的何仙姑有缘,不管真真假假,早已名扬海内外,一颗荔枝就可以卖到五万元;高州根子是唐代名宦高力士的故乡,他总管宫廷大内之时,曾以快马运送荔枝进宫博得了杨贵妃的一笑,故此闻名遐迩;博罗为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的罗浮山所在地,苏东坡曾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他们注册的“罗浮山”牌荔枝,一时畅销海内外。没有这些文化底蕴,再高明的商业炒作家也是无能为力的。
今天我们抢救这些文化,不是为了复旧,不是为了使这些民俗事象重演,而是为了历史的延续和记忆,为了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层的开发和创新,为使新的文化成果具有独特的民族精神,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的抢救已经刻不容缓。
三是关于保护的方法问题:是“死保”还是“活保”。现在不少单位已意识到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图书资料部门列之为珍本,国家更有《文物保护法》,这些都很好。问题是如何使之保护得更好,在保护的同时提高它的使用价值。“保”而不用,这些典籍如同一堆废纸。不准外借,不准复印,可以暂时保住它的安全,但已限制了它的流通,大大降低了它的利用率,更谈不上什么资源共享。就说我们这次为保护典籍,重版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吧,也是背着管理员,派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轮番去“偷”印的,现在已完全复印好并录在软盘里,我们也不怕公开这个秘密了。也许我们的行为使这套典籍遭到一些损坏,但我们却使它在另一种状态下得以永久保存,它从此新生,“凤凰涅槃”了!
我们在复印的过程中已经发现,有的版本已脆烂不堪,如果再这样“死保”,即使没人翻动,再过一二十年,最多百十年,它将会溃不成书。这个问题我想不单我们图书馆存在,许多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都存在。我们要抢救和保护这些遗产,能以现代声光影像技术使之复原、保持真迹的固然最好;对一些不能永久保存的,就要在它“有生之年”,把它用活用好,发挥它的作用;同时设法让它转换一种方式,得以永久保存,这就是我所说的“活保”。
现在话题还回到我开头的木鱼书上,这区区一种区域性的说唱文学,仍牵系着中外许多学者的情怀,并非偶然,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不管它流传的范围大与小,都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段记忆,而且是不可重复的。就以《花笺记》、《二荷花史 》为例,由于先前保存不善,后人为寻找它的踪迹,几经周折,求亲托友,远涉重洋,方有所获。东莞学人杨宝霖先生,从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和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得知,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英国博物院藏有此二书刻本,经牛津大学汉学家科大伟教授和他的来自香港的博士生程宝美小姐的热心帮助,专程飞往巴黎搜寻,终于得到了早期的刻本。经杨先生潜心研究,认定此书早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前就已在东莞流传,从评述者称之为“古人”的口气中断定其成书于明代,又从书中大量使用东莞方言推知作者为东莞人,而《二荷花史》作者为东莞白市的麦琏则未有充足证据,而康熙年间的刻本,国内已无留存,正如我们中山大学民俗丛书之《孩子们的歌声》一样,只有到海外才能找到了,那是多么的可悲呀!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是猛醒的时候了!
当前,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它不可能从天而降,它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说得好:“其中民间文化是保证我们中华文明的传承不中断的依据,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根基之一。”[5]我们党要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根基不牢固是不行的。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的文化整合,如何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防线,这是民族精神存亡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保持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很好领会并付诸实践的。
本刊责任编辑注:“中国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笔谈共五篇文章,本期转载三篇。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