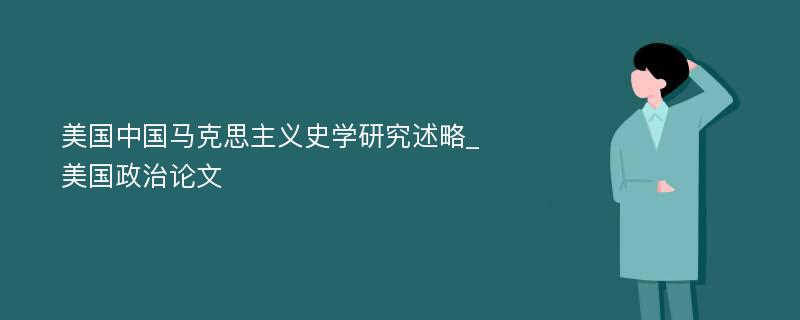
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美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2)05-0039-07
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走过九十年的风雨历程,它是如何一步步地成长壮大,其成就如何,其命运又将怎样,尤其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些不仅是中国学人所重视的问题,同样也为美国学人所关注。美国学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亦有近半个世纪。在这近半个世纪里,美国学人不仅致力于究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概况,还着力于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并关注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农民战争问题理论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观。对于正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建设的我们而言,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对其价值的正视褒扬以及对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究中国历史的评论,不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值得我们对其作深入的分析,因为透过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成败得失的观察和考量,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为深化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契机和有价值的睿见。
一、对峙时期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与之相应的是,广大史学工作者也都自觉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界掀起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在中美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其他问题而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处于尖锐对峙的时期,美国学人基于冷战需要开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极为关注,以至在美国出现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热潮。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曾组织翦伯赞、范文澜、罗尔纲、王重民、白寿彝、邵循正等一批学者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到1957年,中国史学会先后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回民起义》等专题资料11部,共68册,2758万字。[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出版后,费正清和芮玛丽即组织召开关于“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研讨会,邀请哈佛大学的刘广京和张馨保、印第安纳大学的邓嗣禹、哥伦比亚大学的房兆楹和杜连喆夫妇、华盛顿大学的罗荣邦、耶鲁大学的朱文长和执教于华盛顿大学的德裔学者弗朗兹·梅谷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进行评论。①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对于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美国学者进行了跟踪介绍。1958年,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就1957年中国史学界出版的三部有关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著作发表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最近的历史著述》一文,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批判性分析。[2]1961年,费维恺又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文,专门介绍中国史学界关于“五朵金花”问题的争论情况[3]。
与此同时,中国学家积极组织召开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讨会。1961年,包华德(Howard L.Boorman)组织邀请倪维森(David S.Nivison)、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C.Howard)、威廉·艾尔斯(William Ayers)、约翰·A.加拉第(John A.Garraty)等学者召开“中国历史传记方法”研讨会,探讨“当代政治对人物传记写作的决定性影响”。②1964年,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倡导下,《中国季刊》组织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戴维·法夸尔(David M.Farquhar)、费子智(C.P.Fitzgerald)、何四维(A.F.P.Hulsewe)、约翰·伊斯雷尔(John Israel)、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包华德(Howard L.Boorman)、郑德坤(Kenneth Ch'en)、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Harrison)、费维恺等学者参与,他们围绕共产主义中国的史学家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开展史学研究进行热烈讨论。③
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美国出版了专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著作——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Harrison)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该著详细阐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如何分析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农民战争的领导、组织结构、口号、意识形态、宗教态度、作用、进展、特点及失败原因等。[4]此外,美国学者还着手收集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研究成果。1959年至1960年期间,费维恺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S.Cheng合作编撰《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该书收集了500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著作。这500部著作是两位编者从1949年至1959年共产主义中国出版的2032部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编者对这些挑选出的著作进行了介绍和简要评述。[5]
在对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跟踪研究后,美国学者对这期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他们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费维恺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盛装下的中国历史的关键,在于我称之为的无意义无价值问题指的是什么。列文森曾指出,尽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拒绝他们的儒家传统,作为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抛弃,他们并没有轻易的接受这一现实;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取代过去价值观念的思想影响力并非纯粹是西方的。对于新中国人而言,对于过去的这种强烈文化情感要求为部分中国人所神化的东西来填补因拒绝儒家知识界传统所留下的空白。因此,我将描述的这种努力旨在用一种新的过去来取代老的过去,主要集中于农民起义、城市商业发展以及大众文化,这些以前被中国史所遗忘的下层。但是,这种有意创造一种新的、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很显然恶化了,而非改善了在过去中找寻意义的问题。其结果是,大陆史学家陷入一种自相矛盾之中,被迫去复活并吸纳为五四一代所抛弃的传统成分,当然经过了部分的转变。”[6]费正清和芮玛丽在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论文章中这样写道,“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学是这样的一种现象之一:适合现代极权主义秩序,同时也是对2000多年古老帝国传统的回忆。对于后者,绝大多数王朝在资助大型文献编纂之同时禁止异端解释。不计其数的中国学者忠实地保存中央和地方记录,但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应用其去支持儒家学说和王朝政权的正统性。任何人都不应奢望这种方式会在一夜之间得以改变,尤其是当它非常符合北京政府的政治目的。儒家具有教训意味和说教性,共产主义学说也同样如此。”[7]詹姆斯·哈里森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农民战争问题进行研究后认为,通过历史学习以达到历史教育和党的政策普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战争史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大陆关于农民战争的史学并不是学术的胜利——无论是在史料的深度还是驾驭方面很少有研究能够同解放前并驾齐驱的——但是它在大众教育方面却是一项了不起的胜利”[8];威廉·艾尔斯以共产主义中国的当代传记为例,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记并没有免除普遍存在的口号:政治挂帅。它是一种具有高度目的性的工艺。……绝大多数传记的目的是使人信服、铭记或是鼓舞,传记成为一种说教、崇拜或是宣传,是激发大众热情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完成党的任务的一种方法。”[9]总而言之,在美国学者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完全政治化”的史学,即“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其最终目的是“将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宣传,以使现存的政权能够获得中国人民永久的支持;同时,中国今天的历史写作也代表一种真正的尝试,即在中国的过去中为他最近所展现出来的国内和外部发展找寻合法性”。[10]
美国学者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概斥之为完全政治化的史学,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存在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意义及过于强调史学的社会功用等问题;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冷战环境及美国学者的冷战思维。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曾批评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研究,“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联姻在当代中国日渐成为最明显的联姻。不仅学术应直接服务于政治利益,而且它必须在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框架内。”[11]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美国学者及其学术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类似的问题。费正清之所以积极从事并倡导近现代中国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由于“北京出现了许多卷宝贵的历史文件和未必可信的历史论文,主要都是根据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显著题目——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历史分期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历史已在有力的教条主义的基础上,为了宣传目的而重新作了解释。内中大部分是以毁谤美国的历史为目的。”在费正清看来,“在六亿人民心目中系统地灌输引起人民仇恨的半真半假的历史,是使人难安的,特别是我们已经被贴上长期敌人的标签。……还有令人同样不安的事实是,美国公众在现阶段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中,不能分清真实和半真半假。”[12](P306-307)因此,“设法让这些记载得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研究从而为我们自己辩护,将迟早成为对国家利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事情。”[13](P199)1964年《中国季刊》组织召开“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记载将会发生变化”、“我们应如何评价他们”、“当前的历史过程事实上新颖到什么程度”、“它是怎样建立其理论和框架结构”等问题。[14]
基于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研究动机,许多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就难以跳脱意识形态话语、克服政治偏见来客观分析;相反,他们常常超越学术的界限而带有浓厚的政治攻讦色彩。诚然,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存有诸多缺陷;但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决不是如美国学者所说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的学术”,毫无学术价值可言。正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评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时所言,“在冷战史学的幸福时代,中国史家为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所作的努力,被西方从事中国研究的史家草率地批评为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给他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只是中国史学受意识形态的指引。不可否认,这种努力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但必须指出的是努力本身既不是无意义也不是没有价值。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令社会史家困惑的问题,最为著名的就是马克斯·韦伯。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不仅对于希望理解中国社会的动力而且对于理解欧洲的起源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史家在探寻中国史上的资本主义过程中所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改变了曾经一度流行的中国深陷于经济停滞的观点。”[15](P107)
二、解冻后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环境及史学自身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被打破,中美关系逐渐走向缓和,并于1979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持续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于1976年结束。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大陆学者亦逐渐打破“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拨乱反正,开始认真地反思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从各个方面为史学新发展做出种种努力。由此,中国史学开始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气象,美国学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1977年6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参加了由菲利浦·汉德(Philip Handle)率领的美国科学院访问团。在访华期间,他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等专研中国问题的学者参观了史学研究机构和高校,并同史学研究工作者进行了访谈交流。回国后,他撰写了题为《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史学》的调查报告。在这篇报告中,魏斐德认为“史学正逐渐回归学术本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机构、高校和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正在宣告,对于学术讨论更加容忍的时代正在来临;毫无疑问,真正的事实是在同中国史家交流是比四年前容易得多,这是最为温暖人心的。”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他借用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在中国“文革”发生初所说,“文化大革命”的孤独性,将他们自己同过去和他们周围的当代世界隔绝开来。可以预见,某一天这种孤立将终止,中国将重新加入世界性潮流中”,认为对“中国史家而言,这种转变的潮流已经来临”[16]1979年5月25日至6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太平天国史学会和南京历史学会联合组织召开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研究的学术研讨会。魏安国(Edgar Wickberg)受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回国后,合作撰写了《中国史学的新方向:重评太平天国运动,说明与评论》,该文介绍了他们所参加的此次研讨会概况,并通过对研讨会讨论话题及参会论文的分析认为,应该可以相信的是,“史学比过去更少政治性,与当前需要之间的联系也比过去要少”;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发展,他们最后如是评价道,“在某些方面,人们将感受到一种新鲜和新颖之处。……新的思想和新主题正在被逐渐引入。”[17]1979年6月,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魏斐德教授率领的由罗友枝(Evelyn S.Rawski)、贺凯(Charles O.Hucker)、孔飞力(Philip A.Kuhn)、韩素瑞(Susan Naquin)、司徒琳(Lynn Struve)、王业健(Wang Yeh-chien)、卫思韩(John E.Wills,Jr.)等十位明清史专家组成的访问团来华访问;回国后,美国明清访问团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的访问报告。这篇报告介绍了相关图书馆与档案馆尤其是其馆藏的明清史资料,以及中国即将出版的明清史著作;并通过综合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认为中国史家对于明断代史、制度史和明清易代史的兴趣较低,所关注的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战争,但与此同时在明清史学界也出现了关注中西关系史、法制史和思想史等一些新的研究取向[18]。当《中国历史学年鉴》和《史学简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出版后,鲍德威(David D.Buck)即在《中国季刊》上发表题为《中国史学研究复兴的评价》的评论文章。该篇文章详尽介绍了这两份刊物及其内容,认为“他们的出现是自1979年以来中国史学复兴的证据,它们的内容和组织结构反映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学术化,并显示史家回到一个学术环境中开展研究工作”[19](P131);通过对其所刊载学术论文的分析,鲍德威认为“中国历史研究已开始鲜活起来,有关现今时代所有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都受到欢迎。”[19](P141)
如前所述,由于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官方化和国际上冷战思维的存在,美国学界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持有很大的偏见。他们通常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视为一种极权政治的附属物,认为在政治影响和主导下的史学研究是“毫无意义和价值”[6](P323)。由于这种偏见主要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其批评往往越出学术的界限而变质为政治攻伐。然而,伴随着中美关系由对峙逐渐走向正常化,美国学者在究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出现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之同时,亦开始注重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描述转向分析。哥伦比亚大学弗格尔(Joshua A.Fogel)教授于1977年发表了《中国史学中的种族与阶级:对于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及其反满主义的不同解释》。在该文中,他主要通过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如何分析和评价章炳麟的地位及反满主义在其思想中的作用,以此解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性问题。[20]阿里夫·德里克于1978年出版《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一书,作者在绪论中指出:“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分析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起源及其性质,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对的问题,并考察他们对当时中国的革命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并且提出,有三个前提引导着他的研究,这些前提涉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唯物史观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21](P2-4)。1982年,德里克在《近代中国》上发表了《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一文,着力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探讨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所陷入的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原因。[15](P105-132)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学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不再像此前那样带有浓厚的政治攻讦色彩,而是注重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并将评论克制在学术层面上。例如,冯兆基(Edmund S.K.Fung)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关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史学》一文中如是评述道,“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诸如年谱和先烈传并不太关注;相反,对于革命的社会基础及结果影响的关注远甚于台湾或西方学界,其强调的重点是阶级分析和形塑革命领导人思想观念的社会背景”[22](P181);“阶级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探究革命者及其思想的社会经济背景、成就的局限性以及革命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洞见。与此同时,这对于遵循传统史学叙述方法也是非常有价值。”[22](P211)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一书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史意义亦做了公允的评价。他指出,首先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视,“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展现出一种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全新的认识”;其次,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之应用于中国历史,“导致了史学问题的根本性重建,并刺激了发明新方法和新概念以解决在先前的史学思想中至多只是受到边缘性关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努力”。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促使中国史学超越确定历史事实而进入解释历史的层面。而且,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一套解释系统,为新的通史撰作提供了概念工具。[21](P6-8)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理论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视历史分期不仅为一种组织历史资料的方便之道,而且是一种对基本的社会经济作用的表达,所以它要求史学家深入地挖掘社会最根本的层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阐明了那些被早前的史学家所忽视或低估的中国历史的重要方面的意义”[21](P200)对于如何看待诸如历史解释的武断性、排他性、简单化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缺陷,他认为他们“武断地忽略了那些与他们的先入之见不相合的资料,他们是如此地沉迷于自己的新解释,以致根本不考虑运用不同类的资料和概念去解决不同类的历史问题的需要。他们处理历史问题的这些缺陷,部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含糊性,部分是由于超乎史学之外的考虑的干扰。但是这些缺陷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应用尚需如何加以限制的问题,它们并不能取消这些著作对于历史问题的创新性洞见,以及进行与其基本假定相配合的批判性研究的潜力。而且即便有这些缺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意识无疑仍要比其同时代的天真的学院派史学家要精密得多”。[21](P8)
这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价值的正视、褒扬和对其缺陷的公允评论,绝非怀抱意识形态歧见者所能为。从德里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评述中,亦可见其舍政治而从学术的态度及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睿智洞见。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其“问题不在于中国历史而在于中国史家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方式。这些史家自愿成为一种概念陷阱的囚陡,不断探索可供选择的关于中国经济变化的解释。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资本主义并不是无意义的;相反,问题在于在概念与历史之间缺乏任何真正意义的辩证:尽管将概念运用于中国史已揭示出可挑战固有的关于中国社会观点的重要现象,中国史家没有能力解释这些现象,却并没有激发他们去再评价、详细说明以及精确概念或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除非通过一些方式从可资利用的史料中找到内在统一的解释方式,尤其是解释存在没有资本主义结果的资本主义趋势,否则额外累积的史料将仅能制造一种令人乏味的累赘多余——更多没有开花的萌芽。”[15](P108)总而言之,伴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冯兆基、德里克等学者亦开始尽可能克服政治偏见,挣脱意识形态话语,从学术层面而非政治层面客观分析和评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日益融合,国外各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自然科学研究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启示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开展等,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与以往判然有别的新时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是一统天下,其本身在经历挫折之后进入反思阶段;另一方面,在西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之下,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联系亦日趋密切。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成为美国学界的研究热点,只有极个别学者不时有所关注。例如,1989年卜正明(Timothy Brook)主编了题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论文集,收有并翻译了12篇中国学者所撰著的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23]德里克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一文,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所表达的历史意识问题。[24](P305-322)概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再像此前那样能够激发美国学者的兴趣,受到他们特别的关注。
注释:
①这些评论文章载《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17卷第1期,1957年11月号。
②此次讨论会上,这些学者分别提交了《中国传统传记的若干方面》、《近代中国人物传记写作》、《共产主义中国的当代人物传记》、《中国与西方人物传记的比较》等论文。这些论文载《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21卷第4期,1962年8月号。
③这些学者在此次研讨会上分别提交了《新儒家的再评价》、《中国共产党对于外来王朝政权的评价》、《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中国中世纪》、《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皇帝起源和建立的看法》、《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个案研究》、《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的看法》、《作为历史学家的毛泽东》、《共产党中国的考古学》、《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农民战争的解释》、《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等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刊载于《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22、23、24、28、3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