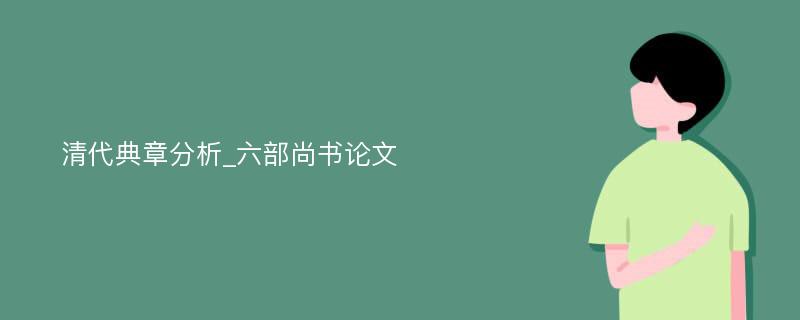
《清会典》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会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会典》是清代的一部“宏篇巨典”,卷帙繁众,内容庞博,复杂多端。关于它的 定性,近代就曾有学者感叹:“会典,吾难言也!”迄至今日,学界仍有多种说法。下 面,笔者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一、是官修史书,还是在行法律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称《清会典》为“记述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 ①许多著述也把《清会典》归入“通制类”史书,与“十通”并列。还有学者称其为“ 会要的别体”,②金毓黻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谈到“明清二代皆无《会要》乃 改纂《会典》,以详典章制度”,③在他看来,《会典》是为取代《会要》而产生的。 就形式而言,《清会典》确实具有典制史书的诸多特点:
其一,记载“故事”。《四库全书总目》中介绍《清会典》时说:“盖一朝之会典即 记一朝之故事,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书,故事之所无,亦不能饰而虚载”。④所谓 故事,即既存典制,记载前朝或本朝故事,乃是典制史书的一大特点。考《清会典》之 纂修,以“各衙门成案”及“本朝颁行诸书”为主要材料,以“述而不作”⑤、“所载 必经久常行之制”⑥为原则,属于创制设法者甚少,基本上是既存典制的直接载入,甚 至大量是前朝或前几朝的制度与规则,所谓“一以祖宗旧制为主”⑦。甚至纂修官也“ 务择学问淹贯、熟悉掌故而见识通敏、勤慎之员”充任,除内阁六部官员外,尚有翰林 院、詹事府等的史官参加,参加编纂的内阁六部官员往往也兼史官之职,而参加校刊的 ,绝大部分为翰林院史官。编修会典的活动兼为编修史书的活动,由此也可略见一斑。
其二,“明因革损益”。史学家金毓黻有言:“非以明因革损益,犹不得被以‘史’ 称”。如《唐律疏议》等诸书。只明典制而不明因革损益,“官撰之书专详一代典制, 又明因革损益者,其会要、会典之书乎”⑧。清五朝会典在时限上首尾相衔,内容上又 相互贯通,通而观之,清代绵延二百余年历史中重要典章制度之演变发展昭然若揭;每 部会典于其附属法会典事例中详其具体制度的沿革,“俾一事一例原始要终用资考覆” ;⑨个别制度在清代的演变情况,也于注文中略加说明。
其三,“以资考证”。典制史书的主要目的与价值就是“以资考证”,《清会典》的 编纂,统治者有双重意图:一为明定规则法度以令官民共守,一为昭示一代典籍以备后 世查考,如嘉庆所言:“百司之所遵行,后世以之为据”⑩。会典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于一代典制最为赅备,凡史志所未详皆具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
其四,庞杂的内容,浩博的卷帙。“会典一书,至详极备,卷帙繁重”(11),有正文 ,有注文,有事例,有图说。所载内容几乎涉及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上自朝纲大 政,国家方略.下至贩夫驿卒,四事芴荛,旁及四夷边防要典”,颇有社会制度史之规 模,《康熙会典》160卷;《雍正会典》250卷;《乾隆会典》100卷,则例180卷;《嘉 庆会典》80卷,《事例》122卷,图270卷;《光绪会典》100卷,《事例》1220卷,图2 70卷。真可谓“宏篇巨典”。
《会典》与典制史书有共同之点,但也存在着质的区别,它具有一体遵行的现实约束 力。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是清代的在行法律。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所载“故事”必须是在行的。《雍正会典》在《凡例》中首条即申明“会典所 载,皆经久可行之事……其事属权宜,不垂令甲者略而不录”。续修《光绪会典》时, 统治者也强调“增修会典皆系现行常例,”“凡庙朝典礼官司所守,皆据现在所行直书 于典”。(12)可见载人会典的祖宗旧制,既存法令,必须是在现实中行之有效的,载入 会典实质上是以国家名义对其法律效力的认可。
其二,编纂目的,首在施诸天下据以“图治”。典制史书旨在昭示史实“以资考证” ,借以“资治”,重在史料价值;法律文献则旨在明确共同规范,据以“图治”,调整 现存的社会关系,重在其应用价值。《清会典》的编纂,其首要目的是“颁行天下,永 远遵行”(13),祖制成宪载入会典如康熙所言是为了“成一代之典”,“以副朕法祖图 治之意”,亦即“上籍列圣之典,足裨经世之用”(14)。
其三,实践中得以行用。考清代史籍记载,《清会典》在清朝各代被遵守奉行的情况 历历可观,“遵照会典”,“照依会典”、“本照会典”、“查照会典”以及“按会典 开载”等字样随处可见。如《清高宗实录》载,乾隆元年六月,“按会典开载选派讲谈 修撰编检数员为小教习之例,……选派数员为小教习”。”(15)又载,“四年三月,外 省州县文庙祭品,照依会典,按图陈设”(16)。清代朝臣也讲“今凡事具查会典”。(1 7)
因持殊情况不按会典行事的,则属特例,需经皇帝御批方才得行,如康熙七年五月, 安南王黎维禧奏请“六年两贡并进”,礼部议“仍照会典定例三年朝贡”,皇帝考虑安 南国“道路悠远山川阻深”的特别情况,“准许进贡著照王所奏行”。(18)
而会典未有开载的,则不准行。如康熙七年“外国非系贡期径来贸易”,因为“会典 并未有开载”,因此“嗣后非系贡期概不准其贸易”。(19)
其四,违反会典要受处罚。会典的实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其后盾的,与会典之制有违 ,要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罚制裁。例如:雍正六年,“辅国公敬桓三陵朔望行礼不遵会 典,违例滥用赞礼郎,其属僭越”,被“革去辅国公”(20)。又如:乾隆八年七月定例 ,“嗣后仪从器仗各遵会典,周旋仪度各凛寅畏,其妄为尊大有乖定则之条,自行除去 ,如被指摘纠,恭照违制例议处”。(21)
作为在行法律,《清会典》为什么具有典制史书的特点呢?
其一,政与史的密切关系。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的“ 早熟性”、正统儒家思想对古制的推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决定了“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2)政治崇尚历史,传统的即是神圣的,祖 行的即是完美的,既存的即是合理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典章制度,往往又被确认为现实 的法律。到了统治已摇摇欲坠的封建社会末期,立法者则更加注重以其制度合于古制成 宪来标榜其统治的合理与不朽。本照“法祖图治”、“述而不作”的精神所编纂的《清 会典》,自然大量确认“故事”,而且“以祖宗旧制为主”,将历史典制与现实法制结 合于一体。清代学者也说“会典非一世之书也”。(23)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史学又重 政务,史书以“资治”为主要目的,以典章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君命官修为主要形式, 与政事法律文献则多有相类之处。政治的历史色彩与历史的政治色彩,使政事法律带有 典制史书特点成为可能。
其二,一维的法律观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法律观是一维的,视法为刑,“法者,刑罚 也,所以禁暴也”。按此观念,中国封建的法律则只有《法经》到《大清律例》这一系 统,在清朝则只有《大清律例》及条例。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大清律例》属于“ 法令类政书”,而《清会典》则归入“通制类政书”。然而,法是客观的,统治者受客 观规律的支配“表述法律”(24),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的观点是必然性的观点”(2 5),不管他是否称其为法律,是否认为是法律,按客观规律的支配表述出来,属于经国 家权力规定、全社会一体遵行的行为规范就是法律。然而,法律观念不影响法的实质, 却影响到法的表述形式,把观念上不认为是法的规范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表述出来,采用的表述形式往往就不够纯正。
其三,诸类合体混然难分,是事物发展不成熟阶段的普遍特点,法典也是如此。古印 度的《摩奴法典》,合宗教、道德法则及法律于一体;古罗马的《法学阶梯》,兼法典 与法律教科书的双重作用;唐代的刑法典《唐律疏议》,同时又是法律解释,律学论著 ;明之《大诰》是“御制圣书”、法制宣传材料,又是法律文件;而《清会典》做为行 政法典兼具典制史书的特点,也并非偶然。
二、是法规汇编,还是法典
《乾隆会典》御制序言中云:“会典以典章会要为义”。就字面含义而言,“会典” 一词就有典章制度的汇编之意。近现代学者对“会典”一词的运用,往往是做为“汇编 ”、“汇要”、“法律大全”的同意语。例如做为罗马法四大组成部分之一的“Digest a”,通常译为《法学汇编》或《学说会纂》,也有译为《会典》的。而罗马法四大部 分的汇集“Corpusiuris”,一般译为《国法大全》或《国法全书》,也有将其译成《 国法会典》的。
从形式上看,《会典》确实具有法规汇编的某些特点:
其一,《会典》的大量内容是现行法规的直接载入,亦即“皆据现在所行直书于典” 。
其二,《会典》在编辑方式上采用“分门汇类之法,提纲举目之式”。典文的编辑, “以官统事,以事隶官”,(26)即按官职分类,法规条例按职掌所关“以类相从”,每 类按时间顺序排列,“凡有年分可考循序分编”。(27)会典事例在编排上是更典型的汇 编形式。康雍二典,事例载于典文内,分类附于职事之后,“编纂之体,因事分类,因 类分年”(28)。乾隆朝则“区会典、则例各为之部,而辅以行”(29),编法承康雍二典 。自嘉庆“于会典之外,别编《事例》一书,如唐宋《会要》以官司所守条分件系,析 为门目,按年编载,俾一事一例,原始要终用资考覆,其图式别附于会典之末”。(30) 《会典》与法规汇编又存在着质的区别:
其一,编纂会典的活动是国家的立法活动,改变法律规范的内容与效力。法典编纂与 法规汇编虽然都属于法律规范系统化的活动,都建立在对一定范围内的现存法规进行全 面审阅的基础上,但法规汇编只是外部的加工整理,不改变所汇编法规的内容与效力, 不别设新法规;而法典编纂则属于国家的立法活动,原有法规的内容甚至效力发生改变 。编纂会典的活动就属于这种立法活动。
首先,内容上的改变。纂修会典时,在行法规及各衙门成案要由会典馆“检阅”、“ 查考”,会同有关部门详酌定议,上报皇帝“请旨定夺”,皇帝“定夺”的结果就存在 着对其是“认可”还是“损益”的问题。尽管绝大多数法规是“直书于典”的,但仍有 “损益”亦即废、改、立的情况。有所“损”者如:“大学士出缺定例请旨开列,亦有 迟至一月后始行请旨者”,乾隆认为“机务重地未容久旷,自应即行开列,不必请旨, 将此载入会典,永著为例。”(31)有所“益”者如: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下谕:“今查律 本内现玩冠老师有心贻误竟无正条,非所以慎重军务,警戒失律也……现在纂修会典, 著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详酌定议具奏,以便载入”。(32)还有的是对现行法规内容进行“ 总括纲领”而载人会典的,如乾隆十三年五月,大学士等奏《纂修会典事例》中有云: “各衙门成例时有损益,数年必当变通,若一概登载恐刊刻未遍,更制已多,应请总括 纲领载人”(33)。再如《大清律》载入会典,其律文数条被概括地纳入一条,且条文只 存其纲目,而具体内容则人于注文。
其次,效力上的改变。编纂会典的活动中存在着一定量的对现行法规的“损益”,但 大量的法规还是“直书于典”的,尽管这些法规内容上没有改变,但并非简单地载人, 而实际上是对其原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的认可”,同时还赋予其以新的法律效力,即作 为国家“大经大法”常久奉行的效力,亦即国家根本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我们姑且称其 为“会典效力”(关于这个问题,后面将有论述)。法律规范“纂入会典”、“载入会典 ”,这本身就意味着它被赋予了这种会典效力,变成了根本法规,而区别于其他的普通 法规范。
再进一步分析,会典的公布,要由皇帝明令“颁行天下,永远遵行”(34),这一点也 足以证明编纂会典是国家的立法活动,如果属于对在行法规进行外部加工整理而不改变 法规的内容与效力的法规汇编,则无需“明诏施行”。明诏施行,这是法典取得法律效 力的必备程序,也是最后一道程序,而《唐六典》恰恰只少了这一程序。《唐六典》于 开元二十六年制定成书,恰处在唐开、天之即社会大动荡的交叉点,被六典采入的成规 多已与实际生活脱解,如果赋予其法律效力,则必然引起实践中的混乱,因此“未有明 诏颁行”(35),虽然皇帝也以命令的形式予以公布,但“只令宣示中外”,(36)作为一 般的官修典籍公布而已。因此严格讲《唐六典》最终未能取得法典效力,只“在书院” ,被“好古者留为文献”(37)而已。
其二,《会典》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会典》并非各种典制规范的简单排列组 合,而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它有统一的编纂体制和原理原则,作为一个整体被“ 明诏颁行”,作一个整体取得“会典效力”,作为一个整体被修改续纂,其具体规范是 会典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视为“会典之例”,对其具体规范的违犯被认为是“ 与会典之制有违”,这是法规汇编无从达到的效果。
其三,《会典》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法典区别于一般法律文件的特点之一就是其相对 稳定性更强一些,《会典》以“典不可变”(38)为原则,“所载必经久常行之制”,(3 9)“非阅世递辑之书,乃一成不易之书”,一旦制定颁布,则“后嗣恪遵勿替”(40), 只能进行续修。《会典》以《事例》为其附属法,目的也在于以事例的灵活性作为具有 超稳定性的典文的补充。会典也规定了“因时损益”的原则,但这种“损益”是有严格 限制的,“如有因革损益之处,其畸零节目止于则例内增改,即有关大体者,并只刊补 一、二条,无烦全书更动”。(41)
作为法典,《会典》却采用了法规汇编的编辑方式,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 方面:
其一,对于祖制与成宪,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多奉行“述而不作”的原则。《清会典》 的编纂强调“一以祖宗旧制为主”,因此主要表现为对既存典制的国家认可,很少创制 新法规,大多是现行法规的直接载人。
其二,古代中国人在抽象思维方面不发达,缺少对事物普遍性的自觉,而重视个别特 殊的东西,强调个别事例,因此个性记述学发达。表现在成文法的立法技术上,是不采 用抽象概括之法,而采用客观具体主义,因一事生一例,在法典的编纂上也往往表现出 这样的特点,甚至相对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唐律及明、清律也是如此,虽然有类似于现代 法典“总则”部分的“名例”,但也不过是“刑名法例”而已。
其三,由于《清会典》属于行政法典(这一论点笔者将在后面论述),而行政法律规范 在形式上具有庞杂、具体与灵活的特点,很难总结出带有原则性、纲领性的总则性质的 规定。目前,世界上只有德国威敦比克邦政府曾于1925年制定了一部行政法总则性质的 法典,而在中国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局现,编纂出行政法总则性 质的法典是不可能的。基于行政法律规范的特点,要以规范化、系统化的法典形式表述 出来,采用法规汇编的“分门汇类”的方式则较为适宜。《清会典》以官制为其大纲, 职官职掌囊括国家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而分类细密,权责分明,采用“以官统典,以事 隶官”的体例,则足以使行政法庞杂、细密而具体的规范于设官分职之间有条不紊。
三、是官制法,行政法,还是根本法
(一)就性质而言,《清会典》属于行政法典
1.《会典》是清之官礼,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与行政活动。
《会典》名之为“典”,在中国古代,如蔡沈所言:“典即礼也”,又称“官礼”。 会典源于周礼,周礼又名“周六典”、“周官”。周礼的内容主要反映西周设官行政的 制度,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掌治、教、礼、政、刑、事六典,是规定国家 机关部门执掌的吏典。沿及唐代,唐玄宗始仿周礼的六典,修订《唐六典》。《唐六典 》以“周礼六官”为编修体例,实行“以官统典”,内容包括中央及地方所有官署的体 制,以及对官吏的考核与监察等制度。真正以会典命名则始于明代,清承之未改。清《 嘉庆会典·凡例》有云:“《会典》一书,如《周六官》、《唐六典》,以官举职,以 职举政”,而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行政管理中枢机关,分掌国家行政事务 ,这与周礼六官掌六典之意相合。所谓“六典建官之法,是以上追姬周。”(42)在清代 ,会典仍被视为“官礼”。如《嘉庆会典》书成,托津进表中有言:“从未有勒官礼为 一经,萃典谟于全帙,垂世大法示民有常如今日者也”。(43)《光绪会典·凡例》中云 :“官无论文武内外清浊,秩之崇卑大小,咸一礼之所弥”。
《会典》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编辑方式,以职官制度为大纲,分列各机关 设置、编制及职掌;以事例为细目,按其执掌所关,附属于官吏执掌之后,是官吏行职 办事的准则。就范围而言,会典“明定中外文武大小官制”,以清代从中央到地方整个 国家机关为规定对象,称其为“官制法”(44)也未尝不可。然就重心而论,用以规范主 管行政的六部中枢机关以及有部分行政职能的机关的组织与行政活动的法规在整部会典 中占绝大多数,会典“特重六部”,以《嘉庆会典》为例,从卷目上看,典文共80卷, 内阁六部就占43卷,而就其所容纳的法规数量来看,占会典全部法规的7/10强。这是由 于六部系统机构庞大,官职众多,分理事务的属官林立;更由于此系统事涉广泛,国家 大量法规皆属六部及下属机关职掌所关。而且,会典所载六部之外的其他国家文职机关 也分理一定的行政事务,做为六部中枢机关在某方面管理活动的扩充。如理藩院掌管少 数民族的行政事务。国子监掌国学政令,钦天监掌天文、气象之事,都察院掌官吏的监 督管理等等。另外主管帝室活动的机关往往也兼理国家有关方面的行政事务,如太仆寺 总理国之马政,鸿胪寺掌相会宾客、吉凶仪礼传赞之事,太常寺掌祭祀礼乐,等等。有 关这些机关的组织及其执行国家管理职能的法规也都属于行政法。至于武官的规定,在 会典中所占比重甚小,康、雍二典仅列有銮仪卫和京卫,嘉庆会典出于使一代典章“灿 然具备”的目的,才将武职全部载入,而且仅列官名、职掌而已。可见,会典是以行政 法规为基本内容的。
2.《会典》是行政法这个法律部门的法典。
有观点认为,《清会典》是一部综合行政法、经济法、刑法和民法等法律规范于一体 的综合性法典,但这是按近现代法的部门分类去衡量中国古代的法典而得出的结论,对 历史问题还应当历史地去分析。
中国古代实际上也存在着法的部门分类,只是这种分类与近现代有异,而且相当笼统 ,大体上分为行政法、刑法和礼仪法三大法律门类。其中行政法部门最为庞大,由于行 政管理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国家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直接进行干 预、控制,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量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刑法在古代颇受重视,被视 为法的正宗,大量社会关系以刑法来规范,靠有效的刑罚制裁力量推行;做为一个“礼 仪之邦”,中国古代特重礼仪,大至国家政事、军事活动,小到个人婚丧嫁娶,都有繁 琐细密、等级鲜明的礼节仪文,而且以法律加以规定,所以礼仪法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 一个法律部门。(45)其他各类法律规范实际上都归属于这三个法律部门。
法律部门的这种分类在中国古代相对固定且由来已久,西周就有这种分类的趋向。“ 治之经,礼与刑”,而礼又有官礼与仪礼之分,官礼又称典礼、经礼,规定以官制为核 心的典章制度,为“经邦之轨则”,仪礼亦即曲礼,规定冠、婚、丧、祭、射乡、朝聘 等方面的礼节仪式,为“庄敬之楷模”,“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各有分界,自古亦然 ”。而刑乃是贯彻执行官礼与仪礼的后盾,“出礼则人刑”。法律规范大体上分为官礼 、仪礼和刑三大类,《尚书·皋陶谟》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 有礼,自我五礼五庸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章太炎在《检论·汉律考》中说:“ 周世书籍既广,六典举其凡目,礼与刑书次之”(46)。当然,那时还无所谓法律部门的 划分,刑还仅仅是刑罚,与官礼和仪礼的规范结合起来方才成为刑法规范,具有独立的 意义,而这种结合在当时又是不固定的,官礼、仪礼与刑的划分也仅仅是法律分类的一 种趋向,但中华法系法律体系的基调却由此确立。在中国古代,西周之制的地位是万不 可低估的,是后世典制之宗。中国的文明早熟,至西周,各类制度粗具规模,孔子叹其 “郁郁乎文哉”,孙中山感其“文物已臻盛轨”。更重要的是正统儒家思想对西周之制 倍加推崇,并以此为基础构筑其理想的政治、法制模式,而中国封建社会又是一个“超 稳定”的结构体系,千载一辙,力求合于西周之制,在其基本精神与样态不变的前提下 不断发展完善。循着官礼、仪礼与刑的分类趋向发展下去,如章太炎所言:“后世复以 官制、仪法与律分治”(47),逐渐形成了行政法、礼仪法与刑法三大法律部门,至唐已 定型,到清臻于完善。与此相应,中国古代有三大法典,行政法典、礼仪法典和刑法典 。例如,唐有《唐六典》、《开元礼》和《唐律》;明有《明会典》、《明通礼》和《 大明律》;清有《清会典》、《大清通礼》和《大清律例》。
足见,《清会典》是用来代表行政法部门的行政法典,而不是综合性法典。
3.中国古代行政法法典化的条件。
行政法包罗万象,内容庞杂,规定的问题也比较具体,灵活性又强,因此从本质上就 不易固定于统一的法典,这一点甚至被归纳为行政法的一个主要形式特征以区别于宪法 、刑法、民法等等。从世界范围来看,仅德国的威敦比克邦政府曾于1925年制定过一部 行政法总则性质的法典草案,而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第一部行政法典就已问世, 后代陈陈相因,至清代已达到较为发达完善的程度。近代日本学者织田万先生曾有感焉 :“夫近世诸国锐意修法,力编成典,而未见有纂修行政法典之事,独清国自二百数十 年前早已有斯大典,岂非可奇乎!”
应该说,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创造了这一法制发展史上的奇迹。
首先,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与西欧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很大 的分散性,而缺乏社会的凝结力,要依靠外在的行政力量。马克思曾对小农经济的这一 特点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 “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 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归根到底 ,小农经济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表现为强大王权控制之下的庞 大的行政系统的存在,对国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实行全面广泛的干预和管 理,而皇帝为实现对庞大的行政系统及其管理活动的有效控制,需要利用法律对其加以 规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而完整的行政法统,其发达程度为世界其他国家无可比拟。 其次,在重视“吏治”的传统和“官本位”观念的支配下,行政法以官制为核心,行 政法的法典化则采用“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方式,将行政法规备于设官分职之间而 靠官制来提挈纲领,则官制体系的健全是庞杂的行政法规得以系统化、规范化而成一法 典的一个前提条件。以六部为核心的国家政权机关体系正式确立于唐代,第一部行政法 典也出现在唐代;宋六部系统不健全,《宋条法事类》也不过是立法汇编;清六部系统 完备,《清会典》也最为完备。
再次,《会典》采用了较为适宜的编纂体例。
(1)“以官统事,以事隶官”。此体例创自《唐六典》,开元君臣集群策群力,“历年 措思”,用九年时间方确定了如此规制,为清代承袭。“以官举职,以职举政,而圣明 作述之大经,朝野率由之定则,即备于设官分职之间”(48)。以官制为大纲,以法规、 事例为细目,所谓“挈官制之大纲,罗典常于全帙”(49),“提纲举目”,使庞杂浩繁 的法规,附隶于“设官分职之间”“有条而不紊”(50),以达“纲举目张”之效果。此 体例乃是带有庞杂性、具体性、灵活性而少原则性的行政法律规范法典化所能采用的比 较系统而科学的程式。
(2)以本领注,以注详本。《会典》有本文与注文之分。会典以“义取简要为原则”, 为保证内容庞博的会典概括简明,采用“分注之法”(51),大量内容入于注文。以注文 详其细则,“官司所守,仪节科条,会计有必须详举者,各分注于会典本文之下”(52) ;以注文释解文意;以注文明其沿革,但“不追溯前代”(53)。分注之法承自《唐六典 》,但《唐六典》分注的主要功用是“以附各官沿革”(54),穷流溯源,《清会典》有 所改进、发展,充分利用了注文。会典注文的比重,远超过本文,本文明“大纲要领” ,注文周“细节详目”,本文为经,注文为纬,“纲目攸分”(55),详略相须,体用结 合。
(3)以典帅例,以例、图助典。广义上的会典由典、例、图三部分组成,而所谓法典从 严格意义上讲是指典文部分,不包括事例、图说,无论事例、图说附于典之内,还是独 立成书于典之外,皆非会典之有机组成部分,只是其附属成分,做为会典的“助法”, 而成一组合体。《唐六典》仅三十卷,基本为典文,而罕附事例;《明会典》乃至清康 、雍二典,尚属粗疏,事例与典文“连篇并载”,“典与例无辩”(56),图也附于典内 ;乾隆会典“分会典为一书,则例为一书,其图式即列于会典之内”(57);嘉庆会典分 会典为一书,事例为一书,会典图也别为一书,事例与图式二书“附于会典之末”(58) ;光绪会典承而不改。会典载“大纲巨目”(59),“取文约而义赅”(60),如“周六官 、唐六典义取简要,必令事赅而文备,条理精密,方为妥协”(61),以备法典体裁。而 事例作为“副册”,载“详节细目”之法,明“因革损益”之迹,务求详尽,“以助典 之施行”,又以图式“昭一代典章”(62)。可见会典正裨分明、主助相须,恰如嘉庆会 典馆总裁托津所言,“如周六官唐六典取文约而义赅,右次史、左次图,俾体分而用合 ,如琴与瑟未尝改弦更张,若网在纲具已有条而不紊”(63)。
综上可见,清会典在结构体例上形成一颇为缜密而系统化的体系,以官制为纲,以事 例为目;以本文为纲,以注文为目;以会典为纲,以事例、图说为目,“巨细毕赅,网 维贯串”(64),而使详略结合,经纬分明,体用相须,以求“提刚挈领”、“有条不紊 ”、“纲举目张”之效果,使会典这部“宏篇巨著”得具“经世之用”。(65)
复次,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相适应,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相对较强,也 包括行政法规。《毛传》云:“典,常也”,《广韵》“典”下注:“主也,常也,法 也,经也”。训“常”、训“经”皆示固定性。法律的制定,主要表现为对“成宪”、 “祖制”的确认,而一旦成文,则以固定不变为原则,所谓“永著为例”。其后往往又 被后世法律所承袭,陈陈相因。法律的这种稳定性为其法典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中 国古代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有关国家的基本组织与基本制度的规定,为一代典章的会要 ,统治者更重其体制、原则基本规范的“师法先王”,宗承“祖制”,合于“古义”, 因此法典的编纂“一以祖宗旧制为主”。如《清会典》的编纂,奉行“述而不作”的原 则,其五朝会典大体内容一致,只是“零节细目”有异,基本上承于明会典,本于唐六 典,而宗于周礼。无怪乎清代学者言清会典“非一世之书,”“其体例虽承有明,而制 度损益实本汉唐,以上溯三代”,(66)梁启超也谓其“所袭者实两千年之旧”(67)。另 外,中国古代的行政法涉及面极广,包容了大量在现代应属于宪法、刑法、民法以及经 济法等规定的内容,这些内容相对来讲稳定性更强一些,较易固定于一部统一的法典中 。此外,法律一但编纂成典即被作为王朝稳固的象征而具有超稳定性,统治者往往采取 积极的措施甚至消极的办法锐意维持法典的“固定不变”,即使某些条文已成为“具文 ”、“虚法”,往往也不轻易改变。
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法典化也决非轻而易举之事,至少相对于古代的刑法来说仍有相 当大的难度。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刑法典《法经》早在战国时期就已问世,而行政法典则 迟迟难产,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唐代陆坚、徐坚等奉玄宗之诏首修六典,虽然“用 功艰难”,但“历年措思,未知所从”,以至“绵历数载”,仍于事无成。(68)玄宗于 是命孙季良、韦述等参撰,其后又有肃嵩、刘政兰、卢若虚、张九龄、陆善经、李林甫 等大批精晓政治官规的官僚及学者参与编修,历十七年终于成书,却因不切实际而“终 未颁行”,没能取得法典效力。刑法典几乎历代都有,而有行政法典的屈指可数仅几个 朝代。
需要强调一点,中国古代的行政法与近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是有差距的,它没有宪法 作为基础,既不以“政府守法”为原则,也不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宗旨,而从古代行政法 向现代行政法的转变,就是从传统进入现代的过程。
(二)就地位而言,《清会典》是根本法
近代研究清朝制度的英国学者美尔斯和普列士顿曾将《清会典》称为“清帝国的宪法 ”。当今意义上的宪法是以民主制为内容的,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在君主专制的清代是绝 无存在道理的,但仅就《清会典》在清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它确实具有宪法区别 于普通法的基本特征,即国家的根本大法。
在清代的法律体系中,主要的法律形式有:会典、律、通礼及例。律规定犯罪与刑罚 的基本制度,属于刑事法律;通礼则规定与国家、社会生活相关的各方面的礼节仪式, 主要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五礼”,属于礼仪法;例则是适应不同时期 、不同形势下巩固统治和维护秩序的需要,因时、因地、因事而制定的单行法规,是臣 僚就国家各方面问题及其如何解决所提出的“题本”、“奏本”经皇帝核准后而奉为法 律的,涉及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具有灵活性和专门性。与其他的法律形式相比较,会 典具有如下特点:
1.全面规定国家各个领域最基本的制度。
《清会典》以“具胪治要”为编纂原则,正如《乾隆会典·凡例》云:“兹编于国家 之大经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总括纲领勒为完书。”一方面,《清会典》具有 全面性,它规定清代一切领域而非某一领域的典章制度,“上自郊庙朝廷,行之直省州 县,凡礼乐兵刑之实,财赋河防之要,城池邮驿之详,大纲小纪无不并包荟萃……足备 一代之典章。”(69)另一方面,《清会典》具有根本性,它规定的是清代各个领域最基 本、最重要的典章制度,非一般之规范,而是“大经大法”,所谓“立纲陈迹之端,命 官辅政之要,大经大猷,咸胪编载。”(70)足见《清会典》全面规定一切领域最根本的 制度,与清代其他法律有明显的不同,如律“事关刑名罪制”,通礼则“只载一定仪节 ”(71),事关“冠婚丧祭一切仪制”(72),而各部通行则例是该部行职办事的准则,各 部专行则例如《铨选满州官员则例》、户部《漕运全书》、《科场条例》等则涉及国家 社会生活更为细小的方面,更具有专门性与具体性。
2.具有高于其他法律的权威与效力。
《清会典》在清朝的法律体系中,如《大清会典要义》中所言,乃“政治刑法之所由 ”,属于“法律的法律”,是清代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与依据,其他法律是将会典的某 些内容予以深化、补充乃至发展。例缘典而生,辅典而行,所谓“缘典而传例”,以其 “详节细目”来补典之“宏纲巨目”。通礼则“羽翼会典”(73),其编修以会典有关礼 仪制度的规定为基础,“有未定者增之,其已定而尚未详明者稍加饰之”(74),使其具 体化、详细化。至于《大清律》,其成书先于会典,编纂会典时将其律文以“总括纲领 ”的形式载人刑部典内,之后作为国之“大经大法”成而未易,而律例之纂修则表现为 对会典刑事方面法律的补充与具体化。
会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法律要与会典的内容和精神相符合,不得与其相抵触 。例之“随时增删”以“不与会典之制有违”为原则,不得“摭例以淆典”(75)。通礼 之制度也必须“与会典吻合,以昭信守”(76),原定通礼与新修会典有相抵触的内容, 在续修时要“悉据会典改正”(77)。而律成而未易,律例之修订增改不得与律文相违, 也自然未有与典文相抵触的道理。
正因为如此,对会典的修改续纂有着特殊严格的程序,要经皇帝批准,设立会典馆进 行,对各衙门成案的确认、增删以及增设新制皆须“仰秉圣裁”,最后要由皇帝“明诏 颁行”。
(三)《清会典》根本法与行政法合一的决定因素
就现代而言,行政法是与宪法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法律部门,《不列颠百科全书》上 说:“宪法和行政法之间很难划分界限。”清会典作为行政法典,首先它具备行政法的 一般特点,与宪法有某些相类之处,而作为中国古代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又具有自 己的独到之处。一般的行政法充其量只能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不可能取代宪法而成为 法律体系的基础和底座,而《清会典》则将行政法与国之根本法合二为一,一方面作为 行政法律调整行政管理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法律的法律”居于国家根本大法的 地位。原因主要是:
1.会典确认的对象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行政权力。中国古代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 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对国家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实行全面广泛的干预和管理,那么 用以确认行政权的行政法,自然也成为权威,有着广泛的调整范围,涉及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与其他各种法律发生广泛的联系,且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国家的 根本法。
2.会典贯穿的精神是“人治”。古代崇尚“人治”,重视“吏治”,强调“为政在人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治人无治法”。所谓的“人治”,并非只是狭义的“贤 人政治”,也不是单纯的人治,而是与“法治”结合起来的,是以“吏治”为内容,以 “法治”为形式,以法律来规范的官吏对社会的治理。这种意义上的“人治”精神,在 会典之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人治”与“法治”通过会典实现了最佳的结合。儒家视 “建官为百度之纲”,设官分职乃是会典之大纲,会典采用“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 体例,将“国家之大经大法”、“圣明作述之大经”、“朝野率由之定则,备于设官分 职之间”。“以官举职,以职举政”,将官吏的组织与规范官吏活动的法规联系起来, 体现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精神。会典其里谓“设官行政”,会典其表谓“以典 范政”,表里结合,“人治”与“法治”合体,整部会典贯穿着发挥官吏职能,从而使 “大经大法”得以遵行进而“图治”的精神,以法规范吏治,以法控制吏治。“官为国 基”,典也当为法本,“建官为百度之纲”,以官为本位的会典当然会成为众法之纲。
3.会典是儒家理论中的礼的现实化、法典化。礼在儒家理论体系中占极重要的地位, 它“实质上具有法律甚至根本法的性质”(78)“礼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天地
之经而民实则之”(79),为“人所共由”,足见礼乃是国家确认并以强制力为后盾,要 求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礼就是法。不仅如此,礼还是“君之大柄”,“王之大经 ”,“政之挽”,“国之命”,它可以“经国家定社稷”,被举到“礼为纪纲”的高度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 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罪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80)可见,礼全面规 定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原则,这种意义上的礼绝非一般的法,乃是根本 大法。
儒家礼的原形是周礼,周礼是西周的官礼,也是西周的根本法。而《周礼》一书乃后 世儒家所杜撰,但反映西周的制度典章,并用以表述儒家理想的礼,虽不是有实效的法 典,却也是一部具有法典规模、根本法特点、行政法内容的法律文献,而成为后世行政 法典之楷模。纪昀言:“《周礼》一经,朱子称其盛水不漏……故其书亦传之万世尊为 法守”(81)。古代行政法典唐六典、明会典、清会典,皆仿《周礼》而作,以合周礼之 “古义”为立法原则,第一部行政法典唐六典之编纂,玄宗钦定原则“错综古今,法以 周官,勒为唐典”(82)。历代相承,至清集其大成,与周礼的原则、精神、体制甚相契 合,纪昀评价《清会典》:“是书之体裁精密,条理分明,足以方驾周礼。”(83)周礼 为儒家礼的典型,会典则也是儒家理论学说中礼在清代的现实化、法典化。会典名之为 “典”,而“典即礼也”,清立法者也认为“会典盖经礼之遗矩”,与周礼一样属于“ 官礼”、“典礼”,编纂会典是“勒官礼为一经”,“事之有关典礼者一律纂人”,甚 至直接称会典为“礼”,“官无论文武内外清浊,秩之崇卑大小,咸一礼之所弥”,此 “礼”即指会典。可见会典实际上就是礼,是典型的儒家的法,它体现了中华法系“礼 法结合”的精神。
传统上一般认为,自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作为制度的礼即退出历史舞台,而转化 为观念形态的礼,它在现实法律制度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律“一准乎礼”,“礼人于律 ”而实现“礼法结合”。实际上永远退出历史舞台的是礼所确认的阶级内容——奴隶制 ,抽出这个阶级内容,溶进地主阶级的意志,礼作为现实制度在后来依旧存在,不过是 改换了名称而已。诸如唐之“六典”、明清之“会典”皆属西周官礼之遗矩,而汉之“ 礼仪”、唐之“开元礼”、明之“集礼”、清之“通礼”则为西周仪礼之滥觞。如果说 中国古代的“礼法结合”主要表现为律“一准乎礼”,“礼人于律”成为律的灵魂,那 么可以说这种礼法结合的范围未免过于狭窄,儒家以礼为内核的理论其能量在现实中并 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而它以西周的官礼为根基、仪礼为辅助、刑为后盾的“礼治”体系 为模式构筑的理想的礼治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全面实现,这与儒家思想理论在封建社会 的正统地位则不相协调。而冲破传统观念肯定礼法结合不仅表现为礼人于律与刑法结合 ,而且还表现为官礼、仪礼被直接法律化、法典化为行政法典、礼仪法典,肯定以行政 法为根本法、以礼仪法为辅助法、以刑法为后盾的封建法律结构体系,正是儒家理想礼 治的实践,这才顺理成章,也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总之,举世无双、发达繁盛的中国古代文明塑造了《清会典》卓尔不群的形体与面貌 ,赋予了《清会典》丰富而充实的内涵。它是个复杂的多面体,作为一部行政法典,同 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典制史书的特点、法规汇编的特点、综合性法典的特点以及根本 法的地位和特点;它是个和谐的统一体,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礼与法的结合、人 治与法治的结合、行政法与国家根本法的结合;它凝聚着儒家思想的精粹,是儒家的法 的典型。它是古代行政法的完备形态,也是最后形态,对它的认识是开启中华法系法律 体系迷宫之门的一把钥匙。
-------------------------------------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②杨金鼎主编:《中国文化史词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91页。
③⑧均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17页。
④(81)(83)均见《四库全书总目》卷81,钦定大清会典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98 页。
⑤(43)(60)(62)(63)(66)《嘉庆会典》卷首,托津等进会典表。
⑥(39)(41)《乾隆会典·凡例》。
⑦《明孝宗实录》卷123。
⑨(26)(38)(40)《嘉庆会典·凡例》。
⑩《嘉庆会典》卷首,皇帝敕谕内阁。
(11)[清]张祥河:《会典简明录》。 (12)(14)[清]杨模:《大清会典要义》。
(13)(34)《东华录》康熙九年五月,张所志奏请皇帝编辑会典。
(15)《清高宗实录》卷20。
(16)《清高宗实录》卷89。
(17)《皇清奏议》卷8。
(18)(19)《东华录》康熙八。
(20)《清世宗实录》卷197。
(21)《清世宗实录》卷71。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1页。
(23)(42)[清]《会典说略》。
(24)(25)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3页。
(27)(28)《康熙会典·凡例》。
(29)(49)《光绪会典·凡例》。
(31)《清高宗实录》卷330。
(32)《清高宗实录》卷331。
(33)《清高宗实录》卷315。
(35)(36)均见《四库全书总目》卷79,《唐六典》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82页。
(37)《全唐文》卷627。
(44)梁治平先生曾将诸如《唐六典》、明清《会典》等称之为中国古代的“官制法” 。见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 44页以下。
(45)参见吕丽:《论中国古代的礼仪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2期,第62~ 68页。
(46)(47)均见章太炎:《检论·汉律考》,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经典·章太炎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48)(50)(51)(52)(53)(54)(56)(57)(58)(59)《嘉庆会典·凡例》。
(55)(65)《大清会典要义》。
(61)《嘉庆会典事例》卷首。
(64)《嘉庆会典》卷首,御制序。
(67)梁启超:《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台湾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5页。
(68)《大唐新语》卷9。
(69)《乾隆会典》卷首,乾隆十二年上谕。
(70)《雍正会典》卷首,御制序。
(71)《乾隆会典·凡例》。
(72)《嘉庆通礼》卷首,乾隆元年六月上谕。
(73)《嘉庆通礼》卷首,乾隆御制序。
(74)《皇清奏议》卷22。
(75)《乾隆会典》卷首,御制序。
(76)《乾隆通礼·凡例》。
(77)《嘉庆通礼·凡例》。
(78)《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79)《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80)《礼记·曲礼》。
(82)《新唐书》卷1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