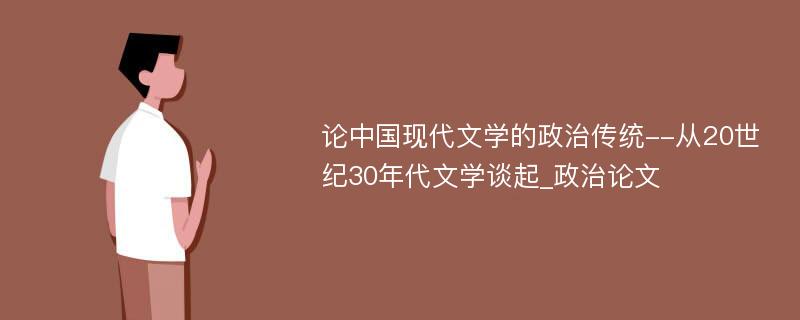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从30年代文学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传统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搞文学的人们很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上个世纪给我们带来的 是什么样的文学传统?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承续那些优良的文学传统而丢弃那些不良的 文学传统?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文学界首要的任务是对20世纪文学即我们通常所谓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作一次认真的清理和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是多方面的,本文在此选择其中之一的政治化传统来加以分析, 是基于政治化传统之于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的考虑。谈论中国现代 文学的传统,不能忽略中国现代文学赖以产生和生存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20世纪中国 文学的发展,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就某种意义上讲,由于20世纪特殊的时代 特点和特殊的历史任务,使这个时代的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不利于纯文学发展的态势。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老作家柯灵曾有过如下的概括:“中国新文学 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 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 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 。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 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 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①这种概括也许尚欠严谨,但多少还是道出了中国新文 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20世纪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得到自足性的发展。文学革命伴随着思想、政治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它与反帝反 封建的政治思潮难以完全剥离。“五四”时期曾提出的反载道的文学口号尚未能落到实 处,而在“为人生”旗号下政治化趋向已初露端倪,并很快便被早期的革命文学口号所 代替。大革命后,文学的政治化终成主潮。此后的文学发展,虽随政治形势变化而呈现 不同态势,但却始终未能避开政治化“浪潮”的裹挟。20世纪文学的发展,确实时时受 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与氛围,这不仅体现在许多文学作品所表露出的在题材上的政 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而且全面体现在整体的文学目的和文学观念上 。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因此,文学的政治化, 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传统之一。
文学的政治化传统在“五四”时期便显端倪,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步演化为政 治的运动,随着思想启蒙的长久历史任务被政治革命的现实要求所中断,文学的政治化 亦逐渐被提出,1923年开始,一些从事于实际政治运动的革命者纷纷从政治革命的角度 向文学提出服务于革命政治的要求,此后又有包括郭沫若、沈雁冰在内的著名作家们的 呼应,但文学的政治化在“五四”时期并未形成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沿袭相传的特点 。文学政治化传统的真正形成是在30年代,这是由30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所决定的。30 年代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为巩固其“权力主体”的地位,实行了种种文化控制方略和文 艺政策,这造成了国民党政权这个权力主体与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权力客体之间的严重疏 离,因而必然地造成了包括文化界、文艺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最大程度上的不 满情绪。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就构成了30年代文化、文艺领域的特殊景观:一方面,是 国民党政权以控制宣传、教育等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文化,压制不同的权力客体的不 相谐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来自权力客体的种种文化反弹,即同样以宣传、教育等途 径来发泄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和发布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从而构成了反国民党 政权的“反权力政治文化”。由于书刊、文艺等宣传媒体在政治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所 以该领域便成了双方进行激烈争夺的战场。30年代,作为权力客体的持各种不同政治见 解的文化群体和个人,不约而同地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出版和言论的自由。这当然 都是针对国民党政权的限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文化控制手段而来的。左翼文化、文 艺阵营作为最直接的“反权力政治文化群体”,最多地也是最长久地发着争取出版和言 论自由的呼声。这在他们30年代的一系列纲领、宣言、和其他文献中已构成了一个很重 要的内容。在30年代,不仅是左翼文化、文艺界,而且在其他作为权力客体的文化、文 艺群体或个人那儿,“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事实上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斗争内容 。就拿“新月社”来说,他们在这方面的有关言论,其言辞激烈程度,绝不亚于左翼作 家。即使象沈从文这样被人视为“远离政治”的作家,也曾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抗争 过。在言论、出版自由问题上,权力客体与权力主体之间之所以构成如此尖锐的冲突, 这完全是由30年代的政治背景所决定的。由于受控制的传播媒介能成为培养政治信念的 有力工具,因而,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和政党自然会利用这种工具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文 化。而且愈是当政治斗争趋于激烈时,对传播媒介的争夺愈加剧烈。30年代国民党政权 依靠文化控制(包括控制文化传播媒介)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将自己的政治文化灌输给权 力客体,而权力客体自发拥有的各种“反权力政治文化”也必须通过传媒来扩大其影响 ,尤其是当权力客体处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包括文学在内的传媒便成了他们的重 要的甚至也许是惟一的与“权力主体”进行抗争的手段。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 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和生产状况,产生了特殊的文 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这种政治化趋向具体体现为: 文学群体中成员常常扮演着政治参与的角色,在其政治倾向上各文学群体都多少代表了 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文学群体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封闭性、宗派性、或党派性;每 一文学群体内部在重要的文学观念上大体相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往往不是出自审美性追 求,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 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各派所依据的常常是其政治文化立场 ,而文学自身的要求则往往被隐去。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明显受其政治意识的趋导, 作家的政治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们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处理题材的方式以 及观照问题的角度。普遍的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导致了主导的审美 倾向的形成,造成了某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等等。②
虽然由于20世纪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形势不尽相同,其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也不同 ,但30年代形成的文学政治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在其后的年代里,以其不同的方式得以 沿袭相承,终而成为一种传统。中国四、五十年代直至文革时期的状况,从政治文化的 社会形态来看,与30年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这些年代里,文学依然作为政治意识形 态而受到关注。文学群体的官方化特征非常明显,任何文学组织都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政 府的管理体系之中,政府直接可以用行政手段控制、支配、左右这些文学组织。文学只 能以官方意识形态工具的身份出现,文学不仅绝对不能传播任何非官方意识形态,而且 也绝对不允许不体现官方意识形态,即通常所谓的不允许“脱离政治”。作家没有任何 文学选择的空间,要么放弃创作,要么就是自觉充当这种工具。文学观念的空前一致, 即一切文学主张、文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本源于官方文艺政策而作的种种阐释,或者就 是官方文艺政策的直接的传声筒。与之相关的文学评价标准也主要是基于官方的政治意 识形态,对任何文学作品都无一例外地或从政治上找寻其可肯定之处,或从政治上找寻 其该否定之处,而毫不顾及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愿望。由于官方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有相 当强的灌输力量,由此形成了官方色彩相当浓厚的普遍的政治心态和政治风尚,这又直 接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并导致了诸多特殊文体的流行③。
可以说,中国在20世纪的不同年代中,虽然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不同,但在文学自 身未能获得自足发展的足够空间这方面却是共同的。而文学的政治化传统也始终贯穿在 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到,自30年代以来,政治化的思路就一直左右 着文学的发展,社会政治环境时时变迁,而这种政治化的思路之于文学的支配作用却未 有根本性的改变,这在历年来的文学论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充分。
由于30年代各文学派别的文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并非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 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 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因此,在3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论争中都无不显示出浓 烈的政治化色彩。与20年代的文学论争相比,30年代文学论争的最显著的特点也许正在 于这种政治文化色彩,即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各派所依据的常常是其政治化立场, 而文学自身的要求则往往被隐去了。其间,倍受重视的是说话人的政治态度,站在何种 立场上讲话,是论争各方最为关注的。在30年代发生的几乎所有的文学论争,其背后都 有着政治的潜因,文学论争往往成为论争双方政治文化观念的交锋,即使是争论艺术问 题或仅仅是艺术形式问题,其基本的思路也常常是首先从政治出发或最终将之归结为政 治问题。也就是说,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化语境中,人们看文艺、谈文学,其基本的角 度在事实上都难以超出政治化视角的范围。因为在论争者看来,文学问题事实上已非关 文学本身,而关系到自己政治意愿的表达和政治见解的阐释。参与论争,是获得政治发 言权的极其重要的也许是惟一的机会。30年代文学论争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热情和 兴趣也可以由此获得解释。这种文学论争中表现出的热情和兴趣,其中有很大的成份是 政治的热情和政治的兴趣。但是,当文学的目的完全政治化,文学的言说一旦被系统化 为政治话语,就成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排他性与专一性的系统。这个系统被用来阐发或 攻击某种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用来阐发或反对某种政治理想的合法性。因此,在30年代 的许多文学论争,事实上都明显表现为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借文学表达政治意愿的话 语权的斗争。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获得,才使左翼文坛牢牢雄踞于霸主地位。也正 因为如此,也才使得30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成为了惟一的文艺运动 。
30年代的许多作家,尤其是革命文学的作家,可说是在人格上完全政治化了,在他们 身上,唯政治化的色彩非常浓厚,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 学家人格的政治化。许多作家,他们从事的是文学的事业,但却对政治非常投入,或者 说在自觉不自觉中总是以“政治”考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自然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 化氛围有关,身处这样的环境,政治心理的积存越来越丰厚,在政治心理的潜在支配下 进行行动,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许多作家在一系列的文学论争中,其政治 意识不断加强,甚至对自己的文学见解等也表现出一种“今是而昨非”的态度,以不断 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政治文化人”特点,首先体现为思维的政治化。普遍的政 治化思维弥漫在30年代的一系列文学论争中,这是30年代文学论争的政治化色彩的显著 标识。
政治化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论争中的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为了政治的需要,往 往将相对真理当作绝对真理。30年代论争中,双方所依据的常常是自己的政治价值观, 而不是追求通过论争将问题背后的道理弄清楚。可以说,没有一次论争最后是哪一方通 过讲清道理,以其自身理论的真理性使对手真正心服口服的。事实上,双方论争时所追 求的,也并不是这样一种学理的结果,原本论争并不抱说服对手的目的,仅在表达自己 的政治意愿和阐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因而不去找寻,也不可能寻找到大家普遍接受的 那样一种真理。这样,每有论争,其兴也暴,而结果却总是不了了之。更值得注意的是 ,论争的兴起、结束,大家所依据、所服从的也不是某种真理,而是政治的需要。论争 的当事人不管在论争中表现如何,使用什么样的言词,有什么理论的阐发,但决定论争 进程和结果的,并不是论争的内容和理论探讨的深度,也不在于谁真正完全掌握了绝对 的真理,而在于背后的政治目的甚至政治的操作。人们论争中亦已形成的政治化思维使 他们心甘情愿地循着政治理路,而不是学理的理路。论争的走向,并不是依据是非观点 的是否明确,不在于理论探讨的进展,而在于其背后的政治。与理论的正确与否相比, 当时的人们也许更相信、更愿意服从的是政治权威,是人们政治化思维中的政治实用主 义支配着人们在论争中的行为。
对党派性特别重视,是30年代文学论争中政治化思维的又一表现形式。30年代的文学 论争往往是或主要是发生在不同的文学群体之间。而30年代文学群是以政治倾向的同一 性来划分的,各群体内部统一性高,且具有较强的组织性意识,因而各文学群体大多具 有宗派性质甚至党派性质,即不管群体成员内部思想有何差异,对具体问题的种种见解 有何不同,但在重大问题上,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上,往往一致对外。这种党派性意 识沉积在文学论争的思维中,就使得30年代各群体成员在对外论争中往往是全伙上阵, 处处以本群体为是,以非本群体为非。这种党派性意识有时并不依据形式上是否参加某 个社团,而是依据政治上的倾向自觉地给自己划线,决定政治立场上的归属。对党派性 的强调,在左翼作家群体中显得最为突出。这种对党派性过于看重,由其党派性来判定 言论的是非,而不是依据真理性来判别言论的正确与否,说到底就是一种宗派主义,而 宗派主义在整个30年代文学论争中始终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
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政治化思维有时还表现为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即有很强的政治防 范意识。这种过度的政治敏感,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有时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猜疑。这种猜疑在30年代的论争中 时有出现,例如“领津贴”,在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猜疑的内容,这种政治猜疑内 容在论争中屡屡被使用。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杨邨人就曾说鲁迅“领到 ”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金”④。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一些左翼作家因胡风 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的杂志《时事类编》发表翻译文章,而称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 领津贴”,并猜测疑他为国民党的特务。鲁迅曾揭过《现代评论》派接受过段祺瑞的“ 一千元津贴”的老底,而在与“新月派”的论争中,鲁迅又曾断言,《新月》将代《现 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其后,“新月派”的梁实秋在与革命文学作家论辩时, 便称左翼作家“到×党去领卢布”⑤。“三民主义文学”作家在与左翼作家论战时,也 一再诽谤左翼作家是“藉了卢布的作用”,“领了卢布的津贴”⑥。上述所谓的拿了谁 的“津贴”,有些确实是属于政治上的猜疑,当然也不乏其造谣和诽谤,以此作为一种 谄害对手的手段。这里“津贴”一词实际上成了一种政治的标签,贴上这种标签就是暗 指其投靠了某一政治势力。指称论争对手拿了谁的“津贴”,成了一种陷论敌于不利的 境地的政治手段,或者是通过造谣,借统治者的政治势力来翦除异己,即“借刀杀人” 、“借头示众”;或者是通过这种猜疑或暗示,借民众对统治者的厌恶来将论争对手“ 政治上搞臭”。另一方面,通过将论争对手挂靠到某一政治势力的实体上,将对手推上 政治的极端,目的也在于引起与之敌对力量的“敌忾”,引起己方同道们“全伙”的政 治义愤。
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中,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20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 的许多问题、许多症结可以从30年代找到源头。在其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 们从文学论争、文学讨论乃至文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文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 特点的遗存。因此,有必要对30年代文学论争中形式的一系列习惯、做法、思维等等进 行研究,这对加深理解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许多政治敏 感时期,政治形势、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 在这种时期,各种文学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 适应,或协调或不协调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种种态势的。在30年代以后的年代, 政治形势虽不断变化,但文学论争中的政治化思路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太多的 改变。作家人格的政治化、政治实用主义、宗派主义、政治性猜疑等,在有些年代甚至 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学主张、文学观念基本上是一种作家的政 治表态,或是对某种文艺政策的阐释,所有的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文艺政策的 翻版,而从文学自身规律和从学理角度提出的文学见解却很难见到的。即使有所谓文学 论争,有所谓论争的双方,那也是基于对官方文艺政策理解的差异,而论争的最后裁判 也理所当然地是有关政府部门或官方政治权威,文学的法则完全由政治规则所取代。论 争中不管观点如何差异,其提出问题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角度都颇为一致,即关注对方 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甚于关心其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从而使许多文学论争一再呈现 出是非标准的相对模糊和朦胧的状况,政治化思维掩盖了理论的探讨。
当我们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时,我们看到,文学的政治化,从30年代开始作为一 种重要传统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传承沿袭。鉴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在 研究上述年代的文学现象时,就不能忽略政治化传统之于文学所起的作用。也许,当我 们真正弄清了这种政治化传统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不同年代的文学,并在 多大程度上,到底以什么形式,最终导致了一些文学现象的产生,以及最终支配了文学 发展的趋向等等的问题时,我们会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同时,我们也才会真正 明白,在这一文学传统中,哪些是值得我们努力继承的,哪些是需要我们下决心丢弃的 。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210093
----------------------------------------
注释:
①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42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版。
②参见拙作:《三十年代政治文艺语境与文学氛围》,《文学评论丛刊》第2卷1期。
③参见拙作:《文学与政治:从整合到非整合》,《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
④文坛小卒(杨邨人):《鲁迅大开汤饼会》,《白话小报》1930年第1期。
⑤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新月》1929年11月10日第2卷9号。
⑥林振镛:《什么是三民主义文学》,《民族文艺论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出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