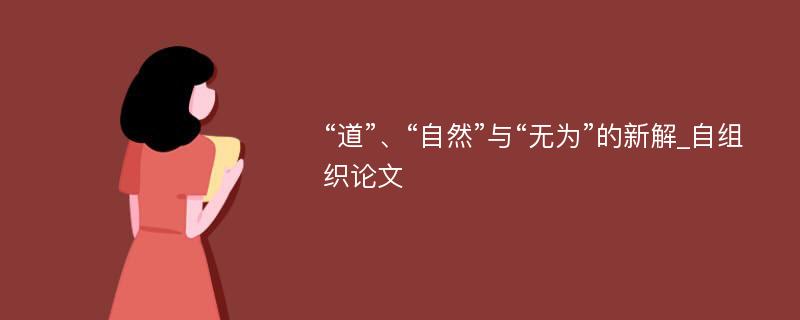
道、自然与无为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解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 (2000)02—0105—07
老子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深奥玄妙的《道德经》,两千多年来,各种训释《道德经》的著作汗牛充栋,然而对它的理解依然没有穷尽,它还时时在为人们提供着新的启发。如今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好几种社会制度,经济、科技与文化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社会、人生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种新的背景下,本文试对老子的“道”、“自然”与“无为”等核心概念做些新的解释,以就教于大家。
一、“道”即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
当今世界的哲学兴趣已经不再像早先那样集中于世界的本源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上,人们的注意力再一次聚集在人本身,把人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社会、历史和传统的背景中加以思考。人对人自身的理解日益丰富完整,日益抓住根本,并深入到人性的深处,从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来解释人的思想与行为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如被誉为一般系统论之父的贝塔朗菲说:“作为最后一着,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如果生活的目的、指导的观念或生命的价值已经衰竭了,那么军事机器,包括最先进的超级炸弹也挽救不了我们。这是由历史变迁中得出的几个稳妥可靠的结论之一。”[1 ](P17)
拉兹洛将这个决定社会运行的因素称为“文化信息库”,他说:“对社会基本活动进行编码的那些准则的总和构成了一个基本信息库,它属社会全体成员所有。这个集体的信息库相当于社会的文化……如果社会的信息库(广义的“文化”)是赶上时代和合用的,那么生产和消费系统就能够恰当地发挥功能并把社会维持在它的环境中。所有必须要有的流体都得到补充,所有基本的下层系统都得到修复或更新。社会是能支撑住的,人与人都能和睦相处并同他们的环境保持平衡。反之,如果社会不能补充那些流体,不能修复或更新它的下层系统,社会就是危机不稳定的,或者说处在一个突变分叉点上,在这种不稳定和不能支撑的状况下,社会成员就必须改进与改变他们的文化形态,即他们集体的信息库,使它现代化。他们要么竭力渡过难关,建立起一种新的有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组织模式;要么他们的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可能会分崩离析,一片混乱,成了比较稳定和强大的敌国可以轻易掠夺和吞并的对象。”[2](P104)
上述作者都是当今西方学术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在看过了他们所谈论的东西后,我们便可发现,老子所说的“道”不正是这些先生所谈论的价值观、文化信息库或者说价值体系吗?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道”不过是老子以象形的方式来表示他所感觉到的那个“物”而借用的名字:任何事物都经历了一个从诞生到消亡的历史过程,这便是其所走过的“道”。每一事物都有其独特的道,自然有自然之道,动物、植物各有其道,各种社会制度有各种制度的道,人有人之道。然而人之道与自然界各种事物之道不同,除了各有不同的发展历程以外,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即人有自觉的意识,在其生命历程中,他的理想、目标,或者说是价值体系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动物只是在自然之手把它铸成之后才来到世上,它只需要实现在它之中已经是现存的东西。”[3](P202 )与动物们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样的生活道路不同,人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自然似乎没有把他铸成就将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没有作出关于他的最后决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成为不确定的东西。因此,人必须独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须试图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他那专属他自己的问题。”[3](P202 )人能否获得充分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人对“人之道”的理解程度。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便可以充分地、全面地发展自己,与社会和自然保持和谐,圆满地走过生命的各个阶段;但如果人们没有能力认识“人之道”,所接受的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就会把人的发展引入歧途,违反人的天性,戕害人的天性,使人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古人已看到的,知识和德行的可能性也包含着错误和罪恶的可能性。人可能把自己提升为一种值得敬慕的、令人惊奇的事物,但‘腐败了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最坏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人也可能利用他自我形成的能力而‘变得比任何野兽更野蛮’。”[3](P203)由于存在着变得更野蛮的危险性, 所以人就有必要研究“人之道”,以引导自己正常健康地发展。这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任何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迟早都要接触到这个主题,老子率先深入到这个深层次问题,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正是其五千言魅力永存的原因之所在。抓住了这个根本,我们便可以连贯地理解这部经典,现以前三章为例试解释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与“可道”、“名”与“可名”所指的是一般的价值体系与具体的发展目标的关系,从理论上说,人具有无限的进化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对这个目标加以定义的话,那就只能是一些一般的方向性的规定,比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斯洛所说的“人的自我实现”等等,而在每一个具体阶段,却又有着具体的目标。在学生时代,我们希望做个好学生,每次考试都得100分;在青年时代,我们希望找个好工作, 成家立业而在每一个行业,也都有着不同的目标,它们引导着人们表现自己的生命。这些说出来了的、写在纸上的具体的目标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常道”的某些要求,但却不是“常道”本身,如果把它们绝对化,作为终极目标,就反而会束缚人的正常发展。比如以分数为标准评价学生,便会引导学生、教师和家长都为争高分而奋斗,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考试、不会做事”。同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对干部政绩的评价,最简便易行的便是经济指标,但如果人们把这一标准绝对化,则会引导干部不顾现实的可能与生态环境的承受力,盲目追求高速度,破坏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
于是老子在第二章便接着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其意思很明白,当人们都知道某个东西是美的善的以后,便都去追求这个目标,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整体效果就不美、不善了。社会的运行状态与每一个人的追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美与不美、善与不善、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等等都是相反而相成的,人们不可能只要其中的一极而不要另一极,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就不能随意倡导什么新的目标,理想的政治制度应当正确地引导人们的欲望,于是接下来在第三章便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尽管老子为了保证社会稳定而开出的药方不好,但他对社会病理的分析却是深刻独到的,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制度或是政治家就必须要注意对人的欲望进行引导。
价值体系在人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它对社会的运行状态也就发挥着重要的制导作用;假如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即“道”在一个社会中没有占据支配地位,而是由一些有缺陷的价值体系占据了支配地位,发挥了主导作用,人们就可以断言,那里的社会运行状态不可能是正常的。比如某些西方国家,人们坚持的是笼统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而社会风尚又不注意把人们往好的方向引导,于是人们便可肆意妄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运行状况就只能是越来越糟糕,诸如政界要人们纷纷被丑闻、绯闻缠身,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在校园里用真枪互相射击,黄色文化与毒品的泛滥等等,都是自然要发生的,就像小牛的头上迟早要长出两只角一样。因而人们只要对某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有所了解,无须实地去考察,便可知道那里的情况。“不出户,知天下。”(四十七章)毛泽东也用不着考察苏联演变的过程,仅仅从苏联领导集团在斯大林之后发生了价值观的转变这一点,就可以准确地预言其“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必然结局。
二、“自然”即存在于各种自然及社会系统中的自组织过程
老子所说的“自然”,如果要想将其翻译成现代用语,最为接近的是现代科学中刚出现不久的“自组织”一词。
所谓“自组织”,是指事物(系统)不是由于外部的强制,而是通过自己内部的组织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的动态过程。拉兹洛说:“凡在出现生命的各种组织层次上的系统,对于要在周围环境中无限期地存在下去而言,……只有能进化出一种复制或再生产自身结构的能力才行。使用H·马图拉纳在60年代引入的一个术语, 我们可以把这类相对高组织层次上的系统称作是自创生的( autopoietic)。确实,细胞、器官、生物体,以及生物体组成的群体和社会都是自创生系统;它们自己更新自己,自己修复自己,并且自己复制自己或自己生产自己。”[2](P45)根据这种理论,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也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可以通过自己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社会是由处在特定关系中的人组成的系统,是人的行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个人的行为举止部分受到有意设立的规章制度的指导,但最终形成的秩序却是自然而然的,更像是一个有机体,而不像是一个组织。”[2](P91)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则做了这样一个类比:“在无生命自然界中,例如在水的液相或固相中,各个分子相互间有一定方式的排列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转而决定水或冰的宏观状态。人类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在不同的政府形式中也是不同的。 ”[4 ](P168)更准确地说,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 人类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处于进化过程中的社会系统,它的宏观状态如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状况造就了社会成员的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制约着每一社会成员的发展水平;反过来人类社会成员的发展水平和行为方式又决定了相互联系的方式,决定了社会的宏观状态,并且面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则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影响和改变宏观环境,为自身的进化创造宏观条件。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老子,他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把自然与社会看作是一个自组织过程了,这个思想是贯穿五千言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十七章)其意思是说,聪明的统治者悠闲自得,少言寡语,放手让老百姓去干自己的事,万事成功遂意,百姓们并不认为统治者起了什么作用,而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然而放手让老百姓自由发展,并不是不管不问,而是要在无形之中发挥影响,用正确的价值体系去引导人的发展,“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由于道与德的尊贵,人们都向而往之,用不着命令,人们都会自然地顺着这个道路走下去。
老子的“自然”除了有自组织的含义以外,它还表示着人和社会的理想状态。老子的“道”所指的是能以保证社会与人性正常发展的价值体系,而不是泛指一般的价值体系;同样的,老子的“自然”所指的是由“道”所制导的社会与人性的成长发育过程,并不包括那些有缺陷的价值体系所制导的不正常的社会与人性的成长过程,这种有缺陷的状态则是不合于自然的。“自然”包括人性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前者是指人获得正常的发展,由生到死,圆满地走过人生的各个阶段,后者是指社会组织得适合于人性的健康发展。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管理者就应当按“自然”的要求来进行管理。在“道”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被摆在比道还高的位置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道”不是来自于某个神秘的意志,它只不过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规律的反映;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就必须要认识、顺应和促进自然和社会的自组织过程,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参天地之化育。这种态度是对普通常见的那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干涉、控制社会过程的做法的否定,然而十分遗憾,精于权术的人难于运用这一管理艺术。“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四十三章)“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五十三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人们用自己的小智来管理国家,他们自己的欲望很多,想把社会和人民都玩弄于股掌之上,干预社会的自组织过程,搞得鸡犬不宁,自己也头破血流,甚至于身败名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七十五章)这样做的结果是倡导出了一种畸形的价值体系,并以这种价值体系来对社会生活进行自组织。
当然,这种自组织过程不是那些蹩脚的社会管理者所有意要做的事。他们也不希望出现“民之难治”、社会的动荡不安等等现象,然而由于他们不知道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其自身对正确的价值体系的践行的密切关联,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无情地剥削民众,恣意妄为,“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但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剥夺别人的人,反过来要被别人剥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最终是“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能强大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老子对社会生活中强弱转化的辩证法体悟得非常透彻。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老节目,在这种经常性的社会震荡中,人们都不可能实现其“自然”。
三、无为而治就是通过调控社会价值体系,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
既然“道”就是价值体系,支配着社会或自然系统的自组织和发展过程,那么,作为有理性的人,应当如何处理与这个自发的过程的关系呢?人作为自然进化较后阶段的产物,比起较早阶段出现的生命形式,他包含着更多的进化层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宇宙的进化都浓缩在人的身上。从人在自然进化中的这种地位来看,人必须理解整个自然的进化,并承担起保护自然、促进这一进化过程的责任。这种对自然进化过程的意识与责任感,是人性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的产物。老子是早熟的,他率先体味到这种感情。然而绝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清醒的意识,在大自然的进化过程中,人获得了最珍贵的成果——理性,但很多人却不知珍惜,不是将其用于有价值的目标,而是肆意滥用,干涉自然的进化过程,破坏自然和社会系统的正常发展,甚至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欲而肆意妄为。现在最令人不安的意外事件不是来自自然界,而是来自人类自身,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受到自然界的报复,人类为了眼前利益而进行的开发往往都会带来一系列难于估量的影响深远的灾难性后果,老子的“无为”便是对此进行救治的药方。
“无为”不是什么事也不干,而是认识到社会生活的自组织过程,从而自觉地促进这一过程。在人性的发展与社会的自组织过程中,价值体系发挥着制导作用,老子看到了这个因素,力倡一种能保证社会稳定、人生幸福的价值体系。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悟道,于是就需要有悟道早的人来进行传播引导工作,把“道”和与之相应的行为规范灌输到社会生活中去,用它来对社会生活进行自组织,从而使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秩序自发地呈现出来。为此,领导者必须率先垂范,“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五十四章)老子的价值体系与普通人的争强好胜截然不同,他所身体力行的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老子希望,通过“侯王”或“圣人”的倡导,使人民群众接受这些价值观,“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四十九章)在倡导这些价值观的同时,他也还要运用权力,“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六十三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六十四章);当危害社会稳定的不良倾向刚刚生于毫末时,就及时地予以解决,不让其酿成大祸,所以他能在不动声色中实现治理社会的目标。采用这种方法,社会管理工作只能是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无事可干,以至于无为,这便是无为而治所要达到的境界。
社会的自组织机制是一个客观存在,社会管理者如果不认识这一机制,那他的管理工作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无论是有为还是无为都不能把社会管好,便会宽严皆误。进一步来说,无论是无为还是有为,都不过是社会的自组织机制借以表现自己的方式,谁也逃不出它的手掌。老子要求人们无为,无非是要人们认识这一机制,顺应这一机制,不做无益的举动,在社会管理上由盲目转为自觉,免去许多由于错误的社会政策而给社会造成的不协调、痉挛与动乱,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个人悲剧。无为而治即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把社会稳定的目标实现在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引导中。“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六十三章)不要轻易地倡导什么,在倡导一个目标之初就已经把人们追求它所带来的社会整体效应都估计清楚了。“事无事”即是通过现在所做的事要使将来无事可做。要是等到问题出来了再去想办法解决,那就是“事有事”了。这种人虽然很忙,胼手胝足,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夙夜操劳,人们亲而誉之,但仍不能算是高明的政治家,因为靠他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把天下的事都办好的。当然,在没有更好的政治家的情况下,碰上这种人也已经是老百姓的造化了。最倒霉的是遇上了这样的管理者,即他们不了解个人追求与社会宏观目标的关系,一方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出一种骄奢淫逸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不想要与之相应的结果,想强制地实现另外一种想当然的目标,那就是自己与自己打架,社会不受他的控制,他想做好事,却带来了更大的混乱,人民“畏之”、“侮之”,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但最终受其祸的还是人民群众。与这些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滥用权力甚至于胡作非为的当权者们相比,老子实在是高明得太多了。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老子所具有的那种对自然与人的进化过程的深厚的情感,他“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二十七章)因此他可以把对社会与自然的自组织过程的认识运用于救人救物的目的。但倘若人们不具备老子的那种情怀,而是怀有自利之心、骄矜之色,那他在把对社会与自然的自组织过程的知识运用于社会管理上时,便会演变为机诈权谋,这种做法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自己都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然而有两个问题,老子的解答不能让现代人感到满意。第一个问题是,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可是,在一种价值观已经相当混乱的情况下,也即是说在民心已乱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让人们回到无知无欲的状态呢?也就是说如何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转换呢?老子也说过,“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三十七章)但这个“无名之朴”是什么,如何“镇”,老子语焉未详,所以就留下了一个谜让后人去猜测。
第二个问题是,一定的人格理想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如何把社会生活组织得适合于人性的“自然”,老子也避不开这个问题,最后提出了“小国寡民”的政治模式,历史的发展已表明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在当时无法实现,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整个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小村庄的现在,更是无法实现。
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稳定是社会在趋向于进步发展的过程中所必须保持的动态稳定。而在老子看来,为了保持稳定,可以牺牲社会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都可以弃而不顾。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会很自然地走向极端,主张使社会回到原始状态,这是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相违背的。他自以为是“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实际上却对人类永不安于现状的天性不理解,企图以自己简朴无欲的生活来规范普通百姓、规范历史,这是办不到的。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必须要经过私有制这个历史阶段,人类必须要经过这口欲望沸腾的大锅的煎熬,才能把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培养出来,为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创造条件。因而不是像老子所设想的那样“镇之以无名之朴”,回到原始的无知无欲的状态,而是要进一步提升人性。在挣脱了私有制的束缚之后,人类才能驾驭私有制社会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联合起来的人,将以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达到这一境界,人类首先必须要同旧的价值体系彻底决裂,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用它来对社会生活进行自组织,在这个更高的历史发展层次上,老子所说的“无为”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2000—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