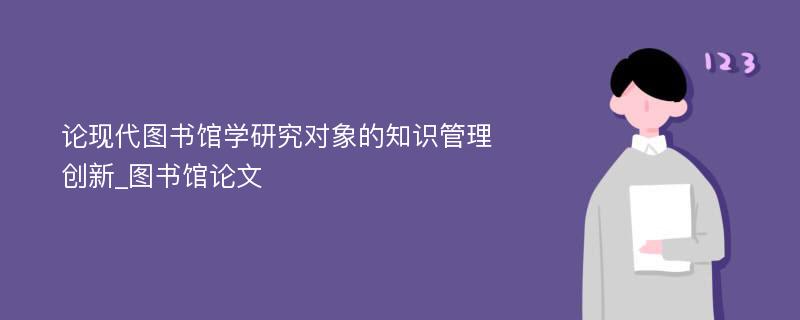
知识管理对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知识管理论文,研究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近几年来,国内出现了知识管理的研究热潮,但是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是介绍和跟踪国外知识管理的理论进展或企业知识管理的,而对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互动的研究很少涉及。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促进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创新和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全面发展[1]。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是确定图书馆学是否可以取得独立地位的前提条件,也是该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形成该学科基础理论的奠基石,它规定了该学科的性质、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2]。笔者拟从知识管理对现代图书馆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对象的创新这一视角来进行初步探索。
1 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概述
1.1 第一阶段——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
此阶段把图书馆视为整体系统来研究并考察其在社会环境中的功能,主要有如下两种观点:
·“社会说”。认为应将图书馆置于社会之中进行考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记忆”或“社会精神”的移植过程。代表人物有巴特勒、谢拉、阮冈纳赞、卡尔斯泰特、王振鹄等。
·“要素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各个组成要素。代表人物有陶述先、杜定友、刘国钧、藤林忠、石塚正成等。
1.2 第二阶段——本质的、规律的认识阶段
此阶段是从图书馆内部的文献、知识与文献信息及其交流来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种观点:
·“管理学”,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不论是机构、过程、资源还是事业,归根结底都是研究对它们的管理。代表人物是孟广均。
·“交流学”。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交流或知识交流,它包括“文献交流学”、“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学”,代表人物有谢拉、丘巴梁、周文骏、宓浩、刘迅、黄纯元、倪波、荀昌荣等。
·“知识学”。认为以知识为核心的图书、图书馆和读者间的互动关系与发展规律是图书馆的研究对象,其代表人物是彭修义。
·“规律说”或“事业原理说”。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及其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或者说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的科学。代表人物有A·H·郝罗帕奇、吴慰慈、邵巍、董焱、何善祥等。
·“图书馆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其代表人物是ю·H·斯托里亚洛夫、H·M·弗鲁明、李景新、黄宗忠、金恩辉等。
·“矛盾说”。认为藏与用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其代表人物是黄宗忠。
·“系统说”。认为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系统,其代表人物是郭星寿。
·“活动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活动。其代表人物是K·H·阿勃拉莫夫、沈继武等。
·“信息时空说”。认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有序化信息时空”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其代表人物是叶鹰。
1.3 第三阶段——深入的、整合的认识阶段
此阶段是从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和文献资源等方面进行整合研究,包括:
·“综合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或者说图书馆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和文献信息。其代表人物是桑健、谭迪昭等。
·“资源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其代表人物有切尼克、徐引篪、霍国庆。
1.4 第四阶段——知识管理阶段
此阶段重新回到文献本身包含的信息与知识上,把对知识信息的组织、整理与集合视为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如下几种观点:
·“知识基础论”。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对象,客观知识的主观化是图书馆学的认识论对象,客观知识的组织是图书馆学的方法论对象。这3方面的整合构成了图书馆学对象的完整结构。其代表人物是蒋永福。
·“知识集合论”。认为知识集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其代表人物是王子舟。
·“知识管理论”。认为在当前,知识是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图书馆工作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是对知识的组织管理;图书馆的工作对象由文献单元深入到知识内容单元,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只能是与知识管理直接相关的一种社会化工作机制或者服务机制。其代表人物是吴慰慈、罗志勇、邱均平、顾敏等。
2 知识管理对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创新
分析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在21世纪来临之际,研究者的目光又重新回到文献本身包含的知识、信息上,这可以说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轮回”[3]。这表现为从1807年施莱廷格提出“图书馆学”至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研究对象的认识是从表象的具体的认识开始的,所形成的“整理说”、“技术说”、“管理说”等观点基本上是围绕图书文献实体的组织与管理(包括技术应用);在现代图书馆学阶段,研究对象经过多次否定与否定之否定之后不断走向深入:由整体的抽象的认识如“社会说”、“要素说”发展到对图书馆本质认识的抽象(包括“交流说”、“规律说”、“矛盾说”、“图书馆说”、“系统说”、“活动说”、“信息时空说”等),再到深入的整合的认识如“综合说”、“资源说”,直至目前刚涌现的“知识管理”诸观点(包括“知识基础论”、“知识集合论”、“知识管理论”等)。那么知识管理能否创新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基本问题。
2.1 知识管理与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
笔者认为,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这个定义体现了知识管理对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创新。我们常说的知识管理是指对知识及其创造、收集、组织、传播、利用与宣传等相关过程的系统管理。广义的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进行管理,而且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4]。不管是广义上还是狭义上,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和利用是与知识管理紧密相关的。
从狭义方面来看,各种知识信息(包括传统文献、电子文献和网络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是现代图书馆的工作核心,读者的信息需求是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出发点,服务依然是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主线,信息资源建设是现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5]。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基础理论和文献资源建设专业委员会2000年工作暨学术研讨会”上,代表们认为面对网络环境和知识经济,图书馆学研究再也不能仅从图书馆这个实体来进行研究,而是要顺应跨学科研究的潮流,考虑将现代情报技术与图书馆学结合,进行一些面向网络信息用户的研究,同时不断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和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法,并指出现代图书馆不能是网络化的藏书楼,而应充分体现图书馆特有的知识组织和深加工功能[6]。明确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上述选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弄清现代图书馆学的本质属性与基本职能,还有利于我们重新构建适应时代需求的现代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最终促进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从广义方面来看,现代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而且要研究和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有关的人力资源、组织机构、信息技术、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等诸多问题,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已经渗透到许多学科和技术领域,涌现了用户视角、知识视角、技术视角、事业视角、管理视角等研究现代图书馆学的多元视角[7]。而“知识管理不仅仅是信息和数据的管理,也不仅仅是指信息技术。知识管理的一个目标是识别有用的、相关的知识,去组织、吸收及综合知识,以及促进创造性地使用知识”[8]。今后图书馆学研究应引入管理学思想,积极参与到知识管理领域中,一方面解决图书馆内部的知识管理问题,另一方面研究社会上各类组织机构中的知识管理问题。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应考虑如何有效地组织、控制知识资源,促进特定组织机构(包括图书馆)的知识共享和创新,服务于组织机构的发展目标[19]。由此看来,以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图书馆学研究能够促进图书馆学和知识管理理论与技术的整合,实现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创新。
2.2 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是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基础
·历史基础。在以往的研究中,尽管一些观点并没有全面和明确阐明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是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它们拥有一些合理内核。如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在193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引论》中指出,图书馆学的基本要素就是社会的知识积累,并由它连续不断地传递给生活着的一代。英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1976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中指出,图书馆是一个保存和便于利用文字记载的系统,是一种社会工具,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怎样获取、吸收和传播知识,必须在图书馆学专业理论中找到依据。
我国学者宓浩、刘迅、黄纯元在1988年指出:“当我们考察图书馆现象时,可以发现图书馆是一个具有复杂层次结构的社会实体,图书馆活动是这个社会实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对文献的收集、存贮、整理、组织、传递和利用,则是图书馆活动内容的具体体现”[10]。
·现实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把知识管理理论与现代图书馆学发展联系起来,试图从某个切入点来探讨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例如马费成(1998年)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基本目标与任务就是组织知识和信息并提供服务[11]。
王子舟(2000年)认为,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转移至知识集合的命题上来。所谓知识集合,是指用科学方法把客观知识元素有序地组织起来,形成专门提供知识服务的人工集合。知识集合不仅包含了图书馆,也包含了百科全书、辞典、书目、索引、年鉴等工具书以及各类知识数据库。图书馆学以知识集合为研究对象,就要对所有类型的知识集合进行分析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图书馆”这个客体上。知识集合在客观知识世界中是一个独特的家族,它是一种多层次的、立体的研究范畴[12]。
蒋永福(2000年)认为:“图书馆不仅对客观知识进行社会化的公共存贮与组织,而且还为了适应个体人知识记忆的需要,其内部活动也是按照个体人的知识记忆结构模式组织起来的。图书馆的这种职能与组织特点,就是为了实现人们客观知识主观化提供社会保障。其实图书馆正是为了满足人们实现客观知识主观化的需要而产生的专门化的社会组织。图书馆组织客观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客观知识主观化的需要,这就是图书馆学为什么把客观知识作为本体对象的意义之所在,同时也是图书馆学为什么把客观知识的主观化作为认识论对象的原因之所在”[13]。
顾敏(2001年)认为:“图书馆学基本上是一种研究知识成长的学门,不同时代的图书馆,融合了各种不同因素的研究,但其总目标则在于知识的成长。图书馆学门与知识管理有不可解除的关系。早在以图书象征知识的年代里,图书馆自然就是知识管理的单位。……知识管理是图书馆学门整体应用于事业集团或社会各层面的使命,知识领航则是图书馆学门为知识管理所做的具体的知识传播服务。……图书馆学门永恒不变的宗旨当是促进知识成长,提供知识服务”[14]。
·实践基础。长久以来,图书馆一直在进行知识管理的工作,只是图书馆员过度强调专业自主的特性,反而忽略了对本身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的管理[15]。在实践中,存在着图书馆概念“泛化”的现象。首先,图书馆工作可以被认为是从事知识的收集、存储、组织、控制、传递、发掘和创新的过程;其次,在虚拟知识空间中,针对用户需求跟踪信息源,进行信息发掘和增值加工,提供专业化信息服务,已日益成为图书馆的显性职能;再次,图书馆界已经认识到,在当前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中,人们已经从技术(IT)回归到内容(content),对知识内容管理的重视程度增强了。图书馆学研究必须果断地参与到知识管理领域中去,也就是要求图书馆学从知识存取的视角,研究如何帮助用户发现知识、获取知识、利用知识。图书馆的工作对象既已由文献单元深入到知识内容单元,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只能是与知识管理直接相关的一种社会化工作机制或者服务机制。因此,图书馆学研究不能忽视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知识管理的若干特征(如重视知识增值和创新)将推动图书馆学研究超越传统图书馆机构的局限,面向更广阔的实践基础[16]。
2.3 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赋予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以创新意义
首先,此定义发展了“社会说”、“知识说”,丰富了“交流说”、“资源说”,集成了“知识基础论”与“知识集合论”,具有“知识管理”的特征。
“社会说”将图书馆界定为移植人类记忆或客观精神的社会机构,确定了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坐标,促进了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但它只取得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整体的抽象的认识,并未提示其中本质的规律性的内容。“知识说”把图书馆工作与知识联系起来,认为“图书馆学要研究知识、图书、图书馆的发生规律;研究它们相互间以及与读者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研究知识的性质和内容,结构和功能;研究图书的收藏与利用,藏书的建立与更新;研究图书和读者、图书馆和读者如何通过知识这一中介而联系起来,以及知识如何通过图书和读者表现自己的存在和实现自己的转化”[17]。虽然它以知识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图书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并未得到业内的共鸣,从而也就没有得到发展,由此说明这种观点并不完善。而以“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作为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不仅阐明了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具体作用,发展了“社会学”;而且它继承了从知识这个角度来研究图书馆学,但同时又摈弃其纯粹的知识学观点,强调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是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而非与知识有关的所有方面,从而使现代图书馆学有别于知识学。
“交流说”首先反映在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中。谢拉指出:“社会认识论要研究整个社会中起作用的所有交流形式的形成、流通、协调和消耗,图书馆正是交流锁链中重要的一环。由此,谢拉把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建立在社会认识论基础上的图书馆工作根植于社会知识文化之中,从根本上讲,图书馆工作就是知识的管理”[18]。但谢拉的“社会认识论”仅仅是一种观念,并未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交流说”在我国可分为“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和“文献信息交流说”3种观点。“文献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本上是利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工作的经验的结晶;“知识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交流”;“文献信息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交流。尽管“交流说”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跨越了从图书馆这样一个具体机构本身认识图书馆学的表象认识阶段,进入了从信息交流角度认识图书馆学本质规律的阶段[19],但是图书馆学研究并不局限于文献(或文献信息、知识)的交流,按照巴特勒的观点——“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社会装置,而图书馆则是将人类记忆移植于现代人的意识中去的社会装置”和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法则”——书是为了用的,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省读者的时间,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原理,我们就可知道图书馆学不仅要研究知识信息的交流,也要研究它们的组织和利用。因而,以“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作为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丰富了“交流说”内容。
“资源说”认为图书馆是针对特定用户群的信息需求而动态发展的信息资源体系,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与过程[20]。它是迄今为止对图书馆本质的最深入与最全面的论述。不过,该理论在承认“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同时,却没有说明以“信息资源体系与过程”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有什么区别。以“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作为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一方面明确了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而非所有与知识信息有关的领域,从而有别于信息资源管理学,也有别于企业知识管理;另一方面它继承了“资源说”的合理内核——抛弃了以图书馆这个实体概念来作为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而直接指向现代图书馆的工作实质。因此,它是对“资源说”的扬弃。
“知识集合论”认为,人的知识主要来自于客观知识世界;知识集合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主要媒介;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它认为把知识集合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有助于厘清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拓宽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地位[21],但是实质上,“知识集合”是一个模糊性概念,它在揭示图书馆本质时,既无法将“原生态知识集合”与“再生态知识集合”严格区分开来,又无法将“知识集合”与“非知识集合”泾渭分明地划界,因而“知识集合”并没有反映出图书馆固有的根本属性,也就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22]。笔者认为,知识集合仅是图书馆知识组织的一种重要方法而非所有方面。以知识集合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确实加深了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但它不是“拓宽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而是把图书馆学研究框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只是知识集合,而应该是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
“知识管理论”认为,在信息时代,图书馆工作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是对知识的组织管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也只能是与知识管理直接相关的一种社会化工作机制或服务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学研究就有可能融入更广泛的知识经济活动中去,一方面从广阔的实践基础上汲取学科营养,发展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也会扩大其适用范围并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虽然目前“知识管理论”初见端倪,基于知识管理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并未建立,但是以“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来作为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将有助于实现传统图书馆与知识管理的整合,最终建立起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虽然笔者认为图书馆学与知识管理同属于管理科学,但知识管理不仅重视显性知识,也重视隐性知识,不仅重视知识创造,也重视知识利用。它关注知识是如何在一个社会组织与机构中运作并发挥作用的;而图书馆学虽然也对隐性知识感兴趣,但它主要关注的是显性知识是如何采集、整序、储存、加工、交流、接受的。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向来所重视的知识是可以编码的、外显的、公共领域的、理论性的知识;知识管理所看重的却是动态的、难以编码的、内隐的、个人领域的、实务性的知识,是与企业营运目标与管理目标紧密相关的“know—how”。因此,知识管理的精髓在于如何把存在于员工脑中的内隐性、经验性、未编码性的知识加以外显化,以便分享、管理,成为组织的智慧资本。如果把知识管理的知识流程分为生产、收集、整理、储存、组织、传递、利用、分享至创新(再利用)一连串知识活动的话,那么,图书馆学偏重在知识的收集、储存、组织阶段,而知识管理则更重视知识在生产、传递、利用、分享与创新的阶段[23]。在这一点上,图书馆学与知识管理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两者之间不宜画等号[24]。
其次,此定义标志着图书馆学范式的转变。图书馆学的范式是图书馆学研究者所共有的东西,即专业的一些科学准则和范例,专业或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共同的传统、学科发展的共同方向,就是用来解决图书馆活动实践问题的基本原理方法[25]。以“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作为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有助于实现现代图书馆学范式的转变。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突出了现代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管理科学。尽管人们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如社会科学、应用性科学、管理科学、综合性科学等),但是以“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图书馆学突出了管理科学的特征,因此笔者主张现代图书馆学应定位在“管理学科”这一坐标上。这正如吴慰慈所说:“当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组织管理知识的一种社会化工作机制或者服务机制,这种机制确切地说就是一种管理过程。图书馆学也研究社会现象——知识本身内在的逻辑性以及人类认知过程(抽象、压缩、存储、再现等)——这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指导知识管理的实践。……在当今时代,图书馆学应属于管理学科”[26]。②创新了现代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内容。不管现代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以“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内容都将发生改变,集中体现为把知识组织、知识检索、知识管理理论与技术添加到原有体系中,使现代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③挖掘了图书馆学新的知识生长点。图书馆在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知识中心、文化中心、信息中心,图书馆有发展成为知识型企业的趋势[27]。现代图书馆所关注的活动不完全或甚至不是信息的。他们所从事的是保存、传播和使用来源于各种途径的任何形式的已记录知识,以便于人类变得更加有见识;通过知识达到理解的境界,最后,作为终极目标,获得智慧[28]。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知识组织和信息组织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关于元数据、人机界面、知识检索语言、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成了现代图书馆学的知识生长点。④标志着图书馆工作重心的转变。道林早在1984年就指出:“今后的图书馆是全国信息网络中的一员。图书馆员的任务是在特定的框架内收集、存储、检索,根据图书馆所在社区的特定需求提供增值(value added)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在信息时代,有无增值服务则决定着图书馆能否继续存在”[29]。实际上,目前图书馆正经历着这样一种转变:工作重心从书本向人本位转移,业务重心从第二线向第一线转移,服务重心从一般服务向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转移[30]。这种转移体现了知识管理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具体应用。因为“图书情报机构知识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捕获、挖掘、利用、传播知识,为读者提供有效的知识共享平台,为读者提供获取图书情报机构可公开的知识信息窗口,以帮助读者做出最好的决策,同时提升图书情报机构的形象,在为读者知识服务的过程中促进自身的发展”[31]。这正如迈克尔·凯夫利所说:“知识管理对图书馆的最直接效果体现在图书馆与信息工作的转换中,以及图书馆文化由‘服务提供’到‘增值服务’的转变”[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