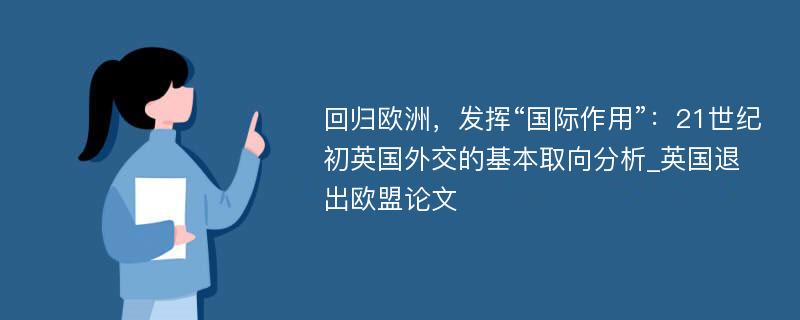
回归欧洲与充当“国际角色”——--21世纪初英国外交基本取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英国论文,取向论文,外交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一些国家在世界历史演变中发挥的作用曾经非常特殊,并且影响持久而深刻。英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人们愿意用“工业革命”、“海上霸权”、“世界工厂”、“殖民扩张”、“日不落帝国”以及“英美特殊关系”、“欧洲化”、“帝国情绪”等许多特有的词汇来描述和分析英国曾有过的辉煌以及回落过程中的无奈。直到今天,许多战略家和学者关注和研究英国,很大程度仍然在于英国还是世界上比较独特的国家。不了解大英帝国的历史,就难以理清几百年来世界发展的线索;而反过来,对于整个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深入认识,往往也会使人们对有关英国的某些疑问消解于无形。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中,英国仍不时表现出非常独特的一些方面,需要人们用心去探究推敲。
冷战结束后,英国在大西洋两岸乃至世界的地位随着欧洲和世界局势的迅速演变而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英国外交,随之也进入到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转化过程,并延续到新世纪,到目前其对外政策已经显现出基本的取向。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欧洲地缘战略结构的变化对英国外交选择的影响尤其不能忽视,英国受到的限制比起冷战时期又进一步增加了。逐步回归欧洲可视为英国一种无奈而理性的选择,但与此同时,由于仍具备一些独特的资源和条件,英国将不可能放弃发挥国际作用充当“国际角色”的各种机会。在伊拉克战争中对美国的追随既可以看做是英国发挥“国际角色”的冲动,也反映出“英美特殊关系”的惯性。未来英国在回归欧洲与发挥国际作用之间难以做出极端倾向性选择。在动态中寻求两者的适当平衡和相互支撑虽有很大难度,英国却只有借助于此才能尽可能维持其外交的特殊性,继续发挥某种超出其自身硬实力所及的国际影响,尽管未来这种影响很可能将继续受到削弱。
一、在欧洲地缘战略结构变化中逐步淡化的地缘优势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国一直都没有停止向一个正常的中等强国回归,它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在起伏波动中没能表现出明显的起色。到今天,英国外交政策的选择范围和主动性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世事沧桑,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精英们做梦也想象不到这后来巨大的变化。英国归向平常国家虽然有其必然性的一面,(注:英国的这种回归可以认为是世界体系整体运行的一个必然结果。有关分析可参阅唐永胜:“英国真的衰落了吗?--兼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王振华、刘绯主编:《变革中的英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但同时也与世界范围一些大的事 变紧密相关,并由此形成不同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战胜国,但是战争中经 济、金融遭受重击,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战舰,英国霸权的基础已经极大地受到削弱 ,支撑起来的是帝国的空架子。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仍然是战胜国,但实力更是遭受 了空前重创。在二战中英国与美国结成了“特殊关系”,但主导者并不是英国,而是洞 察力逊于丘吉尔的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一切都已今非昔比,随之而来的民族解放运动 则更是彻底打破了英帝国的残梦。而冷战的结束对英国的影响虽然不易察觉,但却深刻 而持久。面对日益协调统一的欧洲、领导世界愿望强烈的美国和处于深刻变革中的世界 政治,英国进一步失去了发挥传统平衡作用的空间。简而言之,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削弱 了英国发挥特殊作用的各种条件。
从地缘角度看,英国以一水之隔,游离于欧陆之外,无疑这曾是非常优越的优势。长期以来,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一直具有基础的甚至首要的战略价值,地缘政治角逐的悠久历史揭示,优越的地理位置能带来巨大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优势。岛国的地理位置使得英国可以超越欧陆上各国的纷争而巧妙施展外交谋略的手腕,19世纪的英国自不用细说,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远离欧陆的英国也得以顽强固守住本土,并成为盟国反攻的一个重要的前进基地。冷战时期,英国虽然跟随美国,却由于远离东西方对峙的地缘争夺前线,而能够比较超脱地处理与美苏的关系,甚至成为联结东西阵营的一条重要而独特的线索或桥梁。然而时过境迁,英国的地理优势在今天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地理空间因素依然重要,但毕竟已经不再具备那么多传统意义上的战略价值。如果说英国具有自己的优势,其他一些国家也不乏自己的 优势,甚至拥有更大的优势。德国不是岛国,但它从过去东西树敌到今天的左接右联, 其所具有的优势比英国也许更为明显。
另外与以往不同的是,英国已经不再面对一个破碎或分裂的欧洲,而是一个经济政治日益一体化的欧洲。对于英国,这更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事变。东西方对峙的地缘分界线已经不复存在,西方的影响迅速扩展,英国面对的是日趋一体化的欧洲和合作竞争并存的美俄关系,它能施展外交才能的余地意外地缩小了。在欧陆,边界的功效已经渐渐改变,因为边界已经划分不出一个破碎的欧洲,日益增多的跨国联系使各国彼此获益。日趋统一的欧洲淡化了英国的作用。
在冷战后欧洲地缘结构的变化中,不能不提到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不注入新的活力,欧洲联合的发展就有停滞的危险,因此,欧盟需要通过范围的扩大来获取能量,因为“欧洲如不能变得更加团结,就将可能回到分裂状态”。(注: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BasicBooks,1997,p.199.)与此同时,北约对于一些国家,也许首先对于美国,仍然有 存在的价值,如果不能推动北约的扩大,美国就可能逐步脱离欧洲的主旋律,因此美国 会抓住北约这一纽带继续维系它在欧陆的存在。可以认为,新一轮的欧盟东扩和北约东 扩背后都存在着权力政治的强劲动力。东扩必然带来欧洲地缘界限进一步向东移动,并 且这种界限已远不如冷战时期那么清晰。欧洲地缘战略重心向东移动的重要结果之一, 就是欧陆一些国家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其中德国的情况最为突出。比较而言,英国在欧 洲乃至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却在不自觉中被削弱了。统一的德国、仍然活跃的法国和日 益一体化的欧洲等等,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这些客观现实的存在。对于美国也是如此, 要维持它在欧洲的主动地位,就不可能在英国和欧陆之间选择前者。
虽然目前美国在一些极端行动和选择中(如伊拉克战争)往往需要拉住英国,但为了维持在欧洲的存在,为了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美国更需要与欧洲核心国家进行协调,在许多事情上将越来越多地越过英国直接与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其他有较重要地缘政治价值的东欧国家打交道,而美英之间表现出来的一些密切举动往往有故作姿态之嫌。布热津斯基曾有独到预见,在他看来,英国甚至已经不能算作一个地缘战略棋手:“英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重要选择,对欧洲前途也没有宏伟的构想。它的相对衰落还降低了它在欧洲发挥传统的平衡作用的能力。由于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比较模糊,并同美国保持着一种日益淡化的关系,英国在欧洲前途有关重要选择方面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注:Zbigniew Brzezinski,op.cit.,p.42.)布热津斯基的战略嗅觉无疑是非常敏锐的,他关于英国的上述分析包含着对历史的经验理解和对未来的深刻洞察。当然,布热津斯基还认为“伦敦已经基本退出了欧洲棋局”,(注:Zbigniew Brzezinski,op. cit.,p.43.)这可能就有些过于低估英国应对外界变化的韧性,同时也在不经意间自然 流露出了一种对美国前景过于乐观的情绪。
二、回归欧洲的无奈与必然
历史上英国的欧陆政策,曾深受其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特有岛国文化的影响。其中“光辉孤立”就很具代表性,其目的就在于在处理欧洲事务时能够保持行动自由,免受预期性盟约的约束,充分体现了英国文化中保守主义、功利主义和制衡观念的巧妙结合。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随着实力的衰落和国际局势的发展,英国在欧洲再也不能以那么超脱的姿态置身事外或灵活地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必要的干涉,而是被欧洲事务所深深牵动,并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即便如此,英国对于欧陆仍然保持着距离和戒备。二战结束后,欧洲逐步走上了联合的轨道,对此英国从特立独行到勉为其难加入欧共体,再到逐步适应欧洲,甚至要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欧洲,在犹豫和曲折中透露出许多无奈。
英国外交素以理性见长。当加入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性逐渐展现出来时,英国人被迫踏上了这条路。(注: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56页。)面对欧洲地缘结构的重大变化,尤其是面对欧洲日益深化的经济、社会乃至 政治、安全领域的一体化进程,英国如果不能更多地融入欧洲,就很可能在欧洲联合的 潮流中被彻底边缘化,远离欧洲核心,从而不仅失去一体化能够带来的各种好处,并且 在国际事务中也将失去本应有的依托。不能跨越英吉利海峡,实际上也不可能跨越大西 洋;一个对欧洲都无足轻重的欧洲国家,也不能指望它在世界上会发挥多么大的影响。 麦克米伦的判断是简练而有力的:“孤立的英国对英联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相信他 们是明白这一点的”。(注:《麦克米伦回忆录》第6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9页。 )因为现实迫使英国不得不去靠近欧洲,去争取在欧洲更大的发言权,以通过影响欧洲 ,进而连接美国和牵动世界。实际上,70年代加入欧共体后,英国要想远离欧洲已经不 可能了。自从工党在1997年5月上台以后,英国的对外政策又进行了调整,其中“最根 本的变化是英国与欧洲关系的转变”,(注:Robin Cook,“Britain and Europe:A New
Start”,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1999.)英国开始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欧洲事 务。科索沃战争后,英国更是反复强调要推进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在欧洲独立防务 问题上,英国虽然认为大西洋联盟仍然是欧洲安全的支柱,但是也意识到“英国不能总 是需要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行动,欧洲应当能够承担起这一负担的更加平等的份额 ”。(注:Robin Cook,“Britain and Europe:A New Start”,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1999.)
1998年12月,英法两国首脑在法国圣马洛的会晤可谓标志性事件。在这次会晤中,英法双方发表了《关于欧洲防务的联合宣言》,强调欧盟应该具有解决危机而自主采取行动的军事能力。后来的科索沃战争打乱了欧洲建设的步调,在危机中和危机后欧洲的“无所作为”令欧洲人非常尴尬,“欧洲不仅没有自卫能力,甚至不能维持自己的秩序,在一个范围小、实力弱的地区完全独立地进行有效的维和行动”。(注:布热津斯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欧洲”,《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但经过这次危机,欧洲毕竟认识到了与美国在战略目标、行为方式、政治理念等许多方面存在着抹不去的差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英国基本上还是追随美国的,但战后在政界和思想界却有很多人重新对欧美关系和英美关系进行深入思考。这次伊拉克战争又是如此。在战争中,英军与美军共进退,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英国又开始与法德频频接触以修补一度紧张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英国还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模式:与欧洲在安全领域的协调虽然一直在增加,但只要美国发出战争的召唤,英国虽然不一定十分情愿,但总会积极响应,而与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拉开了距离。英国回归欧洲的轨迹不是直线的,在安全领域尤其容易出现反复。
布莱尔担任首相后,多次强调只有通过欧洲英国才能发挥全球性作用。这种认识无疑是非常现实的。在欧盟内部甚至已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法、德、英形成某种主导性三角关 系的前景。问题在于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实在难以割舍,至少到目前英国还没有找到与美 国拉开适当距离的有效办法。英美关系中有种历史的惯性在起粘合作用,至于回归欧洲 的感觉则已经不那么熟悉,不那么自然,其中包含着过多的无奈和被动。
布莱尔不需要多花时间向他的前任学习就会自觉地努力去使英国的对外政策与白宫的步调合拍。执政初期,布莱尔与克林顿就曾建立了十分融洽的私人关系。后来在美国新总统上台后,布莱尔巧妙地利用了“9·11”事件和随后的阿富汗战争,迅速地与布什靠近,布什也将其视为密友。但是,美国的一些霸权做法毕竟是令人生厌的。2003年初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前,英国媒体曾做过一系列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在对伊拉克动用武力方面,布莱尔对布什跟得越紧,民众的支持率就越低,因为反对攻打伊拉克的英国人数要明显高出同意攻打的人数。实际上,在战争开始前的几个月中,就连美国民众支持 对伊采取军事行动的比例也有所下降,甚至白宫内部对是否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才能对 伊动武也存在分歧。这样的情况下,布莱尔应该站在哪一边呢?也许只有碰运气了。当 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枪声一响,布莱尔不得不随之行动,否则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岂不成 了空谈。可是英国民众却不一样,很难舍得自己的亲人冒着生命危险去讨好美国。如今 战争已基本结束,布莱尔需要回到“现实”,既要面对国内的种种压力,也需要重新加 强与欧洲的协调。
麻烦还远不仅来自英国国内民众的意见。不顾条件地跟随美国,在欧洲在全世界都会感到压力,因为强权毕竟不得人心,并且往往会遗患于未来。几年前,乔治·凯南在评论北约东扩时就曾尖锐指出:“东扩必然会引起许多国家的反感,很有可能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注:George F.Kenann,“A Fateful Error”,New York Times,February 5,1997.)表面看来,后来事情的发展似乎并非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只不过在于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面对美国的强势而放低了姿态而已。而实际上,“9·11”事件的发生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受到过度的压力就会产生变形的反弹。处理国际问题和危机不能过于依赖强权,所谓“失败国家”产生的根源深远而持久,在亚洲、非洲、拉美等一些灰色地区存在难以控制的贫困固然有相关国家内部的原因,但更由于世界体系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在发挥作用而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美国不能独自解决世界上众多的问题和矛盾,加上英国也远远不够,需要全球范围的共同努力,其中主要力量的协调更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追随美国并不一定等于顺应世界潮流,只是目前有许多难言之隐,即使内心难受也不得不跟随行动。
对英国回归欧洲起基础和长期作用的应是经济因素。一段时期以来,英国对欧盟的贸易额一直是对美贸易的3至4倍,英国与欧盟的相互投资上升很快,到目前已经基本赶上英美之间的投资规模。英国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离开欧盟是难以实现的;而以现实和未来 的经济潜力,欧盟对英国贸易和金融资本的吸引力将会逐步增加。除贸易和投资之外, 是否加入欧元区,是对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检验。一旦加入,英国的欧洲特性将得 到难以逆转且实质性的增强。英国加入欧元区的具体条件本来是比较成熟的,甚至比一 些欧元区国家的情况更优越,但却下不了决心加入进去。布莱尔政府曾表示要尽快就是 否加入欧元区进行公民投票,而近来民意测验显示,虽然持赞同意见的民众似乎有所上 升,但还不占多数,英国加入欧元区至少在近期内难有结果。然而,如同当年加入欧共 体一样,欧元区能够给英国带来的经济政治利益至少比可能带来的损害要小。海底隧道 已经将英国与欧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英吉利海峡不再成为天然的阻隔,那么英国 在货币领域也难以长期远离欧元的统一进程。
有许多人说,布莱尔回归欧洲动力不足,或仅停留在口头,因为英国有时与美国绑得太紧。分析问题不能过于注重个别事件而将其推向极端,用较长一些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英国回归欧洲也许更有效。回归欧洲不是绝对的,更不可能是直线式的,有时会被动一 些,有时主动一些,有时步伐快一些,有时步伐慢一些甚至间有反复,但这一进程毕竟 在总体上没有停止过,英国从20世纪中期以后一直逐渐在向欧洲回归。冷战的结束更使 英国失去了退路,与十几年前相比,今天的英国无疑更像一个欧洲国家了。未来只要欧 洲的一体化进一步发展,英国继续回归欧洲的进程也将难以逆转,尽管它会要求享受比 其他欧盟国家多一些的例外,比如强调应该依靠欧洲国家和政府间的有效合作来解决欧 洲的问题。(注:尤其对于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布莱尔既认为“欧洲需要加强能 够对新的危险迅速作出反应的武装力量”,也强调“这种力量的部署是由各国政府决定 的事情”。这里存在一种矛盾心理。)
三、仍具充当“国际角色”的条件及前景
英国向欧洲的回归实乃时势使然。但由此做出21世纪英国将演变为一个普通欧洲国家的判断,却可能是轻率的。道理就在于,如果完全融入欧洲,英国本来就在日益减弱的特殊性将不复存在。
英国与一些中等强国不同的是,它手中握有历史和传统沿袭下来的仍然可观的国际资源,尤其包括无形的软资源。底蕴深厚的外交传统、英联邦的遗产、遍布世界各地十分成熟老到的金融资本以及几个世纪与列强交往的丰富经验,即使在经济模式上,英国也以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不同于德法等国受到国家抑制的资本主义,(注:德尼兹·加亚尔等:《欧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594页。)等等,凡此种种无一不为英国国际作用的发挥提供着历史背景和现实可能。也就是说英国还具备一定的条件担当较为重要的“国际角色”,这种情况在与英国幅员和人口相仿的发达国家中非常少见,或至少在程度上不如英国。
今天英国追求或能够追求的这种“国际角色”与世界性大国并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概念,与“世界霸主”更相差甚远。“国际角色”是在当前国际局势总的背景下,英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利用自身国际资源影响世界的一种姿态、努力及结果的综合。英联邦、“英美特殊关系”的凝聚力虽然不如从前,但毕竟都还存在并能维持;经济、金融和文化各种纽带或网络都有着超出人们想象的渗透力,在这些方面英国比很多大国并不逊色;甚至与中国的关系也由于香港的存在而有深入发展的契机。
“三环外交”曾是二战后英国外交的主旋律。通过“三环外交”,英国比较灵活有效地处理了实力衰落后与世界的关系。至于反恐战争以来布莱尔的“枢纽外交”,也是不 甘心把英国的作用和影响局限在欧洲范围的一种政策应对,只是如何做到“通过影响美 国而影响世界”,似乎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的至关重要性对英国 不言而喻,但是过于注重一条途径是缺乏战略耐心的表现。而在实际上英国能够利用的 国际联系远比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或“天然关系”这一条线索要丰富复杂得多。
一个中等强国要担当“国际角色”要求其外交有很强的适应性,而这也正是英国外交多年来表现出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由于实力的削弱带来的难堪往往被有着深厚外交传统的英国人在不经意间回避过去或轻描淡写地应付过去。有时即使在似乎左右为难的困境中,英国也会找到比较体面而灵活的处理途径。比如,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与法国都遭到了美国的羞辱,但是两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大国雄心”促使法国强调独立,而英国则选择了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对于英国外交,基辛格博士曾深有感触,认为其“具有适应环境变化而调整自己的不寻常能力”,(注:Henry Kissinger,Diplomacy,Simon & Schuster,1994,p.612.)早些时间,陈乐民先生也曾明确指出:“英国外交的总势均是在被动中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从不放弃表现主动性的任何机会”。(注: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在可预见的将来,回归欧洲与充当“国际角色”,如同英国外交的两个轮子,缺了任何一个都运行不起来。如果两者协调得好,就会相互促进:英国由于有了与欧洲的紧密联系会加重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而由于有“国际角色”的辅助则增加了介入欧洲事务的砝码。但如果协调不好,则可能两者皆误:回归欧洲流于空泛而进一步远离欧洲核心,国际作用的发挥也缺少足够的支撑而徒有虚名;或可能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在 亚洲和美国之间有顾此失彼之嫌。如果仅从硬实力上比较,日本也许已远远超过英国, 但是由于历史包袱或负担过重,加上在处理一些问题时过于粗线条,日本在与太平洋两 岸关系中的回旋余地远不如周旋于大西洋两岸的英国那么大。
未来充满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即便以21世纪初叶不长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也将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认定英国将在回归欧洲和发挥国际作用之间做出某种倾向性的单项选择,说服力还是不强的,也不符合英国外交的特点。未来英国将最有可能向一个普通 的发达国家继续回落,向欧洲回归,但同时也会在内外部资源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地继续 担当其“国际角色”。这种回归和“国际角色”的发挥有其必然性。冷战结束以来,国 际政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国际关系中非零和游戏越来越难有施展的空间 ,这一变化具体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中,将越来越不利于非此即彼的简单取舍。 当然,在国际政治的变化中,来自前面曾提到的欧洲地缘战略结构变动对英国带来的影 响也许最不应忽视,因为它从基础上作用于英国外交的选择。
有的时候,即使是最两难的矛盾,当我们用系统的观点来看时,便会发现它们根本不是什么矛盾,(注:彼德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71页。)正所谓“鱼与熊掌可以兼得”,不选择胜于做出选择。排他性的选择有可能产生更大的消极影响,顺时而动才更具有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国际关系的进步为各国提出新的限制但也提供了新的机会,只要能够尽快找到它的脉动特点,就会创造新的空间。由此看来,英国的外交绝非是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做危险的骑墙游戏。欧洲核心不可能约束英国与其进行充分一致的协调,而美国也不会愿意承担迫使英国在美欧之间做出抉择而带来的风险,因为在分裂欧洲的同时,也必然分裂了整个西方,甚至英国社会内部也将出现分裂和动荡。如果美国过于强化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很难设想英国将一如既往地紧紧跟随美国采取一致行动,过去密切的配合与协调将被日益增多的顾忌和有条件所取代。因为如果严格按照美国当前谋求绝对安全的逻辑,就会与更多国家发生冲突和战争,甚至欧洲也不例外。(注:David P.Calleo,“Power,Wealth and Wisdom”,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2003.)
有人会存有疑问:历史上英国曾经抓住过转瞬即逝的机会,一跃而成为世界的霸主,而为什么今天就难以重领世界风气之先?实际上,不仅对于英国,对于其他任何大国或许都是如此。国际政治对国家的规范随着国家间联系的迅速增加而空前加强,机会越来越难以青睐个别国家。国际潮流将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必须更慎重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普遍联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日益增多的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合作中施加自己的影响。减少极端战略途径和手段的选择与运用,于人于已都会有益处。从英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中至少可以看到某种难得的品格,那就是顺势而为,不强为不可为之事,从而降低了权力结构变化过程中发生剧烈危机和震荡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