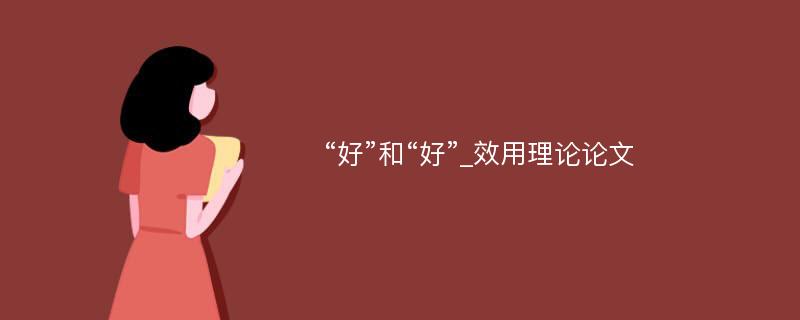
“对的”与“好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伦理学中有二大主流,即是效用主义(旧称功利主义)和道义论。效用主义自边沁和穆勒等人开始以来,曾主导西方伦理学一百余年。但自1971年约翰·劳尔斯出版了《正义论》以后,[1]逐渐衰退,其主导地位为道义论所取代。我相信效用主义,但同意传统的效用主义(行动效用主义)和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兴起的规则效义有其缺点。因此,我把效用主义修改重构,称为统合效用主义理论,[2]并确信这重构的统合效用主义可以避免所有这些缺点,也就是可以驳斥对效用主义的所有反对理由而成为一种能够存活的伦理学理论,而且比道义论更好,更为合理。本文所称的效用主义,系指我的统合效用主义。当然,统合效用主义和传统的效用主义仍有许多地方相同,也有若于地方和规则效用主义相同。但是统合效用主义有其与传统效用主义及规则效用主义都不相同的特色。这些特色,与本文有关者,以后提到时再予讨论,与本文无关者,此处不赘。
本文主要讨论“对的”和“好的”间的关系,这也是效用主义与道义论间的主要差别。效用主义和道义论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其对于“什么是对的?”和“为什么这‘什么’是对的?”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效用主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好的就是对的”。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填入第二个问题的“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成为“为什么好的是对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效用主义的终极原则即效用原则之证立。穆勒的“效用原则的证明”不够清楚和完备,因此引起许多问题和争议。[3](P33-41)
道义论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正义就是对的——但是正义并不等于好的。”因此同时也否定了效用主义的答案。其第二个问题成为:“为什么正义是对的呢?”这是道义论的最终证立的问题,但其回答也并不清楚和完备。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我的统合效用主义的立场,来澄清好的和对的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效用主义者,我先要驳斥道义论的说法,然后建立统合效用主义的说法。
如果,依照道义论的说法,好的并非全是对的或并不完全符合于正义,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结论是对的或正义与好的或效用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相提并论,当然也不能加以比较了。例如一张纸和一块石头,我们可以比较其重量或大小等性质,却不能不指定性质而凭空比较。另一种结论是对的或正义凌驾于好的或效用,不论其好到什么程度。这就意味着对的或正义具有无限大的效用,也可以说它是绝对的。这绝对的说法乃相当于道德原则和规则之不可以有例外。我将没有例外的原则和规则称严格的,而将可以有例外者称为非严格的。根据道义论,道德原则和规则应该是严格的。
以下我将顺序讨论下列三个问题:(1)好的与对的之间的关系,(2)对的或正义与好的或效用是否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不可比较?(3)对的或正义的绝对性或道德原则或规则应该是严格的或是非严格的。
二、“对的”先于“好的”吗?
效用主义者认为好的就是对的。因此效用原则主张社会效用的最大化或促进好的。这基本、终极原则之证立在于人类之目的性。人类需要也意欲生存、进步和繁荣。这一般性的目标是被经验地肯定的。一般性原则之肯定导致了以社会效用的最大化或好处的促进作为基本原则,这原则我认为也是效用主义对‘对的’之定义。[4]
道义论者,相反地,并不认为对的就是好的,因为他们坚持,至少在若干情景中,当事者并非为促进好的而采取行动。因此,对的被认为与好的无关。但即使依照道义论,这种情况也只限于少数,故道义论者对好的并非等同于对的或不一定就是对的这说法仍需要一个证立。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证立是对的是先于好的。即是说,对的、或由道德原则或规则所指示为对的行动,系产生于对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之前,因而应该被认为并非等同于好的。
很多道义论者认为对的是先于好的,如马格儿·商代尔所描述:“对于道义论者……对的乃先于好的。”[5](p7)H.A普列查特也说:“……我们的是非感并不是我们对好的或其他任何事物的了解之结论。”[6](P9)
这里我企图从我的统合效用主义观点澄清这好的与对的间之争议。[2]我从“先于”这术语之意义开始。我认为“先于”有二个不同的意义:“一个意义是对的行动之发生与对的行动所产生的好的后果之发生这二者间的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这我称之为“事实上的先于”;另一个意义是:“行动后果是好的这知识和行动是对的这知识之先后次序”,这我称之为“知识上的先于”。注意这二个意义并非从一特定行动之观点言,也不是从一特定个人之观点言,而是从整个社会或所有人类观点言。
无疑,道义论者对“先于”的概念是第一种意义。一个行动产生后果。所以一个对的行动发生在其后果或好的发生之前。这样的先于概念不限于单一的行动,也可以推展到一个人的整个人生计划。人生活在一个已经有道德原则和规则存在的社会中。这些原则和规则告诉人什么是该做的对的事或什么是指导人建立人生计划的约束。于是,在人建立其人生计划之前,对的这概念就已经在那里了。因此,对的这概念被认为先于好的这概念。
我认为道义论采取“先于”的第一个意义是一个错误。在考虑对的与好的这二者关系所采用的“先于”的意义应该是它的第二种意义,即是从社会的观点之意义,或是从好的和对的这些概念之发展的观点之意义,即是知识上的先于。
众所周知,效用主义是后果论的,因而与新自然主义相容。根据哈利·宾斯横格的观点,人类不但是目的论者,并且是最高水准的目的论者,即是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目标。”[7](P84-103)好的意指人类所追求之各种价值。因此,即使一原始末开化的人也感知到好的事物,而具有关于“好的”之知识。但是关于“对的”或是关于道德之知识,则是在社会组成以后才产生的。为了要解决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冲突,才有必要建立一套社会规则,而道德原则和规则仅是社会规则集合中的一个次集合。所以对的这概念是确切地产生在好的这概念之后的。
以上说明对的先于好的之不合理。但即使对的并不先于好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好的。效用主义主张好的就是对的,需要证立。道义论主张对的不一定是好的,也需要说出“什么”是对的,并且证立为什么这“什么”是对的。
我先要从对的这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说起。站在效用主义的立场,我认为这些原则和规则的来源都是经验的。
三、道义论对“对的”之证立——直觉和自明
对的这概念由道德原则和规则所传达,而这些原则和规则是历史上逐渐发展出来的共识和概括。我相信所有道德规则都是如约翰·劳尔斯所说的概括规则,而并非他所提出的另一种,即惯例规则。[9](p3-32)我的意见是,惯例规则是任意的。它们仅适用于游戏,却不适用于道德。这里所谓的任意的并不是说游戏规则是完全随便决定的,而是说它们并不一定是最适宜或合理的。它们的决定不一定要最佳化。
兹举一个篮球游戏篮子位置高度的例子以说明篮子高度这规定的任意性。篮球的篮系置于某种高度。当人类的平均高度逐渐增长时,将篮球投入篮中的机率也逐渐增大。目前篮球比赛的记录常在100点以上,远高于多年以前的平均记录。假如把篮的位置提高二尺,我相信要将篮球投入篮内将远较目前为困难,而比赛的记录也将远比目前者为低。这样的游戏也许更为有趣,而比目前还高二尺的高度也许更为合理。但是目前我们并未改变篮的高度,也没有对目前的高度抱怨或认为这种高度是错的,或许就是因为篮球是一种游戏,其规则是任意的之缘故。
至于道德规则,则并不是任意建立的。它们的建立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即是所谓的证立。这里是效用主义与道义论间的主要区别之所在。现在先讨论道义论的证立。我认为道义论的证立则是模糊而非确切界定的。传统上,西方道德概念中的证立是上帝,而儒家道德概念中的证立是天道。目前大多数哲学家不再用宗教信仰来作为道义论道德的证立,而由直觉来取代并成为主要的证立。但直觉并非是终极的理由,它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证立,自明似乎是终极的证立。例如,在道义论者中,H.A.普列查特和W.D.劳斯似乎相信直觉之自明性。普列查特道:“我们应该做某件事情的感觉在非反射性的意识中产生,这是一个由我们所身处的各种情景所造成的道德思索活动。”[6](P16)劳斯道:“一个行动……之为自明的乃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是指从我们生命的开始或当我们第一次注意命题时就自明的这意义,而是指另一意义,即当我们已经足够成熟或对命题已有足够的注意时,才自明而无需证明的。”[11](P29-30)
如吉拉特·F·高斯所指出,劳斯之“原则,虽然是自明的,但并非先验的。”[10](P27-42)照我的意见,这些原则在人类的经历中有一经验的基础,不仅是当事者作为个人的经历,且又是社会或所有人类的经历。这样,直觉之根源存在于经历之概括和情感、知觉,以及价值判断之共识中。所以原则和规则一定是概括规则而并非绝对的惯例规则。这是与道义论者一般所相信者相反的。
直觉原初是主观的。它们随人而不同。即使有一共识或规范,它仍不是真正客观的。因此在我的效用主义的价值通论中,我称之为“准客观”。[11](P33-34)一条准客观的原则或规则不应视为绝对的。我同意吉拉特·F·高斯对道德直觉的看法。他道:“道德直觉可以了解为具有原初的最小的可信度,乃自行证立至一最小的程度。这可保持它们作为根本直觉的身份,但它们距离自明的真理则仍是太远了。”[10]
也许是由于“自明直觉”的证立之不足或不完全,兴起了若干高斯称之为“对的为优先之薄弱诠释”。[10]例如大卫,高铁之“因同意而道德”[12]和约翰·劳尔斯之正义的契约理论[11]俱系属此一范畴。就我所见,这些对于对的优先之薄弱诠释并不对其证立有多少帮助,因为若自明的直觉可以用于薄弱诠释,它也可以用于正常的诠释;而若它不可用于正常诠释,它也一样不可以用于薄弱诠释。正常诠释的推理与薄弱诠释的推理之间,似乎并没有区别。这些理论将不再在这里讨论。
吉拉特·F·高斯建议一种论据以支持对的先于好的之看法,称为以原则为基础的价值。高斯道:“这个道义论方法始于这样一种观察,即我们的许多价值;就价值之预设道德原则之证立而言,系奠基于道德原则的……所以友谊之价值在概念上系预设诚实为道德所需要者。”[10]我的意见则认为高斯刚好将好的和对的之次序颠倒了。人类在他们建立人应该诚实这条原则之前先感知并享受友谊之好处(价值)。如上面所述,优先次序不应限于一个特定个人的经历,而应该扩展至全人类或社会之经历。对一特定的个人而言,在他(她)感知到任何好的事物之前,即出生于一个有道德原则的社会中。所以我认为高斯也混淆了我上面讨论的先于的两种意义,而采用了错误的意义。
萨穆尔·佛利门在他对劳尔斯理论中对的概念之诠释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佛利门道:“像这样,对的之优先界定了可准许的目的之理念和(道德上)可准许的好之理念。可准许的好之理念是那些理念其目的和行动乃依照对的之原则之要求者。”[13](P33-63)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道义论对对的或正义之主要证立是直觉,而对直觉的证立则是它的自明性。但是,如上所述,这自明性是很薄弱的,并无足够的说服力。
四、效用主义对“对的”之证立
现在我将说明我对对的或正义的统合效用主义的证立。我会争辩对的并不先于好的,但即使我争辩得很成功并证明我这样说是对的,这仍并不一定意味着好的就是对的。迄今为止,传统(行动)效用主义和规则效用主义都未明确表明这一点。这也许是为什么现在效用主义者不及道义论者那样多的主要原因。但我曾经发展出一种统合效用主义理论[2]和一种效用主义的价值通论。[11]根据我的理论,亦即是依照我对效用主义的诠释,好的就是对的却可以获得证立。这并非本文的主旨,故我仅将把我的推理简单描述如下。
在主观的直觉与道德原则的客观的“真理”之间自然有一鸿沟存在。在我的效用主义的价值通论中,我用偏好来界定效用,并主张效用和价值都是主观的。”[11](P18-29)但是人类有一生存、进步和繁荣的共同一般性目标。任何客体对作为主体的各个个人的价值,虽然是主观的,但是有一统计性的分布。若此分布是集中的,那么就有一规范或共识。事实上,道德原则和规则,作为概括规则,就是这些规范和共识。于是,虽然效用和价值是主观的,人类仍然在寻觅并建立这些规范或共识作为社会规则并将它们视为客观的真理。我称这些规范或共识为“准客观的”。再者,这些规范或共识是经验的,是经过长时期的调适而形成的。所以它们是概括规则。它们当然不是绝对的,并且可以随时间而改变。
于是,我的一串效用主义的推理可以简单重述如下:人类有一种要生存、进步和繁荣的一般性目标,它从个人推展至整个社会。好的乃代表人类为了生存、进步和繁荣这一般性目标而追求之价值。就非道德性行动而言,它们并不影响对别人和社会的效用,所以任何能使对当事者的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自然是当事者应该采取的行动,因为这行动能达成一般性目标。就道德行动而言,因为它们影响对别人和社会的效用,所以我们必须也考虑对别人和社会的效用。因此,我们建立一套作为指导纲领和约束的道德原则和规则用以指示何者为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的行动。这里发生了对的这概念,它自然并非先于,而是后于好的这概念。
在主张将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视为对的行动之效用原则与对当事者作为个人的好处或效用之间还有一道鸿沟存在。即是说,我们应该怎样从一个对的非道德性的行动推论到一个对的道德行动。穆勒的效用原则之证明企图跨越这个鸿沟,但是有很多哲学家对这个证明持保留态度。对于这个推论,我有我自己的论据。简单言之,我认为一个能使社会最大化的行动也能平均地或统计地使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效用最大化,虽然在一特定的情况中,一个对的道德行动并不一定使当事者的效用最大化(当道德满足感的效用并未计及时)。举例说,我们有一个道德规则:“我们不应该偷窃”。现假定有一小偷,他的道德满足感很低,意欲采取一偷窃行动。若他采取了不偷窃这对的行动,那么这个不偷窃行动自然对他自己并不产生最大的效用。所以,“平均地或统计性地”是一必要的关键点,它完成了好的(社会效用)就是对的(行动)这命题的证立。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依照效用主义好的就是对的。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它是一个定义。[4]效用主义特意界定那些产生最大社会效用的行动为对的行动,因为增进好处的行动达成了人类的一般性目标,为常识所普遍接受,并且平均地或统计性地间接对社会每一成员产生了最大的效用。
五、正义的性质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上面提及的另一个问题,即“对的或正义与好的或效用是否具有不同的性质?”也就是说对的或正义与好的或效用二者是否可以相提并论或加以比较?道义论者的主张似乎是二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因为在许多说明效用原则与正义原则冲突的反例中,他们假定根据正义原则的选择应该是J,根据效用原则的选择则是U。这意指U的效用比J的效用为大。这显然表示他们未把J的效用考虑在内。如果赋予J一个很大的效用,那么U的效用就不会比J的效用大,而效用主义者也就不会选择U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道义论者又坚持正义凌驾于好的之上,不论好的好到如何程度。这一点将于下节中讨论,此处不赘。
对的或正义如果凌驾于好的或效用之上,这一定是经过比较的结果,但是比较些什么呢?如果是重要性或用处,那么这就是由效用所代表的。根据我的说法,效用是一个普遍量度。既然正义与效用二者性质不同,除了重要性或用处以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地方。所以这里是道义论的无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说二者性质不同,另一方面又说正义凌驾于效用之上。
至于效用主义的说法,则是明确而一致的。效用是一个唯一的量度,所以正义也可以用效用来衡量。当我们比较不同性质的事物之用处时,我们把这些不同性质事物的用处都投射到效用这一维度上。注意,我们比较的不是这些不同性质的本身,而是它们的唯一的共同点,即是效用。
其实正义本身也可用一重大的效用来表示这种看法并非由我首创。黑斯汀·拉什代尔在很久以前就有一类似的看法。他道:“当正义被给予它应有的作为对社会和其中每位个人的真善的一部分之地位时,我们可以说增进整体的利益永远是一个义务。”[14](P260)汤姆斯·斯肯伦认为分配的平等和程序的公平作为价值乃存在于事物之状态中。他道:公平和平等常作为独立的有价值的事物状态而显现于道德论据中。在被这样看待时,它们乃有异于标准的效用主义中所促进之目标,因为它们的价值并不存在于它们对特定的个人们是好的东西;公平和平等并不代表个人们可以获得好处的方式。它们毋宁可说是事物状态或社会制度之特殊的道德上欲求的特点。[15](P99-100)
在我的效用主义的价值通论中我根据一条“可替性定律”而将价值依照人生中的美好事物而予以分类。[11](p82-91)那些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系统、制度和惯例等是个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之一种,我称之为社会价值。于此可见社会价值其实是应予促进的好处。
拉什代尔称这种价值为事物状态或社会制度之特殊的“道德上”欲求的特点,吉拉特·高斯却指出它们不必被视为道德价值。高斯道:
但并无理由假定平等和公平的好处必须这样被视为一种道德的要求;公平和平等可以视为非道德性的好处。若一个理论要求复式的好处,即包含对个人们的好处和事物状态之优良特色,而所谓对的就是促进这复式好处之最大化,那么,在给定好处间某种互换率的条件下,这理论是纯粹目的论的。[10]
我完全同意高斯对复式好处的看法。事实上,要确定事物状态的价值是道德性的或非道德性的并不是重要的事,因为在我的统合效用主义理论中,效用是一个单一的,所有的价值都可以投射上去的维度。所以不同种类的价值也可以主观地予以比较。
当社会是优良的而到处都是公平和平等时,公平和平等的价值不容易被认知。但是当发生一件不公平或不平等的事故时,这不公平或不平等所造成的伤害或负效用却很容易感受到。我们常自然而然地提升基准点到没有不公平或不平等这一点而认为这状态是具有零价值的正常状态。这也许是为什么事物状态的价值不被计及的原因。
六、正义之绝对性和规则之严格性
现在我将讨论好的和对的所引起的另一个问题,即是对的或正义之绝对性以及道德原则和规则之严格性。道义论认为对的或正义有其绝对性,或至少有些道德原则和规则是应该严格的,即是没有例外的。我的效用主义的看法则是认为对的或正义并没有绝对性,而道德原则和规则也应该都是非严格的,即是可以有例外的。上面曾经提到另一个问题,即有些道义论者认为正义是绝对的,这就意味着道德原则和规则必须是严格的,亦即是不可以有例外的。
南西·但维斯曾清楚说明道义论者之绝对主义。她写道:“道义论者告诉我们道义论的约束是绝对的,我们有义务节制自己勿达犯道义论的约束,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拒绝达犯将引起很恶劣的后果。”[16]
很多道义论者主张绝对的原则和规则是确实的事。例如康德的绝对主义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完整的义务,康德认为不论遵守这些义务的成本是多么高,达犯它们总是错的。查理·佛拉特道:“有些事情你无论如何一定不可以做。”[17](P9)爱伦·陶乃肯也说:“谋杀是不准许的。在负责的人之间有自由通讯的情况下,表达一个并不持有的意见,对任何人而言,即使是为了一个好的目的,也是不准许的。”[18](P88)
约翰·劳尔斯表示正义比任何多么大的好更为重要,也是绝对性的意思。他道:“每个人都有一个以正义为基础的不可侵犯性,虽整个社会的利益也不能凌驾于其上。”[1](P3)罗伯·奥尔森也道:“道义论伦理理论是这样的:至少有些行动是有道德上的义务性的,不论其对人类的后果是福或是祸。[19]
但是也有若干道义论者并不强烈坚持绝对主义。例如苛脱·贝尔接受道德规则有例外之可能性。[20](P117)伯拿特·乾脱也反对绝对主义。他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即任何规则都以被破坏而当事者并不被认为作了不道德的事。为了自卫,即使杀人常也被认为道德上可以证立的,而为了救人一命而毁弃一个承诺通常也并不被任何理性的人认为不道德。”[21](P70)
也许是由于证立道义论论据之困难,如吉拉特·F·高斯所指出,“在当代道德理论中,对的优先之说法乃被典型地被理解为一种较为温和的说法。”[10]这可在马格儿·商台儿的证立中见到,即是这样“一种证立形式其中最初的原则是在这样的方式下提出的,即这方式并不预设任何人的最终目的,也无任何确定的善的概念,”[5]这也可在大卫·高铁的不预设任何对善的实质的概念的“同意而道德”中见到,[12]也可在约翰·劳尔思的“善的薄理论”中见到。[16]
道德原则和规则之绝对性是相当于说道德原则和规则为严格的。规则不仅为道义论者所采用,规则效用主义者也采用规则,甚至于行动效用主义者也采用规则,不过这些规则都是经验规则。我称这些规则为不严格规则,并且也采用它们。
我现将讨论一条道德原则或规则应如何陈述或诠释的主题。首先,我将道德规则(原则)依照其是否容许例外而分为二类:(1)严格的,(2)不严格的。[22](P503-578)哲学家对道德规则有不同的分类。例如约翰·劳尔斯将规则分为惯例的和概括的。[8]大卫·莱翁斯将规则为分理论的和实际的。[23](P145)这些分类,虽然与我的严格的和不严格的有些相似,但却是依照规则的内容或起源而分的。我发现我的依照形式而分为严格的和不严格的这种分类最为确定和清楚。所谓严格的规则我意指它根本不容任何例外,而不严格的则可以容许例外。再者,由于诠释规则所引起的复杂性,实际上可以说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存在:(1)一道德原则成规则并无但书或列出的例外,而这原则或规则系了解为严格的。(2)一道德原则或规则系仅为普通情况而陈述,却有但书或附一特殊情景的例外表。(3)一道德原则或规则附有一容许例外的笼统但书或并无代书或容许的例外表,但这原则或规则则了解诠释成不严格的,相当于容许有例外。
我们很容易看到,形式(1)易于导致逻辑的矛盾和道德的冲突。例如,若我们有“人不应该说谎”和“人不应该毁弃承诺”两条道德规则,可以有这样一种情景发生,即是我们只有这样两种选择:要么说谎而遵守承诺,要么毁弃承诺而不说谎。若两条规则都成立,那么道德冲突就发生了。
在形式(1)的情况下,却解除冲突的唯一办法是将原则或规则排序,即是将所有原则或规则依其优先次序而排列,俾排得高的原则或规则永远凌驾在排得低的之上。在这种情形下排得低的原则或规则,既被排得高的原则或规则所凌驾,就成为不再是严格或绝对的了。这也许是为什么有些道义论者,例如斯丹雷·I·朋,接受单一的绝对原则,却不接受众多的绝对原则之缘故。[24](P70)
即使采用了原则或规则的排序方法,这方法仍遭遇到下列二个困难。一个困难是当原则或规则的数目很大时排列本身的困难。当原则或规则很少时,排序并无严重的困难,但当原则或规则数目很大时,要作一个适当的排序将有严重的实际困难。事实上一个道德典包含许多道德规则,其数目是相当大的。
第二个困难不仅是较第一个困难更为严重,而且是决定性地使排序不能成立。由于道德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在各种不同程度遵守或达犯一条道德原则、德目或道德规则,而达犯的内容也有不同的大小。[25](P125-142)例如再考虑“人不应该毁弃承诺”和“人不应该说谎”这二条规则。假定某人处于这样一种情景中,他不可能同时遵守承诺而又不说谎。即是他必须要么毁弃诺言,要么说谎。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毁弃一个小承诺而不说大谎比较好,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说一个小谎而遵守一个大诺言要比较好。于是,基本上不可能将两条规则排列一个优先次序。再者,即使一种次序已经排定,假定“不毁弃承诺”要比“不说谎”更为重要,但当在一个小承诺与一个大谎间发生冲突时,这冲突的解除就成为不合理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事者可能会怀疑这排序之对否而不一定会盲目遵照这次序。因此,形式(1)是不适切的。
承诺之有大小和有时有理由可以毁弃一个小承诺也为规则效用主义者勃拉特·霍干所接受。他说:
兹说明如下:假定人们遭遇这样一种情况,毁弃一个承诺是避免受到福利损失的唯一办法。他们会不会毁弃承诺呢?若选择是在一重大损失与遵守一小承诺之间,他们会毁弃的。但若选择是在一小损失与遵守一关于重要事物之严肃承诺,则他们就不会毁弃了。[26](P531-552)
霍干承诺不同的环境会导致义务间冲突之不同的解除方法。他又写道:
规则后果主义者及劳斯式多元论者同意一普通义务之严格及其相应的厌恶视环境而定。既然普通的义务是有限的而非绝对的,对二个义务间冲突的正确解决在某些情况下会不同于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者。有无数的情况可以发生普通义务间的冲突。所以事实上也有无数的普通义务间的冲突。[27]
形式(2)将例外列出使其不包含在规律所包括的范围之内。这是留给当事者在遭遇到这样一种例外情况时决定怎样去做的。严格而论,这伦理学理论已不再是周延的了,因为这理论不涵盖有些情况。但是这问题并不严重,因为任何在这种情况中所采取的行动可视为非道德性的行动。举例说,若白谎或仁慈的谎被认为我们所不应该说的普通的谎言之例外,那么在这种我们是否应该说白谎或仁慈的谎言之情况中,不论我们是否说了这样一个谎,这行动并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所以这伦理学理论仍可视为周延的,意思是其所涵盖的范围稍为缩小,将例外的情况和人们有道德歧见的情况不算在内了。但是现在又发生这些基本问题:“谁来决定何者是例外和何者不是?”和“这种决定之证立何在?”要决定某种情景是否应该认为是例外与一条规则是否应该系列于道德典之内具有同样的困难。再者,虽然在一正常的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对于道德规则的意见大致相近而可有一规范,但他们对于例外的意见则可能较为分散。例如,我们大多数人同意我们不应该说谎,但是对于白谎是否应该认为是例外这一问题则一定有争议性的。
再者,即使范围不引起严重问题,仍有一实际的困难存在于形式(2)中。要列出所有道德规则的所有例外情况将是一件了不起的难事。即使一部道德典已经建立起来,它将如法律一样复杂,故很少有人能读完并学到整个道德典。法律与道德之间有一显著的不同。在法律事物中,有专业人才,诸如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等了解、诠释、应用和执行法律。因此,一个普通人不需要学习、查考和使用法律,除非他被牵涉在一件诉讼案件之中。但在道德事务中,并没有专业的道德人才。那么谁去学习、记忆和使用道德典呢?最多我们只能像字典、百科全书或电话薄一样去查考道德典而已。但是我们或许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遭遇到一种道德情景,那我们又怎能在所有时间带一部道德典到所有地方呢?因此,形式(2)也似乎是不实际可行的。还有,例外以外,那是严格的。
所以只剩下形式(3)了,在这形式中,道德原则或规则或者有一笼统的容许例外的但书,或者并无但书却诠释为不严格的,了解为容许例外的。于是,对一道德情景之诠释,即是一道德原则或规则是否适用于某一情景,或这情景是否为一例外,是留待当事者去裁决。但是我们又如何去作诠释,或如何去判断这情景是一容许的例外呢?我相信对于这样一种决策,没有一种伦理学理论曾经或能够供给一个准则的。
我能建议的唯一指示原则是准备一个对牵涉在某一情景中的各种因素的份量之量度,俾使决定这原则或规则是否可以应用,即是这情景是否一个可容许的例外。例如,在“不毁弃承诺”和“不说谎”间的选择中,在那情景中的毁弃承诺所产生的伤害和在那情景中的说谎所产生的伤害可以去量度,或者至少去估计,并予以比较。“效用”恰恰是选出、采用和界定以作为普遍的量度者。于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中,仍旧可以依照效用之份量而作出决策,并且这决策仍旧必须在行动的层次。这是我的诠释与规则效用主义判然不同的地方。既然关于哪一个是对的行动之决策巳留给当事者,不同的当事者或会作不同的选择和采取不同的行动。对于这样的例外情景之不同态度或意见即是我们所称的道德歧见。
关于规则之严格性,林肯·爱列生有一相似的看法。他说:“效用主义能将个人行为之伦理学诠释涵盖于一个经验规则的疏松系统中,包括接受利已是适当的说法。”[2](P1-8)显然的,他的经验规则的疏松系统相应于我的不严格原则或规则。
七、结论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什么是“对的”,和对它的证立,是道德哲学中具有争议性的核心问题,也是效用主义和道义论间的主要差异之所在。站在效用主义的立场,我认为效用主义,或至少我的统合效用主义,对于·好的就是对的”这个陈述有一套完整周延的说法。至于道义论,就我看来,它的证立是不够周延或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从“对的先于好的”开始,道义论至少有下列四个严重的缺点。
(一)“对的先于好的”之先于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的先于和知识论上的先于。我认为道义论者用了第一种意义是一种错误。若用了第二种意义,那么对的就并不先于好的了。
(二)道义论对“对的”之证立主要是直觉,但直觉是主观的,各人的直觉之间,虽大致相同而仍有小异,故需要进一步的证立。一般道义论者认为直觉是自明的。但自明的有三种不同的程度,第一种是先验的(apriori),第二种是劳思的乍见的自明(prima facie),第三种是经过长时期经验的自明(self-evident)。一般所谓的自明是指第三种,其意义是模糊的。我认为它就是概括规则的概括(summary)或共识(consensus)。因此是经验的而非绝对的,也可以用效用来解释。
(三)很多道义论者认为正义的性质与效用者不同,故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或比较。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正义凌驾于效用之上,这其间有一重大的矛盾。
(四)很多道义论者认为道德原则和规则,或至少有若干条,是绝对的。这也就是说,道德原则和规则是严格的而不可以有例外。这种绝对性和严格性除了难以证立以外,还有实际上的困难,即是如果两条绝对或严格的规则间发生了冲突,除了安排一种任意的优先次序外,没有任何要善的解决办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效用主义是一种存活的伦理学理论,而道德论,虽然相信它的人要远比相信效用主义者为多,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