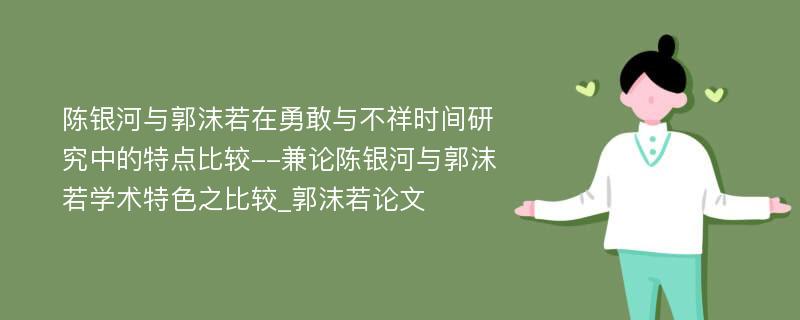
勇预时流——陈寅恪与郭沫若治学特色比较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特色论文,陈寅恪论文,勇预时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与郭沫若生活在同一时代,都是诗人, 都在史学方面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有着这样相同点的两个人,没有像文人学士所惯常演绎的那样成为煮酒论诗、挑灯析文的知友,他们的关系,在1961年郭沫若拜访陈寅恪后传出的一幅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中已经传神勾勒。研读他们的文集,会发现他们之间如风马牛之不相及不是身体方面的生理障碍(郭聋陈瞽),也不是我南君北的地理睽隔,更多的是两人之间“欠缺的正是一种心灵与气质的呼应”(注: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322页。)。现实生活中他们并没有留下“龙虎斗”的明显痕迹,但从普遍联系的观点把“斗”理解为处在相同时空下的事物的关联,则即使在学术上,他们之间那种似无实有的联系仍然处处存在:解放后,郭沫若被尊为“新史学”的权威与称为“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对峙并存;1958年郭沫若公开宣布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20世纪50、60年代郭沫若新拓展的史学研究领域如对《再生缘》的评论、重评曹操、武则天、李德裕的历史地位,陈寅恪早已关注并阐发了真知灼见,陈寅恪曾说郭沫若为曹操、武则天的翻案文章其论点“和自己接近”(注:参见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314—316页。);他们都推崇王国维,陈寅恪曾系统总结王氏的治学方法,深刻揭示其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而无论是治学方法还是研究成果利用,郭沫若都从王国维处沾溉甚多;被郭沫若称为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辨证唯物论的观念”的人们中不知是否包括陈寅恪(注: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被陈寅恪目为“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者中的“夸诞之人”、“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者是否有郭沫若的影子(注: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刘叔雅庄子补正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郭沫若所声称的不但要“实事求是”,还要“求其所以是”,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方法陈寅恪早已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一向以之骄人并凭借它取得了骄人成绩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陈寅恪在研究中与之暗合者比比皆是,并且陈氏的高足汪篯后来改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其转变迅速和成绩斐然都可见陈氏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相通近似之处。
现在两位大师皆已作古,揣摩其治学特色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以管窥其治学门径,也应是不无意义的工作。本文论述陈寅恪、郭沫若治学特色相同之处,至于不同之处,另外撰文再论。
一、出入新史学
陈寅恪在为陈垣所作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那篇著名序文中提出: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日益衰朽,西学日益猖炽,躬逢其时的学者在“师夷长技”的同时对本民族文化的特色与出路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探索,史学界提出建立新史学即产生于这种时代背景之下。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同年章太炎也写有《中国通史略例》,随之而起,夏曾佑、刘师培、马叙伦、曾鲲化等人,共同提出要建设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他们认为传统史学缺乏对历史事实进行归纳,没有总结出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则,新史学需注重归纳历史演变的规则;另外,传统史学叙述重心是帝王将相,是为帝王资借鉴,没有能反映全民的活动,新史学要以全民为本位,通过对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社会文化历史的全面探索,为现代中国人提供历史借鉴。新史学是历史学者面对时代的新问题结合本学科的特点而提出的新的解决途径,它大大地拓展了传统史学的视野,为史学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此后众多的研究者正是在它的指引下取得了大小不一的成就。
苦难的时代不仅召唤学者解决新问题,也给他们送来了新材料:1898年至1899年之交,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出土了许多刻有古字的龟甲兽骨,后确定是殷墟卜辞,它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学人以之实证古史,考察其时社会变迁、礼制沿革,使冥模难辨的殷周之际的社会变化昭然清晰。同时,他们把乾嘉学派治学方法与西方科学方法与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有异于前人的研究方法。其中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可为典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陈寅恪与郭沫若皆可谓“预流”人物。陈寅恪一生所从事的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就是梁启超等所提倡的大文化的视野。在从事学术的前期,陈寅恪把中国文化放在亚洲文化的存在体中考察,着手“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研究,着重于佛教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来转而研究“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到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都没有离开这种大文化的视野。至于对新材料的关注,在他对王国维的推崇与评价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直接运用新材料做研究主要在敦煌学方面。1930年,陈寅恪在他撰写的《〈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首次提出“敦煌学”这一学术概念,文中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新潮流也。”先后发表的相关文章有:《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1929年)、《〈敦煌余劫录〉序》(1930年)、《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1930年)、《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跋》(1930年)、《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1932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1937年)、《敦煌本心王头陀经及法句经跋尾》(1939年)等。正是陈寅恪的呼吁与研究,使当日“吾国学术伤心史”的敦煌学今天已走在世界前列。
如同所研究的问题与所用之材料得预时流一样,陈寅恪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是预时流而又能出神入化。新史学在不满传统史学的治学畛域之时也对其纯粹为考据而考据的治学方法表示不满,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是他们探索的成功代表。传统考据学的方法是“考信于六艺”,王国维则不仅将传统经史还将一些“不雅训”的文献资料以及地下的出土材料纳入考据范围,用它们来验证传统经史的有关记载,这样不但扩大了史学考据的史料范围,也使传统的书面历史变得立体可信。不仅于此,他还在“知其然”的基础上探索“其所以然”,力求由此考索出当时的社会历史的特征。陈寅恪以出土材料证史主要表现在利用敦煌资料来证史、释诗或以历史记载来证明敦煌资料,他写的《韦庄秦妇吟校笺》就是根据敦煌所出唐五AI写作本之《秦妇吟》作校笺的。也许是因为“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注: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见《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陈寅恪后来几乎很少用出土文物与现存史书互证的方法,而是以历史文化的变迁为立足点,凭着个人对历史卓越的“通识”,把乾嘉诸老与西学的科学治学方法融会贯通,通过索求、爬梳、校勘、排比基本资料,用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或演绎的方法,从日常可见的材料中得出人意表又令人信服的结论。分开来看,陈寅恪的治学无论其所用的材料,还是其所用的比较、分析、归纳等方法,都极普通,但联系他由此得出的一个一个令人惊叹的结论,又让人觉得他的治学方法实在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王国维的治学方法以三点总结已很全面,陈寅恪则似“无崖岸可望”,其助手黄萱辞命不肯写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的文章,除时代的压力外,觉得难以全面概括应也是原因之一。其有目共睹的“诗文证史”,从古代诗歌、小说、戏曲等中挖掘历史材料,以补史传记载的不足,是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对传统史料范围的进一步扩展,也是陈寅恪为历史研究开辟的新途径。
1921年5月在《学艺杂志》发表的《我国历史上的彭湃城》是郭沫若最早的史学文章,其后三四年间,他又陆续发表了《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等文章,即使在这些最早的篇什里,郭沫若所表现出的进化论思想与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视角,已经显示了作者善于吸收时代学术思潮而又不被淹没的善于发言的独特本领。1928年,在研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过程中,郭沫若以一个优秀学人的学术敏感发现,恩格斯的这部名著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的情况,于是,他决定用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仅仅依靠文献资料尚有缺憾,又钻研了甲骨学及其研究代表的著作,曾敏锐指出:“(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的放出一段异样的光彩。”并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的业绩为出发点了。”(注:《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一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短短几年里,直接参与时代学术潮流,积极利用罗振玉、王国维等在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写出了诸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等震撼时人的著作。可以说,假如不能运用刚刚在中国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假如没有积极加入时代的新兴学科——甲骨学的研究,不能善于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郭沫若会在史学上有这么大的成就吗?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所用资料上得预时流,是郭沫若取得史学成就的一大原因。
二、唯物辩证法
陈寅恪曾说自己从事学术的原则是“惟知求真而已”(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之《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第109页。),把求真作为治史的第一要义。但我国古代历史,或由于“史臣颇讳饰之”(注:陈寅恪《论唐高宗臣突厥事》,见《寒柳堂集》,第97页。),或因“相传之史料复多隐讳之处”(注: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53页。),致使“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故“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注: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74页。)。为拂去历史的尘埃,治史者应该广泛搜求材料,对比勘校,详辨慎取,来“求得一真确之事实”,“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第126页;《金明馆丛稿二编·杨树达论语疏证序》第233页。)。实事求是必须对历史做精审考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陈寅恪曾在《论再生缘》第45页用括号有一段这样的说明:“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后又疑为乾隆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糖。搜索研讨,终知非是。然以此耗去日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虽是一段短短的文字,其中可见他审慎的治学态度和为求真而付出的艰辛劳动。
求真不仅需要付出精力与时间,还需要渊博的知识。比如在《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这篇跋文中,他为考证该经的译主,凭着渊博的学识,引述法、德、日相关文献资料,又研究了蒙、梵、藏、中文的对音和意译,通过古今中外书籍互相补正比勘,从而得出令人折服的结论。
求真更需要有过人的识见,才能真正地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的原貌。如论述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诏书所起的作用:“此诏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作者目光如炬,把一纸诏书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实事求是地揭示出来,实为发千年之覆。这种例子在陈寅恪著作中不胜枚举。如《世说新语·言语》载晋元帝与顾荣的一段短短对话,陈寅恪对此分析道:“东晋元帝者,南来北人集团之领袖。吴郡顾荣者,江东士族之代表。元帝所谓‘国土’者,即孙吴之国土。所谓‘人’者,即顾荣代表江东士族之诸人。当日北人南来者之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之态度可于两人问答数语中窥知。”并且进一步推导演绎出:“顾荣之答语乃允许北人寄居江左,与之合作之默契。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注: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也许勉力为之,分析之事人所能及,而于寥寥数语中见出它对世局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则非凡俗能及。没有对历史的“通识”谁能为之。
治史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则要求治学者不但有谨严的治学态度,还须才、学、识三者兼备。胡适曾评价:“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注:《胡适日记》1937年2月22日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他做学问不但能求其是,还能求其所以是,不但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把唯物辩证法用得出神入化,毫无生搬硬套之感,甚至使人感觉不到他使用了这种方法。如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陈寅恪指出:“隋唐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分析隋唐制度之渊源,于纷繁复杂中,他抓住两条线索,一是注意门阀制度对于隋唐文化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因而他关注在文化冲突状态下的士族及其表现,二是注意到其时民族的冲突融合、各种文化的碰撞交汇频繁,因而他同时又关注文化冲突下形成的民族关系、各社会集团的复杂表现以及它对文化制度的重要影响。这种视角与方法,在随后完成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其上篇的标题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下篇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其“升降”、“盛衰”、“连环性”、“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等字眼,表明作者将从事物的变化和事物之间的联系中认识事物本质。诚如周一良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所说:“陈先生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如从南北朝分别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陈寅恪坚持“一切不能盲从,要头脑清醒”(注:《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这使他所运用的治学方法在多有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暗合之时又不把它当成僵硬的教条、方法胡乱套用,而是择取扬弃,能以之达到求真者则用,反之则弃。
唯物辩证法之于郭沫若就像一个想学走路的小孩得到的那只有力的牵引之手。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他治学的重大作用,郭沫若早在日本的时候写给成仿吾的信中已经表白:“以前没有统一的思想,于今我觉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于今我觉得寻得了关键。”(注: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见《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三十年后,在《十批判书》的《后记》中他再一次强调:“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确实,就旧学功底来说,郭沫若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并不能胜出,但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方法论武器使他原本驳杂无章的传统文化知识有了纲领和统帅。马克思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20年代在日本的时候,郭沫若就利用它,从分析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入手,发掘了《周易》、《诗经》、《尚书》等古典文献及地下出土资料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物质生产情况、社会面貌和时代思想,阐释了卜辞、青铜器铭文对认识古代社会的价值,以唯物史观的眼光剔去了上古史的神秘外衣,揭示了中国从远古到近代经历的生产方式的更替。在研究、清理了秦汉以前的社会生产关系之后,40年代,郭沫若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清算,他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我并没有把他们孤立起来,用主观的见解去任意加以解释。(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第470页。)”在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它的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整理出一个轮廓后,“依我原先的计划本来还想写到艺术形态上的反映,论到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的情形,或因已有论列,或因资料不够,便决计不必再添蛇足了”。(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第487页。)郭沫若大的治学路线是先研究其时的物质生产再着手精神生产研究,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方法。从每个单篇来看,郭沫若也是以唯物的观点,注意把历史看成一有机体,注重分析事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往往能令人耳目一新,取得卓越的实绩。比如郭沫若尚是甲骨学一新兵,其《卜辞通纂》一出便让时人不能等闲视之,就是因为他能注意体系、注意事物的联系。他说他是“依余所怀抱之体系而排列之”,全书分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猎、杂纂八项,从大处着眼,又注意考察单件与总体的联系,由卜辞本身的规律进而探索到殷商社会的面貌。他对青铜彝铭做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也是运用注重系统、联系的辨证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正是一生成就与马克思主义方法分不开,郭沫若一再表白与马克思的渊源,表示要感谢马克思。
三、社会关怀
中国文化在近代的命运,可以说是风云激荡、翻天覆地。以陈寅恪的话说是“以外族之侵迫,致剧激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是“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在此文化巨变、国家危难之际,思考民族文化前途,寻找挽救国家种族的方法与途径,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学人呈上的纷纭多样的答案里裹挟着的是同样火热的爱国救国之心,这也使中国近代学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千丝万缕。
陈寅恪也概莫能外。他客观理性的学术研究中充满着对时世、社会的关注与思考。蒋天枢曾概括陈寅恪治学特色,其中之一即“以淑世为怀。笃信白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之旨”(注: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之《附录二·陈寅恪先生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1930年,值清华大学建校20周年之际,陈寅恪在所作报告《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提出学术的兴废“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7页。),1964年他在《广州赠别蒋秉南》又以诗句“文章存佚关兴废”再次强调这一看法,他认为研究历史在于“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注: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所以他研究的题目关涉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中国文化存在久远的原因等问题。陈寅恪曾就自己为何重视对我国古代北方文化的研究作了回答:“微默察当今之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注: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44页。)可见其学术中凸显的社会关怀。
“述往事”除为了求真而外,更是为“思来者”。面对中西文化碰撞而莫衷一是,陈寅恪以自己的研究告诉大家,中国早已有过接受外域文化挑战的经验,这就是佛教思想的传入,及儒道思想对佛教思想的包容与吸收。他通过缜密的爬梳史实,论证了外来文化不加以中国化必将如唯识宗之传入般最后消寂灭绝,由此得出了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如此态度,“乃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已经为“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以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来为当时尖锐的文化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域文化——开出一剂良方。
陈寅恪对民族精神的关注还表现在对人的气节的臧否上。他研究涉及的历史人物很多,统治阶级如曹操、王导、武则天等,士大夫阶级如阮籍、陶渊明、元稹、李商隐等。陈寅恪通过对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措施如曹操《求才三令》的颁布,武则天长居洛阳、重用进士的分析,推导出统治阶级为有效维护其统治,在尽量收买士人之时,对于不合作者,则采取摧毁其内心信念与精神堡垒的方式。信念丧失、理想破灭后,则精神抵抗的防线不攻自破。生活于此转移升降之中的士人,“又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神泰名遂”(注:陈寅恪《陈寅恪文集之六——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2页。)。陈寅恪常于其中鲜明地寄寓自己的褒贬,崇尚气节而贬斥势利。联系他曾生活之时世:“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第220页。)他的至交王国维已于其中“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历史的剧变正在陈寅恪身边上演,而贤不肖巧者拙者也在身边层出不穷,鉴往知今,借古讽今,“通古今之变”在陈寅恪这里得到了极好地贯彻,使他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注密合无垠。虽然其平生志愿写“中国通史”与“中国历史的教训”只能付诸阙如,但即使在最后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中,其中融注的社会关怀依然深厚绵长。
假如说陈寅恪于著作中表现的社会关怀似草蛇灰线,须深思熟视,才能发现它比比皆是,郭沫若史学著作中的社会关怀则朗若眉目,无须找寻。其史学研究两个高峰期出现都与社会政治因素的催产大有关系。1927年,郭沫若因北伐战争与南昌起义失败,被蒋介石缉捕,秘密东渡日本,开始了在日本的第二个十年。此时国内,因国民革命中途失败,马克思主义遭到一些人的诋毁、诬蔑,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往何处去?革命者必须作出有力的回答,方可给彷徨者指明前进方向,给甚嚣尘上的反对者以回击。郭沫若虽远离祖国,仍心系革命、关怀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表白自己写作动机: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
他通过古史研究来回答迫切的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重新认识《诗》《书》《易》和卜辞、金文,使上古社会生活历历可见,证明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于中国。从而坚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证明了中国革命理论指导的正确。
40年代,郭沫若在重庆受到国民党的羁縻束缚,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怀着苦闷、愤怒的心情,他“走起回头路来”,写出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历史研究著作,其写作的大目的是根据革命的需要,对先秦社会与先秦诸子“作了一个通盘的追迹”,“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从而筑起建设新文化的宏图。同时,他把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与爱憎倾注在研究的对象上,对心怀人民关心民生的孔子、敢于反抗邪恶热爱祖国的屈原等历史人物进行了热烈歌颂,对专制独裁统治则表达了强烈憎恨。解放以后,或许是与政治距离太近,郭沫若的著作《奴隶制时代》、《管子注》没有表现多少社会关怀,其所作的翻案文章或被人讥为政治跟风。其实,即使是跟风,它也是对社会关注的一种方式。
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当时社会要求和学术热点,陈寅恪与郭沫若所取得的成就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积极主动地利用当时出土的新材料,运用王国维等人的新的研究方法并加以创造,吸收外来研究方法如唯物辨证法同时加以个性化、本土化的发挥,假如说这些是他们勇预学术时流的表现的话,根据时代的需要而确立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则是勇预社会时流的体现。勇预时流是陈寅恪与郭沫若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
标签:郭沫若论文; 陈寅恪论文; 王国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新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