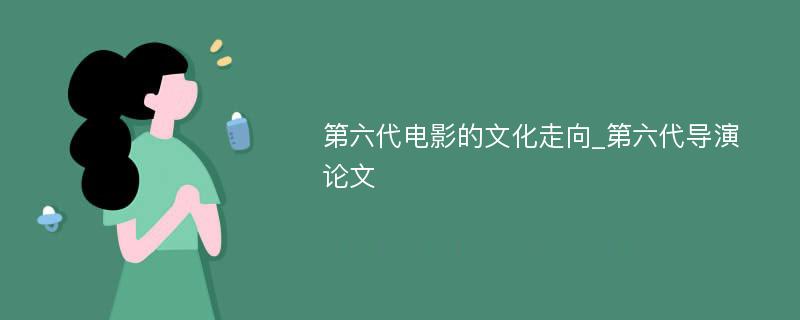
第六代电影的文化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六代论文,走向论文,文化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改铸和重构中,以张艺媒、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民俗奇观与宅院文化已在极度的成功中山穷水尽;而新生的第六代导演群落以全新的电影思维方式、文化内蕴和美学品格颠覆了第五代电影的结构模式和叙事话语,给当下低迷的银幕世界注入了清新的活力,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电影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景观。
关于第六代导演群落
作为一个稳定的“代”的电影导演群落,也许第六代还远远显得稚嫩。难怪张艺谋说:如果把第六代捆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姜文[1]。尽管张艺谋似乎并不看好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出生的这批后辈导演,而他们的作品也没有能像第五代那样以一个整体而震撼影坛,但是在中国电影体制的转型中,第六代导演群落却在悄然崛起:胡雪杨、张元、王小帅、管虎、吴文光、李欣、阿年、陆学长、何建军、娄烨、邬迪等一连串陌生却充满朝气的名字渐渐为观众熟知和关注;《留守女士》、《湮没的青春》、《北京杂种》、《冬春的日子》、《流浪北京》、《悬恋》、《牵牛花》、《周末情人》、《炎热的城市》、《巫山云雨》等一批影片以对第五代电影模式的抗拒,裸露生命的真实状态,追求生存还原,自觉摈弃民族寓言和个人神话,受到国内外电影界的广泛注目。
对第六代导演群落的指称,目前尚不统一,理论界既有人名之曰“后五代”,亦有人称之为“新生代”。其实,他们是由两个彼此无关却又相互联系的创作群体组成:一是由北京电影学院85、87级部分毕业生组成的创作群体;另一群体是一批毕业于戏剧学院或艺术学院的青年艺术家与青年电视工作者。
这群从学校到学校的“新生代”导演不像“三谢”、赵焕章、吴贻弓、吴天明、滕文骥、陈凯歌、张军钊、黄建新等前“代”导演那样,拥有丰厚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们的生活积累主要来源于城市空间内繁复的社会生活和光怪陆离的人生百态,加上他们对自己同龄人的生存情境有着深刻的体悟,因此他们的电影大多以表现当代都市年轻人生存状态的内容为题材,而且大多选择都市社会边缘人物作为影片的主人公,如《湮没的青春》中的打工仔罗小绪和“金丝鸟”敬欧太太,《感光时代》中的摄影师马一鸣等等,表现出青年导演们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思考。著名导演谢飞认为,尽管从技巧上说,第六代导演“片子的节奏处理、影调控制以及电影感都是很光彩的”,但是,第六代导演群落是边工作边走入社会的,“那么,进入社会以后,如何去深入地了解我们的社会,了解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最根本的东西,这才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能成大器的关键。”[2]
对第五代电影的文化突围
自1984年陈凯歌的《黄土地》到1994年张艺谋的《活着》在戛纳电影节获奖,十多年里第五代导演不但全然改变了中国艺术电影传统的历史面貌,更实现了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对话和接轨。但是,以张艺谋、陈凯歌领衔的第五代中国艺术电影,在构建起一种中国艺术电影/乡土电影模式的同时,也铸造出一个个充满畸趣的现代中国伪民俗神话,“为西方观众和电影节提供了一种来自‘中国’的‘他者’的文化消费,使西方对于第三世界的欲望与幻象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3],从而为当代中国艺术电影确立了一种被西方世界的心理期待预制了的中国电影范式。这也便是黄建新的《轮回》、周晓文的《疯狂的代价》两部表现中国都市生活的影片不为西柏林电影节接纳和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二片在西方文化语境里太不“中国化”了。要想在西方电影节获得认同,只好沿袭张艺谋式的电影摹本,继续去演绎这个被西方预设的文化/电影模式。于是,黄建新拍了《五魁》,周晓文拍了《二嫫》(95年获“玛雅美洲豹金奖”),与何平的《炮打双灯》、刘苗苗的《家丑》、李少红的《红粉》(95年在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视觉效果银熊奖”)一起构成了第五代中国艺术电影日落前的辉煌。
自90年代以降,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群落带着对历史的敬意,裹挟着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色彩,以解构性的戏谑背弃了第五代中国艺术电影的话语模式。他们虽不足以威胁第五代电影的生存,也未形成中国新一代艺术电影的强势,但确已构成了对第五代电影/文化屏障的历史性跨越。
在电影的题材内容上,第六代电影面向现实和都市,既不像第五代那样遥望历史和土地,也不像第五代那样编织着一个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寓言故事,“以工巧营造沉重”,而是记述着对当下生活的经历和生命体验。李俊的《上海往事》,透过一段弥漫在30年代上海滩的朦胧而悠长的情愫,折射出历史的变迁和人生的无常;胡雪杨的《牵牛花》借助于一个患梦游症的少年在“文革”时期寄住到农村中的特殊经历,揭示了人性中“恶”的膨胀,以及那个特殊年代中的恐怖暴行;陆学长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将镜头对准一个酷爱音乐的年轻人在“文革”和改革时代中的成长历程,揭示当代青年是如何对待人生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王小帅着手拍摄的一部描述打工仔(妹)感情生活的影片《越南姑娘》,则力图诠释人与人之间的亲善、依赖和互相慰藉这样的人生命题。总之,在第六代电影中似乎很难找到与第五代导演共有的“电影话语”——淡化戏剧性较强的情节张力,强调电影画面的造型功能,以及影片中渗透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反思和强烈的优患意识;迎面扑来的是浓郁的时代气息,电影画面真实、自然地展现着各式各样的现实生活情态,给人一种亲切感和逼真感。
另一方面,第六代以电影的个人化形态颠覆了第五代电影的整体模式。如果说第四代留下了叙事电影,第五代创造了寓言电影,那么第六代电影人奉献的便是个人电影。比如王小帅的影片形式意味较浓,管虎注重情绪化表达,李俊则推崇好莱坞式的主流电影。管虎在拍《头发乱了》时明确宣称:“这理应是一部反叛电影。它在视角上,注定要本着一种区别于当代中国电影的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来叙事。”[4]王小帅在拍《冬春的日子》时提出:“要摆脱技法本身的束缚,把人的本体,人最深处的东西拍出来,这才是电影的真谛。”[5]就总体而言,第六代导演更注重电影的非情节性叙事,在他们的影片里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起承转合的情节过渡,他们力图使空间溶进人的精神状态中去。在时间形态的处理上,第六代导演也不似第五代导演那样静止、抽象,而是以时间切割空间,让时间流动在变幻不息的空间,来表现普通人的命运际遇。他们摈弃了第五代电影的全知叙述,代之而起的是亲历式主观叙述。李欣的《谈情说爱》可谓是最突出的一例。这部充满青春活力的影片,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代人的视觉敏感和影像感受。不可否认,第六代导演在电影叙事和意念表达上还时时袒呈着某种稚气和拙朴,但这些不成熟之处正是每一个导演必有的艺术经历,也是他们将经过反复探索、最终走向成熟的奠基石。
第六代电影的文化境遇
第六代导演群体诞生在目前“外患内忧”的电影生态环境中,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不断受到来自《真实的谎言》、《亡命天涯》、《纽约大劫案》、《生死时速》等西方大片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又受到第五代电影既定叙事模式的挤兑。这注定使他们不能像张艺谋、陈凯歌们一样,可以不受干扰地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探索之中,尤其在当代电影的运行机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付导演工作以外的诸多事务,也不得不因资金问题而削足适履,不得不考虑影片的商业性内涵、包装途径和市场效应。
第六代电影的文化困境还在于电影的个人性。第六代导演不约而同地都在表现城市边缘人上显示了对于时代的敏感性和先锋性,除显现出题材单一化、类型化等特征外,也暴露出艺术视野上的偏执。这些个人电影过分追求情绪性、情节的非叙性,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要不要故事和怎样讲故事?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认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6]而阿诺·理德则从另一角度指出:“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动因,这包括了他过去所有的生活状况,他在创作时的身心状况,包括所有能引起灵感现象的一切情况。”[7]我们并不想由此而否认第六代电影这种文化走向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电影毕竟是一种大众传播方式,呈示社会的价值导向、满足观众的精神诉求、体现观众的审美情趣应是它的价值所在。“如若仅为实验,只为个人先锋一把,则无话可说,但要想生存发展,要想有观众,便不能没有故事,而且还须是个好故事。”[8]当然,我们不是反对实验、反对先锋。必须承认,没有传统的文化是没有希望的文化;同样,没有先锋的文化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但这种先锋如果是带有民族文化特质的先锋,那才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先锋。”[9]的确,第六代电影在叙事上体现出不同于第五代的文化走向,例如他们都比较重视凝重、平实、冷静的电影纪实风格;再比如管虎把摇滚乐引进电影,大量镜头近乎于MTV式的节奏,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也许这对于中国电影语言的发展是一种启示。但同时不可回避的是,在电影技巧上也表现出生硬造作等倾向,有时过分偏重于用“十分暖昧的暗示来达到意义上的深度”[10]。如风格上呈现出一定的超现实色彩的《牵牛花》试图暗示什么,却又表达得过于含混,就颇有些让人费解。再如《巫山云雨》生涩的场景,委实令人沉闷索味,很难获得所谓“心灵的景色”的审美况味。笔者认为中国电影讲故事的方式必须要遵循中国本土的话语习惯和思维特点,完全移植西方的话语方式便无法讲清属于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果第六代电影对第五代电影进行文化突围后,找不到契合中国本土特点的独立的电影话语方式,我想第六代导演恐怕很难生存下去,更遑论“诗意地安居”了。
著名导演谢飞曾这样关切地问第六代导演们:“我说你们为什么非要死盯着都市,死盯着你们这拨人自己,为什么都是自己写剧本不改编?而第五代的优势就在于改编的作品多。”[11]显而易见,第六代导演显得有些过于自信了。过早地与文学“离婚”,恰恰导致了他们的电影文化底气先天不足。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迄今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据前苏联学者波高热娃考证,在电影诞生的第一个十年里,就改编了若干名作。“从那时至今,在这条路上启锚登程的电影导演难以计数。”[12]小说与电影是两门不同的艺术,而电影之所以对小说情有独钟,是因为小说有电影难以拥有而又值得借鉴的长处,比如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结构情节塑造人物的丰富多样等等,所以当电影以无可替代的现代科技作为它的制作工具时,仍然喜欢从小说中汲取故事素材和文化养料。因此,新时期颇有影响的电影诸如《城南旧事》、《牧马人》、《如意》、《湘女萧萧》、《黑炮事件》、《人生》、《本命年》、《香魂女》、《红高粱》、《老井》、《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黑骏马》、《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无不取材于小说。可见“电影的成功离不开小说的基础”[13]。对于起步中的中国第六代导演来说,小说应该成为他们十分倚重的一个基础。因为电影需要不断向小说讨素材、讨灵感、讨文化底气。
当然,对于崛起于电影危难之际的中国第六代导演来说,在面临着凝重的文化困难的同时,也面临着历史性的契机。如果说,第五代导演的贡献在于艺术上的革命,在于“破”;那么,第六代导演的使命则在于“立”。诚如著名导演张暖忻所说:“这就像暴动一样,之后呢,就是如何去巩固政权。”[14]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一系列陈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和禁锢得以逐一解除,这无疑为他们创造了更为宽泛的创作环境,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创作自由和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不可否认,第六代导演达到创作上的繁荣和艺术上的精致还为时尚远,但他们毕竟在沿着艺术的坎途艰难地跋涉,我们坚信第六代电影一定会出现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品。
注释:
[1]见郑向虹《去年中国电影一瞥》,载1996年3月6日《文汇报》。
[2]见《眺望在精神家园的窗前》,载《电影艺术》1995年5期。
[3]见《当代电影》1995年5期第7页。
[4]转引自韩小磊《对第五代的文化突围》,载《电影艺术》1995年2期。
[5]转引自韩小磊《对第五代的文化突围》,载《电影艺术》1995年2期。
[6][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和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载《当代电影》1989年6期。
[7]见《美学译文》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韩小磊:《对第五代的文化突围》,载《电影艺术》1995年2期。
[9]朱枫:《千斤难买回头看》,载《当代电影》1996年4期。
[10]章明:《致友人的一封信》,载《当代电影》1996年4期。
[11]见《眺望在精神家园的窗前》,载《电影艺术》1995年5期。
[12]张煊:《黄健中散论》,载《艺术广角》1993年3期。
[13]何跃敏:《〈理智与情感〉:小说与电影》,载《当代文坛》1996年5期。
[14]见《感受生活》,载《电影艺术》1995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