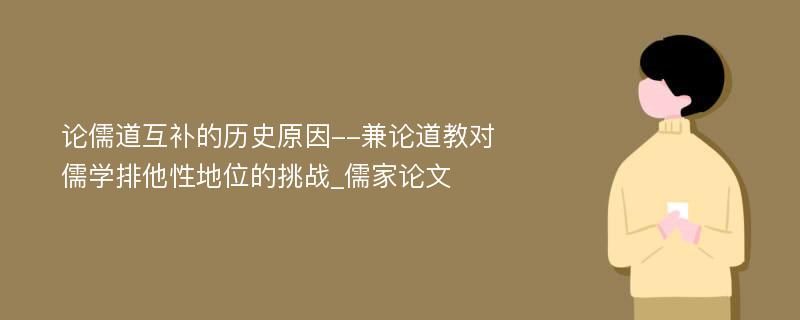
儒道互补历史原因管窥——兼论道家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道论文,儒学论文,地位论文,原因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6-0088-07
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儒道互补是影响士人心性人格的重要现实,对儒道互补格局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行探讨是有意义的。
一
学人将百家争鸣的结束归因于秦汉的一统,尤其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当然是百家走向融合的政治背景。但文化学说有盛必有衰,有开创者,也必有继承融合者。历史文化的走向和学说思想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必然趋势和规律。与其说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结束了争鸣时代,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影响和假手于他们使之成为现实。秦始皇焚书坑儒却灭不尽书和儒,汉武帝也罢黜不了百家,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不由个人意志所左右。说到底,是社会时代造就了秦皇汉武,而不是相反。
就先秦学说发展来看,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过后,融合已是大势所趋。融合诸家的杂家著作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先后出现,就已预示了争鸣的结束和互补的开始,这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融合最终以儒道为主,也有其深刻原因。因为诸子中如阴阳、纵横、小说、名、兵、农、医等都是具体专门的学科,与儒道墨法诸家不属同一层次,不构成对立对等的关系。而墨之于儒,法之于儒道,都有明显的师承渊源关系,墨更多地将儒家原则贯彻于实践中,法家则兼取儒道而贯彻于政治学和统治术中(注:据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伪造秦始皇遗书,赐死扶苏、蒙恬的理由,即是“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可见法家与儒家的不解之缘。),故墨法两家在学理上似乎也不构成与儒道对立对等的关系。如就文艺思想而论,墨法否定文艺的依据实同于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而结论又与道家相同。而惟有道家,才真正在思想学说上与儒家异质同构和对立互补。
这种对立互补可说是全方位的。如名实之辨,孔子强调“正名”[1](p.133),主张以名正实,而庄子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名者,实之宾。”[2](p.18)在文艺思想上,儒家重视文艺,但忽视文艺的审美特性,对政教功能的片面强调束缚了文艺;而道家则从根本上否定文艺,但其审美态度、艺术眼光和自由精神及其对“道”独特的阐述方式,却特别契合于文艺。儒道文艺观恰成互补,且深远地影响了后世文学文论。
儒道学说的相反相成,还深深地根源于人性内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悖论和矛盾。面对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现实,儒道两家开出了不同的治世之方。老子主张回到结绳而治、小国寡民、民无知无欲、朴素自然的原始状态,崇尚“赤子”境界和“婴儿”状态;庄子尊重和关怀自我,崇尚自然、本真、自由、逍遥的心性人格;而孔子则向往周公之治,主张克己复礼,以礼乐刑政制度引导和制约人情,整合与恢复社会秩序。儒家修齐治平的基本精神正是通过对人心性的控制、调节和规范,实现天下大治、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的。《论语》的基本内容便是教导怎样做人,如《乡党》一篇就从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到在朝典礼的进退揖让,详细阐述了一整套行为规范,具体到在朝典礼的步态表情和居家生活的食不语,寝不言,肉不方正不食。
儒道所论虽指向不同,却各有其现实针对性与合理性。从本质上说,老庄是真正的诗人,孔孟则是现实主义者。人们渴望自由,渴望激情,渴望无拘无束、纵横驰骋地去释放和实现自己强烈的生命意志,然而人又只能生存于社会。人与人的差异,生命意志与欲愿的矛盾冲撞,呼唤社会法则与道德律令的产生,以此去调和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与人类文明,这就决定了前述的渴望不可能得到充分实现。孔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人注定没有绝对自由,这是人类为文明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因而,他们呼唤理性,强调礼义,主张以外在礼仪规范制约人的行为,以诗乐来陶冶和引领人的心性,使其将仁义道德作为内心的自觉追求,将规矩方圆化为自然的行为,从而将人纳入合理良性的社会秩序之中。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虽不断发展完善,却远未臻于完美的形态。孔子求“仁”,但在封建社会伦理生活中,君臣、父子、夫妇这二者间的地位人格远非独立平等。社会形态的表象是以抑损一方奉养另一方来维护的。同时,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进步都要付出相应代价。就像美猴王要寻访仙道,由猴进化到神(人),就要离开他的“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亚当、夏娃要得到智慧果,睁眼看世界,就要被逐出伊甸园。人类向自己理想世界每近一步,与原初的伊甸园、花果山就更远一分。老庄似乎和《圣经》作者一样为此而叹惋,觉得文明进化的代价过于巨大。老庄宁愿将智慧果奉还,回到无知无欲、本真朴素、不分美恶的原始混沌的自然状态中。
人类不能不组成社会以进化到更高文明,但又“野性未除”,万物之灵的人不能没有野性,否则就没有了生命的活力,这也许是人类自身最大的矛盾与问题。我们不能没有美丽的梦想,浪漫的激情,酣畅的迷醉和近乎疯狂的野性,然而又不能让激情的洪流、迷狂的野性冲毁社会文明与秩序的堤坝,违反社会成员应遵循的行为法则与道德律令。孔孟注视着人的社会性和人类文明与秩序的前进与发展;老庄关怀着人类生命与心性的和谐、自在与自然,这或许也是孔孟与老庄的最大差异,是儒道两家之所以形成对立互补关系的内在原因。
二
儒道互补的原因还在于:儒家谋取和维护话语霸权的过程,与道家消解和挑战其话语霸权的努力始终相生相伴,而这也正是士人心性人格与民族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儒家制造了一系列关于圣人、经典、语言和诗乐的神话,在与君权建立神圣同盟的同时,儒家早已使对语言文字、圣人经典的信仰敬畏变成普遍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而百家之中,惟有道家通过彻底否定语言文字、圣人经典、君权政治等,对儒学的独尊地位发起挑战。两者相反相成,深刻地影响了士人心性和民族文化精神。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把从董仲舒开始至清代都归为经学时代。的确,综观古代诗学史,实际上就是儒家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诗学体系生成和话语权力释放的过程,也是诗学在道、佛影响下从经学中逐渐挣脱和复归于“诗”的过程。汉武的“独尊儒术”,意味着在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君权,与在思想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儒家经学话语权之间建立了神圣联盟。儒学为皇权提供法理依据和文化资源,而皇权则为儒学提供政治经济支持。五经取士制度使读经成为入仕之阶,更是对儒学的有力提倡。
历代统治者推尊儒学,就内因而论,是由于儒学在逐渐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如《论语·泰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记·大学》“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等富于包容性和系统性的话语体系,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强大的道义力量以及在政治教化与伦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使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自然选择儒学作为其统治的法理依据和文化资源。
儒家极其注重教育师承,儒家师承的谱系比起其他诸家来要完整清晰得多,而且儒经是许多儿童在启蒙时就讽咏记诵,烂熟于心的,是朝廷和社会约定的儿童成人特别是出仕前的必修课,这更是诸家不能望其项背的。钟会母传载:“(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3](p.1161)钟会开始接受其母启蒙时,正是魏明帝曹叡在位时。魏晋之际,经学衰微,而士大夫自幼接受的仍是如此规范而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其他时代可想可知。可见,在童蒙未开的“人之初”的心性中,是儒家经学率先描上粗重的一笔,染上了影响其一生的底色。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尽管“子不语怪、力、乱、神”[1](p.72),但儒家在撰述经典时,还是制造了不少关于圣人、经典、语言和诗乐的神话。这对儒家经典权威地位的确立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吕氏春秋·古乐》云:“(乐)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这明显反映了儒家思想。下文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土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注:参见《诸子集成》第6册《吕氏春秋》,第50~51页。)音乐被赋予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淮南子·本经训》中有文字诞生的传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与《尚书》“神人以和”、《毛诗序》“动天地,感鬼神”、《易传》包牺氏作八卦及文王演《周易》、孔子身世、河图洛书等传说何其相似乃尔,都赋予了语言诗乐等以神秘和巨大的魔力。
对诗乐和儒经的神化与对语言文字的神化是分不开的。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民族深层心理对语言文字敬若神明的心态,而儒家对此文化现象的生成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忽视《易·系辞传》中“立象以尽意”这一命题包含的意义和力量。“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p.307)这段话赋予语言符号,从而也赋予儒经以魔咒般的神秘力量。“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p.320)中国古代理学家何以有这样的底气和自信?说到底是靠经学、靠八卦符号、靠语言文字。通过类似仓颉作书、包牺氏作八卦、“《论语》折狱,《春秋》断案”,“半部《论语》治天下”等神话,通过对八卦文字等的神秘化、神圣化,儒家使自己也使民众相信八卦符号、语言文字、诗歌音乐等等,尤其是儒经有如此神秘巨大的力量,从而取得了话语和文化霸权。儒家话语霸权的获得得力于双重意义上的“挟天子令诸侯”,那就是在与君权建立神圣同盟之前或同时,儒家早已使对语言文字的信仰敬畏成为普遍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
上述文化心理,在经史著作中不胜枚举。《左传》谓“立言”为三“不朽”[6](p.790)之一。《襄公二十五年》载:崔杼杀无道之齐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在权臣方面,反映了对文字记载和以伦理纲常为依据的舆论是何等畏惧;在史官方面,又展现了怎样无畏的“直录”精神和凛凛风骨!这又与对道义的坚守、语言的虔敬不可分割。这种以生命相殉的执著与坚守,和将文章视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观念,“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7](p.120)的苦吟,是与汉宋诸儒及乾嘉学派将全部心血倾注于经典注疏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我们因此理解了阮元《茗柯文编序》之评张惠言“以经术为古文”,也理解了常州词派在敏感到厝火积薪的危机时,要强调词须“有寄托”。令人感慨的是:张周诸公大约料不到古老中国面对的是亘古未遇的大变局、大危机,是生机勃勃的近现代文明和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而他们准备的却仍然是经学和诗词。在历经封建时代春夏秋冬之后,儒生们依然未改那样的虔诚和执著,他们坚信诗乐关乎时运,能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这种信念与对圣人、经典的崇拜,对道义的坚守和对语言的敬畏是多位一体、密切相关的。
这样的虔敬不仅见诸于儒生的立言为文,还广泛体现于民间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在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活动中,我们能看到各种诸如“急急如律令”的咒语和有关语言文字的魔术、禁忌及规范,人们相信借此能逢凶化吉,趋利避害。在祖辈敬惜纸墨的习惯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宗教般的虔敬。前人取名字呼小名,喜取坚牢之物(如石娃、铁柱之类)、强健之物(如阿豹、虎妞之类)或贱而易养之物(如小牛、阿狗之类),相信这会使孩子更好养。又如恐惧数字四,偏爱数字六与八,以及将“福”字倒贴的做法等,处处折射着上述文化心理。
三
《易·系辞传》所述“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方法原则,为后儒诗学所继承。《易·乾》云:“乾。元亨利贞。”《文言》进而阐释为:“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亨者,事之干也。”经汉儒的阐发,这种解经模式被引入诗学并延续数千年。《诗经·殷其雷》显然写的是思妇对行役丈夫的思念。郑玄《毛诗传笺》却说:“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然发声于山之阳。”这和将抒写青年男女相思的《关雎》解为“后妃之德”之举如出一辙。《苕溪渔隐丛话》载:苏轼咏牡丹有“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句,即被指摘为讥刺变法:“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8](p.301)一直到清代,张惠言《词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9](p.29)其《周易虞氏义序》自述:“依物取类,贯穿比附。”论诗也是如此,因而受到了王国维的批评(注: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在《毛诗序》作者及其后继者看来,诗歌中的字字句句,每一个意象,都关乎天下兴亡治乱,承担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重大使命。在此,我们看到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代复一代、循环往复的文化现象(注:汉儒以解经模式误读《诗》(“我注六经”),与后人仿“六义”之“风”以诗(模经为式之诗)讽喻世事、发表见解(“六经注我”)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是误读现象的重要例证,也是中国文字狱的重要背景之一。)。
当儒家赋予语言诗乐、圣人经典以神秘魔力和社会重任时,也就给诗和诗人披上了不堪重负的黑袍;而老庄却通过对语言、经典的彻底否定,来消解儒家施加于诗乐的魔咒和重负。
语言的发明和运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正是借助语言,人类才构建了自己的精神大厦,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因此,对语言的重要性似乎怎样重视都不会过分。但是,当儒家将圣人经典推上神坛时,人和人的思想顿时黯然失色。当儒家诗学过分夸大诗的作用,将扭转乾坤的重任强行赋予诗和诗人,并以此来解析诗作时,实际上就已把作为人类思想工具的语言变成了奴役人和人的思想的沉重大山,将人的工具、人思想的工具化为把人工具化、把人的思想凝固化的可怕实体。可以说,是儒家经学给诗乐、语言和人们本该自由的思想笼罩上了厚重的黑袍,将诗乐、语言从思想情感存在的家园变成了牢笼。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以老庄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儒家发起的第一道冲击波便由此开始了。
庄子承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2](p.558)之说,对儒家诗乐论进行了根本否定,并提出“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师旷之耳”及“灭文章,散五采”[2](p.259)的极端主张,他借轮扁之口,谓“圣人之言”不过是“古人之糟粕”[2](p.357),在他看来,语言经典也是物,人应该“物物而不物于物”[2](p.498)。作为使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主体,人不能死于章句之下,不能死于人所创造的语言和由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中。故庄子强调:“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2](p.725)他以其“谬悠”、“荒唐”、“无端崖”、“恣纵而不傥”的“卮言”、“重言”、“寓言”来消解儒家话语对人及人的思想的束缚,来“得意”,并抵达“独与天地精神往来”[2](p.884)的境界。庄子诗化的哲学以其艺术的气质、审美的态度、自由的精神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向儒家发起了有力的挑战。他以其无所滞碍的思想和汪洋恣肆的文风,轻轻消解儒家经典与诗学对语言与诗的威压和重负,他那“解衣般礴”的自由精神,所轻轻解脱的正是儒家给诗披上的那袭厚重的黑袍。由此,我们能够深切理解苏轼何以由衷地感叹:“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10](p.2813)庄子解除了笼罩于语言和诗的禁忌、威压和重负,使苏东坡找到了自己的言说方式,从而臻于“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的境界[11](p.315)。
不能否认,儒家话语霸权的取得,与儒生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在转相授受儒经时,他们大多自觉维护其地位霸权。但当儒生通过确立或依附于这样的地位和霸权谋取利益时,他也就交出了自由思想的权力,不管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许多儒生都不同程度地成为经学的奴隶。造神和依附神者,很少能避免成为神的奴隶;制造或依附规则者,也必然要遵循规约。几千年中不知有多少儒生死于章句之下,其鲜活的生命和思想被消融和黯淡于皓首穷经的生涯中。“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12](p.66)也许是他们最好的写照。
儒经地位的确立及其成为进身之阶,为一代代儒生树立和圈定了终生的目标与范围,像一座沉重的大山,使其一生都局限于此。即使是反叛者,操戈也必须入室,要将浩繁的经传之学作为自己熟悉和挑战的对象,很难不落入“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循环怪圈。面对凝聚了千百年儒生智慧,且具有很强的自我复制、繁衍和改良能力的经传之学,许多叛逆和挑战者也许还没有横渡和超越,还来不及发出反对的声音,就已经被吞灭和淹没了,淹没在同样循环往复的朝代和历史中。
尽管如此,中国古代仍不乏这样的叛逆者,因为没有人甘心做奴隶,哪怕是思想的奴隶。一方面,总有文士试图在名教之中或之外去寻找“乐地”,谋求精神上的自由和在人间世诗意地栖居。就连夫子面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都会喟然叹曰:“吾与点也!”[1](p.119)孔子“与点”的,正是人类向往精神自由和诗意境界天性的自然流露,这使后儒煞费苦心将“曾点境界”论证为祭祀仪式之举显得多余。其实,“曾点境界”是否祭祀仪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在此感受到了美和自由,就像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1](p.70)一样。“名教中自有乐地。”[13](p.14)乐广的名言,也许已然有隐性的、不自觉的叛逆意向。古代儒生就这样徘徊于诗史(经)之间。
有破有立,有建构者就有解构者。当儒学开始走向庙堂时,以老庄为代表的思想家也开始了诗性的自觉的思想历程,直至今日,我们还在继续着这样漫长的思想旅程。
[收稿日期]2003-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