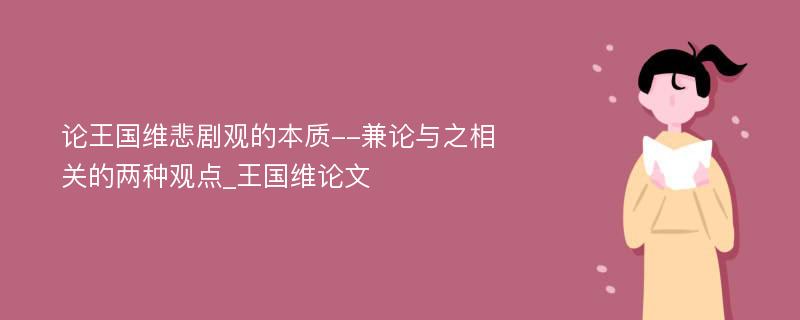
论王国维悲剧观的实质——兼评与之相关的两个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之论文,实质论文,悲剧论文,观点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悲剧意识的诞生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的一大景观。中国近代悲剧意识标举忧患意识、痛苦意识与抗争精神,冲破了以“中和”为美的古典审美理想,因此,近代悲剧观念在文学上的提倡及表现便更多带有鲜明的冲突性及崇高性特征。但从王国维的悲剧观念中,却看不到鲁迅等人所宣扬的旨在与现实相抗争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昂扬精神,因为王国维的悲剧观念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受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悲剧是人生命运的一种“自感”的表露,“人生之命运,固无异于悲剧。”因此,我们称王国维的悲剧观念为“人生悲剧”。
王国维的人生悲剧观直接脱胎于叔本华,因而,在具体把握叔本华哲学对王国维带有人生体味的悲剧观的影响之前,有必要把叔本华的悲剧观念放到西方美学发展史中考察,这样,就会发现西方现代悲剧观从叔本华开始已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即西方悲剧理论在经过古希腊时期(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德国古典美学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悲剧研究的三个高潮之后,进入了第四个高潮期。悲剧观念在现代美学中的蜕变是与现代美学的人本主义思潮相一致的,这种新的悲剧观念与传统悲剧观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现代悲剧观将悲剧的研究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得出了生活本身就是悲剧的结论,使之成为人类固有的某种特性。叔本华说:“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基础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 (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7页。 )叔本华将人类的生活本身看作是一种悲剧的存在。尼采虽然不完全同意叔本华对人生的悲观主义理解,主张以悲剧来激发人的生命意志力量,但他对人类的悲剧存在状态的认定却仍然同叔本华保持了一致性。这种悲剧观在20世纪的其他美学家的思想中也有表现,成为当代美学中的一大潮流,其代表当推存在主义悲剧观。雅斯贝尔斯就从叔本华、尼采、齐克果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那里受到启示,他的悲剧观就定位于人的存在的荒谬性上。雅斯贝尔斯认为,人在实现其可能性时,往往不受规范限制,会对神或绝对者背弃(注: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第43页。)。因此,人的存在显然是具有悲剧性的。这种悲剧观的产生是与现代西方社会的现实状况分不开的,它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在哲学、美学领域的折射和投影。现代哲学家置身于资本主义异化环境中,正是在对现代生活的无从把握中产生了关于人生的悲观主义态度。因此,便有了现代悲剧观念与传统悲剧观念相区别的第二点,即现代悲剧观的悲剧精神发生了变化,它们往往把悲剧理解为“不幸”和“可怕”的事情,虽然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主张超越悲剧人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类观念对人的生存状态基本上是持悲观态度的。将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同样放到世界现代美学史上看,多少也能说明中西美学发展的某些同步性。王国维对叔本华悲剧观念的吸收,实在是不能完全如缪钺先生所说“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虽然王国维的悲剧观念在中国近代特殊的背景下,显得有些背时,但它与西方现代悲剧观又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它的出现至少为中国近代现代美学提供了理解悲剧的另一种思路。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将具体讨论王国维的人生悲剧观及其所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中说:
叔本华于知识论上奉汗德(即康德——引者)之说,曰:世界者,吾人之观念也。一切万物皆以充足理由之原理决定之,而此原理,吾人知力之形式也。物之为吾人所知者,不得不入此形式。故人所知之物,决非物之自身,而但现象而已。易言以明之,吾人之观念而已。然则物之自身吾人终不得而知之乎?叔氏曰:否。他物则吾不可知,若我之为我,则为物之自身之一部,昭昭然矣。而我之为我,其现于直观中时,则块然空间及时间中之一物,与万物无异。然其现于反观时,则吾人谓之意志而不疑也。而吾人反观时无知力之形式行乎其间,故反观时之我,我之自身也,然则我之自身,意志也。而意志与身体吾人实视为一物,故身体者可谓之意志之客观化也,即意志之入于知力之形式中者也。吾人观人时,得由此二方面,而观物时只由一方面,即唯由知力之形式中观之,故物之自身遂不得而知。然由观我之例推之,则一切物之自身皆意志也。
在这段文字中,王国维指出了叔本华对世界与人的本质的基本看法。叔本华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向,即由传统的实在的绝对的本体论转变为个体——感性生命的本体论。在叔本华这里,本体已不是绝对的实在,不是什么上帝,而是人的生命意志。他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世界是我们的表象”,第二个命题是“世界是我的意志”。叔本华主张意志是万物的本原,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意志的客体化一级比一级明显。从叔本华的两个基本哲学命题中可知,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意志第一的人,也是一个彻底的唯意志论者。其中的偏颇是不言自明的。
唯意志论必然导致唯我主义。叔本华无限夸大人的意志,而人的个体自由又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意志不可能天马行空,不受限制,因此,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自然而然地走向悲观主义。他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生命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人生的痛苦来自于生命意志的冲动。王国维几乎完全照搬了叔本华的观点,得出了人生即痛苦即悲剧的观点: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也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厌倦之间者也,夫厌倦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解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处,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之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逾于生活,而生活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悲剧观中还融入了老庄的厌世哲学。他援引老庄的话,认为人之所以有忧患和劳苦,在于人自身有“形”有“体”,所谓“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这一点与叔本华所宣扬的带有基督教观念的“原罪”也是契合的。
谈到王国维的“人生悲剧”观,我们对学术界在讨论王国维的悲剧观时所涉及的两个问题进行一些评论。其一是王国维依叔本华之说提出的“第三种悲剧”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中将悲剧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极恶之人”造成的;第二种是由“盲目的命运”造成的;第三种是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亦即由生活本身造成的。在这些悲剧类型中,第三种的价值最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有学者仅仅抓住“普通”二字,然后加以延伸,认为王国维的观点“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强调的是对现实关系的如实描写。”(注:张本楠《王国维美学思想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如果说王国维所认为的“悲剧中之悲剧”的《红楼梦》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话,那么认为王国维的“第三种悲剧说”具有强调对“现实关系的如实描写”的价值,则是我们不能苟同的。
王国维强调“第三种悲剧”的目的在于证实他的人生悲剧论的有效性和普遍性。“第三种悲剧”的意义在于“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已,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叔本华认为“第三种悲剧”是由于剧中人物彼此间所处的相互对立的地位,“由于它们相互的关系而造成的。”(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2页。 )所以这种不幸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人已完全没有了自主性,而且也无法挣脱悲剧的结局,这种不幸的对立是无法克服的,生命意志的盲目冲动决定了这一点。这才是叔本华也是王国维对“第三种悲剧”大加推崇的目的之所在。王国维正是从人生悲剧的角度指出了《红楼梦》在美学上和伦理学上的价值,并结合贾宝玉、林黛玉的悲剧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这种悲剧观念:
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厌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已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第八十一回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由此观之,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在于表现了人生固有之痛苦及其解脱之道,它展示出人生就是一场悲剧的真相。因此,王国维“第三种悲剧”的意义在于最真切地昭示出人生就是悲剧的观念。
其二,关于悲剧人物的典型性问题。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唯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涌之孙’,亦随吾人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根据王国维这段文字,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认为王国维的典型论比较接近歌德的典型说。其实,这种说法大谬不然。表面看来,王国维所说的“个人”与“全体”似乎与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相同,然而,他所说的“个人”其实只是表达某种理念的符号,而“人类全体之性质”是从叔本华那里借来的,是指生活的“苦痛”。王国维并不关心前者的“个性”特征,对于后者而言,他所说的带有共同性的东西也不是典型论中的“共性”。王国维以上观点仍然没有摆脱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美学观点的影响。叔本华曾明确讲过艺术是对“理念的认识”,文艺的本质特征是“复制那被认识了的理念”。叔本华在讲到“理念”的表现时,也涉及到性格、典型等概念,但它们是作为显现理念的工具被对待的。王国维“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名字之下”的目的显然仍在于表现抽象的“理念”。叶嘉莹先生也发现了王国维的这一特点,指出:“从通古今之全人类的哲理来探寻作品之含义,乃是静安先生衡定文学作品之内容的另一项可注意的标准。”(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要正确理解王国维对悲剧作品人物塑造的有关问题,必须紧密联系其“人生悲剧”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