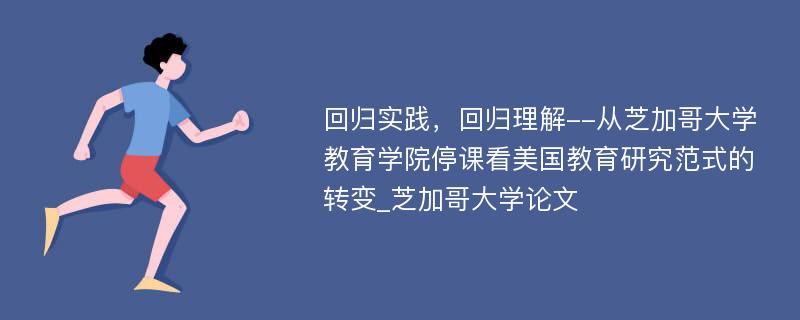
回归实践回到理解——从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停办看美国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芝加哥大学论文,范式论文,美国论文,教育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8)07-0012-05
一、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从创立到停办
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总是与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约翰·杜威——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历史学家亨利·科马格曾经这样评价杜威:“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因而他成为了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威而得以启蒙。”[1]
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其前身为教育学系)一共工作了10年。[2]这10年对杜威来说意义重大,它是杜威教育哲学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10年里,杜威通过创办实验学校,亲自主持了很多应用性研究,形成和发展了内涵广泛的教育哲学思想,使得他在教育界声名大振,直至被人视作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袖。随着杜威影响的传播,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也声名鹊起,成为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教育研究中心之一。
二战后,美国出现了所谓“高师改大”的变化,许多单一目标的师范学院纷纷向多目标的州立学院或州立大学发展。在教师教育培养模式上,“教学文硕士”的“4+1”培养模式在三次全国师范教育研讨会后,很快取得了主导地位。[3]在师范教育改革的大潮之中,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完成了由以本科教育为主向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转变。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研究生招生规模急剧萎缩。70年代末,芝加哥大学把教育学院降格为一个系并入研究生学院的社会科学部,同时停办了日常的教师培训。教育系的教师们基本上中断了与实验学校的联系,研究工作也越来越脱离了中小学的教育实践。芝加哥大学在教育研究和教师教育方面的影响逐渐微弱。[4]
1996年11月,社会科学部的全体教职员投票表决部主任理查德·P·塞勒教授提出停办教育系的提议,最后获得通过。消息传出后,尽管芝加哥大学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全国的信件和抗议书,尽管第二年春天,大学委员会多次开会讨论恢复教育系的可能性,但是大学委员会主席、神学院院长克拉克·吉尔平教授(W.Clark Gilpin)最后还是不得不宣布:“恢复教育系已经没有可能。”[5]在第二年秋季开学的时候,《纽约时报》进行了报道:“开学伊始,校园重新塞满学生,红色斑点的常春藤爬满新哥特式建筑,黄色的自卸卡车隆隆地沿着街道行驶……一个多世纪以来,教育系第一次空荡荡的,没有来报到注册的研究生。”[6]
二、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停办的原因
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在美国甚至全世界曾经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和影响,那么,历史悠久同时又具有象征意义的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为什么会停办呢?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研究要达到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花费太多,而且得不偿失,所以停办。提议停办教育系的社会科学部主任塞勒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学院筹不到更多的办学和研究经费,于是一切向钱看的大学当局选择关闭教育学院。[7]
首先,让我们看看经费方面的原因。芝加哥大学日常的办学经费主要由捐款、学费、研究项目经费等组成,政府提供的经费只占很少的部分。尽管捐款是芝加哥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落到教育学院身上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教育学院的毕业生从事的基本上是教师职业,他们不像商学院、法学院的校友那样财大气粗、出手阔绰。至于学费,在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基本上不招收本科生,主要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本科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赖学生交纳的学费,但是研究生教育的经费更多地依靠教授们争取到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在20世纪60、70年代,怀疑学校、怀疑教育的心态在美国社会迅速蔓延,无论是政府还是各种社会基金对教育研究的兴趣大大减弱,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虽然,州以及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在芝加哥大学办学经费中所占比例不高,但还算得上是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而石油危机爆发后,这部分来源也大大减少。这四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芝加哥教育学院在70年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费短缺,进而导致招生规模急剧萎缩,也就是这个时候大学当局把教育学院降格为教育学系,并入社会科学部,这是教育学院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由此看来,停办教育学院,经费短缺是直接和主要的原因之一。
再让我们看看学术标准方面的原因。教育学科从诞生之初就不断地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教育学和教育研究能不能以及怎样才能达到像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的成就与地位?在教育研究史上,对教育研究的批评与对教育研究“科学化”的诉求相伴相随。这种由来已久的批评和诉求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达到了顶点,并对教育研究的范式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在与前苏联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美国社会针对学校教育掀起了一片讨伐之声。60年代的科尔曼报告以及兰德公司有关“影响学校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的大型调查,更加引起人们对学校和教育研究的怀疑。紧接着伊里奇(Ivan Illich)《非学校化社会》一书的出版,把当时美国社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共舆论对学校教育以及教育研究的怀疑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此,古得莱得曾经总结道:“在70年代,公众的批评不仅是针对学校管理者,也是针对学校的。学校和我们一样对政府、对法律体制、对教师职业,甚至对自己都失掉了信心。对学校内在功能的怀疑,其实也是对教育的怀疑,迅速地弥漫开来。”[8]学校机构和教育研究共同体面临着一系列挥之不去的问题:“学校有用吗?”“教育研究有用吗?”
教育研究者为了反击这些怀疑,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有效学校”(effective school)研究,希望为学校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也为教育研究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但是,怀疑学校教育无用、怀疑教育研究达不到科学研究的学术标准,这些对美国教育研究事业和大学教育学院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经费的减少。社会和政府管理部门批评教育研究不是科学研究,不能为教育决策提供确定无疑、直接可用的研究成果,减少了对教育学院的经费资助。间接的影响就是在“怀疑——追求学术性——脱离教育实践——引起更多的怀疑”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首先,由于对教育研究科学性的怀疑,社会和政府管理部门对教育研究经费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市场化管理,迫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取实证主义的研究立场。“市场隐喻”开始在教育研究领域大行其道,研究经费的提供者成为“顾客”(customer),研究者成为“合同方”(contactor),研究者必须根据“顾客”的需要按“合同”生产“产品”,即精确性更高、更科学的研究成果或知识发现。迫于压力,教育研究努力向成熟的社会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等学习,努力向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靠拢,希望以此提高研究工作的科学性。但是,教育问题不同于其他问题,一旦教育研究者采用科学范式或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以发现确定的知识、规律为己任,教育研究就可能远离教育实践。与教育实践离得越远,教育研究成果在教师和官员眼里的直接实效性就越低;实效性越低,反过来又使教育研究承受来自教师和官员更多的批评;批评和怀疑越多,研究机构得到的经费支持力度越不够。这种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就是:教育研究不仅没有达到社会科学的学术标准,反而因为追求实证主义的学术标准而远离了教育实践,并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经费的原因与学术标准的选择在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停办这一事件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究竟是经费的原因起了主要作用还是学术标准和研究范式的选择起了决定作用,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笔者看来,学术标准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经费紧缺的影响。理由很简单,如果是因为经费紧缺而停办,那么,我们可以在经济状况好转以后重新开办。以著名的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为例,它也曾由于经费短缺于1974年停办,但大约10年后也就是1983年又重新开办。但是,如果是因为学术标准而停办,即使筹到了充足的经费,只要不放弃原有的学术标准,那么停办了的教育学院将永无重生之日。正如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前院长格拉汉姆(Graham)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所说,70年代芝加哥大学停办教育学院,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只不过它并入社会科学部以后,却不能像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那样对变化了的社会形势做出迅速的反应,重新焕发生机。[9]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并入研究生院社会科学部以后,不仅没有迎来转机,反而在20多年以后最终选择了停办。从教育研究范式的角度看,它的停办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实证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穷途,标志着美国教育研究向新的范式转换。
三、从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停办看美国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
所谓“范式”(paradigm),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用它来指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形成的、由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承认和分享的一套理论模式。范式包含着科学共同体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也包含着相同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包含着近似的研究问题与解决办法。[10]所有从事教育研究活动的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式。在杜威领导时期和杜威离职后,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杜威常常被认为是教育研究领域科学范式的代表,他的作品常常被实证主义教育研究者引用,比如杜威《教育科学的来源》就常常与心理学家桑代克的作品放在一块,被实证主义教育研究者奉为圭臬。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教育研究的科学范式或者实证主义范式遵循的是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它们在认识论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在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做二元论的划分。而杜威是极其反对二元论的,在认识论上,杜威信奉的既不是理性主义的知识论,也不是经验主义的知识论,而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知识论。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实验学校,他所领导的应用性研究,并不像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那样以发现知识为己任,相反,他关注实践,关心儿童的经验。正如威廉·舒伯特所说,“杜威的认识论框架和他对人类思想的描述性解读,很明显是实践性的”。杜威强调人们面对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他有关科学方法的观点众所周知,但是他强调的日常问题的情境性、暂时性特点却被人们忽略了”。在研究方法上,“杜威反对教育研究向历史悠久、相对成熟的科学学科借用研究方法的倾向”。[11]理查德·普林也认为:“(尽管)杜威永远不会否认在定量和定性之间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区分……但是,杜威会反对把‘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区分。要想把握‘真实生活的世界’或者‘常识世界’,仅凭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一方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它需要两者的结合和交叉,才能真正地把握。”[12]
杜威离开芝加哥不久,教育学院的研究范式很快就脱离了杜威倡导的道路,重新回到科学/实证的道路上来。1909年就任教育学院院长的查尔斯·贾德(Judd·Charles)是“教育科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在随后的20多年内一直主导着该学院的教育研究,不遗余力地推行实证性研究。同样以倡导“社会效率主义”而闻名的课程专家博比特也在同一年到该院任职。怀特(W.White)在《教育实践之衰退与芝加哥大学的教育研究:1909-1929》一文中,曾对杜威的“教育科学研究”与贾德的“教育科学研究”进行过对比。他说,杜威的“教育科学研究”是指实验学校中的实践性研究,而贾德的“教育科学研究”是指大学研究室中的实验性、统计性调查研究,两者是不同的。贾德所倡导的“教育研究科学化”不仅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而且中断了杜威命名为“知性方法”教育研究的发展道路。[13]
二战以后,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完全摆脱了杜威的传统,迎合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面对社会民众和政府管理部门对教育研究产生的强烈怀疑,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选择了实证主义范式。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的选择在当时是一种占主流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接受社会的批评,继续以发现知识为己任,以更高的社会科学的学术标准要求自己,采取数理统计、实验等方法,试图生产具有确定性、普遍化的知识,向教育政策决策者和教师提供理论武器。霍根(Pádraig Hogen)曾发现这一时期的教育研究:(1)在经费拨款上,主要偏好实证的研究;(2)在研究者培训上,强调统计测量、数据分析、问卷设计的技巧、流利的语言能力和对概念进行操作性的定义能力;(3)欧洲和北美学生为获得高等学位提交的论文在本质上大多数是实证的;(4)美国出版的《教育研究大百科全书》中两篇研究教育研究题目的文章认为,教育研究差不多都是科学/实证的研究;(5)尽管教育研究成果的写作风格在近几年逐渐发生变化,但是很明显,大多数教育著作都按技术专家的写作风格进行写作。[14]埃德蒙·金也有类似的发现:“大约在4年之前(指1971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关于世界教育研究的书中列举了数千本参考书,几乎仅限于心理学研究、‘智力’测验、授业科目和测验的分析,以及其他类似的书目。”[15]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部管辖下的教育系,当时采取的正是这种态度,他们更加远离教育实践,只关注教育数据的统计分析。该系的心理学和教育学教授贝塔·科勒尔(Bert Cohler)说:“我们变得越来越‘象牙塔’”,“教育系如果只关注对数据的统计分析,而不关心学校教育的真实世界,(这样做)肯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16]
另外一种态度不占主流,主要以芝加哥大学施瓦布(Joseph J.Schwab)为代表,他强调教育研究的独特性,反对向心理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看齐,认为教育研究方向应该回归实践。施瓦布在领导课程改革失败后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指出,课程领域要实现复兴,课程研究者就必须从理论转向为实践的、半实践的和折中的。他所指的实践“关注选择和行动”,与理论“关注知识”形成对比,他认为,“实践的方法,导向站得住脚的决策;理论的方法,导向证明过的结论”。[17]舒伯特从四个方面对施瓦布提出的有关课程研究实践范式进行了阐述:一是问题的来源,强调课程研究(包括教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要从研究者头脑中的抽象概念和模式,转向对具体的事例。二是研究的方法,反对课程研究采用社会和行为科学所采用的归纳研究方法,主张采用审思(deliberation)的方法。三是研究主题,反对课程研究主题的一般化和抽象化,主张研究主题的具体化。四是研究目的,反对把知识生产作为研究的目的,主张在具体情境下做出具体的决定和行动。[18]
施瓦布提出课程研究(教育研究)的主题从理论回归实践的同时,霍根提出教育研究的目的要从“改进”(improvement)回到“理解”。科学/实证传统中教育研究把“改进”教育系统,提高教育效率作为首要的追求。霍根认为,以“改进”为目标的教育研究关注的是教育系统,而不是教育活动本身。在这种教育研究中,“理解”失去了绝对的重要性。霍根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的任务”。他还引用海德格尔的话来强调“理解”在教育研究中的作用:理解不仅仅是认知,理解是“人类在世的一种基本样式”。[19]
当施瓦布提出转向实践,霍根提出回到理解的时候,他们都是少数派,但是,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教育研究可能的一种路径。近30年来,教育研究领域确实出现了他们所期望出现的一些变化。马克·康斯特斯(Mark A.Constas)通过考察后现代教育研究的特征,为我们描绘了这些变化中的一部分情景。[20]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在就任英国教育研究协会主席时,要求大家重新认识教育研究的作用,即“教育研究为人们提供的主要成果,不是知识,而是实践智慧:在特定环境中判断和分辨改变什么可以、改变什么却不能改善教育的一种能力”。[21]恩斯纳(Elliot W.Eisner)等人也对研究成果呈现方式的变化进行过总结。这种种变化,尽管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称呼,但是它们确实存在并发生着。在这里我们暂且把这些变化归结为教育研究从科学范式向实践或者理解范式转换所表现出来的征候,并把这些征候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1)在研究目的上,从强调生产“知识”、提高教育效率,转而重视实践智慧、改善参与研究各方的生存状况;从强调“改进”,回到强调“理解”;
(2)研究主体和研究机构从以大学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为主,变成把广大的教师群体包括进来。原来投向大学的许多研究经费越来越多地直接投向教师;[22]
(3)研究内容和主题,从重视概念研究、理论研究,转向重视实践研究,从重视整体解决模式和理论体系建构,转向关注具体问题;
(4)研究方法从偏爱社会科学的“常规方法”如定量研究方法,强调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转向大量采用质性研究方法。[23]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带有后现代研究特点的研究方式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同;
(5)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从严格遵守社会科学的写作标准,转向多样化的呈现方式,自传体、文学、小说、叙事也被不少研究者采用;[24]
(6)在研究隐喻上,从“市场”隐喻,转向“协商”、“对话”隐喻。
(7)在教育研究的质量评价上,从倾向于以论文发表的数量、研究经费的多少以及论文的引用率等为指标,转向注重研究者以及研究活动参与者更好地理解自身所处的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