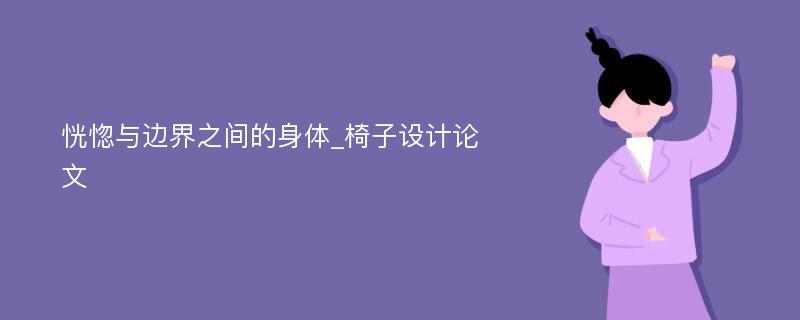
恍惚与界限之间的身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界限论文,恍惚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6)03-0014-08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6.03.003 钟鸣说过,诗人张枣发明了只对一首诗有效的私人语汇。而敬文东则认为:“钟鸣自己却正好相反:他发明了一套对自己整个书写都有效的语汇。”[1]243在《涂鸦手记》中,解释“地理学”(Geographic)这个词时,钟鸣说它源于希腊文的两个字:ge和grapho,字义是“地球”和“我写”。他诗意地称之为“关于地球的涂鸦和描述”,这也是作者写作本书的野心和梦想。在《中国杂技:硬椅子》的后记中,钟鸣写道:“在我看来,真正的才华不在于一得一失,也不在于此时此地,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终其一生的耐性才是其秘密武器。”[2]8-9他一再强调卡夫卡的说法:缺乏耐性是我们无法回到天堂的真正原因。耐性在钟鸣身上,也许是一个秘密,并非意味着别人不知晓,而是很难做到。某种程度上讲,耐性缓解了速度与反应的灵敏度。写作,在他那里获得了一种自己的速度与成长。他的才华不属于机智型的,或者说性格决定了这一切。有耐性等待某种东西自然地在头脑中成长、思考与接受,就少了即兴与趋附;有耐性等待那些迟迟不发芽的东西在冻土中酝酿,就少了浮躁:“我们将忘记南方那挥霍的习性,而记住北方冻结在土里的鸟食。”[3]253南方性,近乎浪费与颓废的美学,灼灼生华,自燃般地消耗,却缺少抵御的能力,很难持久。在1980年代,四川众多诗人和他们的诗作即如是。寒冷的北方赋予诗歌与诗人另一个向度,那种持久性,能够耐得住漫长冬季的荒芜与枯燥。 钟鸣曾说:“在别人写抒情诗的时候,我延续过去的爱好跑去写叙事诗了;在别人写‘史诗’时,我却热衷于短诗或相反;而在许多人大获成功接近自封的‘大师’,或以过来人自居的时候,我却开始对诗歌保持距离,采取陌生化的方式写上了随笔;等别人开始成年人的文学路线——青春期诗歌,中年小说时,我又像小学生亲切地回到了诗歌的门槛上——其中有下意识的成分,但绝不是存心作对,而是性格所使然,命运所使然。”[2]16当人们专注于自己所思考的问题时,就悄然与世界产生了疏离感。甚至,也和自己,和那个即兴的、冲动的、热衷新鲜与好玩事物的自己产生了距离:“蜗牛觉得自己的鼻子很短,/但它却探得书中的路程,/终将获得结局。在圆桌上/它抛弃了胜利,尤其是/那种轻而易得的胜局。”(《蜗牛慢行纪》)无论是诗歌还是随笔,在钟鸣那里,都因为他的耐性,他思考的反复与深入,逐渐蔓延为一个相互勾连的整体,获得了深度与辐射度。在他身上,又呈现着南方的精致性、趣味性与神秘性。他个人化的语言中,身体是在场的;并且语言标识的,却不仅仅是这种单纯的在场——还有它的延伸、恍惚与错位。钟鸣的书写,下意识地包含了自己的对立面,不是玩弄修辞的对立面,而是他在身体持久的感受与思考中,不得不遇到的尴尬与矛盾。在他的这里,对立是不确切的,有着语言和道德难以去定义的暧昧性。《旁观者》一书中,他反复用“恍惚”一词。恍惚在他那里是无意识的,他无法控制笔下的滞涩、停顿与飘忽,这是他的作品难以被理解的原因。然而钟鸣本人又能洞察到这种恍惚,他思考它,甚至迷恋它,却不放任它。 钟鸣的整个书写,都是清晰而理性的,却有一种难以定义的轻盈性与模糊性。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徘徊,这个深度思考者与语言的唯美主义者,已经为自己划定了界限:一方面是可以超越的自己,另一方面是永远不能打破的界限。卡尔维诺谈到文学的繁复性,他说:“我们是什么?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又是什么?是经历、信息、知识和幻想的一种组合。每一个人都是一本百科辞典,一个图书馆,一份物品清单,一本包括了各种风格的集锦。在他的一生中这一切都在不停地相互混合,再按各种可能的方式重新组合。……但愿有部作品能在作者以外产生,让作者能够超出自我的局限,不是为了进入其他人的自我,而是为了让不会讲话的东西讲话,例如栖在屋檐下的鸟儿,春天的树木或秋天的树木,石头,水泥,塑料……”[4]钟鸣也有这个梦想,用他繁复的笔触,唤出事物身上比人更持久的品质,它超越于时代的变幻与人性的阴晴不定。甚至,他走得更彻底,从器物入手,研究三星堆和上古文化,重建金石学上的研究。身体召唤人们去写作,写作朝向的尽善尽美,又呼吁出了一个为世界而行动的身体,日臻成熟与健全的身体则再度召唤写作……在钟鸣这儿,循环进入了良性的状态。不尽完美的现实让人们朝向梦想中的词,词语却让人们重新发现事物身上可贵的品质。于是,不满足于词的人开始触摸与了解物,用语言为他人与子孙后代记录重新发现的物,记忆延续、诗意与物性延续,人们于其间锤炼而成的品质也延续了下去…… 我只能这样。盖子里 是一个多么慷慨的世界, 把各种刺耳的声音容纳, 即使是一块粗糙的石头, 我划破的也是自己的喉咙, 我用水浓缩了的酸性掌纹, 惊扰的是我自己的灵魂, 它粗糙得实在不成样子, 那是个什么样的岁月哟! (钟鸣《我只能这样》) 在钟鸣身上,有一种聚敛性,对外在于自己的和自身的一切。他在自己身上过滤它们的伤害性,即使他忍不住发出感慨:那是个什么样的岁月哟!但这位深度思考者显然不愿意让自己陷入盲目的牢骚中。齐泽克谈“内在违越”,他说:“权力一直是,也已经是自己的违越,如果权力要发挥效力,它就必须依赖某种卑劣补充。”[5]33意识形态本身包含它的对立面。钟鸣说“虚假意识形态的人格化”[6]666,实际上就是人们画地为牢,陷入边缘者的自我框定中,自以为站在了对立面。他们批判与违背某种意识形态,却盲目地陷入了“违越”式的补充地位。诗人一旦意识到这点,就会让那盲目的、冲动的、自以为是的仇恨和牢骚被调节与转化:“我决不在城市里疯跑,/也决不和任何人交换,/我伤害着自己的灰尘。”(钟鸣《我只能这样》)他与他不满的一切保持距离,认清它们,却不会去“咬人”。诗人说:“灵魂只能按照自己的性质/分配给未来碳化的界线。”钟鸣追溯了时间中的碳化物,他用的更多的一个词是“氧化”:“而秘密则意味着美丽和氧化,秘密仅仅因为美丽。现在人们一般不说氧化,而说牺牲。”[3]33他想在自己的写作中记录氧化物与氧化作用,那些过去时代的隐秘与美丽:“在咽气断壳的氧化物中,我看清了/它华丽的隐身术。”(钟鸣《凤兮》)诗人的写作,也有意识地将自己列入了这个氧化过程中,即给所有的后来者梳理出一条隐秘的脉络。母语的美与疾在他这里,褪去了大而不当的华丽和骇人听闻的怪诞。诗人聚敛它们,用耐性等待时间的沉积、筛选与挥发,开出那朵奇异的玫瑰。博尔赫斯讲过一个故事,炼金术士的玫瑰:好奇的、满怀热情的人终于等不住了,失望了,嗤之了,离开了……炼金术士对着已成灰烬的玫瑰吹了一口气,它重新绽放于手中。 在钟鸣看来,那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即人们必须心怀敬畏与感激:对于我们已经生活其中的世界,对于我们已经其中一环延续下去的历史,对于我们前人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尽管如此,在他那里,这一切并非简单的接受与承认。然而一旦他把它们称之为界限,就是自己必须予以尊重的。谈到张枣诗歌中的谶语时,他说:“圣人也早已提醒众生:不知生焉知死。”[7]界限并非不存在,如果人们不只是把它当作言辞——当作令实际的冲突在其中闭合的言辞[5]12。就像齐泽克讲的笑话:一个顾客在吧台前喝威士忌,有一只小猴子跑过来,在顾客的酒中洗自己的卵;顾客换了杯酒,猴子还是照样。顾客很愤怒,问服务员为什么,服务员说他不知道,让顾客去问在酒吧里唱歌的吉普赛人。这个吉普赛人听了之后,就开始悲伤地唱起猴子洗卵的歌曲,他以为顾客要听自己唱歌。齐泽克说这个吉普赛人:“当他听到具体的抱怨时,他也唱起了永恒命运的悲歌,也就是说,他改变了问题的语气,把它由具体抱怨变为对命运之谜的抽象接受。”[5]53这就是所谓的冲突在叙述中闭合。当人们的身体遇到了现实世界的种种,那些不可知的和不敢知的时,禁忌并不能够在言说的“界限并不存在”中消除。 钟鸣说:“我对人道主义的胜利才是人的最后胜利这点深信不疑。其实,人无时不在自己的局面中。它常令人陷入尴尬。哲学的困惑,其实也就是现实的困惑。”[6]293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在钟鸣的文字、生活、他所专注的事情中,找到一个整体的精神脉络。他谈论“词的胜利”时,并没有贬斥语言。他忧虑的是人们陷入语言与现实恶性循环的怪圈中,无法自拔。因此,诗人希望用物的坚实性和生活的实际性消除词语带来的种种幻想。齐泽克说:“同‘真正的艺术’相比,流行剧和低劣仿制品更接近于幻想。……幻想本身就是个谎言。真正的艺术巧妙地操纵幻想,愚弄了幻想对思想的管制,从而揭露出幻想的虚假本质。”[5]24罗兰·巴特也曾经说过:“全部文学意味着:‘Larvatus prodeo’,即‘我一面向前走,一面指着自己的假面具’。……真诚性需要虚假的,甚至明显虚假的记号。”[8]26-27或许区别仅仅在于:人们是用虚假伪装真诚,还是让虚假揭露自己、指向真诚?界限,是人们的身心在与世界最深刻的相遇之时,不得不为它而却步或沉默的东西。写作的真诚性源于界限:人们说什么或不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界限的丧失,对于词和物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野兽惨遭灭绝,灵魂继续恶化, 时间测算痛苦的是另一个框架, 地质学中沉寂的部分已被发掘, 巨大的行星被非人的力量吸吮。 (钟鸣《时代》) 在《旁观者》中,钟鸣提到“文化名人”:“这是奇特的社会现象。不是我们室内人所能解决的。它像鸦片,具有兴奋和麻醉作用,来自人群最幽暗的部分——谭嗣同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它:阴疾。”[6]248贩卖苦难,用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来煽动人群和自身。这是我们文化中的疾,常年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把阳光本身连同阳光下的罪恶,一同列为憎恨的对象。某些东西一旦滋生与蔓延开来,就勾连起人们心中的阴暗部分,成就他们自以为的“美丽心灵”。这样的传奇故事与文化名人任何时代都有——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是因为人群需要它们,所以在不断演绎与流传。人群是滋生与助长阴疾的地方,看与被看,看者与被看者的表演与心态,隐秘地构成了一幅奇特而玄妙的景观: 当椅子的海拔和寒冷揭穿我们的软弱, 我们升空历险,在座椅下,靠慎微 移出点距离。椅子在重叠时所增加的 那些接触点,是否就是供人观赏的, 引领我们穿过伦理学的蝴蝶的切点? (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1》) 杂技中椅子在叠加,不断将危险推向更危险的状态。然而对于供人观赏的杂技来说,这令人屏息凝视的危险,只是表演的一部分,它唤起人们的一次次悸动之后,冷冰冰地走向自己专注的更高的高度。参与其中的身体是脆弱的,椅子重叠之时,却给观赏者带去的一次次震撼,让人们忽略了表演者身体微小的变化。诗人洞穿了我们文化属性中的冰冷与生硬。诗歌有一种唯美情调,却也冷冰冰地滑向了硬度:“椅子绷紧的中国丝绸,滑雪似地使他滑向/冬天,他专有的严冬。”(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2》)丝绸柔软、精致,却特有一种冰冷,尤其是当它冰冷地覆盖于硬椅子之上。他并不需要挖空心思地描绘文化中的美与疾。丝绸覆盖椅子的状态,让他找到了呈现物的切入点:冰冷、美丽、不可言说的神秘感全都出来了。叠加椅子的技艺在不断升高海拔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寒冷。自然现象中正相关的比例,实际上隐喻着技艺本身的完美度与它的冰冷度:每一次叠加都推进更危险的美,更不可及。然而对高度与完美度的追求,仅仅是表演本身的要求,仅仅是人们能够在一场技艺中化解对危险的紧张感——又回到了冲突在叙述中闭合这个问题。其实,身体是不在场的:“轻身术会使人更加超然吗?”(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1》)钟鸣指涉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被观看者与观看者一同参与了表演,前者对身体柔软度和适应度的训练,以及后者的惊诧、唏嘘和紧张,都是预先被设计在场景之内的。表面上看,是一个身体在呼唤另一个身体,是表演者在调动观看者。实际上,他们的身体都是作为技艺的一部分被差遣、调动,即使出现了恐慌,也会圆满地在最后化解。身体是缺席的,即使它看起来是在场的,紧张与焦灼都那般真实。这是文化的吊诡之处,它让人们以为身处真实,实际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已经成为虚假的操练:“爬高者在椅子上,像侏儒般倒立,露出些破绽,/看它是诗,天梯,还是椅子,或椅子上的木偶?”(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1》)在《旁观者》中,钟鸣虚构了一个场景:人群发出热烈的叫声,对着马戏团的表演,有三个人站了起来,蔑视了一下观众,然后消失了,这三个人是罗伯特·穆希尔、卡夫卡和曼德尔斯塔姆。“后来,穆希尔写了《黑色魔术》——探讨有趣的场景,什么是生命呢?生命就是活着谴责每件事。但以上帝的名义,什么又是活着呢?这是个难题。”[6]1228什么又是活着呢?像侏儒般倒立,还是像椅子上的木偶?技艺的轻身术无法让人更超然——如果技艺只是在掏空身体,不是减轻身体。人们看起来还活着,实际上已经不再活着了。他们身处一场杂技表演中,只是表演,无论它如何精彩。 这场表演中,处于最高处、最寒冷之处的人就是皇帝。“皇帝最怕什么,椅子。”(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2》)钟鸣说:“其实,皇帝并不怕椅子,他的权力足以让所有看得见的椅子顷刻消失……他坐如针毡怕的是附着在椅子上的那些神秘的意识。”[2]185他怕的是那些“深邃的目光,将要/对付他”,他们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盯着他的“不清洁”。这是身居高位者最寒冷的事情,目光的聚焦让他不得不谨小慎微,于是这显赫的身体,也只能沦为目光中的躯壳: 因此我们有责任让嘴和椅子光明磊落。 在皑皑而无雪的冷漠和空虚里, 在绷得像陶土一样的千人一面, 他坐出青绿,黄色,绛紫,制度,吃住软硬, 兼施暴力和仁慈。 (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2》) 目光的聚焦经由被聚焦者返还到了投射者的身上。皇帝亦返还了他高高在上的看。正如罗兰·巴特描述的埃菲尔铁塔,它兼具了观看与被看的功能。人们同样沦为目光的躯壳:“把经筵像巨缸顶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便有了读书月,有了丰雪兆年。”(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2》)表演者一旦上升到了危险的高度,他的身体就沦为维持高度的系数。观看者们盯着他,想象他会不会摔落。然而高度同样截获了观看者,他们必须要向自己紧紧盯着的高度持仰望姿态,拥有高度的人就成为了他们臣服的对象。表演者与观看者彼此被捕捉与束缚,实际上是表演这一形式,把它们置于自己的牢笼中:“我们有‘私’吗?公开后将不存在。”(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3》) 当所有人都被置于看与被看的表演中,“历险”“轻身术”,王的“光明磊落”和书生们的“读书月”,就都成为人们谨防目光的表演。文化把人们置于怪圈中:用自己的目光捕捉他人,再接受他人返还的目光,将自己束缚,直到人们之间的羁绊千丝万缕,分不清究竟谁盯着谁。习惯着想象自己置身于被凝视中,并让这种凝视摆弄身体、左右身体,直至身体形成表演的惯性。诗人说:“我们能否有被公开后/依然存在的那种‘私’,那种恪守,/因传种的原理而被爱和它的狭义撬动?”(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3》)那种“私”,即身体的真正脉动所在,不为表演而存在的恪守:“仅属于攀援之手,唯一的,非别的手,/不是所有的时候,也不会在别的椅背上。”(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3》)诗人试图释放一种唯一性:身体在发挥它自己,却并不是作为一种随时随地可以被取代的依附之物。人们身处杂技般的文化背景中,是选择不断地把自己置于更高的海拔,成就那冰冷的、让身体消失的表演;还是仅仅退回到身体的感受中,摸索另一种可能性:“或靠着它难以理解地步步高到风险和/众矢之的?在它私下沉落的光亮之中,/有轻抬的腕托给它永远被遗忘的轮廓。”(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3》)诗人选取椅子,已经暗示了一种被做出来的、缺乏呼吸的感觉。树也有硬度,但是它亦有生命和呼吸,它的生长以不被察觉的方式改变硬度,既柔韧又坚强。椅子只是被“拼凑”起来的“薄木板”,即使可以做到龙椅那般精致,覆盖着无比轻柔与美丽的丝绸,却只具有丧失呼吸的硬度。无论怎样的叠加,塑造出多少惊奇感,本质上都是僵死的不变,是没有呼吸的做,而不是生长。文化一旦陷入“做”的怪圈中,人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置于风险的最高处,让身体消失在最顶端的椅子中,那僵死的制高点。新一轮的表演与观看往复循环:“是谁呢,/使得我们的面子像拼凑椅子的薄木板,/因为没有表情而被瓦解。”(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3》)身体的轮廓被遗忘了,身体的呼吸消失了,身体也就成为了椅子——那叠加到更高地方的薄木板。是谁呢?诗人也追溯到了这个问题。张枣的《何人斯》中,有“究竟那是什么人”的追问,对古典诗意的追溯与重新发明。在钟鸣这儿,也是一种追溯,不过他追溯的是另一个方面:让身体与真正的诗意消失的,那种被人们信奉的虚假与冰冷的美丽。“让铁人和硬骨头,/从杂耍里走出来,而人间私事则成了‘丑闻’。”(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3》)这是另一个极端,在不断做出高度与完美度的表演之外,私的污点被放大为人尽皆知的丑闻。同样是一种不真实,在人们的观看中,一切都成了表演。丑剧?闹剧? “她们练就一身的柔术,却使我们硬到底,/不像肋骨在我们体内,能赎罪,得救;/不像一株蔓,牵引着鸟和它定时而归的幸福。”(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4》)这做出来的柔软,这应表演而生的柔软,是缺乏呼吸的。它不能变作夏娃的肋骨,也不是牵引鸟儿的蔓。柔术在制造一种柔软,像硬椅子一样缺乏呼吸,它充其量只能唤起一种生理性的硬,或者冰冷的、制度的、死板的硬。因此,人们不能像亚当与夏娃那样,被逐出伊甸园后,在之后的真实生活中,仍然可以通过身体感受到切实的痛苦与快乐,以此赎罪。诗歌,如果不能唤起呼吸的身体,只是把自己嵌入文化表演的怪圈中,就无法告知真实的处境,仅仅让问题堕入在表演中闭合的矫饰与空虚中:“她们的柔和使椅子像要一个软枕头/似的要她们,要她们灯火里的技艺,/要她们柔软胸部致命的空虚。”(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4》)无关痛痒的柔软,仅仅作为一种技艺的锤炼,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抬头瞩目它达到的那种高度,这是文化怪圈需要的。沉溺于这致命的空虚,就忘记了生活的真实所在。然而生活不是表演,什么才是活着?从表演的舞台、看与被看的伎俩中退出,思考一切是为什么,“我”的身体究竟在什么地方。 在写出《中国杂技:硬椅子》二十年之后,钟鸣创作了组诗《耳中优语》。不同于表演性的、将身体置于公共凝视中的杂技,耳中的优语是一种贴近身体的隐秘诉说:“它几乎是个少女,从竖琴与歌唱/这和谐的幸福中走出来/通过春之面纱闪现了光彩/并在我的耳中为自己造出一张床。”(里尔克《致俄尔甫斯十四行》)[9]在此之前,钟鸣创作的长诗《树巢》中,有《风截耳》一节,他在那时就已经开始关注这贴近身体的诉说与倾听。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杜伊诺哀歌》的开头:“有谁在天使的阵营里倾听,倘若我呼唤。”[10]对于俄尔甫斯来说,倾听者就是知音者,诗人呼唤的即是知音。在里尔克那里:呼唤是朝向神性的,知音者是让普通人震骇的天使。耶稣布道的时候,对他的门徒们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Who has ears to hear,let him hear)重点在于听,而不是耳朵。耳朵可以听得到神性、听得到世间万物的声音:“风里生出小兽和伶俐的耳朵,听宇宙的声音。”(钟鸣《风截耳》)也同样可以形同虚设,有耳相当于无耳:“变光明为黑暗,变万里长风为污染的双耳,/人被盯死,耳朵被晒干!”(钟鸣《风截耳》)贴近耳朵,表面上是贴近了身体。然而,耳朵本身却会被规训、污染,甚至晒干而丧失听的生命力。就如同练就柔术的柔软,其中可以呼吸与感知的身体是不在场的:“就像皇帝在风里梦见消灭了灰尘,/墙壁上挂满了铁笼子,/挂满了鱼鳃,要把风/送入所有在逃的耳朵,混淆其视听。”(钟鸣《风截耳》) 敬文东认为,在钟鸣的诗歌中,“树的海拔是理想的高度、人性的高度”,“椅子的海拔是现实的高度”[1]225。或许,还有一种高度,是天空的高,不过,那显然已经是不可企及了:“‘请保持距离’,太阳对夸父说,/‘那就是保护你的尊严!’火球开始/西沉,‘当心,残屑会刺伤你!’”(钟鸣《追太阳的人》)夸父追逐的太阳,在人神不隔的年代已经是不可及了,人们只会被这高度带来的温度灼伤:“而他则变得诡谲,/像一枚因哭泣而淌血的桃子。”(钟鸣《追太阳的人》)身体聚集了超出它承受范围的能量,走向自毁。也许,八十年代的诗人们或多或少地有过这种追逐的妄想,看着天空张开双臂,却无视身体所处的深渊。听力所及之处,同样有高度的差别——神的高度、理想的高度和现实的高度。张枣的诗歌是在寻找知音者与对话者,而他本人达到的高度,就决定了曲高和者寡这样一种状态。钟鸣则从听的角度,去辐射世界与万事万物。其中有理想的听、现实的听,甚至听的沦丧。也许,他从一开始就假定了知音者的丧失——如果人们能够遇到,那也只是很偶然的事情。物作为倾听者而丧失物性与自然性:“从树叶卷起两只耳朵,/偷听公开的暴力。那些还在土中的人,/秘密的萌芽。”(钟鸣《风截耳》)说到底,是人的阴谋与恐慌玷污了自然的自然性,让风声鹤唳转为草木皆兵。人的耳朵,则更早地经历了沦丧:“再没人涉水过河,/像壮士那样唱‘风萧萧……’”“地上有无数三只耳朵的秀才”(钟鸣《风截耳》)。耳朵失去了对理想之歌的耐心,转向卑劣的、利欲熏心的窃听。看可以转化为监视,听也有监听的功能。耳朵与世界相互污染、抽空,最终也难免不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表演:被监听者为监听者而说,监听者的耳朵被监听者束缚。 “但我一定要说出真理,/宁可麻雀叫我大嗓门。”(钟鸣《我只能这样》)诗人的目光,犀利地透过这个已丧失倾听者的世界。唯唯诺诺、为琐事而争吵与计较的麻雀们,显然受不了这深度的透视:“深渊逐渐在扩大,眼泪,/像廉价换来的肺痨和干瘦”“小市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习气。/遍地都是唐璜似的音节和古板”(钟鸣《我是怎样一个失踪者》)。如果说八十年代,“深渊”有时还可以算作一种理想主义的高蹈;此刻的深渊,则是从生命与生活的烦琐、无聊、乏味开始扩大,势不可当。牺牲、死亡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要抗拒的是将自己淹没于灰色之中的凡庸。在这样的情形中,交流与对话是不可能的:“那些彼此不信任的人,/他们谁也不愿意记住/那些曾扼制名字的力量,/我的失踪乃是一个无名者的失踪。”(钟鸣《我是怎样一个失踪者》)淹没于灰色中的人,宁愿用同样的灰色眼光淹没别人,他们彼此消解对方的存在。诗人自诩为失踪者,一方面是自身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则是无可奈何地被这个世界所烙印的身份:“你可听说,树林要把喧阗的麻雀开除?/用什么方式呢?——请飞到别处去吧!”(钟鸣《曼德尔斯塔姆失业》)在麻雀的时代中,诗人也自嘲地将自己列入其中。归根结底,人们是无法逃开时代和时代病的。 钟鸣说:“如果说曼德尔斯塔姆的太阳是黑的,那么我们的太阳恐怕就只能是灰的了,因为一旦道德降格以求,颜色便不会专一,而那恰恰是我们自己的传说空间,和我们自己的希波吕托斯。”[2]177-178在曼德尔斯塔姆那里,“黑太阳”是有牺牲性质的。诗人与祖国、与母语之间的关系,是希波吕托斯-淮德拉式的,因为拒绝乱伦,拒绝以不洁的方式玷污祖国与母语,而遭到迫害。但诗人所遭遇的传说空间,已不是黑色的恐怖与迫害,而是灰色的狂欢与腐蚀。通常情况下,人们可以对这个隐蔽的地狱视而不见,让自己接受它直至成为它的一部分。然而对于诗人来说,灰色的太阳在另一个意义上,让家园与语言流离失所。囚禁和放逐都会剥夺什么,前者的更可怕之处在于,它可能会被安然接受,以至于我们遗忘了真实处境,以为自己从来都是自由的。 钟鸣写了一组以曼德尔斯塔姆命名的诗歌,实际上,也在呈现自己生活中的事情。他谈到诗歌所处的希波吕托斯式的地位,但是却远离了“地下诗歌”这一说法。钟鸣说:“很少有人去想想那里面真正属于我们的阴影和困窘。”[2]219他对“虚假意识形态的人格化”很警醒,用苦难来哄抬自身与诗歌的地位是他所不屑的: 沙尘已将他们掩埋,像狗一样 把生命全都误解, 所有的牺牲全都出自口误和悲伤, 然后像盲人论英雄 (钟鸣《曼德尔斯塔姆遭流放》) 我们的时代甚至消解了牺牲,让它显得不真实。人们崇拜英雄与牺牲,也就是去误解它们,像视力欠缺的盲人一样,最后只得到了虚假。身体更真实的处境是它的阴影与困窘:“他们向庸人致敬,向贷款的银行出纳员鞠躬,/他们接受毫无愧色的雄辩家和局长的儿媳妇。”(钟鸣《曼德尔斯塔姆失业》)张枣说:“做人——尴尬,漏洞百出。”(张枣《空白练习曲》)这是身体的所在,必须要被直视的真实:“我不信麻雀一下就从庸俗经济学滑倒了后现代,/请注意,现在,他们一定在什么地方抓耳挠腮。”(钟鸣《曼德尔斯塔姆赶火车》)钟鸣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对话者的不存在。他的目光投向时代与我们自身缺失的部分,在这个深度思考者看来:身体在丈量诗歌,然而身体获得的存在感是基于它对缺失的感知,即对与我们相关的过去和未来中的美和美的失落的感知:“但我知道你高耸的颧骨和黝黑的肩膀/丈量着诗歌实际的距离。”(钟鸣《曼德尔斯塔姆遭流放》)也许,这是诗人选择曼德尔斯塔姆的原因,他带给诗人的并非黑太阳,而是一种对处境真实的感知,一种让人倍感无奈的缺失:“我想遇到英雄,却尽是狗熊/尽是小摊上仿制的皮货。”(钟鸣《曼德尔斯塔姆遭流放》)流放是一种心态,为什么人们在自己的家园和语言中,依然若有所失?我们丢失了什么?就像张枣所说的,人们丢失了宇宙、与大地的触摸,还丢失了一种表情。或者说,我们在家园中丢失了家园,母语中丢失了母语。胡冬说:“母语早已先于我们流亡了。”[11]在钟鸣看来,因为缺失,我们缩小了:“一些人的死亡把我缩小了。”[2]219也许,这是他的出发点。在《旁观者》中,他让优秀的亡魂们来到他的语言中,向他们致敬——对于不得不为之哭泣的缺失,人们谦卑地弯下腰。钟鸣透视到了那个伟大的精神图谱,一如他透视到正在缩小的我们和时代,他的目光从未离开二者。因此,不难理解他古怪的调笑:“麻雀叽叽喳喳作了自己的面包渣,/升至天堂的灰色大楼是那么讨厌。”(钟鸣《曼德尔斯塔姆失业》)这是身体真实的卑微与琐碎,在缺失之后的世界中。他的深邃与复杂,同样来源于缺失,来源于曾经在一些人身上存在过、却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的东西。 钟鸣不赞赏圆熟,他说:“圆熟的文本特征,也正是技术的单一化”“写作技术的有效性,必须在更开阔的视野中探讨。否则,就不可能有客观合理化的判断”[6]439。生命是有摩擦感的,钟鸣期望容纳于他诗歌中的,也是这些驳杂的摩擦痕迹。他深邃的写作中,不是跟着感觉走的状态,因此,他的诗歌中缺少呼之即出的婉转与流畅。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恍惚感,在扰乱思考与感觉之间的界限: 这些传说带走了一年又一年的灰尘, 坐在镜子里,鸦雀无声一下就老了, 开始像蚯蚓一样胆怯,再不敢放肆, 再也不能神气活现地蔑视乘坐地铁 (钟鸣《我仍然只能这样》) 忧伤的抒情性中,会忽然出现戏谑感,这也是诗人身上存在的“双面雅努斯”。或许,我们根本不曾看清他是双面的还是更多面的,或者仅仅是单面的。钟鸣制止自己将这一切纳入正反或此彼的二元思考中。含混的身体,原本就无法理清这些状态。而他坚决划定的界限,总在谨防被恍惚感僭越。好在,他是防着的。诗人说他们这代人,“要么是不幸福的,要么就是不道德的”,这是人们身处恍惚与界限之中的两难。 随笔集《畜界·人界》中,钟鸣提到了一种动物“果然”,现在它成了一个虚词,动物的身体消失了。钟鸣说:“生物的灭亡,对过去遥远活泼的生命之存在,或许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和一种莫名的恐惧,但对未来,那仅仅是一个极简单的名词或虚词化的过程。”[12]钟鸣以一种类书的做法,在他的书中重新召唤出那些真实存在、存在过的、想象中的动物的身体。然而他已经透露出了对消失与缺失的悲哀感。“果然”的身体是缺失的,而孔雀的身体正在消失。词语的迷人之处在于,它魔力般地呼唤出了人们的梦想,以及他们对遥远年代与事物之神秘性的追溯。然而词语的无奈之处也在于,追溯之物是此时此刻不能拥有的缺失之物。这其中的暧昧性在于:词的魅力取决于它对缺失之物的追求,人们为了更好地拥有它才让它缺失?或许,人们生而缺失。我们追溯前人与过去,我们的前人又追溯他们的前人,大家都在不安地寻找自己缺失的东西,都认为自己是缺失的。这种追溯,实际上是一个记忆问题。身处此时此刻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缺失——天堂以降人们就天然携带一种缺失,而在于如何去看待它。致命的不是失去了,而是漠视与遗忘这种失去,钟鸣忧心的就是这个记忆问题。尤其是,记忆中的身体。 人们无法理解的不仅仅是人,还无法理解石头、树木、大地、天空和它们身上的品质。记忆,若不沦为对“果然”那样虚壳般的记忆,就必须连同记忆中彼时彼刻的身体一同铭记。“要特别小心那些玩针孔相机的摄影家——应该是照相师即摄影界所称的‘红色摄影家’,他们会摇身一变成为觉悟者,什么时代都不服输,而且十分得逞。”[3]43所谓“红色摄影”,在时间的流逝中,将会沦为人们任意填充意义的空洞符号,倘若健忘的人不能回忆起自己彼时彼地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赞美和控诉都会变得毫无意义,词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缺失了身体。有时候,人们因为太过忠实于身体,而让它滞留在语言的僵壳中,直至被后者吸纳到看不见;有时,人们又因为太过圆滑,而让身体在语言中摇摆、左右逢源,语言就成为了游戏,至多是一个看起来漂亮点的躯壳。 首先是生活的真实:“掌握事物,而不是服从命题。”[6]1494其次是思考,在我们命定地要让自己陷入思考的地方,对跟着感觉走的那个自己喊停:“只能画事物的表皮,事物并非事物。”(钟鸣《涂鸦》)这是诗人对语言的质疑:“他画你外省的乖张/你却要一个永恒的形象。”(钟鸣《涂鸦》)“就像画了一千遍的抚摸。/墙把我们小心翼翼浇筑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无法感受肢体的膨胀,/肉感的威胁和麻木不仁的怯弱。”(钟鸣《涂鸦》)或者是不足,或者是过度,归根结底都是不足。对于身体而言,表皮的描摹和过度的描摹都让我们失去了它。他说自己“从曼德尔斯塔姆那里,学会了对形容词的削减,就像国家裁军”[6]93。恪守真实,当人们开始修饰感情时,感情就要消失了。诗人一直在召唤与抵抗那个身体。不仅仅是记忆自己,还要评价与思索那个曾经是“我”、现在正和另一个“我”融合的自己。 钟鸣笔下,时代与它的元素出现得很多,他们就像旁观者书房外的喧嚣,他听它们,思考它们,却仿佛从不属于它们。他关注它们像关注记忆链条中的一环,寻找我们的断裂与丢失。而他真正关心的,是更遥远的物和它们的时代。从那里,也许可以溯及民族最古老的记忆。物往往比人更富有耐心,它们被制造、接受摆弄、做修辞之用或被销毁与埋葬;在时间中静候被发现,被丢弃、贩卖,成为新一轮的修辞附着物;或者机缘巧合地出现在某个命定之人的手中,他打量它们,触摸它们的纹理与磨损,让它们释放出自己承载的记忆。那些记忆是残缺的,却有关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生活;有关我们从何而来。而已经缩小的我们,正是在溯及缺失之物、溯及记忆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所在。诗人不愿沉溺于语言带来的恶性幻想,他试图从物的坚实性中,发掘出身体的真实所在。 钟鸣为什么要在《涂鸦手记》的开头谈地理学?“那个书从高地开始,最后到低地,就是到东南亚,其实我里面的很多地方都专门谈到这个地方,这条线正好是《山海经》的路线。中国的地理是地趋东南嘛。”[13]“关于地球的涂鸦”,这诗意本身来源于某种真实性与坚实性。马可·波罗那儿有一本涂鸦,卡尔维诺那儿也有一本以前者的涂鸦游历为题材的涂鸦,并且取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看不见的城市》。人们用看似真实的口吻诉说虚假,或者用虚假的语气吐露真实。人的痕迹就是对世界的涂鸦,在钟鸣那里,这个词是意味深长的:重要的还是真实,涂鸦掩盖了真实,也泄露了真实。古老《山海经》中就记录的路线,任凭时间中的人们来来往往,留下自己的涂鸦,修改或装饰它的表面,而它本身,却不动声色地向人们昭示持久与坚实。 界限源于对真实的尊重,一旦明白这一点,言说与生活就不会脱节,这是前提。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谶语,才有了避谶之说,也有了避不开之说。语言有时候摧毁了我们,有时候拯救了我们。说出还是不说,其中的玄妙是在它们之间徘徊了几个圈、往复了多少回,那就是人们正在过的生活。谈到顾城死后,无聊之人以诗人生前的“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与被杀都是一种禅的境界”来为他的行为做出辩护时,钟鸣引用了帕斯卡尔的话:“一个人的德行所能做到的事不应该以他的努力来衡量,而应该以他的日常生活来衡量。”[6]93实际存在于生活中的界限,并非通过言辞就可以找到逾越的理由。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无关德行,而是幸福。界限不能解决幸福的问题,或许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解决,幸福只是很偶然的事情。罗兰·巴特说:“文学的写作仍然是对语言至善的一种热切想象,它仓促朝向一种梦想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清新性,借助某种理想的预期作用,象征了一个新亚当世界的完美,在这个世界里语言不再是疏离错乱的了。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当此文学仅是为了如下的目标才创新其语言之时:文学应该成为语言的乌托邦。”[8]55乌托邦即不可能,即人们追求却到不了的地方。史蒂文斯说:“不完美才是我们的天堂。”也许在这一点上,只能保持缄默。 [引用格式]曹梦琰.恍惚与界限之间的身体——钟鸣论[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3):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