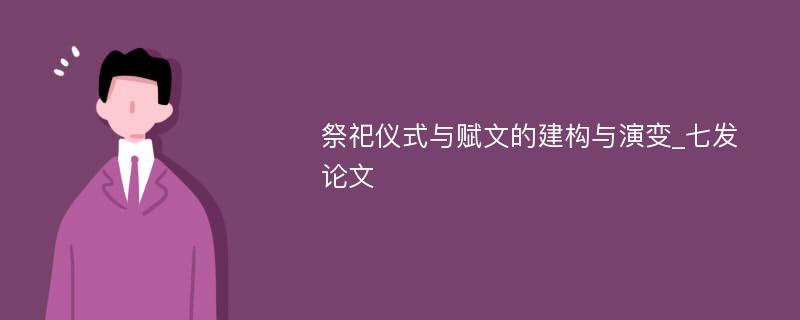
宾祭之礼与赋体文本的构建及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礼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起源于宗教(宗庙、巫术)作为一种常见的说法,赞成与否,中外学者多有论列,无须复赘。然而落实到中国文学的产生,其溯源之论又必须着眼于文体,因为不同文体又有着不同的指向,例如赋体与宗庙的关系,则更典型地体现在古老的宾祭之礼中。赋体的文本初起于先秦,盛于两汉,影响波及魏晋六朝,以至唐宋有清,尤其是“献赋”与“考赋”的传统,成为诸文类中与朝廷政治关联最为紧密的一种。选择“赋体”与“宾祭礼”之渊承作考论,一在二者间具有深密的内在联系,这突出表现于“宗庙献赋”与赋体立名、“宾祭执礼”与赋体结构、“备物以享”与赋之体物以及“媚神观德”与讽劝传统诸方面。二在赋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这又突出表现于四方面:其一,赋是最早的有名姓的文人创作,是纯文学的肇端;其二,赋是描写物态的文体,这无论汉人所说的“感物造”,还是晋人所讲的“体物浏亮”,皆以“物”为中心;其三,赋是修辞的艺术,以“铺采摛文”为美尚;其四,赋的兴盛与礼乐制度关系紧密,例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论赋源“殷人辑颂,楚人理赋”,内含了先秦时代的祭礼颂神传统,而其《时序》篇说“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①又并称汉代“辞藻”与当朝礼乐,费经虞《雅伦》卷4《赋》谓“至于孝武,升平日久,国家隆盛,天子留心乐府,而赋兴焉”,②亦明赋与礼的关联。正因如此,对赋体起源的探讨,也就具有了我国文士创作的发生意义。 而对赋体起源的讨论,又呈多元态势,有的偏重内涵,有的偏重结构,有的偏重功用,有的偏重词章,是以有源于《诗经》、《楚辞》、纵横家言、隐语、俳词等说,莫衷一是。论源于《诗》者,又有如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③歧分为三,以对应“六义”中之三体。古人由于宗经,所以又往往将文学起源归于“六经”,其如清人袁栋《诗赋仿六经》云:“诗赋等文事略仿六经:诗体洁净精微似《易》,文体疏通知远似《书》,诗余温柔敦厚似《诗》,赋体恭俭庄敬似《礼》,歌曲广博易良似《乐》,四六属辞比事似《春秋》。”④其就创作形态论,所言“赋体……似《礼》”,颇有启发。而近人刘师培又说“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⑤实据《汉志》所载就“宾礼”一端考源,亦多新思。⑥然而,我们根据秦汉时人“辞”与“赋”、“赋”与“颂”经常连用且不刻意辨别的情况来看,赋的起源与同为“宗庙之事”的祭祀、聘问之礼联系十分紧密,落实于赋体文本的构建及演变,其源正在古代的宾祭之礼。质言之,赋体导源于称为“宗庙之事”的祭祀与聘问,本文将从“赋”的内涵演变及其礼仪性的角度做一探索与论证。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赋体文学的发展比较复杂,从创作主体而论,有文人赋和俗赋两条线索;从创作形式来看,在汉代又分为四言诗体赋、骚体赋与散体大赋。相对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的俗赋文献极少,同时文人赋中也是以散体大赋为主流,因此本文论述赋体文本之构建与演变,是以文人赋尤其是散体大赋为主要对象的。 一、宗庙献赋:赋体文学的立名因缘 “赋”的立名,古人多兼两说,即“六义说”与“瞍赋说”,前者义源《周礼·春官宗伯》与《毛诗序》,后者义源《国语·周语》,绾合而论,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开宗明义:“《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⑦取义均源自《诗》。然校考赋体,《诗》之“赋”法与文体之“赋”迥异,其实,就“赋”字言,文体之“赋”、“六义”之“赋”,包括“瞍赋”及《左传》中“赋诗”之“赋”,都是后起义,至于汉赋与楚辞、隐语及纵横说词等渊承关系,也是作为赋体文本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因子,绝非赋之立名缘起。因此,辨明“赋”之本义及其如何与文学发生关系的历史进程,是我们厘清赋体文学起源的关键。 先从“赋”字原义看,有两点值得申述:一是赋与铺。《尔雅》谓“赋,量也”。郝懿行谓“赋敛、赋税即为量入,赋布、赋予即为量出”。⑧而赋由“敛”转为“铺”意,王念孙《广雅疏证》认为“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⑩是从文学批评的意义将赋税之铺(布)引入文体之赋。二是赋与傅。《汉书》载:“初,安入朝……使为《离骚传》”,(11)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离骚传”条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12)尹湾汉简中出土《神乌傅》后,裘锡圭便指出:“由于《神乌傅(赋)》的出土,可以肯定王念孙的意见是正确的”。(13)《汉书·高帝纪》:“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如淳曰:“《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14)汉代将到了服徭役和兵役年龄时向官府登记称为“傅”,而成丁开始服徭役和兵役也称为“傅”。这就表明,“赋”与“傅”都有征发兵役的义项,且“赋”、“傅”通假。 与“赋”相同的“铺”、“傅”均与赋税相关,适证“赋”的本义指征收田赋及其所得。故《说文解字》云:“赋,敛也”,(15)作为动词,意在征收财货。然而中国古典语词的特点往往是动、名词性合一,因此“赋”又可指称征收取得的财货。《尚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注曰:“赋谓土地所生。”(16)《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孔颖达疏:“服虔以为子产作丘赋者,赋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马三牛,复古法耳。”赋田出牛马等实物,乃古法之遗。“赋”的基本义项,就是征收所得的田赋。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17)指军赋,引申为军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赋”作“军赋”意是“六书”中“转注”用法,(18)为后起义,本义则宜如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所解“赋敛”、“田赋”。(19) 征收田赋的重要内容是“赋牺牲”,据《礼记·月令》记载: 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之所以“赋牺牲”,是为了“飨祀”皇天等神祇。《礼记·曲礼下》载“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孔颖达疏:“此言牺谓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赋敛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牺赋。”(20)可见自天子以至诸侯、大夫均需征收牺牲以供祭祀,其享神的牺牲(牛色纯者为牺,体全为牲),统称“牺赋”。农耕是征集田赋的前提,《国语·周语》载: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之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21) 天子行籍田礼是为了号召天下“务农”,目的是“媚神”以“和民”,“享祀”与“布施”,提供的是物质保障。古人享神,不仅包括“牺牲”,《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章载鲁庄公云“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章,宫之奇曰“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22)《墨子·尚同》谓“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23)酒酿、黍稷、牺牲、玉帛等皆所征收之“赋”,均为土地所生,用以享神求福。 上古享、飨二字相通,献神为“享”,待宾为“飨”,享、飨礼数相近,行礼环节所用之物曰“赋”。《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24)杨宽解曰:“礼的‘始诸饮食’,不外乎二个方面,一是把鬼神看作活人一样,给予饮食……一是在聚餐和宴会中讲究对长老和宾客尊敬的方式”,(25)这又衍生出后世祭祀之“享礼”与待宾之“飨礼”。关于古“飨礼”的完整记载已亡佚,许维遹《飨礼考》一文论“飨近于祭”,计述同者有六:需斋戒、用六尊六彝、用腥俎、有祼事、庙中立而成礼、同乐。(26)待宾之礼分飨、食、燕,而飨主敬,于礼最隆。因此,上古文献中享、飨二字的通用,不仅音近通假,更在于礼数相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臼季谓晋文公曰“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27)《论语·颜渊》载孔子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语应答“仲弓问仁”,(28)深明宾、祭二礼的重要。而宾、祭之礼作为探讨赋体文学立名的关键,有三点先需申述。 第一,宾、祭均用赋。祭祀用赋,前文已论,如“牺赋”。聘问之时有献礼环节,其物曰“庭实”,杨伯峻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中“庭实”一词曰:“诸侯朝于天子,或互相聘问,必将礼物陈列庭内,谓之庭实。”(29)“庭实旅百”指朝堂所陈贡品之齐备,庭实乃土地所生,无疑是征收所得之“赋”。聘问之后行飨食之礼,宋易祓《周官总义》解“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云“祭祀以牲为重,所谓入牲者,其牵牲欤?……大飨,则有司从牲之后,即杀牲于庙门之外”,(30)宋朱申《周礼句解》曰“大享宾客,设牲于庙门外,因即烹之”,(31)均明“牺赋”为宾礼所用。 第二,宾、祭用乐相同。《周礼·春官宗伯》:“凡乐事,大祭祀……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帅国子而舞。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32)祭祀牵牲入庙,而待宾则于庙门之外杀牲烹之,因此不用《昭夏》,飨祭因程序不同而在乐舞上略有不同,其他方面则完全一致。又《左传·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33)享最重,故可该宾礼,此为宾祭乐舞相同的证据。 第三,宾、祭统称“宗庙之事”。周人尊祖而敬宗,“从西周金文的内容看,周人对土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自然神的崇拜观念比较淡薄,而对祖先却十分崇拜”,(34)故祭祖多在宗庙之内,聘问亦如此。《春秋经·庄公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胡安国云:“享者,两君之礼,所以训恭俭也。两君相见,享于庙中,礼也。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非两君相见,又去其国而享诸侯,甚矣。”(35)此论正与刘宝楠《论语正义》解“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句意相合: 正义曰:“宗庙之事”,郑《注》指祭祀。胡氏绍勋《拾义》云:“宗庙之事,祭祀在其中,独此经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案:胡说是也。(36) 公西华所言“宗庙之事”非一般祭祀,专指诸侯聘问。值得注意,春秋时礼虽多端,但诸侯正式的聘问及享礼,均在宗庙。《仪礼·聘礼》载,宾国之使初见主国之君,国君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郑注:“迁主所在曰祧。《周礼》:天子七庙,文武为祧。诸侯五庙,则祧始祖也,是亦庙也。言祧者,祧尊而庙亲,待宾客者,上尊者。”(37)祧即宗庙,可证宗庙中相见之礼。 由上可知,祭祀、聘问均在宗庙内举行,以“享礼”为核心,行礼用赋。而享礼用“赋”包括礼神与宾之“辞”,所以据“赋”与“辞”之关系,又可观察一条赋体文学立名的线索。作为文体的“赋”发展至汉代时,无论其名称抑或篇制皆已奠定,而据《汉书·艺文志》载,先秦“赋”有屈原赋、唐勒赋、宋玉赋、孙(荀)卿赋等。荀子的《赋篇》命名并非自为,而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所加。然汉人将屈原的骚体作品称为“赋”,已是常见之事,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乃作《怀沙》之赋”,(38)《汉书·贾谊传》所谓“屈原……作《离骚赋》”,《地理志》“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39)班固《离骚赞序》“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40)如果我们重新细缕文献,或可发现“辞”与“赋”的本质联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41)这就表明,在汉人看来,赋是体裁,其以逞辞为表现形式。辞由人发,故附着于人,宋玉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而“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42)专指作品时又以“赋”名篇,实则辞、赋为一事,因此汉人习于“辞赋”连称,如“会景帝不好辞赋”,(43)“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44)著者显然无意将辞、赋作为文体来区分,后世反复讨论汉代辞、赋之别固属无谓,偏离当时实际(两汉以后辞、赋发展有别另当别论)。那么“辞”与“赋”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呢?这正是我们探讨赋体文学立名的线索。 第一,赋体文学的立名源于祭祀过程中的“献赋”活动,而“辞”正参与其中。刘师培《古政原始论》第十《礼俗原始论》称“上古五礼之中仅有祭礼”,“礼字从‘示’足证古代礼制悉该于祭礼之中,舍祭礼而外,固无所谓礼制也”,(45)在早期祭祀中,收集起来的各种物品即“赋”是用以享神的重要媒介,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辞”的献上(详见第二节),正如恩斯特·卡西尔通过研究“未开化语言”指出,“命名法的秩序并不依赖事物或事件之间外在的相似之处;不同的物体,只要它们的功能意蕴相同,也就是说,只要它们在人类的活动与目的的秩序中占据相同或至少相似的位置,它们就往往具有同一个名称,归在同一个概念之下”,(46)因为“赋”的使用,而使得一并献上的“辞”与“赋”发生联系,因此推断赋体文学得名于祭祀过程中的“献赋”。与此同时,“辞”在表达祭祀者的虔诚时,还要陈说献赋的明细即清单,这便是“礼法”到“赋法”——铺排的转变(详见第三节)。 第二,“赋”的原始义项包括创作、收集、使用“辞”与“诗”。《尔雅》“赋,量也”,与“赋车”、“赋牺牲”等用法一样,辞令、歌诗也需要创作、收集,属于“赋敛”义,而陈辞、颂诗属于“赋布”、“赋予”义,一并可用“赋”概括之。刘大杰认为,“《诗经》中较早的作品,是宗教性的颂诗。这类颂诗以《周颂》为代表……在艺术的功能上,正履行着宗教的使命”,(47)郑樵《通志》云“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又谓“宗庙之音曰颂”,(48)郑玄答赵商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49)《颂》诗作为《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包括《大雅》中西周初年的祭诗),可见是属于“造篇”之列的,而宾礼源自祭礼,且两者乐制相近,因此后世外交场合的“赋诗”源于祭祀用诗。 由此思路,我们对前人“不歌而诵谓之赋”语或可作进一步的理解。《汉书·艺文志》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50)前后两句有着内在的联系。“不歌而诵”之“诵”是诵读、言说之义,“登高能赋”出自《毛传·鄘风·定之方中》:“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51)其早初的语境诚如章太炎《辨诗》所言:“《毛诗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52)祭祀、聘问行礼于宗庙之中是谓“登高”,如《礼记·明堂位》:“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升歌《清庙》”,《祭统》:“声莫重于升歌”、“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仲尼燕居》:“两君相见……升歌《清庙》”,(53)“升”、“登”二字古音相通,这是祭祀、聘问用乐的制度,行礼过程中的陈辞与答辞也会一同进行,巫、祝、傧参与其中,因此在宗庙之中行礼而使用言辞的行为就是“赋”,后又转化为具有名词性质的“赋”。这里的“赋”尚是作为文体之“赋”的早期义项,但对后来作为文体的“赋”具有诵读、言说功能奠定了基础,如《汉书》载“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54)即为明证。 缘此,赋的立名与形成并非如刘勰所言经历了“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的进阶程序,(55)而宜为“六义”之“赋”与“体物”之“赋”并列产生于上古的宗庙行礼。换言之,是田赋体现于宾、祭之礼的赋物与赋辞,被借用于“赋诗言志”,再转而命名以铺陈辞藻为特色的文体之赋,赋体文学结构的衍生亦当于中追寻。 二、宾祭执礼:赋体结构的衍生机制 赋体文学以逞辞为特征,当追溯于古代宗庙之礼献辞、用辞的传统,转向于“行人辞令”与“贤人失志之赋”(楚辞),影响到汉赋发展的体势,其中“尚辞”及构篇,与宾祭执礼有着异质同构的联系。如前所述,周人祭祀在献赋即献物、献诗之外,还有一项最为重要的活动即“祝辞”,需要将自己所献方物与虔诚之心陈述出来。《周书·金縢》载“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史乃册祝曰”: 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56) 周公通过祭祀周世三代先王而为武王祈福,其祝辞明言:“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璧与珪是其享神之物,而自称具备的“多材多艺”,同是媚神的资本。周人祭祖一般会设“尸”,呈上“祝辞”之后“尸”代答辞即“嘏辞”,郑玄注《礼记·礼运》“修其祝嘏”谓“祝,祝为主人飨神辞也;嘏,祝为尸致福于主人之辞也”,(57)可见“辞”的重要。 不惟祭礼尚辞,宾礼之中,也有重辞传统,且多对问形式。古人待宾之礼,聘而飨,次食之,再次燕之。“三者具,则谓之礼备。若有飨而无食或燕,则谓之礼不终”,(58)飨、燕均多文辞。《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赵衰因有“文”而陪侍公子重耳赴秦穆公之“享”,所谓“文”,注曰“有文辞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注曰:“因享宴之会,展宾主之辞,故仲尼以为多文辞。”享多文辞,方得孔子赞许。《左传·昭公元年》:“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赵孟为客,礼终乃宴”,(59)《国语·晋语》:“秦伯享公子(重耳)如享国君之礼……卒事,秦伯谓其大夫曰:‘为礼而不终,耻也。’……明日,宴”,(60)“宴”即燕礼,“燕”本作“言”,主言语对答。刘雨《金文中的飨与燕》一文指出: 在西周早期金文中,不见用“宴”或“匽”来记燕礼,但有若干件器铭用“言”字来记燕礼。……盖古时燕礼乃因外交活动,欲有所“言”而设,故以“言”字记之。……后世以音近而假宴、匽来记言(燕)礼。(61) 祭祀中的“祝嘏”与宾礼享多“文辞”,其“言礼”彰显出宾祭之礼重辞的传统,已开后世辞赋问对之途。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认为“今即《周礼》祝官职掌考之,若六祝六词之属,文章各体,多出于斯”。(62)“楚辞”源于巫祝,前贤备论,汉人“赋”、“辞”并称,且多描写天子礼仪,亦由此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外交辞令同样源于“祝辞”,这与汉赋的形成联系更为紧密,主要原因则是外交辞令由“大祝”造作,而且两君相见,必以“先君”为辞,彰显宗庙事与礼仪性,原因就在对祭祀与聘问诚敬之心的要求。 《周礼·春官·大祝》载:“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其中“祠”与“命”均与外交相关。“祠”作为“六辞”之首,最为重要。郑玄注:“一曰祠者,交接之辞。《春秋传》曰‘古者诸侯相见,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辞’之辞也。”(63)此为两君相见之礼,而国君及君主的代表在言辞中均可称“先君”,证之《左传》,如《僖公四年》齐桓公讨伐楚国,谓屈完“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等,不胜枚举。而“先君”与“祠”的关系,恰是行人辞令与祭祀的渊源所在。据《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孔颖达疏:“凡公行者,或朝,或会,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亲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庙,反必告至。……诸侯朝天子则亲告祖祢,祝史告余庙。朝邻国则亲告祢,祝史告余庙。”(64)此为国君出行告庙的各种制度,无论亲自告庙,还是由祝史代替,既然称“告”,均需“陈辞”,又继之以“币”即物品,《礼记·曾子问》载孔子之言曰“凡告用牲币,反亦如之”,疏曰:“天子、诸侯出入,有告有祭。”(65)告、祭合一,告是目的,祭是手段,告知祖先出入的情况,与正式祭祀所需的陈辞、献礼相同。由此又引出两点问题。 首先,就性质而言,无论君主或使臣均需告庙而出,行人辞令既代表在世君主,也代表去世之“先君”,之所以多称“先君”,是为承继旧好。《左传·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来聘,执币傲。叔仲惠伯曰:‘是必灭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杜预注:“《十二年传》曰:‘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明奉使皆告庙,故言傲其先君也。”此引《文公十二年》秦国使臣之言“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以证其义,(66)说明出聘告庙所带礼物可称“先君之器”,至于所用辞令,自然附着了“先君”的色彩。 其次,论产生过程,祭“先君”作“祠”,以供辞令之用。按《说文》:“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67)沟通人神关系时,文辞较多之祭称为“祠祭”。《周礼》所谓“大祝作祠”以供辞令之用的描述,在于出聘本需使用辞令,而告庙后犹如代替先君出使,沟通人神关系,与“祠祭”近似,这又是专用之“祠”的泛用(泛指祭祀)。(68) 理清祭祀祝辞、外交辞令的一源分流的发展过程,试以享有“一代文学”之誉的汉赋为例,进而辨析赋体文本与二者的关系。可以说,鼎盛于两汉的大赋作品,当以枚乘《七发》、扬雄《长杨》为正宗,《七发》一系有《子虚》、《羽猎》诸篇,铺排美食、声色、音乐、物产、车马、游猎等题材;(69)《长杨》一系有《两都》、《二京》等篇,承传物产、游猎之外,重点张扬大汉天子祖宗之圣德。(70)赋体结构分别与交聘之礼、太一信仰、庙制之争、五德终始、月令之学密切相关,推究其源,祭礼为其本根,其中经历了从祭祀祝辞到聘问祝祠、纵横辞令的演进,直至汉赋文本的形成。试述三点证据如次。 证据之一,早期汉赋的文本多以聘问为发端,此为汉赋与祭祀、聘问关联的直接依据。如《七发》首句“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是为吴、楚相问;《子虚》开篇“楚使子虚使于齐”,(71)是为齐、楚交聘,诸侯聘问之礼尚存,且汉初藩国势力尤强,俨然以宗周封国自居。到武帝强化中央集权之后,《上林赋》描写则变齐、楚臣服于天子,及至《长杨》、《两都》、《二京》之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东都主人与西都宾、安处先生与凭虚公子,仍是主客之辞,聘问之遗,“祝辞”为宗,显而易见。 证据之二,“三驱之制”为汉赋游猎、美食题材提供了描写的范围,此为赋体与祭祀、聘问关联的第一重内在依据。考“三驱”义,颜师古曰:“三驱之礼,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也。”(72)此田猎三种功能,分指祭祀、待宾及日常食用。《七发》、《子虚》写游猎,分昼夜两端,而饮食为其所出,车马为其必备。《左传·昭公三年》载“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吉日》,《诗·小雅》宣王田猎之诗,楚王欲与郑伯共田,故赋之。”《昭公四年》“楚子合诸侯于申……宋大子佐后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见,椒举请辞焉。王使往曰:‘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将堕币焉,敢谢后见’”,杜预注“宗祧之事”:“言为宗庙田猎。”(73)以上都表明聘问、会盟之礼与田猎活动的内在联系。西汉末年至东汉中期,扬雄《羽猎赋》谓“武帝广开上林”的行为“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74)《长杨赋》论成帝猎长杨,“恐不识者,外之则以为娱乐之游,内之则不以为乾豆之事”,班固《东都赋》“申令三驱”,张衡《东京赋》“成礼三殴(一作驱)”,(75)也是对古礼的摹写与历史的反思。 证据之三,“问君之富”为汉赋土地、物产、饮食题材提供了铺写的对象,此为赋体与祭祀、聘问关联的第二重内在依据。《礼记·曲礼下》:“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孔颖达疏曰:“数地以对者,数土地广狭对之也;山泽之所出者,又以鱼盐、蜃蛤、金银、锡石之属随有而对也。”(76)故“赋”之夸饰“土地”、“物产”、“饮食”正从“聘问”礼中而来。如《子虚赋》中楚使子虚对齐王问: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范围】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地形物产】其山(山势)……其土(矿产)……其石(玉石)……其东(香草)……其南(平原地势)……其高燥(蒿草)……其埤湿(蒿草)……其西(池景)……其中(龟鳖)……其北(林木果树)……其上(飞禽)……其下(虎豹)……(77) 礼书与赋文两者相校,正可对读。至于刘师培说“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78)而“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79)行人辞令与祭祀又一脉相承,倘认为汉赋直接起源于纵横辞令,显然断章取义,没有深抵问题本真。 三、备物以享:体物特征的文体融升 赋体文本最大的特征在于对“物”的描绘以及向“事”、“理”的提升,无论是对赋家“感物造耑,材知深美”(80)的称许,还是对赋作“体物而浏亮”(81)的要求,显“物”以彰事明理,是作赋的核心问题。落实到具体创作,宏篇大制固然当“体物写志”与“体国经野”,而那些“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小赋,同样要“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82)然追溯“物以赋显”(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之源,正是宾祭执礼时“备物以飨”、“享以显物”的传统,其中“飨礼”发挥重要作用,“六义”之“赋”与“体物”之“赋”的学理基础于此并列产生,而归投于“辞赋”。祭而享自不待言,而飨是宾礼中最为重要的环节,由于飨近于祭,又飨、享兼通,故可以“享礼”统称。 第一,“备物”、“显物”是为“大享之礼”的主要特征,奠定了诗赋体物的基础。《礼记·礼器》云: 大飨,其王事与!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丹、漆、丝、纩、竹、箭,与众共财也。其余无常货,各以其国之所有,则致远物也。(83) 此指天子礼,故曰“王事”,然则古人于此争论甚多,聚焦点在“大飨”究竟是指飨宾还是祭祀。贾公彦疏《周礼》“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一语云:“凡大飨有三:案《礼器》云:‘郊血,大飨腥’,郑云‘大飨,祫祭先王’,一也;彼又云‘大飨尚腶脩’,谓飨诸侯来朝者,二也;《曲礼下》云:‘大飨不问卜’,谓总飨五帝于明堂,三也。”(84)前文已论祭祀、待宾之礼共同起源于饮食之礼,因此大飨兼括祭祀、聘飨而言,其三牲、鱼、腊、笾、豆、金、束帛等,品物繁多,于祭祀言之则是献食与诸侯贡献助祭,于聘礼言之则是款待宾客以及所用庭实,即“飨用备物,以象其德”。(85)《左传·僖公三十年》载: 冬,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歜、白、黑、形盐。辞曰:“国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飨,以象其德。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以献其功。吾何以堪之?”(86) 飨需备物,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国语·周语》载晋侯使随会聘于周,“定王享之,肴烝”,并称“夫王公诸侯之有饫也……饫以显物,宴以合好”,“饫”指享礼,韦昭注曰:“显物,示物备也。”(87)显物、备物,归指一事,范畴约十一项之多,包括体荐、羞牲鱼、腶脩、大羹、白黑形盐、十二牢、五味、鬯礼、嘉谷、加笾豆、庭燎等,与《礼记》“大飨”所致之物相近,涉及地域囊括“四海九州”。享以显物的传统影响到后起的赋体文学,其规模与体制,正可借鉴于对文学批评术语“赋”与文学体式“赋”的“铺陈”与“体物”两大特点加以诠解。 第二,享礼“备物”、“显物”的传统使《诗经》“六义”之“赋”经历了从“献物”到“敷陈”的形成过程,前者为行礼手段,后者为批评方法,其间有着逻辑联系。首先,“六义”之“赋”本为行礼献物的手段,即献上田赋,引申而言,则献诗、献辞皆为“赋”之内容。以《诗》最先出现的《周颂》诸篇为例: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我将》) 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潜》)(88) 朱熹《诗集传》注《我将》“赋也。……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乐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盖不敢必也”;注《潜》“赋也。……《月令》,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季春,‘荐鲔于寝庙’。此其乐歌也”。(89)献神“享赋”之法,陈设备物,当为六义“赋法”之本。 其次,从《诗经》“三颂”所用赋、比、兴的比例来看,作为批评术语的“赋”乃是沿用行礼之“赋法”。据《诗集传》统计,“三颂”中,“赋法”64处,“比法”未见,“兴法”9处。关于“兴”,《周颂·振鹭》1处,“振鹭于飞,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句,本书“赋也”,后附有“或曰兴也”,按其辞应为“赋法”,朱熹所论为是;《鲁颂》中《有駜》、《泮水》各4处。(90)据此,《颂》以“赋法”为主要形式,《周颂》、《商颂》只用“赋”,唯《鲁颂》两诗用“兴”。孔颖达疏《毛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一句说:“王者政有兴废,未尝不祭群神,但政未太平则神无恩力,故太平德洽始报神功,颂诗直述祭祀之状,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报德可知,此解颂者,唯《周颂》耳。……《鲁颂》……如变风之美者耳。”(91)值得注意,《周颂》纯用“赋法”,“赋”与“颂”可合为一,用行“大享之礼”以歌颂功德,祝尧论屈赋“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矣”,(92)汉代“赋”、“颂”二体连称或互代,实渊源有自。 第三,享礼之“备物”、“显物”为散体赋提供题材的同时,其中蕴含的“物有其容”的观念为其从状物“小赋”到骋辞“大赋”的演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最终形成“物以赋显”的理论诉求。《东京赋》言天子行礼的场景曰:“于是备物,物有其容。”(93)“物有其容”出自《左传·昭公九年》,晋国大臣荀盈去世,晋侯饮酒作乐,膳宰屠蒯借行酒国君而劝谏:“又饮外嬖嬖叔曰:‘女为君目,将司明也。服以旌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见。是不明也。’……公说,彻酒。”(94)所谓“服以旌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服饰表示礼仪,礼仪用以行事,而事又有不同的种类,需要相应的仪容来配合。“物”作“类”解,小则品物、形容,大则物类、万象,且“容”、“颂”相通,“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就铺排容饰以尽其貌的特征。分而述之: 战国小赋体现出“物尽其容”的细腻笔法。以《荀子·赋篇》为例,其通过细致的刻画,从而揭示礼、知、云、蚕、箴等五种品物,《文心雕龙·诠赋》以为“荀结隐语,事数自环”,描述事物的高下、大小、品性等特征,最终判断其名称。至于“秦世不文,颇有杂赋”,(95)《汉书·艺文志》“杂赋”类中包括“《隐书》十八篇”,(96)可见“隐语”与小赋关系至为紧密,关键因素在于小赋力争“物尽其容”,与隐语隐去名称、详述其特征的表述相同。 汉代大赋体现出“物尽其类”的宏大气象。冯友兰以为“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97)正与汉赋特征相契,刘熙载《艺概·赋概》强调指出: 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太史公《屈原传》曰:“举类迩而见义远。”《叙传》又曰:“连类以争义。”司马相如《封禅书》曰:“依类托寓。”枚乘《七发》曰:“离辞连类。”皇甫士安叙《三都赋》曰:“触类而长之。”(98) 刘氏此论可谓卓见。其实早在曹丕《答卞兰教》中即云“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99)考诸《七发》之于音乐、美食、车马、览观、游猎、海涛之事穷形尽相,及至《子虚》、《上林》中关于土地、物产描述之包容万有,已足证京都大赋犹如类书的总结性表述。(100)京都大赋之外,专题赋也是如此。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铺排“岿然独存”的灵光殿时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对一宫殿极尽铺写之能事,至如《洞箫赋》、《长笛赋》等音乐赋对乐器原材料生长的环境、制作过程、演奏效果的描述更是达到极致。东汉马融《长笛赋序》称:“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101)仅音乐一门而言,已洋洋大观,足见汉人对事物之“类”有独特的爱好,这也是汉大赋形成的重要条件。 由享需“显物”到“物以赋显”,无论是小赋表现出“物尽其容”的细腻笔法,还是大赋展现出“物尽其类”的宏大气象,均与宾祭之礼的备物、陈辞与明义(象德)相吻合。对照赋体文本,以汉大赋为例,关键正在宾祭礼的物、辞、义三端。 一曰“托物”。汉赋大篇,以博物知类见长,赋家托物而明理,构成其体类特性,这恰与宾祭礼之“赋物”与“赋辞”以享神、享宾相关。如果我们对照周礼祭祀中的贡献(五献或九献等)、聘问中的贡物,并与之相关的“朝贡体系”,再看汉赋中如班固《西都赋》所言“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踰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东都赋》“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张衡《东京赋》所言“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102)就能理解其托物及义描写方式的渊源。 二曰“陈辞”。汉代赋家本领,重在词藻华丽,无论“丽则”或“丽淫”,“丽”之评价在文学批评中的彰显,实缘汉赋尚辞,所谓“赋者,敷陈之称”,这也引起后人“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的批评。(103)对照古礼,无论告庙还是出行,除献物之外即用辞,其间繁杂多重的告诉制度,以反复陈辞为表现形态,这是礼仪所需,也是享神所用,赋家不避陈辞,与此契翕。 三曰“兼义”。汉代宫廷大赋的功用,诚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104)“讽”(刺)、“颂”(美)兼义,是赋家创作心志,而且往往一体化呈现。这一方面可从赋家的创作中清晰看出,例如司马相如“天子游猎之赋”的颂中寓讽,扬雄《甘泉》等“四赋”的讽中兼颂,一方面又可从当时的赋学批评中观其矛盾,所谓“(相如赋)与《诗》之风谏何异?”(105)“赋可以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106)其实,这种创作现象及批评中内涵的矛盾与疑虑,与古礼媚神观德相关。享神是为了得其佑护,亦即“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107)否则就会出现如《尚书·金縢》周公祷祝时威胁“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其媚神、讽神,正合赋家之媚上(君)、讽上,“寓讽于劝”是赋家“昭德”主旨,这又牵涉到宾祭之礼媚神观德与赋家讽劝传统的内在联系。 四、媚神观德:讽劝传统的语境迁迭 从赋体文本出发,前贤对其特殊的修辞艺术颇多关注,如祝尧评述司马相如《子虚赋》时阐论大赋的体制特征云: 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璧綵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壮。(108) 其言“夸”、“媚”、“赡”、“藻”、“壮”,皆缘修辞技巧而呈示的艺术风格,这是汉赋家共通的语言形态。而由“物”联“类”,因“丽”生“媚”,又是赋家描绘的常见手法。究其渊源,此亦与宾祭之礼的“赋物”与“赋辞”相关;推进一步,赋文夸饰,炫色耀采,却多归“曲终奏雅”,旨在讽喻,由此形成的汉赋“讽”、“劝”传统,实源自“大享”用于祭、聘时构成的“媚神”与“观德”的双重功用。 由媚神观德来看享礼与赋体,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享神”时的“媚神”心态是赋体“劝而不止”的宗教根源。“享神”无非是为了获得神灵的护持,《左传·庄公十年》载鲁公认为可以迎战齐国的条件之一便是“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僖公五年》载虞君认为国家可以长存的前提为“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109)以此看汉赋,天子与神灵,分别为人世与天界的尊者,“媚神”与“媚上”,理义相同。这又可分述为两点。 一则是“媚神”的专一性对汉赋一味逢迎君主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祭祀坚持“专祀族神”的原则为汉赋选取了颂德的对象。《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宁武子之言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110)祭则“专祀族神”,与汉大赋歌颂君主同质,都有固定的取悦或讽谏对象。《七发》、《子虚》本是献给诸侯王而作,武宣之后,大赋几乎全为颂德,集中逢迎天子,《上林》所谓“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颂武帝之新政,(111)及至扬雄《甘泉》、《河东》专一赞述成帝祭神求嗣,直可视为献给神祇以歌颂天子的祝辞。因此,祭神的专一性影响到汉赋专一歌颂天子观念的形成,可以作为武帝以后中央集权强盛的注脚。及至东汉,《两都》、《二京》专以帝京为辞,如《东都赋》写“元会礼”,以天子之德为核心。天子主宰人间一切,汉大赋专言天子,犹如祀神,是其发展的必然。其二,影响到汉赋选择君主属地作为铺写题材,这一点与《礼记》“问国君之富”近似,因此《子虚赋》中子虚、乌有分别夸饰楚之大泽、齐之巨海,至于扬雄《蜀都赋》、张衡《南都赋》都是以属地、乡邦为荣,可等同视之。然而《上林》、《两都》、《二京》等俱以京都为辞,需加辨析。《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语“三代命祀,祭不越望”,(112)各因所处之地而祭。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意在使齐楚折服,批评两国“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但又归结于“独不闻天子之上林”(113)以夸饰天子苑囿。究其实,作者虽有以“上林”包揽天下之意,但根本原因在于“上林”乃天子私产,与“祭不越望”同义。《汉书·食货志》载:“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114)汉代设置“少府”一官管理天子私产,山川、池泽均在其中,而上林苑为其辖属,犹如天子汤沐邑。所以《上林赋》没有明言“天下”,而以天子“苑囿”涵括,不过是表明天子私人领地的雄伟、富饶罢了,而若言及天下,犹以天下为“苑囿”,岂非直言天子失德! 一则是“媚神”需要罗列大量供物为汉赋铺排各种物象用以“媚上”提供了方法。《子虚赋》本来献给梁孝王,由于其中物类齐备,“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而拟效故辙的《上林》写就,故“赋奏,天子以为郎”。具体分析汉人以博物“媚上”,基于两种心态:一为充当天子弄臣,西汉多如此。以汉赋最为兴盛的武宣之世而言,由于推行“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的国策,儒学的地位尚且低下,作为文学侍从的赋家更可想而知。武帝时,司马迁《报任安书》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而《汉书》记载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相如与倡优无异,至于东方朔也只能“应谐似优”自保,因此“上颇俳优畜之”。(115)二是赋显才学,东汉应作如是观。西汉末年扬雄“悔赋”,根本原因在于经过元、成之世,天子好儒,一改祖宗之法,纯任儒生,儒家学说的地位得以大幅提高,汉赋娱乐的本质为论者所发掘,因此被排斥。班固的《两都赋》为赋体正名,宣示“赋者,古诗之流”,从诗史的角度重构汉赋与《诗经》的关系,以致其《两都赋》以“五德终始学说”夸饰两都景象,衡裁前后汉之高下,张衡《二京赋》,更以《月令》之学充斥其中。如此将各种物象囊括进学术背景之中,根本原因在于班、张皆为一时大儒,作赋犹如治学,是对“媚神”之劝的反思和对“观德”之讽的阐扬。 第二,“享宾”时的“观德”意识是赋体“寓讽于劝”的内在要求。《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夫享,所以昭德也”,以揭示享礼本质。《成公十二年》:“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此为正面论述“享”的意义,主旨在训俭、布政。而对行享礼中的失礼行为则多批判,如《成公十四年》载“卫侯飨苦成叔……苦成叔傲”,宁惠子批评说:“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116)“傲”为享礼之恶态,亦“取祸之道”,这从反面证成“观威仪、省祸福”是“享宾”之礼的重要目的。缘此,以汉大赋为代表的赋体文本,以两汉为界线,形成两大阶段,或谓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以西汉赋为主,重在“省祸福”,主题为“训诫”、“改作”。 枚乘《七发》批判楚太子奢靡的生活,最终使之归于有道,“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117)侧重献赋对象的主观觉悟,而不是直接否定,扬、马呈天子之大赋多循此法,与西汉赋家的“弄臣”处境契合。这又主要表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专写天子大而不当的行为。《七发》不过将各种事项陈列,供楚太子选择,但在司马相如笔下,则直接将天子写入赋中,成为主角,扬雄赋亦然。如《上林赋》写幅员之大、品物之多、游猎之盛,扬雄《甘泉赋》、《河东赋》写出行之盛、祭祀之诚,皆以非常态论之。如写上林苑的范围,“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上林赋》),汉成帝车骑的豪奢,“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而翳华芝,驷苍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绥,漓乎襂纚”(《甘泉赋》),(118)俱非现实中所见,此乃赋家采用的一种“变态”手法,将天子的“傲”展现出来,寄托讽义。这也正如扬雄所论:“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119) 二是主动表现天子的自我省悟。西汉大赋往往以天子“省悟”作结,犹如一幕自编自演的戏剧。如《上林赋》在描写各种活动之后:“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据史书载,相如作《上林赋》本为继《子虚》而为天子提供新的娱乐材料,但正因渊承“享宾”之礼的内在要求,不自觉地在文末加上一个尾巴,曲终奏雅,归于正则。至于扬雄的《甘泉赋》大肆铺写祭祀求子的非常态过程后,“于是事毕功弘,回车而归,度三峦兮偈棠黎。天阃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登长平兮雷鼓磕,天声起兮勇士厉。云飞扬兮雨滂沛,于胥德兮丽万世”,无中生有,歌颂成帝“求子”行为带来的万国和谐、扬德万世的功绩,成为“观德”的代言与变化。 另一模式以东汉赋为主,归于“观威仪”,主题为“昭德”、“宣威”。 西汉赋作固然有颂德的成分,但比重较轻,直至西汉末年扬雄《长杨赋》才确定纯一颂德的体式,直接改变了汉赋的写作手法,对东汉赋体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原因有二。 一是更换题材。东汉大赋如《两都》、《二京》,分述两京的政治形态,然“西”为“宾”而“东”为“主”,其如《西都赋》中“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与《西京赋》中“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独俭啬以龌龊”的叙述,犹如愚人自炫,拥有一般常识者均可识其败德。而《东都》、《东京》则完全改变西汉赋作夸饰物产、游猎的描写手法,罗列历代君主的德行,铺写他们的功劳与善政,使得在西汉赋作中的附庸演为大国,颂扬君主的功德,成为东汉赋作的主旨。 二是因礼宣威。班固《东都赋》所述光武帝、明帝之德,归乎“制礼”,其中内涵现实施行的礼仪,也包括了国家践行的制度。及至张衡《东京赋》主旨尤明,其对明帝时朝觐礼的描写,意在宣扬大汉帝国四海臣服、万邦来朝的盛况,试观天子出场时的肃穆、雄壮: 是时称警跸已,下雕辇于东厢。冠通天,佩玉玺,纡皇组,要干将。负斧扆,次席纷纯,左右玉几而南面以听矣。然后百辟乃入,司仪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贽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礼礼之。穆穆焉,皇皇焉,济济焉,将将焉,信天下之壮观也。(120) 因礼仪制度而彰显汉家威仪,与周天子朝享诸侯之礼相同,其实质又回归我们所强调的“享礼”,于中可见东汉“物以赋显”的观念,也是“礼以赋显”的表达。当然,通过对礼制、威仪的宣扬,除去颂德的成分,赋家是希望读者能够对礼仪纲常存有服畏之心,达到因讽而规正统治者行为之目的。 在我国文体史上,赋最具有包容性。就其内涵看,赋或“抒下情”,或“颂上德”;就其性质看,或“体物”,或“言志”;就其风格看,或为典雅之章,或为俚俗之篇;就其形态看,或“鸿裁”,或“小制”,鸿裁则“体国经野”,小制则“随物赋形”,诸多不一。如就语言特征划分赋体,古代又有“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律体赋”、“文体赋”等等,也因时而变,应运而生。然探究其源,明辨其本,又当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待体制的成型与艺术的地位,这就是以汉大赋为代表的“一代之文学”。(121) 针对赋体文本的批评,古人说法亦多,然论其要,宜观汉人的自评,其中尤以“讽谏说”与“丽则说”值得关注。前说见史迁评相如赋,所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相如列传》);(122)后说见扬雄《法言·吾子》,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23)二者皆指向于《诗》,即似是而非的“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因为汉人论赋倡导“讽谏”,对应的是“虚辞滥说”,论“诗人赋”之“则”,对应的是“辞人赋”之“淫”,在此对待关系间,隐含的恰是赋体最突出的词章与教化之矛盾,溯源而论,亦即宾祭执礼过程中媚神观德的思想原生态。对此,还可从先秦典籍中论“文辞”之用得到印证,如《国语·周语》记载单襄公对其子顷公曰:“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124)又《礼记·曲礼上》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125)二说论文及辞的起源,皆主“敬”,并归于“礼”,实与宾祭所内涵“宗庙事”与“礼仪性”相契合,本文中所讨论的“献赋”、“执礼”、“显物”以及“媚神观德”所推导出的讽劝传统,又喻示了文辞之娱戏与教化的关系。而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有名姓之文士的辞赋家创制的认知,包括对赋体文学名称、结构、质性、功用的考源,不仅可以打破“赋者,古诗之流”的误解,以厘清由“赋”之本义到“赋诗”、“赋体”的线索,而且对整个中国学术(包括文学)源起“宗庙”或“王官”的争议,也能提供一新的思路。 注释: ①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5、672页。 ②费经虞注,费密补:《雅伦》,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97册,第63页。 ③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6页。 ④袁栋:《书隐丛说》卷11,清乾隆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37册,第545页。 ⑤刘师培:《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26页。 ⑥许结:《从“行人之官”看赋之源起暨外交文化内涵》,收入氏著:《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5—78页。 ⑦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4页。 ⑧郝懿行:《尔雅义疏》,《汉小学四种》(下),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影印本,第999页。 ⑨王念孙:《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1页。 ⑩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4页。 (11)《汉书》卷44《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45页。 (12)王念孙:《读书杂志》(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58页。 (13)裘锡圭:《神乌傅(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 (14)《汉书》卷1《高帝纪》,第37—38页。 (1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经韵楼刻本,第282页。 (16)《尚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6页。 (17)《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35、1986页。 (18)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之《豫部第九》,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220册,第493页。 (19)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18,清同治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209册,第542页。 (20)《礼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84、1258页。 (21)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21页。 (22)《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67、1795页。 (23)吴毓江校注:《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8页。 (24)《礼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15页。 (25)杨宽:《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页。 (26)许维遹:《飨礼考》,《清华学报》1947年第14卷第1期。 (27)《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33页。 (28)《论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02页。 (2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23页。 (30)易祓:《周官总义》卷13,《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2册,第434页。 (31)朱申:《周礼句解》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册,第172页。 (32)《周礼》,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90—791页。 (33)《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47页。 (34)刘雨:《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35)胡安国:《春秋传》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1册,第61页。 (36)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69页。 (37)《仪礼》,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051页。 (38)《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86页。 (39)《汉书》卷48《贾谊传》、卷28《地理志》,第2222、1668页。 (40)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页。 (41)《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第2491页。 (42)《汉书》卷87《扬雄传》,第3583页。 (43)《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2999页。 (44)《汉书》卷64《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829页。 (45)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刘师培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97页。 (46)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65—66页。 (47)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48)郑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84、1980页。 (49)皮锡瑞:《郑志疏证》,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1册,第311页。 (50)《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55页。 (51)《毛诗》,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16页。 (52)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53)《礼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89、1604、1607、1614页。 (54)《汉书》卷64《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829页。 (5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4页。 (56)《尚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5—196页。 (57)《礼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16页。 (58)许维遹:《飨礼考》,《清华学报》1947年第14卷第1期。 (59)《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16、1995、2021页。 (60)徐元诰:《国语集解》,第338—339页。 (61)刘雨:《金文论集》,第68—69页。 (62)《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 (63)《周礼》,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9页。 (64)《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3、1851、1743页。 (65)《礼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89—1390页。 (66)《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47、1851页。 (6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8页。 (68)《尚书·伊训》:“伊尹祠于先王”,陆德明《经典释文》:“祠音辞,祭也。”(《尚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2页) (69)详见蒋晓光:《交聘之礼与〈七发〉的章法及承传》,《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1期。 (70)详见蒋晓光、许结:《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71)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478、119页。 (72)《汉书》卷27《五行志》,第1319页。 (73)《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32、2035页。 (74)《汉书》卷87《扬雄传》,第3541页。 (75)萧统:《文选》,第136、32、62页。 (76)《礼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68页。 (77)萧统:《文选》,第119—120页。 (78)刘师培:《论文杂记》,第116页。 (79)《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40页。 (80)《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55页。 (81)《陆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8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4—135页。 (83)《礼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42页。 (84)《周礼》,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91页。 (85)许维遹:《飨礼考》,《清华学报》1947年第14卷第1期。 (86)《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31页。 (87)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7—59页。 (88)《毛诗》,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8、595页。 (89)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25、230页。 (90)朱熹:《诗集传》,第228、238—240页。 (91)《毛诗》,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2页。 (92)祝尧:《古赋辩体》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718页。 (93)萧统:《文选》,第61页。 (94)《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57—2058页。 (9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35、134页。 (96)《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53页。 (9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 (98)刘熙载:《艺概》,第99页。 (99)《三国志》卷5《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58页。 (100)袁枚《历代赋话序》曰:“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浦铣撰,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页) (101)萧统:《文选》,第168、249页。 (102)萧统:《文选》,第24、33、64页。 (103)挚虞:《文章流别论》,引自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905页。 (104)萧统:《文选》,第21页。 (105)《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73页。 (106)扬雄著,汪荣宝义疏:《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页。 (107)《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5页。 (108)祝尧:《古赋辩体》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750页。 (109)《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67、1795页。 (110)《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32页。 (111)萧统:《文选》,第129页。 (112)《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62页。 (113)萧统:《文选》,第123页。 (114)《汉书》卷24《食货志》,第1127页。 (115)《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卷9《元帝纪》、卷62《司马迁传》、卷22《礼乐志》、卷65《东方朔传》、卷64《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533、2575、277、2732、1045、2873、2775页。 (116)《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48、1910、1913页。 (117)萧统:《文选》,第484页。 (118)萧统:《文选》,第123、112页。 (119)《汉书》卷87《扬雄传》,第3575页。 (120)以上赋文见萧统:《文选》,第129、115、23、50、57页。 (12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22)《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73页。 (123)扬雄著,汪荣宝义疏:《法言义疏》,第49页。 (124)徐元诰:《国语集解》,第88—89页。 (125)《礼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29—1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