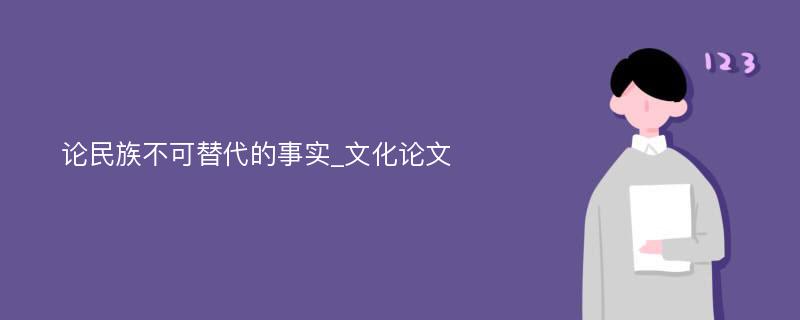
论族群不能取代民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5-0025-05
族群理论是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研究的新兴理论,这一理论的兴盛,是与当代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分不开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使世界上不同的人群同居一处,或不同的群体频繁交往,构成复杂、多元的社会与文化。在这种复杂多元的格局下面,群体内部成员的相互适应、群体之间的外部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处理、推动、观察、剖析群体内部适应、外部协调?族群理论应运而生。
族群理论涉及面较广,主要内容包括:族群的定义,族群性,族群认同,族群的结构、符号与象征系统,族群文化诸要素,族群与边界,族群关系理论等等。族群理论的引人中国,较早应是在台湾。20世纪60年代后,我国台湾的人类学者首先运用族群理论分析岛内不同群体和海外华人社会。进入90年代以来,港、台人类学者的分析方法渐为大陆学者所熟悉和借鉴,族群理论也随之在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界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更多的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开始运用族群理论来研究、剖析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给理论相对单调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吹进许多新鲜空气,开拓了思路、开阔了眼界、创新了观念,应当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族群理论推动了并且将继续推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这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族群理论作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研究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归纳,在具体运用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时,并非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其中,对“族群”与“民族”这两个人类学、民族学基本核心概念关系的认定,就集中体现出这种现实。近几年来,国内一些族群理论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民族”概念主要是一种政治概念,并不具有太大的科学性,应当以族群理论中的“族群”概念取代“民族”。这种观点在族群理论研究中,似乎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观点。但事实上,由此而引起许多概念上的混淆、矛盾,其本身并不能自圆其说,因而,也遭到许多同行的异议与质疑。
这种观点从英语词汇nation,nationality与ethnic group汉文翻译上的不同以及其英文含义本身的差异出发,认为“民族”(nation)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具有国家或民族的双重含义,且国家层面的含义应用更广泛,多指“国民国家”;而“族群”(ethnic group)才是我们通常理解层面的民族。中国学者为了避免“国民国家”的含义,常用nationality而不用nation表示民族,其实nationality的准确含义是“国籍”,用反映主权特征的nationality一词来套用我国没有主权意识的少数民族,本身就不确切。在汉译英的情境中,用nationality来对译同为56个族体的“民族”概念,以示与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之“民族”与56个民族之“民族”的概念差异,但nation和nationality词根相同,含义相近,根本无法反映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民族”概念的层次差异。同时nationality所含的国家、国籍意义极易造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误读和误解。因为以上以及类似的一些原因,这些研究者认为,具体在中国,“民族”概念应主要是指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而国内的56个民族以及其下的各个支系,应称作“族群”(ethnic group)。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民族”是一个泛义的政治概念,而“族群”(ethnic group)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而主张用“族群”一词取代“民族”一词。并且认为,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发展,“族群”一词在学术界的使用越来越多,有取代“民族”之势。[1]
如有的论者提出,“族群一词的流行主要在人类学界,……新时期的人类学正是高扬‘文化’或‘社区’研究的旗帜而从旧民族研究阵地里脱离出来的,当然宁愿把‘Ethnic group’译为‘族群’。实际上,多数使用族群概念的学者都强调‘族群’的文化性和‘民族’的政治性,强调使用‘族群’一词的较自由和宽泛的学术取向。因此,族群一词的流行也反映着学术界对传统民族概念的反思和解构。”[2]
本文认为,以“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要讨论“族群”和“民族”的关系,涉及到这两个概念尤其是英文“ethnic”、“ethnic group”、“nation”、“nationality”等词汇及其含义的生成、传承和变异,这方面,学者们已经作了颇为详尽的研究论述,此不赘述。[3]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从中文对“族群”、“民族”含义的理解切入,以另一种思维模式来探讨“族群”与“民族”的关系,质疑“族群”取代“民族”的主张。
一、以“族群”取代“民族”引起了概念与认定上的混淆与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因而,缺乏科学的严谨性
按“取代论”者之说,只有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或中国人(在与外国互动时)才能称为“民族”,而国内56个民族均应称为“族群”,同时还认为每个民族的支系也应称为“族群”。事实上,中华民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的概念,按照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定性,中华民族是文化上的多元,政治上的一体。如果按照学术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恐怕还不在其中。而把国内56个民族与其属下的各支系均以“族群”一词概之,则显然自相矛盾,概念混淆,因为外在民族与其内在支系的关系,是主体与构成要件的关系,主体的民族特征体现于支系构件之中,众支系特征综而合之,才呈现出民族总体的外在特征与族性。就像人作为主体是由五官四肢构成,但不能将构成人的五官四肢与表现外在的人一并称为人一样,将民族内部的支系与民族本身一并称为族群,明显存在概念上的混淆与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尽管论者试图以族群层次的理论澄清上述混淆与矛盾,但显然这种辩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至于主张以族群概念全面取代民族概念的说法,其自相矛盾之处似乎更为显然。中华民族是“族群”,56个民族也是“族群”,各民族支系仍是“族群”,这种理论模式尽管有族群概念层次作为域定,其非严谨性仍然是十分抢眼的。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所能给予人们在使用不同概念(即便是层次上的不同概念)时所可选择的词汇远不至如此贫乏。民族与支系两个词原本就十分贴切地表述了个中关系的内涵,犯不着因为英文翻译上的烦恼而生出许多自扰。有些研究者提出“上位民族”与“下位民族”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可称为“上位民族”,而56个民族则属于“下位民族”,[4]这种观点仿佛与“上位族群”(中华民族)、“下位族群”(56个民族)似曾相识,本身也是上述族群观的一种表现。
二、从“族群”与“民族”的概念界定上看,以“族群”取代“民族”并无科学根据
族群(ethnic group)一词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开始使用,用来描述西方社会中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二战以后,族群(ethnic group)一词被用来取代英国人的“部族”(tribe)和“种族”(Race),运用更加广泛。国外有关族群的概念众说纷纭,如:
族群(ethnic group)意指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尤其是共享同一语言,并且文化和语言都能相对保存并代代传承下去。
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在同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的、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质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5]
社会学家马科斯·韦纳的定义认为: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因体质的或者习俗的或者对殖民化以及移民的记忆认同的相似,而对共同的血统拥有主观信仰的群体。这种信仰对亲属的共同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6]
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的定义为:族群(ethnic group)是指一群人或自成一部分,或是从其他群体分离而成,他们与其他共存的、或交往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区分的特征可以是语言的、种族的和文化的;族群(ethnic group)这一概念包含着这些群体的交互关系和认同的社会过程。[7]
国内对于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界定,以吴泽霖先生主编的《人类学词典》的定义最具权威和影响:族群(ethnic group)是由民族和种族自己集聚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限在其成员上是无意识的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同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聚居。因此,族群是个含义极广的概念,它可以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居民中的不同文化的社会集团。族群(ethnic group)概念就这样综合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8]这一定义更易为中国民族学界所理解与认可,也符合至今仍热烈讨论中的族群概念界定的发展趋势。
随着族群研究的深入,关于族群的界定逐渐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传统上关于族群的认定主要强调的是共同的起源、文化的话,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族群的认定上,强调更多的是共同的现实利益,即将共同的现实利益视为族群形成的主要动因和边界。在这一界定之下,族群可以是短期内形成、产生的,可以是随时变动不拘的,甚至可以是主观要求加入或选择加入的。族群的层次性、变动性等特点也显得十分突出。比如,族群认同的情景论者会认为,一个在香港的上海人,可能自称上海人、香港人、汉人、中国人,每一个自称都让他与一群人结成一个族群;一个人可以通过结婚、改名、改变宗教等方式,从一个族群转向另一个族群;有学者指出,在澳门,1999年后随着澳门和内地经济、政治的整合,文化的涵化,澳门将会出现一个产生于不同族群基础上的新的“澳门族群”等等。[9]
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于民族的界定,原则上仍遵循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0]尽管近20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提出这样那样的补充、完善或发展,但应当承认,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对民族概念科学定义的认可仍然是奉此为圭臬的,其核心内容仍然是人们认识民族、研究民族的基本准则。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人们认识斯大林民族定义儿乎把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四个共同点上,而忽视了其他两个其实也同样重要的民族构成要素,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笔者认为,如果没有这两个要素与四个共同点相呼应,同样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意义上的科学的“民族”。如果说四个共同点主要是表现于“民族”外在特征的话,那么“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其实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民族”的内在本质。
比较上述各种有关族群的(ethnic group)定义,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定义都是从群体外部的共同特征出发的,即强调语言、种族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却根本未涉及到“历史形成”和“稳定的共同体”这两个重要涵义。如果说语言、种族、文化等特征是族群(ethnic group)和民族都有的特征的话,那么“历史形成”和“稳定的共同体”这两个民族所具有的本质内涵,则是族群(ethnic group)所没有或非必备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族群”(ethnic group)是与“民族”有着重大的区别甚至本质的区别的。以“族群”取代“民族”是不科学的。
其实,在中文的理解中,我们可以把族群界定在与民族截然不同的层面上。按照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通常的用法,族群一词的本质含义主要是指以现实利益为基础、以共同文化为边界的人们群体,它与上述民族的概念明显有着根本的区别。明确族群的这一内涵,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它与民族本不应有的纠缠。我们相信,只要研究者们不主观地、甚至有所偏爱地将两个概念随意互换,混为一谈,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应当是很清晰的。
三、从“族群”与“民族”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上看,也不存在以“族群”取代“民族”的前提
族群与民族虽然都可指代人们共同体或人类群体,但侧重点不同。族群强调的是“群”,重心在“群”;而民族强调的是“族”,重心在“族”。“群”更多的时候是利益共同体,它特别强调即时性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可使人们结成各种各样的族群;而历史的血脉、对共同历史的认同与记忆则是“族”永恒的纽带。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演化而来,血脉相承,一以贯之,它是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历史的范畴。有学者指出,民族是历史结构的产物,而族群是利益互动的“宠儿”,可谓一语中的。“族”可以是“群”,而“群”断不能等同于族,甚至难以与族相提并论。
正因为“族”与“群”的差别,在中国,以族群取代民族会扼杀民族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即它的历史性和稳定性。中国民族大都源远流长,包括大部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有着同样悠久的数千年历史,中国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沉淀,而族群可以是在近十几年甚至近几年来形成出现的,以这种“族群”与数千年沉淀而成的古老“民族”相提并论,甚至以“族群”的名称取而代之,“取代之说”的捉襟见肘显而易见。所谓族群层次化也是无论如何都难以跨越这般深厚的历史鸿沟的。
从族群与民族所涵盖的范围上论,族群范围似乎要比民族范围更大,伸缩更机动。如上述所言,“它可以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居民中的不同文化的社会集团”。族群可以是在民族内部,也可以是跨越民族界限存在于多个民族个体之间,而民族内部不可能有民族,民族之间也界限分明。在当今市场经济化的社会里,民族的个体可能没有民族意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不会也没有必要时刻在脑子里绷着一根“民族”之弦),但可以有族群意识。然而,这些都并不构成族群取代民族的理由。相反,正因为这样一些差别,才显示出两者间的不可替代。同时,并不能因为民族个体在特定情境中没有民族意识而否定民族的存在,突显族群的现实。可以预见的事实是,一旦族群意识与民族意识在脱离特定情境的状况下正面交锋,民族意识无疑是会战胜族群意识的。族群边界在一定的条件与环境中确实可以无视民族的边界,但绝不会否定或完全取代民族的边界。相反,从历史的视角审视,民族边界绝对可以否定、抹杀族群的边界。
族群交流通常以在民族内部的交流最为常见,当不同民族间的族群交流发生时,往往表现为民族交流。从这个层面上看,民族交流大于族群交流,民族又可大于族群,族群不可能大规模地形成于不同民族之间。
四、从族群取代民族论的“动因”分析,其初始“动因”恐怕源自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与英文nation、nationality等词汇的国际接轨上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将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即可指国内56个民族,也可指中华民族即整体中国人)与相应的英文词汇nation、nationality对译或对应,则会产生误读或误解,因为中国国内56个所谓民族并不具有nationality所含的“国籍性”,因而主张将民族与族群分开或仅用一个族群概念同时分出族群层次。同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包括56个民族的认定也是政治上的考虑。对于此类“取代动因”,如果只是考虑为了与英文词汇的国际接轨,或出于担心国际误读,其实大可不必勉强中国传统民族概念令其委曲求全,因为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其含义本来就是十分丰富,即便是形式上与nation,nationality们接了轨,也未见得nation,nationlity能真正反映中国民族概念的全义。而指中国民族概念为政治概念之说,应当承认的是,即便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民族认定的确有出于政治的动因,但整个中国民族的认定过程以及随后数十年对民族的研究所赋予民族的各种涵义,绝对是科学的,而不是政治的。
在中文词汇里,“民族”(民族一词来源于西方,但在中国已被赋予了中国特有的含义)与“国家”本来是两个界限分明、清晰可辨的概念,在族群理论引入之前,很少有人会将它们混为一谈。如今一些学者在这两个概念上模棱两可、是非难辨,仿佛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一夜之间变成了非此即彼、亦此亦彼、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实说到底,不过是受到英文nation,nationality的困惑。英文的nation,nationality其本义既有中文所谓的“民族”的含义,也有中文所谓的“国家”的含义。在中英互译对接的过程中,这些研究者在两组词汇的对应上颇感棘手,难以取舍,于是反过来质疑中文“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最终舍中文而就英文,即将“民族”以所谓“族群”(ethnic group)取代,而以“国家”对应英文的nation,nationality。笔者认为,英文中的nation,nationality既可当“民族”又可当“国家”,处在英文语境中及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本身是没有争议、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国家大多是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与此相反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民族”与“国家”显然是不能等同的。“国家”是统一的“国家”,在“国家”的框架内,在中国大地上,生息繁衍着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的“民族”。中文语境中的“民族”和“国家”概念从来就是很清楚的,我们总不能仅仅因为中英对应翻译的需要,而混淆我们本来十分清楚的中文概念吧。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中文“民族”一词特有的含义并无合适的西文词汇与此相对应,所以才有人建议在中西翻译中干脆用汉语拼音“Minzu”来指代中文的“民族”。基于此,那些因困惑于中英“民族”、“国家”概念对译而主张以“族群”(ethnic group)取代“民族”的观点,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综合上述,在当代族群理论中,族群更多的是以现实的利益为纽带,是基于现实利益基础上的利益认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共同的历史为纽带,是基于历史基础上的文化认同体。也正因为此,族群具有极强的可变性,可变性是其重要特征;而民族则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具有极强的稳定性,稳定性是其重要特征。族群突出的是利益的现实,而民族突出的是历史的传统。民族可以是有主权意识的国家,但不等同于国家,世界上民族的数量远远多于国家就是明证。国家可以通过人为的因素来组织,族群可以通过人为的推动来整合,而民族则永远不可能基于人的意志来拼凑。族群不能等同于民族,不能与民族互换,更谈不上取代民族。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以族群理论中的族群概念取代中国传统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概念,是大可商榷的。当然,学术研究贵在争鸣,任何学术研究不应预设政治功利的前提,关于族群与民族二者关系的探讨还应继续深入下去。族群理论给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引入了新思维、新视角,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在族群理论进一步研究过程中,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与个案实证的结合,在个案实证研究中检验和发展族群理论,应是今后族群理论研究的一个方向。
收稿日期:2004-07-20
标签: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民族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民族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人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