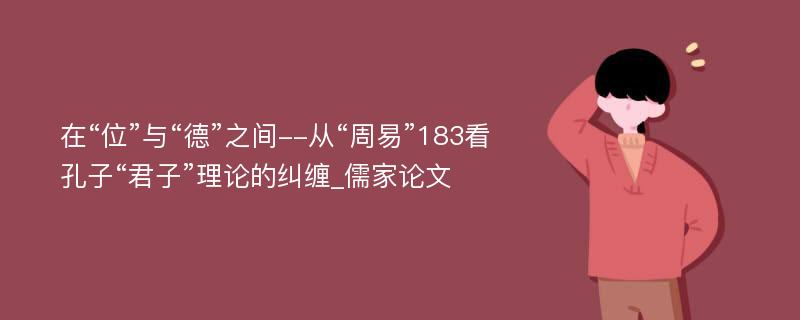
“位”与“德”之间——从《周易#183;解卦》看孔子“君子小人”说的纠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孔子论文,君子论文,小人论文,解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221;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2)01-0010-10
“君子小人”说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论语》中,“君子”有107见,“小人”有24见,“君子”与“小人”同时对举者则有19见。何谓“君子”,何谓“小人”?杨伯峻先生指出:“《论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①。那么,反过来能不能说,《论语》中的“小人”,是否也是“有时指‘无德者’,有时指‘无位者’”呢?如果是这样,孔子为什么有时候用“德”来区分君子与小人,有时候又用“位”来区分君子与小人呢?这样的区分逻辑是从哪里来的,它对我们理解孔子“君子小人”说的真实含义又有什么启发呢?从《周易·解卦》的解读中,我们可以解开这些谜团。
一、以位为别:《周易·解卦》中的“君子小人”
“解卦”是《易经》的第四十卦,其经文为:“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初六:无咎。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其中的六五爻:“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周振甫先生译为:“贵族把他(按下文,指“战俘”——引者注)捆绑了又解开,吉。俘虏成为奴隶。”②这里将此爻辞中的“孚”字解为“俘获”、“战俘”似不妥。尽管“孚”字确有一义是“俘”的古字;但《易经》本身就有“中孚”卦,《易传·杂卦》指出:“中孚,信也。”徐锴解释道:“鸟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因此在这里将“孚”字解为“诚信”、“信服”应更为妥当。如此,这句爻辞应解读为:君子能够解困纾难,获致吉祥,以诚信之德感化小人。至于周先生在这里将“君子”解读为“贵族”、“小人”解读为“奴隶”,虽然其内涵稍嫌窄化,但从社会地位的角度将君子小人二者区别开来,其思路还是可取的。
其实“解卦”经文本身就包含着理解君子与小人内涵的钥匙。这就是六三爻:“负且乘,致寇至,贞吝。”其大意是:背负重物而乘车,招致寇盗来抢夺,占问有艰难。为什么一个人背着东西乘车,就要遭到强盗的抢夺呢?关键是这个人的身份引起强盗的注意。在经济不发达、财富不丰富而又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本来只有贵族才有乘车的资格和能力,孔子就说过:“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下引《论语》,仅注篇名);而贵族“四体不勤”,背负重物这样的工作应该是不会干的。在这种生活背景下,如果在道路上突然看见一个人背负重物乘车,那就必然让人产生怀疑:此人非偷即盗,财产(包括车和物)来路不正;这样,引发强盗的争夺之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这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易传·系辞上》引用孔子的话做了回答:“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在这段话的前半段,孔子解释了《易经·解卦》六三爻所述“负且乘,致寇至”的原因:背负重物,这是小人做的事情;车乘,则是君子使用的器具。自身是小人的身份却要使用君子的器具,当然就会引发盗寇想来抢夺他了。按照这一解释,所谓“君子”显然就是属于统治者的贵族阶层;“小人”则属于被统治者的平民百姓。
孔子这种理解应当说是延续了君子小人概念的原始内涵。按“君子”一词,由“君”与“子”两个单字组成。“君”从“尹”从“口”,本义为发号施令的统治者;“子”则泛指后代,包括儿子、子女和子孙等。“君子”即为“君”的后代——这里的“君”,包括天子、国君即诸侯、家君即大夫等,其子孙繁衍生息,即形成一个庞大的“君子阶层”。而在当时的宗法血缘社会里,“君”即统治者的后代生来就具有进入统治阶层的资格,所以“君子”就成为当时社会统治阶层成员的通称。“君子”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故又称“大人”,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小人”。“小人”又称“野人”、“鄙人”、“庶人”,本指众多在城外田野上劳作之人,他们的职责是通过赋税徭役等形式,为住在城里的君子阶层成员提供生活上的保障③。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又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同上)由此可见,所谓“君子”就是“大人”,他们是“劳心者”、“治人者”,属于统治阶层;“小人”就是“野人”,他们是“劳力者”、“治于人者”,属于被统治阶层。总之,“君子”居于上位,“小人”居于下位,这应该就是“君子”与“小人”最原初的含义。
征诸经典,春秋时期及之前(即所谓“六经”所反映的时代),人们对于“君子”与“小人”的理解,基本上都是着眼于其地位上的区别。试举几例:《尚书·周书·无逸》谓:“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这里的“君子”指安逸享乐的统治者,“小人”则指从事稼穑生产的老百姓。《诗经·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里的“君子”指阔步走在大路上的贵族,“小人”则指站在一旁观看的民众。《左传·襄公十三年》:“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这里的“君子”指尊重贤能的管理者,“小人”则指努力侍奉上级的被管理者。由此看来,从地位的角度区分“君子”与“小人”,前者是上位者,后者是下位者,——这是包括《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在内的那个时代的共识。
但是,起码从《易传》开始,对“君子”与“小人”的这种划分就开始有了一点变化。还是回到《周易·解卦》,其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之后,即有:“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这里的《象传》作者对“负且乘,致寇至”这一事件作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丑”。在他看来,“负且乘”者拥有了(甚至可能是掠夺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丑陋的;而由于他自身的无德窃位,所遭受的强盗抢夺的“兵戎之灾”,只能是咎由自取,又怎么能够责怪他人呢?
由此出发,孔子在《易传·系辞上》中也对这一事实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在孔子看来,居于上位的君子惰慢懈怠而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使得居于下位的小人乘机犯上作乱,盗寇就会思谋侵伐他们了。孔子还进一步发挥道:轻忽于收藏财物就是教人为盗,妖冶其容貌就是教人淫荡。《易经》所说的“负且乘,致寇至”,盗贼就是这样招来的啊!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易传》的作者包括引文中的孔子在内,都对“负且乘,致寇至”这个事件做出了道德上的评判,但他们都无意也没有改变从地位角度划分君子小人的时代共识;相反,《易传》中的孔子在用君子小人的概念解释这一事件的同时,在道德评判中还特意以“上慢下暴”这种明确的地位区分的语言,来批评造成这一事件的上下关联者即君子与小人,而不是如《象传》作者那样,仅仅是一味地谴责和嘲笑小人。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理解《论语》中孔子的君子小人说,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位德纠结:《论语》中的“君子小人”
孔子自称“从大夫之后”,本身就是“君子阶层”中的一员;但与其他君子阶层成员不同的是,孔子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及其引起的君子阶层的危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当时君子阶层中的许多人,只沉醉于物质生活的享受,不培养品德,不讲求学问。听到义在那里,却不能亲身实践,有缺点又不改正,如此等等,这正是孔子所感到忧虑的地方。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孔子的应对之方是从教育入手,收徒办学,以培养一批“德位一致”的新型君子。但令人尴尬的是,那些天生具有“君子”资格的贵族子弟们,一开始对孔子的这个“君子学校”看来是不买账的,于是才出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先进》)的现象。这里透露出一个历史事实:在孔子办学初期,跟从他学习的实际上是那些并没有天生具备“君子”地位的“野人”(即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只是到了后来,孔子名气大了,那些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贵族子弟们,才投到孔子的门下。而孔子本人则秉持“有教无类”的原则,来者不拒,“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那么,这样的学校教什么呢?孔子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因此,当他的学生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回答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门以后,孔子评论道:樊须真是个“小人”!在上位者重视礼制,民众就不会不敬上;在上位者重视道义,民众就不会不服从;在上位者重视诚信,民众就不会不动真情。如果是这样,那么四方的民众都会背着子女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这段话表明,孔子办学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培养真正的“君子”而不是培养“小人”。不管你的“出身”是“君子”还是“小人”,进入这所学校,就是学习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君子”。这样,孔子就给自己设定了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让那些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有其位者有其德”;另一方面,又要让那些天生没有君子地位的人进入“君子”的行列,“有其德者有其位”。这种双向的努力,造成了《论语》中“君子小人”说的纠结。
在《论语》中,以“君子”与“小人”同时对举者,共有19处。其中,明确指向地位差异的有四处:1.“君子怀德,小人怀土。”(《里仁》)2.“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同上)3.“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4.“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明确指向品德差异的也有四处:1.“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2.“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3.“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4.“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对这些较为明确的“君子小人”所指,在此暂且存而不论。
比较复杂的,是其中的11则以“君子”与“小人”对举者,自汉唐至宋元明清,历代注家中,既有以地位差异作解的,也有以品德差异作解的,莫衷一是,使得《论语》中“君子小人”说的纠结更加纠缠不清。其实,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决定道德。如果我们从地位差异出发,去探寻不同阶层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差异,对于我们梳理其中的纠结,应该是有帮助的。
这11则的“君子”与“小人”对举,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况:地位所带来的眼界差异(4则)、地位所导致的能力差异(4则)、地位所引起的修养差异(2则)。以下分而论之。另一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则在本文第三节专门解析。
关于地位所带来的眼界差异,指的是君子与小人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接触的对象不同,认识上的差异造成了二者眼界上的差别。比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尚书·盘庚上》云:“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所谓“天命”是当时统治者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信仰的根源,行事的依据。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作为统治阶层成员的君子们,对于“天命”,当然应该耳熟能详,并且能够敬慎遵从,进而对体现天命的“大人”、“圣人”敬畏崇拜了。而“小人”们是被统治者,根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统治者的“天命”究竟为何物,“无知而无畏”,有“冒犯”所谓“大人”和“圣人”之事,也就毫不奇怪了。
孔子曾经告诫弟子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这里以“君子”与“小人”地位的高低,分别出了两类儒者的眼界。孔子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是领导者,他一定要广泛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而小人是执行者,服从命令听指挥就是统治者希望他们谨守的本分。孔子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居于社会的上层,考虑的是国家的大事,见多识广,因而胸怀宽广;而小人居于社会的底层,整天为个人的生存和家庭的温饱而奔波劳累,其忧愁不是很正常的吗?
关于地位所导致的能力差异,指的是君子与小人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工作的岗位不同,职责上的差异导致了能力上的差别。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君子是国家的领导者,却不一定掌握某个方面的具体技能;小人是具体事务的操作者,也很难具备高屋建瓴的领导能力。换句话说,君子应当是个“通才”,不必要样样精通,却能够容人领众,任贤使能,因而可以担当统筹全局的大任;而小人则应当是个专才,精通业务,有一技之长,因而可以领受并完成某些方面的具体任务。作为一个组织来说,既需要担当“大任”的领导者,也需要具备“小知”的执行者,二者并无道德上的高低,而只有职责和能力上的不同。正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
与此相适应,孔子指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这里说的是由于二者的地位不同,对能力的要求不同,因而努力的方向也不同。《易·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作为领导者,应该掌握通达大道的能力;小人作为操作者,则应该掌握制作器物、通达技艺的能力。孔子又指出:“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这里说的则是因为地位、能力的差异而造成的工作作风的差别。君子以道取人,以道使人,一切以道为准则,而不以感情的亲疏为取舍,因而能够用人所长,像使用不同的器具一样,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小人平时接受上位者的指挥,习惯于从感情的亲疏而不是从道的原则去处理人际关系;如果让他指挥他人做事,只能是任人唯亲,或者求全责备,根本不会按照人的能力才干来分工合作。既然君子以道用人,突出的是个人的领导能力,因此他就会“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重在充实自己(的道),而轻于责备别人(的行)。所以,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同上)君子在管理关系中处于主动的地位,他就必须也只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而小人在管理关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他只能要求别人(尤其是他的领导者)如何如何,而很少考虑自己的充实和提高。
关于地位所引起的修养差异,指的是君子与小人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素质的要求不同,身份上的差异决定其修养上的差别。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对于这句话,唐以前的注家一般是从地位的角度解读的,如皇侃《论语义疏》引袁氏云:“此君子无定名也。利仁慕为仁者不能尽体仁,时有不仁一迹也。夫,语助也。小人性不及仁道,故不能及仁事者也”④。按此观点,这里的“君子”是不固定的概念,本来身份上属于君子阶层,但在修养上尚未达到君子的境界,即所谓“无定名”。在其修德求仁的过程中,尽管追慕仁者却不能完全体现仁的精神,所以偶尔出现一些“不仁”的状态也属正常。至于“小人”,这里强调的是“不及仁道”——由于其地位、身份的原因,本来就达不到仁的境界,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仁的行为。
宋以后的理学家则更多地从德性的角度解读这句话,如陈埴《木钟集》曰:“君子容有不仁处,此特君子之过耳,盖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丧,天理已自无有,何得更有仁在?”⑤按照这种观点,君子偶尔有不仁之处,只说明其存在道德上的瑕疵;而出现这种情况,无论从君子整体还是从某位君子个人的行为来看,其概率都是很低的。至于“小人”,这里强调的是“无有仁在”——根本就没有善心,没有“天理”,又怎么可能有仁的存在呢?
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孔子所提倡的“仁”,究竟是对君子还是对小人的修养要求?前面说过,孔子对当时的君子阶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的情况忧心忡忡,因而收徒办学,目的是培养一批“德位一致”的新型君子。而在孔子给弟子讲授的德目中,“仁”是最基本最首要的内容。孔子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只有让君子们了解仁学、接受仁爱、实践仁道,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心目中所要造就的新型君子实际上就是“仁者”,“仁者”就是“君子”的同义词。因此,孔子强调“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这里的“仁者”、“智者”、“勇者”,都是对新型君子的期许。孔子所提倡的“仁”,本质上是对君子们的修养要求。
杨伯峻先生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句话的注释中说:“这个‘君子一小人’的含义不大清楚。‘君子’‘小人’若指有德者无德者而言,则第二句可以不说;看来,这里似乎是指在位者和老百姓而言。”⑥如果我们明白“君子”与“仁者”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对于上述这句话中的“君子”“小人”含义所指,应该就很清楚了,不是“似乎是”,而是根本上就是“指在位者和老百姓而言”。同理,我们对《论语》与此相关的另一句话中的“君子”“小人”,也可以做如此观。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既然君子与小人都有可能“有勇而无义”,二者之间显然就不是“有德者无德者”的区别,而只能是“在位者和老百姓”的区别。“义以为上”则是对君子们的修养要求。
三、回归原点:以《论语》“喻义章”为例
自宋代儒学的理学化以来,“君子小人”已经固定成为“有德者无德者”的代名词,即朱熹所谓:“君子小人只是个正不正。”(《朱子语类》卷七十)在此话语背景中,笔者重新提出《论语》中“君子小人”说的纠结问题,并不是要玩文字游戏,而只是想恢复历史原貌,使今人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孔子学说的真谛。在这个原则下,回归原点,重新起步,可能是我们最好的诠释策略。而《周易·解卦》中“君子小人”的解读,很可能就是我们可以依托的一个“原点”。下面,以《论语》中“喻义章”的解读为例。
首先,看看《论语》中的原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在这句话中,“喻”是知晓、明白的意思,“义”指道义,“利”指利益——这些,无论是汉儒还是宋儒都无异议;但对于其中“君子小人”的解读,二者就大相径庭了。
我们先来看宋儒的解读。据王植之《四书参注》记载:“陆象山在白鹿洞讲《喻义章》,学者听之悚然警惕,至有泣下者,可知义利严界,为学者最要关头。”⑦让学者听得毛骨悚然,甚至痛哭流涕,陆九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据其转述:“夫君子小人其学业之就将,心力之勤厉,早作夜思,经营尽瘁,无一不同。然君子之为学也,究心圣贤之道,致力伦常之间,事事从己身起见。故知则真知,非徒博物;行则力行,非有近名。潜修默证之中,自有欲罢不能之趣,乃足谓之深喻。此其人处则不愧《诗》《书》,不愧衾影;出则不负朝廷,不负民物;遇有国是所关,民命所系者,不惮廷诤力谏,而一身之利害不问;即至死生祸福之交,不难捐躯致命,以成一是,乃其喻义之究竟。小人之矻矻孜孜,何尝让于君子?然其所计者,辞章之善否,声誉之有无。忍目前之苦,正以图异日之甘;矫违心之节,正以冀非道之遇。而钻营之巧,迎合之工,后先效尤,闪倏诡变,凡可以幸功名伺意旨者,无所不至,乃足谓之深喻。此等人即令名位可就,但知肥身家,不知爱百姓;但知取容说,不思报国家;营蝇狗苟,而事之不可告人,寤寐不堪自问者不知几何矣。倘遇利害得丧之顷,心沮气馁,患得患失,虽至生平尽丧,名节荡然,而前此谈道立名之身,矜己笑人之口,亦瓦裂尘飞而不堪回首,正其喻利之究竟。学者思此,直当捶心刻骨,岂惟泣下数行已邪!”⑧
这一大段话,真可谓“诛心之论”,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痛快淋漓,确实是对道德高尚者的由衷褒扬,对道德卑劣者的当头棒喝;乃至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可以引起强烈的心灵震动和共鸣!可惜的是,如果用之以解读《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则是牛头不对马嘴了。因为它将“君子小人”仅仅局限于“学者”圈内的道德分野,明显与《论语》本身的历史语境不符,也完全抛开了前人特别是汉儒的解读成果。
我们再来看汉儒的解读。杨恽是汉太史公司马迁的外孙,曾位列九卿,后来因为遭到别人的陷害而被贬为“庶人”。他不甘寂寞,在家经营产业,建造室宅,“以财自娱”。他的老朋友孙会宗写信给他,劝他应当闭门思过,而不应该治理产业,结交宾客。杨恽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报孙会宗书》,为自己辩解。这封书信被称有其外祖父《报任安书》之遗风,写得也是慷慨激昂,痛快淋漓;而其中最关键的辩护理由,竟然也是儒家的君子小人说!杨恽认为,自己原来高居卿大夫之位,履行君子之责,当然要忠于朝廷,报效国家;但现在已经进入庶人之列,因此而亲自率领妻子儿女,竭尽全力耕田种粮,植桑养蚕,灌溉果园,经营产业,用来向官府交纳赋税,这样做又有什么错呢?为此,杨恽专门引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话为自己辩护:“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汉书·杨恽传》)杨恽的意思是说:按照董老先生的话,卿大夫追求仁义以教化民众,民众追求财利以安居乐业;我如今已经是“庶人”一个,你怎么还用卿大夫的规矩来责备我呢?
杨恽在这里引用的董仲舒的话,出自后者的《举贤良对策》,原文是:“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汉书·董仲舒传》)这句话本来不是对《论语》“喻义章”的专门解读,但后世的《论语》注家,在解读“喻义章”时,却又纷纷加以引用⑨。其实,我们要了解董仲舒的本意,应该回到《举贤良对策》的语境中去。
《举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对汉武帝问策的回应,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决策,就是来源于《举贤良对策》第三策的结语:“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正是在这段话之前,董仲舒谈到了社会分工问题:“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其大意是说:上天公平地分配万物的长处,比如:长牙齿的动物都没有角,长翅膀的动物就只有两只而不是四只脚。根据这一“天意”,取得俸禄者就不应该再去从事农业和商业,而谋取额外的利益。为此,董仲舒专门举了一个例子:公仪休做鲁国相,回到家里看到家人织布,非常气愤,休了自己的妻子;在吃饭时吃到家人种的葵菜,也很生气,跑到园子里拔掉了菜秧。为什么如此不近人情?公仪休的理由是:我已经吃上国家的俸禄,家里的生活就有保证了;而我的家人却要自己织布、种菜,那么那些专门织布的妇女、专门种菜的农民靠什么生活?这不是抢夺他们的饭碗了么?
其实,董仲舒这里是意有所指的。针对当时官府乃至官员个人与民争利的现象,他批判道:“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在这里,董仲舒明确区分了“君子”(贤人、大夫)与“小人”(庶人)的不同生存状况和心理状况:急急忙忙地求财求利,常担心贫困匮乏,这是平民百姓的情状;急急忙忙地求仁求义,常担心不能用仁义感化百姓,这是卿大夫的情状。如果居君子之位,又要做小人的事情,那就会带来灾祸;如果居君子之位,去做君子应该做的事情,那就要像公仪休那样,不与民争利。
董仲舒这里所主张的“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实际上正是孔子“君子喻于义”思想的重要内涵。根据笔者的研究,孔子所谓的“义”,主要是针对“君子”即当时的社会统治阶层说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首先,统治者必须克制个人的私欲;其次,统治者对人民不能横征暴敛;再次,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最后,统治者要以义为利。与此相应,所谓“小人喻于利”,则要求统治者承认和满足被统治者的物质需要,并提供各种必要的条件以促其实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利民”,正是国家管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国家管理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回到本文的论述主旨,笔者感兴趣的是上述董仲舒在论证自己观点时,所引用的一个重要论据:“《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从本文第一节中我们已经知道,“负且乘,致寇至”这句话,正是《易经·解卦》第三爻的爻辞,《易传》的作者对此事从“君子小人”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尽管与《易传》中孔子所说“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的观察角度不同,董仲舒在这里想到的是“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但是,在二者心目中,这里的“君子小人”是指“有位无位者”而不是指“有德无德者”,是从“位”的角度区分而不是从“德”的角度别异,应确定无疑的。正是回归这一共同点,使我们找到了解开孔子“君子小人”说原始密码的钥匙。
余论
清代经学大师俞樾在《群经平议》中,谈到《论语》“喻义章”的解读时指出:“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汉世师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矣。《汉书·杨恽传》引董生之言曰:‘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数语乃此章之确解。此殆七十子相传之绪论而董子述之耳。”⑩如果此论成立,则意味着宋儒以来,一切“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的解读,都完全搞错了对象。
笔者从学术上赞同俞樾的意见,但从思想史的角度,却对宋儒的“君子小人之辨”抱着同情的理解。儒学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解释史,不同时代的学者依据其时代需要和时代精神,不断回归原典而又不断超越原典,由此造就了儒学精神的多向性。在这种学术传统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袭前人,沿用旧说,“接着讲”;而应该按照我们的时代需要和时代精神去重新诠释,大胆创新,“放开讲”。但是,这种“放开”又不应该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应该是有所依据、有所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前贤的“确解”和“误解”,都是我们后学者的宝贵财富。
注释: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②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0页。
③商代的“野人”绝大部分是由战俘转来的奴隶;周代的“野人”则是非本部族的客民;二者的职责则基本相同。
④⑤程树德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58页,第958页。
⑥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7页。
⑦⑧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268页,第268页。
⑨参见: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267页;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9页。
⑩程树德撰:《论语集释》,第267页。
标签:儒家论文; 君子论文; 孔子论文; 易经论文; 举贤良对策论文; 国学论文; 论语论文; 董仲舒论文; 卫灵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