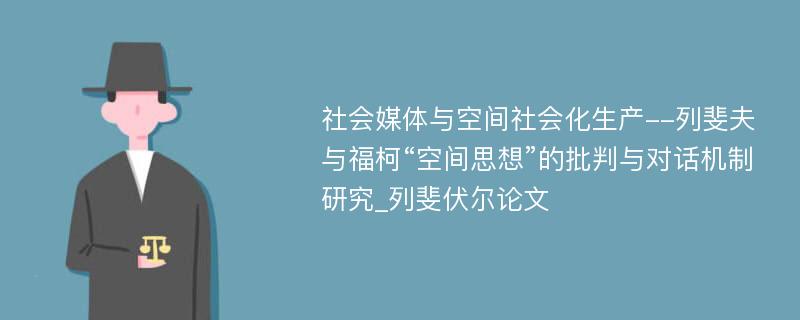
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机制论文,思想论文,媒体论文,列斐伏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空间与空间性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空间批评因此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话语思想。菲利普·韦格纳(Philip E.Wegner)将空间与文化理论的联姻称为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称其是与生态批评、散居批评、伦理批评、超性别批评等并列的21世纪西方最前沿的批评理论。有代表性的空间批评话语包括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米歇尔·福柯的“空间规训”、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安东尼·吉登斯的“时空分延”、多琳·马瑟的“空间分工”、德里克·格雷戈里的“地缘想象”、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空间”、理查德·桑内特的“空间混杂”、约翰·厄里的“消费空间”、爱德华·索亚的“异质空间”等。这是一场与现代性批判密切相关的文化转型,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在《后现代地理学:重述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中将批评领域对空间问题的关注称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在“空间转向”勾勒的诸多批评话语图景中,不同的空间思想纷纷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思考空间以及空间性问题,尤其是从空间批评视角回应现代性批判问题,虽然在对待空间的认识上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内涵,认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①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都将空间视为一种生产话语进行考察,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内涵以及权力和资本在空间意义上的体现。②正如爱德华·索亚所说:“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③因此,空间就是社会本身,甚至被直接推崇为“现代性的体制性推动力的组织媒介(organizing medium)”。④当空间从其原始的自然属性和物理属性维度挣脱出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此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批评向度,空间认识论也成为哲学、美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领域一种自觉的研究方法和批判范式。 在“空间转向”铺设的诸多空间批评话语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空间批评思想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思想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空间规训思想,⑤其代表性成果分别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1974年)和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年)。不得不说,空间论兴起于现象学思潮中的场所主义,⑥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存在主义空间思想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则是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思潮深刻影响下的后现代空间论。从空间批评的历史谱系来看,“后现代空间论的起始点通常被追溯到福柯以及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批判性阐述。”⑦作为后现代空间论的两位先驱者,列斐伏尔和福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空间批评范式,前者关注的是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后者关注的是空间的微观政治学批判范式。⑧不同于其他空间思想的批评维度,列斐伏尔和福柯关注的是空间实践,尤其是空间实践的生产性内涵。简单来说,列斐伏尔关注的是空间的经济学意义,强调空间在整个商品生产中的决定性意义。资本生产首先体现为对作为商品的空间本身的生产过程;福柯致力于考察权力如何在空间向度上发挥作用,也就是通过对空间的“技术操作”来传递某种压制关系。空间规训根本上体现为对某种隐蔽的、匿名的、生产性的微观权力的生产。显然,列斐伏尔和福柯都强调空间意义上的生产实践,只不过二人给出了不同的生产“果实”——列斐伏尔强调对经济利益的生产,福柯强调对微观权力的生产。可见,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强调两种不同的空间批评范式,而且指向不同的权力思路和生产实践,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缺少知识性的对话基础。 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都根植于20世纪60、70年代特定的政治与社会土壤,然而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整个社会语境发生了根本性变迁,我们有理由对理论本身的适用性及其工作机制进行再审视。具体来说,考察一种空间思想在当下语境中的现实对接程度和社会批判力度,首先面临“再语境化”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其置于新的社会语境下进行再解读、再审视。今天,以SNS、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何塞·凡·戴克(José van Dijck)看来,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属性是社会性(sociality)和聚合性(connectivity),⑨其标志性产品是由粉丝数、转发数和分享数等数字化指标所表征的人脉关系,而这正是布尔迪厄提到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核心构成内容。⑩借助关注、分享、评论、转发、私信、拉黑等互动途径,社会化媒体实际上是一个具备人脉关系再造与社会动员能力的信息互动平台,通过对微文本形态的生产与传播而完成其赖以存在的社交圈子的再生产。如今,社会化媒体已经深刻地介入、影响,甚至接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诸多文献研究指出,社会化媒体不仅建构了个体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11)社会认知、(12)情感经验、(13)行为方式(14)和个体的社会化过程,(15)也建构了社会结构深层的文化心理、(16)社会变迁、(17)公共参与(18)和政治变革。(19)显然,社会化媒体已经深刻地改写了当代社会的交往模式、社会形态和政治现实。“媒介化社会”逐渐得到了传统社会学的重视和认可,并成为一种逼真的社会形态。在迪拉伊·默西(Dhiraj Murthy)看来,社会化媒体直接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结构性转向,因为它创设了一个文化话语得以重新诠释的崭新的“社会语境”。(20)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既然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转化,那么,认定有新的空间形式与过程正在浮现,应该是个合理的假设。”(21)因此,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重新审视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批判与发展,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研究思路。 本文选择从空间批评视角研究社会化媒体以及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生产实践。之所以选择空间视角,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路径的一般逻辑。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原理,“不管在什么地方,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22)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依托于一个个具体的空间,与此相应的社会实践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空间实践。所谓空间实践,其实就是社会实践的“空间化”过程,即权力和资本在空间向度上的施展智慧和生产策略。社会化媒体不仅参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因为其与生俱来的社交属性,因而直接参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同时介入“生产空间”和“关系空间”的生产实践。因此,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生产实践本质上也体现为一种空间实践。从空间视角切入进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化媒体的生产机制及其深层的理论创新。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空间批评视角,探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和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的理论批判与创新问题。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探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两种空间思想的工作机制和适用性问题,二者是否获得了新的意义内涵;第二,对两种空间思想进行批判性思考,致力于揭示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理论本身的发展与创新问题;第三,进一步挖掘两种空间思想的内在联系及其对话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二、列斐伏尔与碎片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关于空间生产,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给出了系统的论述。空间生产关注的是一种正统的、公开的、社会化的空间形态,特别强调空间在整个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如果说莱布尼茨、康德、笛卡尔将空间放逐到理性的边缘,空间被理解为绝对的空虚,被推向日常生活的远处,被视为存在的条件而非存在本身,列斐伏尔则创造性地发现了空间的生产性价值,也就是空间之于资本生产的决定性的经济学意义。(23)因此,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被视为一种“工具性空间”,“它既是意识形态的(因为是政治的),又是知识性的(因为它包含了种种精心设计的表现)。”(24)谁拥有对空间的表征权力,以及如何来表征空间,这无疑伴随着权力的生产过程。空间和金钱的属性一样,“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25)就此而言,列斐伏尔断言:空间“是一个中介,即一种手段或者工具,是一种中间物和一种媒介”,(26)“它是某种权力(比如,一个政府)的工具,是某个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或者一个有时候能够代表整个社会,有时候又有它自己的目标的群体的工具,比如技术官僚。”(27) 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中,空间既是生产的场所,也是生产的工具和目的,更是消费的途径和果实。资本正是通过对空间的发现、利用与管理来达到剩余价值回收的商业目的。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就是社会的产品”,(28)即“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生产模式,每个特定的社会关系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29)按照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资本主义进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物质化进程完成的,而物质化进程的关键就是空间意义上搭建生产关系,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空间实践。在无限延伸的资本生产链条中,工厂、地铁、步行街、中心广场、高速公路等空间形态被巧妙地占有和开发,生产关系沿着这些特定空间的布局和结构而搭建起来,空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性物质资料。当空间超越了生产场所而上升为一种生产对象时,空间进入了列斐伏尔所说的生产状态中——空间中事物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30)比如,一条商业步行街的开通,所表征的不仅是一种暧昧的时尚生活,同时是资本意识形态在都市生活中的缓慢穿行;一条地铁线路的规划,不仅生产了地铁沿线一个个具体的资本空间,同时也生产了空间之间的某种隐秘的经济关系…… 与景观碎片、认知碎片、文化碎片等碎片形态一样,空间碎片是现代社会一种常见的空间形态。(31)在周而复始的生产、秩序、仪式的轮番改造下,人们永不停息地奔波于工厂、学校、教堂、商场、医院、广场之间。在两个空间的连接处,甚至同一空间内部的不同单元之间,出现了各种形态的缝隙、边角和空挡,这便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碎片空间。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体系中,空间生产关注的是碎片空间之外的重大事件和资本生产,强调一种永恒的、结构性的、成体系的生产过程。碎片空间被历史忘却,被资本抛弃,被权力忽视,是资本生产的“盲点区域”。碎片空间是黑暗的,是非理性的,是反社会状态的,因而它本身没有价值,仅仅是资本活动需要极力克服或躲避的“过场”,因而被视为资本生产领域的“垃圾”或“废弃物”,即“最卑微的、为传统史学所不齿的零碎、另类的事件、行当和人物”。(32) 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空间生产的意义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转向”,除了关注那些正统的、公开的、社会化的资本空间,空间生产的对象开始转向那些黑暗的、缝隙化的、边缘性的碎片空间。如果我们认可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33)那社会化媒体在空间意义上的开发行为可谓是彻底的、全方位的、立体化的。在社会化媒体所制造的新的空间生产图景中,一个个过渡的、偶然的、短暂的碎片形态被生产出来。社会化媒体的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激活、利用、收编这些被遗忘的碎片空间,使其成为一个资本生产空间。如今,微博、微小说、微电影、微摄影、微访谈、微公益等微文本形态无缝进入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成为碎片空间里最常见的填充物。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课间休息等一切碎片空间里,人们忘我地浏览微博、更新状态、转发评论。今天的“低头族”之所以主导了碎片空间的视觉景观,只不过是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空间生产实践的微妙注释。 社会化媒体的根本使命就是重构社会关系,也就是在空间意义上发现、激活并搭建新的人脉网络,这一过程正是通过碎片空间的社会化途径(socialization)实现的。微博的“周边的人”、微信的“摇一摇”、陌陌的“地点留言”、人人的“人人报道”、遇见的“邂逅游戏”、群群的“随意群组”等社会化媒体应用服务大都致力于发现一个个碎片空间,并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联系。当一个空间被其他空间所识别、所认领、所发现,它便进入社会化的关系网络中,空间之间的物理障碍和距离关系随之被消解了。因此,碎片空间展示的是利益关系和经济神话,然而沉淀的往往是阶级关系和政治内容,空间生产的目的就是对建立在碎片空间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的持续性再生产,这便构成了碎片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34)正因为碎片空间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被发现并利用了,成为社交关系搭建的生产性资源,空间生产转向了碎片空间的社会化生产,这显然是列斐伏尔始料未及的空间生产局面。 在碎片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实践中,社会化媒体改写了传统的空间生产的经济学思路。按照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逻辑,两个空间之所以建立联系,往往存在某种稳定的经济联系和生产逻辑。空间关系一旦破碎,那便意味着沉重的经济灾难。然而,社会化媒体平台上,人们可以轻易地关注他人、添加好友、建立对话,也可以通过拉黑、屏蔽、加密、取消关注等途径撕毁这种关系,一切是如此的随意而无需承担任何经济后果。在微信的“摇一摇”那里,只要两个人同时摇动手机,两个陌生的空间便戏剧性地建立了联系。社会化媒体正是通过对诸如摇手机、碰手机、扫二维码等“新媒体仪式”的生产,也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去仪式化”和“再仪式化”改造,源源不断地试探着空间生产的可能的社会化途径。(35)因此,与传统的空间生产逻辑不同,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空间生产,无所谓理性的、严密的生产逻辑,只是感性的连接,是无意识的结合,是反生产逻辑的短暂相遇。这也注定了碎片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实践是随意的,是松散的,是不稳定的,是稍纵即逝的。可见,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空间实践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空间生产逻辑,这极大地批判并发展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的话语内涵。 三、福柯与空间规训的微观政治学 与列斐伏尔致力于探讨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不同,福柯的空间思想集中指向空间规训,也就是从微观政治学逻辑思考权力在空间向度上的运作模式。在福柯那里,空间既是权力争夺的物质场所,同时也是权力运作的实施媒介,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权力的空间化”过程实现的。福柯的权力观是建立在建筑学或几何学意义上的一种空间构形(configuration),认为其是“一种能够和应该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36) 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集中体现在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中,主要思考权力如何通过对空间的精妙设计和监视而达到社会治理的政治目的。(37)福柯超越了传统的权力观念,试图发现各种弥散在暗处的“权力的眼睛”,即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各种隐蔽的、匿名的、生产性的权力技术。在福柯那里,空间规训的本质就是对空间的监视,使其成为一个被栅格化的监视对象。福柯借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设想的“全景敞视监狱”来揭示一种普遍存在的空间规训模型。福柯认为,“凡是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视模式。”(38)“全景监狱”是一种典型的建筑学形象——囚犯被安排在环形设置的透明囚室里,监视者则处于中心的瞭望塔上,他可以随时躲在暗处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空间构形就是“全景监狱”,它的功能就是对权力的空间化处理——“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39)在一个个类似“全景监狱”的空间构形中,来自监视者的“目光压力”构成了一种极为逼真的管制形式,权力最终以一种极为简易而高效的监视途径完成了对新的主体形式的规训与生产。 现代社会发明了一张巨大的“观看网络”,“权力的眼睛”已经渗透到一系列社会空间中,一系列新的主体形式被生产出来。由于地理地图、安检系统、遥控装置、监视摄像、人口统计、身份验证、红外捕捉、GPS定位、网络实名、身体检查、IP追踪、城市规划及各种电子传媒的隐性在场,相应的社会空间被推向了一个透明的、可视化的监视状态。当个体进入一种监视体系,躲在暗处的“权力的眼睛”实际上虚构了一种压制关系,“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40)而这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41)现代都市广场不再是按照演讲、集会、运动所需要的结构特征进行设计,而是以一种便于管理的政治意图和资本逻辑进行布局和构造。草坪、商场、小贩、LED屏、广场舞、高音喇叭等“符号身影”的在场,不断挤占、吞噬,甚至收编了原本属于广场的政治内涵。当空间开始按照权力的意志适时地调整自身的构形、功能与结构,“通过空间的治理”成为一个不那么陌生的微观政治学命题。 因为空间从其原始的黑暗状态中走出来,进入权力话语特别关注的可见状态和透明区域,空间才作为权力实施的媒介和途径不断发生作用。因此,空间规训本质上体现为对空间可见性(visibility)的生产。在福柯看来,空间规训的主要后果就是在被监视者身上“造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42)当可见性被生产出来,其实意味着对空间的监狱化处理,目的就是“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43)进而使空间获得“产生意义的权力,进入特定序列的权力”。(44)当可见性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福柯所说的“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便成为一个逼真的主体规训与控制命题。(45)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见性的生产,不仅构成了空间规训的方法论基础,也成为空间规训的附加产品。 如果说空间规训的本质是对空间可见性的生产,那社会化媒体则将可见性生产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产趋势。在可见性生产策略上,社会化媒体已经不单单满足于对主体位置的定位与描述,更是在社交关系上“大做文章”,即强调可见性的社会化生产。如今,空间场景及其可见性是社会化媒体特别关注的生产对象。(46)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中,罗伯特·斯考伯(Robert Scoble)和谢尔·伊斯雷尔(Shel Israel)特别提出了著名的“五种原力”:社交媒体、移动设备、大数据、传感器、定位系统。(47)在“五种原力”中,定位系统是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其实,定位也是一种监视,而且是一种最彻底、最隐蔽的监视途径。今天,微信、微博、陌陌、图钉、飘信、啪啪、密友、嘀咕、维达遇见、网易八方等社会化移动应用服务内置的“基于位置的服务”(LBS)功能其实就是一种“定位系统”,其特点就是可以根据手机或可穿戴设备来定位主体的空间位置和行动轨迹。微信的“附近的人”、微博的“地理周边”、陌陌的“地点留言”、遇见的“邂逅游戏”、对面的“社交广场”、人人的“人人报道”、群群的“随意群组”、微拼车的“搭车服务”都是在用户的地理位置上发现或再造可能的社交关系。于是,个体被清晰地标注在一张巨大的LBS大网中,成为一个可见的、公开的、不设防的观看对象。 在可见性的生产策略上,社会化媒体特别强调对主体及其空间信息的可视化表征,这无疑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监视方式和控制观念。在LBS无处不在的监视体系中,不仅个体的位置被推向一个可视化的监视网络,而且整个社交关系的空间实践及其行踪结构同样进入一个可视化的表征体系。在高德地图那里,个体可以通过微博账号登录,随后,用户的一切行为信息和微博信息都会清晰地显示在地图上。如今,在大数据技术的直接干预下,可视化构造的是一种不对称的观看关系,权力话语不仅在观看个体,也在观看群体,进而监视、管理或控制群体。美国研发了一款新型的手机APP,它可以利用手机中的GPS系统来动态地检测个体所在空间的地面运动状况,并在大数据基础上进行可视化表征。当这些数据汇集到政府那里,一个庞大的地震预报系统随之建立起来。(48)当空间进入一种可视化的表征状态,同时意味着对黑暗状态、隐蔽状态、野蛮状态、非理性状态的“视觉驱逐”。因此,可视化技术已经远远超越了地理学范畴,而是构造了一个权力施展的建筑学或几何学模型,权力话语正是通过对主体位置的可视化表征和追踪达到社会管治的规训目的。 不同于“全景监狱”的生产逻辑——个体处于被动的监视状态,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个体开始主动而自愿地暴露自己的空间景观和地缘信息,这就不能不提到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正在急速蔓延的一种新文化形态——窥探文化(peep culture)。在霍尔·尼兹维奇(Hal Niedzviecki)看来,当前社会最为重要的“文化转向”就是从流行文化转向窥探文化。(49)窥探文化的本质就是“有话就说、有事就秀”(tell-all,show-all),社会实践上体现为“过度分享”(over share)。2008年,美国《韦氏新世界词典》将“过度分享”推为年度关键词。人们发布微博、上传图片、更新状态、分享信息时总会习惯性地附上自己的空间位置,甚至主动地暴露自己的位置、状态和踪迹,这是一种逼真不过的炫耀性“存在方式”以及主体在现代性背景下的“喧嚣的孤独”。(50)如果借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前台”(front)概念,(51)社会化媒体试图将一切都纳入“前台”,“后台”(back)逐渐消失,日常生活即是窥视对象。于是,暴露自己和窥视他人成为一个同步行进的过程,人们完全进入一个不设防的“操演”(performance)空间。(52)人类学家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中指出,网络社会中普遍泛滥的分享行为直接改变人的本质,即主体开始退缩,成为一个“超媒体自我”。QQ空间、微博好友圈、微信朋友圈完全按照有利于“表演”的内在逻辑设计,点赞率、粉丝数、转发量、关注度等来自他人的“评判”则反复冲刷着日常生活的表演欲望。显然,在由“过度分享”主导的窥探文化景观中,社会化媒体改写了主体意义,改写了人们的存在方式,改写了原有的监视状态。 如果说“全景监狱”的工作原理是“少数人观看多数人”,社会化媒体无疑呈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发达的另一种监视状态——托马斯·马蒂森(Thomas Mathiesen)提出的“对视监狱”(Synopticon)(53)和杰弗里·罗森(Jeffrey Rosen)提出的“全视监狱”(Omnipticon)。(54)“对视监狱”的观看方式是“多数人观看少数人”,而“全视监狱”则是“多数人观看多数人”。由于个人的肖像、位置、行踪轨迹等信息散布于社交网络,权力部门可以轻易地追踪并定位个体行为,尤其是对一些潜在的群体性事件进行预测和干预,以此达到社会控制和管理的政治目的。美国ARO公司研发的一款名为Saga的手机APP,能够利用手机的摄像头、气压表、话筒、LBS定位器等动态分析个人的周围环境,并准确锁定个人的空间位置,从而自动记录、搜集、掌握个人的一举一动。(55)欧盟委员会公民保护与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发现,通过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蛛丝马迹”来寻找犯罪分子的成功率高达56%。(56)可见,从“全景监狱”到“对视监狱”或“全视监狱”,空间意义上的社会管制成本大大降低。当一切黑暗的、模糊的、不确定的空间都被毫无保留地推向公共视域,可见性的生产趋势远远地超出了福柯早期设想的空间规训逻辑,这极大地批判并发展了福柯的空间思想。 以上分析不难发现,社会化媒体创设了一个新的社会语境,两种空间思想远远超越了原初的理论假设和批判范畴,尤其是在理论观念和空间实践上获得了新的意义内涵,这使得对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创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两种空间思想是否存在对话的可能性?关于对话性的理解,本文主要从空间观念和空间实践两个维度进行考察:所谓空间观念视角,本文侧重分析一种空间思想对另一种空间思想的意义补充与深化,对此我们将从“碎片空间”和“可见性”两个维度讨论二者在话语观念上的统一性和辩证关系;所谓空间实践视角,本文核心探讨两种空间思想在生产实践层面的关联性和对话性,而流动空间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生产对象与生产语境。 四、双重主体与碎片空间的可见性生产 如果说列斐伏尔那里发现了碎片空间这一崭新的空间形态,福柯那里发现了一种可见性生产的全新的规训机制,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碎片空间和可见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这不能不提到社会化媒体与生俱来的传播属性和生产方式。社会化媒体致力于生产一张无限延伸的“关系大网”,客观上要求将一切躲在暗处的碎片空间都抛入公共视域,如此才能打通并完善原有的“空间拼图”。而碎片空间是如何被发现的,这又离不开社会化媒体无与伦比的“LBS化表征”功能,也就是对碎片空间可见性的生产能力。如同微信“摇一摇”、微博“周边广场”、遇见“邂逅游戏”、百度“挚爱推荐”等社会化应用服务,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之所以能够在两个完全没有现实逻辑的空间向度上展开,一方面需要对模糊的、黑暗的、不确定的碎片空间进行激活和识别,另一方面需要对碎片空间进行表征,使其成为一种可见的甚至可视化的感知对象和生产对象。因此,从空间实践视角审视社会化媒体的关系实践,这既是面向碎片空间的空间生产实践,也是面向可见性生产的空间规训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说碎片空间和可见性是我们接近两种空间思想的话语立足点,但二者都服务于人脉圈子的聚合与再造功能,本质上都统一在“关系大网”的生产逻辑和空间实践中。 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列斐伏尔和福柯不仅都关注“碎片空间”这一崭新的空间形态,而且都强调一种公开的、透明的、理性的可见状态,因此二者在对待可见性的态度上是统一的,是对话的,更是辩证的。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生产关注的碎片空间之所以成为一种崭新的生产对象,本质上还是因为碎片空间的可见性被发现并激活了。可以设想,如果碎片空间的黑暗性、动物性、非理性没有被“征服”,依然停留在一种不为人知的空间状态,那它终将是资本极力回避的“垃圾”或“废弃物”,建立在碎片空间上的资本生产行为便无从谈起;反过来,在福柯那里,空间规训关注的可见性之所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产景观,本质上是因为“权力的眼睛”开始转向那些原本黑暗的、模糊的、非理性的碎片空间。由于公共空间或公共生活原本就“暴露”在权力目光的观看视野中,而碎片空间里又潜藏或酝酿着各种形式的抵抗与威胁,因此权力技术的施展目的就是“征服”我们时代残存的一切碎片空间,如此才能拼接并组建一个更大的规训之网。总之,社会化媒体语境下,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就离不开可见性生产意义上的规训实践;而谈福柯的空间规训,同样离不开资本话语对碎片空间的生产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列斐伏尔那里的“可见的碎片空间”与福柯那里的“碎片空间的可见性”是内在统一的,是互为前提的,具有深刻的辩证关系。 尽管列斐伏尔关注的是碎片空间的经济学意义及其深层的资本生产,福柯关注的是碎片空间的可见性的生产及其深层的权力生产,但资本生产和权力生产本质上是同步行进的,甚至是共时意义上的“共谋”行为。在福柯早期设想的空间规训图景中,可见性生产的直接力量来自政治权力的空间实践,但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除了政治话语在社会管治和公共治理层面的权力思考,更为重要的权力来源则是资本话语的扩张欲望和生产潜力。因此,可见性的生产主体,本质上体现为资本权力主导下的商业与政治的共谋行为。今天,社会化媒体运作的基本思路就是对一切可能的空间场所和用户场景的深度开发。(57)当碎片空间进入资本话语的关注视野,它不仅意味着一种重要的生产对象,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窥视对象。与此同时,空间规训意义上的过度分享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空间生产方式。换言之,“全视监狱”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监视方式,根本是因为社会化媒体在技术层面创设了“多数人看多数人”的可能性,而这场技术革命无疑是由资本话语主导并驱动的。资本的思路非常清楚,只有整个社会进入“多数人观看多数人”的表演模式,资本才能将碎片空间整合到已有的商业网络中。因此,社会化媒体深刻地改写了空间实践的基本逻辑,可见性生产的背后,是资本权力之于政治权力的主导意义。 其实,在对待可见性的态度上,尽管福柯看到的是可见性的监视和规训意义,列斐伏尔看到的是可见性的经济价值和生产意义,但二者都将不可见性视为一种威胁或改造对象,在空间实践上都强调对黑暗状态、非理性状态、野蛮状态的“克服”与“祛蔽”行为。在福柯看来,黑暗为各种蠢蠢欲动的抵抗行为提供了某种保护,因为“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58)这也是为什么哥特小说和黑帮电影总是在极力地构筑一个由石墙、地牢、洞穴、废堡、丛林、修道院等黑色元素搭建的抵抗世界;在列斐伏尔那里,可见性甚至是一个通往公共性的政治路径,因为“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59)由于公共领域中的行动完全依赖于可见性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互动,(60)这使得“社会化媒体支撑的‘可见性’本身构成了公共生活的意义来源,成为赋予人类存在感的基本方式。”(61)纵观整个资本话语的进化史,其实就是对一切可能的黑暗状态和模糊区域的规训史和改造史。资本的想象力不仅仅是对公共空间或类公共空间的开发,还体现为对注入乡村、森林、湿地、古墓、太空等原本黑暗的未知区域的“进犯”,它的目的就是将其纳入到科学、技术与理性可以把握的公共话语框架。因此,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可见性生产实践,打通了列斐伏尔和福柯的话语壁垒,既满足了空间规训对于社会管理的直接需求,也满足了空间生产对于公共性的深层呼唤。 当空间被视为一种生产性话语,福柯和列斐伏尔都强调可见性意义上的主体形式的生产,也就是对“双重主体”的生产实践。从空间话语的运作后果来看,列斐伏尔关注的是作为消费对象的主体形式,而福柯关注的是作为规训对象的主体形式。具体而言,在福柯那里的主体形式往往是作为权力的管治“对象”出场的,他是消极的,是被监视的,是他者化的,是权力在空间意义上的施展结果;列斐伏尔意义上的主体形式更多是消费的主体,是生产的主体,更是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主体话语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权力对象的主体形式与作为消费主体的主体形式是一个同步行进的生产过程,二者深度勾连,彼此对话,统一在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中。一方面,列斐伏尔意义上的主体形式,首先建立在主体规训的基础上,而这一过程离不开政治话语的暗中介入和推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政治话语的默许,如果政府在政策设计上能够保证个体足够的隐私界限,那今天社交网络上的大数据技术何以跨越个体隐私和数据正义这道“伦理屏障”?政治和资本在大数据那里“各取所需”,甚至暧昧地纠缠在一起,只留下一个个被伦理放逐的主体形式;另一方面,福柯意义上的主体形式,最终在资本话语的空间生产实践中愈加失去主体性。当人们在社会化媒体铺设的“秀场”中尽情地“表演”时,这种“被看的存在”不正是由资本话语所驱动的一种全新的主体规训吗?因此,社会化媒体的空间实践正在生产一种崭新的“双重主体”形式——个体既是空间生产的消费主体,也是空间规训的规训主体。当两种原本相去甚远的主体形式走到一起,并且统一在社会化媒体的空间实践中,深层揭示的恰恰是空间生产与空间规训的一体状态,或者说资本话语与权力话语的杂糅状态。显然,从主体实践来看,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具有积极的对话性和辨证性。 如前分析,就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对话机制而言,碎片空间揭示了生产对象的一致性和同一性,可见性揭示了话语逻辑上的对话基础和依存关系,因此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对话内涵和辨证关系。要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对话机制,就不能不提及可见性生产基础上的对话实践,也就是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空间实践,而这直接指向社会化媒体语境下一种急速扩张的空间实践——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 五、流动空间与两种空间思想的对话实践 社会化媒体对人脉关系的聚合与再造,并非是一种静态的、程序性的、模式化的生产行为,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流动状态和流动结构中完成的,这无疑创设了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和实践话语。人脉关系的识别与再造过程,往往伴随着信息、符码、资本、组织、技术的流动过程,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主体的自由流动,以及由于主体流动而带动的交往“节点”和空间关系的流动。微信、几米、陌陌、旺信、比邻等社交APP允许人们搜索附近的好友,因而可以实时地发现并激活周围的空间关系,深层带动的是一种变化着的人脉圈子的生产和流动;Sports Tracker、Nike+Running、益动、乐疯跑、咕咚运动等社交APP能够实时记录并显示用户的运动线路和空间信息,个人的空间轨迹不仅被发现了,而且被可视化表征了,最终呈现的是一种流动着的空间实践和空间体验……显然,正是在各种形态的“流”(flow)的作用下,流动空间成为一种基本的存在景观和生产事实。 流动空间是曼纽尔·卡斯特于1996年分析网络社会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从空间维度揭示网络社会的本质内涵。在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是在流动意义上组织并建立起来的。(62)信息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符码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流动还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和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63)卡斯特进一步指出,流动构成了现实世界的基本特征,包括空间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围绕流动而建立起了某种隐秘的关系。因此,流动强调空间与空间的链接,流动空间的本质就是空间关系的生产。正是在流动中,人们征服了地方空间(local space),抛弃了原有的空间体验,发现、触摸并试探着新的空间关系。在流动空间那里,现实中的空间场所被吸纳并整合到整个网络结构中,这直接促进了网络“节点”和主体“核心”的流动。至此,空间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栅格化了的地方空间,而是被信息化了,被社会化了,并且进入一种关系结构和流动状态中,动态地与其他空间发生着某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和资本关系。 流动,是空间实践的外在表征,也是现代性在空间意义上的认知向度,更是我们接近空间性以及空间的社会性的基本审视路径。社会化媒体极大地拓展了流动的深度和想象力,主体被吸纳到一个巨大的空间网络中,微妙而传神地与他人发生关系,这使得流动空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变化的、瞬间的、过渡性的“空间场”及其深层的空间关系的流动。流动的背后,是人脉圈子的激活,是主体所处空间关系的生产与再造。无论身处何地,社会化媒体都会动态地跟踪主体的行动轨迹,以主体为原点的空间区域被“照亮”了。因此,社会化媒体“虚构”了一种空间关系,也就是主体与周围空间场所的可视关系,这一可见的空间区域就是“空间场”。今天,高德、谷歌、百度地图会随时显示主体所在位置的周边信息,而且在地图上清晰地标注周围的商场、餐厅、地铁、广场、游乐场等信息。当主体在现实中流动,深层带动的是一种“空间场”的流动,而社会化媒体则动态地捕捉“空间场”及其流动轨迹。显然,“空间场”的流动,其实关注的是一种变动不居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从主体流动到“空间场”的流动,流动空间思想完成了对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液体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微妙注解。(64) 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空间生产和空间规训都已经不单单满足于对某种静态的、稳定的、结构性的空间状态的征服与生产,而是开始转向了对“流”的征服与生产,这极大地拓展了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的内涵体系。无论是主体流动,还是符码流动,社会化媒体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空间本身而是空间关系。正是在各种形态的“流”的作用下,一个空间总是实时地、动态地、不间断地与其他空间发生关系,空间关系的搭建与重组进入一种流动化的生产趋势,因而制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生产和空间规训事实。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生产从基于空间本身的价值发现转向了“流”的价值再造,所谓的“空间场”不过是被资本精心虚构和炮制的想象物,这与现实逻辑无关,更多是资本的狂欢与胜利;在福柯那里,空间规训从传统空间转向了对“流”的关注,尤其是对流动着的“空间场”的监视与规训,这是福柯从未想象过的一种生产景观。因此,在流动空间实践中,“流”成为空间生产和空间规训共同关注的生产对象和生产结果。当各种形态的“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流动空间实践既可以说是一种空间生产实践,也可以说是一种空间规训实践,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前所未有地统一在流动空间中。 大卫·盖勒特(David Gelernter)指出,当前社会结构的特点体现为从“平台”向“流”的转变,即从基于空间的“生活流”(lifestreams)转向基于时间的“世界流”(worldstream)。(65)所谓世界流,强调一种时间意义上永不间歇、漫无边际的流动景观。社会化媒体创设了一个巨大的流动语境,流动不单单意味着主体的流动,同时体现为各种符码的流动,如即时消息、RSS源、BitTorrent种子、Twitter对话、Facebook留言墙和时间线。其实,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符码流动,惟妙惟肖地模拟、复制并征用了现实交往的各种逻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观念和伦理细节在这里得到了近乎逼真的再现——有一种暗恋叫关注;有一种冷酷叫拉黑;有一种示爱叫评论;有一种友谊叫红包;有一种相爱叫互粉;有一种调情叫私信;有一种分手叫取消;有一种支持叫转发;有一种暴力叫加密……不难发现,当日常生活中这些温情脉脉的伦理话语被生产出来,成为流动空间实践的“交往法则”,这既是空间生产意义上的空间关系再造智慧,也是空间规训意义上的可见性生产智慧。 在大数据和可视化技术所主导的流动空间实践中,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与再造呈现出智能化、匿名性和生产性的特征,(66)这是列斐伏尔和福柯从未设想过的一种空间实践。在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批评体系中,空间更多是规划的结果,是权力和资本精心设计和直接干预的结果,然而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流动空间实践逐渐超越了这一生产逻辑,而且愈加隐蔽且具有生产性。在百度“挚爱推荐”那里,用户只要连续一段时间使用百度地图,系统便会记录个体的生活轨迹,同时推荐与自己行动轨迹比较匹配的另一个用户。如果用户接受服务,系统会自动启动导航,引导二人“相遇”。显然,社会化媒体创设了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空间关系开始进入一种“流动化生产”的生产结构中,而且作为一种逼真的空间体验打通了线上与线下的空间距离,这是列斐伏尔和福柯未曾料及的空间体验和生产实践。 在社会化媒体的生产欲望和想象图景中,流动空间本质上是对“流”的可见性的生产实践,这无疑拓展了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话语内涵。一方面,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生产的视野之间延伸到对社会空间中的一系列“流”的生产、整合、收编和利用。传统的空间生产实践之所以忽视流动,是因为流动是资本难以把握的,因而才陷入资本话语的黑暗区域或认知“盲点”。然而,社会化媒体发现了流动中的可见性,使得编织流动中的资本神话成为可能。因此,从静态空间转向流动空间的生产,这有效拓展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的话语内涵。另一方面,福柯空间规训的思路也发生了相应调整,权力的目光已经不单单满足于发现某种具体的、栅格化的、结构性的可见性,同时还关注那些流动的、变化的、稍纵即逝的可见性。流动原本增加了规训的难度,某种意义上是对规训的反抗,但随着LBS技术和可视化技术的发展,权力对于“流”的敏感和管制已成事实。正是因为对流动中的可见性的发现,社会规训的权力网络开始蔓延到一切的流动区域,空间规训转向了对流动空间的规训和管理,而这无疑意味着对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批判性发展。 当空间进入流动状态,流动便不单单是一种空间状态,还是一种空间属性,更是一种关于空间的认知话语。原本静态的时间意义上的空间实践开始转向了碎片化的、过程中的、状态性的、关系中的空间实践。因此,批判性地审视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生产思想,社会化媒体无疑赋予了其新的生产语境和生产内涵——二者都强调对流动空间的生产趋势,而且统一在流动空间这一崭新的空间实践中。 结语与讨论:重提“断点”与通往一种空间叙述史 本文将空间批评引入社会化媒体的批评范畴,从空间实践视角进一步接近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生产实践,致力于思考并发现社会化媒体研究的一种可能的学术视角和理论框架。在碎片空间、可见性、流动空间共同搭建的空间实践和诠释体系中,无论是空间观念上,还是空间实践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福柯空间规训思想都嵌套在彼此的阐释体系中,即一种空间思想都对另一种空间思想给出了极为重要的话语补充和深化,并在空间实践上存在明显的对话性和辩证关系。其实,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诸多空间实践已经远远超越了列斐伏尔和福柯原初的理论范畴和实践模式,无疑对理论在新语境下的适用性和批判性提出了挑战,那这究竟是对理论的颠覆或否定,还是对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回答这一问题,绝非易事,因为这不仅涉及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空间实践的复杂性,还涉及“何为理论”、“理论边界”以及“批判的边界”等问题。限于研究问题的聚焦,本文开展的是一项关于批判的批判研究,也就是关于空间批评的批评。尽管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空间形态、主体实践、空间逻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现实的想象力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列斐伏尔和福柯最初的理论框架,但在批判逻辑上依然延续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和空间规训的微观政治学路径。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框架来谈空间生产,同样也有必要跳出福柯的空间规训框架来谈空间规训。正因为如此,本文将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出现的新的空间形态、新的空间逻辑、新的空间实践视为对两种空间思想的批判性的发展与创新。正是在这一前提下,由于碎片空间、可见性生产、流动空间等话语的积极介入,空间生产和空间规训两种空间批评话语建立了积极的对话性和辩证关系。 当然,空间批评思想仅仅是列斐伏尔和福柯的哲学与社会思想的一部分。探讨空间生产与空间规训的深层关系,有必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思想体系中予以批判性审视。社会化媒体发现了碎片空间,也激活了碎片空间的可见性。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社会思想体系中,碎片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见性又意味着什么?这直接指向列斐伏尔和福柯对于“总体历史观”(total history)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推开的空间叙述史命题。 列斐伏尔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历史观”批判逻辑,空间生产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基于“联合—分离”的空间假设:在传统的生产空间之外,依然存在公园、游乐场、俱乐部、新的居住区等被分离出来的空间。这些空间场所虽然远离了生产,但却是人们休闲娱乐、恢复体力的场所,因而构成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简单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包含两种空间形态:作为商品生产的空间场所和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场所。这两种空间场所既是联合的,又是分割的,既是连续的,又是断裂的,共同书写了总体性批判的历史辩证法——“这是一种关系,一种在分解(dissociation)中对内在性(inherence)的支持,在分离(separation)中对包含(inclusion)的支持。”(67)在列斐伏尔看来,接近社会形态的总体性,除了特别关注传统的生产空间,还应该关注那些“分离的空间”,即“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然而,黑暗的、非理性的、默不作声的碎片空间并不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分离的空间”,因为那里缺少总体历史观所需要的连续形式和重大主题。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碎片空间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成为人脉关系聚合与资本链条延伸的生产性场所,确切地说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显然,重提碎片空间的生产实践,这不仅发展了空间生产的批评内涵,也发展了总体历史观的方法论基础。 与列斐伏尔试图接近那些“分离的空间”来接近历史的总体性不同,福柯对这种象征连续的、编年的、先验性的“总体历史观”持怀疑态度。福柯借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接近知识的历史,他关注的不是历史的连续性,而是那些不连续的历史断点(rupture)。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考古学分析的文本对象是一系列象征断裂和不连续性的“话语的单位”,因此要抛弃“传统”“发展”“演进”“心态”“精神”“书”等“总体历史观”所要求的连续形式和主题概念,转而关注那些碎片性的、边缘的、躲在暗处的微小文本(如档案)。他坚持认为,“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序列、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68)显然,福柯提供了一种接近历史的另一种思考范式,也就是讲述“邻近的和边缘的历史”,讲述“日常生活领域中影子哲学的历史”,(69)从而打捞被总体性历史忽视或遗漏的历史话语。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碎片空间从黑暗状态中走出来,那里便悄无声息地沉淀了权力话语的生产旨趣和技术策略。从碎片空间那里去触摸可能的有关知识与话语的历史,这是一种合理的假设。因此,重提碎片空间的规训实践,这是社会化媒体时代权力话语或资本话语研究绕不开的一个研究“文本”,因而极大地拓展了知识考古学的文本范畴。 总之,尽管列斐伏尔和福柯在对待“总体历史观”的态度上存在差异,但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二者开始重返原本被历史忘却、被知识忽视的空间形态——碎片空间,并尝试将其整合到自身话语的陈述体系中。在列斐伏尔这里,碎片空间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的总体性;在福柯这里,碎片空间则致力于呈现一种关于话语/权力的历史。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正在泛滥的过度分享趋势中,当碎片空间的可见性被生产出来,并且进入一种流动的空间实践中,权力和资本能够轻易地捕捉个体的空间信息和行踪轨迹,我们有理由去想象并建构一种空间叙述史。所谓空间叙述史,也就是强调从空间性与空间实践视角来接近和把握社会史或观念史。之所以提出空间叙述史,根本上是因为社会实践依托于具体的空间,一定意义体现为一种空间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基本逻辑。纵观以往的空间叙述,只有结果和轮廓,没有状态和细节;只有时间节点,没有过程跟踪;只有静态呈现,没有动态演绎;只有空间位置的绝对表征,没有空间关系的相对表征。碎片空间的“出场”,无疑在叙述逻辑上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空间拼图”。因此,从空间意义上来观察社会实践的“空间化”过程,便可以在历时意义上相对清晰地揭示资本运作的社会史和权力变迁的观念史。一方面,空间生产意义上的碎片空间不再是现实世界里可有可无的边角或空挡,而是直接构成了日常生活本身,因此可以在一个更完整的“空间拼图”中来把握资本实践的社会史;另一方面,空间规训意义上的可见性呈现出空前发达的生产趋势,不仅碎片空间成为权力的监视对象,流动空间也一并被送到权力话语的规训视野,因而考察碎片空间的进化史和改造史,便能够在空间向度上揭示权力技术的观念史。 注释: ①[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04页。 ②Wegner,P.E."Spatial criticism:Critical geography,space,place and textuality",in Julian Wolfreys (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180. ③[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1页。 ④Friedland,R.& Boden,D.,Nowhere:Space,Time and Modernit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4,p.vii. ⑤Hubbard,P.& Kitchin,R.,Key Thinkers on Space and Place(2[nd] ed.),London:Sage,2010,pp.1-17. ⑥与空间论不同,场所主义立足于存在主义思潮,认为空间是存在意义上的物质世界,而且与人的存在直接关联。场所主义反对空间认知的科学化、实证化倾向,也反对空间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更多地强调空间的质的内涵和意义。 ⑦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⑧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00-109页。 ⑨Dijck J.van,"Facebook as a tool for producing sociality and connectivity," Television & New Media,vol.13,no 2,2012,pp.160-176. ⑩Rojas,H.,Shah D.V.& Friedland,L.A.,"A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1,no.4,2011,pp.689-712. (11)Bechmann A.& Lomborg,S.,"Mapping actor roles in social media: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value creation in theories of user participation," New Media & Society,vol.15,no,1,2013,pp.1-17. (12)Valenzuela S.,Park N.& Kee,K.F.,"Is there social capital in a social network site?:Facebook use and college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trust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14,no.4,2009,pp.875-901. (13)Lee,C,S.,"Exploring emotional expressions on YouTube through the lens of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 New Media & Society,vol.14,no.3,2012,pp.457-475. (14)Heinonen,K.,"Consumer activity in social media:Managerial approaches to consumers' social media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vol.10,no.6,2010,pp.356-364. (15)Debatin,B.,Lovejoy,J.P.,Horn,K.& Hughes,B,N.,"Facebook and online privacy:Attitudes,behavior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15,no.1,2009,pp.83-108. (16)Arora,P.,"Typology of Web2.0 spheres: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social media spaces," Current Sociology,vol.60,no.5,2012,pp.599-618. (17)Gilbert,E.,Karahalios,K.& Sandvig,C.,"The network in the garden:Designing social media for rural lif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59,no.9,2010,pp.1367-1388. (18)Bennett,W.L.,"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litics:Political identity,social media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44,no.4,2012,pp.20-39. (19)Howard,P.N.& Parks,M,R.,"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change:Capacity,constraint and consequ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2,no.2,2012,pp.359-362. (20)Murthy,D.,"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media:Theorizing Twitter," Sociology,vol.46,no.6,2012,pp.59-73. (21)[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04页。 (22)[法]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页。 (23)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Blackwell,1991,pp.1-4. (24)[法]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25)[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99页。 (26)[法]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27)[法]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28)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Blackwell,1991,p.30. (29)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30)Lefebvre,H.,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Blackwell,1991,pp.36-59. (31)[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芦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1页。 (32)郭军:《关于〈拱廊计划〉》,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33)[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3页。 (34)关于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碎片空间的社会化生产机制论述,详见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阐释》,《当代传播》2013年第3期,第13-16页。 (35)关于社会化媒体与日常生活的“去仪式化”和“再仪式化”问题,详细论述参见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戴维·哈维“空间压缩思想”的当代阐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45-51页。 (3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31页。 (37)福柯的空间规训论述最早见于《疯癫与文明》中,他详细分析了“精神病院”这一特殊的空间形态的规训机制,即权力通过对精神病院的“技术操作”——缄默、镜像认识和无休止的审判,使得疯癫患者变成了“精神病人”,最终医学变成了司法,治疗变成了管治。详见[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4-259页。 (38)[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31页。 (39)[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31页。 (40)[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 (4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7页。 (42)(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6页。 (4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0页。 (44)[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6页。 (45)[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46)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新闻记者》2005年第3期,第20-27页。 (47)[美]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赵乾坤等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目录。 (48)Prigg,M.The App that can predict an earthquake:New system uses GPS in phones to create early warning system,April 10,2015,Required from http://www.Isooker.com/archives/13094. (49)Niedzviecki,H.,The Peep Diaries:How We're Learning to Love Watching Ourselves and Our Neighbors,New York:City Lights Publishers,2009,pp.153-162. (50)关于社交媒体与现代社会四处蔓延的“喧嚣性孤独”,参见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5期,第48-63页。 (51)[加]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52)Dayan,D.,"Conquering visibility,conferring visibility:Visibility seekers & media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7,no.1,2013,pp.137-153. (53)Mathiesen,T.,"The viewer society:Michel Foucault's 'panopticon' revisited," Theoretical Criminology,vol.1,no.2,1997,pp.215-234. (54)Rosen,J.,The Naked Crowd:Reclaiming Security and Freedom in an Anxious Age,New York: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2005,p.11. (55)Simonite,T.,"Using a smartphone's eyes and ears to log your every move," MIT Technology Review,July 2013,Required from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news/516566/using-a-smartphones-eyes-and-ears-to-log-your-every-move/. (56)网易:《社交媒体照片将成警方破案新武器》,2014年10月http://digi.163.com/14/0507/10/9RKTL8R6001620UT.html。 (57)谭天:《从渠道争夺到终端制胜,从受众场景到用户场景——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关键》,《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第15-20页。 (58)[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5页。 (59)(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60)[美]理查德·森尼特:《公共领域反思》,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2页。 (61)孙玮、李梦颖:《“可见性”:社会化媒体与公共领域——以占海特“异地高考”事件为例》,《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43页。 (62)关于流动空间的思想内涵及其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生产实践,详细论述参见刘涛、杨有庆:《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卡斯特“流动空间思想”的当代阐释》,《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2期,第73-78页。 (63)[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05页。 (64)Bauman,Z.,Liquid Modernity,Oxford:Blackwell,2000,p.2. (65)Gelernter,D.,"The end of the web,search and computer as we know it," Wired,Feb.1,2013,required from http://www.wired.com/opinion/2013/02/the-end-of-the-web-computers-and-search-as-we-know-it/. (66)相关的案例与理论分析,详见刘涛、杨有庆:《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卡斯特“流动空间思想”的当代阐释》,《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2期,第73-78页。 (67)[法]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68)[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0页。 (69)[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