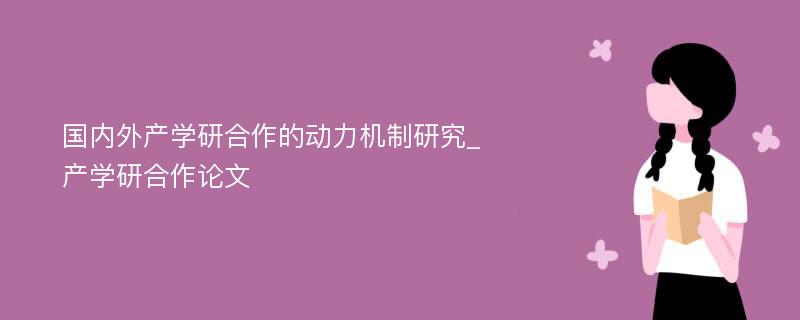
国内外产学研合作动力机制面面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学研论文,国内外论文,机制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系统要正常运行,需要有强大、稳定而持久的动力。系统运行的动力来自于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内在动力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外部动力。产、学、研合作的动力机制是指产业界、高校、科研院所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产学研合作的动力机制。在单一计划经济条件下,产学研合作主要是由产学研外部的国家计划和政府行为来推动的,即使有一些自发的合作,也仅仅是一种补充。高校、产业界、科研院所的经费、设备、材料等都由国家统一调拨,合作与不合作并不威胁着产、学、研各方的生存与发展。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产学研各方如不主动地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不协作,不联合,不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其生存就随时受到威胁,更难谈发展了。因此,一种出自内在(或自身)利益需要的驱动力,促使产学研各方联合起来去承担更大的项目。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内部驱动和外力推动两者往往不是相对立的,在很多情况下,两种推动力是同时起作用,并且相互依存和促进的。有时,是在政府推动下,产学研各方才产生了合作的可能;而有时,政府的支持是以合作各方的实际合作成效为前提给以政策倾斜和扶持的;有时,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先前的产学研各方的合作才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动力机制还涉及到如何解决从共同合作的低级阶段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问题,即如何协调产学研各方的利益和联合体内外的利益关系,通过合作发展上升到新的台阶和新的水平。由此,笔者认为产学研合作的动力机制有三个层次。
一、外力的推动
即政府及有关部门通过组织和实施一系列产学研合作的计划项目,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设立各类“基金”来推动产学研合作。这方面,发达国家已有相当成功的案例。
如美国科学基金会(NSF)自1971年开始,陆续制定了7个促进产学合作的计划,即:“大学工业合作研究计划”、“小企业等价研究计划”、“大学工业在材料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工业与大学在生物技术和高级计算机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等,这些计划实施的宗旨是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国家工业未来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为遇到困难的合作发展雪中送炭,或为成功的合作锦上添花。美国商务部1990年拨款着手组织“先进技术计划”,计划的经费使用原则是,支持那些申请该计划的企业、政府部门的研究单位、大学都按“食物链”的方式集团化,以确保集团内各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密切配合,达到缩短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时间。他们预测计划实施后到2000年,在新材料、新兴电子技术和信息系统、新兴制造技术、新兴生命科学应用4大领域方面可开辟3650亿美元的国内市场,10000亿美元的国际市场。
再如加拿大近年来为促进产学研合作,组织了“优秀中心网络计划”,总投资2.4亿加元,时间为5年,目的是激励开展长期科技发展项目合作。还组织实施“研究伙伴计划”,由工业界和政府各承担一半经费,拨向大学。促进了工业界研究人员和大学、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
还有英国的“科技联合开发计划”,是英国工业界和科技界的联合攻关计划,最初联合开发项目有5项,研究经费1.45亿美元,50%由政府资助,设置该计划的目的是使工业界增加对研究开发项目的投资,帮助工业部门利用研究成果。以贸工部为主推出的“联合计划”,也是一项支持合作研究的计划,政府投资1.94亿英磅。此外,英国还曾于1986年10月,宣布了一项投资4.2亿英磅资助产学研合作的宏伟计划,规定高校科研机构选定并得到企业资助的研究项目,政府将拨给该项目同样数额的支持经费。
从美、英、德、法、澳等国家提出并组织实施产学研合作的计划部门来看,有科技主管部门,也有经济主管部门;计划实施的目标,有的针对科技目标,有的则为经济目标。
我国近几年也设立了各种计划项目,如“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计划”等等,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进程和产学研合作运行机制的形成。
从各国的做法和经验来看,政策法规的制度,对产学研合作起到了强有力的导向作用。美、日、法、德各国在教育法规中均制定有条款,支持产学研合作。如日本的《产业教育振兴法》对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形式、税收、拨款、管理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原西德的《高等学校总法》对高校参与企业间的研究与合作作了原则规定;巴伐利亚州的州法律甚至还具体规定州教育经费的15%用作高校与企业的合作经费。
此外,还通过制定单项的法规,鼓励产学研合作。如美国著名的《莫雷尔赠地学院法案》规定,可将国家拥有的部分财产出售,所得收入用以资助高校与产业界的合作。这种方式被不少国家仿效,如奥地利政府将电力公司所持部分股票转让给私人公司,以所得资金作为“技术基金”,用于支持高校与企业合作研究和开发高技术。法国制定了《高技术莫雷尔法》也属这一类型。德国的科尔政府最近也颁布了类似法令。日本早在1987年就制定了一项《捐赠讲座,捐赠研究部门制度》,即利用民间企业捐资,在国立大学开设《讲座》和设立研究机构。
发达国家还通过科技政策法规激励产学研合作。如美国国会1980年通过的“史蒂文森、威尔德勃法”,该法明确规定,应把技术向工业和商品化转移定为联邦实验室的一项任务。规定实验室必须以经费总额的0.5%用于这项任务。1986年国会通过《联邦技术转移法》,规定许可证、专利出售中的15%提取给发明人,鼓励发明人向企业转让专利成果。1981年日本科技厅和通产省分别制定的“创造性科学技术推进制度”和“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明确规定,通过产、官、学合作,进行创造性研究。日本制定的《官民暂定合作研究制度》、《促进研究交流法》、《关于促进产学研及对国外研究交流有关制度运用的基本方针》等则属于专项激励性法规。
我国除了国家制定了一些促进科技进步的法规外,各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如有的地区对产学研合作项目有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贴息贷款政策、技改贷款政策等,再如有的地区对企业购买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研成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对中试基地的产品在初始几年免收产品税、增值税,还有鼓励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让的政策等。这些政策和法规鼓励高校和研究机构向工业转移科技成果,对产学研合作项目在税收、资金上给以优惠,对科技人员向企业转让专利成果给以奖励,均有利于激发产、学、研合作各方的主动性,有利于调动科技人员为企业服务的积极性。
资金是产学研合作的经济基础,各国政府在这方面均作出了多种尝试和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较稳定的资金渠道。如“风险基金”,即对一些可能产生重大技术突破,但风险大、投资多的研究开发项目,企业又不敢冒此风险投资的,由政府用“风险基金”给以阶段性的资助,或由政府组织资金力量给以支持。这种基金既有助于扶植高新技术发展,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又有利于高校和科研机构充分发挥基础和应用研究的优势。如“匹配资金”是美、英、德、法、澳、加等一些国家在确保产学研合作计划实施时的普遍做法,即对产学研合作的计划项目,由政府出一部分资金、再要求参加合作的企业出一部分资金,一般比例为1∶1。再如“科学基金”也是不少国家的一种共同举措,政府若认为高校或研究机构的某项研究成果有较大的潜在市场价值,即给其一定的资金投入,帮助其完成技术开发和中试研究,促使高新技术成果尽快投入生产、转化为商品。美国的高新技术“孵化器”大都是政府用科学基金资助建立的。
此外,各国还设立了各种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奖金”。如英国政府1987年设立了“教育与工业或商业联合奖”,用于奖励取得成效的大学与公司的联合体。政府下属的各部也设立了各类基金,如“工业种子基金”,用于开展工业应用发展的基础研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设立了三种奖学金鼓励产学研合作,即“研究院学生奖学金”用于奖励大学内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内产学合作有贡献者;“持续教育奖学金”资助大学生在业余时间选修大学与企业共同设置的课程;“产学研究讲学金”用以奖励大学科研人员到企业参与研究或企业技术人员到大学参与课题研究。工业部设立了“教育与企业合作奖”、“高校企业竞赛奖”等,专门奖励大学与企业合作研究有成效的教研室和教师。
日本文部省设立的“学术振兴会基金”、“青年研究员资助金”、“科研费补助金”,其中有一部分专用于资助产官学合作研究项目。各类资金从外部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条件,推动并保证了产学研合作的顺利发展。
二、内部利益的驱动
在单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产业界、高校、科研院所是依靠国家生存的。如产业界,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家规定的计划指标,企业的原材料由国家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生产量、花色品种、产品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因此,企业与企业之间无须协作劳动,也无竞争意识,企业缺乏活力,缺乏对科学技术的需要。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进入了市场,尤如在大海中搏击风浪的船一样,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经受着竞争风浪的冲击。企业如果不能及时地改变产品,适合市场的需要,就有可能被淘汰。因而,许多企业纷纷设置技术开发部组织开发新产品,但他们同时发现,如能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起来,形成综合交叉优势,推进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就有可能缩短产品更新周期,把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推上市场。在竞争中由于企业内在利益的需要,增加了追求技术进步的内在压力和动力。使企业对科技成果、科技人才的渴望与需求大大增加。产学研合作可使企业取得少投资、见效快、获益大的结果,使企业确信走联合发展之路对自身发展有利。如上海交大与上虞风机厂的合作案例就是一个明证。上虞风机厂建厂初期只有2000元投资,7名工人,以90平方米的土地庙为厂房,对风机技术一窍不通。经过与上海交大合作,建立联合体后,到1990年已开发出14个系列新产品,300多个品种规格,实现年产值3000万元,利税600万元。“六五”计划以来,累计生产各类风机、风冷设备17万台(套);与国内同类产品相比,节电20%,噪声低10分贝左右,为国家节电约15亿千瓦时。该厂产品获得省(市)、部(委)重大(优秀)科技成果奖16个项次;获得省、部、国家级优质产品奖的有7个项次,1987年被定为国家二级企业。再如武汉油脂化学厂、洛阳石化研究所、武钢研究所联合开发的新产品“扎制油”,替代了进口产品,成为企业的先导产品之一,创产值近6000万元,利税1800万元。
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后,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主权得到了扩大,增强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它们的风险也增加了,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全靠国家拨款支持了。有相当一部分科研经费(主要是产业相关的应用开发部分)逐步由国家拨款转变为通过市场,从需要科技成果的企事业单位获得。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机构如果不能主动适应社会,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和重大课题,研究机构的生存、科技人员的生计及发展、自身价值的实现都要受到威胁。因此,寻求各方面资金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支持,已成为当前科技界的内在重要动力。即使是列入中央和地方的重大科研开发项目和重点实验室、试验基地的建设项目,也是在普遍利用经济杠杆,通过竞争、实行招标后才能获得。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高校和科研院所也主动寻求企业在资金、生产工艺、生产经营上的支持。如清华大学在70年代后期研制成功的陶瓷刀具,经过10年的改进和应用,证明了这种新材料制成的刀具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开始,清华大学自己生产这种刀具,但规模不大、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亦不高。后与国内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公司(具有研制大型生产设备与流水线的能力)、香港的华晨公司(从事金融、贸易、房地产业务,资金力量雄厚),合资建立了“北京方大高技术陶瓷有限公司”,实现了优势互补,形成了技、工、贸一体化的格局。据1993年预测,根据其生产规模和市场前景,每年可获几亿元以上的效益,合作三方均分别获得各自的利益,再如某通信电气产业集团与某大学合作,使企业新产品增值率由1989年的16%提高到1993年的53%,在合作的基础上又共建了联合研究所,不仅学校按投入股份获得了经济利益,集团还持续从利润中拨款作后续研究开发经费。
社会实践和大量事实证明,市场经济的建立,对产业界、高校、科研院所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压力,促使他们自发地、自觉地走上合作之路,这种合作机制使各合作主体受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利益需要的驱动,在分析各自的长短、利弊的基础上,通过自主选择结成合作伙伴,这比计划经济下的“包办婚姻”或“拉郎配”更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反馈与有效控制
产学研合作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合作,即通过合作,使资源合理配置,达到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目的,且合作各方(包括集体和个人)均可获得各自企求的利益。为了达到有效合作,反馈机制和调控机制是必不可少的;而反馈则是调控的前提。
笔者调研的案例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企业和高校或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始是松散型的合作,合作取得了成功,各方获得了利益,增进了了解和友谊,反馈证明合作是有效的,进而促使双方都前进一步,发展到共同投资、共建实体的紧密型合作。紧密型的合作取得显著成果后,各方尝到甜头,得到了有效的反馈,又促使合作向更高阶段的方向发展。如某厂和某所共建了紧密型合作实体,经过多年的合作,取得了成功经验,反馈结果是有效的,进一步调动了双方合作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双方争取得到国家计委和中科院的支持,共建国家工程研究发展中心,使厂所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形成了科研—小试—模试—中试—半工业化—工业化的完整的成果转化通道,加快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再如某大学和某公司合资共建了一个研究开发机构,合作前期,由于各方较多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究竟研究开发哪些课题的问题认识不一致。学校方从高科技、高起点、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产品市场竞争为出发点,提供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力求取得一批能填补国内空白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而企业方希望能在短期内出成果、出经济效益,尽快收回投资。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影响了合作的顺利发展,但得到信息反馈后,董事会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取得了共识。双方一致认为,高科技课题的拟定必须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与生产、使用单位密切结合并充分利用企业的优势,才能使科技成果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而不是作为样品、产品供人参观。经过充分的交流,双方了解了对方的需要、沟通了思想,在尽可能兼顾双方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了一批工业急需的、能与国际竞争的新产品研究开发项目,利用企业的原材料和学校的科技力量,研究开发出了能替代进口的系列电缆专用新材料。及时准确的反馈导致了有效的协调、控制,使合作继续健康发展,当年获利税15万余元,第二年43万余元,第三年70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