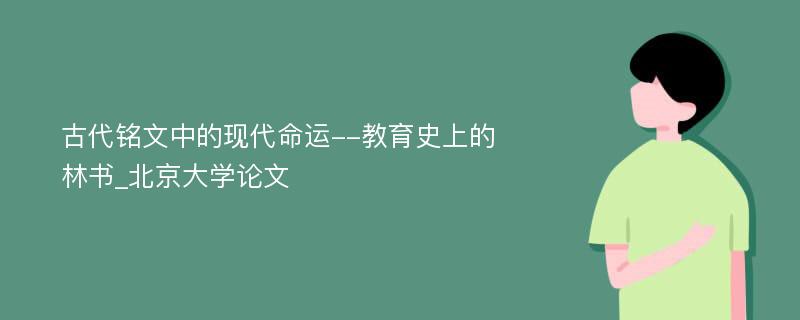
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教育史上的林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古文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早期北大的教员,林纾当初的热情投入,中间的突遭解聘①,后期的积怨成仇,都有深厚的教育史及思想史背景,而不仅仅是偶发事件。本文从“大学教员”的角度,讨论林纾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个人恩怨以及冲突的历史必然性,希望借此凸显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及教育的艰难转型。 一 “至死必伸其说” 离开北大教席六年之后,林纾以一篇备受争议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而“名扬青史”——日后凡谈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靶子。此文的中心论点,第一,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者乃“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第二,反对“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强调“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②。其实,此类不合时宜的卫道之语,进入民国以后,林纾经常提及。被解聘前不久,林纾为北大第一届文科毕业生写序,已在感叹欧风东渐,“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因而导致“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日渐暗淡,呼吁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③。至于1917年在天津《大公报》及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的《论古文之不宜废》,态度依然很好:“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④你谈你的新文化,我爱我的旧道德,本可以相安无事的。即便《新青年》上的《复王敬轩书》有所冒犯,也不是特别严重。直到这篇《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以及蔡元培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出现,林纾与新文化人的冲突才全面升级。因蔡元培的辩驳有理有据,不愠不火,且提出了日后广为传扬的“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⑤,这两封立场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于是格外有名,任何一位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校史或“大学精神”的学者,都不会轻易放过。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五天后,又在同一个报纸刊出“劝孝白话道情”。只见老道挟鼓板上,说唱起《闵子骞芦花故事》,引言部分乃夫子自道: 报界纷纷骂老林,说他泥古不通今。谁知劝孝歌儿出,能尽人间孝子心。咳!倒霉一个蠡叟,替孔子声明,却像犯了十恶大罪;又替伦常辩护,有似定下不赦死刑。我想报界诸君,未必不明白,到此只是不骂骂咧咧,报阑中却没有材料,要是支支节节答应,我倒没有工夫。今定下老主意,拼着一副厚脸皮,两个聋耳朵,以半年工夫,听汝讨战,只挑上免战牌,汝总有没趣时候。⑥ 真是好谐谑的老顽童,值此论战的关键时刻,还有心思开这样的玩笑。民国初年,林纾曾在《平报》上连载《讽谕新乐府》,讥时事,骂政府,痛快淋漓⑦;那时既无人认领,也没人干涉。可这回不一样,林纾明显低估了此次论战的严重性,即便你高挂“免战牌”,其后续影响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消解的。 但到此为止,还是君子之争,无伤大雅。林纾的失策之处在于,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撰写并发表影射小说《荆生》与《妖梦》。如此授人以柄,难怪日后谈及这段历史,林纾明显落了下风——还不是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是新学理直气壮,而是此等指桑骂槐的“小动作”,不入高人眼。小说的事暂且按下不表,先说这位好谐谑的老先生,为何这个时候要跳出来,让正感到寂寞的新文化人有一个鲜活的靶子,可以畅快淋漓地集中火力猛攻? 如此提问,是因当初中国政界、学界及文坛,比林纾位子高、资格老、名气大的还有好多,怎么会轮到林纾来独挑重任,替“旧文化”出头呢?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称: 然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与崇魏晋之章炳麟争;继又持古文,以与倡今文学之胡适争;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殆所谓“俗士可与虑常”者耶?⑧ 这句“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很能说明林纾的性格。文化立场与林纾接近的严复⑨,虽也看不上北大陈、胡“文白合一”的主张,但懒得跟他们争。因为,在他看来: 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⑩ 让见多识广的严复跌破眼镜的是,陈、胡之说并没有如春鸟秋虫自鸣自止,日后竟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论述。虽然判断不准,但严复深藏不露,不与后生争锋,避免成为新文化人的论敌,乃明智之举。至于另一位老友姚永概,也对林纾的“好辩”不以为然,故林纾《惜宜轩文集序》才有“吾友桐城姚君叔节恒以余为任气而好辩”的说法(11)。别人对新文化不以为然,只是腹诽或私下议论,为何独独林纾跳出来叫阵?除了《冷红生传》所说的林纾性格“木强多怒”(12),以及《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所说的“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林纾之“拼我残年,极力卫道”(13),应该还有别的缘故。 这里最为关键的,还是六年前被北大解聘的心结尚未解开。相对于陈、胡等后生小子,他是北大的老前辈,在这所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有其自尊与自信。基于自家的政治及文化立场,林纾对北京大学另有想象与期待。也正因此,当听到社会上不少关于这所大学的风言风语时,林纾自以为有责任替北大“纠偏”,于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公私兼顾,说了一些情绪性的话。这一心情,给蔡元培写第一信时已有表露,而在《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中说得更清楚: 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拾以为言,不无过听,幸公恕之。然尚有关白者:弟近著《蠡叟丛谈》,近亦编白话新乐府,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14) 检讨自己因听信谣传而“孟浪进言”,但辩说初心是爱护北大名誉。这样的申辩,我以为是可以接受的。就连一贯激进的陈独秀,也称林纾的公开道歉了不起,值得佩服(15)。只是林纾撰文时,离开北大只有六年,而不是九年;另外,那篇刊于《公言报》的《致蔡鹤卿书》,收入《畏庐三集》时,改题《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隐约还能见其对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感情。 二 从《荆生》《妖梦》到《续辨奸论》 林、蔡之争,单就《公言报》和《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公开信而言,双方都不失风度,基本上都在说理,即便有挖苦的味道,仍相对委婉,给对方留足了面子(16)。但小说《荆生》《妖梦》就不一样了(17),明显带人身攻击。尤其不智的是,林纾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你可以说“好谐谑”乃其天性,再加上小说既然“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自然没什么好话;但辩称《蠡叟丛谈》的文字“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那是说不过去的。《荆生》里的“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指胡适,不必考证,当初的读者一眼就能认出,这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至于《妖梦》里被“罗睺罗阿修罗王”全部吃掉的白话学堂的人,包括那位“谦谦一书生也”、见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毁谤伦常、提倡白话,竟然“点首称赞不已”的“校长元绪”,不是蔡元培又能是谁呢? 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蔡元培复张厚载函,并附有张的来函,后者对林纾影射蔡元培一事并未隐瞒: 《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不甚介意也。 蔡元培怎么能不介意呢?如此北大学生,挑拨师长是非,且在报上传播诸多不利于学校的风言风语,说轻了也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报记者”风格。校方将其开除,处罚虽稍重,却也不无道理(18)。至于蔡元培的回信,显得很有风度: 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19) 无论新派、老派,读这两段文字,都会觉得林纾骂人不对,蔡元培修养很好。这一局,林纾输得很惨。 至于传闻林纾写《荆生》是在怂恿手握兵权的弟子徐树铮动用武力来消灭新文化人,目前没有找到任何旁证材料,大概属于新文化人的“哀兵之计”。张厚载说的没错,那只是林纾一时兴起的“游戏笔墨”,偶有杀伐之声,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想想林纾本人自幼学剑,且“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20),再加上撰有记录闽中武林轶事的《技击余闻》,还有《剑腥录》中吹嘘邴仲光如何仗剑行侠,这“伟丈夫”实为林纾的自我期许(21)。只是三人成虎,日后史家也懒得仔细追究,林纾“勾结军阀铲除异己”的罪名,就这样被派定了。 林纾在新旧文化论战中发表“游戏笔墨”的《荆生》与《妖梦》,确实不太妥当,起码是有失大家风度。可这也说不上多大的罪过。新文化人因没有对手,太寂寞了,演起双簧戏,在《新青年》上刊出钱玄同代拟的王敬轩来信,以及刘半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答王敬轩书》,不也是一种假托与戏弄?这与林纾写小说骂陈、胡,不过是五十与百步的差别。 在《新青年》与《学衡》的对抗中,后者批评前者“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22)。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变革年代,很难真的像胡先骕所设想的,“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学衡》上的文章,论及新文化时,同样充满怒气与怨气;但胡君最后提出的“勿谩骂”戒律,还是发人深省(23)。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同人中,对“骂人”公开表示不妥的,只有胡适一人(24)。而且,就连胡适本人,后来也承认陈独秀之“不容他人之匡正”自有其道理。在叙述文学革命进程的《逼上梁山》中,胡适引述了他与陈独秀关于是否允许批评的通信,然后加了个按语:“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25)只讲运动效果,不问手段是否正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此百无禁忌的“革命”,不无深入反省的必要(26)。 林纾致蔡元培信,前一封开篇叙旧,后一封又有“与公交好二十年”的说法(27)。这可不是胡乱攀附,读蔡元培1901年下半年日记,五处提及与林纾同席或晤谈(28);此前两年,日记中甚至有:“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入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惟《红楼梦》有此境耳。”(29)早年友人,日后立场迥异,“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这本是很可钦佩的态度。论战激烈时,双方都控制不住自己“正义的怒火”,难免出言不逊,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时隔多年,林纾还用刻毒的语言来辱骂蔡元培,这就有点太过分了。我指的是林纾本人特别看重的、撰于1923年春的《续辨奸论》(30)。 《续辨奸论》是骂新文化人的,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所谓“用最传统的语汇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响应者统统斥为‘巨奸’”;“直到此时,林纾对那些鼓吹‘新文化’的‘五四’新人物,依然是满怀着憎恶和反感”(31),说得没错,只是不够贴切。因为,这篇文章直接针对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章开篇,先痛斥“巨奸而冒为国学大师”,这可不是无的放矢。请看下面进一步的铺陈: 彼具其陶诞突盗之性,适生于乱世。无学术足以使人归仰,则嗾其死党,群力褒拔,拥之讲席,出其谩譠之力,侧媚无识之学子。礼别男女,彼则力溃其防,使之媟嫚为乐;学源经史,彼则盛言其旧,使之离叛于道;校严考试,彼则废置其事,使之遨放自如。少年苦检绳,今一一轶乎范围之外,而又坐享太学之名,孰则不起而拥戴之者?呜呼!吾国四千余年之文化教泽,彼乃以数年烬之。 如此不学无术而又占据高位,能够号令学界,而使得“吾国四千余年之文化教泽”毁于一旦的,可不是一般的学者,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都不够格。尤其是使得太学废置考试、学生遨放自如、男女媟嫚为乐的,只能是同意招收女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如果说这还有点虚,下面这两句用典,可是彻底坐实了林纾的矛头所向: 鱼朝恩之判国子,尚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如;贾似道以去要君,尚有文采,彼乃椎鲁而不学。来为祸而去为福,人人知之,余尚何辩也?其辩为吾道辩也。(32) 唐代太监鱼朝恩(722-770)安史之乱后随唐玄宗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重用。永泰年间,代宗加封鱼朝恩判国子监事,兼光禄、鸿胪、礼宾等职,进封郑国公。朝恩既已贵显,乃学讲经为文,执《周易》升高座。宋理宗时权臣贾似道(1213-1275)多次以弃官相要挟,逼迫度宗不断给他封官加爵。贾除撰有《悦生堂随钞》及《促织经》外,还是个很有造诣的艺术鉴赏家。这两个都不算僻典,林纾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大概都能读懂。以判国子监(国子监最高长官)来影射北京大学校长,这很容易理解;而更贴切的“今典”是1922年年底及1923年初,蔡元培一直与北京政府抗争,1923年1月17日更是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愤而辞职并立即离京。此事引起很大风波,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可谓路人皆知。林纾可以不同意蔡元培的立场,但嘲笑他没有学问,且辞职是为了加官晋爵,这明显不入流。因为,按照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及学术标准,这位前清翰林、留学德国多年、曾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北大校长,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 这篇《续辨奸论》当初并没有引起关注,若蔡元培看了,必定还是那句话:“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林纾空有一腔卫道热情,可惜不太会说理,再加上喜欢骂人(33),那就更是落了下风。用这种办法,不但打不倒蔡元培,反过来还伤害了自身。 三 “修身”抑或“古文辞” 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蔡元培反驳林纾关于北大主张“覆孔孟,铲伦常”的指责,称教员“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接下来,蔡校长软中带硬,反唇相讥: 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因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34) 这里的各学校,主要指向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授课经历。 林纾之“主大学讲席”,分为前后两段: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至宣统元年十二月(1906年9月-1910年1月)任预科及师范馆“经学教习”,宣统二年正月至民国二年阴历三月(1910年2月-1913年4月)任分科大学“经文科教习”。不是林纾转行,而是大学堂在发展,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后,酝酿已久的分科大学方才得以成立。其中文科大学设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两门,林纾于是得以专心讲授古文。只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林纾便被正值风雨飘摇的北京大学解聘了。 主大学讲席七八年间,林纾有很多著述,但与教学密切相关的,主要是1916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修身讲义》,以及1913年6月起在《平报》连载,1916年由北京都门印书局刊行的《春觉斋论文》(35)。在现代大学教书,必然受制于学堂章程及课程设计,不是自家擅长什么就讲什么。这两种与职务密切相关的著述,毫无疑问,前者对应的是预科及师范馆的伦理课,后者则属于大学部的中国文学课。有趣的是,讲授时间在后的“论文”,发表却在《修身讲义》之前,隐约可见世人评价以及作者的自我定位。 林纾所编《修身讲义》分上下册,封面及书眉均有“师范学堂、中学校”字样,标明适用范围。撰于1915年的序言,对该书的编纂宗旨及讲授效果有完整的记述: 南皮张文襄公长学部时,令各校以儒先之言为广义,逐条阐发,以示学生。时余适应李公柳溪之聘,主大学预科及师范班讲席,取夏峰先生《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诠释讲解,久之积而成帙。迨业毕,遂移文科讲古文辞,不再任此矣。窃谓集英俊之少年,与言陈旧之道学,闻者必倦。而讲台之上,亦恹恹以晷刻为长。践此席者,多不终而去。自余主讲三年,听者似无倦容。一日钟动罢讲,前席数人起而留余续讲。然则余之所言,果不令之生倦邪?后此又试之实业高等学堂,又试之五城中学堂,皆然。似乎此帙为可存矣。(36) 第一,此讲义除在京师大学堂预科及师范班讲授外,还在实业高等学堂、五城中学堂等使用;第二,作者认同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1584-1675)的讲学宗旨,同样“朱陆并举,以有益于身心性命者为宗”;第三,具体讲授时,选择孙纂《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逐条阐发,以示学生”;第四,因讲者对先贤之言体会深刻,表达生动,教学效果极佳,因此,才有必要在结束讲课多年后,刊行此讲义。 “伦理”作为新式学堂的必修课,小学、中学(及师范)、大学均有开设。查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无论政科、艺科还是预备科,每年均必须开设伦理课,其教学目标是:“考求三代汉唐以来诸贤名理,宋元明国朝学案,暨外国名人言行,务以周知实践为归。”(37)具体到林纾任教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同样是伦理课排第一,不过四年教学任务略有分工:第一年“考中国名人言行”,第二年“考外国名人言行”,第三年“考历代学案,本朝圣训,以周知实践为主”,第四年“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38)。这只是纸面文章,查当年坊间所刊各种伦理或修身的讲义,没有如此细致划分的。倒是林纾与蔡元培各自所编“修身讲义”在宗旨及体例上的巨大差异,值得认真辨析。 1910年2月商务印书馆刊行陆费逵所编“师范讲义”之《修身讲义》,版权页上有“山阴蔡元培编辑”之《中学修身教[科书]》的广告:“此书原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要旨,参取东西伦理学大家最新之学说,自修己,推及家族、社会、国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说理精透,行文简亮,毫无枯寂干燥之弊,非寻常修身书所可比。”此时书尚未刊,两年后商务印书馆正式推出时,曾在1912年6月22日《民立报》刊登广告,措辞多有修订,删去了“自修己,推及家族、社会、国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以及“毫无枯寂干燥之弊,非寻常修身书所可比”,增加了“本书为山阴蔡先生留学德国时所著”,目的是说明此书为何能“熔中外于一冶”。至于结尾处的“出版后大受学界欢迎,原书分订五册,今重行修订,合订一册”,终于让我们明白,此乃旧书重刊。 这就说到了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编纂及出版过程。因作者曾因言论大胆而被张之洞斥为“谬妄”,商务印书馆为稳妥起见,此书前三册1907年12月出版时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1908年3月刊行后两册,方才称“蔡振编”(39)。民国成立,蔡元培成了首任教育总长,1912年的订正本于是堂堂正正地标明“山阴蔡元培编辑”(40)。问题在于,蔡元培1907年6月10日随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启程赴德,此前三天,张元济已有信称:“修身书第一册稿本已收到,感谢无已。未去国以前,如有续成者,仍望见寄为祷。”(41)考虑到此书不久即公开刊行,其撰写与作者之“留学德国”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对比此前蒋智由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1906年)或此后陆费逵所编《修身讲义》(1910年),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最大特点在下篇。上篇五章分论“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属于规定动作,那时的修身教科书大都如此结构(42);而下篇除“绪论”及“结论”外,第二章“良心论”,第三章“理想论”,第四章“本务论”,第五章“德论”,很能显示蔡元培“熔中外于一冶”的学识与关怀。 相对于蔡书的学有本原,兼及中外,林纾的《修身讲义》仅以孙奇逢《理学宗传》为蓝本,引一句格言或一段妙语,再以“纾谨按”或“林纾曰”的形式加以发挥,明显落后多了。但有一点,林纾这么做,符合当年朝廷公布的章程,属于中规中矩。查1903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在第一类学科第一年的“人伦道德”课下面有注:“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明显简要者。”(43)介绍过三类学科各三年的修身课程,章程中还有总论性质的一段话: 外国高等学堂均有伦理一科,其讲授之书名伦理学,其书内亦有实践人伦道德字样,其宗旨亦是勉人为善,而其解说伦理与中国不尽相同。中国学堂讲此科者,必须指定一书,阐发此理,不能无所附丽,以致泛滥无归。查“列朝学案”等书,乃理学诸儒之言论行实,皆是宗法孔孟,纯粹谨严;讲人伦道德者自以此书为最善。惟止宜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其说理又明显简要、中正和平者为学生解说,兼讲本书中诸儒本传之躬行实事以资模楷。若其中精深微渺者,可从缓讲;俟入大学堂后,其愿习理学专门者自行研究。又或有议论过高,于古人动加訾议,以及各分门户互相攻驳者,可置不讲。讲授者尤当发明人伦道德为各种学科根本,须臾不可离之故。(44) 同是“勉人为善”,“发明人伦道德”,因中外情势有异,章程要求修身课的教习重在阐发宗法孔孟且纯粹谨严的“理学诸儒之言论”。为了防止“无所附丽,以致泛滥无归”,最好是“指定一书,阐发此理”。而这正是林纾所做的——选择“列朝学案”性质的《理学宗传》,讲授时注重“切于身心日用”。局限于传统的“修齐治平”,仍在理学框架中打转,与蔡元培之以“修己”、“家族”、“社会”、“国家”等来展开论述,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这不等于说,谨依章程、固守传统的林纾,其课堂就一定不精彩。说到底,这种中学、师范或预科的“政治课”,没必要有那么高深的学理——连“章程”都称“其中精深微渺者可从缓讲”——关键在于养成立场与趣味。可就像林纾说的,“集英俊之少年,与言陈旧之道学,闻者必倦”,这门课其实是很不好教的。而林纾竟然有本事,让听众欲罢不能,他到底是怎么教的,值得仔细观察。 谈及宋儒张载(1020-1077)的“挤人者人挤之,侮人者人侮之”,林纾的《修身讲义》有曰:“时彦言平等自由,纾始闻之,以为说近于释迦、庄周之言。既而思之,吾人亦万万不能离此而立。平等宜作敬人说,自由宜作不侵犯同类说。……以守旧人发斯义,诸君子或不齿冷我也。”(45)很明显,谈论“自由”、“平等”等新词,非林纾所长,连他自己都必须自我解嘲。整本《修身讲义》,极少引用新词,更不要说新学说了,一是不懂,二是不屑。于是,林纾调转方向,不纠缠“学理”,而直奔“文章”而去。如辨析程颢(1032-1085)的“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林纾将其掰开来,分两段讲,前半不引,请看后半: 至学问一道,尤非骄人之具,人人知之矣。纾则尤谓学问与武技同其危险。武技之有少林,可谓精极,然张三峰则尤称为内家。以外家之术,遇内家,往往而败。故善兵者,不言兵,正防高出于己者,适足为人所踣。唯学亦然。外国之名为普通,即中国之所云博也。既名为博,则当无所不知,犹之然灯于高竿之上,持之四照,以为足以遍烛。然宁无暗陬所不必至之地,伏弩骤发,亦不胜防。道在博其学,弗博其名。名者万矢之所注也。而矢来有响,则能备;矢来无响,则又何从而备之?贵在重闭而已。重闭之云,即不骄之谓。不骄则遇人能容。须知学士之大病痛,是当面揭人之短。人家言语谬误,从而正之,居心岂不忠厚?然亦须有礼,始不招怨。(46) 接下来,林纾讲某人因逞能而得罪了强人,落得悲惨结局,以此来说明有学问的人须学会藏拙。如此讲述,没什么高深学理,但“切于身心日用”。更重要的是,道理虽然简单,讲述却很生动,课堂效果肯定不错。某种意义上,这与作者译著小说的经验不无关系。至于讲“学问”而引入“武技”,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此前三年林纾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笔记体小说《技击余闻》(47)。 与此类似的以人情练达且讲述生动著称者,还可举出畅谈朱熹的“直须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治病救火,岂可悠悠岁月”,以及辨析明代理学家薛瑄的“将圣贤言语作一场说话[话说],学者之通病[患]”(48)。可惜校订及考证均非林纾所长,书中不时出现若干讹误。 如果说蔡书的特点是“说理精透”,那么林著则以“讲述生动”见长。1915年秋,林纾写信给五儿林璐,教诲他“不把有用之光阴虚掷”,除“每日功课刻刻留意”外,还可读自家所编《修身讲义》:“《修身讲义》时时披览,此中不惟可以修身,而且可学文法也。”(49)这是个很有趣的提醒。如此“阅读秘诀”,或许正是作者的潜意识——发挥自家“古文辞”方面的特长,将“政治课”讲成了“语文课”。 在成为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习之前,作为该校预科及师范馆的经学教员,林纾有责任讲好“修身”课。西洋伦理非其所长,宋明理学也无专研,林纾的诀窍是,以讲授古文的方法来讲修身,沉潜把玩,妙趣横生,效果很不错。若不考虑教育宗旨,单从课堂效果着眼,将“修身课”讲成了“古文辞”,未尝不是一条讨巧的路。更何况,林纾对古文确有体会,娓娓道来,犹如一则则浅白但生动有趣的短文,难怪“听者似无倦容”。时过境迁,绝大部分修身教科书早就被淘汰了,反而是林纾的《修身讲义》值得一读,这实在是个奇妙的错位。 说到讲授古文,比起《修身讲义》更为本色当行的,无疑是林纾离开北大后不到两个月便开始在《平报》上连载的《春觉生论文》(1916年都门印书局刊行时改题《春觉斋论文》),以及第二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韩柳文研究法》。按时间推算,这两种林纾最重要的“专著”,应该是其在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教书时的讲义,或曰“科研成果”。正是此二书的得与失,让我们明白时代转型中林纾的困境。 四 传统文人与现代学堂 当初新文化运动兴起,旧派人物颇多不以为然,但挺身而出与之直接对抗的,却是前北大教员林纾。按世俗观念,这位前清举人、以翻译西洋小说起家的老先生,作为旧派人物的代表,分量其实是不够的(50)。你想代表旧派发言,可人家旧派并不怎么领情。林纾的这一尴尬处境,陈独秀早就说透:“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51)既然如此,林纾为何还要强出头呢? 除了上面提及的他与北大的“离合悲欢”,还有就是林纾对于自家古文水平的过分自信。1906-1913年任大学堂教习期间,除了结交名士,出版译作与自家小说,林纾在古文教学及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1907年应张元济、高梦旦之邀,编选十卷本的《中学国文读本》。这套1908-1910年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的古文读本,由当下(清朝)上溯周秦汉魏,林纾不仅自选篇目,逐文评批,每卷前还有序言(如《六朝文序》《唐文序》《宋文序》等)。类似的选本及评点,还有《评选船山史论》(1910)、《左孟庄骚精华录》(1913)、《〈古文辞类纂〉选本》(1918-1921)、《左传撷华》(1921)、《庄子浅说》(1923)、《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共十五册十六种,1924),以上各书,都是由当年在出版界坐头把交椅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在林纾为“力延古文之一线”而作的四种努力中(52),比起亲自写作(如《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理论撰述(《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文微》)、招生授业(组织古文讲习会等)来,这选文及评点或许更值得注意。此等事务,琐琐碎碎,卑之无甚高论,但发行量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不可小觑。 大概是互相关联,评点家林纾刊行自家所撰古文,销路也很好。1910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畏庐文集》,选历年所作古文109篇,据前京师大学堂及北大同事姚永概1916年称:“畏庐名重当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53)到了1924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畏庐三集》,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为其撰序,调门进一步提升:“畏庐之文,每一集出,行销以万计。”(54)为人作序,总是多说好话;但林纾的古文集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这应该不会假。正是因为有很好的销售业绩,商务印书馆才会在刊行林译小说的同时,不断邀林纾编选及评点古文。 无论出版文集还是选评古文,均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就难怪林纾充满自信。所谓归有光以后古文第一人的“自我期许”(55),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同是闽籍老乡,年岁相仿且志趣相投的严复(56),对林纾的古文评价就很高。《严复集》中收录二诗,《题林畏庐晋安耆年会图》曰:“纾也壮日气食牛,上追西汉攡文藻。”《赠林畏庐》则是:“尽有高词媲汉始,更搜重译续虞初。”(57)后者乃严复为预祝林纾七十寿诞而撰,成于1921年9月27日,一个月后严复病逝于福州(58)。不仅严复这么看,史家钱基博对林纾的古文也有肯定的评价:“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盖中国有文章以来,未有用以作长篇言情小说者,有之,自林纾《茶花女》始也。”(59)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两句评语,可是“一字千钧”。不过,这里所说的“文章”,特指古文——准确说,应该是文言文。 出书多,在社会上影响大,不等于就学问渊深,文章精美。在专门家眼中,即便限制在唐宋古文派,林纾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同为福建壬午科举人、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同事且多有唱和的陈衍,便喜欢嘲笑林纾没学问。1932年阴历除夕,陈衍与后辈钱锺书谈近世学人之不能“根柢经史”,单靠“道听途说,东涂西抹”,举的例子便是严复、林纾与冒鹤亭。严复是留学生,“半路出家,未宜苛论”;而“琴南一代宗匠”,学问竟如此空疏,实在不能原谅。据陈衍称,林纾“任京师大学教习时,谬误百出”,“予先后为遮丑掩羞,不知多少”(60)。这还只是私下议论,无伤大雅;章太炎不一样,公开撰文抨击。1910年,流亡日本的革命家章太炎在《学林》第二册发表《与人论文书》,其中论及严、林文章: 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61) 在尊崇魏晋文章的章太炎看来,林纾与严复的国学修养及古文写作,水平都不高,起码在同代人中不算优秀。这里有文派之争,牵涉章氏的学术立场;除此之外,也与太炎先生好作高论有关。 问题在于,辛亥革命成功,章太炎的声誉如日中天,弟子们纷纷进京任教。相形之下,历来对喜欢在文章中卖弄学问的“汉学”不以为然的林纾(62),则显得日渐没落。在《与姚叔节书》中,林纾大谈如何“不容于大学”,尤其对“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钜子”大加讨伐(63)。几年后,在一则公开发表的书札中,林纾称此“好用奇字,袭取子书断句,以震炫愚昧之目”的“庸妄钜子”,其弟子沈君在大学堂讲《说文》(64),这等于是不点名的点名。很明显,林纾是将自己的去职直接归咎于章太炎此前的批评。不能说这种怨怼没有任何道理(65),但只是埋怨章太炎,将此学术史上的大转折解读为个人恩怨,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在林纾看来,前有“庸妄钜子”章太炎的恶毒攻击,后有“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的何燏时校长的昏庸裁断,自己才会被北京大学解聘。可实际上,导致林纾等老派人士去职的,是整个大的政治环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说白了,林纾讲授古文的特长,如今已“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某种意义上,这一教育制度变革及思想文化演进的过程,林纾还曾积极参与其中。 1897年年底由友人魏瀚出资在福州刻版印行的《闽中新乐府》,是林纾的第一部诗集,内收新乐府诗29题32首,属于那个时代常见的提倡变法维新、救国自强的启蒙读物。其中多首涉及教育制度的反省,如《村先生》《兴女学》《知名士》等。《破蓝衫》之嘲笑八股文与科举制,尤其值得注意:“吁嗟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此诗篇以“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结束(66),显示了林纾的见识。虽系一介书生,且以教书及写作为业,但林纾很清楚国家的命运在于变革学制。 甲午战败,改革教育制度的呼声日高。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广开学校(67);同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变通书院(68)。一反省新式学堂之得失,一提倡旧式书院的改造,共同目标是培养具备“真才实学”、能够“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具体策略是加强“天算格致农务兵事”等西学课程,而摒弃“溺志词章”这一中国旧式教育的通病。日后的创建京师大学堂等,大致依此路径。 改革旧的学制,引进西式学堂,这是那个时代开明人士(包含封疆大吏)的最大共识。因此,即便康梁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照样成立,学制变革仍在推进。这一历史潮流,毫无疑问,林纾是认可的。在1907年所撰《〈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有这么一段: 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今日学堂,几遍十八省,试问商业学堂有几也?农业学堂有几也?工业学堂有几也?医业学堂有几也?朝廷之取士,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则已视实业为贱品。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不能不随风气而趋。(69) 中间省略部分,是论证过去读书人苦攻八股,学的是宰相之业;如今八股消停,则转而专力于法政,“法政又近宰相之实业矣”。在林纾看来,只有学生们愿意攻读实业,才是国家之福。因此,“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70)。此文很有时代气息,也很能显示林纾的眼界与胸襟,故曾被郑振铎选入1937年生活书店版《晚清文选》。 可也正因为新式学堂注重“实业教育”,这一时代潮流,促使林纾等传统文人日渐边缘化。因张之洞、张百熙等人的努力,“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终于得到了部分落实,大学堂里设立“中国文学”科目乃至学门。查1903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范本。此前讲授词章之学,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诗文一事,虽说“诵读既多,必然能作”;但新式学堂排斥吟诗作文,将文学教育的重任主要交给了“文学史”,这已经注定了林纾等古文家在现代大学迅速没落的命运(71)。 现代大学设置很多专业,“中国文学”只是其中一课程、科目或学门;即便专研“中国文学”,也并非只学“古文”,还有诗词、小说、戏曲乃至外国文学等可供选择。退一万步,特别青睐“古文”者,也不一定对林纾的教学方式感兴趣。这就说到了林纾等桐城文家教学的长与短——长于体味、鉴赏、模仿,而短于视野、考辨、阐释。无论选本及评点,还是《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文微》等,林纾编撰的诸多涉及古文的书籍,均有此特点。不要说版本及考证,单是文章源流的辨析,陈衍的功力也在林纾之上——《石遗室论文》中若干重要论述,经由弟子陈柱《中国散文史》的传播,日后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印记。林纾《春觉斋论文》的精彩之处,在于“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等,至于“流别论”则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正如舒芜所说,林著“对散文技巧的研求,一些个别论点,今天也还有可以借鉴的”,但“形式主义的烦琐,马二先生式的鄙陋,例如津津乐道归有光、姚鼐的圈点之妙之类”,实在不敢恭维(72)。这半个世纪前的评述,虽稍嫌苛刻,但大致判断准确。与此相近的,还有黄霖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评价:“林纾的文论著作,虽有综合前人之功,条分缕析之力和不乏真知灼见之处,终因缺乏一种恢弘气象和新的理论开拓,故难免给人以陈腐、琐碎的感觉。”(73) 这不全然是才气问题,首先是工作目标的设定。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时,在序言中含沙射影,批驳那些主张“古文宜从小学入手”或作文“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者(暗讽章太炎及梁启超),而后极力推荐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下面这段话,前半指向姚鼐,后半更像是自我表白: 鄙意总集之选,颇不易易,必其人能文,深知文中之甘苦,而又能言其甘苦者。则每篇之上,所点醒处,均古人之脉络筋节;或断或续,或伏或应,一经指示,读者豁然。(74) 虽说熟读韩文(75),沉潜把玩,深思有得;而真正作文时,林纾追摹的是桐城文派。在林纾眼中,桐城古文“取径端而立言正”,而“天下文章,务衷于正轨”(76)。严整、干净、不枝蔓、无芜辞,这确实是桐城及林纾文章的特点,可过分循规蹈矩的结果是文章干瘪,缺乏生气。若连姚鼐装点门面的“考据”,以及曾国藩竭力引进的“经济”都不要了,只剩下那并不怎么高明的“义理”,和若干琐琐碎碎的技法(“辞章”),这古文是没有出路的。 要说学作古文,林纾不避琐碎,肯说多余话,循循善诱,确实能使“读者豁然”。虽说无法深入堂奥,但毕竟引路有功,这或许是教书匠的宿命。1916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浅深递进国文读本》,很能显示林纾的特点——此书精选历代古文78篇,依原题重作一浅一深两篇,供学习参考用。可以这么说,教人学写古文,林纾很用心,也很有一套。问题在于,科举制度已经废除,而大学里讲授中国文辞的,重学养而轻技巧,不再以模拟写作为目标。在新的教学体系中,林纾的才华派不上用场。对比早年北大的四部文学史讲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除了学派(前两者推崇六朝,后两者独尊唐宋),还有就是: 前者学养丰厚,后者体会深入,本该各有千秋。可为何前者一路凯歌,而后者兵败如山倒?除了时局的变迁、人事的集合,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六朝的文章趣味与其时刚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比较容易会通;一是朴学家的思路与作为大学课程兼著述体例的“文学史”比较容易契合。因而,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史学”,走的基本上是刘、黄而不是林、姚的路子。(77) 专业化教育的大趋势,使得即便讲授“中国文学”,注重的也是文学史的演进脉络,而不是具体的写作技巧。这么一来,大学堂里的位置,“文章家”必定逐渐被“学问家”所取代,这对林纾等古文家的打击是致命的。 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刊行《文科大辞典》,林纾为其撰序言,对借古文存国故仍有强烈的自信: 综言之,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席,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78) 可当有一天,人家告诉你,新学、旧学确实可以并存,古文也很有价值,只是不能像你那么教,应在“文学史”的框架中重新定位并阐释。现代大学所需要的,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而非趣味高雅的文人——借用传统术语,那就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开始从“文苑传”向“儒林传”转。如此大趋势,对于林纾等传统文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还有一点,时代变了,大学选教员,不是看古文水平高低,也不管你尊桐城还是崇六朝,关键是看“学术背景”。林纾的去职与北大的转型,二者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系。沈尹默谈及何燏时、胡仁源两任校长陆续引进朱希祖、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章门弟子,理由是“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79)。老师声誉高,这固然好;但弟子们都是“陆续从日本回国”,这一点也很重要。稍为排列一下:朱希祖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学专业;马裕藻1905年公派赴日,先入早稻田大学,后转东京帝国大学;沈兼士1905年自费东渡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同时拜入章太炎门下;黄侃1905年赴日避难、游学,师从正在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的章太炎;钱玄同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1908年与鲁迅、黄侃等师从章太炎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沈尹默1905年与其三弟兼士一起自费赴日,游学时间不长,也未正式注册(80)。如此履历,对于浙江老乡、同样留日的前后两任校长来说(81),是很有诱惑力的。 其实,林纾很敏感,也了解时代风气的变化。人前捍卫古文尊严,似乎很自信;私下里教孩儿读书,也都充满困惑与挣扎。熟悉近代史事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两个细节:1924年9月5日,林纾为擅长古文的四子林琮立下遗训:“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宝贵”;10月8日病情恶化,林纾以食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82)第二天,一代文豪林纾与世长辞。 可现实生活中的林纾,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不断叮嘱孩儿学洋文。先看林纾如何提醒古文根基甚好的四儿林琮:“学生出洋,只有学坏,不能有益其性情,醇养其道德。然方今觅食,不由出洋进身,几于无可谋生。余为尔操心至矣。”(83)再看林纾给五儿林璐的信: 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84) 正如周作人所说,家训这种文体,“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诚实的”,因为“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不能唱高调,要近人情,单是“思想通达”还不够,还得“计算利害”(85)。个人可以坚持,但为了孩儿日后的生存,林纾竞要求他“七成之功治洋文”,如此委曲求全,对于这位不可一世的古文家来说,内心无疑十分悲苦。 从事后诸葛亮的立场,当初林纾与新文化人争得死去活来时,古文的地位实已岌岌可危,甚至到了一推就倒的地步。1898年开启的创办西式学堂热潮(重“实学”而轻“虚文”)、1903年《大学堂章程》所制定的文学教育方针(以“文学史”取代“文章源流”)、以及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度(“文章”不再是读书人谋生的基本技能)——这一系列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已经注定了古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只不过古文可以“载道”的最后一丝荣光,被新文化人毫不留情地摧毁,才使得林纾痛心疾首。 清末的开民智、办学堂,引领了整个转型时代的风气。林纾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且积极投身其中。但历史大潮汹涌,不久便转过来,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立足的根基。这种在新旧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两难处境,包括其犹豫、忧伤与困惑,以及日渐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某种意义上,转型时代读书人的心境、学养与情怀,比起此前此后的“政治正确”来,更为真挚,也更可爱。 最后,还是得回到林纾念兹在兹的古文的现代命运。世人谈及林纾之捍卫古文,或彻底贬斥,或极力表彰。但有趣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林纾在文学史上的真正贡献,不在桐城古文的复兴,而是西洋小说的引进。这一点,林纾去世一个月后,新文化人郑振铎撰写了初刊《小说月报》第15卷11号的《林琴南先生》,就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九十年,“林译小说研究”始终是中外学界的热门话题,且不时有精彩论述出现(86)。这里换一个角度,谈论林纾翻译及创作小说的经验,如何反过来促成了古文的自我改造与更新。 桐城名家马其昶为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作序,开篇即称道:“今之治古文者稀矣,畏庐先生最推为老宿。其传译稗官杂说遍天下,顾其所自为者,则矜慎敛遏,一根诸性情。劬学不倦,其于史汉及唐宋大家文,诵之数十年,说其义,玩其辞,醰醰乎其有味也。”(87)表面上好话说尽,可你要是熟悉桐城文家的思路及语汇,这表扬之中(从“传译稗官杂说”入手),其实包含着某种贬抑。马序无意中说出了林纾的古文为何名气那么大,一是凭借翻译小说积累的声望,二是用小说家的趣味来经营古文。从传统古文家的眼光看,林纾的古文并不纯粹;可正是这种夹杂着小说笔调,使得林纾的古文别有洞天。 除了众所周知的林译小说,林纾还自撰长篇小说五种——《剑腥录》(1913)、《金陵秋》(1914)、《劫外昙花》(1915)、《冤海灵光》(1915)、《巾帼阳秋》(1917),以及短篇小说(笔记)集五种——《践卓翁小说》(1913-1917)、《技击余闻》(1914)、《铁笛亭琐记》(1916)、《畏庐笔记》(1917)、《蠡叟丛谈》(1920)。这些创作,除了自身业绩,更是大大拓展了古文的表现空间。这一点,先贤早有论述。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表扬林译小说,称“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88);1932年,鲁迅给增田涉写信,谈及早年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背景:“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89)到了1964年初刊《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的《林纾的翻译》,钱锺书对林纾的“古文”做了精彩的辨析,称若严格遵守桐城古文的清规戒律,根本就无法翻译;林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90) 这段关于林译小说语言的描述,同样适应于其自撰的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单从文体角度看,用古文译介外国小说,林纾的努力越成功,古文的危机就越大。因为,公众养成了阅读外国小说的兴趣后,离古文只能越来越远。这一过程,说得不好听,乃“引狼入室”。 但如果跳出独尊古文的褊狭趣味,就文章论文章,林纾的译述,确实是大大拓展了“古文”(严格上说是“文言文”)的表现能力。某种意义上,这与他看不起的梁启超等人的“报章文体”,可谓异曲同工。若着眼于清末民初语言及文体变革的大潮,由幽深的文言到平实的白话之间,有个过渡形态,那就是浅白文言;而由洁净的古文到芜杂的小说之间,也有个简易桥梁,那便是林纾那些一身二任、徘徊于雅俗之间的译述小说。若承认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非简单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91),而是必须兼及文章与学术(92),纵横小说与散文,杂糅口语、古文、方言、欧化语等,“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93),那么,林纾对于现代白话文的意义,便不只是扮演反对者的角色,而是有某些实实在在的贡献。 2015年11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①参见陈平原《林纾与北京大学的离合悲欢》,《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 ②《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畏庐三集》第26页上至28页上,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③林纾:《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畏庐续集》第20页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④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1917年2月1日《大公报》及1917年2月8日《民国日报》。 ⑤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闵子骞芦花故事》,初刊1919年4月23日《公言报》,见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第23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⑦以初刊《平报》1913年9月14日“讽谕新乐府”栏之《共和实在好》为例:“共和实在好,人伦道德一起扫。入手去了孔先生,五教扑地四维倒。四维五教不必言,但说造反尤专门。问君造反为何事,似诉平生不得志。乘兵一拥巨款来,百万资财可立致。……男也说自由,女也说自由,青天白日卖风流。如此瞎闹何时休,怕有瓜分在后头。”见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第227页。 ⑧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99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⑨严复《遗嘱》第一条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见《严复集》第二册第36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⑩《与熊纯如书》(八十三),《严复集》第三册第699页。 (11)《惜宜轩文集序》,《畏庐三集》第5页下。 (12)《冷红生传》,《畏庐文集》第25页上,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 (13)(14)(27)《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1919年3月25日《大公报》。 (15)参见《林琴南先生致包世杰君书》,1919年4月5日《新申报》;陈独秀:《林琴南很可佩服》,《每周评论》第17期,1919年4月13日。 (16)《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是蔡元培少有的驳论文章,有条不紊,不愠不火,挡过众多飞来的子弹,转而阐述自家主张。只是在谈及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的古文修养以及“了解古书之眼光”时,隐含对于林纾学识之讥讽。 (17)《荆生》初刊1919年2月17-18日《新申报》,《妖梦》初刊1919年3月18-22日《新申报》,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第81-8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1919年3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校方公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章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 (19)《复张厚载函》附《张厚载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8页。 (20)《七十自寿诗》其二,见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46页,《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版。 (21)关于“荆生可以说是林纾想象中有点美化了的自我”,以及新文化人的“运动之术决定了阐释的方向”,陆建德《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有精彩的论述,请参阅。 (22)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23)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24)参见《胡适答蓝志先书》,《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这段关于“革新家的态度问题”的自我批评,收入《胡适文存》时删去。 (25)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7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26)参见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第五节,《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91-1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参见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第176-1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9)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第112页。 (30)林纾去世前一年编定《畏庐文钞》(1926年刻本),除选自《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者外,便是此置于卷首的《续辨奸论》。 (31)参见张俊才《林纾评传》第239-240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32)林纾:《续辨奸论》,《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60-61页,又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94-95页。 (33)去世前三个多月(1924)所作《留别听讲诸子》,后半截很能显示林纾的立场坚定与骂人习气:“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参见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62页。另,周作人《谈方姚文》曾批评桐城诸家为人刻薄,诅咒所有“欲与程朱争名”者皆“身灭嗣绝”,真是“识见何其鄙陋,品性又何其卑劣”。见周作人《秉烛谈》第158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34)《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71-272页。 (35)据张俊才《林纾著述系年》,此连载原题《春觉生论文》,起于1913年6月,因9月30日后《平报》未见,无法判定终于何时。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第493页。 (36)林纾:《修身讲义》卷上第1页,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37)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41页、55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38)《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57-558页。 (39)参见汪家熔《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480-48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朱锦丽《蔡元培与清末〈中学修身教科书〉》,2013年7月31日《中华读书报》。 (40)收入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依据的是1921年9月第16版《订正中学修身教科书》。 (41)参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32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2)如陆费逵编“师范讲习社师范讲义”之《修身讲义》(商务印书馆,1910年),除“绪论”外,第一章“对己”,第二章“对家”,第三章“对社会”,第四章“对国家”,第五章“教育家之天职”。 (43)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69页。 (44)《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75页。 (45)参见林纾《修身讲义》卷上第37页上、38页上。 (46)林纾:《修身讲义》卷上第5页上、下。 (47)商务印书馆1913年5月刊行林著《技击余闻》,收笔记体小说46则,皆为乡里拳师轶闻,叙事简劲,甚为可读。 (48)参见林纾《修身讲义》卷下第8页下至9页下、第24页下至25页下。 (49)《畏庐老人训子书》,见李家骥等整理《林纾诗文选》第365页。 (50)罗志田在《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中称:“恰恰是在后来林纾公开认同的传统范畴里,一个只有举人功名的小说家是没有资格作士林代表的。”见罗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6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1)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36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52)参见张俊才《林纾评传》第199-201页、256-258页。 (53)姚永概:《〈畏庐续集〉序》,《畏庐续集》。 (54)高梦旦:《〈畏庐三集〉序》,《畏庐三集》。 (55)林纾晚年曾致信李宣龚,谈及古文,称“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参见钱锺书《七缀集》(修订本)第104-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6)除了在《尊疑译书图记》(收入《畏庐文集》)中为严复打抱不平,林纾还在《洪罕女郎传》的跋语中称:“或谓西学一昌,则古文之光焰熸矣。余殊不谓然。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彼严几道先生不如是耶?”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7)见《严复集》第二册第388页、413页。 (58)参见孙应祥《严复年谱》第546-54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93页、189页。 (60)参见钱锺书《石语》第31-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61)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1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2)林纾早年所撰《闽中新乐府》中,就有一《知名士》:“知名士,好标格,辞章考据兼金石。考据有时参《说文》,谐声假借徒纷纭。辨微先析古钟鼎,自谓冥搜驾绝顶。……”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第3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3)参见林纾《与姚叔节书》,《畏庐续集》第16页上。类似的抱怨,还有《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畏庐续集》第20页)、《慎宜轩文集序》(《畏庐三集》第5页)等。 (64)参阅林纾《与本社社长论讲义书》,见张旭、车树异编著《林纾年谱长编》第30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6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述及此段公案:“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纾愤甚。”(第194页) (66)林纾:《闽中新乐府·破蓝衫》,见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第288页。 (67)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43-148页。 (68)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69-71页。 (69)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第113-114页。 (70)林纾:《〈爱国二童子传〉达旨》,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第115页。 (71)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初刊《学人》第十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第二节;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3-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2)舒芜校点:《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第1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73)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2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4)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序》,《古文辞类纂选本》,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75)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开篇就是:“韩氏之文,不佞读之,二十有五年。”参见《韩柳文研究法》第1页,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 (76)参见林纾《与姚叔节书》(《畏庐续集》第17页上)及《慎宜轩文集序》(《畏庐三集》第5页下)。 (77)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1-22页。 (78)林纾:《〈文科大辞典〉序》,《文科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版;又见《畏庐续集》第10页下。 (79)沈尹默:《我和北大》,初刊《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1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80)沈尹默称:“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见《北大旧事》第164页)即便如此,沈也能挂着留学日本及太炎弟子的招牌进北大教书。 (81)何燏时1899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1902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1905年7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胡仁源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此后又留学英国学习造船,毕业于推尔蒙大学。 (82)参见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二第65-66页。 (83)《林纾示琮儿书》(夏晓虹释文),《现代中国》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4)此信收入商务印书馆即将推出的《林纾家书》(夏晓虹、包立民编注),此前林大文在《后人心目中的林纾》(钱理群、严瑞芳编《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第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曾引用。 (85)参见周作人《关于家训》,《风雨谈》第62-65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86)关于林纾的翻译,近年成果甚多,实证研究中,最值得推荐的是樽本照雄的《林纾冤罪事件簿》(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2008年版)、《林纾研究论集》(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2009年版)。 (87)马其昶:《〈韩柳文研究法〉序》,《韩柳文研究法》。 (8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第28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89)《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第4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0)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修订本)第95-96页。 (91)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全集》第1卷第53页。 (92)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四章“学问该如何表述”之第四节“白话文的另一渊源”。 (93)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第78页,岳麓书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