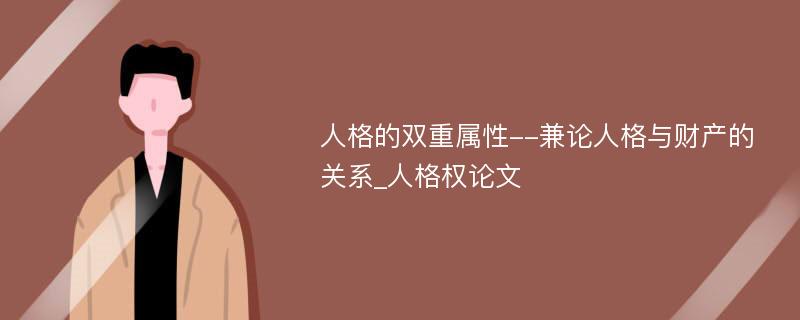
人格双重属性之思辨——兼评人格与财产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思辨论文,财产论文,属性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6)01-0030-06
我国民法学界自从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提出新人文主义的民法典制定思想以来,人(格)与财产(物)的关系问题所引发的论争就再没有平息下来。2004年北京大学尹田教授撰文提出“无财产即无人格”的观点[1],此观点与他提出的“人格权为宪法性权利”以及“法人无人格权”等观点共同构筑了其独特的人格与人格权理论体系。而“无财产即无人格”的命题与徐国栋教授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民法观形成明显的分歧,由此双方进行了一场影响甚广的论战[2]。
作为一次对真理的无私讨论,它使我们再次深刻反思人与财产的关系问题,也让我们坚定了中国民法典人文主义的信念。鉴于双方对如何实现人文主义产生了较大分歧,正确选择中国民法典中人文主义的实现途径显得十分重要,否则难免会陷入南辕北辙的尴尬。本文将从人格概念的语词结构出发,运用存在哲学的思辨方式探寻人格的属性以及人格与财产的关系问题。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给学界提供另一种思考人格以及人文主义问题的方式,以深化对人格问题的思考,并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人格”的解构——从“词源学”开始
“人格”问题由来甚久,人格这一词语也在历史的进程中被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尘埃,而其原始意义始终未得彰显。为准确地把握人格的涵义,笔者选择了探究“人格”词源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以拭去“人格”一词上的层层尘埃并找回其原初意义及其历史轨迹。同样重要的是,由于语言的结构本身也暗含了关于世界性质的特定观点,因而通过对语言的学习,我们可以获得一套我们本身无法完全认识的思维框架[3]。毫无疑问,这种知识框架将帮助我们去更准确地认识“人格”问题。
“人格”在英文中可用两个单词来表示,即" humanity" 和" personality" ,下文将以这两个词为线索展开追溯。
" Humanity" 来源于拉丁文" Humanita" ,后者则是属于拉丁词根" homo-" 的派生," homo-" 在拉丁语中表达了“人、人属”的涵义。在语言的历史流变中" homo-" 曾衍生出诸多变体,如" huma-" 、" homi-" 、" home-" ,这些变体都保留了其原初形态中所蕴藏的“人”的内涵并一直延伸到现代的英语,最典型的为" human" 一词表示“人、人类”,再如" Homosapiens" 表示“人类、智人”," homicide" 意为“杀人”;而" homo" 也常常被直接用来表达“人”,比如西方学者还常用" Homo Economicus" 、"Homo Politicus" 分别表示“经济人”和“政治人”。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表示“人、人属”的意思外," Homo-" 还表达另一个含义,即“同类、同质、同种”,例如我们熟知的" homogeneous" 表示“同类的、均匀的”;" homologue" 表示“同系物”;" homosexual" 指“同性恋的”等。由于笔者收集的资料有限而无法考证此涵义产生的准确时代,但根据语言学的常识我们不难看出,从拉丁语到现代英语," homo-" 同时表示“人”和“同类、同质、同种”两种含义绝非简单巧合,它说明人们在使用当中意识到这两种含义之间的深层联系,即“人与人具有同质性”。更重要的是个人只有和其他人保持一致性方能成就其“人”的属性。这种一致性就是人类的共性,它让人区别于神、野兽、机器,最终使“人性”(humanity)从“兽性”(animality)中超越出来。对此种人与人之间的共性,笔者将其视为人格的第一属性,即使“个人”保持与其他人一致的那种人格。
表示“人格”的另一个词为" personality" ,通说认为其起源于希腊语中的“Ллробωлоυ”或“Ллробωлειоυ”。在古希腊时代,人格一词曾特指头的部分,但它更为常见的意义是戏院里演员的“面具”。根据伦理学家John Zizioula的研究,面具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是悲剧性的,正如古希腊人擅于以悲剧的形式表现人的自由与理性的必需之间的冲突。戏剧中,戏院被当做是统一与和谐的背景世界,剧中的角色努力成为一个独特的“人格”,进而反抗那个逼迫他作为理性与道德必需品的和谐统一的世界。但是最终他还是悲惨地服从了柏拉图的定律,即世界不为人而存在,而是人为世界而存在(that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 for the sake of man,but man exists for its sake)。他的“人格”只能是一个“面具”,只是对自己的真正“位格”感到惶惑而没有本体论(ontology)内容的东西。
“Ллробωлоυ”(或Ллробωлειоυ)还被理解为戴上面具的演员,甚至包括观众,他们稍稍获得一些自由和“人格”,一些他所生活的世界中理性与道德不肯给他的特定身分(a certain identity)。由于面具,他终于成就为一个人格,虽然时间短暂,却已学会如何生存为一个自由、独特和不能复制的实存[4]。
到罗马时代,罗马人使用" persona" 表示人格,这是希腊文“Ллробωлоυ”(或Ллробωлειоυ)在罗马的运用①,在其人类学的内涵(anthropological connotation)上,罗马的" persona" 与它的希腊前身相比表现了更为深刻的个体性观念。不过,在其社会学和后来法律的使用上,它仍然体现了人格与面具的微妙关系,作为面具的人格(persona)是一个人在他的社会或法律关系中(舞台上)所扮演的与众不同的角色,但无论其如何扮演,都无法影响本体论意义上的人格。值得注意的是,在古罗马人格与身分密不可分,如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里一语破的:“人格变更就是改变先前的身分。”
它告诉我们,身分是人格的要素或基础,人格由身分构成,复数的身分构成了单一的人格,诸项身分之一的缺失将导致人格的减少,丧失殆尽的结果是人格消灭[5]。而我们知道,身分是用以区别人与人的工具,特定身分的享有意味着获得与众不同的人格。
通过分析人格一词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沿革,我们发现不论是作为身分载体还是作为面具载体,人格(personality)都蕴含着一个根本性的意义——差异性。此差异性让人区别于同类,将人格从单一、抽象的人性(humanity)具体为活生生的人类舞台上的角色。对此我称其为人格的第二属性,就是使“个人”保持与他人差异性的那种人格。
二、人格双重属性的关系——以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为背景
对人格的双重属性可以从道德论、价值论、本体论等多角度进行解读。然而,笔者通过对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② 的阅读,发现海氏的存在哲学蕴含着解释人格属性的独特智慧,因而笔者在此选择海氏的存在哲学作为分析的背景。
在运用存在哲学理论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海德格尔认为,以往哲学家们质问世界时,他们都无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世界存在”。哲学家们的头脑总是先被世界中的事物所占据,而不去关注更原始的事实——世界本身的存在。海德格尔毕生追问“一般存在的意义”,海氏的存在(Being总是大写的" B" )是允许其他一切事物进入存在的原始状态或“根据”。海德格尔称其他一切事物——人、植物、动物——为存在者(beings总是小写的" b" ),它们是存在于世界上的那些实体。与存在相对应的概念是海德格尔所称的“无”——万物不存在的可能性。就人而言,人是通过生存而参与存在,通过不再生存而参与“无”,在这个生存者的世界,只有借助生存与不生存,“存在”与“无”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为了标志出我们生存的意义,海德格尔把人这种典型的存在者称为" Dasein" (“存在在此”即“此在”)。他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因为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赢获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6] (46~49)。因此对于“人”这种特殊存在者而言,追问人格存在的意义只能通过追问此在的人格方能实现,根据存在哲学的诠释,可以看出存在与此在的关系也反映于人格的双重属性之间。
人格的共性(humanity)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是一种与上帝的无限相对的有限,是与野兽无理性相对应的自由理性。个人无法选择这种“存在”,他在出生时便被抛入这个世界(出生对人来说是一种无意义的行为,因为他无法选择)。个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存在,“共性”让个人进入人属中,并遵从人的伦理;这种存在赋予人格共有的东西——生命和自由。生命是人的存在基础,自由则是人属天赋的权利,以帮助人从存在世界进入此在世界。
人格的差异性(personality)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它是存在的具体,包括构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格”(personality)的形形色色的东西。此在的原始生存活动以三种样式现身,无差别的(undiffentiated)、非本真的(unauthentic)和本真的(authentic)。就生存的时间性来看,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沉沦的方面,即其被抛的“所是”;二是超越的方面,即其本真的“能在”。就超越方面看,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最积极的思想之一就是,人“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换句话说,“此在是什么,依赖于它怎样去是‘它自己’,依赖于它将是什么”[7] (P.49)。
此在对于存在而言是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此在的人格(差异性)在沉沦与超越中斗争,多数人格难免将沉沦于人的“存在”,即陷入“无差别或无意识”的状态,但也不断有人格要超越有限向无限发展,这是一种斗争(本真的或非本真的),尽管多数以古希腊式的悲剧结束,而悲剧性的力量能促使人格独立,推动人的“存在”向无限发展。同时,此在人格对人格存在的超越并非无限度的,“共性”是“差异性”的基础,在人属当中任何人的个性(personality)都不能以牺牲其人之共性(humanity)为代价,维系两者之间张力的是现实的伦理与法律。
三、人格与财产的关系——两个层面的探讨
运用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对人格双重属性进行的诠释为我们理解人格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种另类路径,跟随这一路径我们进而得以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另一个与人格关系密切的重要问题——人格与财产的关系。
人格与财产反映了人类世界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统一,由于该问题涉及民法哲学最为敏感的部分,而成为近来我国民法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然而就笔者的观察而言,学界的讨论大都习惯性地集中于实在层面,即人与财产的主客体层面,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人与财产在存在层面的讨论,实在难以谓之全面。因此,下文将划分为两个层次进行探讨,一是存在层面的人格与财产;二是此在层面的人格与财产。
(一)人格与财产——存在层面的讨论
1.人格存在(humanity)与其他存在(包括财产存在)
在展开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前提,即世界由其他存在与人的存在共同构成,只是因为思维和哲学从来都是人类的思维和哲学,所以人类一直坚信所有的存在者都是为人而存在,这成了理所当然的道理。我们在讨论人与其他存在时总是忽略其他存在本身,而仅仅是根据人类的需要赋予其他存在以意义,并思考它与人类的关联。世上的所有存在物,环绕我们的一切都被视为供我们消费之物,整个世界变成了仅仅为我们的目的而存在的“材料”(bestand),比如当我们谈论财产或者物时,实际上是将它们当做对人类具有效用的“材料”。这种只以一种存在者为中心来看世界的方式排除了以多重方式看世界的可能性,它被海德格尔称为“技术态度”,在这种态度下我们无法与世上的万物和谐共存。如果说海氏的观点在70年前显得颇为离经叛道的话,那么在70多年后,这种观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开始反思“技术态度”并从存在层面关注自然环境、动物、能源等问题。
笔者认为,与神的彼岸存在相对,自然界的人属和物属遵循的不同存在,一起被抛入这个世界,人格存在与其他存在互不影响,两者同受自然法的调整并组成和谐而统一的自然,在自然法面前它们是平等、独立的。
2.人格存在(humanity)与此在的财产——无财产亦有人之共性(humanity)
作为存在的人格(humanity),与此在的财产没有直接关系,不论财产是广义上还是狭义上的,这个道理几乎是透明的,其所体现的人格共性不会因为此在的外物而蜕变或丧失。因此自由与生命无法用实在的财产来进行度量或因财产而改变。即使一个天生愚钝、残弱、在社会中不堪一击的人,即使一个降生于贫寒之家的人,即使一个没有任何物质财产、流离失所的人,尽管他们丧失了充分表现其人格差异性的机会,但他们拥有的人之共性(humanity)和其他人一样,不仅完整而且神圣。
(二)人格与财产——此在层面的讨论
1.分立的财产造就人格的此在——无财产即无人格(personality)
海德格尔说:“此在是什么,依赖于它怎样去是‘它自己’,依赖于它将是什么。”人格的差异性正是基于人类社会的此在而确立,它追求差异性又在抗拒着差异性。就个体而言,实现差异性的人格无法离开分立财产的支撑(此处财产作广义的理解),既包括外在的物质财产又包括个人内在的才智和身体,同时我们必须强调,能够保障人格独立是“分立的财产”。
“分立的财产”提供了每个人在各自的具体环境下充分利用个人与他人的局部知识去创新的激励[8] (P.78)。这一概念源自于哈耶克对洛克意义上“财产权利”的引申③。分立的财产是个人自由、人格独立的基本保证,这一思想贯穿于众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毕生的著作中,它与洛克的劳动财产学说、休谟的人性论、亚当·斯密以及哈耶克、布坎南等的自由学说一脉相承,并为自由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
在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通过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真相,即当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供给被他人控制了的时候,我们的自由、人格、尊严、生命都会受到威胁,或者说,最严重的威胁,就是为我们创造美好天堂的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引导我们走向奴役(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9]。哈耶克称分立的财产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布坎南也指出财产的私有与其说是因为对效率的追求,毋宁说是让每个人拥有一个逃避权力垄断的私有财产堡垒,在那里,你可以保持消极的自由和独立、骄傲的人格,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家”的感觉[10] (PP.2~4)。
从“存在论”视角来看,个人因为分立的财产而获得发展和超越的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生命和自由的能量。个体所具有的共同的被抛状态成为可控制的个体差异性。此在(差异性)完成对存在(共性)的超越,并通过此在的无限可能来实践人属的存在意义。所以我们有了康德,有了比尔·盖茨,有了乔丹和姚明……而且,只要存在分立的财产,我们就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差异性人格出现。
2.财产意义的再升华——避免人性(humanity)的异化
如前所述,人区别于神、野兽和机器的共性特征是人属存在的标志。人格的存在只能被人格的此在所实践和丰富,并通过伦理和法律保持此在与存在之间的张力。但是此张力是有极限的,一旦突破极限,神就会惩罚我们,人性(humanity)的悲剧也随之发生。
悲剧的发生往往是从剥夺人的此在开始到异化人的存在结束,扼杀人的此在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剥夺个体的财产,使个人无“家”可归并直接暴露在国家机器或暴政面前。有人这样描述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禁生活:人们完全丧失了隐私权,因而他们不再试图掩饰人性中最阴暗最恶劣的一面,在可以随意暴露人性中最低下和残忍性情的环境里,人们渐渐丧失了人性,沦为野兽。
中国的文革何尝不是如此,私人领域的丧失最早是从财产公有制开始。私人领域被“一大二公”的政治叙事所遮蔽,个体失去了与他人的交流的权利,从而“自我意识”逐渐沦为“受奴役”的愿望,人不但成了野兽,也同样成了机器。与个人沦为野兽、机器相对的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层出不穷的造神运动,个人变成了神本身,当然其结果只能是悲剧。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以财产的分立为标志的法治和市场经济被我们所选择,它们也许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起码也不是最坏的,在这里,人的差异性得到尊重并避免了人性的异化。与此同时,财产的意义也得到了升华。
四、启示兼结语
由于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对人格属性以及人格与财产的关系问题,从古至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进行解释,不同的解读方式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社会发展程度,并进而对社会文化和立法模式产生影响。在当下中国,此类问题的探讨与澄清关系到未来民法典中诸多基本理论的定位和民法典本身的质量及品味。
笔者认为,就实现未来中国民法典中人文主义理想而言,通过对人格双重属性以及人格和财产关系的理论剖析可得出下述三点启示。
启示一,民法典作为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实在法,它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人格问题,民法典中人文主义的张扬应该沿循保障人格的共性和促进人格差异性两个维度展开,并围绕这两个维度构建具体的民事法律制度。鉴于民法典中人格双重属性的重要性和根本性,笔者赞同未来民法典在结构上采用人法前置的形式。理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前置的人法中规定反映人格共性的相关内容,随后才是促进人格差异性的各种制度(包括财产法律制度),此结构符合民法典将“人格”关怀贯彻始终的规范逻辑;另一方面,在更深的层次上,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的权利圣经,其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的证明,它更加需要人性精神的引领,而人法前置的形式正凸显了人格的重要性与人性的至高无上性。
另外,以人格问题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绝对的人类中心论。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是所有存在者中的一个,其他存在者并非是因人而存在或为人而存在的。人类的法典需要对自然界其他存在者的尊重,保持此在与存在之间的谦卑关系。我国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以“技术态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危险性,并就如何在法律中处理人类与其他存在者的关系提出了建议。如江山先生一直倡导的人际同构的法哲学,反对那种绝对的、封闭的人类自我中心论[11] (PP.2~10);徐国栋教授在《绿色民法典》中提出的“绿色”思想,表明人与资源的平衡,绿色是对人类与其他生灵的和平共处关系的描述,是对人的谦卑地位的表达[12] (P.10);薛军博士在谈及人与物的关系时指出,人类生存危机的现实已经证明,人类自我中心论是一种致命的偏见。万事万物皆有其自在自为的自由属性,我们没有必然的理由把那些自在之物都划归到“无主物”、“共有物”之类的范畴中[13]。这些观点突破了人类狭隘的“言必称我”的思维惯性,为法律注入了新鲜的、进步的精神实质,这种思想体现在民法典中则提升了民法典的品味,赋予了人文主义更加深刻的内涵。
启示二,作为人法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格权是人格双重属性的权利影射,民法典中人格权的规定既要反映人格的存在即共性,也需要反映人格的此在即差异性。涵盖人格的两个层面,一方面可以充分实现民法典对人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明法典对人格此在多样化的宽容和开放。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二元人格的思想在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中得到了体现,该法典将人格权分为保障人的自然存在的人格权与保障人的社会存在的人格权。显然这种分类是基于对人格的另一种理解——作为自然存在的人格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格。笔者认为此种分类值得赞同。因为人格的自然存在可以对应人格的共性;人格的社会存在可对应人格的差异性(因为社会是人格此在的真正舞台)。然而在该法典中所规定的人格权的具体构成种类方面,笔者认为有所不妥。该法典中的“保障人的自然存在的人格权”规定了生命权、自由权和家庭权,然而根据前文所析,人格的共性反映了人属存在,它最本质的内容是生命和自由。因此,作为反映人格共性的权利类型并非越多越好,只应包括生命权与自由权,它们本来属于“存在”的范畴,但因为人法的需要而将其成文化。徐先生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同时规定了“家庭权”。笔者认为,“家庭”是一种典型的人类社会存在方式,属于人格此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将“家庭权”归入“保障人的社会存在的人格权”之范畴为宜。除此之外,对于自由权的内容确定问题,笔者认为仍然值得研究,限于本文篇幅此处不赘。
与人格共性相对,其他的人格权类型都应属于人格的“此在”,它们反映了人格之间的差异性以及社会存在的种种形态,笔者赞成那种详尽规定“此在”人格权的思想与实践,因为此类人格权已经脱离人的存在层面,是人格超越状态的无限可能性的写照,考虑到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法典也需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的人格权类型留下开放的通道与空间。
启示三:在民法典中张扬人文主义与强调财产对人的意义并不矛盾。人文主义不是一种膨胀的感觉,而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基础上的立法导向。笔者不赞同笼统地将财产与人格对立起来,而是主张在讨论人格与财产的关系问题时区分探讨的层次,并且充分考虑各层次间的内在联系。
人格与财产是民法典规范的基本因素,财产、人格的差异性以及人格的共性三者之间的递进结构成就了民法典的一种金字塔般的稳定与和谐。金字塔的顶端是共性意义上的人格——人的存在;其下方则是反映差异性的形形色色的人格此在;最下方乃是支撑着人格的财产。当我们仰望这座金字塔时,目光和心灵将久久地停留在它的顶端并赞叹它的高度和神圣;当我们走近它时将会感叹其构成的细致和复杂;而当我们亲手触摸它时便能够体会到,其底部构成的坚定和沉着以及这种坚定和沉着的真正意义。
注释:
①人格、面具(persona)一词是否源出希腊文或有其他来源,或多大程度上受希腊的影响,专家们为之辩论不休。同源学的问题且不谈,实际上,罗马人至少在开始使用此词时,实质上和希腊文并没有什么不同。
②由于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主义对“自我”抱有成见,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故其本人拒绝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
③洛克的财产权利概念包含三个要件,即生命权利,自由权利,财产权利。三者以先后顺序自然展现了人的生命过程。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