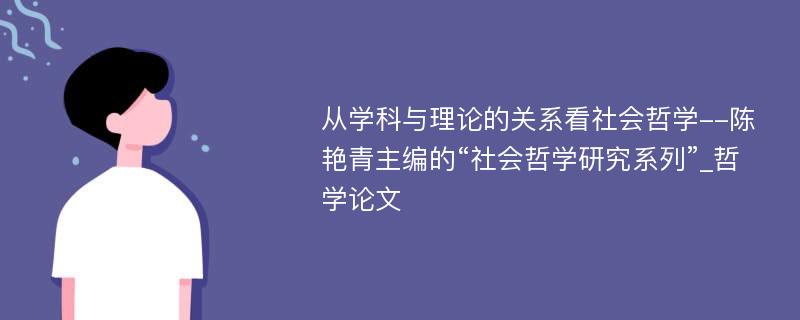
从学科与学说的关系看社会哲学——评陈晏清主编“社会哲学研究丛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社会论文,学说论文,丛书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陈晏清教授为主编、王南湜教授为副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最近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首批著作共4部, 分别是:陈晏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王南湜著《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李淑梅著《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重塑》、杨桂华著《转型社会控制论》。这套丛书将在今后10年间分批出版,不啻为社会哲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工程,首批著作初步展示了这项工程的气魄与水准。读罢几部著作,我们很受启发,这里拟从学科与学说关系的角度谈几点体会。
一、从学说到学科——社会哲学的兴起
社会哲学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兴起的根本原因无疑是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直接原因则是旧的社会历史理论在解释这一变迁上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理论创新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我们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现象,只能用一种学说,那就是由苏联教科书所表达的那套社会历史理论。那时虽然也存在不少学科,但所有的学科都服从这种学说,学科不复为中立的研究领域,以至于学说压倒学科。这种状况跟当时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是完全吻合的,这种学说自然也能够成功解释以它为蓝本设计的社会生活。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大量新的社会事实涌现出来,特别是商品经济被引进计划体制,这对该学说造成了巨大冲击,——它无法解释又难以接受这些事实,竭尽余力也不过解释为“补课”而已。到“南巡讲话”后,“补课”一说已无立足的余地,于是,苏联教科书理论陷入不可逆的解释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形下”学科纷纷冲破理论一统局面,致力于营建独立的学科领域和学术规范,为不同的学说提供平等的生长空间和竞争机制。在哲学这一“形上”领域,社会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等“哲学”以及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批判理论、日常生活理论等“理论”也纷纷挣脱苏联教科书理论的束缚而自立“门户”,力求有效地解答旧学说无法应付的难题。理论创新在这里不是表现为直接地以一种学说取代另一种学说,而是表现为从一种学说代替所有学科转向通过构建各种学科来涵养和培育更多的学说。社会哲学便是这种转向的一个结果。
国内以“社会哲学”为名号的有关研究,大致有四种情况:发掘马克思的本文资源,以克服教科书理论的危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引进国外社会哲学思想,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将各“形下”学科的理论提炼出来,并加以哲学化;以现实社会问题为中心,多方寻求理论解答。当然,这四种情况之间不无交叉关系。根据我们的观察,以陈晏清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社会哲学研究,主要属于第四种情况。
就我们了解的情况看,陈晏清教授明确地以社会哲学作为研究方向,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最初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由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90年代中期,他所在的南开大学哲学系先后将社会哲学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的主要研究方向。1998年,南开大学成立了国内首家社会哲学研究所,“社会哲学研究丛书”是该所第一项重大研究工程。
二、从学科到学说——“丛书”的初步理论成就
“丛书”虽然才出了首批著作,但理论成就是突出的。这些成就可从学科建设和学说建设两方面来看。
脱离教科书的僵化学说后,自立“门户”的各学科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划分“地盘”,包括确定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等。社会哲学也不例外。在这方面,“丛书”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哲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到理解。社会哲学究竟研究什么?“丛书”编著者的回答主要是:总体把握社会生活,是社会哲学的一般内容;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当代中国的社会哲学研究应以社会结构的转型为最适宜切入点,并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为典型对象;中国社会哲学在当前的首要的理论任务,应是揭示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趋势,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哲学把握为考察和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解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内含着一种问题中心主义的学科划界观,与方法中心主义和价值中心主义的学科划界观明显不同。方法中心主义的划界观是根据方法找对象,特定方法不能处理的问题不作为本学科研究对象。价值中心主义的划界观则是根据立场找对象,不符合特定立场的问题不能进入本学科研究领域。问题中心主义的划界观,则是直接将问题作为对象,再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确定方法和价值立场,从而能使我们自觉地从社会哲学的时代背景及历史责任出发,去关注现实生活的重大问题,更切实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服务。
关于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丛书”主编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界说的。一是社会哲学作为“哲学”,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特征,那就是总体性、反思性和批判性。二是社会哲学作为“社会”的哲学,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哲学的方法特征。在这一方面,陈晏清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存在两个维度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历史哲学维度和社会哲学维度,前者揭示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后者研究具体社会历史形态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社会哲学是历史哲学的基础,离开了社会哲学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与旧的历史哲学相区别;过去我们只注意了历史哲学维度而忽视了社会哲学维度。以此为依据,他主张社会哲学不应是超时空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第12—13页)这就将先前的各种教条主义研究方法摈斥于社会哲学研究之外。对社会哲学研究方法的这种理解,显然是以上述对社会哲学对象的理解为依据的,——问题是第一位的,方法以至价值立场等都是第二位的。
从学说到学科,只是事情的开始而非终结;在初步清理出来的学科地基上构建新的学说,以有效解决旧学说解决不了的问题,才是有关研究的根本目的。如果说此前国内社会哲学研究主要忙于学科建设的话,那么,“丛书”首批著作则显示了一种重要的变化:研究重心在从学科建设向学说建设移动。我们在“丛书”中已经看到了较为成型的个人学说和学派观点,其中最重要者为“从领域分离到领域合一”的转型学说。
能够成为学说的理论见解,与关于学科建设的一般性主张有质的差异,这就在于:学说是理念的逻辑系统,而一般学科主张只是理论材料的组合。关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些年说得比较多的有马克思的“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说、滕尼斯的“共同社会”和“利益社会”说、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说等,这些都是我们用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常见理论框架。但由于这些看法都是在没有观察到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的情况下得出的,因而用以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难免有乏力之处。因此,创建中国人自己的转型学说,是一个比引进、运用国外有关学说更加重要的工作。我们感到,“丛书”著者的“领域合一”和“领域分离”说,不失为这种工作的一个颇具分量的收获。
“丛书”著者转型学说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结构分为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在前市场经济时期,诸领域以政治活动为中心而直接地统合为一体,这种结构方式就是领域合一;在市场经济时期,政治领域不再具有中心地位,三大领域各以本己的目标为目标,相互间拉大距离,这就是领域分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可以作为理解社会转型,包括中国当下转型的一个普适性原则。这个核心观点还统帅了大量具体观点,并形成了一个理论逻辑,这是一个必须肯定的新贡献。我们注意到,“丛书”首批著作都很重视这套学说,表明这是陈晏清教授所代表的南开学派的一个重要见解;其中,王南湜教授以“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为书名,对该学说作了集中而全面的阐述,其学力和见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李淑梅博士在《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重塑》中以“实践论的人性论”为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和阐发,既为转型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人性论前提,又通过转型研究揭示了新的人性内涵,杨桂华博士在《转型社会控制论》中把现代系统科学的方法和一般哲学方法结合起来,对转型社会的控制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既初创了一套概念系统,又设计了一套操作机制。
总之,无论在学科建设上,还是在学说建设上,“丛书”首批著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学科和学说的互动——对“丛书”的建议
上述四部著作只是这项工程的开头部分,主要的工作还在后头。唯其如此,我们感到有义务提出一点建议,或许有助于工程的实施,并供社会哲学的其他研究者参考。
我们认为,处理好学科与学说的关系,是“丛书”及整个社会哲学研究的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形象地说,学科是地盘,学说是房子;否弃旧的学说,好比城市改造中折迁危陋平房;折迁危陋平房是为了腾出地盘,腾出地盘是为了盖高楼大厦。学术研究也是这样:在有些领域,旧的学说不肯退出,新的学说无处立足;在另外一些领域,学科地盘开辟不少,而真知灼见罕有建树;更有一些领域,炒作甚热的学科地皮其实子虚乌有。单就社会哲学而言,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学科空间过于局促。空间局促,首先是因为拆得不够,其次是因为没有与邻近领域相连成片。就后者而言,突出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理论、发展哲学等领域的关系不明确,强调分的时候多而注意合的时候少,从而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视野。二是学科规范尚待建立。学科作为公共领域,必须有公共认可的学术规范,这是展开学说竞争的前提。目前,社会哲学领域,跟其他许多新兴领域一样,研究者或研究群体大多各有一套规范,这使得研究成果的公共性受到普遍削弱。三是学说意识十分淡薄。拓展研究空间,订立学科规范,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学说的繁荣,是为了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因为只有学说才具有对于经验事实的解释力,而学科本身则不具有解释力,正如空地不能住人而房屋才能住人一样。
学科空间与学科规范等学科问题属于共性问题,学说问题则是个性问题,这就要求社会哲学研究必须在学科建设和学说建设两个方向同时用力,在共性与个性的张力中实现学科与学说的良性互动。
鉴于以上认识,我们对“丛书”的最后目标有一定的疑义:那个最终要建立的社会哲学理论体系究竟是一个学科体系还是一个学说体系?如果是学科体系,则它确实必须与他人共建共有,但这样一来,它就只能作为这项工程的公共条件,而不能作为最后目标;如果是学说体系,则它确实是最后目标,但这样一来,它就只能是个人之见或学派之见,而不可能与他人共建共有。在此,我们对“丛书”编著者有两点建议。其一,更加积极地联合社会哲学的其他研究者和相邻领域的研究者,协力推进社会历史理论的观念变革,除旧布新,构建空间宽阔、规范健全的社会哲学学科。当然,这里面也有困难。比如,在界定学科对象上,问题中心主义的划界观与方法中心主义的划界观及价值中心主义的划界观在逻辑上很难兼容,其间最多构造为一种互补关系。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值得进一步探讨。其二,更加自觉地进行学说建设,培育学术个性,鼓励学说竞争。最后,我们祝愿把“丛书”建成一个在最具公共性的学科领域中个性化学说林立的学术“示范园区”,以带动哲学学术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