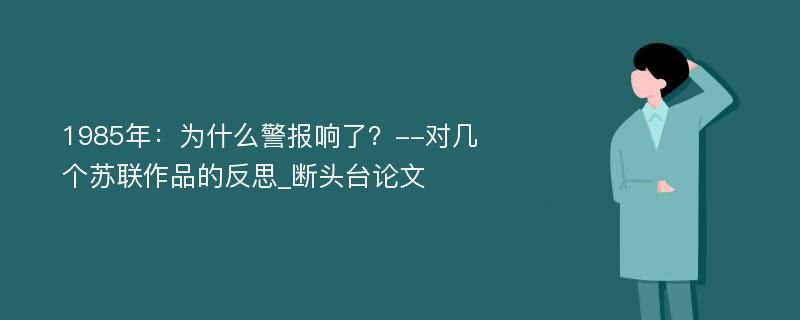
1985:警钟为何而鸣——对几部苏联作品的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警钟论文,沉思论文,几部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历史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自然在艺术中也是如此,一种强烈的感觉上升到了第一位,再不能如此下去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列夫·托尔斯泰写下了名扬世界的文章《我不能沉默》,他向同时代人详尽地描述,刽子手如何把浸湿的绳索套在受骗的农民的脖子上,每干一回这种勾当他可以挣到多少卢布。
今天我们没有托尔斯泰。但这样并不能使俄罗斯文学摆脱使命,缄口不言,而要倾尽我们的全力大声疾呼:再也不能如此下去了!维·阿斯塔菲耶夫的《悲惨的侦探》喊出了这愤怒而强烈的感觉。作家质问读者,对官僚主义的冷漠,自鸣得意的颟顸,地痞流氓的横行无忌,作奸犯科之徒的逍遥法外,杳无人迹的村中老人的孤立无援,被弃婴童的父母的不负责任,我们大家,我们每 个人,还要忍受到什么时候。①
在《警钟》一文中,批评家叶·斯塔利娃为《悲惨的侦探》如此辩护。
1985,这个符号,在前苏联的历史上,与其说是一个年头,不如说是一个象征,一场社会政治地震的先兆。一群赋有社会使命感而又目光敏锐的作家,就象灾变前的灵性动物一样,感受到了种种奇征异兆,变成勇敢无畏的先知,毅然用一部部惊心动魄的作品,为同胞敲响了警钟。
1985年7月,《我们同时代人》杂志发表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火灾》:林场小镇松林镇的工人供销社仓库失火了,有人积极抢救货物,减少火灾损失,有人却趁火打劫。通过描写抢险救灾和表现主人公叶高洛夫的回忆思索,作品表达了一个深刻的隐喻:失去了家园、传统和公民责任感的人正经历着内心的火灾。1986年1月,阿斯塔耶夫的长篇小说《悲惨的侦探》在《十月》杂志上发表。小说的主人公列昂尼德·索什宁是一个退休警察,妻子和女儿离他而去(不是中国电视剧中的路子:丈夫忙于综合治理而怠慢了妻子,妻子愤然出走;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因为赌气他们分居了),成天沉浸于写作修改关于警察的小说,他总是处于现实生活和回忆的交叉之中。他的眼睛看到的是一幅幅阴惨的图景;年老色衰的格拉尼娅姨妈被四个醉鬼轮奸了。一个失意的人杀了他碰到的第一个女人,一个有孕在身的母亲。劳改释放犯在一个无人的村子里强迫一个老太婆与他同居。市里的官员向上边来的人大肆行贿。聪明的老警察让新手冲前面,后者死于非命,前者照样升迁。业余剧团中的女明星,成了整天烂醉如泥、横卧街头的“垃圾桶”。主人公索什宁是正义、善良的卫士,他挺身而出,勇敢无畏地同犯罪、同腐败、同堕落作斗争。但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差点连老命都搭上了,在那一幅幅阴暗的画面上没有出现一丝光亮。这就是他成为悲惨的侦探的原因。
1986年《新世界》杂志第6、8、9期连载了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断头台》。这部结构独特的长篇小说共分三个部分,表现了人给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小说写了一对狼阿克巴拉和塔什柴纳尔及它们的狼崽的遭遇。在这群狼栖居的莫云库梅荒原上,出现了世界末日般的惨景。州里面为了完成畜肉生产的五年计划,决定大规模捕杀荒原上的羚羊。直升机、吉普车和手持冲锋枪的捕杀者把荒原变成了恐怖的屠宰场。这一对狼崽就丧命于这末日之中,他们后来产下的一窝狼崽死于飞机投掷的烧荒的燃烧弹。最后这一对狼转移到牧区,又产下了四只狼崽。这些狼崽却被贪心的牧人巴札尔拜掏走了,被他卖了换酒喝。这个举动引出了悲惨的结局。因为巴札尔拜带着狼崽进了另一个牧人鲍斯顿的家。这一对狼叼走了鲍斯顿的儿子。鲍斯顿一怒之下打死了巴札尔拜,自己去自首。《断头台》还揭示了日益严重的毒品灾难。被神学院开除的阿夫季·卡利斯特拉托夫当了某小报的编外记者。为了报道贩毒集团在中亚地区收集贩运毒品的情况,他隐瞒身份,混进了一个贩毒小组。当他试图劝告这些贩毒分子时,他被从飞驰的火车上推了下来。此后,他为了阻止枪手在莫云库梅荒原上的滥杀行为,被掉在一棵树上,死于非命。
1986年11月,莫斯科的批评家开会讨论《断头台》,阿·柯冈在讨论中指出:
艾特玛托夫用自己的方式敲响了警钟,这也就是《断头台》与阿斯塔菲耶夫的《悲惨的侦探》和拉斯普京的《火灾》成了同一性质的用品。②
绝非杞人忧天
敲响警钟的还有其他一些作品,比如,别洛夫的《一切都在前面》等等。上述几部作品加在一起就全面地暴露了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
《火灾》唱了一曲田园式微的哀歌:当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被汽车蹂躏,被水电站冲毁的时候,人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亲爱的土地,人们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根。如果我们将这部作品与拉斯普京纪念俄罗斯皈依东正教的文章《来自最深刻之处》联系起来,这种悲剧的实质就清楚了。在那篇文章中,拉斯普京说:“在西方人中居于首位的是外在的生活建设,在我们当中居于首位的是心灵和与其他民族的亲近的感情”。③在拉斯普京的独特的语境中,俄罗斯的传统农村正是俄罗斯文化的优越之处的象征:这里人们注重的是与大自然相一致的内心的和谐宁静,人们的价值观念是认同群体而忽视个人;当代表现代西方文明的各种物质;汽车、水电站、伐木的电锯打破这和谐宁静,并且“外在的生活建设”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俄罗斯人的传统丧失了,而与物质文明相联系的个人主义、道德败坏就开始侵略和瓦解他们。所以“火灾”这个题目就成了一个隐喻,它表明,俄罗斯人心中正经历着可怕的火灾,火灾的劫难之后,俄罗斯人将只剩下可怕的心灵的焦土。仿佛是为了冲淡这种凄惨可怕的结局。在《火灾》的结尾中写到了春天的消息,大自然“必然把留存下来的和未曾死亡的一切聚集起来组成一个生命世界”。④尽管这样,火灾的恐怖和劫后的余灰,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在他的《为玛丽亚借钱》、《告别马焦拉村》中的一样,拉斯普京作为捍卫传统的斗士在孤独地哀鸣,《火灾》揭示的是人们丧失精神家园的悲剧。
在《悲惨的侦探》中,阿斯塔菲耶夫用频繁列举案子的方式,探讨了犯罪问题。犯罪固然可怕,更可怕的则是整个社会对犯罪现象的容忍和姑息,而这本身就是犯罪现象最好的温床。流氓无赖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侮辱姑娘,甚至欲行强暴时,过路的人视若无睹。受害的姑娘撕心裂肺地喊道:“公共汽车站上的人都是苏联人,我们的人,当地人,可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助我!……卑鄙!……卑鄙!……全都是卑鄙!”⑤一个凶犯杀人之后,满身血迹,镇定自若地买冰淇淋吃,围观者无动于衷,听凭凶手扬长而去。警察与罪犯格斗时,旁观者不但不帮警察,反而替罪犯说情。在作家看来,这些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某种民族特性——“俄罗斯性格”。索什宁长期认真思索关于“俄罗斯性格”的问题:“为什么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怜悯囚犯,却常常冷漠地对待自己,对待邻居,哪怕他们是战争和劳动中的残废者?俄罗斯人愿意把最后一块面包送给犯人,送给打折别人骨头、使别人流血的人,不惜从民警手中抢走那些被反绑着双手的、刚刚行过凶的凶恶的流氓,可是却为了同一居室的邻居忘了关厕所的灯而憎恨人家,”索什宁得出了深刻的结论:“在这样慈悲心肠的人中间,罪犯生活得自由、傲慢、舒适,在俄罗斯他们历来就是这样生活的。”⑥到这里,《悲惨的侦探》已不限于犯罪问题进行探讨了,作品上升到了文化批判的层次,对历来受到高度赞扬的苏联公民作了深刻的解剖,揭示了国民劣根之所在。正象索什宁没有把这个问题想透彻一样,作家也未能更深入地挖掘国民劣根性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文化批判在作品中时时与艺术形象相脱节(这是下面将讨论的问题。)
如果说《悲惨的侦探》是对一个民族的劣根性的反思的话,那么《断头台》则通过揭示人类的缺陷而表达了终极关怀。阿夫季·卡利斯托拉托夫同伪善的僧侣、贪婪的毒品贩子和凶残的枪手打过交道后,对人的恶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想到:贪财、权欲和虚荣心弄得人痛苦不堪,这是大众意识的三根台柱,无论何时何地,它们都支撑着毫不动摇的庸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藏匿着大大小小的罪恶,充斥着形形色色空虚而贫乏的观点……”⑦艾特玛托夫具有很强的全球意识,他揭示出,在核时代,人们的上述阴暗品质与核弹和将军们结合,变成了一种更为可怕的力量。如何救赎陷于如此深重危机的人类,这是这部小说中试图解决的问题。小说没有采取一元决定论,提供了两种救赎的途径。一种是阿夫季从基督耶酥那里继承来的弃恶扬善的方法,就是以善去感化人,兼爱众人,绝不搞以恶抗恶。第二种方法,是作品第三部的主人公鲍斯顿的办法:将怨报怨,以恶抗恶。鲍斯顿在丧失爱子的悲痛和狂怒中,持枪打死了引发狼叼走人的惨剧的巴札尔拜。这两条路子似乎都行不通。阿夫季·卡利斯托拉托夫本来相信,通过宗教可以使人成为人,但是,当他用上帝来劝告滥杀羚羊的枪手的时候,他遭到了无情嘲笑和狠毒殴打。他的死,固然是遭殴打被悬吊的结果,但实际上是他精神的必然的归宿。当他救赎世界的许诺彻底破灭后,他生存的价值就丧失了。牧场的先进工作者鲍斯顿的正义的复仇行为,虽然可以为他挣得好汉的光彩,但在消灭恶的体现者巴札尔拜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好牧人的形象和生计也毁了。因此小说中未能提出拯救世人的妙方良策。所以《断头台》这部小说,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悲观。作家解决人类的危机时,不再从主流意识形态中去寻找武器,而借助于在当时的苏联社会处于边缘地位的宗教时,他所预示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就是文学中心话语消解的重要标志。
传统的消亡,国民劣根性的暴露,人类危机的日益深重,就是作家们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敲的警钟,作品问世的时间次序与有识之士洞察社会危机的深化过程达到了契合,越后发表的作品暴露的矛盾越尖锐,揭示的危机越严重。而后来苏联社会的解体证明,作家们的忧虑和警醒,绝非是杞人忧天。
孤独的愁容骑士
更大的悲剧也许在于:同人们的道德堕落、精神崩溃作斗争的,不是整个社会,也不是某个阶层,而是一个个单独的、赤手空拳的“英雄”。
在《火灾》中,真理的探寻者伊凡·叶高洛夫同他的精神兄弟索什宁、卡利斯托拉托夫相比,也许不那么孤独。来自被淹没的叶高洛夫卡的庄稼汉们还在顽强地抵御“外在生活建设”的侵袭,竭力保持传统的美德。哈姆卜大叔为了守住集体的财产,宁愿与盗贼同归于尽。阿方尼亚同叶高洛夫一起,总是出现在火情最危险的地方,抢救物资。但是伊凡·叶高洛夫在松林镇这个林场小镇上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他是个不错的司机,挣的工资挺高。他在这个充满道德堕落的外来人的小镇上感到活得很累,于是他毅然决定离开。他递交了辞职报告,要去当庄稼人,耕地种粮,收获自己的辛劳。他终究是个传统的孤独的捍卫者。
《悲惨的侦探》中的索什宁几乎陷入了堂·吉诃德的处境:普天之下充满了犯罪者的时候,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借用莱蒙托夫的话说,索什宁生于一个倒楣的时辰。他陷身于一个异质的环境。在他的周围大致就是三类人:一类是罪犯,甚至索什宁亲爱的利娜姨妈,他的抚养者,一个来自乡下的好心肠的妇女,也成了可耻的罪犯,被判了刑。索什宁的良心和敬业精神促使他同罪犯作不懈的斗争。第二类是受害者,也就是刑事犯罪分子伤害的对象,铁路新村所有孩子的(包括当年幼小的索什宁在内)可敬的格拉尼娅姨妈,被四个色狼轮奸了。如果不是过路的索什宁相救的话,列尔卡(她此后成了索什宁的妻子)险遭强暴。第三类就是同情罪犯的公民,索什宁在主持正义、执行公务、擒拿凶犯的时候,也必须忍受他们的冷嘲热讽。索什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充当正义骑士的。而他得到的是什么呢?受伤,致残,提前退休,妻子的冷落。解读到这里,《悲惨的侦探》这个书名用在索什宁身上,就产生了强烈的效果。阿斯塔菲耶夫通过对通俗文学(侦探小说)的反讽突出了这个孤独的警察的悲惨处境。
在《断头台》中,阿夫季·卡利斯托拉托夫始终是个被放逐的“多余的人”,他在他所处的环境中都没有找到归宿,没有获得周围的认同。在神学讲习所当学生时,他想将基督教现代化,甚至对宗教经典提出了疑问,进而要塑造一个所谓的当代上帝。他的思想和行动都被当成了异端邪说,因此把他逐出了宗教讲习所。后来他作了州共青团报纸的编外工作人员,开始,他写的文章还有读者,后来他不合时宜地去采写关于毒品的搜集贩运的社会新闻时,他的文章就被束之高阁了,他再一次被社会抛弃了。后来,阿夫季同毒品贩子和射杀羚羊的枪手们打交道时,他想通过呼唤上帝来唤醒这些不法之徒的良知,这些人反倒嘲笑他,宣称该把他“放逐西伯利亚”⑧,最终,他们把他放逐到了另一个世界。阿夫季·卡利斯托拉托夫始终处于这样的喜剧境地:教会中人视他为异己分子将他革出教门,而世欲中人又把他当作无可救药的僧侣,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鲍斯顿,则因为他作为一个牧人太优秀而成了独特的人。最后他以自己的杀人行动把自己从社会中放逐出去了。
在这个“警钟”时期,这些寄托着作家理想的主人公,完全不同以前苏联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或正面主人公。那时的英雄或正面主人公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是与他相似的一大群优秀分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保尔·柯察金,是朱赫来、丽达这样的英雄群体中成长起来的。而敲响警钟的这些主人公则成了异质环境中的“孤胆英雄”。如果这是现过实程的真实的反映,那么在这里英雄不可能不“悲惨”,作家也不可能不“悲惨”。
政论化与内省化倾向
从艺术价值的角度看,《火灾》、《悲惨的侦探》和《断头台》各具特色,读者在为它们的艺术创新激发起新奇感之际,又会感到有些失望。它们让多数读者感到失望的共同原因是,政论代替了艺术形象。
《火灾》的艺术结构类似于一首回旋曲。作品中有两种时间:现实的时间,即伊凡·彼得洛维奇在火灾中的历险,由傍晚时把车停进车库到整个在火中抢险的过程,直至第二天早上。这个时间是以火灾的发生的自然过程为叙述顺序。第二种时间是回忆,即伊凡·彼得洛维奇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回忆与思考。这两种时间的布局是互相交错的。通常是写一、二章火灾,便让伊凡·彼得洛维奇“闪回”到过去(一般占一章)。把一次次出现的火中抢险(现实时间)设想为一个不断重复的音乐主题,回忆部分(第二种时间)就是插入部。这样整个小说就以回旋曲的结构形式展开,显得很匀称,很有法度。在揭示《火灾》的结构方式时,我们不免要产生疑问:作品未免有些生硬。在奋不顾身的抢险中,主人公伊凡·彼得洛维奇有这么多功夫去回顾过去,思索人生吗?如果在真实的烈火抢险中,有谁如此“走神”,他早就成为火魔的牺牲品了。拉斯普京如此违背生活真实,自有他的迫不得已的原因:他必须要让主人公触景生情,长时间沉浸在过去中,这样才能展开政论部分。而政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部小说的主体的最重要的部分。
《悲惨的侦探》的结构没有《火灾》那么严缜,但基本方法是一样的:这部作品尽管名为长篇小说,但只写了主人公索什宁两天的经历:从头一天上午他到出版社开始,到第二天晚上,为邻居图特希哈奶奶举行的丧后宴之后。这期间,索什宁基本上没有什么行动,小说写的几乎全是他的回忆,也有超出回忆之外的,由叙述者全知全能的视角展开的故事(比如图特希哈奶奶的身世)。显然作家借鉴了意识流的表现方法,但是又基本没有触及人物的下意识。阿斯塔菲耶夫谈到《悲惨的侦探》时说:“《侦探》显得有些生硬和瓷实,因为它太短了。写这部长篇小说时我很少打底稿。有些地方径直由信息在活动,因为我相信很有素养的读者”⑨实际上这部作品也是由行动(很少)——回忆——政论构成的。
《断头台》的结构更复杂,甚至复杂到了被某些批评家称为“大杂烩”⑩的地步。作品包括三部,前两部写阿夫季·卡利斯托拉托夫与贩毒分子和枪手们斗智、斗勇、斗力,直至死于非命。后一部分写鲍斯顿因狼叼走爱子而杀人。把三部分连结成一个整体的“粘合剂”竟是那一对狼,它们才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主人公。在小说中除了对现实的描写之外,还由阿夫季引入了当年罗马帝国派驻犹太国的总督本丢·彼拉多审问判处基督的故事(这显然是对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模仿)。与前两部作品相比,《断头台》中现实的情节要多些,回忆要少些。但是,在有关阿夫季的部分(即前两部),政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除了我讨论的这部作品外,那个时期的其他作家也受到政论激情的诱惑,把文学的地盘拱手送与它,比如叶甫图申科的《伏库》(Φуку),切尔尼钦轲的《自己的面包》,小说(还不光是小说)政论化的趋势引起了作家和批评家们的关注。1986年1月,《文学报》上以“从政论开始(当今散文复兴的方法)”为题展开了讨论。批评家娜·伊万诺娃指出了散文政论化的弊端:“政论对散文产生的体裁方面的影响,尽管使主题从外部得以扩展,题材更加迫近现实,但这会使内部的艺术的说服力供血严重不足。演讲的雄辩战胜了艺术的说服力……艺术性被政化性吞噬同样是当前散文的现实的过程”。(11)确实,叙述作品应有的形象性在政论中消弥了。
其实,我们回顾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前苏联文学逐渐出现了一种内省倾向,而政论化不过是内省倾向达到相当程度的表现。前苏联文学在它出现的早期是充满朝气和动作的,那时的主人公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行动上了,没有如此的功夫来洞悉社会,反思自我。与这种积极行动相适应,作品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并且是外视角。如《铁流》、《毁灭》、《士敏土》、《青年近卫军》等等。大约是以《日瓦戈医生》为转折,内省倾向出现了。这种作品的特点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实际上不存在了,往往采用将视角限制于主人公的叙述方式,即作品中的一切,并不是由叙述者本人呈现。一切都通过主人公眼睛的折射,心灵的过滤。在这样的作品中,行动已经失去了价值,回忆、思索、顿悟,构成了叙事的动机。别克的《新的任命》、特玛托夫的《大地母亲》、邦达列夫的《岸》、顿巴泽的《永恒规律》等等,莫不如此。这种内省倾向可以追求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的反躬自问。在无休止的自省中,文学丧失了朝气,凭添了暮气。小说的政论化就是由这种自省倾向引出的。这种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欲望的主人公,在寻找自己与急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的契合点,而又没有找到的时候,既抱怨世道,又深深地自我谴责。在《火灾》的第十一节中,伊凡·彼得洛维奇发出了关于“周围世界颠倒混乱”,“你自己内心颠倒混乱”这样整整一节慨叹,这是这篇小说中两处最重要的政论之一。在这里,伊凡·彼得洛维奇强调了自己对自身的一切的责任。在《断头台》中,阿夫季·卡利斯托拉托夫的很多内心话语都是非常精彩的政论,在为人心不古而大声疾呼之时,他那种甘愿受苦的自白,具有明显的自虐情结,这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自省的主人公们是一致的。所以有批评家把他称为当代的梅希金公爵。小说政论的另一种形态是愤世嫉俗,这是一个道德完善、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发出的怒吼,或自我辩白。那段政论式的独白就成了无能为力的人的自我辩白。而那些在其他作品中俯拾即是的愤世嫉俗的政论,往往也是在没有行动或不能行动的时候,对行动的渴望。
因此,小说中政论的泛滥是有志之士悲剧境地的折射,也是好反思的民族性格的显现。
注释:
①《文学问题》,莫斯科,1986年第11期第82页。
②《文学俄罗斯报》,莫斯科,1986年11月28日。
③《立场·文学论争》第二集,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90年,第7页。
④《火灾》,《外国文艺》,上海,1987年第4期第76页。
⑤《忧郁的侦探——苏联当代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32页。
⑥《忧郁的侦探》,第298页。
⑦⑧《断头台》,外国文学出版社,第141页。
⑨《星火杂志》,莫斯科,1986年第31期。
⑩参见《文学与现实》第579页,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6年。
(11)《文学报》,莫斯科,1986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