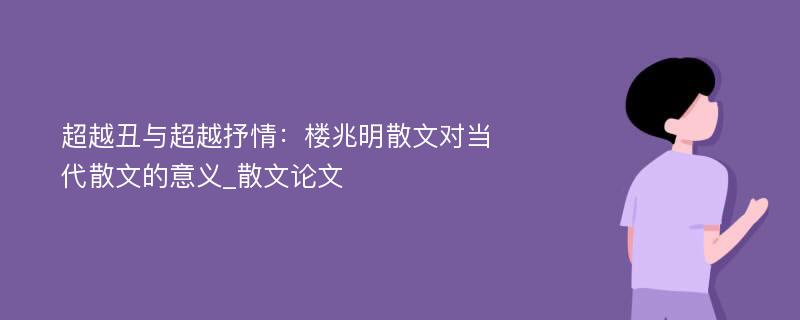
超越审丑 超越抒情——楼肇明的散文对当代散文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抒情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楼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楼肇明先生以研究散文理论著称,他的散文理论得到海内外华人散文家的重视,但是楼先生超越他理论的散文创作却一直为散文研究所忽视。也许这是因为楼先生的散文创作数量较少,至今只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一个集子《第十三位使徒》,第二个散文集尚在编定过程中。在将楼氏的集子反复读了五遍(这是很少有的)之后,我感到他的散文提炼了凝聚了一种不可重复的散文艺术人格,这不但与已经泛滥成灾的晚报散文风格,就是与余秋雨的智性与诗情融合的风格,张承志、梁晓声的思想锋芒毕露的大男子汉风格,李辉的历史文化心灵的探求风格相比,也显出了不同凡响的特点。上述散文家都在追求美与善,而楼氏的追求不限于美善,而是以形而上的沉思超越了审丑,超越了抒情。
在楼氏的散文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作品写得晦涩了一些,就拿也许是他最重视的《第十三位使徒》(不然不会拿来作书名)来说,在思想上,无疑是有纲领的性质。他以一本不存在的书为由头,从现代西方文艺史上的浪子尤内斯库、贝克特的荒谬中看到对现实冷漠世界的严肃的反讽,从伯格曼《第七封印》以丑为美中看到人性的堕落,接着是苏俄诗人勃洛克的《十二个》中的革命使徒,革命同路人作家拉甫涅列夫笔下的《第四十一》,作者文笔迷离恍惚,曲折盘旋,缺乏时间性和耐性的读者可能因此而迷失了追随的线索。然而,它所要揭示的是真正的能负起宣喻真理,追求人生真谛的当代使徒是个永恒的空缺。不管真诚的艺术家或哲人用何等创新的手法和怪异的方式去追求那理想的人生境界,都只能发现那不过是一个“浮在空中的不得其门而入的城堡”。在十九世纪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在“白痴”身上看到神性的使徒之魂的作家,到了二十世纪,“使徒形象的下滑和衰落已到了无可复加的极限”。加缪的局外人索默尔以个人的有罪之身承担了现代西方更大的罪行,在加缪看来索默尔虽然可以说是使徒的“替补者”,他也只是“以虚无反抗虚无”,已与小偷、流浪汉、杀人犯融为一体,失去了使徒头上理想的光环了(《第十三位使徒》)。接下去他把目光转向东方,比较了西方的神与东方的神(包括白痴)的异同。作者娴熟地驾驭着复杂的逻辑和飘飘忽忽的比喻,一再说明:整个陷入了文化危机。尽管如此,理想的使徒虽不存在,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梦”,正是这个梦中的人格追求,让他更多地关切人类生活境况和生存意义。如果我们不过分吹求他那多少有些晦涩的文风的话,并不难和楼先生一起在检阅现代艺术和文化思想史的历程中,去苦苦反抗世界文化危机,追求人生的终极意义,在充满感性的纷纭的形而下的形象和经典话语中去体验形而上的价值。
读这样的散文是不轻松的,要求读者动脑筋,甚至带着一种肃穆的心情去受他思想的折磨。
也许,在这通俗文化泛滥的时代,作这样艰难的思想跋涉是不合时宜的,然而作为散文智性风格创造和散文作家的人格提炼却是可喜的。虽然它不是完美的,可能过分飘忽,脉络省略过甚,但是它却有相当广博、相当深刻隽永的思想容量。
2
中国当代散文既是空前的繁荣,观念却也是空前的混乱。五六十年代主流散文观念是把散文当作诗(战歌、颂歌、牧歌),其社会功能是匕首、投枪。到了八十年代把散文当作诗来追求的杨朔、刘白羽模式遭到了冷落,散文的主流观念变成了“散淡”[①a]。许多作家都强调了散文的自由自在,在有心与无意之间,涉笔成趣。其实,这里说的是散文家族中的随笔,或者絮语散文的某些特点,对于随笔以外的散文,例如那些思想相当严肃的“大散文”,我们的理论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地、过细地概括。
在楼肇明的散文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他追求的并不是散淡自由而是苦心孤诣地表现自己知性文化心灵和文化人格的深邃。
当他面对世界和人生时,他既不是抒情的,甚至也很少是完整地叙事的,不论是面对人和事、物和情,他都力图把他文化心灵世界(或者图式)和外部世界作对比,有时是同化,有时是顺应,有时既坦率地表现自己的惶惑。不论受到什么刺激,从他内心世界、内在图式中激发出来的,往往并不限于形而下的情感,还有他关于宗教、神话、文化史、自然史和人的生存状况的焦虑和追索。
如果这种思考是抽象的,绝对形而上的,那么他在散文艺术上的创造也就不值得称道了,他那些最成功的作品常常能在最形而下的、最感性的现象中激发出相当深邃的形而上的哲思来。他有一系列属于旅行观感一类的作品,但是楼氏对当代旅游散文有相当尖锐的批判。他说:“光凭一双俗不可耐的肉眼和切割过的慧眼写诗作文的人,把诗写成导游说明书和商品推销广告是可悲悯的。”[②a]他甚至对于中国古代的山水游记也并不完全满意,他说:“中国古典散文中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往往让位给了写人与自然关系的散文了,对人自身的思考反而被忽略了。”[③a]对于中国古代山水游记作这样尖锐的批判,也许并不全面,但这也足以显示出楼氏作为理论家的勇气。更可贵的是作为散文家的执著追求。楼氏与一般散文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散文创作是带着理论的自觉性的。他在早年的散文诗中就追求过诗与哲学的结合,使浪漫的热情超越时空,而带上哲学的意味。到了后来,楼氏就在理论上明确了:“一方面生活的具象和另一方面的哲理的抽象所构成的艺术的张力,也是散文艺术的一个一般特征。”[①b]懂得了楼肇明对于形而上的哲思的偏爱,就不难理解楼氏散文的思想和意象的特异性。例如,面对三峡风景,我们已经有了郦道元的散文、李白的诗、刘白羽的和余秋雨的散文,这些都是名家手笔,风格形式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充满美感、热情、诗意,外部感觉在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刺激下迅速膨胀饱和。楼肇明的可贵在于他在《三峡石》中冲决了名家感觉透明的网罗。他在面对三峡石时感到的,或者说创造的是“宇宙被创造和被毁灭的历史”。
那不成规则的球形、椭圆形、圆锥形、圆柱形,你挤我压,交叠粘合,隆起上升,沉落倾斜,那经过生命和死亡的大轮回大劫难的一堆堆岩石的云团,岩石的羊群和牛群,被排闼而来的长江水挤开,在两边站立。[②b]
一向在诗人、散文家、画家笔下都是雄伟壮丽的三峡的自然景观,在楼肇明笔下竟是窥视“宇宙被创造和被毁灭的历史”的窗口和“经过生命和死亡的大轮回、大劫难”的遗迹。楼氏并不是以诗人的眼光去寻求三峡之美,而是以一个自然史学者,以一个宗教史学者的悲天悯人的目光洞察着人类生命的苦难的遗迹。他没有把三峡当作情感的载体,而是把它当作自然和生命兴衰“可解说的文本”加以解读,加以探索的。正因为这样,他所感到与其说是美的愉悦,毋宁说是盲目的自然力所造成的残忍和生命的悲壮。这里不能说没有激情,但是更多的是冷峻的悲悯、无奈的愤慨。
因此,三峡峭壁在他想象中是“岩石被送上旋风的绞刑架,从地质年代的墓坑里被挖掘到了阳光下,让苍天去冷漠地阅读”。也许,在中国散文史上,壮丽的三峡景观还是第一次和墓坑、绞刑架联系起来,而那些巨石的形状也许还是第一次在艺术散文中以“脱毛的骆驼”、“懒惰的家猫无所用心地弓腰”的煞风景的姿态出现[③b]。楼氏善于用他那“地质人类学”的想象加上人类文化史和人类生命生存状态的体验重塑人们早已在日常生活中和美文中司空见惯了的景观。从自然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他是相当冷峻的,可是从人的生命生存状态的体验来说,他又不能不流露出惶惑和焦灼。他因而老是无法摆脱深层心灵的危机感,在惶惑甚至在恐怖中直面人生和自然。
楼氏不是把散文当作消遣、当作游戏,而是当作生命的探险和灵魂的升华才不惜耗费宝贵的年华的。楼氏将散文作家定位于存在的诠释者和质询者的角色的岗位上,他是将散文作为“人类文化历史和人性运行的艺术方程式”的。他在《第十三位使徒》一书封面装帧中的那一段题辞说:“以个我未经污染的感受和体验,写人性和人类历史最一般、最抽象的方程式;以不可剥夺的憧憬和理性清理民族文化人格深处的心理积淀,寻觅两者之间那超越时空的永恒律动,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目标。”楼肇明的这一做法,事实上他是在努力实现惟有史诗和神话才可与之比肩的散文了。说改造也罢,赋予新意也罢,他所欲强调和赋予散文以新质的努力,即在对史诗性、神秘性和哲理性的涵盖、试验和实施上。
在四川乐山大拂前的一次旅游,他通过大佛的两只眼(法眼和佛眼)概括人和神、诗和宗教、偶像与精神解放之间的关系。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世俗的旅游变成思想的漫游,习惯于从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升华到形而上的庄严妙相。楼氏的全部散文创作立意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那就是“不断地探究自身”,“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他引用卡西尔的话说:“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之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之中”[①c],他的全部散文创作的核心主题就是“追索人类生存的意义”。在他自己的实践中,他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文化人格,在迷惘和怀疑中,在精神拷问和批判中,向往着最高精神境界,沉浸于终极关怀的智者人格。
在散文中表现自己的人格,现虽已成为普遍的潮流,但是在这么广阔的文化哲学背景上,在这么深邃的智性思考中,驾驭着那样诡奇的感觉,作着这么自由的精神漫游,达到这么超越的形而上的境界,在我国当代散文界还属罕见。
3
这自然得力于楼氏本身的内心文化结构的丰富,同时也不能低估楼氏自我表达能力。并不是所有散文家都能自由、自如地表述自己的内在文化心理结构的,相反,由于内在文化图式的抽象性,现成的流行的散文模式又有难以觉察的排它性,绝大多数未曾被名家表现过的文化心理因子和深部结构,往往被作家在不知不觉中窒息了。而在楼氏的散文里,则恰恰相反,他的文化心理因子和深层结构却得到了超饱和的表现。以他取都市卡拉OK舞厅场景为题材的《凶险的图腾》为例[②c],他对于夜总会的描绘和思索所调动的意象和想象的因子,从最现代化的物质文化引发起最原始的宗教文化的联想(如把夜总会的迪斯科和霹雳舞比作“奠祭人性的仪式”),在现代科技设施的描绘中调动了西方达达主义立体派绘画的“不似之似”的变形技巧。如把旋转灯光扫过时,扭动的躯体写成切割成片片断断,把人的肢体变成原件,在拼凑和组装,从反面联想中他否定了它和汉墓砖刻上的狩猎和农耕的相似,从正面智性的批判中,他把人在物欲统治下的精神分裂和疯狂比作回旋加速器上质子、介子、中子,从原子核中分裂出来的景象,说明楼氏心理感受机制中有一种特殊敏感和灵活的反弹性能,凭着这种性能,楼氏能很轻松地通过一个感受的焦点把他的文化学养自由地释放出来。正是借助于这样的学养,他才构成这么怪异的意象和独特的话语。结合着他基督教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层次分析,他对现代城市物质文化畸形发展,精神空前贫乏作出了批判:
躯壳和皮囊表现着灵魂受难的活剧。那埋藏在最深处的第二第三魂灵,从获得暂时的解脱中大摇大摆,狂呼乱叫,装模作样地模仿其受压迫、受挤压,毫无自卑之感,毫无羞怯之心,解脱即放纵,放纵即净化,卑猥和雄健倒错,渺小和崇高易位,自我作践和自我怜悯成了最神圣的自豪感,仿佛在风雨中祈求宁静的光荣旅程,临了只余下瞬息间的麻醉和浑然忘却。[③c]
楼肇明就想到了这么多,概括得这么深。这种深度,不仅仅是学养的深度,而且是精神追求高度的反照。更可贵的是所有这些反照都是用楼肇明那相当独特而丰富的感觉,用充满书卷气的隐喻表述出来,他把夜总会中缺乏精神内涵的笑脸形容为“印刷机印刷出来的木然的笑容”,把现代都市的娱乐暗喻为“现代人的祭祀”,以此来批判现代城市大众文化缺乏终极关怀。
4
在当代散文逐渐为闲适小品所淹没,散文的文体意识不觉为随笔意识所束缚,楼肇明引用英国亚瑟·本森“随笔作家乃第二流诗人”以示轻视。楼氏以他散文比他的理论更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他同意西方有些评论家把散文定义为“思考着的人格的艺术体现”,不过不是像在诗中那样经过“一番修饰幻化、愿望化的处理”,“散文作家的自我人格要依赖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的原装货”,“容不得人格错位脱节的现象”。他主张散文“采取随机和散漫”的方式[①d]。自然,随机散漫有利于从某种诗化的集中模式中解放出来,但是也容易流于轻浅。楼肇明自己的散文,就其比较成功的而言,都不属于轻浅散淡之列,相反,倒是苦心孤诣地追求深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追求“生活图画的本体象征”,但是如何将“思考着的人格”艺术地而不是概念地体现出来呢?又如何使生活图画的本体成为深层意蕴的象征呢?他在分析杨绛的散文时指出了她“具有思想高度的自审心理”,触及了一点要害。
事实上楼肇明思考着的人格之所以能得到比较艺术化的体现,其原因就在他在散文中的思考,常常是借助“有思想高度的自审心理”来将对外部世界的感觉和内心世界的学养结合起来,形成楼肇明式的审美话语。
楼氏内心世界的学养,无疑地深化了他稳定的审美图式。这种审美图式以其高度活力同化着、选择着、组合着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且赋于其意蕴。在他的散文中,自然不乏早期充满诗情的散文,带浪漫色彩的散文诗,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也有楼肇明式的对自然、生命的哲理思考。他常常把时间、空间自由地放大缩小,以便于他对自然史、生命史、文化史作超越现时的共时性俯视。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审美图式是以生命哲学为中心的,他的审美价值取向,也是以生存状态的关注为纲领的。
身居美国的台湾散文家王鼎钧先生,认为楼氏散文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新派散文”。因为散文这种形式向来是为真的理性、善的德行和美的抒情所君临的天地,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很少有散文家有足够的勇气,在这种形式中不作美的探索,当作审丑的历险。即如王鼎钧先生称为“动物散文”的写鹰、大雁、八哥的一组作品,表明了他从审美的形式规范中开拓求索,找到了自己审丑的突破口[②d]。他自己在本书的《自叙》中说:“早期作品以刻画人性的纯美为宗旨,中间有一个从思想到审美的转折,力图在这一文体中恢复从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到鲁迅的《野草》这一审丑的现代主义传统。”[③d]
楼氏的审丑与上个世纪象征主义者充满了感官刺激不同,也与鲁迅的《野草》所流露的清醒而痛苦、探索而又绝望异趣,楼氏的笔锋,更带睿智的沉思的色彩。不论牺牲的雄鹰,还是中了人类奸计的大雁,冤死的八哥,误人子弟的教师都只是他思绪的经络上的一个穴位,点中了这个穴位,其功能就弥散到穴位之外。他总是习惯于超越具体的事与物、时与空,从容不迫地升华到对人类命运宿命式的思考。但又回避作出哲理性的结论,即使有吉光片羽理性格言的闪光,但又总是淹没在游移的、充满苦苦思索而又难免有结论不明确、不完整的遗憾。而正是这种看来无结果的探求中交织着不疲倦的睿智和平静的隽永的艺术张力。这种张力,正是楼氏智趣之特点。
把审丑提高到形而上的层次,同时享受着美学和玄学不可排解的焦灼和隽永的微笑,是楼氏智者文化人格的一个侧面。
5
然而楼肇明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充满不确定的犹豫和焦灼的。当他把过分形而上的眼光转向生命本身,包括丑和恶的各个侧面时,他的笑容就开朗得多了,他的智慧的光华就能充分地照彻他所描述的形而下的世俗生活。这时,他对生命的理解就显得特别的明确,他对生命现象表现出了少有的洞察力,连他的行文风格也一扫晦涩神秘的云雾。这时他就写出他在思绪的深度上和表现的力度上最统一的作品,譬如说《刺猥宴》、《鸡之圣》、《四月,玩过就扔掉的爱情》。
《四月,玩过就扔掉的爱情》,开头写的是纯美的爱情的萌动,接着就毫不手软地对这种浪漫的诗情施以残酷的打击,永恒的世界本体为一幅蛇的交媾的景象所代替。在这里出现了生命的贪婪和冷漠,令人震惊。楼肇明笔力相当不凡,也许这正是楼肇明写得最精彩的、最有语言冲击力的地方,楼肇明式的刁钻古怪的才情最充分地得到发挥:
这幕戏的开头我没有看到,我观摩到的已经是高潮和尾声了。它们像两股麻花、幽蓝色的钢缆绞在一起,呈菱形的鳞片支楞着,扭绞着,滚打中嚓嚓有声,暗红色的火花,明明灭灭,似乎是把仇恨撒落在灰褐色的泥地上……它们嘶嘶咻咻了一阵,沉默了一阵,又嘶嘶咻咻了一阵,蛇信和尾巴是传达爱抚的双手。有多少爱抚就有多少等量的仇恨,就像一对势均力敌的盗贼在抢劫掳获的赃物,搏斗、拼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赐予就是占有,占有就是赐予。情欲的贪婪是惊心动魄的,连短暂的和谐也像粗野的阴谋。[①e]
本来光是这二蛇交媾细节就够惊人的了,更令人震惊的是楼肇明对这种生命本能的理解,这种自发的生命的冲动正是人类性爱的隐喻或象征。这种性爱经楼肇明的感觉图式同化后,与恨等量交织,在这种生命的奇观中,爱的强烈,正是“贪婪”的表现,因而在死去活来的相互需要中,楼肇明最敏感的是那些不善又不美的东西,他用了“仇恨”来形容还不够,又加上了“盗贼”、“阴谋”。
楼氏对于恶似乎比对于善更有洞察力,更深邃的是他发现在你死我活的情欲之后:
我知道在情欲冷酷的序列表上,蛇并不名列榜首,蜘蛛、螳螂才是最为不齿的,但是我还是错了。我原以为拒绝了食夫惨剧的蛇,情侣们的告别,终会有一番缠绵悱恻,天地低回的表现。纵然是萍水相逢,没有引诱,也曾倾心,纵然是劳燕分飞,无须再见,来年的四月还有预期。我只见泥路上掠过一阵惊风,路边的草丛划开,眨眼间大路上又一无所有,只留下我这呆看客在凭吊一片光秃秃的灰白了。[②e]在这里,楼肇明以他惯常的概括方法,把这一切归之于“生命力和情欲的残酷”,使他震动的不但是欲的贪婪和情的寡薄,而且是“宇宙秩序”本来如此。这里最令人难忘的不仅仅是情欲中包含着阴谋和仇恨,得到满足以后的冷漠,而且还有理所当然地如此。
对于人情有着多元的洞察,对于生命有着形而上的理解,楼肇明更加多的是对于生命本体的时而困惑时而看破。在这方面,浪漫的热情和智者的理性都成了陪衬,因而他不像许多学者散文家那样,花很多篇幅去引经据典,他只是在热情与智性之外,稍稍展示了一种狡黠的揶揄,然而又欲说还休地声称“谐谑不起来”,这样丰富的物象和这样复杂的心象结合在一起,使得楼肇明的散文风格、散文艺术人格充满复调的和声,这是与一般散文的单纯风格迥然有别的。就说蛇的交媾,他说他不知道如何来“揶揄”这路遇的情欲剧,“因为它既不崇高,也不滑稽”[①f]。好像他宁愿作一个形而上的智者也不愿作一个审美或者审丑的艺术家似的。其实,他毕竟是醉心于审丑的创造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审丑放在形而上的框架之中,而形而上的思辨对艺术的审美与审丑常常起某种消解作用。这是楼肇明的矛盾。他经常以一种宗教哲学眼光看芸芸众生。老是沉湎在放大了的微观时间和缩小了的宏观时间里,难免觉得人生处在一种荒谬的悖论之中,有点像西方现代派浪子文人那样有点虚无,惶惑于生活、世界(自然)、人生都缺乏足够意义。因而他对于生命现象时时有掩饰不住的冷漠,他时常自称为“看客”,这时,就无所谓美丑、悲剧、喜剧。但是他从本质上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诗人,因而他在审丑过程中就克制不住自己的激愤、讥嘲,乃至作刻毒、刁钻的讽喻。他这种“看客”并不是完全旁观的,他常常无法压抑自己对生命本体的欣赏,甚至把生殖力很强的乌骨鸡称之为“鸡之圣”。有时,哪怕是在外表看来是滑稽乃至卑琐的现象中,他也看到了生命的奇妙。这时这位“看客”居然有时幽默起来,很难得地以喜剧情调,写出了他可以称之为绝唱的《鸡之圣》。
那只生命力、主要是性生命力很强的乌骨鸡。楼氏欣赏他“情场上”的计谋和力量,赞赏他把“绅士风度和强盗品格完美地统一了起来”,在决斗中有“青皮无赖”式的顽强,无往而不胜地“展开了以掳获和侵占别人妻女为目的的征讨”,在得胜之后,便有“峨冠博带的王者之风”,使全村的母鸡变成了它的“嫔妃姬妾”。甚至在一次鸡瘟中,它成了唯一的幸存者。新一代的母鸡们又无一不成为它的臣属和嫔妃。每一次“婚配仪式”后的高歌,被楼肇明称之为“物竞天择的胜利之歌”。楼氏在对之尽情反讽调侃的同时,禁不住对它“超凡的生命力,它的生殖力叹为观止”。楼氏很少对形而下的事情作连续不断的描述,通常都是以一件事实的片断和他思绪的板块作浮动性组合,然而这一篇(和另一篇《刺猬宴》)是例外。而这一篇之所以可以称为当代散文之杰作的原因,是否可以归结他自己所倡导的“人类文化历史和人性”的艺术方程式呢?是否可以归结他所追求的“史诗性、神秘性和哲理性”呢?乌骨鸡王的行状确是仿史诗英雄的征程的,它的“乌鸦的私生子”抑或“鹰的后裔”的不明身份,无疑是一种图腾的翻版。到文章结尾处这只乌骨鸡又逃脱了一次横遭宰杀的灾难,挨了刀,血流了个半死不活,居然能挣扎着躲起来,直到可以“艰难地挺着脖子,竖着脑袋”行走。奇迹似地康复之后,仍然统治着它的臣民,令行禁止,母鸡们仍然排着队等候它的恩宠。后来为治疗一位画师的不育,这只乌骨鸡被无辜地阉割了。画师并未因此使他的妻子受孕,而这位鸡国之王者却失去了雄性功能,只在夜间警觉地守卫着鸡巢,扮演着“不是父亲,却是父亲,不是祖父,却是祖父”的不可替代的家长角色,最后牺牲在与黄鼠狼的搏斗中,黄鼠狼为此胜利留下了一颗带血的眼珠。
这最后牺牲的结局,使得楼氏的幽默与调侃的轻喜剧风格,愚昧和正义本为一体的悲剧美学主题变成了正剧,有了这一笔,凭添了一种“间离”效果,更引出了楼氏特有的另一番形而上的思绪,这种思绪由于赋予楼氏学养中颇有特色的佛学话语,楼氏的神来之笔就出现了:
我和我师父离乌骨鸡王的精神太遥远了。乌骨鸡亦魔亦佛,由魔入佛,入佛非易,魔非天成。魔佛莫辨的生命本性,倘若没有自身可以探幽索微的基础,往往越是深究就越是混沌一片了。[①g]
这里的形而上不像楼氏其它散文那样直接、反复,那样借助大量形象的隐喻,不那么晦涩,因而既能充分表现楼氏睿智的深邃又能有充分的感性色彩。正是这样,楼氏创造了一种在当代散文史上毫无依榜的仿史诗风格和戏拟风格。
这种风格有相当丰富的内在结构,在现实场景的白描中透着调侃,在反讽中又掩饰不住欣赏,在二者互渗中又升华到宗教哲学与生命哲学礼赞,而在礼赞之后,往往禁不住又要调侃一番。这在《暮色忆念中的大佛》的结尾表现得尤为精彩。当作者正沉浸于“诗与宗教之谜”,人格神偶像与人性自由的矛盾的庄严思考之时,楼氏笔锋一转:
我悠然自得,踌躇满志地沉思在冥想中,耳边猛地传来几声大炮轰鸣、晴天霹雳般的巨响,一连串“阿秋——阿秋”的喷嚏声。我坐不住了,恼怒地站起来走到儿子的房间里,我看到这个小捣蛋用纸捻子在捅自己的鼻孔。一阵短暂而又尴尬的沉默。儿子笑嘻嘻地说:“爸,我在作试验呢,一篇科普文章上说,喷嚏与飓风的时速相同相等。”[②g]
这里由三组对比构成的:第一,庄严妙相的哲学沉思与孩子的顽劣的捣蛋;第二,儿童的顽劣煞风景又与科学的精确数据相对比;第三,父亲的恼怒和儿子的嘻皮笑脸形成对比,都有不伦不类的性质,本来是不属同一范畴的事,偶然地凑合在一起构成了无类比附的谐谑之趣,而这三组对比之间本身又形成了不伦不类的反差,因而其幽默的效果才更强烈、更隽永。
楼氏习惯于在形而上的求真和形而下的求善之间寻求怪异和庄严的错位,在审美和审丑之间捕捉反差,因而他的散文天地特别广阔,思绪特别自由,幽默感具有某种多声部的复调性质。
尤其在《万石园》等作品中他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不仅是用来对读者作想象定势的冲击,而且用来作形而上的沉思的诱导。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读懂结尾处的哲学、历史、寓言的观念,但在想象与心智的升华上则完全是一次新异的享受。这对于散文艺术想象天地的开拓无疑具有不可小觑的历史价值。
我们的散文评论家也许过分地给了一些在艺术常规之内的流行散文以太多的注意了,而对突破常规的散文家的关注太少了,这也许有某种人为的因袭或自然的因素在作祟,关键的是这会使得文学评论家艺术鉴赏力的钝化和贫困。
6
楼肇明散文中形而上的成分制约了他对生命本体的热情,他的美学原则不是由激情主宰的,相反,他认为在当代,正是以激情贬值为特点的,他的激情未走向浪漫,而是走向冷峻。“冷峻能够抒发激情,正是当代美学中的第一大课题”[③g],这也是楼氏的夫子自道。在楼氏的散文中,冷峻的外部感觉和内在激情、焦灼、危机感相互交融,因而我们在他的作品看到了不是对鲜花,而是“对枯枝败叶的偏爱”,但是他又不颓废。他不否认枯枝有绝望挣扎的姿态,他从中发现了美,把它称之为“不朽的雕塑”[④g]。他冷峻,在对于他所礼赞的生命现象的一种超然的心情,从形而上的角度观之,从缩小了的时间来看起点和终点,太阳和墓地连接着,生命暂短得可以略而不计,他时而悲观、怀疑、看破红尘。从形而下的角度观之,他对奇妙的生命现象的礼赞也往往带着反讽,然而对于恶和丑又刻毒又愤激,双向互动式地交织着对生命本体欣赏和批判,《四月,玩过就扔掉的爱情》有云:
渐渐地,我作为一名生命力的观赏者,被冗长的乏味的剧情,拖疲沓了。我终究是一名被迫的看客。
痛苦没有导致清醒,理智导致迷惘,楼肇明为自己刻画了一幅痛苦而迷惘的心灵肖像。这样,他把主体的投入和旁观结合起来,在这里,“自我”作为认识主体和同时作为认识的客体,一个层面上的分离,一个层面上的融合,先是“一分为二”,继而又“合二为一”,这在智者散文中可谓独树一格。他的激情只有面对丑恶才充分激发出冷峻来,他审丑时形而上的冷峻始终与他对丑的愤激有矛盾。他在微观中对恶、丑、庸的痛恨时时被他宏观的洞察中有所消解。正因为这样,他不论是对于沉重的文化遗产的批判,还是对自我的解剖都是十分宁静的,也就是既不怕丑,也不怕恶的。形而上的逻辑不是偏激的,而是全面的。冷峻要求客观,乃至无动于衷,没有任何偏激的情绪、片面的逻辑。但激情却偏偏不能离开极端的逻辑,这样,就造成了楼肇明散文中比比皆是的二者的张力,这给楼肇明的本来有点抽象智性的话语增添了动人的感性色彩。在《不能出卖的影子》中,一方面是冷峻地承认某种现实的悖论:青春的梦(美神远了)幻灭了,但是又说,梦幻和我都是历史的过客,都不能出卖,既非我粉碎了障碍,又非障碍粉碎了我,但是历史的过客中又成为历史的见证。所有这一切在形式上都相当全面,但在内容上却相当富于激情,尤其是轮到自我解剖的时候:
在自我的世界里,我是我自己的对手,也是可耻的同谋,面对这一片发了疯的土地,我甚至没有一则温柔的日记,没有一纸痛苦的祈祷书。
形而下的撕裂和形而上的统一,爱的阻扼到缺席空位的爱的统一,这是楼氏在形而上层面的一个一以贯之的线索。
7
在楼肇明与笔者多次私下的闲谈而未及形诸其文字的言论中,他批判有些作家文化人格面具太厚。他说:“人人都会有一副乃至几副文化人格面具的,对文化人格面具的批判,特别是对自我所选定的文化人格面具的批判,是散文家义无返顾、通往深刻的必由之途。没有面具,就没有灵魂的深刻性(尼采),人格面具是一种可见的超越性(萨特)。但同时,面具是一个灵魂的城堡、掩体、盾牌和甲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格面具,与作家的自我人格角色定位有关,是自我、本我和超我一个结构功能性的混合物……。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有自我萎缩和自我膨胀的两个极端,但其共同的是其文化人格面具的符志化、掩体化、武器化功能被强化了,而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却反方向地弱化了,乃至相当大一部分通道被其人格面具所堵塞了,凋零了。文化人格面具也是一把双刃剑,不是反弹,面具还有面具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楼肇明关于文化人格面具学说中的两个主要观点:与作家的角色定位息息相关;与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息息相关。楼氏偏爱繁复的意象和本体象征,偏爱“复调”,《啊,老师……》一文有云:“一个主题中包含两个母题,一个意象里容纳两个缩影。在两个层次和两个侧面上展开。”[①h]这是他从自己评析帕斯捷尔纳克“复调诗歌”中所挪借过来的,也不妨视为他的“复调散文”的一种图式;被西方文论家们指出的“史诗性直喻”,(即对喻体的描绘极尽笔歌墨舞之能事,达到浓墨重彩、排山倒海般地描绘被喻体的艺术效果),前文援引的《三峡石》、《凶险的图腾》等作,即是例证:想象层面上的超现实主义的奇诡怪诞,在修辞层面上偏爱“矛盾修辞法”(或曰:“诡论语言”),例如他每每在要紧处装聋卖傻,说得好听叫“大智若愚”,说得难听一点是刁钻古怪,甚至刻毒,他偏爱用陈词滥调去形容霉烂腐败、华丽俗气的美,反讽的艺术效果也由此凸现出来……所有这一切,即是他的“诗性阐释”或曰“诗性思维”的特点。
楼氏由审丑而冷峻,冷峻为超越浪漫、潇洒地抒情,他说的“冷峻抒发激情是当代美学前沿阵地上的一大课题”,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概括,我们粗略分析一下他的创作实践,即可发现“冷峻”的前提条件是“离间”和“距离”,“冷峻”是对激情的审视和提炼,归根结蒂是对“认识主体”的一种拘囿,有时还是一种不信任或疑惑。冷峻不是不要激情,而是不要作为激情的附加物的浓烟和感伤,它要的是高温的蓝色的火焰和不见火焰的冷炙。楼氏将“冷峻”视为浪漫、悲伤的解毒剂和冷却过滤器。手段有三:其一,为“悖逆离间”,以一种对立的情感去削弱占主导地位的情感,不是在黑白反差中加深其对立的鸿沟,而是达成某种中和与平衡,他写得最成功的作品,以喜写悲,以悲写喜,亦悲亦喜,悲喜莫辨。其二,是用相比邻的情绪去稀释和淡化占主导地位的情绪,或者拿相距遥远、不相干的事情拉到镜头前进行比附,“宕开一笔”,在对立情思之外“斜刺里”杀出第三种情思,或可称为“枝杈离间”或“旁支离间”。其三,楼氏的思想者身份、学者身份、诗人身份在作品中是三者统一的。以理入情是他的看家本领,每当以情入文时,他也往往迫不及待地将抒情升华为理,返情入理,在情和理的悖逆中完成其情思和话语流的统一。不过,这已不是我们传统中的情理交融的统一了,在楼肇明的成功和留有缺憾的作品中,情理之间,都或多或少存在一种情、理背反的苟安。楼肇明的冷峻抒发激情,显而易见,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散文”,如香港的也斯、台湾的林耀德那样,“后现代主义散文”是“作者的死亡”、“情感的零度介入”,几乎是完全废止抒情的,放逐抒情的。“冷峻抒发激情”,或者说它的“离间”原则,这虽不是楼氏的首创,仍不能不说,对正在走向繁荣的中国当代散文来说,为拓展思维空间,春风化雨,带来了蹊径和助力。
楼氏主要是一名散文和诗歌的理论家,散文创作是他的“左手的缪司”,他时而理论先于实践,时而实践先于理论,他的理论是后设的,且烙上了强烈的个性印记。不过,两者孰先孰后,无关宏旨,两者都不是一蹴而就,前后有变化、有发展、有修正,从“人格智慧的艺术表现”说到“人格面具论”即可佐证。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名散文作家的楼肇明,不论其理论的自觉性如何清醒,在其作品中仍会留下作为理论家的楼肇明所未曾意识到的,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东西的,此即“形象大于思想”,“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之谓也。当他的创作主体拥抱世界时,始终未曾忘记过主体同是一个认识的客体。这是他“冷峻抒发激情”的根本由来,他的论说是作品的参照系,理性是作品的主导光源和框架,但作品的张力并非来自由理智(或思想浮动的板块)所组合成的理性磁场,艺术张力只能来源于心灵深处的艺术转换。因此,楼氏作品仍然是他的论说无法遮蔽和拘囿的,逸出其理性框范,用不着诧异,不同的评论者有不同的评说,也不意外。
中国当代小说和诗歌早已接受西方现代诸流派乃至后现代诸流派的影响,作了许多成功的和牺牲惨重的试验,而中国大陆散文则似乎特别具有大将风度,至今除了个别少数作家有所尝试以外,探索性散文寥寥无几。楼肇明的散文显然是吸收了西方当代哲学思潮和文学观念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楼氏并没有狂热地以颠覆中国古典和现代散文传统为务,他似乎是力图在诗情和智性,形而下的写实和形而上的超越,传统价值观念和现代西方价值观念之间,在叙述、描写、抒情的连续和纷繁的以隐喻为特色智性思绪板块组合之间寻求某种综合和平衡。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都是创造性思维,但创造性思维并不排斥综合和平衡,因此,这就使得他的创造有了某种只停留于逆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而未曾抵达的历史的启示性。
1996年3月17日
注释:
①a 钱谷融:《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北京)。其实钱先生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念,不过他概括得很准确,我本人也曾有过类似的散文观念。
②a③a 《第十三位使徒》(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北京,第178页)。这里虽然说的是诗,从上下文来看,也包括散文。
①b②b③b 《第十三位使徒》,中国对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85页,第213页,第12页。
①c②c③c 《第十三位使徒》,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3页,第242-244页,第243页。
①d②d 《第十三位使徒》,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57页,第67页,第383页。
②d 美国纽约《侨报》,1995年10月26日。
①e②e 《第十三位使徒》,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16页,第217页。
①f 《第十三位使徒》,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18页。
①g②g③g④g 《第十三位使徒》,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81页,第222页,第217页。
①h 《第十三位使徒》,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