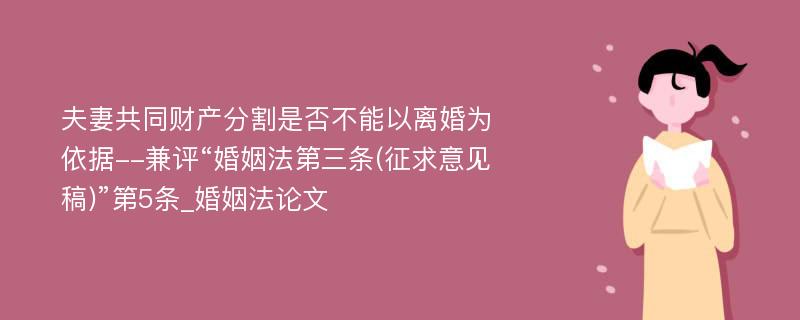
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可否不以离婚为前提——兼评“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5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婚姻法论文,不以论文,征求意见论文,财产论文,前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6-0123-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须以共同关系的解体为前提条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这几乎已成共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99条似乎为夫妻共有财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分割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将这一条款适用于夫妻共同财产制时,我们可以理解为:夫妻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共有财产时可以请求分割。所谓“共有的基础丧失”系指离婚,婚姻关系解体,应无疑义。但何谓“重大理由”,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一直未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说明。
新近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第5条似乎可以视为对《物权法》第99条的一个注解。该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一方在夫妻因感情不合分居期间及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所谓“可以受理”,应理解为“法院可在不判决离婚的前提下,准予分割夫妻共同财产”①。因为作为这一条款的“但书”部分,其前提条件仍然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但书”部分可看做是对《物权法》第99条中“重大理由”的一个说明。
问题在于,“但书”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夫妻因感情不合分居期间及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这一时间上的限制是否必要?难道“重大理由”只可能发生在这个期间吗?从第5条的文字表述我们不难揣测最高院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基本立场:首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是不可以向法院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其次,法院准予分割仅在夫妻一方“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时,因此,“准予分割”显属例外情形;第三,人民法院准予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须以“不损害债权人利益”为前提。下面,本文就结合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征求意见稿第5条所体现的上述立场加以评析,并冀望“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这一议题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和讨论,以期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二、比较法上的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包括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以及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混合制(第19条)。适用何种财产制,可由夫妻自行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该法第17、18条所确定的法定财产制。相对于分别所有制和混合制,共同财产制在我国的适用有着更为深厚的历史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1]104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夫妻分别财产制已经具备了越来越强的适应性。遗憾的是,我国《婚姻法》虽然规定了三种夫妻财产制,但理论与实践都片面认为,夫妻或家庭的共有财产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不得分割,其分割必须以共同关系的解体为前提条件。②这意味着:三种夫妻财产制,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并贯彻始终,而绝无中途变更的可能。当事人只能在缔结婚姻的初始阶段确定选择何种夫妻财产制,然后一以贯之。但在现时社会,当事人多数情况下是不经约定而自行受到法定财产制的约束,如何创设一种机制,使夫妻一方在个人财产利益出现危机时通过行使分割请求权来维护自己在共同财产中的应有份额,或者在需要共同财产来履行法定义务而自己又无法处分财产时,通过行使分割请求权来获得对自有财产的现实处分权利,实乃婚姻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之所以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亦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是因为:其一,前述情形未必导致婚姻关系的解体,所以没有必要以离婚作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前提条件;其二,把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与婚姻关系的存续适度分离,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财产的价值,发挥财产的效用。
综观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变更夫妻共同财产制是非常普遍的一项制度,只要符合法定事由,夫妻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提出变更夫妻财产共同制的诉求。
(一)法国
《法国民法典》第1443条规定:“如因夫妻一方理事混乱、管理不善或行为不正,继续维持共同财产制将使另一方配偶的利益受到危害时,该另一方配偶得诉请法院分别财产。”与征求意见稿第5条相比,法国法强调的是“另一方配偶的利益受到危害”,而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在此强调“夫妻共同财产利益”,显然不合时宜。因此,征求意见稿没有必要在列举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理由时,强调对“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维护,因为夫妻双方在财产利益上的共同性在这个时候已经降到了最低。
(二)德国
《德国民法典》也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变更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具体情形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在符合法定事由的前提下,夫或妻一方可通过向法院提起取消之诉(Aufhebungsklage)来分割共同财产。所不同的是,德国法将夫妻财产共同制区分为两种:一是由夫或妻单方对共同财产进行管理的财产共同制,二是由配偶双方对共同财产进行共同管理的财产共同制。对于第一种财产共同制,取消之诉又分为共同财产的非管理方提起之诉和管理方提起之诉。《德国民法典》第1447条规定,非管理方提起取消之诉的法定事由包括:(1)管理方无管理能力或者滥用管理权,使其将来的权利可能显著受到危害;(2)管理方违反其协助扶养家庭的义务,并且就将来而言,扶养有显著受到危害之虞;(3)管理方自身招致的债务让共同财产负债过度,致使非管理方日后的收益显著受到危害;(4)对共同财产的管理属于另一方的照管人(Betreuer)③的职责范围的。第1448条规定,管理方提起取消之诉的法定事由仅一项:非管理方在配偶双方的相互关系中负担的债务,使共同财产负债过度,致使管理方日后的收益显著受到危害。
对于第二种财产共同制,即由配偶双方对共同财产进行共同管理的财产共同制,《德国民法典》第1469条规定,在有下列情形时,配偶任何一方都可以提起取消财产共同制的诉讼:(1)另一方单独实施了仅得共同实施的管理行为,使其将来的权利可能显著受到危害;(2)另一方无充足理由而坚决拒绝协助对共同财产进行通常的管理;(3)另一方违反协助扶养家庭的义务,使其将来的扶养可能受到显著危害;(4)因另一方自身招致而由双方负担的债务使共同财产负债过度,使其日后的收益显著受到危害;(5)另一方基于财产共同制而享有的权利被其照管人的职责范围所涵盖。
上述取消之诉获得胜诉后,财产共同制被取消,夫妻双方适用财产分别制,婚姻关系并不因此而解体(第1470条)。
首先,与《法国民法典》第1443条相类似,《德国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取消之诉的法定事由,强调的也是对原告财产利益的维护,而不是像征求意见稿第5条那样,强调“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其次,法国、德国民法典对原告提起分割共同财产的诉讼都没有像征求意见稿第5条那样附加“在夫妻因感情不合分居期间及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这样的时间条件。
(三)日本
《日本民法典》第758条第1款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可见在日本,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适用夫妻财产共同制,夫妻一方不得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也是一项基本原则。其例外是第2款规定:“夫妻一方管理他方财产,因管理失当危及该财产时,他方可以请求家庭法院许其自行管理。”以及第3款规定:“对于共有财产,可以与前款请求一起,提出分割请求。”从这两款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与法国法、德国法中的规定相一致的结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均不强调“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不以“夫妻因感情不合分居期间及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作为时间限制。
(四)台湾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一方在不离婚的前提下提出分割共同财产的法定事由作出了明确规定,其第1010条第1款:“夫妻之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时,法院因他方之请求,得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一、依法应给付家庭生活费用而不给付时;二、夫或妻之财产不足清偿其债务时;三、依法应得他方同意所为之财产处分,他方无正当理由拒绝同意时;四、有管理权之一方对于共同财产之管理显有不当,经他方请求改善而不改善时;五、因不当减少其婚后财产,而对他方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有侵害之虞时;六、有其他重大事由时。”
与前述立法例相比,台湾地区的立法同样不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中强调“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不以“夫妻因感情不合分居期间及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作为时间限制。所不同于前述立法例的是,台湾地区“民法”在列举分割共同财产的法定事由时,增加了“有其他重大事由时”这一兜底条款,这意味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此获得了适用的空间,说明台湾地区的法定夫妻财产共同制相较于前述国家更为松动。因为法国、德国和日本对于此种情形之下对法定事由的列举,均属封闭性条款。征求意见稿第5条对法定事由的列举,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之后附加了“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从文意解释来看,将“(其他)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视作兜底条款也未尝不可,但正如本文对于前述国家和地区立法例的介绍,其均不以维护“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必要条件,因此第5条中的所谓“兜底条款”其实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若改为“等严重损害夫妻另一方财产利益的行为”,才更符合现实中夫妻双方在此种情境之下的对立状态。但问题是,有必要在此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吗?既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我们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什么又通过兜底条款的立法形式对这项原则的贯彻采取了松动主义?我们可否像法国、德国和日本那样,通过封闭性条款的立法形式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呢?
三、征求意见稿第5条评析
我国《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均未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作出规定。因此,征求意见稿若通过生效,其第5条将成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指南针条款,意义重大;该条款也是对《物权法》第99条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中的适用所作的回应,尤其是对《物权法》第99条中“重大理由”的有权性解释。因此,我们应本着最大限度促进婚姻关系稳定、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和最大限度发挥财产效用的三项原则来审视这一条款的立法效果。
(一)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不得向法院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基本原则
夫妻双方在婚前或者结婚登记之时,均可对夫妻财产制做任意约定,这是私法自治原则在婚姻法领域当中的具体体现,也为大多数国家立法所承认。但是,在婚前未做约定时,婚后是否仍可任意约定?因为大多数国家立法均规定,夫妻双方在缔结婚姻时,如果未对夫妻财产制做约定,那么径自适用法定财产制,即夫妻共同财产制。如果允许夫妻双方在婚后才对财产制做有别于共同财产制的约定,那么意味着:只要夫妻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便可不经法院裁判而对法定财产制作出变更。大陆法系各国对此规定略有不同,法国和日本是禁止主义,其中日本是严格禁止主义;德国和台湾地区是许可主义。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不得向法院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却是一项普遍的基本原则。
《法国民法典》第1387条规定:“仅在没有特别约定时,夫妻财产关系,才适用法律之规定;夫妻之间的特别约定,只要不违反善良风俗和以下各项规定,如其认为适当,得随其意愿订立之。”但第1396条第3款规定:“结婚一经举行,只有在分别财产或采取其他司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应夫妻一方的请求,或者在以下条款所指情况下,应夫妻双方的共同请求,依判决之效力,才能对夫妻财产制进行变更。”可见,在婚姻存续期间,未经法院干预,夫妻双方是不能随意变更他们之间正在适用的夫妻财产制的,尤其是在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应当事人请求可由法院通过判决所作的变更,仅限于“在分别财产制或采取其他司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而且,未经法院干预,同样不能变更他们之间业已达成并生效的关于其财产契约的条款。上述未经法院许可的变更,均属于“受到禁止的变更”。[2]1122
《日本民法典》对于夫妻财产制的立场,有点类似于法国。其第758条第1款规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于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这自然也涵盖了“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不得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内容。因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不得向法院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对于日本的夫妻财产制来说,同样是一项基本原则。而前述第758条的第2、3款所述法定事由构成其例外情形。
《德国民法典》对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变更夫妻财产制并无限制性规定,不过,对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第1419条第1款第2句明确规定:“配偶一方无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权利。”这意味着,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可以任意变更夫妻财产制,但单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不会获得支持。正是有了这一基本原则,夫妻一方才需要在具备法定事由的情况下,方可向法院提出分割共同财产的诉求。
台湾“民法”没有关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不得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但从第1010条对“宣告分别财产制”的法定事由的列举可推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不得向法院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也是其夫妻财产制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第1010条中作为“例外”之法定事由的前提,因为“无原则,即无例外”。
综上,征求意见稿第5条所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完全符合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本质要求的。如果当事人可以在不具备特别法定事由的前提下,随时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不仅有违共同共有的法律内涵,也有损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严肃性。确定这一原则,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严肃性,也是对法定事由作为例外情形加以规定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法定事由
从以上立法例所规定的内容来看,原告提起形成之诉皆源于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可能受到损害。换言之,原告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可能受到损害这一事实状态构成了其提出分割共同财产诉求的正当性理由。而造成这一事实状态的原因必须是来自被告,夫妻的另一方。从各国立法例来看,来自被告的损害原告财产利益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财产管理方面的原因
这里包括三种情形:(1)因被告对共同财产管理不善导致原告在共同财产中的利益受损的情形,所谓管理不善,包括共同财产的不当减少;(2)被告单独实施了仅得共同实施的行为,使原告将来的权利可能显著受到危害,如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而将共同所有的房产转让他人;(3)被告无充足理由而坚决拒绝协助对共同财产进行通常的管理,包括依法应得被告同意所为之财产处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时。在上述情形之下,原告提出分割共同财产的诉求,不过是其行使财产所有权中的处分权能的体现。
2.履行法定义务方面的原因
夫妻共同财产应服务于夫妻双方对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日常家庭开支等法定义务的履行。如果共同财产全部或大部分由一方管理,影响或者阻碍了另一方对家庭法定义务的履行,那么其可以提出分割共同财产的请求。这里必须强调是扶养家庭的法定义务,尤其是对双方父母的赡养义务和对双方子女的抚养义务,而基于道义对非直系亲属或者朋友的帮助则不包括在内。对双方子女的抚养义务,不仅包括双方的共同子女,也包括再婚夫妇与前婚中的夫或妻所生的未成年子女。
3.共同财产负债过度方面的原因
这主要是指夫妻一方基于单方面的个人原因使夫妻共同财产负债过度的情形。因为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只要未做特别约定,夫妻一方所欠债务均由夫妻共同财产来偿还。而单方面的个人原因不应该包括因履行法定义务而欠债的情形,如夫妻一方为身患重病的父母而欠下巨额债务,另一方不得以此为由提出分割共同财产;夫妻一方为前婚所生未成年子女治病而欠下巨额债务,也不能成为另一方提出分割共同财产的法定事由。
从以上总结出的法定事由来看,征求意见稿第5条所规定的“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已经被其基本覆盖,因为“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皆可导致共同财产的不当减少,属于财产管理方面的原因;而“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在没有经得另一方同意也并非为了履行法定义务的情况下,可视为夫妻一方基于单方面的个人原因使夫妻共同财产负债过度的情形。但履行法定义务方面的原因等诸多内容却无法被征求意见稿第5条所涵盖。由此可见,第5条对法定事由的列举是不全面的,无法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
(三)重大事由必须是封闭性条款
法国、德国和日本对法定事由的列举都是封闭性条款,这些条款所列举的法定事由没有一条具有兜底条款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杜绝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介入,保证形成之诉的严格适用,从而保证夫妻财产制的稳定性。毕竟,原告提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虽然并不导致婚姻的解体,但还是会给婚姻肌体造成某种程度的损伤。因此,此类诉讼只应在夫妻财产状况出现不合理的恶化情形时,方可“例外地”允许提起。尤其在我国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的当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适用更应慎之又慎。
因此,征求意见稿第5条对法定事由的列举也应该采取封闭性条款的做法,对在不解除婚姻的前提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做法进行严格限制,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介入,从而保证夫妻财产制的稳定性和婚姻的严肃性。
(四)如何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婚姻法解释一”第18条对此作了一个补充规定:“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是否意味着:如果夫妻一方不能证明,第三人知道该约定或者夫妻财产已适用分别制,就应该由夫妻双方的财产来偿还其对外所负的债务呢?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有道理,但对夫妻另一方却显属不公。而且,如果举债的夫妻一方是蓄意制造夫妻共同债务的话,那么另一方就很难受到保护。因此,从保护夫妻另一方的角度考虑,应对举债的夫妻一方课以向第三人告知该项约定或者夫妻财产已适用分别制的义务。如果第三人在与其缔约时不知道该项约定或者夫妻财产已适用分别制的事实,那么夫妻一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问题是,缔约过失责任是否就足以补偿债权人的损失?尤其在夫妻一方偿债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债权人是否仍可以向夫妻另一方求偿,以使其信赖利益得到保护?本文认为,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应允许债权人向夫妻另一方求偿,这样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并且保障了交易安全。
但从夫妻另一方的角度而言,最好的保护方式还是效仿德国法,建立夫妻财产登记制度。即在适用夫妻财产分别制的情况下,允许夫妻一方或者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就财产状况进行登记。登记具有公示性,夫妻财产登记簿应允许任意第三人查询。登记的内容只应涉及财产分别制,而不能涉及财产的多少及其分布情况。此外,登记制度应采取对抗主义,而不是登记生效主义,即只有在夫妻财产分别制已经登记的情况下,才可以对抗第三人。这样就能使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四、结语
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到达某一阶段之前,家庭生活具有显著的本土性,并在婚姻家庭法上有所反映。但超越此阶段后,婚姻家庭法上的本土性必然减弱。因此有学者断言,婚姻家庭法的民族色彩和本土性,并非永久存续,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减弱,最后消灭无踪。[3]10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各国的夫妻财产制有共通的倾向。[3]6前述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有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即其著例。因此,我国婚姻法的相关立法,尤其是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不能无视各国已有的立法成果,故步自封。另一方面,夫妻财产制是社会经济在家庭中的一种折射,它应该反映社会现实的需要。但相对于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却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
征求意见稿甫一公布,便因其众多条款皆涉及离婚时的财产分割而被称为“离婚法”,似乎有要对其大加讨伐的意味。其实,具体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在具备法定事由时请求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样一个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对草率离婚有所制约。因为在私人财产日渐增多的时代,捍卫个人财产的完整性是每个人须臾不会忘却的权利,包括婚姻中的夫妻。如果不需离婚即可保障个人财产的完整性,相信有很多人不会选择离婚。而如果我们的制度所能提供的,只有婚姻与财产不可得兼的不二选择,婚姻就成了易碎的玻璃球。让财产在与婚姻的纠缠中适度地分离,如前所述,能避免财产的不当减少,最大限度发挥财产的效用。如果财产的分割必须以离婚为前提条件,那么,只要其中一方不愿意离婚或恶意拖延,就有可能造成财产的不当减少,并影响另一方当事人对法定义务的履行。
总而言之,征求意见稿第5条的出现适逢其时,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奠定了基础。它不仅是《物权法》第99条在夫妻财产共同制中的具体适用,也是对《物权法》第99条中“重大理由”的有权性解释。但这一条款所附加的“夫妻因感情不合分居期间及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这一时间条件以及对“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强调,皆属多余,应予删除。而其对法定事由的列举亦不够全面,应比照相关立法例予以补充完善。
注释:
①我们姑且把条文中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理解成“人民法院准予分割”。因为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为主要夫妻财产制的我国当下,法院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始终是持保守态度的。虽然“可以受理”还意味着另一种“不予分割”的可能,但在本文看来,夫妻一方提出分割共同财产,并不仅仅因为另一方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还有可能因为夫妻一方为了履行法定义务的需要。因此,司法者的态度不应该是保守的,至少应该是中立的。本文试图用“准予分割”这样的积极立场对法院的保守态度作一矫正。
②参见《人民法院报》2008年2月13日第8版《能否析产众说纷纭》一文。
③成年人因心理疾患或者身体上、精神上、心灵上的障碍而完全地或者部分地不能处理其事务的,监护法院即根据该成年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为其选任一个照管人。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896条以下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