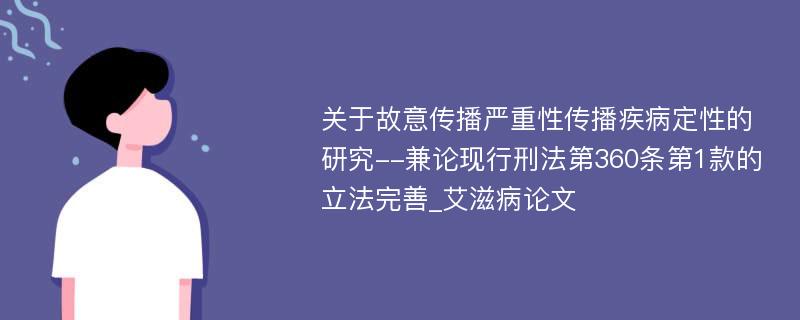
故意传播严重性病行为定性之探究——兼论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的立法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法论文,性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26【文章编号】1002—6274(2006)03—063—05
一、若干故意传播严重性病行为的定性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的规定,传播性病罪的主体限于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患者,客观上限于卖淫、嫖娼的行为,不具有卖淫、嫖娼性质以外的性行为以及其他方式传播严重性病的不能构成传播性病罪。那么,对于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卖淫嫖娼的可否以传播性病罪论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于非卖淫、嫖娼以外的性行为或其他方式故意传播严重性病的行为当如何定性?在理论上开展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无疑会裨益于刑事司法。
(一)明知自己是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而卖淫嫖娼的行为定性
对于艾滋病患者或者感染者卖淫嫖娼的行为如何认定,理论上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构成传播性病罪,其理由在于:我国《刑法》第360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艾滋病属于严重性病的一种,对于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而卖淫嫖娼的理所当然地应以传播性病罪论处。[1] 另有学者主张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卖淫、嫖娼的社会危害性比普通性病(如淋病、梅毒)患者更为严重,应该受到比普通性病患者更为严厉的处罚。对于此类行为应同用自身携带的艾滋病病毒报复社会、危害不特定人群人身安全的一样,均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这既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又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①
对于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卖淫嫖娼行为之定性问题,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理由在于:艾滋病的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简称为AIDS,它是一种由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侵入人体后破坏人体免疫功能,致使感染者体内的免疫系统完全瘫痪,最终致使人体发生多种不可治愈的感染和肿瘤而最终死亡的严重传染病。自从人类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直至今日尚未找到一种有效的药物和方法来治疗艾滋病,因此艾滋病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头号大敌,并被人们认为是“超级癌症”,死亡率极高。相比较而言,梅毒、淋病等性病被感染之后,只要治疗及时,一般很快就能治愈。从这一点来看,严重性病这一用语含义内应包括艾滋病,此其一。其二,笔者注意到,不论是1991年卫生部发布的《性病防治管理办法》,还是2004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都将艾滋病列在淋病、梅毒之前,特别是《性病防治管理办法》在列举8种法定性病时,将艾滋病列在众性病之首,这也可以说明艾滋病属于比梅毒、淋病更为严重的性病范畴。鉴于此,尽管我国《刑法》第360条第1款仅仅列举梅毒、淋病两种严重性病,未能具体列出其他性病的名称,但根据“举轻以明重”的解释原则,在刑法解释论上完全可以将艾滋病纳入严重的性病范围之内,而且这一解释完全符合刑法规定传播性病罪的实质的、正义的标准。
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同意论者所主张的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卖淫、嫖娼的社会危害性要比普通性病(如淋病、梅毒)患者卖淫嫖娼的更为严重,因而应给予更为严厉处罚之观点,但对论者所持的定性结论持不同见解。“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保护法益是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所谓不特定,是指犯罪行为可能侵害的对象和可能造成的结果事先无法确定,行为人对此无法具体预料也难以实际控制,行为的危险或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可能随时扩大或增加。所谓多数人,则难以用具体数字表述,行为使较多的人(即使是特定的多数人)感受到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受到威胁时,应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2] 而且,不论是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抑或是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根本特点在于:行为一经实施,就可能同时造成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人身安全,以及大范围财产的损害的严重后果,亦即具有骤然性、同时性,对公共安全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和严重的破坏性的特点。由于卖淫、嫖娼行为的反复性,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卖淫、嫖娼就会可能使得不特定的多数人感染艾滋病,从而造成一定的疫情隐患;但具体到每次卖淫嫖娼的行为而言,其侵害的法益则是特定个体的生命、健康,而不是一次就可能危及到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就像一个人出于对社会的仇恨而连续杀人一样,他在某一段时间可能连续杀死不特定的多数人,但我们并不因此认为行为人连续杀害不特定多人的行为就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其一。其二,艾滋病患者卖淫、嫖娼的行为的危险性及破坏性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放火、爆炸、决水以及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相提并论,亦即它对公共安全并非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和严重的破坏性的特点。其三,艾滋病同梅毒、淋病一样,都是性病。故意传播艾滋病与传播梅毒、淋病的行为,两者之间只是情节轻重不同,而并无罪质的不同。因此,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卖淫、嫖娼的行为应构成传播性病罪,这不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充分发挥了传播性病罪此一罪名所应有的评价、威慑或教育功能。
(二)其他常见的故意传播性病行为的定性
1.携带装有含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见人就扎的行为定性
对于携带装有含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见人就扎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呢?对此,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行为人携带含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见人就扎的,其行为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已经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3] 另有学者认为,扎针行为的对象不是特定的个人,而是随机的在人群中寻找目标,这就使得不特定多数人面临感染艾滋病的威胁,从而危害了公共安全。其次,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的是《刑法》第114条明文列举的行为方式之外的行为——扎针。而投放危险物质罪中的投放是指将某物质有意放置于某个地方的行为,该行为并不直接作用于行为对象的身体。可见,投放行为并不能包容扎针行为。因此,用扎针的方法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是《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应按照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4]
上述两种观点对利用扎针传播艾滋病的行为认定的罪名虽不尽一致,但不论是认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抑或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者的本质都是认为此种扎针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理由有二:其一,携带装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逢人就扎的行为,虽有可能使得不特定的多数人感染艾滋病,造成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从表面上看似乎危及了公共安全。但具体到每次扎针行为时,其侵害的法益则是特定个体的生命、健康,而不是一次就可能危及到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人身安全,因之,此种见人就扎的“扎针”行为的危险性及破坏性同样也不能同放火、爆炸、决水以及投放危险物质行为相提并论。其二,我国现行《刑法》第234条第1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一个人如果感染了艾滋病,其肌体免疫系统就被破坏,容易患上正常人能够克服的各种疾病,在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的情况下,感染艾滋病病毒就意味着身体健康遭到严重危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使他人感染的行为,属于一种故意伤害他人健康的行为。具体到上述见人就扎的“扎针”行为,其本质上如同连续伤害不特定的个人的身体健康一样,属连续犯,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同样的道理,在艾滋病患者或者感染者在明知自己是艾滋病患者或者感染者的情况下,其不论实施的是扎针行为,还是输血、共用注射器、捐献器官或者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希望或放任他人被感染艾滋病的,均可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
2.严重性病患者出于传播性病的目的而卖淫、嫖娼的行为的定性
严重性病患者基于泄愤、报复的动机,抱着将性病传染给他人的目的,实施卖淫、嫖娼行为的,应当如何定性呢?对于此类行为的定性,学界存有分歧。有学者认为,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伤害他人,在客观上采取了以传播严重性病的手段,构成牵连犯,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5] 笔者以为,上述两种见解均值得商榷。第一种见解显然对牵连犯的理解有误。“牵连犯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行为。这是牵连犯的客观外部特征。换言之,行为人只有实施了数个相对独立并完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社会行为,才可能成立牵连犯。”[6] 行为人基于报复、泄愤的动机,企图将严重性病传染给他人而卖淫、嫖娼的,其实施的只是一个犯罪行为,而并非存在两个独立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因而牵连犯的成立也就无从谈起。至于第二种观点认为该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这一点自无问题。但问题就在于:传播性病罪虽然并不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追求被害人被传染性病的后果,但至少行为人对该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因之,严重性病患者出于报复、泄愤的动机而卖淫、嫖娼的,其行为在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同时,又具备传播性病罪的构成特征,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构成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论处。
3.严重性病患者明知自己患有性病,还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的定性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的规定,传播性病罪的客观方面特征表现为:行为人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这是其一;其二,行为人实施了卖淫、嫖娼的行为。这两个条件是故意传播性病罪的必备条件,缺一不可。所以,患有淋病、梅毒等严重性病的人即便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如果不属卖淫、嫖娼的性质,如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恋人间的性行为、通奸行为、同性恋性行为等,就不能构成传播性病罪。但问题是这些不具有卖淫、嫖娼性质的性行为有时也具有反复性、多次性的特点,因此也就很容易将性病传染给对方,造成对被害人的身心严重伤害。因此,对严重性病患者明知自己患有性病,还多次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值得一提的是,行为人对自己患有性病主观上存有明知,但自认为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即可避免将性病传染给他人的,但对方却因此而被传染性病的,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在主观上应当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因此,如果对方因感染的性病构成重伤程度的,可依过失致人重伤罪论处。当然,如果严重性病患者事先告知对方自己患有性病而造成严重性病传播的,则免除行为人的责任。
二、关于我国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的完善
由于我国当前性病发病人数较多,传播途径广泛,现实生活中的传播性病案件形形色色,手段千奇百怪。但因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对严重性病范围的不明确以及传播性病罪的行为方式的单一性,加上学者们对本罪的构成特征及其具体认定问题存有诸多争议,导致司法实务部门对相关传播性病案件的刑法适用产生了困难,且有不统一之现象发生。因此,有必要完善立法,规范严重性病的范围和扩大传播性病罪的行为方式,以为惩治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故意传播严重性病行为提供法律依据,从而达到定纷止争、促进司法统一的目的。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应明确将艾滋病列入严重性病的范围
法律采取列举与概括相统一模式规定了本罪主体的范围,亦即在明确列举梅毒、淋病患者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之外,又采取了“等严重性病”此一抽象语言进行“兜底”,以打击、惩治各类严重性病患者的卖淫、嫖娼行为,以防挂一漏万,此为可取之处。但由于此一条款未能突出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处罚规定,从而使得一些学理解释中不少将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携带者排除在本罪的主体的范围之外。如前所述,对于艾滋病目前尚无有效的药物,死亡率极高,因之艾滋病患者卖淫嫖娼的社会危害性较之于梅毒、淋病患者卖淫嫖娼的,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若刑法对之不予以规制,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不合情理。因之,有必要对《刑法》第360条第1款予以修改完善,即将艾滋病与梅毒、淋病等性病规定在严重性病范围之列。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艾滋病、梅毒、淋病之外,究竟还有哪些性病属于严重性病的范畴②,至今尚无有效的司法解释或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之予以明确界定,从而造成司法认定上的困难。因之,当务之急应是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严重性病”的范围予以界定,以为实务部门在办理相关案件时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
(二)传播性病罪的行为方式不应限于卖淫、嫖娼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传播性病罪的构成特征之一就在于须以严重性病患者实施卖淫、嫖娼为条件,这就把非卖淫、嫖娼而传播性病的其他危害行为全部排除犯罪之外。但从立法原意来看,立法者设立本罪主要旨在遏制、防止严重性病的蔓延和流行,而性病传播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除了卖淫、嫖娼之外,其他诸如通奸、非法同居、猥亵、故意将性病病毒涂抹在他人的内裤、马桶、浴缸、毛巾等物品上或者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将带有性病病毒的血液、器官捐献给他人等行为同样可将性病传播给他人。而且随着医学的发展以及性病研究的深入,还会发现一些新的途径。对于这些不具有卖淫、嫖娼性质的传播性病的行为,尽管有的可以在现行刑法框架下解决其定性问题,但有的尚存在司法认定上的困难。笔者以为,如果取消传播性病罪的卖淫、嫖娼行为方式的限制,即规定不论是卖淫、嫖娼,抑或是其他行为,只要故意将严重性病传染给他人的,均成立传播性病罪,司法认定之困难和不统一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有些国家对传播性病罪的行为方式并没有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即无论是卖淫、嫖娼的行为,还是非卖淫、嫖娼的性交行为,抑或其他方式,只要可能将性病传染给他人的,即可成立传播性病罪。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21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有花柳病而传染给他人的,处数额为20万卢布以下罚金或被判刑18个月以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1年以上2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拘役。”第122条规定了传播艾滋病,即(1)“故意将他人置于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之中,处3年以下的限制自由;或处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拘役;或处1年以下的剥夺自由。(2)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而传染他人的,处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此种立法例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三)调整本罪的法定刑
如前所述,艾滋病的危害性极大,迄今为止尚无有效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任何人一旦被感染上艾滋病,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因此,传播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的行为之危害性与传播艾滋病的行为的危害性,二者不可等量齐观。因此,现行刑法关于本罪的法定最高刑为5年的设置情况显然不能适用于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因此,有必要调整本罪的法定刑幅度,将本罪的最高刑予以提高,以能适用传播包括艾滋病的各种严重性病的行为,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四)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之重构及其新解读
综上,可将我国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的罪状修改为: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而故意实施传播行为的,处一定的刑罚。至于设置何种幅度的法定刑较为合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根据笔者关于传播性病罪罪状的重新设计,可在理论上对传播性病罪的构成要件做如下解读:其一,本罪主体是艾滋病、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患者。由于性病传播途径不限于性行为,因此,非性病患者也可通过其他方式传播性病,诸如将性病病毒涂抹在他人的内裤、马桶、浴缸、毛巾等物品上或者携带含有艾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器,在公共场所见人就扎等等,此类行为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特征,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其二,本罪的客观方面是严重性病患者实施可能使他人被感染性病的任何行为,而非仅仅限于卖淫、嫖娼行为。本罪并不要求实际上发生将性病传染于他人的后果,而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将性病传染给他人的可能性即可。其三,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患有性病。如果行为人虽然患有性病,但不明知自己患有性病,则不构成本罪。这里的“明知”,并非要求行为人确实知道自己所患的严重性病种类,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患有严重性病即可。至于行为人主观方面意志因素,并不必须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希望把性病传染给他人,只要行为人对自己所患的严重性病可能传播给他人采取了无所谓的放任态度即可。换言之,成立本罪仅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间接故意的内容。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由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类罪名,而非一个具体的罪名,因此,论者在这里所言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实际上指的是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载http://news.163.com/05/1201/04/23S2SDU00001124T.html。
②关于严重性病的范围有哪些,理论上意见不一。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尚无有关司法解释对严重性病予以明确界定,可以将1999年8月12日卫生部发布的《性病防治管理办法》中所列的八种性病均认定为严重性病,即艾滋病、梅毒、淋病、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非淋菌性尿道炎、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参见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页)。另有观点认为,严重性病的范围应以国际上公认的性传播疾病范畴为标准,即1975年世界卫生组织常任理事会规定的梅毒、淋病、软下疳、性病性淋病肉芽肿和股腹沟肉芽肿、艾滋病等30多种性传播疾病(参见鲍遂献主编:《妨害风化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笔者以为,“刑法不过问细微之事”,因此我国刑法中的严重性病范围不宜界定过宽,否则会造成打击面过大,从而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本质。从这一点来看,多数学者的见解是可取的,即严重性病的范围当前应以《性病防治管理办法》中所列的八种性病为限。
标签:艾滋病论文; 传播性病罪论文; 性病性淋巴肉芽肿论文; 梅毒感染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