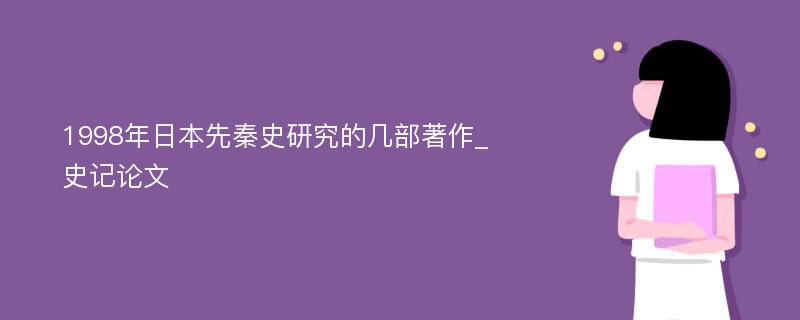
1998年日本先秦史研究的几部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日本论文,力作论文,几部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度日本的先秦史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本篇所评介的只是其中几部著作,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几部力作。按照我国史学界的分类习惯和术语,先秦史属于断代史范畴。但先秦史包括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因而其中既有夏史、商史、周史之类的断代史,也有带有通史性质的著作。这里所要介绍的、由鹤间和幸教授负责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由尾形勇、 平势隆郎两教授所著《世界历史2·中华文明的诞生》(中央公论社)就属于通史性的著作, 而由平势隆郎教授著的《左传的史料批判研究》,以及由工藤元男教授著的《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和社会》则属于断代史中的专题研究。
《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是《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8卷本中的第3卷,它由鹤间先生负责,由鹤间和幸、冈村秀典、工藤元男、 林俊雄、平势隆郎、江村治树、佐原康夫、藤田胜久、富谷至、原宗子诸先生合作撰写。在结构上,从纵向看属于通史性质,从横向看又带有专题色彩。全书由“前言”、“结构与展开”、“境域与局所”、“论点与焦点”诸栏目组成。“前言”和“结构与展开”栏目由学习院大学的鹤间和幸先生执笔,在“结构与展开”中,鹤间先生以“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为大标题,其下又分为“绪论”、“一、历史的视点”、“二、中华与东方世界”、“三、文明时代”、“四、由城市国家到中华——三个地域的扩大”、“五、从地域到走向统一的视点”诸章节。在这部分,鹤间先生从理论的层面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了全新的论述,很值得一读。
我们知道,30年前,日本第一次出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当时尽管因中日尚未建交,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对于新史料的入手较为困难,然而仅以笔者曾阅读过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4·古代4·东亚世界的的形成Ⅰ》而言,它一问世,就以其鲜明的学术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年后的今天,作为第二次《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中的第三卷——《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给人第一个印象就是打破了近20年日本的中国古代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沉默。
《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的理论构筑主要体现在《结构与展开》之中。在这里,鹤间先生首先通过对《史记》史料性格的讨论和对近现代学术视角的反省,提出了该卷的出发点。其视角核心就是把先秦时期的中国置于多元、复杂的世界来把握。他既反对黄河文明一元论,即反对把由文明的发生到中华帝国形成的历史描绘成以黄河中下游为同心圆的中心而不断扩大的历史;也对长江文明论持有异议。他提出了从城市国家的出现到中华世界形成过程中三种地域扩大的概念。其第一地域——城市,指的是从殷周到春秋时期,“领域国家”(即所谓“领土国家”)形成之前以城市为基础而出现的城市国家。在领域国家形成之后,它们以郡县的形式成为传送中央政府意向的地方行政组织的基础。第二地域——战国国家,指的是国土空间扩大了的战国时期的诸“领域国家”,但依然是扎根于各地域的国家。第三地域——华夷共存的世界,鹤间先生称之为广义上的“中华”,它超越了战国地域国家框架,相当于诸子所言的“天下”这样的地理概念。以上述三个逐渐扩大的相重叠的地理概念为基础,鹤间先生转换了日本学者对秦汉统一帝国形成史研究的视点。
鹤间先生的研究也反映了近年来虽说为数不多但却很有思想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因而该篇主张应把那种以近代欧洲为标尺来衡量亚洲的做法,转变为将欧洲和亚洲都相对化,而且还应避免用近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标尺来套用古代,即与其像过去那样用“中国古代国家”、“中国古代帝国”、“中华民族”和“汉民族”、“乡里共同体”和“豪族共同体”来替换“国家”、“帝国”、“民族”、“共同体”这种近代社会科学的概念,还不如回到中国固有的“国家”“天下”“中华”之类的意义中去。
关于太史公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性质问题,鹤间先生强调太史令不是民政官,也不是王朝的史书编纂官,而是掌管国家宗庙礼仪的太常所属的记录官——太史之长,《史记》是对应天事而叙述人事,不是一般的人事行政记录。这些都是深入研究和了解《史记》的结果,但笔者以为也不能由此而矫枉过正。与《春秋》这一编年体形式的史书以及先秦时其它风格的史书相比,《史记》更具有自己的创造性,特别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保留了许多年代矛盾的记录等,显示了司马迁对记述历史的态度,这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至于太史令的所属和《史记》有对应天事而叙述人事的现象,用司马迁的话说亦即所谓“究天人之际”,这正反映了“太史令”这一职官和《史记》所处的承前启后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点。在这点上,小南一郎教授最近发表的《史的起源及其职能》很有启发,也很有说服力。在该文中,小南先生从《周礼》和《仪礼》各处所涉及到的“史”及其“史”所担当的职役与角色入手,进而分析构成“史”字要素的“中”的含义,并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的陶器符号特别是数字符号来论证“史”的起源和最初的职能,因此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史”这样的阶层原本是掌握计算及其记录技术的人们。这种计算和记录,既包括从地方向中央贡纳物资的记录,也包括封数符号的计算和记录,因而,“史”也从事筮占工作,筮在根本上就是从这样的数字技术派生出来的(注:小南一郎《史的起源及其职能》,《东方学》第九十八辑,1999年7月。)。可见, 史官从其起源开始,就有“对应天事来记录人事”的特征,司马迁的《史记》也保留了这些因素,因而今后我们阅读《史记》时,还应留意发掘其中所蕴藏的宗教文化和人类学现象,并对宗教、神灵与祭祀在国家的机能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加深认识。
《境域与局所》栏目由《农耕社会与文明的形成》、《围绕禹传说的中华世界与周边地区》以及《草原游牧文明论》三编组成。其中,冈村秀典先生撰写的《农耕社会与文明的形成》,在论述农耕社会开始之前,专列一节来概述中国新石器时代地域与文化系统的划分,这显然与鹤间先生在《结构与展开》中的论述是关联的。诚如冈村先生所述,这是沿着苏秉琦先生所提倡的区系类型论(注:苏秉琦等《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石兴邦先生的三大系统论(注: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1986年。),严文明先生的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东南系统、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北系统、以辽河为中心的东北系统这样的三系统论(注: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4,1994年。)而展开的。
冈村先生论述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叙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二里头文化出现之前的一千年间社会的复杂化和地域性的统合时,援引了“酋邦”概念。接着在论述初期国家形成时,使用了“祭仪国家”一词,并与殷周王朝的祭仪相联系加以叙述。这种对祭祀在殷商社会中起着维系王朝统治和国家结构的机能与作用的论述,是继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日本史学界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注: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之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中心的殷周史研究》,(日本)创文社,1975年;赤塚忠《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殷王朝的祭祀》,(日本)角川书店,1977年。)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所提出的学术观点的进一步强调。诚然,这也是实证史学中由后代推论前代亦即由已知推论未知所要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史前到商周社会文化的连贯性。只是冈村先生把初期国家形成的时间划定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可以说代表了日本史学界较普遍的观点,但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国家是否属于殷商之前的夏王朝国家或别的某种国家,冈村先生尚未展开论述。在日本史学界,对于夏王朝的存在普遍持谨慎的态度,这一点与欧美学者相仿,而与我国古史学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工藤元男先生执笔的《围绕禹传说的中华世界与周边地区》,既含有工藤先生对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和其他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中的有关研究,也包含对四川民族走廊的调查,使有关禹的传说的研究别开生面。传统的做法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来研究禹的传说,工藤先生在依据竹间帛书等出土资料研究战国到秦汉的社会史时,发现禹是当时社会民俗中的信仰对象,进而根据中国古代西南夷在“禹生石纽”的传说中,还有作为庇护隐匿逃亡者的特定圣域——避难所之神的性格,由此将禹的传说追踪到西南夷古羌人中,并与白川静先生把仰韶文化“人面鱼纹”解释成洪水神禹和鲧的说法以及《山海经·海内南经》“氐人”条有“人面鱼身,无足”的记载和氐与羌往往互用等现象相联系,认为作为洪水神的禹的神话首先在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发生,并被二里头文化所继承,同时禹的神话又由于古羌人的迁徙而传播到岷江上游,与当地固有的自然环境(石缝和荒地)相结合而产生了禹诞生于石中的神话,但是在禹的传说中有关洪水神的神话和石中诞生神话这两个要素并不是有机结合的。总之,工藤先生关于禹的研究启示我们,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增加和有关古文字资料的新解释,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也将会推动有关古代族落的迁徙移动与古史传说的研究。
《境域与局所》中的第三编《草原游牧文明论》由林俊雄先生执笔,这一章林先生举出东西广达7000公里的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人和匈奴这样的骑马民族,来论述与定居的农耕文明具有相反价值基准的社会和国家面貌。如果说近代文明史观的传统做法是把农耕作为唯一文明的话,那么林先生的论述就可以作为传统文明观的反命题来阅读。骑马游牧民族在生态环境的制约下,其家畜的放牧及生计活动等与定居的农耕民族不同而具有移动性,同时由于骑乘马匹,既有利于信息情报的迅速传递,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很容易形成优越的机动力而在军事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此外,在广阔的欧亚大草原地带,古代的游牧民族有时也会形成自己的向心力,在游牧国家中也可以容纳某些定居的聚落,使其游牧经济中也有手工业和农业的补充,并发展出自己的贸易。游牧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当年的司马迁已注意了这一点,林俊雄先生对此进一步论述,对丰富我们的文明史观显然是有意义的。
《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中的第三个栏目《论点与焦点》由六编构成,其中,平势隆郎先生执笔的《殷周时代的王和诸侯》,在叙述殷商和西周时代的国家结构时,使用了由松本光雄、宇都宫清吉等先生在50年代提出(注:松本光雄《中国古代邑与民、人的关系》,《山梨大学学艺学部研究报告》第三号,1952年;又《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分邑与赋》《山梨大学学艺学部研究报告》第四号,1953年;宇都宫清吉《古代帝国史概论》,《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收,1955年。)、松丸道雄等学者在60—70年代进一步论述了的“邑制国家”(注:松丸道雄《关于卜辞中的田猎地——为殷代国家结构研究而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三十一册,1963年,又《殷周国家的结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4·古代4》,岩波书店,1970年。)这样的概念,即殷周时代王和诸侯等国家是由被城垣所围起的大邑和从属于大邑的小邑为基础而构成的。在论述由殷周到春秋战国向“领域国家”发展过程时,强调了春秋时代“县”的性格与机制和战国时代“封君”的登场。认为诸如齐的孟尝君、楚的春申君等战国四君子所代表的封君,一方面具有战国各王之下的诸侯的身分,同时他们封地的统治方式则是(郡)县制的,由此而形成区分“城市国家”与“领域国家”的明显的差别。此外,文中也贯穿了平势先生所主张的在运用考古遗物时应该具有史料批判的眼光这一研究倾向,对此,后面介绍平势先生另几部著作时还会谈到。
江村先生于1998年发表了《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城市规模与分布》一文(注:江村治树《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城市的规模与分布》,《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31·《史学》44,1998年3月。),该文附有“西周春秋城市遗迹表”、“战国城市遗迹表”和“秦汉城市遗迹表”,网罗了截至1998年的西周到秦汉的城市遗迹的全部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从西周春秋到秦汉时代城市的规模和分布特征。在该文中,江村先生再次证明,与春秋和秦汉相比,战国时代许多巨大的城市得到发展,然而战国城市的发展的重要原因当在政治的、军事的因素之外,特别是河南省中部诸侯国都以外的城市的发达,仅用政治、军事的原因是不能说明的,其第一位的因素是经济性的原因。这也是江村先生继1986年发表《战国三晋城市的性格》(注:江村治树《战国三晋城市的性格》,《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XCV·《史学》32, 1986年。)、1988年发表《战国时代的城市及其支配》(注:江村治树《战国时代的城市及其支配》,《东洋史研究》第四十八卷第二号,1988年。)、1990年完成《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城市结构与居民的性质》(注:江村治树《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城市的结构与居民的性质》,《平成元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 1990年。)等有影响的相关作品中又一篇有价值的论文。
由以上介绍可以看到,这部由十位就职于不同大学的中青年学者共同撰写的《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既在整体框架、视角和思路上保持了前后一致性,又在各章节具体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上体现了每个人的个性持征。这也是日本学术界由多人合作著书时的传统做法,即在集体著作中充分展现每个撰写者独特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在观点不一致或矛盾,而在署名上也是将每位执笔者的名字直接放在著作前面的“目次”中。对于这些,我以为是值得我国学术界借鉴的。
1998年出版的另一部通史性著作《中华文明的诞生》是30卷本《世界历史》中的第2卷,由尾形勇和平势隆郎两教授共同撰写, 内容为从新石器时代到三国时代,其中“第1 部”即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的先秦史部分由平势先生执笔。在先秦史部分,平势先生首先在相当于“导读”的栏目内,以《翻阅本书前半部之前》为题,通过概述的形式叙述了他近年来在《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以及《左传的史料批判研究》等著作中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新认识。其中“数的秩序与历史认识”一节指出,战国中期以后出现把天、地、时间、季节的秩序用九、六、八这三个圣数的调和来说明,并以此说明天子与皇帝的正统性,同时也以这种被重新整理过的史料来构筑历史的现象。在《伟大的预言书》一节中指出,包括《论语》在内的所谓经典是在战国时代渐渐被整理而成为现在的体裁,在这些经典中一般所揭示的是理想的世界,而混杂其中以预言为主要目的的乃是《春秋》。许多人认为这本经典是孔子将鲁国的记述加以笔削而成。“笔削”意味着并非原来的记述,而是圣人孔子将内容加以增补或删减,以揭示未来的理想。那么,战国时代究竟是如何说明其理想的?在“战国时代的帝王理念”一节,首先以“文、武的继承与武、文的继承”为小标题,指出战国以前的王在其血族集团中处于值得夸耀的传统的血缘谱系的顶点,战国时代,新兴势力抬头,取代了夸示传统血脉的族集团而称王,他们为了表示自己具备为王之德,说明为王的正统性,于是从历史中撷取模范,加以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这也就是经书所揭示的理想的世界。所以经书乃是为具体提示战国时代的王或汉代皇帝的正统为何物而出现、并被加以利用之书。主要被利用的是已成为远古人物的周成王与宣王以及贤人周公旦等。成王是继承文王、武王之王,周公旦被认为是担任确认成王具备王德这一工作的贤人,成王的继承并非完全取决于血缘,而是由于具有王德。武王去世之后有贤人治世,经过那段时期以后,成王被认为具有王德而即位为王。宣王的情形亦相同,在周王朝内部的政争中,厉王被逐,共伯和替代年幼的宣王执政,后经共伯和确认宣王具备王德后让他即位。这样,在历史事实被重新解释的过程中,受到重视的是经过贤人治世之后,另行称元即位的这种“形态”(包括架构、理论等整体形态),并产生重视与此种形态重叠的系谱,形成文→武→成,或文→武→宣的继承关系。前者如继承魏武侯的魏惠成王(既是惠王,又是成王),后者如继承田齐桓公(桓为桓武之桓)的齐威宣王(威乃威武之威,宣则有文的意味)。此外,秦称王后为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襄有成的意味),也是文、武、成的继承;赵称王后为武灵王—惠文王—孝成王,乃是意识到武、文、成的继承。其次以“音乐理论与天之方位、地之方位、时间与季节的方位”为小标题来概括战国时代帝王的第二个理念,指出新出现的王的正统性也体现在统掌着天、地、时间与季节的方位,自战国中期始,将以前使用的十二支充当为十二方位,并与十二律、十二音相配(因为音乐在古代使用于祭祀,自然会被用来配合新的帝王理念)。当时正值五行理论盛行,故以子音为标准而定出五音,以辰为地上之方位,此方位在冬至的黎明,可看见角宿、房宿、心宿、尾宿等代表性的星座。于是,以此方位为起点,将星座旋转分配到十二方位上。以天之方位重叠地之方位,此乃是将天比作雨伞而从外侧观看的观点。至此,一直只仰望的天,变成从天的外侧远方俯视。这是宇宙观的大转变。此种视点在战国中期出现,以辰为起点而从角宿排列的天的方位中,冬至点正当丑的中央。“天下”的概念亦与此相关联而出现。新的王不只君临地上,而且还由于此视点而成为从高处掌握整个天的秩序的统治者。在季节的方位配置上,包含冬至的月分为子,春之始的月分为寅,此三个方位被赋予“起始”的意义。冬至是太阳最低的终了与起始,春天是承接冬至的第二起始。与此同时,历日数据被聚集分析,太阳与月亮回到原来关系的周期被认为刚好七十六年。将此周期进一步细分而制定了大、小月的排列模式。此新历在计算上可一直延续到未来,王通过对太阳和月亮的观察而永恒掌握时间与季节的秩序。最后以“战国各国之历与三正说、逾年称元法”为小标题来论述战国时代帝王的另一些理念,指出战国以前的传统历法是观象授时之历,但战国时人认为周初就有与战国时的新历相同的历,其原理被战国时新王之历所继承,并认为发生王朝革命时,也显示在历的形式上,这就是所谓的“三正”说。三正中以子月为正月的历是周正,以丑月为正月的历是殷正,以寅月为正月的历是夏正。一般认为替代周而新兴的王朝将复归到夏,因而以夏正为正统历。《春秋》所提示的季节排列中,关于周正的月的记述是,正月至三月为春,四月至六月为夏,七月至九月为秋,十月至十二月为冬。战国时代的历代诸王,于前代王去世之年尚未称元年,逾年(渡过此年)而于正月称元。夏正亦适用于此逾年称元法。《春秋》与《春秋左氏传》的鲁国君主的追溯纪年(即《春秋》鲁国君主的纪年并非实际的年代,而是战国中期换写的年代)、《竹书纪年》的惠成王改元以后的魏国历代诸王纪年,都采用逾年称元法。魏惠成王是新兴势力最初称王的人物,公元前351年年末成为夏王。正是举行以周被委让权威的典礼时, 被齐威宣王打败。其后,无称夏王的记载,但魏、齐、韩、赵、燕、中山六国均采用夏正。楚排斥夏正而另外制定别的历,为了与意味春之始的夏正对抗,而以冬之始为正月(楚王)将包含冬至的月份固定为二月。并且不采用与夏正密切结合的逾年称元法,而袭用旧来的立年称元法,即于前君主去世之年称元年的方法。由楚正与立年称元法可提示楚王乃唯一正统之王。秦折衷楚正与夏正而制定独自的历,既将月序配合夏正,又不以正月为岁首,而以相当于楚正正月的十月为岁首,岁末为九月,闰月亦置于此。然而采用夏正的六国,各自都认为自己的君主是正统的王,因此即使同样是夏正,亦各有相异点。其相异点在论证正统时成为关键。主要的相异点在于,以何处为七十六年周期的起点,以及如何置闰。历算的起点有三种,即将公元前352 年末冬至丁亥视为朔而当作起点;或将此日视为晦而当作起点;还有将公元前366 年立春甲寅视为朔而当作起点。置闰法有两种,即将包含冬至的月固定为十一月,以及将包含冬至月的下下个月固定为正月。合计夏正共有六种历。他在“再论伟大的预言书”一节指出,《竹书纪年》、《春秋》、《春秋左氏传》分别是战国时魏、齐、韩国为了显示其为正统的年代记。《春秋》的历日符合齐历,同时对于与齐历起点相同的赵、秦历而言也具有相适性。汉朝至武帝为止沿用秦历,因此汉朝可由自己的历直接追溯到《春秋》的历日。武帝时发生改历之议,董仲舒导入五德终始说,利用《春秋》所提示的夏正之到来,将自己的见解在理论上加以补充。
《中华文明的诞生》的先秦史部分,就是贯穿作者上述对中国古史研究的新认识而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殷王朝和周王朝”、“春秋战国时代”诸章节撰写的。全书文图并茂,写得既概括,又驾驭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包含作者许多新看法,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通史性著作。
平势隆郎教授1998年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左传的史料批判研究》亦颇具特色。该书由对《左传》的史料分析检讨、有关春秋时代的县、《侯马盟书》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作为附录的“《左传》分类一览”等组成。平势先生认为《左传》中有关冬至的记载是将公元前352 年年末冬至视为朔并以此为起点的,由对置闰方法的微言式的批判,亦可知被《左传》视为正统的历是将正月固定在从冬至月算起的第三个月的历。据此可知,《左传》所提示的正统历为韩历。因而他认为《左传》是在战国中期韩国的朝廷完成的。韩国将搜集来的史料重新归纳整理,赋予独自的风格。《左传》的基本史料是《春秋》。《春秋》中,各国记事在鲁国君主的年代下被重新归纳整理,但此《春秋》的年代并非原来鲁国君主年代,而是战国中期齐国的朝廷用逾年称元法改写的。因此,《春秋》记述“朔”时,所选择的是适合战国时代齐历的记载。《左传》从这本《春秋》中选择不与自己的正统观相抵触的记载加以利用,然后再寓以独自的微言,利用在诸国中已有的许多故事,而将其词汇加以适当的改换。例如楚王的故事,先参照《春秋》而被写作“楚子”,在故事的会话部分中再将“楚王”置换为“楚君”。
平势先生进而指出,《左传》的微言中有“夫子”、“吾子”、“君子”的组合。以往根据《论语》,一直将夫子当成是男子的美称。但《左传》所使用的“夫子”,是指同族灭亡、出奔他国或致使主君灭亡、出奔的人物。“吾子”也相同。这些“夫子”、“吾子”被用来称呼赵氏、魏氏的宗主,暗示他们终将灭亡。相对而言,“君子”被认为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是用来扫除“夫子”、“吾子”的不吉暗示的词汇。被称为“君子”的韩宣子与郑子产,有时也被称为“夫子”、“吾子”,但他们并不是无法预知未来的“夫子”、“吾子”,而是能预知未来的“夫子”、“吾子”。受到子产称赞的人物是韩宣子,在此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后所确立的由贤人确认是否具备王德的仪式。《春秋》的微言显示在《公羊传》中,主要在开头与结尾。开头部分论述属于周文王之法的逾年称元法,并说明从贤人“隐”(暗喻隐公)到“桓”(暗喻桓公)的权力委让。开头部分的“隐”乃是心想着古代周公的摄政,“桓”则意味着“武”。这是在隐隐约约地预言:战国中期齐国威宣王经过诸侯时期之后,将逾年改元而成为“威宣王”(威意味着“武”)。此处亦提示了《春秋》是在齐作成的。《左传》否定《春秋》的这些“形态”,在开头部分叙述至“惠”即惠公为止的历史,在结尾则排列相当于《春秋》结尾部分所记述的“获麟”以外的记载,更进一步增补年代并叙述田氏的恶行,再记述孔子于“获麟”的两年后去世,以提示孔子无法作《春秋》。《左传》末尾用“悼”的微言表现,记述包括韩氏的三晋灭智伯的情形,形成称赞其灭智伯的“形态”。在此,《左传》已用“夫子”、“吾子”的微言显示赵氏、魏氏将来会灭亡。《谷梁传》参照《左传》的这些微言,变更《春秋》与《公羊传》的微言结构,对晋伐鲜虞的记事加以批评,因为晋自己身为夷狄却讨伐中国的鲜虞。接着在结尾部分叙述“获麟”之事,声言麟将永居“中国”。总之,《春秋》与《公羊传》是论述齐国正统的史书,《左传》是论述韩国正统的史书,而《谷粱传》则是论述中山国正统的史书;这些书籍都是阐述各个正统将迎接王出现的预言书。到了汉代中期,《春秋》被重新解释为论述汉朝正统的预言书,而《左传》则在新莽时期被重新解释为论述王莽正统的预言书。这些解释或明或暗地被历代继承,因此,为了将这些书籍当作史书来使用,不仅有必要了解其原本的正统主张,而且还需理解汉代以后的正统观下所作的重新解释的情形,这样才不至于将那些后代的理解或解释误认为史实,将后代的思想误认为前代即已存在。
1998年在日本的中国先秦史研究领域颇值评价的另一著作,是工藤元男教授著的《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和社会》。该书由日本创文社出版,受到日本学术界多方面的好评(注:池田知久《基于出土资料的新的中国史学的尝试——读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创文》403,1998年); 富谷至《睡虎地秦简研究的胜利者》(《东方》212,1998年); 大栉敦弘《工藤元男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东洋史研究》第五十八卷第一号,1999年6月); 汤浅邦弘《工藤元男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3号,1999年3月)。)。全书由序章睡虎地秦简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第一章内史的再编与内史·治粟内史的形成、第二章秦的都官与封建制、第三章秦的领土扩大与国际秩序的形成、第四章睡虎地秦简《日书》基础性的讨论、第五章通过《日书》所见的国家与社会、第六章先秦社会的行神信仰与禹、第七章《日书》中的道教性的习俗、第八章禹的变容与五祀、第九章《日书》所反映的秦·楚的视线、第十章战国秦的啬夫制与县制、终章睡虎地秦简所见的战国秦的法与习俗,即十二章构成。
在以往的秦简研究中,或者是通过秦律及“语书”、“为吏之道”这些法制史料的分析来探讨中国法制的历史,或者是只对《日书》等术数史料进行考察和研究。而拥有日本“秦简研究第一人”(注:大栉敦弘《工藤元男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东洋史研究》第五十八卷第一号,1999年6月。)之称的工藤元男先生, 在本书中,把秦律和《日书》共同作为分析的对象,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书中第一章到第三章,以秦律等法制史料为中心,对“内史”、“都官”、“属邦”、“臣邦”等作了制度上的探讨。诸如“都官”之类,都是文献中未见而通过秦简才知道的机构,因而,工藤先生采取在秦简中进行整合性的解释,并将其放在战国、秦汉史的前后关系中进行探索的方法加以研究。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在统一过程中战国秦国家的统治体制的面貌,例如领域的扩大、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统治秩序的结构等各个侧面,也就具体地浮现了出来。从第四章到第八章,是以《日书》为主要对象对当时的社会习俗、民间信仰等作的系统研究。其中,参照运用了诸如历法、天文、占卜法、五行说、道教、民俗学等各领域的成果,展开了整合性的颇有说服力的论述。第九章通过对《日书》中占法原理差异的分析,例如对二十八宿占、招摇、玄戈、稷辰、建除、岁等详细的分析,发现秦和楚的占法交错地存在于《日书》之中,从而得出与过去那种秦对占领地施以强权的印象不同的结论,认为秦的统治与当地的习俗是和睦的,它反映了秦采取的是“松缓的现实性的法治主义”。第十章通过啬夫制与县制的关系和结构问题,对秦的法治主义特色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其结论和第一章到第三章所讨论的内史、都官、属邦以及第四章以降所讨论的《日书》内容相同,即秦在推进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采取的是“松缓现实的法治主义”。最后,在终章中论述了睡虎地秦简中,既有容忍当地社会习俗的倾向(《日书》),也有把这些习俗斥为“恶俗”而试图进行一元性统治的倾向(《语书》),这是因为墓主某喜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秦的法治主义统治转换期的缘故。那么,在转换期秦的法治统治是如何进入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书中通过对《封诊式》的分析,认为《日书》中所见的宽松的法治,在《封诊式》的时期已经转换了,公元前258 年昭王采用帝号和变更历法岁首就是走向一元性统治的转换点。
睡虎地秦简是近年来战国秦汉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在对它进行解读和利用时,必然要碰到史料的性格问题,例如它究竟反映的是战国时代哪一段历史?其适用范围是限定在秦本土的关中地区好呢?还是适用于包括出土秦简的南郡在内秦的全领域?《日书》中所见的习俗是秦的东西还是楚的东西?诸如此类若不弄明白,显然会制约秦简的利用。对此,本书以“秦的法治主义的转换”这样的视角为纵轴,以“秦、楚的地域性”为横轴,来分析秦统一六国的过程,是一创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秦统一六国的过程大约可分为:秦的统治和支配首先经历了秦律被当地很厚的习俗之壁所阻而不得不通融的阶段,然后是渗入当地共同体内部,进而秦的支配体制向一元性方向转换等。此外,本书对秦简从法(制度)与习俗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既符合秦简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也有助于解开秦统一过程中支配体制的具体面貌。书中使用电脑将《日书》全文资料库化的手法,也是很值得借鉴的。总之,《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的国家与社会》一书超越了以往研究的框架,并对开拓相关联的新的研究领域亦颇有启迪作用。
标签:史记论文; 儒家论文; 日本战国论文; 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考古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春秋论文; 公羊传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