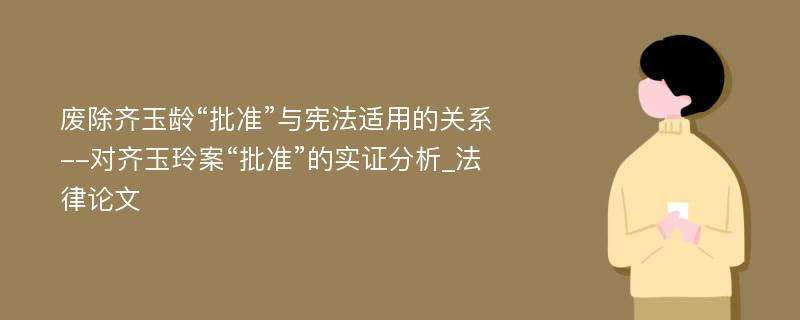
废止齐玉苓案“批复”与宪法适用之关联——“停止适用”齐玉苓案“批复”之正面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法论文,齐玉苓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欲探究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18日宣告废止齐玉苓案“批复”对宪法适用的影响,须追溯齐玉苓案“批复”本身的法律意义和法律性质,即该批复是否创制了一个宪法性的司法规则。如果是,则宣告其停止适用的法律意义非同寻常,可能对宪法适用产生消极影响,令人无限遗憾与叹惋;如果否,则该批复宣告停止适用的法律含义应另当别论。这需要重新追忆并检视当年该批复在理论与实践中产生的各种争执,并得出一个必要的宪法论点。
一、齐玉苓案“批复”创制了一个宪法性的司法规则吗
齐玉苓案“批复”本身存在诸多法律疑义,曾引起过激烈讨论,各种观点莫衷一是,不一而足,俱有学者撰文论证发表。归纳起来,这些论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齐案性质的认定。该案并非一个宪法案件,而是一个民事案件。其二,被告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是产生于宪法关系之中的,它是一个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①该案是一个民事案件,因而被告并未侵犯原告的宪法权利,而是侵犯了被告民事上的姓名权。其三,宪法上受教育权的法律关系属性如何?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或相应的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在此法律关系中,须有一方是公权力主体。其四,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的责任主体是谁?既然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的主体必须是公权力行使者,公民并不能成为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的主体。其五,违反宪法上的受教育权应承担何种责任?鉴于宪法关系的属性,如果公权力机关侵犯宪法上的受教育权,应该承担相应的公法责任而非私法责任,即不可能是民事法律责任。其六,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有权适用宪法?有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只是一般的司法解释;也有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是司法越位,或者司法“抢滩”。它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宪政体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了按照宪法规定本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的职权。②其七,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是一种宪法解释吗?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才有权解释宪法,法院无宪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在以批复为形式的司法解释中,实际上行使的是宪法解释权。
综合以上观点,齐案并非一个宪法案件,而是一个民事案件。在本案中,原告被侵犯的只是民事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并未受到侵犯,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无权解释宪法,结合本案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的批复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宪法上均有瑕疵,且鉴于批复本身的法律性质,从理论上来说,齐玉苓案“批复”并未创制一个宪法性的司法规则;从实践中来看,该批复亦未大规模推动宪法的司法适用。正如当年一位台湾地区学者所言,该批复虽然蕴涵着大陆违宪审查的曙光,但“法理有疑,用心良善。”③个中原因,皆因该案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本身性质所限,即其既非一个典型的宪法案件,其批复亦非创制一个宪法性的司法规则,反而是作为该批复的副产品,基本权利“第三者效力”理论在我国得以深入研究,它符合当年有学者就该批复所作出的预言,即其学理意义大于其实践价值。④
二、“批复”等同于“解释”吗
虽然齐玉苓案“批复”并未创制一个宪法性的司法规则,但毋庸讳言,废止该批复依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但其效力究竟何为,既取决于批复一般的法律性质,也取决于齐玉苓案“批复”本身。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分为三种,即“解释”、“规定”和“批复”。什么是“批复”?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法律含义究竟如何,须预先予以辨明。
1997年6月23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三种。对于如何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适用法律所作的规定,采用“解释”的形式;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对于审判工作提出的规范、意见,采用“规定”的形式;对于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采用“批复”的形式。既然针对不同问题所作出的广义上的解释有三种不同称谓,其法律含义和效力自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的相关性,这里主要区分“解释”与“批复”的法律意涵之差异。
解释是一种法律创制活动,我国宪法虽未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但实践中其已成为一项惯例,其解释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其第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其第14条规定:“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这里,明确规定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在将解释作为判决和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文书中援引,即是明确指出了解释的“法律效力”,且这一法律效力带有较强的普遍性。⑤
判例法国家的个案解释是一种附随解释,是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就所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的活动,释法的效力不是普遍的,而是被本级法院、本司法管辖区的下级法院所遵守。而且,为避免在特定案件中确立的规则产生普遍意义上的造法认识,通常宣称某一判决只针对本案中的特定事实,而不使该规则产生适用于一切案件的普遍效力。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某一法律”、“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个案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对于审判工作提出的规范、意见”在实际上也涉及法律的普遍适用。这是我国司法解释“立法化”,造法功能远大于判例法国家的一个有力例证。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及其后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来看,解释的对象不拘泥于个案适用的法律,而是“关于法律的具体应用”,带有立法的普遍性。
然而,从现有有关司法解释的理论与审判实践来看,有关“批复”本身的法律效力究竟如何,却语焉末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对于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采用“批复”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所作出的只是一个“批复”,在2008年12月18日作出的公告中,再次明确这是一个“批复”。“批复”与“解释”的法律效力当有如下差异。
1.该批复不产生“司法解释”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是“对于如何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适用法律所作的规定”。这类“解释”产生的是近似于立法的普遍拘束力,其在实际上具有创制规则的“立法”性质,尽管鉴于法院的职权性质,此处的“法律效力”与立法机关立法的普遍“法律效力”尚有很大分别。而“批复”则不然,它针对的是具体案件,针对的是“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以不产生最高人民法院“解释”那样的“法律效力”。
2.该批复只产生个案拘束力。由于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因而只有“批复”类似于判例法国家的判例规则,该批复并不产生最高人民法院近似于“普遍立法”那样的法律效力,对下级法院审判案件具有约束力,且只局限于个案。这也是为什么审判实践中没有出现大量援引此“批复”的原因之
3.“批复”的性质仅为一个“答复”。对于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有四个组成要件:一是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作出的;二是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作出的;三是就请示作出的;四是就请示所作出的答复。因此,它是一种“答复”,带有咨询性质。
三、“废止”与“停止适用”的法律效力何为
“答复”的法律含义何为,涉及“废止”与“停止适用”的法律效力。既然“答复”带有咨询性质,不妨检视一下世界各国的规定与惯例。
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创下了禁止咨询意见的先例,其理由是美国宪法明确规定法院的权力范围仅是“案例”和“争议”,且这一咨询仅仅是针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要求。其理由有三:一是三权分立原则确保法院超脱于立法程序之外;二是保存司法资源,法院的咨询意见有可能不被立法机关通过;三是确保提交至法院的案件是需要裁决的特殊争端。⑦
德国宪法法院有咨询的权力,且咨询的请求者不仅包括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也包括普通法院。咨询属于广义上的,包括“答复”和“解释”,对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具有指导作用,为此,设立在德国“司法之都”的德国宪法法院素有“卡尔斯鲁厄占星术”之称,它形象地表明了德国宪法法院的咨询意见对立法机关乃至行政机关的指导力量。虽然宪法法院咨询意见的效力并不明确,但其指导作用亦是不可低估的。该效力并非来自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是一种惯例,是基于宪法法院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其威慑作用,如果立法机关偏离这一指导作出立法,其后的立法可能会被宪法法院宣布违宪。与本文关联性更强的是德国宪法法院对包括行政法院在内的普通法院就宪法问题所作出的解释,这类解释在《宪法法院法》赋予的宪法法院职权范围内,也是德国普通法院与宪法法院权力界限的划分,即普通法院负责普通案件,审查事实,适用法律,而宪法法院负责宪法问题,解释宪法,裁决宪法诉讼。当包括行政法院在内的普通法院审理案件需要解释宪法时,须停止案件的审理,将需解释的条文提交至宪法法院,等宪法法院作出解释后,再依据解释内容裁决案件,而宪法法院自身并不对普通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作出查明。
我国宪政体制与美国和德国不同。宪法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最高人民法院并无宪法解释权。我国的宪法解释权集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手中,既非美国那样的分散式,联邦各级法院都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亦非德国那样的集中式,宪法解释是联邦宪法法院的专属权。因此,当下级法院遇到宪法解释问题时,应停止案件的审理,依据宪法,参考我国《立法法》对提起法律解释程序的规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宪法,俟解释发出后依解释内容判案,其具体的解释程序、方法、规则与效力亦可参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基本法解释所作出的规定,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次释法。
齐玉苓案“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所作出的答复,齐案已审结,鉴于当时认定该案宪法性质所存之瑕疵,以及答复本身只具个案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该案请示所作出的答复本身由最高人民法院“废止”、“停止适用”,既符合法理,亦在其职权范围内,某种程度上是最高人民法院重申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宪法解释权这一基本的宪法决定,属于正本清源。即使在判例法国家,对过往的判例规则,法院既可通过判例废除,也可以更改,还可不予适用,立法机关也可以通过立法程序废止或者修改判例规则。倘若最高人民法院不以公告的形式“停止适用”这一批复,就“批复”本身而言,其也应因时过境迁而自动失去效力;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废止”行为,则是一种依职权而作出的司法解释行为。
四、旧话重提:宪法实施是一个神话吗
齐玉苓案“批复”虽然被停止适用,但宪法“实施”的脚步不会因此停止。
在一个法治国家,包括司法判决在内及广义上属司法解释的司法文书和一切法律文件都具有法律效力,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停止“法释[2001]25号”即齐玉苓案“批复”的决定之法律效力自不应予以质疑,但亦不宜过分夸大其意义,一如当年“批复”本身。该批复既在齐案性质认定上存有偏差,也超越了我国宪政体制设立的权力分工;既然该批复并无创设一个宪法性的司法规则,其停止适用对宪法实施的消极影响也不应高估。这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澄清宪法实施、宪法遵守、宪法监督实施、宪法解释、宪法适用,以及“法律效力”等概念的含义。⑧
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宪法序言中载明的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最高之“法律效力”的含义何为?它是指以法律程序作出的成文规定,抑或仅仅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立法性宣示”,还是指法院可以实施的规则?联想当年德国基本法第1条“下列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规定对德国宪法及宪法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超越意识形态与道德因素,从纯粹法律实证主义角度予以审视,其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含义当在思考之列,而适时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亦迫在眉睫,它可激活我国宪法规定的宪法解释条款,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客观上推进宪法实施,维护宪法尊严。
注释:
①参见许崇德、郑贤君:《“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法学家》2001年第6期。
②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化引出的是是非非——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律师》2001年第12期。
③参见李鎨澂:《大陆违宪审查制度之曙光: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25号“受教育基本权遭侵害案”批复》,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4-4%5C13%5C1029226462.htm,2009年3月10日访问。
④参见沈岿:《宪法统治时代的开始?——“宪法第一案”存疑》,http://www.publiclaw.cn/article/Details.asp? NewsId=274&Classid=&ClassName=,2009年3月10日访问。
⑤这里姑且不去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规定自己明确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本身的妥当性问题,即审判机关是否有权自行赋予自己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而是这一规定所明确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的普遍拘束力本身。因而,我国司法解释具有立法化倾向,从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可见一斑。
⑥参见郑贤君:《美国司法保护多大的自由》,《中国律师》2005年第6期。
⑦See Enwin Chemerinsky,Constitutional Law:Principle and Policies,Third Edition,Aspen Publishers,2006,p.54.
⑧饶有趣味的是,在这些尚有些模糊的宪法概念中,其中宪法实施、宪法遵守、宪法监督实施、宪法解释俱为规范用语,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唯有“宪法适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用语。
标签:法律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时政论文; 立法机关论文; 最高人民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