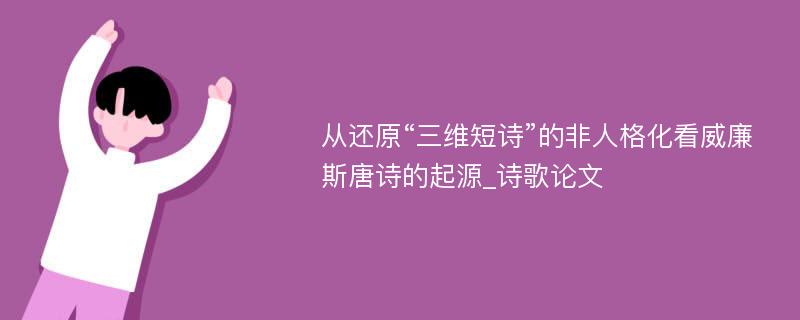
《勃鲁戈尔诗画集》——从回归非人格化“立体短诗”看威廉斯的唐诗缘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诗论文,唐诗论文,戈尔论文,画集论文,威廉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3-0034-10 美国诗评家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曾指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有两派,一派以叶芝、艾略特和史蒂文斯为代表,承袭法国象征主义传统,另一派以斯泰恩、庞德和威廉斯为代表,与法国象征主义背道而驰。(4)庞德早年曾在叶芝影响下追随象征主义,但1914年即与其决裂,称“象征符号好比算术里的数字1、2、7,价值固定不变”,其手法“往往让人想到低劣的技艺”。(1970:84,85)威廉斯亦不屑于“粗制滥造的象征主义”,他在1923年出版的《春天与万物集》(Spring and All)中强调,自己的诗歌“每个单词只代表其本身,而不为象征”。(Williams,1986:189)庞德的《诗章》(The Cantos)和威廉斯的《春天与万物集》乃反象征派现代主义非人格化、多层次诗歌的典范。必须指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威廉斯曾一度偏离反象征派现代主义的传统。用帕洛夫的话说,他的长诗《帕特森》(Paterson,1946—1958)“归顺了象征主义”,“是一部浪漫主义传统的自传体抒情诗”。(152,153)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四五年,亦即后现代主义诗歌兴起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威廉斯终于又重返他原属的反象征派现代主义传统。他的最后一部诗集《勃鲁戈尔诗画集》(Pictures from Brueghel,1962)不仅是他重振非人格化“立体短诗”的宣言,也是他复兴反象征派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 威廉斯偏离反象征主义传统由创造“阶梯型”诗体、替代其非人格化“立体短诗”而始。所谓“阶梯型”其实就是将一长句诗割成三行,逐行缩进,构成一诗节。他于1948年出版的长诗《帕特森》第二部开头即为一“阶梯型”诗节(triadic stanza): 在我自己外 有一个世界(43) 威廉斯一度认为“阶梯型”诗体长短不一的“可变音步”(variant foot)更符合美语的节奏,是“解决现代诗问题的出路”。(1957:334)沿用至1955年他却意识到这种诗体“用过了头,做作、古板——有斯宾塞和他后期的英雄诗体的味道”。(Buffalo University Poetry Collection)尽管如此,其后两年他仍继续用“阶梯型”诗体写《帕特森》第五部。不是他改变了主意,而是他写惯了“阶梯型”不好改,也无从改起。 1957年9月,威廉斯通过庞德新结识的青年诗友王燊甫(David Wang)提议同他合译汉诗,这是威廉斯求之不得的合作项目。庞德曾把翻译称为诗人探索新诗路的“最佳的训练”。(1968:7)同来自杭州的新移民诗人王燊甫合译汉诗能否为威廉斯晚年的创作生涯开辟新径?拙文《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以下简称《诗体探索》)详析了1958至1960年威廉斯与王燊甫合译汉诗的过程和效应,为解读威廉斯最后的杰作《勃鲁戈尔诗画集》、评论其文学价值作了重要铺垫。 威廉斯与王燊甫于1958年1月18日开始合译汉诗,他们合译的第一、二首诗为王维的《鹿柴》和《山中送别》。如《诗体探索》揭示,1920年前后威廉斯诗体突变,由抑扬五音步(十音节)长句改革为二、三音步自由体短句,他切割诗句的本领从“立体派”画家毕加索那里学来,而革新组合成的四行小节却取自翟理斯(H.A.Giles)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中所介绍的唐代绝句。因为运用了立体画家切割拼合的手法,诗又写得极其短小,他的这类诗被称为“立体短诗”(minimal,spatial poetry)。王维的《鹿柴》和《山中送别》让威廉斯又回想起四十年前按翟理斯收录的绝句排列创作《彻底摧毁》(“Complete Destruction”)、《红红的独轮车》(“A Red Wheelbarrow”)等立体短诗的情景。(钱兆明:58—59)改译王燊甫提供的初译稿时难免拘泥于译诗的形体。王燊甫阅后并不欣赏,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意思走了样”。(Yale Beinecke Library)威廉斯又译一稿,仍未被选入威廉斯、王燊甫译诗合集《桂树集》(The Cassia Tree)。可慰的是,两次改译王维绝句所下的工夫并没有白费,威廉斯重新尝到了“立体短诗”的甜头。 1959年春,威廉斯带着摆脱“阶梯型”、回归“立体短诗”的念想开始创作《勃鲁戈尔诗画集》。《诗画集》所收63首短诗均由两行、三行或四行小节构成,其中仅《礼品》(“The Gift”)和《海鳖》(“The Turtle”)两首诗尚保留“阶梯型”的倾向。美国学者斯密特(Peter Schmidt)评论《勃鲁戈尔诗画集》时曾指出,这些诗歌“简短整齐的诗行和诗节同‘阶梯型’诗体错落而喋喋不休的诗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43)为论证他的观点,斯密特将收入《春天与万物集》的《花盆》(“The Pot of Flowers”)与收入《勃鲁戈尔诗画集》的《蝴蝶花》(“Iris”)作了比较。按他的分析,《蝴蝶花》虽用了泛指人称代词“我们”,却同不含人称代词的《花盆》一样客观、非人格化。该诗仿《花盆》不顾句法,在不该断节的地方断节,制造一现即逝的悬念。首节用一连串带“咝”声的名词(“burst”,“iris”,“breakfast”)模拟惊讶,创造愉悦的气氛(244): 用早餐 蝴蝶花的清香致使(Williams,1988:406) 第二节端出人物和后续动作(“我们穿梭一间间屋子/寻找/那”),但同时又播下了“寻找何物”的新悬念。第五节,亦即末节,在找到清香来自“怒放的蝴蝶花”的兴奋情绪中结尾。 《蝴蝶花》固然给威廉斯晚年诗作带来了一股清风,集子里更有助于探索威廉斯非人格化“立体短诗”回归过程和动力的却数十几首由四行小节构成的诗歌。《舞蹈》(“The Dance”)一诗共九小节,首节用拟人的手法描写飞扬的雪花: 下雪天雪花 围着它眷恋的 长轴不停旋转 一对一飞舞(407) 每行控制在五六个音节,不禁让我们想起威廉斯改译《鹿柴》与《山中送别》所作的实验。威廉斯在这里运用“雪花”、“不停旋转”等形象,且六次反复名词或动词“舞蹈”(“dance”),又让我们回忆起威廉斯1920年所作《致白居易》中在雪地里不停奔跑的“戴红帽的姑娘”和“亡故的灿烂舞后”。(Williams,1986:133;钱兆明:57) 《勃鲁戈尔诗画集》中形似绝句的有《短诗》(“Short Poem”): 你打我一记耳光 啊,如此地温柔 这一轻抚 让我甜蜜一笑(1988:416;卢巧丹译) 《菊花》(“The Chrysanthemum”)一诗则如律诗,或两首叠加的绝句: 如何才能把 鲜亮的花瓣 与天空中的 太阳区分开 枝头的花朵 团团又簇簇 谦逊略逊色 竞相放光彩(396;卢巧丹译) 《诗体探索》已讨论威廉斯开创“立体短诗”时所作《彻底摧毁》如何模仿五言律诗方方正正、上下两节的形体,这里无须再指出他回归“立体短诗”所作《短诗》、《菊花》与绝句、律诗的雷同处。 《勃鲁戈尔诗画集》同《春天与万物集》一样,是用文字创作的立体主义拼贴画。除第一至十首为勃鲁戈尔诗画,该诗集所收其他短诗与勃鲁戈尔均无联系,且互不相关。例如,《蝴蝶花》、《菊花》、《鸫鸟》(“The Woodthrust”)、《小鸟》(“Bird”)和《北极熊》(“The Polar Bear”)写的就是蝴蝶花、菊花、鸫鸟、小鸟和北极熊。它们并不象征任何人或事物,却各自传达一种感受,涵义开放,因读者的想象而易。要说威廉斯用了什么修饰手法,那就是词汇、句法的反复。反复是反象征派现代主义诗人标新立异的惯用手法。对帕洛夫而言,威廉斯频繁运用反复、“非人格化”诗歌的老师是19世纪法国反象征派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110)兰波固然为威廉斯开创了以反复求“异化”的先例,但笔者认为,除了兰波谜一般的散文诗集《灵光》(The Illuminations),威廉斯还借鉴了白居易的闲逸诗。《诗体探索》用威廉斯私人藏书眉批揭示,他曾于1919年前后细读过韦利(Arthur Waley)所译白居易《嗟发落》: At dawn I sighed to see my hairs fall; At dusk I sighed to see my hairs fall. They are all gone and I do not mind at all! I have done with the cumbrous washing and getting dry; My tiresome comb for ever is laid aside. Best of all,when the weather is hot and wet, To have no top-knot weighing down on one’s head!(Waley:84) 译诗首句“At dawn I sighed to see my hairs fall”(“朝亦嗟发落”)为叹息,下句“At dusk I sighed to see my hairs fall”(“暮亦嗟发落”)反复“I sighed to see my hairs fall”(“嗟发落”),加深叹息,并变异为自嘲,表现了诗人的诙谐、乐观。威廉斯曾效之,于1920年作《致白居易》: 工作多繁重。只见 秃树枝上白雪累累。 我以花甲之年的你 来安抚我自己。 一个戴红帽的姑娘一闪而过, 她跌倒了起来又跑, 齐脚踝的大衣上沾满了雪 除了亡故的灿烂舞后 我又能想到什么?(1986:133) 此诗以“秃树枝上白雪”起笔,戴红帽的姑娘大衣上“沾满了雪”承上,反复“雪”字,内涵亦由沉重变为明快。 反复常用词汇、推陈出新,杜甫更胜白居易一筹。杜诗之高超威廉斯至晚年才领教。1957年威廉斯为《诗刊》(Poetry)评瑞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译《一百首中国诗》(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时,曾盛赞唐诗:“就我所知的英美诗歌、法国、西班牙诗歌,无一能与中国诗歌比拟,无一像中国诗歌那样潇洒自如”;“中国诗人追求简洁,其意象各异,个个刻入我们的脑海”;“诗中的女性仿佛出现在我们跟前,用我们不懂的语言,跟我们直接对话,让我们跟她一起哭泣。”(1985:241—43)写到这里,他引了两首杜诗,《晓望》(“Dawn over the Mountains”)和《宾至》(“Visitors”)。《晓望》首联“白帝更声尽,阳台曙色分”,瑞克斯罗斯草率译为“The city is silent;/Sound drains away”。《宾至》“喧埤方避俗,捉快颇宜人”一联,在瑞克斯罗斯笔下成了“It is quiet too,No crowds/Bother me”。这两首诗中,杜甫捕捉了不同的客观细节作渲染。威廉斯称赞道:“所见客观事物顺诗人笔端,跃然纸上,美不胜收(不都美妙,有时也让人毛骨悚然)。传至今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1985:245)“所见客观事物…… 跃然纸上”赞扬的是杜甫做到了庞德所提倡的“直接处理主观或者客观的‘事物’”(1968:3)和威廉斯本人提倡的“思在物中”(“no ideas but in things”)。(1992:6) 改译王维《洛阳女儿行》时,威廉斯是否在模仿杜甫,让王维的叙述者直接同读者说话?王燊甫提供的译稿首句和第七句本无反复,威廉斯却各加了一个Look。反复的句式,“Look,there goes the young lady across the street”和“Look,she’s coming thru the gauze curtains to get into her chaise”(1988:364),让读者身临其境,仿佛窥见了诗中美貌的女主人公。具反讽意义的是,威廉斯与王燊甫合译杜甫《佳人》时,却没有译出其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联的反复。这也不能责怪威廉斯,王燊甫提供的初稿“Spring in the mountains is clear,/Mud underfoot”(Yale Beinecke Library)已略去杜诗的反复。 《勃鲁戈尔诗画集》中意象、句法的反复,不能不让我们回想起威廉斯译过的唐诗和读过的英译唐诗。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威廉斯译过两稿,虽未能照样反复“人”字,第一稿却背离原诗在首尾反复“复照青苔上”一句中的“青”字:“Empty now the hill’s green...the green of the moss there”。白居易《耳顺吟寄敦诗梦得》首句“未无筋力寻山水”,其中“山水”一词又用于《山游示小妓》(“今为山水伴”)等闲逸诗,表现诗人引退后平和静谧的心态。1958年10月威廉斯第二次中风,病瘫中的他在《诗画集》中一再引用花鸟,是否在仿效白居易?像四十年前为丧父而悲痛时那样,写下《致白居易》一诗,“以花甲之年的你/安抚我自己”? 花有花开花落日,鸟有鸟飞鸟栖时。威廉斯抑或记得韦利所译白居易《暮春寄元九》首联“梨花结成实,燕卵化为雏”(“The flower of the pear-tree gathers and turns to fruit;/The swallow’s eggs have hatched into young birds”[Waley:45])隐含的轮回的哲理? 步入晚年的威廉斯,显然对人生的四季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更能感悟世间万物皆有四季,循环往复不已。他关注的唐诗往往都论季节。李白的《春歌》乃春之歌,王维的《洛阳女儿行》是夏日的故事,杜甫的《佳人》吟寒冬的佳人。《勃鲁戈尔诗画集》里的诗亦几乎每首都点明季节,连十首勃鲁戈尔诗画也不例外。《伊卡洛斯坠海之景》(“Landscape with the Fall of Icarus”)首节即明示“按勃鲁戈尔名画/伊卡洛斯坠海/是在春天”(“According to Brueghel/when Icarus fell/it was spring”[1988:385]);《收玉米》(“The Corn Harvest”)起笔第一句就是“夏日”(“Summer!”[389]);《农民婚礼》(“Peasant Wedding”)是秋季的婚礼,“新娘座位旁的墙上挂着麦穗”(“a head/of ripe wheat is on/the wall beside her”[388]);《雪中猎人》(“The Hunters in the Snow”)“整幅画都是冬天的景象”(“The over-all picture is winter”[386])。十首诗画还包含人生的四季:《国王的礼拜》(“The Adoration of the Kings”)耶稣诞生,《儿童游戏》(“Children’s Games”)学童玩耍,《农民婚礼》和《户外婚礼狂欢》(“The Wedding Dance in the Open Air”)男婚女嫁,《收玉米》和《翻晒干草》(“Haymaking”)喜逢收获,《盲人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Blind”)盲人遭灾,《伊卡洛斯坠海之景》伊卡洛斯坠海身亡。花鸟四季变化,人生四季更迭,周而复始,皆在其中。 《勃鲁戈尔诗画集》第一至十首用专用术语说,属“艺术转换再创造诗”(ekphrasis)。它们再造了文艺复兴时代尼德兰大画家勃鲁戈尔(Pieter Brueghel,1525-约1569)的名画。老勃鲁戈尔以画农家乐著称。1924年春,威廉斯偕夫人访欧,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欣赏过老画家《伊卡洛斯坠海》(The Fall of Icarus)等名画真迹。1959年他中风康复后以诗歌形式再造这些杰作并非单凭回忆和想象,而是参考了革鲁克(Gustav Glück)编注的画册《老勃鲁戈尔》(Peter Brueghel the Elder,1952)。这十首诗一概用三行小节写成,每行限于一至五个单词或一至七个音节。从《勃鲁戈尔诗画集》的这些主题诗,我们可以洞察唐代绝句、律诗,特别是白居易绝句、律诗的影子。开篇《自画像》(“Self-Portrait”)再造了一个慈祥可爱的老画家的肖像: 红色的呢帽下 一双微笑的蓝眼睛 脸盘和肩膀 占满了画面(1988:385) 现已确定,所谓勃鲁戈尔《自画像》非勃鲁戈尔所作,画的也非勃鲁戈尔。1924年威廉斯参观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时,此画确实依旧错标为勃鲁戈尔《自画像》。然而,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欧美艺术界就已纠正了这一错误。威廉斯不可能不闻不问。他参考的《老勃鲁戈尔》画册并没有收这幅画。这里,威廉斯显然在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似乎在仿效1938年纽约出版的一本畅销画册《老勃鲁戈尔》(The Elder Peter Brueghel),这本画册用《自画像》作封面,而不论及此画的作者。我们不妨不去追究《自画像》的作者究竟是谁,他画的又是谁。无论怎么说,《自画像》刻绘的画家总还是同《致白居易》中兴高采烈地奔跑的姑娘一样戴着红帽。换一个角度,诗画中的老画家又同晚年的白居易或晚年的威廉斯一样,不修边幅,但仍勤于耕耘: 双眼带血丝 想必他 用眼过度 细巧的手腕 显示他不常 干体力活 棕黄色的胡子 没有刮干净 除了画画他 哪有空顾那些(1988:385) 《勃鲁戈尔诗画集》其二《伊卡洛斯坠海之景》首句一笔点明此景不依据古罗马《变形记》而“依据勃鲁戈尔”(“According to Brueghel”)。景中的农夫不像《变形记》叙述的那样,被伊卡洛斯坠海而惊呆,甩掉手中扶着的犁,去赞叹所谓下凡的神仙。他照常埋头“在耕/地”(“was/ploughing his field”)。 沿海的 村民们 在晒化 [伊卡洛斯]蜡翼的 太阳下躺汗 忙自己的事 不打紧 大海里 扑腾一声 无人注意 伊卡洛斯 坠海了(1988:386) 熟悉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的人都知道,古代克里特岛国的能工巧匠代达罗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被囚禁在他们替国王设计的迷宫里。父子俩戴上自制的蜡翼飞上天,企图逃离迷宫。伊卡洛斯上了天便忘记父亲的谆谆告诫,“不能飞近太阳”。他渐渐飞近火辣辣的太阳,以致蜡翼融化,坠入大海。根据《变形记》,伊卡洛斯坠海时沿海耕地的农夫、捕鱼的渔夫和牧羊的牧羊人都以为神仙下凡,惊讶得分别甩掉了手中的犁、鱼竿和羊鞭。可是20世纪的威廉斯、文艺复兴时代的勃鲁戈尔和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都不相信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在他们看来,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时刻都会发生,没有人会因此而停止正常生活。 这十首诗画与收入《桂树集》的唐诗同期再创造,于1960年春在纽约《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上先发表。它们既再造了勃鲁戈尔的风格,也掺入了威廉斯自己乃至他仰慕的唐诗的美学观。韦利所译白居易闲适诗的乐天精神和辨证观亦体现于这些艺术转换再创造诗。例如,勃鲁戈尔名画《伊卡洛斯坠海》的中心思想已不是伊卡洛斯坠海,而是照常劳作的农夫。威廉斯的诗画将此颠倒的主题置于生死的辩证框架:春天初醒的村民成了主人公(“the whole pageantry/of the year was/awake”),坠海的伊卡洛斯(“Icarus drowning”)只是配角。据中央位置是生命而不是死亡。勃鲁戈尔的画题毕竟还因袭罗马神话的《伊卡洛斯坠海》,而威廉斯取题即将伊卡洛斯坠海置于次要的位置,“The Landscape with the Fall of Icarus”要是直译应为《含伊卡洛斯坠海的景色》。 勃鲁戈尔名画《雪中猎人》以白雪覆盖的山林为背景描绘了几个夜归的猎人。威廉斯仅用寥寥两句诗将猎人一笔带过,更多的笔墨刻划了“画面右边/几个农妇凑在一起/拨弄篝火/让它在大风下/烧得更旺/远处山边/有人在溜冰”(“a huge bonfire/that flares wind-driven tended by/women who cluster/about it to the right beyond/the hill is a pattern of skaters”[1988:386—87])。旺盛的篝火与冬夜寒冷的雪山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人在溜冰”的意象,恰如白居易闲适诗中“山水伴”的意象或威廉斯《致白居易》中在雪地里蹦跑的“姑娘”的意象,把整首诗的气氛从阴暗转化为明快。 勃鲁戈尔画笔下的《收玉米》(The Corn Harvesting)展现了一个丰收繁忙的场景。有人批评威廉斯的艺术转换再创造诗无视画面上百分之九十二的细节,无视紧张的劳动,去写一个躺在大树下酣睡的青年男子。(Lawson-Peebles:19)威廉斯哪里无视了紧张的收获?有张也有弛,有劳也有逸,有“有为”也有“无为”。这里威廉斯是通过“逸”写“劳”,“静”写“动”,“无为”写“有为”。他笔下的男子是“干了一上午活/彻底放松”(completely/relaxed/fromhis morning labors”[Williams,1988:389])。这让我们想起未满四十岁的威廉斯,受白居易《嗟发落》的影响,在仿俳句诗《春天》(“Spring”)中,破西方诗歌的俗套,用“早春”而不是“晚秋”写自己初见的灰发:“啊,我的灰发!/你确实跟杏花一样白”。(1986:158) 凡事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威廉斯同白居易一样遇事偏向于光明的一面。从勃鲁戈尔名画《户外婚礼狂欢》威廉斯看到的除了欢乐还是欢乐。他笔下“穿着蹩脚皮鞋/干农活的工装裤/张大了嘴/一圈又一圈旋转”(“round and around in/rough shoes and/farm breeches/mouths agape”[1988:390—91])的狂欢农民同白居易《山游示小妓》中的老少舞伴一样悠闲自得、忘乎所以。《盲人的寓言》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勃鲁戈尔名画描绘了六个盲人,一个牵一个的竹竿往前走,一个跟一个跌进陷坑。威廉斯的艺术转换再创造诗粗一看很忠于原画,末行“得意洋洋地遭灾”(“triumphant to disaster”[391])一句却暴露了他添加的东方意识。西方学者只知道威廉斯用了“矛盾修饰法”(oxymoron),殊不知“得意洋洋地遭灾”还隐含中国所谓“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辩证哲理。 《勃鲁戈尔诗画集》讴歌四季轮回,写得最多的还是冬天。生怕有人会误读他的人生观,威廉斯以《复苏》(“The Reawaking”)为题又写了一首压轴诗,重复周而复始的主题,重申他对阳光、玫瑰花、紫罗兰和爱的憧憬: 我们要走到 重构玫瑰 玫瑰意象 的尽头 但还没 你说要把相爱 的时光 无限延长 让紫罗兰 重开到 夫人脚跟前 让阳光 你的爱 再复活(1988:437) “重构”、“重开”、“再复活”皆强调诗题“复苏”所点明的主题,同白居易《暮春寄元九》首联一样,影射世间万物周而复始的自然规律。这首诗可理解为老诗人同他夫人推心置腹的对白,但亦可理解为他同他热爱的生命和诗歌创作事业的对白。 《勃鲁戈尔诗画集》问世于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年代。以金斯堡(Allen Ginsberg)为首的“垮掉的一代”、由奥尔森(Charles Olsen)领军的黑山诗派、以洛威尔(Robert Lowell)为代表的自白诗派等应运而生,从不同的角度向庞德、艾略特和威廉斯等老一代诗人倡导的“非人格化”诗歌创作原则发难。威廉斯当时似乎没有理会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但他的《勃鲁戈尔诗画集》却披露了他对这场论战的态度。1952年8月威廉斯首次中风,而后又连续中风四次,其中后三次发生在1958至1963年间。在生命的最后四五年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带着半瘫的躯体坚持用“开放型”、“非个人化”的美学原则创作。在最后一部诗集中,他重振并发展“立体短诗”,为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又谱写了辉煌的一章。 “非人格化”是上世纪初艾略特从反浪漫主义着眼,在论文《传统和个人才能》(1917)中提出的一个强调以“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表现主题的诗歌创作理论。威廉斯历来反对艾略特滥用西欧经典,为的是其“新经典主义”阻扰了以他为代表的、独立的美国现代诗的发展进程。威廉斯也承认艾略特是一个了不起的现代派诗人。1948年在给出版商劳克林(James Laughlin)的一封信中,他曾称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The Four Quartets,1942)为“庞德不再创作诗歌的今天,唯一的真正有独创性的诗歌”。(Mariani:571)在“非人格化”这个原则问题上,威廉斯和艾略特并无分歧。威廉斯开创“立体短诗”的启蒙老师,兰波和白居易,都是“非人格化”的高手。唐代诗人王维、李白、白居易追求的“无我之境”和艾略特讲的“非人格化”说的大致是一个意思。“无我之境”也好,“非人格化”也罢,其实都是“表面无我,实质有我”。唐诗《洛阳女儿行》、《春歌》、《佳人》和《长恨歌》均“无我中有我”。威廉斯的《红红的独轮车》、《春天与万物》、《伊卡洛斯坠海之景》、《盲人的寓言》、《菊花》等诗何尝不是如此?白居易的《嗟落发》和威廉斯的《春天》似有不同,但这类诗中的“我”非自白诗中的“我”,此“我”因摆脱了“私欲”和“自我主义”,已非通常意义上的“我”,走的依然是艾略特所谓“不断牺牲自我、不断消灭自我”(Eliot:7)的路子。 毋庸讳言,后现代主义诗人和评论家在攻击现代主义“非人格化”原则时通常将威廉斯撇开,矛头直指艾略特和他的正统规范。金斯堡、洛威尔等自称是威廉斯的继承人,有一定的道理。威廉斯在评论、书信乃至自传中曾多次攻击过艾略特的新经典主义,他“开放式”、富有美国特色的诗歌确实对垮掉的一代、自白诗派等有巨大的影响,他与金斯堡、洛威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并撰《在悲剧的情绪中》(“In a Mood of Tragedy”)、《为卡尔·索罗门嚎叫》(“Howl for Carl Solomon”)等文肯定过他们的诗歌。(1985:187—88,225—26)人们往往容易忽视金斯堡、洛威尔等与威廉斯的共识限于推广“开放式”诗歌和使用地道的美语。他们之间虽然没有公开争论,毕竟代表着两个不同的诗歌创作方向。首先,金斯堡和1959年以后的洛威尔全盘否定“非人格化”的现代主义创作主张。金斯堡的成名作《嚎叫》(Howl,1956)和洛威尔的代表作《生活研究》(Life Studies,1959)都写个人与美国现代社会、美国现代家庭的冲突,表现诗人内心的愤怒、恐怖和痛苦,都离经叛道,代表所谓“美国反抗文化”。威廉斯虽然在《帕特森》和《爱之旅》(Journey to Love,1955)中也曾尝试过摆脱“非人格化”,探索过矛盾心理,但他从来没有真正否定过“非人格化”。在逝世前四五年间,他通过与王燊甫合译汉诗,又重新领会到了“非人格化”高超的美学价值,从而在《勃鲁戈尔诗画集》中不折不扣地贯彻了这一原则。其次,在处世哲学上威廉斯与金斯堡、洛威尔等后现代主义诗人也有本质的差别。威廉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现代社会也有不满,他的婚姻、家庭生活也有矛盾冲突。然而,他在诗歌中表现的胸怀、心态始终是平和、乐观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唐诗对他的影响。如果说读英译白居易诗、研究绝句为威廉斯1916至1920年探索独特的“立体短诗”、确定“平和无为、随遇而安”的美学观铺垫了道路,那么同王燊甫合译王维、李白、杜甫等人的古典诗歌则为他晚年重温并回归这种诗体和这种心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60年春,金斯堡继《嚎叫》再版之后,又抛出哀悼母亲、厌恶社会的《卡迪绪集》(Kaddish and Other Poems)。1960年夏,洛威尔自白派代表作《生活研究》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同年,另一位自白派诗人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出版《巨人集》(The Colossus and Other Poems)。后现代主义诗歌风靡一时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叶芝、斯泰恩和史蒂文斯已不在人世,艾略特已沉寂。病瘫的威廉斯却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创作了又一部“非人格化”的现代主义杰作《勃鲁戈尔诗画集》。21世纪的评论家在审理那个时代的美国诗歌时,有理由将其视为老诗人对后现代主义诗歌反“人格化”的应战,更有理由将其视作他为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吹响了“再复活”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