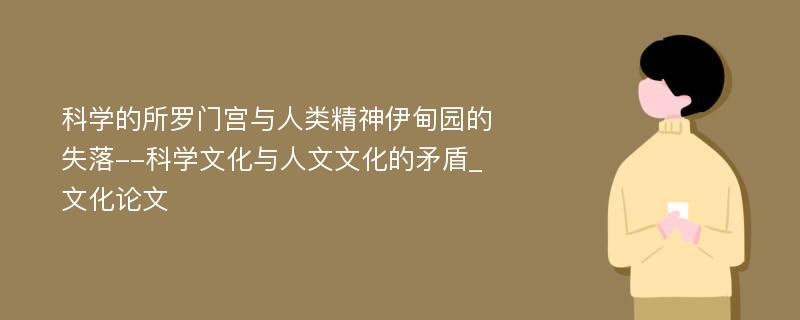
科学的所罗门宫与人类精神伊甸乐园的走失——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罗门论文,伊甸乐园论文,科学论文,文化与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曾构想过一个无知无欲、幸福美好的精神乐土——伊甸乐园,培根也曾设计了一座充溢着知识氛围的科学圣殿——所罗门宫。人类总是具有不同的文化朝向,而现代社会这种科学与人文文化间的距离似乎在不断拉大;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却并未能沿着这两条路径重新找回伊甸园或真正建立起科学的圣堂,相反却日渐感到价值、信仰的贫乏和这两种境界的走失。
一、若即若离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被马克思誉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培根曾精心设想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新大西岛的所罗门宫,在那里国王不再是柏拉图推崇的哲学家而是睿智的科学家。这种纯科学的乌托邦可能使当时同样笃信知识就是力量的人心潮澎湃;但在时光荏苒数个世纪之后,人们发现这种纯然的科学圣境仍只是一片海市的虚茫。
人们当然不能不诚服科学的成就,在整个文明史上用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功业来譬喻科学的功勋并不为过,科学甚而使许多的神话成为现实。然而社会发展至今,却也有了许多与科学相违的事实:曾认为必将被科学逐出的宗教峰回路转,在那歌特式建筑高耸的尖券下仍回荡着教徒虔诚的赞歌;科学本是人的创造物、是文化中的珍品,但人在惊异于科学的突破、惊异于自身无限的创造力的同时,对科学的恐惧也在潜滋暗长,因为人们已然置身于一片肮脏嘈杂的环境中,置身于为越来越多冷漠的机器排挤或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尴尬境遇中、置身于毁灭整个人类的核武器的危胁中——人们对于科学正在由绝对信服转为怀疑。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人类自尊心先后从科学手内受到了两次重大打击。第一次是知道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仅仅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的一个小斑点……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人的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而同样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兽性……然而人们的自尊心受到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最难受的打击,这种研究向我们每个人的“自我”证明就连在自己的屋子里也不能自我主宰〔1〕。科学与人有了异化的趋向,人在科学面前感到了一种生畏的自失,而这种异化更明显地表现在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离散上。现代人文文化的主张者不乏对科学的指摘甚至贬斥:在未来主义派电影的创作中艺术家们有意放弃科技的应用而转向手工着色;而早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小说家乔治·吉兴就曾写道:我憎恶和害怕科学,因为我相信如果不是永远也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将是人类残忍的敌人,我看到它破坏着生命的一切朴实与和善,破坏着世界的美丽〔2〕。这种状况倒不禁让人想起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旦偷吃了禁果获得了智慧就被上帝永远逐出了伊甸乐园……。人们一贯倾向于用“爱智”标明西方文化的特点,可有意思的是西方文明源流之一的希伯莱文化一开始就把智慧与痛苦联系在了一起。或许人类对于科学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止过,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却日益扩展了一条疏离的代沟,英国著名科学家兼作家C·P斯诺在其所著的《两种文化》一书中淋漓地描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背离,似乎古代人对智慧的忧思真的成了现实的预言。
所有这些使我们几乎淡忘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甚至一切文化间曾有过的和谐。古代最早从事科学活动的是祭司和僧侣;基督教会也曾为了强化人们的宗教意识鼓励人们去认识自然,因为自然界的和谐秩序有助于确证有一位超人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存在——科学与同它最大相径庭的宗教也有过一种畸形的默契。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医学数学成果与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绘画等彼此交融、相得益彰,甚至当时如达·芬奇、委罗基奥那样的艺术大师也同时是在天文学、数学、地理、诗歌、音乐等方面造诣颇深的博学者。文艺复兴运动使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双双摆脱了神学的阴霾。科学与人文的联姻使当时的人们对一切都显得信心十足: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康德也表白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文化的协调使那时以至其后的一段时间里科学、人文领域都缭绕着云蒸霞蔚的祥和。即便是现代,虽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间出现了种种反常,但我们仍能看到两者间断续的统一:曾把捍卫科学的布鲁诺处以火刑的罗马教廷却在1936年正式成立了罗马教廷科学院,不断表明对科学厌恶反感的文学也不可能完全超逸于科学所提供的丰硕成果,更不用说人的日常生活了。在人类历史中真正使人的主动性、优越感不断提高的多种原因里不可能排除科学。它的确正成为改造人类思想的整个模式的一个决定因素,人类不能不怀着敬畏的心情褒奖科学的创造发明者,并在人文领域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科学交融。于是,如歌德歌剧中所塑造的为了知识而出卖灵魂的浮士德式的悲剧形象便不单单是艺术虚构:人们在科学面前忐忑不安,可对知识的渴求又不肯松懈。我们看到的是科学与人文裂痕之上某些断续的接界,是人类对于科学亦喜亦忧的矛盾心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与交融的并存。
人们可以把科学尊奉为阿拉亭的神灯又可以把它贬斥为潘多拉的盒子,那么什么导致了这种矛盾,造成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疏远呢?
二、两种文化走散的原因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走散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文化中至真、至善、至美价值取向向度的多重性。人类情感愿望的丰富多样决定着人们对文化的创造、选择是基于不同向度的。人类崇尚实现至真的科学创造也渴望着人文文化来满足对于善和美的需要。因循哲学的逻辑,我们也许可以推导出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但作为文化取向向度,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复杂的。如果说在文化发展的幼年这种统一还是主要的,那么在现代芜杂繁多的文化图景中,它们已日渐偏离了这种统一的肇端。
实际上,人类文化取向往往是多元、矛盾的。苏格拉底曾提出道德即知识的命题,认定知识就是普遍的善,而中国的道家则竭力主张“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3〕;倘使人们慎重而不是武断地考察中世纪宗教神学时也应当承认,宗教虽然禁锢了人,可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一大批神学家致力于宗教研究、虔诚的崇拜者沉迷于宗教氤氲的神秘氛围并不是绝对的盲从,宗教以其独特的价值形式贡献于人们的道德观念、理想境界并深刻地影响着欧洲文学、音乐、绘画等古典艺术,人们在宗教中得到了一种稳固的安全感、归属感以及教义的诗意美;相反现代许多人批评社会一切技术化、商品化而使美感丧失。在科学技术把人从繁重的体力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匠人们却又在安闲中感受到失去了陶醉于劳动创作带来的美感后的沮丧。
真、善、美的价值是文化存活延续的前提,不过很少有一种文化能兼有真善美多重价值而相应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正因如此,人类文化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文化完全湮灭取代其他文化,人类文化始终是博杂的。同时,人类文化取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可能朝向日神阿波罗梦的幻觉,也可能欣赏酒神狄奥尼索斯醉的迷狂;可能追求着宇宙中高深的真谛,也可能固守着人类童年时期某些崇拜的痴迷。大概人们自身都还不很清楚至真至善至美究竟哪一个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源、哪一个是人类文化追求的鹄的,但人们的确在不断地选择、不断地试图从一种文化的长期压抑下挣脱而追寻另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在这中间,大多数人在潜意识中把科学规定为至真的圣地、把人文文化设想为美和善的家园,这使得人们已然在文化选择时把二者对立起来,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表达的“没有美的科学,只有美的艺术……至于一个科学,若作为科学而被认为是美的话,它将是一个怪物”〔4〕。这样,当人们希图一个充满着善和美的幸福人生时,人类在文化选择上已不自觉地倾向于人文文化而轻易地放弃了科学,那种认为一个科学数字也可能是美的人毕竟是少数。文化取向向度的多重性影响着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契合。
第二,人类注意的焦点从人与自然关系到人与人关系的转向。目前,学者们在探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时习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认为人由万物主宰的尊贵地位向在由科学发现的神秘宇宙前日显卑微的处境的变换使人对科学、对自身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无助感,科学在加速发展但人类面前仍堆积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许多就是科学自身导致的“恶果”。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一般来说大致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分两种基本哲学气质,但是否可以据此轻易确定文化类型、诠释文化矛盾的产生呢?按照很多人主张的,西方文化是一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文化,但实际上在其高度发展的科学文化面前并没有隐没人文文化的异彩;而中国古人倡导天人感应的和谐关系,可中国的科学仍然保持了上千年的领先地位,相比而言,人文精神却没有象西方那样得以充分地孕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然而它却并不构成文化离析的主因。既然否定了人与自然关系转变在这中间的重要作用,那么比它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表述了这样的思想——人与人的关系正代替人与自然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成为相互交往的首要方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人对于自然,无论是主张人为自然界立法、制天命以用之,还是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总归是相对简单的:社会发展至今人们认识上虽稍有偏差,可对于人具有征服自然的能力同时又受制于自然的观念还是基本认可的。相较之,人自身、人与人却是亘古纠缠的斯芬克斯之谜。在人猿揖别二百万年之后,人们对于情欲、罪行、战争等人间百态仍感到恍惑,人们赞颂人又贬低人,把人奉若天使又把人斥为地狱。人口数量的剧增、联系的密切使人在外在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得不内向地把关注的焦点移至自身。在这方面科学虽然有过帮助,但它的迅猛发展也使得人在还来不及完全适应它时又动摇了固有的价值、伦理观念,于是人变得更为恍惑。科学是人确认了对自然主体地位的筚路蓝缕者,但在解决人类自身问题时却碰到了赫拉克勒斯石柱,它不能有效地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在这种关系转变的过程中,人们自然地朝向人文,希望实现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格言,人们开始渴求一种精神的皈依、渴求一种终极关怀的寄托。正如在文学上鲁宾逊、桑提亚哥式的征服自然的硬汉在减少,更多的是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劳伦斯的《虹》之类的作品,尽管其文字费解但却表现着对人、对人与人关系的关注,为我们勾勒着复杂的人性和复杂的人类生活。我们不能说科学在这方面已然隐遁,不过至少它不能完全补白人们迫切需要充填的精神空间。
第三,科学发展历程表现出的批判性与现代人追求超越的心理迎合,使人倾向于对原有文化的背弃。科学发展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不断变换,不断否定,既清晰又模糊的世界图景。曾被人们确认过的、长期垄断科学界甚至影响整个社会观念的牛顿经典力学也终有一天为后来的科学理论所修正。人们瞠目地看着一个个科学理论、假说的提出和覆灭,每一种流行的理论几乎都可能成为明日黄花。本世纪量子力学、自组织、混沌理论的出现更在科学这个天经地义地被认作纯客观的领域内加进了越来越多的主体的影子,世界面貌变得摇曳复杂,而科学并没有给人们一个确定性的说法。
这种状况恰好与现代人追求超越的心理相迎合。人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生物,他意欲、期望着,思考、想象着,人对未来持着种种杞忧却又总试图超越,摒弃已有的圭臬达到自身和认识的完美,这是人类进步的心理机制也是人性中的污浊。于是往往对于世俗头脑越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得到人们的信仰反而可能会越多。存在主义所倡导的“超越就是最本质的存在”成为现代人精神、心理的写真。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反对自身的凭借,它熏陶了人怀疑、批判的心态,这种心态不仅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发生着影响,而且即便是人文文化内部也难得统一。种种文化流派接踵而至,人们刚刚还沉醉于蒙娜丽莎安祥、恬静的微笑,歆享文艺复兴时代浓郁的人文氛围,却又不得不面对法国画家杜桑为这种美的化身强行加上的两撇胡须,牵强地附和它为达达派风格的“艺术”。
如此,将来面对挑战的不仅仅是科学,也有人文文化自身。我们无法断定人对一种信念究竟愿意笃信多久。
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合璧的断想
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离移“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超然心境而必须对自然、对社会以及人类自身进行认识和抉择。在一定意义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反映着文化发展日趋丰富和人类文化选择自主性的增强;不过选择的任意性、文化形式的彼此排斥也造成了文化的畸形,于是我们看到统一、正确的文化精神的匮乏所造成的:一方面是科学理论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是巫术、神秘主义的虚幻、诡谲;一方面是清新可人的美文诗品,另一方面是洋洋数百万字却晦涩难懂的怪诞梦呓;有卢浮宫中灿烂的艺术,也有诸如杜桑送到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上展出的《泉》之类的作品:有皓首穷经的学者,也有恣情纵欲的人群——文化和人都走向偏执的极端反科学,反传统,又都在这中间感到信仰失落后的茫然,希图能找到一种可以依凭的关怀、眷注。是否科学与人文文化注定要走散、文化创造和选择注定要成为随意呢?
我们的确经历过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融合、协调时期,马克思曾赞颂它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5〕,较为统一的文化气韵使那个时代实现了人的价值,科学与人文文化领域取得了令人感唱的成就。这样的时期不应该成为唯一,因为人类日渐感到需要一种文化精神主旨的找回,并且作为服务于人的创造物,它们也是具有协调的契机的。当代西方新人本主义、科学人性化等思潮的兴起也表明人们正在试图寻求二者的合壁。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是要使文化划一,前面所谈到的文化矛盾的诱因决定着文化面貌必然是多样的,就我理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贴近在于找寻文化联系交融中“度”的界标,以避免僭越这种“度”的界限而孕育出文化畸形的怪胎,这种“度”首先是一种在判断力、价值观、审美道德标准等方面健康正常的文化心理。
人文主义者对科学文化执有偏见在于他们片面地强调了科学的负效应,其实这只是因为人类还未曾适应科学所赐予的支配大自然的能力。事实上,科学文化的品质不仅在于它所提供的物质手段,“除此之外,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不那么具体,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6〕,科学文化验证着人万物之长的地位、能力,并使人类文化发展具有了永恒进取的自信心,这种信念也应成为人文文化心理的支点,朝向科学,人文文化中颓废、消极、玩世不恭的文化因子会减少许多。同时,透过那些看似怪异的人文文化,我们也不难发现许多非理性文化本质上也渴望着对理性的召唤,荒诞派剧作家尤金·尤内斯库在日记中写道:世界是什么?我们周围的一切是什么?我是谁?……我将要做什么?我打开始就用这些问题问自己。我等着回答,而我应该自己提出答案,发明答案。我等着奇迹。奇迹没有来。大概一无所知,但一个人必须有一种理性,必须寻找一种理性,更不失掉他的理性〔7〕。科学文化正是人文文化所要求助的理性答案,以科学的文化心理为源流,灿烂瑰丽的真正的人文文化就不会断流。另一方面,就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的意义来看,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综合,这种综合必将突破科学文化圈内的囿制、横亘到包括人文文化在内的广阔领域,因为科学也需要灵感、顿悟、美与道德观念并从人类文化视野中汲取思维方式,成为综合自然、人类、历史的更为全面的理性。科学文化的缔造者们对于人文文化的选择,接纳也影响着科学的发展。爱因斯坦在《文集》第三卷中多次谈到他虽不信奉宗教,但对科学抱有一种宗教样的情感——即他经常称颂的那种神秘体验。科学同样需要人文文化心理中炽热的情感,执著的意志,这样的科学文化才真正具有人的创造物的特点。
文化心理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文化构建中极难改变但又必须改变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合壁首先的,根本上的都在于突破彼此隔绝的心理防线:人文文化从科学那里寻找自信心、理智的意念,科学文化从人文文化中吸取朝向人的情感、价值观念,从而使文化获得不断进取的健康心态。这种心理上的贯通是文化融合的起步,而真正使科学文化、人文文化相辅相成还在于文化创造的主体——人的不断努力,在于人能否负责地对待文化,从潘多拉盒底发现寻找回文化精神的希望。
注释:
〔1〕《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8页。
〔2〕陈清硕:《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时代特点和取向》, 《自然辩证法》,1993年12期,第64页。
〔3〕《庄子·肢箧》。
〔4〕康德:《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6〕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542页。
〔7〕翁义钦主编:《外国文学与文化》,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 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