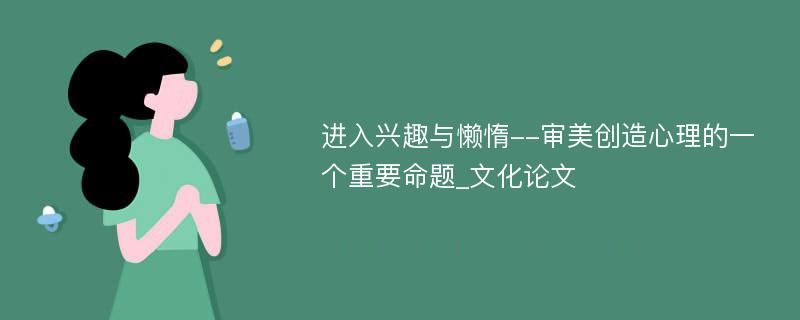
入兴贵闲——关于审美创造心态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个重要论文,命题论文,心态论文,入兴贵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34(2000)01—0077—06
一
“入兴贵闲”这样一个说法并未受到古代文论界的重视,但在我看来,却是一个关于审美心理的重要命题。它与“虚静”说有密切关联,十分相近,而又有着深刻的差异。如果说“虚静”是一种自觉进入的空明澄静的精神世界,那么,“入兴贵闲”则是指无意为之的闲适心态进入审美感兴。
“入兴贵闲”一语出于刘勰《文心雕龙》的《物色》篇,其云:“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而造极,或精思愈疏。且诗骚所标,并具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唱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作家应该把握描写对象的特征,使作品产生历久弥新的审美情味。而“入兴贵闲”则是主张在一种闲适优游的心态下才能产生创作上的感兴。有的论者以规矩法度训释“闲”字,这样译解“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因此,一年四季的景色虽然多变,但写到文章中去要有规则。”[ 1](P119~120)释“闲”为“法度”[1](P119~120 )固然并非全无依据,但通观《文心雕龙》的整体来看,这种解释却是扞格不通的。
“闲”在这里无须曲为之释,就是闲适心态。纪昀的评价颇为中肯,他说:“四序纷回四语尤精。凡流传佳句都是有意无意之中,偶然得一二语,无累牍连篇苦心力造之事。”[2](卷九、 卷十)纪昀显然是认为此中之“闲”即闲适无意的心态。联系《文心雕龙》的其它篇章,可以看到纪昀的阐发是符合刘勰原意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有关创作论的一些篇章的论述中,提倡作家平素的陶养文气,以优游闲适的心境获致诗文创作的灵机,而不主张临纸苦吟,强刮硬搜。较为集中地表达这种思想的是《养气》篇,其中的论述颇为值得我们注意:“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夫学业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锥股自厉,和熊以苦之人。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斯亦卫气之一方也。”《养气》通篇都可以视为“入兴贵闲”这个理论命题的系统阐释,而刘勰是从“养气”的角度来谈创作心态之“闲”的,易言之,“闲”的含义就是指作者“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的身心状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认为:“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之常利也。”这样来看此篇之旨是对的。《养气》所论,与《神思》篇中“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联系非常密切,但又是“虚静”说所不能全然包括的。刘勰主张,为了更好地进行诗文创作,不能过于劳累,以致于气衰神疲,即所谓“销铄精胆,蹙迫和气”,而应该颐养精气,使自己神完气足,“从容率情,优柔适会”。“弄闲”也就是“率志委和”,其反面则是“钻砺过分”。范文澜先生这样阐述“养气”之旨:“彦和论文以循自然为原则,本篇大意,即基于此。盖精神寓于形体之中,用思过剧,则心神昏迷。故必逍遥针劳,谈笑药倦,使形与神常有余闲,始能用之不竭,发之常新,所谓游刃有余者是也。”[2](卷九、 卷十)此言极是。也正是回答了什么是“入兴贵闲”的问题,把“养气”与“闲”的关系揭示得非常清晰。刘勰最早把“养气”概念引进艺术理论之中,并作专章论述,把养气同感兴、神思等相联系起来,强调养气对于艺术构思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刘勰这里,“养气”是使作家呈现身心闲逸状态的根本途径。
二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入兴贵闲”这个命题,我们不能不对刘勰的“养气”说的理论意义作一点必要的探讨。“气”的概念,在中国哲学发展中有这样几个主要含义:一是指自然万物的本原或本体;二是指客观存在的质料或元素;三是指具有动态功能的客观实体;四是指人生性命;五是指道德境界;等等。可以说,气是一个有着多重内涵的范畴。“养气”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最早提出的便是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而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并非自然界的天地之气,也不是人体中的阴阳之气,而是一种道德精神。孟子回答什么是“浩然之气”时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同上)孟子所说的“养气”,是纳入其主体心性之中的。荀子也提出“治气养心”的理论,他说:“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荀子·修身》)“治气”与“养心”,其实是互文见义。可以认为,荀子所谓“治气养心”,是以气质涵养为主的。孟、荀的“养气”,更多的是一种道德境界和气质函养,属于主体心性的范畴,这与刘勰所说的“养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刘勰的“养气”,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而颐养自己体内的“精气”或云“元气”,在这一点上,刘勰主要是发挥了《管子》、《白虎通》、王充和葛洪关于“气”的思想,并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的。
中国气论哲学中关于“气”的一种重要阐释是人禀受天地阴阳之气而充于体内和精神中的“精气”。《管子》把气规定为精气,即指不断运动变化的精微的气。精气是形成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精微物质,赋予人以生命和智慧,又赋予人的形体,这比《易传》“精气为物”的命题更为明确深刻。汉代思想家王充以元气为天地万物之木原,构建元气自然论的哲学体系。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生,随元气运动而发展变化。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同时,也是智慧生灵的本原。在王充看来,人是最有灵性、最高级的有智慧的生命,构成人体及其道德精神的气是最精的。“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论衡·论死》)刘勰作《养气》,是颇受王充影响的,其在开篇即云:“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这里所说王充的“养气之篇”,是指其《养性》一书。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说:“章和二年(公元88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养性》一书已佚,但从这篇《自纪》中可以得知这是作者晚年所作的一部关于“养气自守”、“爱精自保”的书。东晋道教大师葛洪从道教养生之学的角度论气,提出“人与气互涵”的思想。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抱朴子·内篇·至理》)葛洪把气作为生命的本原,所以他论气与命说:“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之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同上)葛洪主张养性保命,其中关键在于养气。命受气的制约,气决定生命力的盛衰。气盈则精力充沛,气竭则生命终结。
应该说,刘勰所谓的“养气”,更多地是沿用王充——葛洪“养气”说的含义,颐养体内精气,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刘勰最先把它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指出作家在创作时不宜“钻砺过分”,那样不但不能创作出艺术精品,反而会“神疲气衰”,而如果能“率志委和”,则会使作品“理融而情畅”。通过养气而使自己精力充沛,在一种闲逸充盈的心境中进行创作,方可使文思灵动,如新发之刃,无往不利。刘勰从葛洪的“宝精行气”之说受到深刻启示,移之以说明作家创作时所应具有的充盈闲逸的心态。这就不仅具有创作心理学的意义,而且是将生理和心理联系在一起来揭示审美创造的奥秘。“闲”的创作心态,是“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的结果。
三
如果说刘勰的“入兴贵闲”说还是在诗文创作的范围内提出来的命题,那么,无独有偶的是,著名的画论家宗炳也在其山水画论的开山之作《画山水序》中论及“闲”的心态在审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以成巧,早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远天励之丛,独无应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于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这段话当然不如刘勰的“入兴贵闲”那样具有高度概括的理论价值,但在绘画领域中提出了以“闲居理气”而进入审美过程的观点,反映出当时的理论家对于“闲”的审美心态的共同认识。“畅神”是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而欲得“畅神”的体验,则必以“闲居理气”为其心理前提。
这种闲逸的心态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可以使创作主体在面对最普通的日常事物时进入感兴状态,以一种浓厚的审美兴趣来观照生活,从而使再平凡不过的景物或生活场景闪烁着美的光辉。不妨举人们非常熟悉的大诗人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来说明这种情形。像大家都相当谙熟的《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移居》(春秋多佳日)、《饮酒》(结庐在人境)这几首名诗,都是诗人辞官归田以后不久所作。诗人的心境闲适恬淡,脱离官场污浊,忘却世事营营,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心远”。在这种心境中,本来是非常普通的乡村景色与农家风物,进入诗人笔下,则变成了十分优美的诗意境界,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精品。诗人所谓“虚室有余闲”,并非仅是身体之休闲,更主要的则是从官场中抽身时的心境之闲。没有这种“余闲”、“心远”,就不会写出如此富有审美韵味的诗境。用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敞开”。海德格尔这样来表述艺术的真理:“真理从来不是现存和一般对象的聚集,不如说,它是敞开的敞开,是所是的澄明。是作为投射描划出的敞开的发生。这使它在投射中出现。真理,作为所是的澄明和遮蔽,在被创造中产生,如同一诗人创造诗歌。所有艺术作为让所是的真理出现的产生,在本质上是诗意的。艺术的本性,艺术品和艺术家所依靠的,是真理的自身投入作品。这由于艺术的诗意本性。在所是之中,万物是不同于日常的另外之物。……诗作为澄明的投射,在敞开性中所相互重垒和在形态的间隙中所预先投下的,正是敞开。诗意让敞开发生,并且以这种方式,现在敞开在存在物中间才使存在物发光和鸣响。”[3](P67~68)这段看上去颇为晦涩的论述,却深刻地道出了“存在物”与艺术品或诗之间的关系。正如海德格尔在同一篇文章所举的凡高所画的农鞋的例子,作为具体存在物的农妇劳动时穿的鞋子,是一种被遮蔽的存在,而当它进入了凡高的画中,就得到了“敞开”。“一个存在者,一双农鞋,进入作品,处于其存在的光亮之中,存在者的存在的显现恒定下来。”(同上)这对于我们理解日常的、普遍的景物与事物何以在进入真正的艺术品中时,具有了浓郁的审美韵味,是颇富启示意义的。而中国美学中的这个“入兴贵闲”,正说明了在审美创造主体方面的重要条件。“闲”其实也正是一种“澄明”。在无意的闲逸心态之中,世俗的功利杂念都已消遁了,隐逝了,充盈调畅的精神气息,使诗人在观照日常的、普通的景物和事物时都感受到了充沛的诗意,而使其笔下创造出的意象或意境焕发出美的光彩,甚至具有一种审美“乌托邦”的性质。
四
我们再来看一下唐宋时期一些诗人、艺术家在这种“闲”的心态下所创造的诗歌意境有着怎样的特点。
在唐宋一些著名诗人那里,“闲”的心态也许潜藏着颇为丰富的内蕴,大概可以说是一种饱谙人生况味而后的心灵恬适。“闲”主要不是指身体的休闲,而是安恬的心境。这又多半是与诗人们的禅学濡染很有关系的。王维、孟浩然、裴迪、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都是与佛禅有很深的因缘、而又在其诗歌创作中流露出“闲”的心态的。禅学中所说的“不应住色生心”(《金刚经》),“无心之心”,“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坛经》)等,对唐宋时期的诗人们的人生观是有很大影响的。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诗人大多是在经历了仕途的失意、政治上的打击以及人生的磨难之后,对禅理有了更深的体悟,进入一种萧散闲淡的心境的。这种心境又使其诗歌创作在从容纡徐之中有着更为渊深的含蕴。
在这方面,王维是相当典型的。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磨难后,虽然仍在朝中挂职,却更为栖心释梵。他中年以后卜居辋川,游心禅悦,心境闲淡,如他在诗中写到的:“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长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不妨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往还。”(《答张五弟》)“端居不出户,满目望云山。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遥知远林际,不见此檐间。好客多乘月,应门莫上关。”(《登裴迪秀才小台作》)“井邑傅岩上,客亭云雾间。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岸火孤舟宿,渔家夕鸟还。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登河北城楼作》)“寒更传晓箭,清镜览衰颜。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川闲。借问袁安舍,悠然尚闭关。”(《冬晚对雪胡居士家》)等等。这些篇什,意境空明玲珑,神韵悠远天然,而且,很明显都是出自于“闲”的创作心态的。裴迪是王维的“法侣”(禅友)与诗友,在辋川时常与王维唱和,也在诗中不断表露出这种“闲”的心态:“不远灞陵边,安居向十年,入门穿竹径,留客听山泉。鸟啭深林里,心闲落照前。滔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同王维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其诗中的心境、风格,与上述摩诘诗可谓同调。白居易晚居洛阳、分司东都之后,最典型的心态便是“闲”。“闲适诗”是其为自己诗集编类的重要一类。白居易的后期诗歌创作,就多有以“闲”为题者,如《闲乐》、《夏日闲放》、《闲坐》、《闲咏》、《闲居》、《春池闲泛》、《闲卧,寄刘同州》、《闲园独赏》、《唤起闲行》、《晓上天津桥闲望》、《初夏闲吟》、《喜闲》、《池上闲吟二首》、《闲出》等等,约有数十首之多。这种情形并非偶然。饱经宦海浮沉后的闲逸中潜藏着很深的感慨。这种感慨遇到外物的触发便转而为诗之感兴。可以举白居易的《闲咏》一诗以见其一斑:“步月怜清景,眠松爱绿荫。早年诗思苦,晚岁道情深。夜学禅多坐,秋牵兴暂吟。悠然两事外,无处更留心。”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白居易晚年的闲逸之情与其佛学濡染是颇有关系的,而这又牵动着诗兴。柳宗元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被贬永州,在永州期间,他也是以一种“闲安”的态度来面对自然山水,从而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佳篇。柳宗元对佛教的态度与韩愈不同,韩愈排佛甚力,而柳宗元则颇为嗜佛,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推崇“为其道者”那种不入名利场中、“乐山水而嗜闲安”的人生态度,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他认为这些佛徒禅僧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不争权位,有着“乐山水而嗜闲安”的恬淡超脱,这正是他所向往的,如他称许僧浩初所说:“今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为其道,以养而居,泊焉而无求,则其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其亦远矣。”(同上)这也正是他所说的“忘机”。在其诗歌创作之中,诗人一再抒写“忘机”的体验:“发地结青茅,团团抱虚白。山光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禅堂》)“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旦携谢山人至愚池》)诗人在其中忘却了朋党倾轧的险恶,在“忘机”的闲逸中得到心灵的宁静与愉悦。王安石晚居钟山,诗人的心态也是一种摆脱政争纷扰的闲适,其诗作多有一种闲适之趣与宁静之美。如他在诗中写道:“屋绕湾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临溪放杖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定林所居》)“乌石冈边缭绕山,柴荆细路水云间。吹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乌石》)这类诗的风格与其表现出的诗人心境都不脱一个“闲”字。由上面所举的几位诗人可以看出,唐宋诗人创作中的“闲”,又大都是与禅学有关的,易言之,唐宋时期诗中的“闲”,多有佛禅因素在其中。禅家以心为本体。而其所谓“心”,乃是一种“无心之心”。也就是不造作,不染著,无拘无缚。这种观念对唐宋诗人们是有很深影响的。
“入兴贵闲”是关于审美创造心理的一个有价值的命题,它与“虚静”说有密切联系,但又有着独特的内涵。对于诗歌创作来说,“闲”这种创作心态给诗作带来的是徐纡从容的气度和悠远空灵的意境。我们在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探颐中,应该充分认识“入兴贵闲”作为理论命题的意义。
收稿日期:1997-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