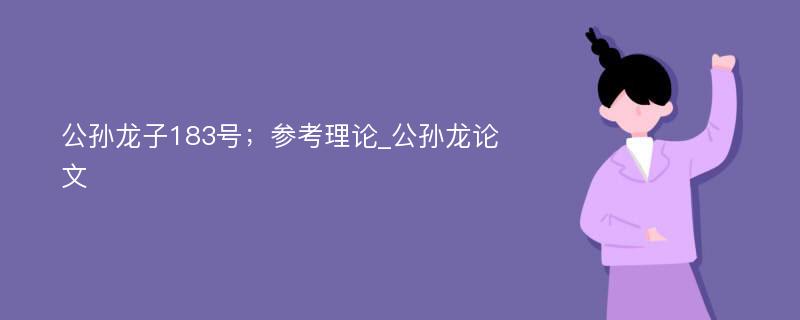
《公孙龙子#183;指物论》绎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孙龙论文,绎旨论文,指物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孙龙子古称“辩者”(《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则将《公孙龙子》列于“名家”。《汉志》载《公孙龙子》十四篇,自宋而后流传至今的只有六篇。其中,记载公孙龙子生平行事的〈迹府〉乃汉晋时人掇拾旧文、拼凑断章而成;其他篇什,特别是〈白马〉、〈坚白〉、〈指物〉以及〈名实〉(尤其是开头的部分),都是研究公孙龙子哲学思想的可信资料。
庞朴曾说:“《公孙龙子》是诸子书中最难读的一本,而〈指物论〉又是《公孙龙子》中最难读的一篇。”①的确,《公孙龙子·指物论》前言不搭后语、曼衍支离,充分体现了“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及“诡辞”(扬雄《法言》)的特点,很难读通;由于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宋谢希深《公孙龙子注》又不可征信,遂使《公孙龙子》成了失传千载的绝学,不易董理。但我们不敢畏难,期望通过校释、解读、分析和阐释,抽绎〈指物论〉中隐含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它的理论预设。
幸运的是,近现代以降,人们对《公孙龙子》及其哲学思想的兴趣越来越浓。俞樾(《俞楼杂纂》)、孙诒让(《札迻》)开始了对《公孙龙子》的精细校订;胡适、冯友兰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重新认识和发现了公孙龙子;而陈柱《公孙龙子集解》、王琯《公孙龙子悬解》、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沈有鼎《〈指物论〉句解》、伍非百《公孙龙子发微》、庞朴《公孙龙子研究》、杨俊光《公孙龙子蠡测》、许抗生《先秦名家研究》诸书②,都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真知灼见,我们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阐释〈指物论〉。
一
我们认为,虽然〈白马〉、〈坚白〉、〈名实〉和〈指物〉诸篇讨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都是反映《公孙龙子》哲学思想的基本材料。换言之,它们(不同论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沈有鼎先生注意到了〈指物〉和〈坚白〉之间的差别,认为前者的主旨是“合同异”,而后者却是“离坚白”,因而推测〈指物论〉也许出于晋人爰俞之手。③我的看法是:沈氏判断〈指物论〉晚出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从内容上推敲,它恰恰发展了〈坚白论〉中的“离”的思想倾向。总的来说,〈白马〉部分地以〈名实〉为基础,〈坚白〉进一步推进了〈白马〉的核心论点,这些论点终结于〈指物〉,就是说〈指物〉极端地推进了公孙龙子的主要思想。简言之,贯穿于《公孙龙子》——尤其体现于〈指物论〉中——的哲学思想就是那种以名辩形式出现的感觉主义。试详论之:
〈白马论〉提出的“白马非马”,从逻辑上说是把“同一律”绝对化了,仿佛只能说“马是马”、“白马是白马”。这一思想的端倪已见于〈名实论〉,特别是其中关于“位”、“唯乎其彼此”的讨论;而且〈名实论〉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名”、“实”间的疏离,其曰:“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据谭戒甫的透辟分析,所谓“物以物其之所物”就是“形色”,第二个“物”字训“相”(动词)。④既然如此,公孙龙子所谓“实”其实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色”而已,而公孙龙子所说的“名”基本上也只能抵达“形”、“色”(而不能标明物的所谓本体)。那么,儒、墨两家坚信的抽象的名(概念)表述、把握事物(以及物理)的常识观念就受到公孙龙子的质疑和挑战。公孙龙子执著地认为作为物性的“形”与“色”诉诸不同的感觉(对形态与颜色的知觉),因为: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形者,非命色也。故曰白马非马。
就是说:“白+马=色+形”,因为“色+形”(白+马)不能仅仅归结为“形”(马),所以只能说“白马非马”。
〈坚白论〉进一步发展了〈白马论〉中的感觉主义主张,其核心论点是“坚”、“白”(物的属性)是相互分离的“两样东西”,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感知的不同功能,例如“坚”(性)对应于触觉(拊)而“白”诉诸于视觉(视)。〈坚白论〉曰:“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谢希深解释说:“坚非目之所见,故曰无坚;白非手之所知,故曰无白也。”这里所说的“无坚”、“无白”,只是宥于感官感知而已,但在公孙龙看来,这是导致“见(白)与不见(坚)离”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只承认“坚石”抑或“白石”,却不承认存在什么“坚、白石”。如果说“坚、白离而不盈”表明了不同感觉(视觉与触觉)间的割裂的话,“白马非马”则表明了同样缘于视觉的色、形两者亦是割裂的。可见,公孙龙子把感官诸根的不可替代性孤立起来,甚至绝对化了,从而割裂了感觉,否定了感觉的统一性。儒(例如孟子和荀子)、墨两家都认为感觉统一性系于理性,知觉受控于心,道家(例如庄子)亦未否认“心与心识知”整合感性知觉的功能与作用,然而公孙龙子却继起了彻底感觉主义的思想逻辑,根本上否认了理性统驭感性的作用:
且犹白以目见,目以火见,⑤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面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坚以手(知)而手以捶(知),是捶与手知,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坚白论〉)
对于诉诸于视觉而能认识的“白”来说,是什么原因或条件才能使人们获得对它的认识呢?是眼睛(目)吗?可是眼睛(目)之所以能够“看到”东西是因为有光(火)的缘故。“目”是能知,光(火)是条件,如果没有“光”(火),“目”也不能见物。旧注说:“人谓目能见物,而目以因火见。是目不能见,由火乃得见也。然火非见‘白’之物,则目与火俱不见矣。”如此说来,能见“白”的东西是什么呢?这段话里的“神”颇为触目。“神”笼统地说,就是精神的意思;确切地说,就是理性认识的能力或功能。“目”与“火”不能见物之“白”,那么是由于“神”才能够看见“白”么?可是在公孙龙看来,“神”也不能“看见”物的“白”。同样,对于“坚”的属性来说也是如此。公孙龙的结论似乎就是“神不见、神与不知”,简单地说就是“神不能知见”⑦,而不是沈有鼎所认为的“不以目见而以神见”⑧。
显然,公孙龙子认为“神”既不能“见”(诉诸视觉)亦不能“知”(诉诸触觉),所以它(神)是不起什么作用的(“离焉”)。那么,《公孙龙子·坚白论》表明了:感觉的感知是所谓“知”的唯一来源,“神”不能认识事物的属性(如“坚”和“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神”这么一回事,所以他要反问“神乎?”既然没有“神”,那么“坚”和“白”必定就“分离”了。不难看出,这里的“神”扮演了感觉深处的、可能被当做是感觉统一性的角色。不过,公孙龙否认这种作为感觉统一性的“神”,从而彻底地维护了自己纯粹的感觉论立场。因而,谭戒甫孤明先发,透辟地指出:《公孙龙子》只承认物的“形”而不承认物的“实”,或者说“实”乃是悬而不可知的东西;相应地,《公孙龙子》只承认感觉而不承认心神,从知识论上说,“感觉所及,形物自著,并无心神运乎其间”,此即感觉主义(Sensationalism)。⑨当然,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而不可知论与感觉主义(Sensationalism)往往就是孪生兄弟。也许这正是我们深入分析、正确认识《公孙龙子》哲学内容和思想特点的关键所在。⑩
既然人们只能借助自己的感官诸根感知事物,而诸根又不能互通,那么呈现于我们感觉之中的事物就只能是它的形色之类的属性。至于事物背后是否隐匿了一个看不见的本体,人们是否可以借助概念思维把握这个本体,公孙龙子显然是持有异议的。冯友兰以为,公孙龙子(指物论)中的“指”乃是“共相”(11),我们不敢苟同。从共相与殊相的角度来分析,公孙龙子乃是绝对的、不折不扣的“殊相论”者,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感觉主义者。很明显,沿着“殊相”和感觉主义的思想逻辑推而广之的话,取缔“名”(概念)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殊相和感觉世界里,“名”(概念)充其量是空洞的符号而已。实际上,〈指物论〉的重要旨趣就是瓦解那种企图透过物表深入本质的“名(谓)”,而与纯粹感觉相互匹配的只是也只能是“指谓”。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指物论〉开卷伊始的命题“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之中。由此可见,《公孙龙子》诸篇什问亦呈现出互补、转折和递进的理论关系,从〈名实论〉到〈指物论〉的展开,犹如剥笋抽丝。
总之,〈指物论〉不言自明、默认的理论前提就是公孙龙子“一以贯之”的感觉主义及其思想逻辑,而它的宗旨却在于阐明“指不至”命题。《庄子·天下》篇所载“辩者遗说”里有“指不至,至不绝”命题,《列子·仲尼》篇亦载“有指不至,有物不绝”之语,一般认为它们源于公孙龙的思想。(12)伍非百先生认为〈指物论〉的目的就是阐明“指不至”,它的核心思想是说:万物本体不可知,可得而知者,不过都是“指”而已。进而言之,〈指物论〉洞见到当时人们热衷讨论的“名”与“实”之间的疏离,由于“实”无法通过概念来认识与把握,所以“实”即物的本体不能直接进入人们的认识范围。(13)谭戒甫也认为,公孙龙子主张“指不至”,“谓物的现象不能达到实体”(14)。这样一来,作为哲学概念的“名”之存废,就成了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追问,〈指物论〉中“指”、“物”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也是一个不能望文生义的问题,而以往的研究看法亦莫衷一是,我们认为,“指”这个字,伍非百所说的“指而谓之”,王琯所说的“指定”,较为近是。而陈柱解作“名”,未谛;至于谢希深《旧注》释为“是非”,更加莫明其妙了。然而,〈指物论〉中的“指”本身也是有歧义的,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指非指”中的两个“指”的含义就迥然不同:第一个“指”是“指而谓之”(能指)的意思,但第二个“指”(所指),似乎可以引申为“恉”或“旨”,即意旨。(15)“物”这个字也值得推敲,因为它多少有点游移不定。实际上,《公孙龙子》中的“物”、“实”,准确地说就是“物之形色诸德”,也就是说,“物”(或者说“实”)仅仅诉诸它的形色,可见《公孙龙子》的“物”、“实”概念并不意味着“物之本体”。(16)因为《公孙龙子》认为,“物”的属性与样式就只能是诉诸“形”、“色”;而人们对于“物”的认识也只限于感觉,如“眼”能看到“形”(马、牛),能辨别“色”(黄、白),再如手的触觉能感到“物”的“坚”(性)等等。
接下来,我们不妨取诸〈指物论〉本文,随文略加校释,以期深入探讨公孙龙子的感觉主义名理学思想。
二
〈指物论〉“玄之又玄”,很难读通,原因之一就是,它本来是一篇主客往返答问、相互辩难的“对话”,因为篇中省去了许多“曰”字(其中的某些“曰”字甚至讹为了“且”字),延误已久,以致许多注释家都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了。傅山、陈澧、陈柱、沈有鼎和庞朴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沈有鼎对此讨论尤详。(17)然而,篇中语句哪些反映了“论主”的思想,哪些出自于“问客”之口,则人言人殊。我们主要依据〈指物论〉的思想脉络,参取陈柱、沈有鼎和庞朴的“分析”意见,大致确定了主、客的“分野”,并随文校释,只是为了便于深入讨论而已。
(主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释] “论主”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核心命题。“物莫非指”的意思是说,凡“物”都是“指而谓之”的东西。“指(谓)”不同于“名”,它仅仅是“指马为马”、“指鹿为鹿”而已;倘若“指鹿为马”,那么“鹿作马时我亦鹿”了。“指非指”句中的两个“指”有不同的含义:第一个“指”是“物指”,即“物之所指”,也就是“物”的“指谓”;后一个“指”的意思较复杂些,乃是“所指”,甚至还包含了某种“指之所指”代表的“物之本体”的意味。公孙龙不是柏拉图,他根本不承认什么“马的相”,也不承认人的心眼儿能够看到那个超乎视听的“马的真形”(Eidos)。〈指物论〉反复阐明了这一命题(“指非指”),甚至说“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意思是说:“指非指”是一个绝对原则,适用于一切“物”而不必诉诸具体的“物”来证明它。这就是“指非指”命题的微言大义。
(客曰:)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无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所无,未可。
[校] “非指者天下无物”原作“非指者天下而物”。王献唐、伍非百、庞朴读作“非指者天下”,兹从谭戒甫《发微》将“天下”属读下句。“而”字,从俞樾《诸子平议》改为“无”。陈柱《公孙龙子集解》曰:“‘而’字当为‘之’,之误。”也是一种可以参考的解释。
[释]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命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第二,“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第一句话“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乃是问客承接论主提出的问题而发。既然“物莫非指,而指非指”,那么反过来说,“物”必须借助于“指”而呈现于我们的感觉或观念之中;然而,“指”所“指谓”、“指明”的“物”不过是“指而谓之”而已,也可以说“物”即是“所指(之物)”。但是,“所指(之物)”并非“(自在之)物本身”。这样,“指”的对象(所指)有二:一是“所指(之物)”,即“所(指)谓”,也就是“指谓”(二者可以等同)范围内的“所指”,而“物(本身)”的本体不可知;二是“所指”的“物(本身)”,与“所指谓之物”未必吻合。如此一来,则“指(指谓)”就不是“所指的‘物本身’”,故曰“指非指”。可见,“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是对“物莫非指”命题的发挥与引申,因为“无指则物无可谓,无物则指无所缘”(18)。
次句“非指者”一语是“指非指”的概括性说法。举凡篇中的“者”多含有指代一种说法、一个命题的意思。在承接论主(代表公孙龙的思想)提出的“物莫非指”命题的前提下,问客设难说:“(指)非指者,天下无物,可谓指乎?”其实这是“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的相对之论。就是说,既然“没有指(谓)”就没有“所指(谓)的物”;那么相反,从“指非指”命题出发,如果没有天下的物(注意问客并不清楚“指谓的物”与“客观自在的物”的分别),“指”(谓)还能成其为“指”(谓)吗?显然,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没有“物”的话,“指谓”将无所依托。但是,公孙龙子与〈指物论〉企图阐明的观点正是:“指非指”意味着“所指(谓)的东西”(所指、所谓之物)并不就是“物之为物的物本身”。可见,〈指物论〉中的“物”具有两重含义:“指而谓之”意义上的“物”和自在之物(物本身)意义上的“物”,前者依于“指”而后者却是公孙龙子拒绝承认的、隐匿于“物形”之中或悬在“物形”之外的“物的本体”。显然,问客未能明了其中的歧义,故而提出疑问。
(主曰:)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校]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八字,沈有鼎认为是衍文,因为它既与上句矛盾又见于下文。(19)伍非百则于“莫”下补缀一“非”字,改成“物莫非非指也”,原因也是“义与上牾”,疑脱一“非”字。可参。
[释] 论主正面阐述说,“天下无指(指之所指的物的实体)”,那么自在之物或者本体意义上的“物”就不可以指谓,因为指谓一种不可指谓(亦即不可视听)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
(主曰:)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释] 针对客难,论主答辩说,“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这一说法的根据,不在于“非指”(即“指非指”命题),他论证了“物莫非指”这一命题(“者”)等同于“指非指”命题。〈指物论〉反复阐明的观点是:“物”之不可以指谓(“谓指”,以“指”来“谓”之)的原因在于,“物”仅仅是感觉中的“物”,同时也只是“指而谓之”的“物”,至于物表(例如形色)之下、之上的“物本身”是不可知的,因而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在“所指(谓)之物”之外;同时,人们所知的“物”,却又是(可以)指谓的东西。〈指物论〉论证过程中的繁复、甚至矛盾大都出于这一点。
(客曰:)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20)不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
[释] 问客还是“钻牛角尖”,对“天下无指者”这一问题紧追不舍。这里所说的“天下无指者”,指的是上面所讨论的那些相关问题。什么是“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伍非百解释说:“譬如言‘冰’,非谓冷也。又如言‘火’,非谓热也。言有‘马’者,非谓黄、骊。言此‘石’者,非谓坚、白。”这暗示了“名”与“谓(指)”的区别。至于“指”,俞樾云:“指,谓指目之也。见牛而指目之曰牛,见马而指目之曰马,此所谓物莫非指也。”(21)谭戒甫则认为:“其指目牛马之指,谓也;因而所指目牛马之形色性亦曰指,名也。”(22)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指物论〉所说的“指”的确包含了不少歧义,既有“指而谓之”的“指”,亦有近于“名”(概念)的“所指”。但〈指物论〉之所以启用了“指”的概念,主要旨趣仍在于否定、取缔“名”。
问客所说的“天下无指者”,就是上文所言“物不可谓指”的意思。而“物不可谓指”的原因是:物都有各自的“名”,而“名”不同于“指”,所以说“不为指”。如此,“物”就兼有“指”与“非指”两义,这就是说,“物之一方面为指,一方面为非指,一物而兼有‘为指’与‘不为指’两面,于义似相矛盾,故曰未可”(23)。显而易见,在问客看来,论主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略加分析,就会得出将“指”(无不为指)等同于“非指”(不为指)这样一种在经验上是荒谬的结论。
主、客双方的基本区别在于:问客从常识观念出发,认为物各有名(如马有马之名),而“名”(如马的概念)不同于“指而谓之”的“指”(即指着马呼之为马)。既然如此,他的看法与“论主”(代表了公孙龙子思想)恰恰相反,因为问客以为“马”之“名”意味着必定有一个抽象的“马”(概念中的“马”),而“论主”则不以为然。
(主:)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
[校] “且指者”的“且”也许是“曰”字的讹误。
[释] 〈指物论〉中的答问有时显得驴头不对马嘴,因为论主提出的命题和观点,在问客看来不免多是经验上荒谬的东西。自兹而至终篇,论主长篇大论,多方面反复阐述了起初提出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命题。
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
[校] “与”,伍非百训“于”;谭戒甫训“对”。(24)
[释] 这段话比较曲折难解,但主旨还是清楚的:对于“物”的“指”来说,其意义是“指谓”,它所指的是物的形色而已,绝不能深入“物之为物”的存在本身(Being),故曰“非指”。这样的话,“指”不离“物”;同时,所谓“物”者,其实都是所“指”(指而谓之)之“物”。(25)
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指?天下无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
[校] “使天下无物指”中的“指”,疑衍(伍非百说)。
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
[校] 原文作“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依伍非百说,补一“非”字。
[释] 指,兼有“指”与“非指”两面,一方面为“指”,另一方面为“非指”。(26)“指非指”命题直接挑战了诸子蜂起时热衷讨论的名实问题。儒家“正名”的一个主要思想就是“名”副其“实”,而〈指物论〉却一方面挖空了“实”(只余下物表),另一方面又显现出否定“名”的思想倾向。总之,〈指物论〉提出的“指非指”命题表明了“指谓”(或名言)不能达到物象之后的本体,因此“名”的意义也颇值得怀疑,因为二者都游离于纯粹感觉之外。〈指物论〉之所以提出如此极端化的理论,无他,根本原因仍是《公孙龙子》中“一以贯之”的感觉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而这种感觉主义的独特性正在于它是由抽象名辩的形式“包装”起来的。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感觉主义乃公孙龙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与特征,同时还可以把公孙龙子的感觉主义名理学抽绎为两个方面:第一,“唯形(色)无实”原则;第二,“唯(指)谓非名”原则。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个原则乃是公孙龙子思想的基本内容,亦是他的哲学基础和理论预设。
所谓“唯形无实”,简单地说,就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就在于它们的“形”,万物除了“(物)形”之外空无所有,在它们之上、之后没有什么抽象的或“形而上”的所谓“本体”。公孙龙子所说的“形”,包括形状(外形)、色相、坚柔之性等,这些属性与人的感官的感觉能力有关;实际上,公孙龙子所说的“形”对应着人的感官的感觉能力,如:形状对应着眼的视觉,色相(黑白)对应着眼的色觉,坚柔之性对应着手的触觉。反过来说,公孙龙子认为万物乃是我们感觉中的万物,我们依靠感觉可以完整地了解事物本身。人对万物的“知识”,或者说关于万物的“知”,其实就是“感知”(感官之知),而且仅仅限于“感知”。因为物的“属性”(即属于物的东西)对应着人的感觉终端,才是人所能真正了解的东西。
我们知道,“有形有名”是诸子哲学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27)当然,这也是(白马论)的理论出发点之一。所谓“有形有名”,就是说有形的东西是有名的东西,也就是说有形的东西是可以名言或名状的。依此,公孙龙子认为有形之物是可“名”的。不过,对于所谓的“名”,公孙龙子却自有他自己的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名”(如儒、墨所说),较为抽象,因为“名”相对地脱离了物形。而在公孙龙子看来,对“物”的“名”既然可以看做是对“物”的认识,那它当然就不能脱离“物形”,不能脱离人对它的感知。那么“物”的“名”对应着怎样的感觉能力呢?显然,这种感官感觉能力就是人的语言能力。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阐明的那样,〈指物论〉根据感觉主义思想逻辑的要求,拈出了一个“谓”取代“名”,颠覆“名”。这就涉及了〈指物论〉中反复揭明的“唯谓非名”原则。当然,“唯形无实”和“唯谓非名”原则之间自然能够“曲径通幽”。
《墨辩》批判公孙龙子的思想时,提到了公孙龙子的两个观点,就是“唯谓”和“非名”。〈指物论〉集中体现了“唯谓非名”的主张。〈指物论〉提出的“唯谓非名”原则,出于对“名”(概念)的深刻质疑,否弃“名”而代之以“指而谓之”的“指”(28),毕竟“指”比“名”更能吻合感觉主义的思想逻辑。庞朴指出:“它(唯谓非名)实际上是用‘谓’来代替了‘名’,从而取消了‘名’。”(29)是也。所以说,“唯谓非名”原则也是公孙龙子的感觉主义针对理性主义哲学原则的诘难与反动。儒家虽然没有充分地讨论过知识和认识的问题,但有证据表明儒家所说的“名”(即建立在亲亲尊尊基础之上的礼法制度)与“智”或“心”有关。孟子、荀子都认为“心”是思的器官,高于诸感官的感觉。墨家注重经验,主张“知,接也”(《墨经·经上》);同时,墨家强调“心”和“智”的重要性。相反,公孙龙子却有否认“心智”作用的倾向(例如他否定“神”),因为他只承认感官的感知。在儒、墨两家(甚至包括道家)看来,关于“名”的认识,其实是抽象的认识,它来自经验,但却并不一定要诉诸感官的感知,当然更不能归结于感官的感知。公孙龙的看法与众不同,他坚持认为关于“名”的认识归根结底是感官的感知。所以,他否认通常意义上的“名”,并且将这种“名”替换成“谓”,更有甚者,他还把“谓”归结为“指”。公孙龙子的“指”、“谓”,都是对“物”的称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物形”的称呼;因为“物形”的下面或背后没有“使物成其为物的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名”并不能表征什么,它无可标明。另一方面,“名”对应于“心”,也就是说,对“名”的认识和把握依赖于“心”的功能(如“神”),而在公孙龙子看来,“心”却不是感官,那么“心”对外物的认识也不是“感官的感知”。因为“心”无所依托,无所依归,所以它是虚枉不实的东西。换句话说,公孙龙子只承认感官(手指、口舌)所能“名”(标明事物)的“名”,也就是“谓”和“指”;却对“心”、“思想”所能把握的“名”(概念)不以为然。这便是“唯谓非名”的主要含义。
就是说,儒、墨两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做出了旨在克服认识论上的感觉主义、维护经验知识的常识观念中的感觉统一性的努力,他们都强调以理性(“心”)控驭感官(“耳目”)。荀子提出“心有征知”,子思佚说“君子以心导耳目,小人以耳目导心”,孟子阐论“心之官则思”,《墨经》在承认“知者,接也”的前提下,同时强调了“知而不以五路”的观点,这些看法都是从不同方面阐述以心或寓于心的知性(包括人文理性)主导、驾驭感官、感性的思想。(30)道家则从另外的方向上否定了感性知识,那就是直接否弃了感性知识把握道的真理的可能性,而道家著作中常见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以及“不以目见,不以耳闻”正表明了这一点。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公孙龙子所谓的“物”其实就是感觉中的“物”,也就是“指”、“谓”所标明的“物”(仅仅触及了表面的物之形色而已);在“指”或“谓”之外没有“物”的存在,更没有游离于“指谓”之外的、所谓的“物之所以为物”的东西(例如本体)。究其实,《公孙龙子·指物论》只承认有“物”(或物形),否认有“物”的本体;只承认能感知“物(形)”的感觉,否认“心”、“思想”(包括“神”)对事物的把握。
总之,“唯形无实”、“唯谓非名”这两个原则是《公孙龙子》“一以贯之”的立场和观点。对于《公孙龙子》来说,这两个原则是根本性、支配性原则,按诸《公孙龙子》的主要篇什,可以确认感觉主义名理学就是《公孙龙子》主要内容的基本特征。《公孙龙子》确立了“唯感觉论”的原则,质疑甚至排除了所谓的“物的本质”或“物的本体”,因为它们终究处于人的直接经验(即时感觉)之外,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诸子时期关于名理的讨论。尽管“坚白相离”、“白马非马”、“万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诸命题不能见容于常识观念,但他提出的问题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至少我们可以说,《公孙龙子》是诸子时代“正名”思潮中独存孤迥的“一家之言”。儒家标榜“正名”,焦点仍在政治社会方面“礼崩乐坏”引发的“名实散乱”;墨家造作《辩经》,可以说是沉湎于逻辑上的兴趣;道家高唱“无名”,目的在于阐明形而上的“道的真理”,并借以批判儒家企图以仁义宰制人心;邓析、商鞅、韩非、申不害以来的刑名理论,讲究法律意义上的“循名责实”、“参伍之验”(31),或者相反的“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列子·力命》对邓析的描述),其实是政治理念、制度更张的思想形式。而公孙龙子往而不返地推进一种本质上原始而朴素的感觉主义,并赋予了这种感觉主义以独特的名理形式,既深奥又曲折。实际上,古代哲学家很难正面回应公孙龙子提出的理论诘难,因为很好地从理论上解决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毕竟还不具备条件;而我们知道古代的“芝诺悖论”也不易解决,直到晚近仍在探讨。然而《公孙龙子》哲学思想的“另类性格”,引发了诸子百家的如潮批评;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公孙龙子》的“荒诞说法”多少刺激了诸子百家思想的深化发展。我们不妨从公孙龙子与其他诸子百家(特别是道、墨和杨朱学派)之间的理论切磋关系当中,进行稍深入一点的讨论,以期更准确地把握他们各自的思想特点。
班固《汉志》列公孙龙子于“名家”,认为“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长于“正名”,却流于“苟钩鈲析乱而已”。班固“诸子出于王官论”不十分可靠,他暗示包括公孙龙子在内的“名家”与孔子“正名”间的联系同样也不那么可靠。《荀子》曾批评惠施、邓析“乱名析辞”,却没有提到公孙龙(《荀子·正名》)。杨倞却认为《荀子·正名》正是针对公孙龙、惠施之徒“乱名改作,以是为非”而撰写的,他还说,公孙龙“白马非马”命题“惑于形色之名而乱白马之实也”(《荀子·正名》注)。这也许就是儒家学者对公孙龙子比较内行的批评吧。比较起来,公孙龙子和道家、墨家间的理论关系也许更深入、更引人瞩目。自晋人鲁胜《墨辩注序》以来,认为公孙龙子出于墨家的说法,几乎代不绝人,近人胡适亦附益其说。注意到道家与名家(特别是惠施、公孙龙)之间关系的人就更多了,甚至江瑔《读子卮言》还认为公孙龙出于道家(32),蒙文通还认为道家思想取资于名家(33)。我们认为,公孙龙既不是出于墨家,也不是出于道家,反之亦然;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甚至无视公孙龙子和道、墨间的思想关联,不过这仅仅是思想关联而已。另外,我们也认为,公孙龙和杨朱亦不无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典型的唯感觉论者,虽然他们的遗说当中找不到可资相互印证的“同心之言”。下面我们分别讨论公孙龙与墨家(主要是〈墨辩〉)、道家(主要是《庄子》)、杨朱(主要依据《列子·杨朱》篇等)之间的理论关系。
(1)〈墨经〉针对《公孙龙子》的若干主要观点进行了分析和驳正,主要涉及〈坚白论〉、〈白马论〉、〈指物论〉和〈通变论〉的具体内容。例如它对〈坚白论〉提出的“坚白盈离”及其相关的知识论问题——例如“知”是否仅仅是依于感官——展开了比较详细的讨论。〈指物论〉中的一些问题,也受到了后期墨辩学者的重视。比如〈经下〉明确地说:“坚白不相外也”,“必相盈也”。〈经说〉解释说:“坚:于石,无所往而不得,得二。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34)很显然,〈墨经〉企图维护一种常识观念,毕竟“坚白离”是反常识的。前面我们简单讨论过〈坚白论〉中“神与不知”的观点,这一观点从实质上否定了理性对感性的统摄功能,从而坚持了感觉的绝对优先性。〈墨经〉当然不能对这种观点听之任之,它批评说:
于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经上〉)
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举,重。则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举也,是一。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则“是智”之“是不智”也,恶得为一?而谓“有智焉,有不智焉”。(〈经说上〉)(35)
这段话的针对性很强,因为〈坚白论〉曾说:“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而我们知道,“坚”、“白”不得同时存在的原因就是〈坚白论〉强调的独立感觉的绝对性。至于〈经说下〉中的一条讨论了“见与不见离,一二不相盈”的问题,应该也是对〈坚白论〉的批判。
〈指物论〉的“指”究竟是什么意思,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主要就是“指而谓之”;〈经说下〉中的一条材料恰好说明了这一点:“或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指是‘霍也’,是以实示人也。”(36)这里,“以实示人”就是“指”,与“以名示人”的“名”迥然不同,这一点十分关键。〈墨经〉中更有两条材料指出并论证了“指而谓之”在知识论上的局限性:
所知而弗能指。说在春也、逃臣、狗犬、贵者。(〈经下〉)
所:春也其执(37),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处。狗犬不智其名也。遗者巧弗能两也。(〈经说下〉)
有指于二而不可逃。(〈经下〉)
有:指,若智之;则当指之智告我,则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参直之也。若曰:“必独指吾所举,毋举吾所不举!”则者固不能独指,所欲指不传,意若未校。(〈经说下〉)
〈墨经〉的观点十分明确:所知的是物,能知而能指的是心。固然〈墨经〉的思想更吻合经验或常识观念,但〈指物论〉立论的基础却是:如果我们不能直接目击并“指而谓之”的话,就只能通过概念(“名”)来把握事物。〈指物论〉拒绝诉诸“名”来把握事物,因为诉诸“名”和“心”毕竟预设了“物的本质或本体”这一理论基础。而我们知道,《公孙龙子》倾向于否定“物的本体”,只承认“物的形色”。总之,如果说后期墨家主张“名以举实”的话(〈小取〉),(指物论)则主张“指非指”。
(2)《庄子》中的公孙龙形象滑稽而可笑(《庄子·秋水》篇),《庄子》对公孙龙思想的评说也比较负面:“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庄子·胠箧》)这些都是《庄子》对公孙龙子的一般看法,而〈齐物论〉、〈天道〉两篇则“入室操戈”,从理论层面批判了公孙龙子,特别是〈指物〉、〈白马〉两论中的思想。〈齐物论〉曰: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
指马之喻,旧注采详。陈碧虚引《公孙龙子》〈指物〉〈白马〉注《庄》,已经意识到了道家(名学)思想与名家公孙龙学说间的关系问题。(38)章太炎《齐物论释》援引佛说解《庄》,以所指(境)、能指(识)诠释〈指物论〉中的“指”,亦有所创获。伍非百《齐物论新义》也从道、名家的理论关系上予以详细分析。森秀树也注意到〈齐物论〉中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论说,以及用“名家”理论作为“跳板”而超越之的气魄和趣向。(39)〈齐物论〉所说的两句话旨在攻讦辩者“名学”的内在缺陷,从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破斥辩者之说。显然,“指之非指”出于《公孙龙子·指物论》的核心命题“物莫非指,而指非指”,“马之非马”则概括了〈白马论〉的核心命题“白马非马”。《公孙龙子》的这两个命题,不仅反常识,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直接提示并挑战了旧的(或说传统的)形名理论,即有形(实)必有名、有名必有形(实)的理论。《公孙龙子》的“指非指”的理论意味是:“指谓”(第一个“指”,即“指而谓之”)并不就是所指的物(对应概念所把握的物的本体),因此它说明了“名”与“形”或者“指”与“实”之间的分离。如果说“有形有名”是道家“名学”的出发点的话(40),《公孙龙子》则从感觉主义角度揭示了这种观念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危机。道家哲学理论展开的关键步骤就是如何超过“有形有名”而趋向“无形无名”,所以道家超越形名(物论)的方式就是“彼是莫得其偶”而“得其环中”;换言之,就是从“道”的高度,以“无形”(“非马”)和“无名”(“非指”)说明“形”(比如“马”)和“名”(比如“指”),说明形名理论(如形名相偶)的内在矛盾和理论困境。显而易见,道家的旨趣与《公孙龙子》迥然不同。据此,我们认为“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两句话可以解释为:通过“名”(“指”)阐明“名”(“指”)与“形”(所指,即上句第三个“指”)不能相互匹配而相偶,或者说“名”“实”不能相符,不如直接用“无名”(“非指”)来阐明形名的局限性,况且这样的解释恰恰与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庄子》所说“形形者不形”若合符节!后一句话则意味着:通过“白马非马”揭示“形”(以及感觉)的割裂,并由此阐明“名”的割裂,不如直接掠过拘守于形名的各种关于物的理论,以“无形”(“非马”)论证“(白)马非马”。因为“指非指”和“(白)马非马”仍然拘囿于物,也就是说泥于形名,所以,在《庄子》看来,〈指物〉、〈白马〉诸论皆未谛。从无形无名的视野看,有形有名的物并无什么分别,更无由拘执于知、言、形、名的分别;所以道家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庄子·天道》),“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这种说法显然旨在超越《公孙龙子》。
(3)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杨朱和公孙龙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庄子》曾把杨朱和公孙龙归为一类而加以批判,是不是暗示了什么呢?更何况杨朱亦有自己的“名学”,胡适还认为杨朱的“名学”也是一种“无名主义”,很容易和道家(老庄)混淆。例如杨朱说:“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名乃苦其身,焦其心”,“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列子·杨朱》篇)。从表面上看,杨朱上述论调接近《老子》“名与身孰亲”和《庄子》“名者实之宾”(《列子·杨朱》篇确曾引述了这句话),但是“他所谓名即物,所谓实即生”(41),因此他完全把“名誉先后,性命多少”抛诸脑后,与道家“无名”理论所包含的心灵境界的超越和精神性命的修养内容相去甚远,不能不察。可见,《列子·杨朱》篇所载的杨朱遗说表明了杨朱的主要思想是一种“从心所动,不违自然所好”、“从性而游,不逆万物之所好”的享乐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就是一种感觉主义伦理学。(42)这样看来,公孙龙和杨朱刚好代表了古代哲学中感觉主义的两个方面:《公孙龙子》代表了一种知识论上的感觉主义,而杨朱则代表了伦理学上的感觉主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真可谓无独有偶,相映成趣。
注释:
①庞朴:《公孙龙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页。
②王琯:《公孙龙子悬解》,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陈柱:《公孙龙子集解》(〈指物论〉部分),载王琯《悬解》第53-55页;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沈有鼎:《〈指物论〉句解》,载《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伍非百:《公孙龙子发微》,载《中国古名家言》第499-6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庞朴:《公孙龙子研究》;杨俊光:《〈公孙龙子〉蠡测》,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许抗生:《先秦名家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沈有鼎:《沈有鼎集》,第215、255-2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④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第57-58页。
⑤此句原作:“且犹白以目以火见”,孙诒让引《墨子·经说下》:“白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加以校正(《札迻》卷六),兹从之。
⑥按〈坚白论〉的一般说法是“白以目见”而“坚以手知”,那么我们根据上下文,不妨将原文“坚以手而手以捶”的“手”、“捶”两字之下酌补一“知”字,以完文意。第二句原作“是捶与手知而不知”,末三字“而不知”疑即衍文,芟之。另外,玩味末句的“神乎”,可能是反问句式。
⑦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第56页。
⑧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载《沈有鼎文集》,第306页。
⑨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第85页。
⑩详见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05-110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57、262-263页;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5-109页。
(12)冯友兰先生曾将“至不绝”改为“物不尽”,恐非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第273页)
(13)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520-523页。
(14)谭戒甫:〈前言〉,《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第3页。
(15)杨俊光引《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惠施、公孙龙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16)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513页。
(17)沈有鼎:《现行〈公孙龙子〉六篇的时代和作者考》,载《沈有鼎集》,第245-268页。
(18)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524页。
(19)沈有鼎:《沈有鼎文集》,第265页。
(20)“兼”,俞樾改为“无”,庞朴从之。非是。
(21)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第18页。
(22)同上。
(23)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528页。
(24)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第23页。
(25)亦可以参考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529页。
(26)亦可以参考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530页。
(27)详见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第2章;以及郑开:〈道家“名学”钩沉〉,载《哲学门》第1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8)我们这里根据〈指物论〉提炼出来的“唯谓非名”原则,殊不同伍非百曾提及的“唯(应)谓无名”(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第510-517页)。
(29)庞朴:《公孙龙子研究》,第92页。
(30)荀子〈正名〉:“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案“天官”,俞樾以为当作“五官”)子思佚说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子思子)。这里所说的“心”不同于“心知”的“心”,也就是说,知性所居的“心”不同于神(明)所居的“心”(“无心之心”);“接”则意味着“神应”,而不是那种“知接”(如《吕览·知接》),也不是那种“官接”,这里的“接”正是道家所常言之“神明接而万物生”的意思。《玉函山房辑佚书·子思子》,《说苑》卷16,132条:“圣人以心导耳目,小人以耳目导心。”《孔子家语·好生》:“孔子谓子路曰:君子以心导耳目,立义以为勇;小人以耳目导心,不慈以为勇。”《墨子》云:“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经下》)“以五路知(下心)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经说下》)
(31)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评论“名家”时说他们能够“控名责实,参伍不失”,而“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更多地与法家讨论的“刑名”有关。
(32)详见王琯:《读公孙龙子叙录》,《公孙龙子悬解》,第14-15页。
(33)蒙文通:〈论学杂语〉,《蒙文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13页。
(34)“坚:于石”句中的“坚”原错置于“得二”两字之下,兹据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0页)改;“石”原误作“尺”,从孙诒让《札迻》(卷六)校改。
(35)关于这条材料的文字校订,请参考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第146-147页。
(36)句中的“示”,原均作“视”,与“示”通,兹从沈有鼎说校正。详见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载《沈有鼎文集》,第316页。
(37)“执”,沈有鼎校订为“死”;“春”乃是人名(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第317页)。下文的“臣”即臣仆的意思。
(38)陈景元说:“‘指马’之义,自司马彪、向秀、郭象至有唐名士,皆谓漆园寓言构意而成斯喻,遂使解疏者指归不同。今按《公孙龙》六篇,内有〈白马〉、〈指物〉二论,乃知漆园稽考述作有自来也,故备录二论附《章句余事》之后,以示将来云。”(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895页)
(39)森秀树:〈道家与名家之间〉,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40)详见郑开:〈道家“名学”钩沉〉。
(41)王博:〈论杨朱之学〉,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5辑。
(42)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第219-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