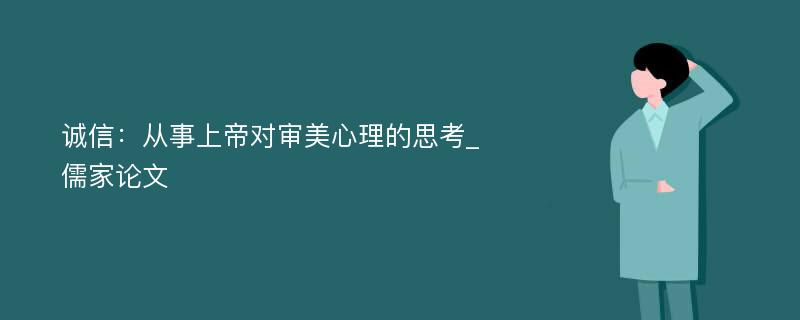
诚:从事神心态到审美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4)02-0203-07
“在儒家所塑造的学术传统中,美学、伦理学和讲天人相遇的超越的神学、形而上学,是一气贯穿的”[1](第139页)。这种相通集中体现在诚这个范畴上。诚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兼具有神学、伦理学、美学、本体论等多重含义。在先秦儒家美学中,作为审美心态的诚是对事神心态、事人心态(其核心是道德之诚)的批判继承的结果,而在审美取代宗教之后,审美之诚又充当了通往本体之诚必经之途。本体之诚与心态之诚的这种统一,正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鲜明体现。
一、作为事神心态的诚
从历史的发展看,诚首先是一个宗教神学范畴,诚是原始宗教活动中诚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在巫术和原始宗教中,人们对神的存在的深信不疑。这是“诚”这一概念出现的基础,它构成了“诚”的发展中的始终一贯的一个本质规定:在人面对任何一个他希望与之打交道的对象之时,他都应该相信对方的真实性,并以此来展示出一个真实的自我。这既是人神交往的原则,也是人际交往的原则,更是审美的原则。无论诚后来怎么发展,它都没有离开宗教性的诚这个基础。
作为事神心态的诚具有三个突出内容:敬(注: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除个别外均将敬释为“严肃认真”,似乎不妥。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畏和信。
我们可以通过对祭祀的考察来了解原始宗教中人的心态。祭祀心态的突出特点是“敬”。“尔克敬,天惟畀矜迩;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2](第220-221页)。对神的敬的态度,是沟通神和人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世间一切事业成功的根源。对上天不敬被看做是失败的原因,是失德的具体表现,也给了政敌最好的攻击理由,这在“文武革命”中再清楚不过:“今商王受不敬上天,降灾下民”[2](第180页)。“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2](第182页)。商纣不敬神灵,导致天怒人怨,从而不能再承担伟大的天命,故有德者要起而代之。
在“敬”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原始的事神心态:畏。夏商周三代对鬼神态度的一致之处是对鬼神的尊敬和疏远,疏远就是“畏”的表现。只有畏才会敬而远之,无畏则能敬而亲近之。“畏”在自然神信仰的原始时期,表现更为明显。因为自然界被神化为一个对人类的目的根本不关心的对象,它表现法力的多数场合对人类而言都是一种灾难,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恶”的代表。因此原始人对自然神有一种强烈的畏惧情绪。以后随着在自然神的社会化,神的人性人情成份日益增多,畏的成份也就逐渐减少了。
信的基本含义是相信,对神的存在没有怀疑,而且对神应该真实无欺。信不是神之存在的条件,神在个体存在之前便已存在,但信却是神存在于个体心灵的必要条件,只有信才能使神在个体心灵生成,只有信才能敬。“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3](第1603页)。
“信”的具体要求有四:其一,事神者不能对神抱任何欲望:“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3](第1610页)。有求于神才去信神者的心态是不“信”的,其行为注定不能取信于神。这一点对于以后的审美心态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审美心态的突出特点也是无欲的。其二,作为信仰对象的神不能随便更改。对至上神尤其应遵守此条,否则“非其鬼而祭之,谄也”[3](第2643页)。对业已选定的至上神系统之外的其他至上神的信仰,意味着对这个至上神的不信任和对其法力的怀疑,这就是不诚不信。其三,在事神的礼拜活动中,要如实申报自己的牺牲贡品,不能随意虚报,这也就是《左传·庄公十年》所载的“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3](第1767页)。其四,祭祀形式要以情感的真实为内容,“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2](第72页)。“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3](第1285页)。祭祀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礼仪,而是其精神实质,即内心的诚实,这种诚实是和情感的真实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真实的情感,再堂皇的礼仪也没有意义。而情感的诚实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其说是一种宗教目的,不如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掩护的道德目的。“祭思敬,丧思哀”[3](第2531页)(《论语·子张》),敬与哀的结合,意味着以情感来保证道德目的的实现。人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发现,宗教的神学目的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个体情感的需要,二是起到社会规范的作用。而将神学目的存而不论,直接从现实的层面来探讨诚的人生意义,是在先秦儒家这里实现的。
二、作为事人心态的诚
先秦儒家揭示了事神心态中的情感内容,并把它扩大到人际关系的调理中,从而使诚不仅是人神关系的准则,而且是人际关系的准则。不仅如此,它还揭示出:在心态的个体生成中,不是事人以事神为基础,而是事神以事人为基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3](第2499页)。事人成为事神的必要条件,这正是儒家区分于神学家之处。
为什么只有处理好人际关系之后才能处理人神间关系呢?在孔子时代,神灵的存在理由已经受到充分怀疑,社会的发展已经引发出信仰危机。要从根本上挽救这种信仰危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时代已远不是原始时代,那个时代巫术和原始宗教的产生是有足够理由的,人们因信仰需要而产生了巫术和原始的宗教。而在孔子时代,这种信仰的需要已经大大降低了,人的主动性、自觉性使得人们不再动辄就去求神保佑其行为的顺利实现,成功的信心不再是靠外在的神灵,而是靠自己,靠道德修养。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人们牢牢地保持对神灵的诚心是不可能的。对于一般人而言,信神之心态由于既缺乏如对自己祖先那样的“慎终追始”的情感动机,又缺乏现实的互惠互利的利益动机,因此是很难生成的。故孔子认为事神比事人更难,关键是事神心态难以出现。因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培养起恰当的事人之心态,这才是现实的态度。
事人之诚包含敬、谦、信、亲等方面内容。
敬、谦与事神之心态有着直接联系,它们可以看作事神心态的世俗化。敬,指对他人的尊敬,与礼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3](第2469页);“所以治礼,敬为大”[3](第1611页)。敬是对事上的要求,“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3](第2518页)。“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3](第2471页)。敬是君子不可须臾离开的素质,它和其他品质一起构成了君子的行为特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3](第2507页);它和恭、惠、义等概念一起被看作是“君子之道”[3](第2474页)。
谦,指对自己的贬抑。贬抑自己是为了抬高他人,以示自己对他人的尊敬。在宗教中谦走了一个极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贬抑自己,而是从根本上否定自己,对信仰者的心理和生理造成压抑甚至损害。而事人之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尊敬他人来赢得他人对自己的尊敬,自谦有时是自信、自尊的表现。周易六十四卦中的“谦”卦对“谦”推崇备至:“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2](第31页)。谦来源于天地人神四者之和,是天人合一的体现,是君子修养到了完成阶段的人格特征。君子愈是谦,其人格光辉就愈明显。儒家之谦是建立在刚强之上的,这与道家之谦有别。谦是君子的立身之本,“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2](第79页)。它既是君子自我完善的手段,“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2](第31页),也是君子以德服人的手段,“劳谦君子,万民服也”[2](第31页)。
信不仅是人神间交流的原则,也是人际交流的原则。信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基本心态,讲信用被看作是成就事业的一个关键,“君子……信以成之”[3](第2518页)。信不仅适应于下对上,“敬事而信”[3](第2457页),也适应于上对下,“上好信,则民莫不敢用情”[3](第2506页)。它是一个人际交往的普遍规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3](第2463页)。人与人之间是通过基本的信用关系来维系的,而这个规则的实现是与信这一心态的形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孔子看来,一个忠信之人走遍天下也不怕,“言忠信,行笃敬,虽蛮夷之邦,行矣”;相反,“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3](第2517页)?这种人在自己的居住地都无立足点。
亲作为事人之诚的一个内容与事神之诚的畏构成了二者间最突出的差别。神作为人的对立面,是人畏的对象,与人保持一种疏远关系,这是事神之诚的突出特点。与对象亲近是事人之诚的突出特点,它有两个立足点,其一是人间普遍存在的亲情。亲情是一种生而知之的心理反应,“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3](第2765页)。“亲”构成了先秦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范畴“仁”的基本内容。“仁之实,事亲是也”[3](第2723页)。仁就是爱人,而爱人的现实表现,是亲近之心态的出现,“爱人不亲,反其仁”[3](第2718页),不出现“亲”的心态,就不能说明仁已经出现。因此对于仁者而言,他所需要的就是有一颗爱心,就是要对他人有亲近之情,而他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也应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亲近之情的产生,亲、爱都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汎爱众,而亲仁”[3](第2458页)。只有以爱心为纽带将众人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才是接近仁的行为。其二是人人平等这一设想。孟子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3](第2749页)。在理性的层面上孟子否定了人的天生的不平等,相反他认为人与人是同类,人皆可以为圣人。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无差等的“亲”的实现。作为缓和矛盾冲突的亲合剂的“亲”的出现一直是开明的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共同心愿,先秦儒家关于家国一体的“礼”治政权的构想正反映了这一心愿。
以亲为内容的道德情感不是如西方人那样的源于原罪意识的内疚感,而是一种人际交流的和谐实现的亲近感、愉悦感,因此这种道德情感要发展为审美情感,可以说是势所必然,这正是事人心态对审美心态的贡献之所在。
三、作为审美心态的诚
审美之诚对事神之诚的历史继承性表现在:二者对自己的对象都信以为真,而且实际上审美和信仰的对象都是自己创造的结果,这是一种对虚幻世界的创造,审美和事神之诚的重要特点就是化无为有,以假为真,而且人们对自己的对象的真实性从来没有怀疑过,只有在冷静的反思中才能知道这个过程的虚幻性。
它们之间的历史否定性表现在:对于审美之诚而言,它并不忌讳自己的对象是自己的创造物这一点,而且它要求审美主体去体验这一过程,品味对象对主体而言的合目的性,只有这样才会因诚而乐。而对于事神之诚而言,它是非常忌讳这一点的,处于事神之诚的人不是无力去体验这一对象的合目的性,就是对这种合目的性有意回避,视而不见,任何有可能产生这种合目的性的想法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对于事神之诚而言,对象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是绝对真实;而对审美之诚而言,对象的真实性是有限的,是明知为假,却信以为真。
审美之诚与事人之诚的历史继承性表现在:二者都与对象有一种亲近感,这正是这二者与事神之诚的最大区别。在审美之诚和事人之诚中,主体与对象之间是一种亲近感,而在事神之诚中主体与对象之间则是一种疏远感,这种疏远感使得宗教活动中的虚幻世界并不能转化为审美王国。
审美之诚与事人之诚的突出区别首先在于:这两种心态产生的对象不同,在事人心态中,它所产生的对象是真实的,而在审美心态中,它所产生的对象实际上是虚幻的,是一个信以为真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事人心态中的谦、敬等内容与审美心态之间还是有差距。审美之诚的最大特点可能在于它满足了人类的“自大”需要。人类之所以需要审美,是因为它需要一种优越感,哪怕要在虚幻世界中实现也行。
“畏”与人的本性相违,但“亲”却与人的本性一致。审美心态所强调的是“亲”,它建基于人与人之间渴望建立一种亲近感,渴望交流沟通这一需要。“亲”是人神间关系通常所缺乏的一个共通性(注:在神的观念的发展后期,神日益被人化,神与人之间也有亲情存在。),也是事神之诚所不具备的一个内容。在和谐的人际交流中,人直接从对方的心身获得对自己的心身的确证,从而获得一种归属感。审美之诚的重要任务就是获得这种归属感。归属感所反映出的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不再是畏,而是亲,是和对象的距离的消失,并获得一种全面的自我确证。亲是事人之诚中的最高要求,而亲又能由事人之心态转化为审美之心态。“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3](第1612页)。在这一过程中,爱人是一个人作为人(而不是一个自然物)而存在的基础,也是一个人成就自身的基础,由爱自己的亲人进而爱一切人,由爱一切人进而爱整个世界,那么就会“乐天”,“乐天”是对天机的洞悟所导致的乐,乐天是成就自身的标志,没有出现乐天这一状态,说明人的主观修养就还没有完善。乐天和知命有着必然联系,乐天知命,才能无忧无惧,这是审美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乐天带有强烈的审美意味。
但是现实的事人心态毕竟不是审美心态,审美心态的重要特点在于它对现实的社会关系具有否定性,它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现实世界。去“畏”与“亲”人是对这个虚幻世界的改造的同一过程,对个体所创造出来的某一虚幻世界去除其“畏”的内容之后,它更能亲近自己。因此审美心态的出现,是对信仰心态和事人心态的综合,它以事人心态之亲去对抗事神心态之畏,使人在与周围世界的交往中确立起自己的优越性。同时,它又以事神心态实际存在着的人与对象之间的合目的性来对抗现实世界中的人与对象之间的功利目的,使得这“周围世界”并不是现实的周围世界,而是一个自己的想象中的“另一世界”。在事人之心态中,已经初步建立起人类的优越感,但对于个人而言,这种优越感还没有生成,或者说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偶然出现。以调整人际关系为目的的礼对人的心灵的压抑,是现实社会个人难以形成优越感的重要原因。因此人们需要一个能够确立其优越感的世界,在这个“乐土”才能找到个人自己的安身之处。这个“乐土”对于实现世界中的人来说,如果他不能超越现实的人际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它就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甚至于在想象中也不可能。而对于能超越现实的功利性的主体而言,这个“乐土”就是想象中的虚幻世界,它是对现实世界的某些方面的否定。审美世界与一般想象世界的区别之处在于它被审美主体信以为真,不只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去处,而且是一个积极的树立起自我的优越性的地方。它的既虚幻又真实的特点使它既与现实拉开了差距,也与一般想象世界拉开了差距。
从信仰之诚到事人之诚,再到审美之诚,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信仰之诚的情感性发展到事人之诚的理智性,这是一个否定。事人之诚虽以亲情为标志,但亲情的背后根源是理智,是人类理性的发展才使事人之诚扬弃了信仰之诚中的畏惧,凸显出事人之诚。在事人之诚中,信仰之诚的神秘色彩不再存在,就是因为理性的觉醒。由事人之诚的理智性再发展到审美之诚的情感性,这又是一次否定。受理智制约的情感在事人之诚中总是被压制、被束缚,不得不以谦、敬等方式表现出来,这是让人比较难受的。理智的进一步发展,不是压制情感的发展,而是给情感的发展以空间,让情理共生共存,和谐为一,于是有审美之诚的出现。这次否定与上次相比,其重点不是理性的片面发展,而是情感地位的提升,使之获得与理性平等对话的地位。从信仰之诚到事人之诚再到审美之诚,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正题:情感(情绪)为主导;反题:理性为主导;合题:情与理的和谐共存。
从另一角度,诚的这个发展路线又可概括为人的本质力量同时发展的两方面:情的发展和理的发展。情和理的同时发展并非必然矛盾的,它们可以在互相认可中齐头并进,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二者的发展速度并不一致,有时是情发展得快一点,有时则是理发展得快一点。从巫官文化发展到礼乐文化,情由情绪发展到情感,理性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理性由原始理性发展到先秦儒家的理性精神,又和理性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情感的认肯和刺激有关,情感对理性的进化起到催化作用。情和理的发展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而这两者共同发展的最后结果,就是审美之诚,它是情和理在较高层面的统一,并且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统一。
审美之诚的突出特点是虚静。
先秦儒家美学对审美之诚的特点的认识,集中体现在认识和发现对象的意义所需的心理准备这一点上。对对象的意义的发现,不是一个被动的感知过程,“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心),则其小者(感官)不能夺也”[3](第2753页)。只有“心”才具有使物透明的能力,物的感性实在只有在“心”中才能被消解,它所蕴藏着的意义才能被所发现。那么怎么样的“心”才能使对象的意义显现出来呢?“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4](第283页)。只有虚壹而静的心态才能破解对象的意义。
虚壹而静包括三个关键词:虚、壹、静。虚,作为对人心的一个规定,意谓无所成见。成见的第一层意思是认识上的先人之见、偏见。成见的第二层意思是欲望,或功利性观念。对第一层意义上的成见的破除,在认识中具有重大意义,而对第二层意义上的成见的破除,在审美上具有关键性作用。我们通常习惯于从功利角度来思考对象的意义,这就使得对象的实用价值之外的其他意义完全被遮蔽了,在有这种成见的主体看来,这个世界的任何对象的存在依据都是它是否具有实用的功利性,整个世界在他眼中就是一个欲望世界,他所寻求的就是这些欲望的实现,这种欲望主体是先秦儒家所坚决反对的。“虚”在审美上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功利性成见消失了。审美之诚以虚为其根本特点,它所实现的只是虚幻的欲望的满足,即在虚幻世界满足欲望,而这种虚幻的欲望,其主要内容是一种自我优越感的确立。
“壹”要求对对象保持一种持久的关注。它不是对对象的浏览,而是长时间注视、倾听某一对象。这个要求欲望主体是不可能做到的,欲望主体所追求的就是更多的欲望对象,在对“丰富多彩”的对象世界的浏览中获得欲望的满足。如果这种满足能够实现的话,那审美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但是欲望主体的欲望根本无法从现实获得满足,于是他需要替代性满足,而这种替代性满足中只有在欲望主体对对象保持一种持久的关注才能实现,因为虚幻的欲望对象只有在专注中才能生成,而在此持久的关注中,欲望主体的欲望也就逐渐忘记了,从而转化为非欲望的审美主体。使自己心志专一的手段是“齐”。“齐”,即斋,斋是从日常的吃斋引申而来的,吃斋与吃荤相比,在感官快感上大大收敛了,对此感官享受的收敛可以扩展为对欲望的压抑,“不齐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君子之齐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3](第1603页)。“交于神明”既是巫术和祭祀的目的,如果将神的人格色彩淡化则它也是审美的目的,事实上“交于神明”的手段往往就是“乐”(yue),而其结果则是“乐”(le),这是精神之乐,而不是感官之乐。“齐”是区分精神之乐与感官之乐的标志。在这段引文中有“齐者不乐”之说,那是否与我们要说明的观点矛盾呢?显然不是,因为这里的“乐”被认为是欲望满足的结果。而欲望之乐是原始宗教和审美所坚决反对的,所以“齐者不乐”。但在今人看来,“乐”并非笼统的欲望的结果,它也可以是一种精神的愉悦。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齐”的话,则“齐”不仅可以是信仰心态的必备准备过程,也是审美心态的准备过程。在宗教中,去欲往往是通过禁欲来实现的,而在审美中,“齐”的程度有所缓和,禁欲淡化为忘欲,精神之乐和齐获得了统一。
静是对欲望之动的否定。经过“齐”之后的主体心态,应该是“心如止水”的,这既是求知的心态,也是审美的心态。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对象的为人存在的意义有所发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3](第1673页)。这里的定、静、安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对欲望之动的禁止的结果。但所谓“虑”并非审美活动,而是概念性的认识活动;而审美活动则是非概念化的,是想象和直观相统一的活动,但作为心态的准备过程,由止欲而定、静、安,既适用于认识,也适用于审美。
“虚壹而静”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欲望的否定,在无欲中统一为“虚静”心态,这在先秦儒家被看做一种获得真知的心态,也是一种能产生审美的心态,它构成了审美的一个必然条件。对对象的真、美的发现,都与虚静这一诚的特殊表现形态密不可分,虚静心态为其后的心理和思维活动的高度活跃准备了条件,就审美而言,是为随后的想象活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从心态之诚到本体之诚
审美心态之诚具有过渡性,它还不是选秦儒家最终追求的目标,它还要推动心态之诚与本体之诚会合,实现主体与本体的统一。《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3](第1633页)。这段话和《孟子》的有关论述相关参照可以清楚见出审美是如何推动心态诚与本体之诚实现天人合一的。
成己,是指君子在修养中获得诚的规定性。“成己”包括两方面来内容:一是从本体论角度,成己是对本体之诚的分有,使自我具有诚的规定性。二是从人生修养的角度,成就自我是使自己获得仁的规定性。“成己,仁也”,仁和人的相通性使得成己就是成人,是人格修养的完善。但“成己”还不是精神运动的终点,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为“成物”。只有成己者才能成物,而且他必须在成物中去成己。成己的标志是心态之诚的生成,这种心态之诚是成物的必要条件。成物是知,它包括两个方面:认识自我和认识对象,而这种两种认识之所以在同一过程中统一,是因为它们都被“诚”所规定了的。
“成己”和“成物”是互为条件的。一方面只有“成己”者才能“成物”,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成物”才能“成己”。二者从来就是不可分离的。“成物”的原因,可从“诚者,物之始终”见出。从时间性来理解,物的前后都是诚。作为物之始的诚,包括两个方面内容:本体之诚,是万物的根源,即物之始;心态之诚,是认识对象、发现对象的意义的先验心理结构,没有它就没有认识、审美的可能性。而作为物之终的诚,是指本体之诚,它是物的发展方向。物最终是要回到这一终极的。“不诚无物”,没有诚就没有物,也有两种理解:没有诚本体就没有物,这是一种神学——本体论的理解,但更现实的理解则是由于没有诚就没有人,而物只有面对人才有价值,故没有人物就不具有意义,“无物”就被理解为物的无意义。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3](第2764页),并不是我创造了万物的自然形态,而是我所赋予了物以意义。物之“诚”在人去发现之前,还只是一个潜能,只有在它被具有“诚”的本质的人所观照之后,其潜能才变成现实。因此物之诚是心态之诚和本体之诚同时赋予它的。
在“成己”与“成物”的统一的过程中,就包含一种审美过程,它既是认识对象与认识自我的统一,也是实现自我之诚与实现本体之诚的统一。由于对象与自我都有诚的本质,成己必须发展成物,成物必须以成己为基础,且成己以成物为标志,故成物也是成己,其中必然渗透着对自我的体认,这种在对象上实现的自我确证,就是对自我之诚这一本质的切身体认。由此必然导致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故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4](第2764页),这种在对象身上发现了自我之诚的快乐,就不再是一种道德之乐,而是一种审美之乐。在此心态之诚以审美为中介实现了的主体与本体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