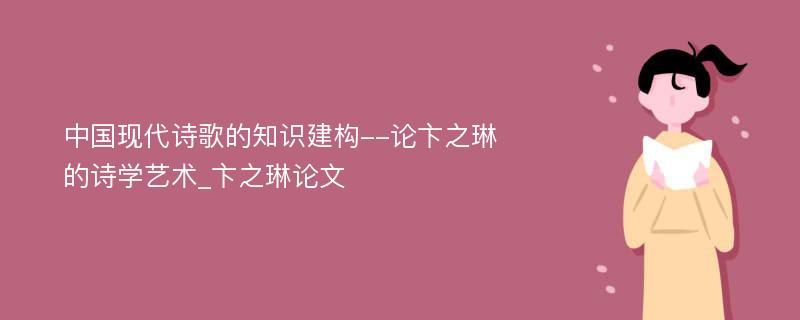
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诗歌论文,现代诗歌论文,艺术论文,卞之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0)04—0554—05
卞之琳出自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营垒,他上承新月派、象征派,下启九叶诗派,具有独特的诗歌史地位。他在创作上融西方现代派技巧与中国古典诗歌神韵于一炉,为中国新诗的成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诗歌不再追求主观抒情效果,而重视诗思的提炼和凝聚,追求诗歌的智性之美。当绝大多数现代诗人仍在主情的道路上滑行时,他却在主知这一新的诗艺途径上艰难而执著地探索,其主知诗即新智慧诗,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这是卞之琳对于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他创造的新智慧诗在现代诗坛上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智慧诗在中国生长的土壤一向贫瘠。古典诗歌奉行抒情言志的传统,注重主观情绪氛围的营造,因而难以承载客观、冷峻、深沉的诗思。加之国人一向重经验主义的感受与顿悟而轻本质主义的观察与思索,所以古代诗人也难有对哲思、智慧的表达,甚至“以理入诗则诗无”的观念相当普通。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理诗传入中国以及思想革命、启蒙意识对文学的影响,诗歌终于在表达哲理方面有所发展。到“五四”时期,理性主义高涨,言理之风盛行,诗歌也被染上了浓厚的智性色彩。特别是小诗派将诗与哲理联姻,抒发人生感悟和对宇宙自然奥妙的探索,对诗歌的智性化倾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小诗也有其自身局限,由于格局小,三言两语所承载的思想意蕴毕竟有限,而且作者常凭刹那间感悟,即兴而成,其哲思的表达往往一闪而过,给人以入境未深之感。因此,以理入诗又遇到危机和挑战。此后,随着现代派诗歌的崛起,中国诗歌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现代派在主情与主知这两个诗艺途径上并行发展,相互推进,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绝大多数诗人都向主情一途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以卞之琳为代表的少数诗人则在主知这一艰难道路上奋力探索,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为中国主知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卞之琳为中国新诗开启了一道智慧之门。在他的诗中,无论是海边一枚小小的“白螺壳”,还是神奇瑰丽的“圆宝盒”;无论是偶尔的一道“风景”,还是“寂寞”的“音尘”,都让人感受到诗的智性之美,体悟到启人心智的力量。他的诗,展示了一位多思者在历史风云摇曳里的孤独和寂寞,更揭示了一位现代人在“寒夜”和“苦雨”的人生“长途”中深重的叹息和深沉的思索。精心磨砺而又客观冷静的诗歌语言,化腐朽为神奇的诗歌意象,都凝聚着他对人的生命本体的追问和对自然、宇宙人生的形上探索。他的诗歌创作有着明显的指向,那就是追求现代诗的深度模式,为诗歌主知开拓一条艺术通道,真正达成中国现代诗的智性建构。他的新智慧诗的成功,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智美和诗意美的诗歌境界,而且证明理智完全可以入诗,而且可以写很好的诗。从此以后,新智慧诗在诗坛理直气壮地存在着,发展着。
综合考察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可以发现其新智慧诗建构的几种主要诗艺途径和方式。
一
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曾说到他写诗常“通过西方的‘戏剧性处境’而作‘戏剧性台词’”,戏剧化是一种客观化的表达方式,“即是设法使意志与情感都得着戏剧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倾向”。戏剧化的诗歌艺术策略在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创作中已有所运用,卞之琳的诗歌更是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艺术倾向。他的许多诗都因戏剧性情境的设置、戏剧性独白与对白的掺入而弱化了主观性的叙述色彩,使诗人的激情得到放逐与规范,呈现出明显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特征。
卞之琳称自己“常用冷淡盖深挚,或者玩笑出辛酸”。他擅长在不动声色的戏剧性图景呈现中表达生命的沉思和人生的体悟。他常以非凡的观察力和感知力,截取生活流程中的某一片段,剪辑成一幅幅静态的蒙太奇画面,尽管画面上没有较大的戏剧性情节冲突,却具有强烈的内在艺术张力。特别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画面,经过诗人戏剧化的艺术处理后,具有启人深思的诗性效果。如《寒夜》一诗,仅呈现了一幅寒夜里的生活图景:一炉火,一屋灯光,老张衔着烟卷,老陈喝着热茶。全诗隐退了诗人自己的声音,只有客观化的戏剧图景的陈列,然而在老张、老陈寒夜里抽烟喝茶、慵懒无聊、昏昏沉沉的生活表象里,却表现出市民阶层的苍凉无奈,庸常麻木的生存状态。再如《苦雨》,完全是照相式的客观扫描,仅将雨中生活琐碎进行如实记录:老王苦雨,连茶馆门都未开;拉洋车的小周,等候在屋檐下;卖烧饼的到处走动,这纯属生活原生状态的呈现,但这种生活细节经过作者客观化处理后,显得意味深长,它传达出小市民被大雨所困的悲哀以及他们在生计维艰的境遇里的多种心态:有的消积屈从;有的仍抱希望;有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句“卖不了什么也得走走”的画外之音,更揭示出市民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坚韧。全诗无一处提到“雨”字,但戏剧性的雨中图景,却让人联想到人生路上处处是风雨的胁迫和威逼。
诗人在客观冷静地描摹市民生活图景,揭示芸芸众生麻木昏沉以及卑微艰辛的生存状态的同时,更注重对生活中富于戏剧性情境的表现,在明显的戏剧冲突和情感艺术张力中揭示心灵深层的运动变化,揭示人生经验里各种矛盾张力和辩证运动过程,使其诗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哲学的沉思,辩证的思想。如《叫卖》一诗,短短几行,但因冲突性的戏剧情境的设置,而拓深了诗歌表现的内蕴。它通过“叫卖”这一特定情境场面,展现了“妈妈”、“小孩”、”“叫卖者”这三个戏剧角色之间的冲突,揭示了希望与失望、自由与限制、主动与被动之间的矛盾关系。叫卖者寄希望于小孩,小孩则求助于妈妈,而妈妈则希望叫卖者不要引诱小孩,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戏剧冲突情境显示了人的生存处境、生存角色的相对性,充满辩证的哲学思想。《道旁》一诗,更是通过道旁戏剧性的一幕,展开对人生命运和人生态度的冷静思考。它以现实生活情境直接入诗,描写了具有内在性格和心态冲突的两个戏剧角色:一个是“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腿”的倦行人,一个是“闲看流水里流云”的树下人。作者抓住他们在道旁问话的这一特定情景,呈示了两种相对的人生态度。倦行人代表不辞辛苦、勇于探索的一类,树下人则是不思进取、麻木度日的一类;倦行人还可看做是忙忙碌碌、疲于奔命的一类,而树下人则是超然脱俗、清静守拙的一类。作者对这两个戏剧性角色未作任何主观评价,只是通过直观生活流的呈现来引发读者的智性分析和思考。
卞之琳的戏剧化途径,更注重戏剧性独白和对白这一手段的运用。如《酸梅汤》通过“我”与卖酸梅汤老头儿,树下睡觉的老李以及某先生的对话,透视市民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光流逝中昏昏沉沉、日渐苍老的无可奈何的感慨。《投》以“我”与“小孩儿”客观的陈述,揭示了生命的偶然性,即人的命运就像随便一投的小石块。在《影子》中,“我”对“你”的倾诉,凸现了生命的寂寞。形影相吊、茕茕孑立,已是极其孤独和寂寞的,然而,“我”却连影子也丢了,这种孤寂也许只有“你”懂,但“你”何尝不寂寞呢,其实也需要“我”的影子陪伴,作者以“我”这个抒情主体与虚设的远在古城的“你”这个倾听者的对话,揭示了生命莫可名状的孤寂。《奈何》通过在黄昏里和一个人的对话,表现一种找不到人生意义与目标,找不到生活出路的精神苦闷,一种无所依傍无所追求的茫然若失感。《鱼化石》以“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的方式阐释了爱情的真谛以及相对观念。总之,作者善于将生活的感悟,人生意义的探寻,哲学的思索隐藏在客观的陈述和对话之中,极力避免主体情感的泛滥,从而使诗变成哲学视界的冷风景。
不管是戏剧性图景的剪辑,还是戏剧性情境的凸现,以及戏剧性独白与对白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诗歌表现的客观化效果,使诗人的激情得到控制与规范,使诗在智性表达上获得艺术的维度与张力。
二
卞之琳的新智慧诗创造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意象凝聚,这也是现代派诗人惯用的艺术手段。正如庞德所言,意象是“理性和感性的复合体”。意象的使用,使主观情绪投射于客观物象,以避免诗人情感的矫揉造作和毫无节制的宣泄,使诗趋向客观化。卞之琳说过,“我偏又喜爱淘冼、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他通过对意象的淘冼、提炼而结晶为饱含哲思的晶体,因此,其诗格局虽小,但内蕴深厚,意味深长。在卞诗中,意象作为哲理与情思的载体,具有较强的象征暗示功能,其诗背后含有“大的哲学”。在意象营构上,卞之琳与戴望舒运用“以我写物、以物化我”的方式,追求情绪的感染力量不同,而是采取“以物写我,化我为物”的方式,将哲思隐藏凝聚在客观对应物上,从而引发人的智性思考。
从卞之琳诗歌意象营造的内容层面来看,可分为三类。一类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常见的意象。如雨、雪、泪、路、流水、月夜、新秋、灯虫、镜、窗等等,这些意象虽取法传统却又能推陈出新,融入现代人的人生经验与感悟。如卞之琳的“泪”(《泪》)这一意象,虽取自李商隐的“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枝”这极浓极艳极悲之诗句,但却另辟蹊径,自创新意,诗人由“泪”想到与圆的切线,空虚的一点,比喻露水姻缘,表现其色空观念。他还提出“人不妨有泪”,这正是现代人的人生感悟和喟叹。再如“雨”、“雪”意象,不管是“丁香空结雨中愁”,还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其中,“雨”、“雪”都是为了烘托一种怅然若失,缠绵悱恻的情绪,而卞之琳在以“雨”、“雪”入诗时,更注重表达现代人的人生体悟。如《雨同我》中“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明朝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以雨喻人生无尽的忧愁。再如《水份》中的“凉雨”、《白螺壳》中“一壶烟雨”、《夜风》中“满城冷雨”,都通过“雨”的象征暗示作用,揭示现代人在各种境遇下的复杂的人生感受和对自然宇宙的认识和思考。
另一类意象则是选取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物象,通过诗人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的点染,使其诗意化。如《记录》中叫卖的晚报,引起人对一天光阴消失的感慨。《一个闲人》里摸着两个小桃核的闲人,令人想起生命的苍白和时光的飞逝。《一个和尚》中的香炉、佛经,是对善男信女的嘲讽,揭示芸芸众生的麻木。《投》由一枚小石头竟联想到了人生命运的偶然和无常。《长途》中那挑夫肩上的扁担,象征“人生长途”。《奈何》中转过了十几圈的空磨,隐喻百无聊奈的人生。《倦》中的烟蒂头,在绿苔地上冒一下蓝烟,象征人生的疲惫感。卞之琳往往在日常生活中选取平淡无奇的意象来表达独特的人生感悟与思索。
还有一类意象取材于现代自然科学,使其诗歌著上了浓厚的智性化色彩。作者对时代生活中新事物、新知识的关注是相当密切敏感的,他开放的眼光,敏捷的思维,对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关注,有利于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把握其本质。新的宇宙空间观念,使诗人不再停留于狭小空间的自我咏叹,而着力于对物质世界的客观实体进行冷静考察和智性思索,“对于事物的本质或精神的了解十分重要,因为离开本质,诗人所得,往往止于描写,顶多也只是照相式的写实,不会引起任何精神上的感染”。因此,他注重对客观事物本质力量的探寻,其诗中许多意象,莫不与此有关。如《水成岩》和《鱼化石》都涉及到了地质学知识,后者由自然界中物质特性联想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泪》中关于圆的切线的比喻,巧妙地利用数学知识来表达对人生思考的理性之美。《航海》通过地理时差现象来揭示多思者与自命不凡者的不同人生心态。《候鸟问题》中“我岂能长如绝望的无线电,空在屋顶上伸着两臂,抓不到想要的远方的音波”,用“无线电”、“音波”等物理学上的概念,将自己对远人急切的渴念倾吐得淋漓尽致。
卞之琳有意识地进行诗歌意象选择的同时,更关注意象的组合方式。意象组合的实质,是依从诗人情绪或意念的线索,按照一定的构思,对其进行有机组接和排列,从而完成诗的整体建构。从卞诗意象组合形式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中心意象型,即一首诗中以一个意象为中心,贯穿其他次意象,中心意象是诗的主脉,其他次意象只起补充的作用。如《群鸦》中的“冷北风里的群鸦”,《鱼化石》中的“鱼化石”,《妆台》中的“妆台”,《西长安街》中的“西长安街”都是贯穿全诗的中心意象。诗中的不少次意象是由中心意象派生出来的,它不仅为了表达丰富中心意象,而且其本身,又有一定的内涵。如《圆宝盒》中的“圆宝盒”是统摄全诗的中心意象,它是“悟”、“道”、“知”的凝聚,象征着“智性之美”。作者将人生层面上的智性之美上升到哲学层面即关于宇宙万物的相对思想:“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息……”,其中“水银”、“灯光”、“雨点”这些次意象揭示了人生的洞察与彻悟、获得与失落、欢乐与痛苦的相对关系,将“圆宝盒”所寓示的“知”与“悟”编织在一张相对关系的网里。诗中“钟表店”比喻现在时光,“骨董铺”暗示陈旧的传统,这两个意象隐喻了获得圆宝盒必备的人生品格,既不能无谓地消耗现在的时光,也不可一味地眷念传统,诗最后“舱里人”与“蓝天”两个意象,象征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只有主客精神的契合,才会有真正的智性之美的获得。诗中一系列的次意象都是围绕中心意象展开的,中心意象在次意象的昭示下,意蕴也更加丰富和深刻。
与中心意象组合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意象型。一首诗中,将丰富的、众多的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意象加以集合,像电影蒙太奇的手法那样进行组接,以表现复杂的情思,这类意象组合方式在卞诗中也很常见。如《傍晚》将三组意象集合在一起,形成三幅画面:1.“夕阳”与“庙墙”构成一幅夕阳残照图景;2.“老汉”和“瘦驴”构成老汉归家图;3.“乌鸦”啼飞图。全诗聚合丰富的意象,剪辑成电影蒙太奇的画面,形成特殊的审美感知效果,让人在这样的背景画面中感受傍晚的孤寂和无奈,体悟生命的枯涩和灵魂的震颤。再如《古镇的梦》,也是将几组意象进行并置组合,形成整体的意象网络结构。“瞎子”、“算命锣”构成一个幽冥的世界;“更夫”、“梆子”则象征尘俗世界;而“桥下的流水”则寓示着光明理想的世界,作者将这些表面上看起来联系不大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却起到特殊的整体效应。在这些群体性意象的象征暗示作用下,20世纪30年代“寻梦者”对中国现实的荒原性感受在本诗中得到了强烈的表现。
卞之琳在凝聚意象,寻找情思的客观对应物时,一方面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面又注重对自然科学文化知识的接纳,有效地进行意象类型的选择,这些多种多样的意象很好地承载了作者的沉思和体悟,使其诗歌饱含无限丰富的意蕴,从而更好地达成了诗歌的智性建构。总之,意象凝聚这一现代诗艺法则,在卞之琳的主知诗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三
卞之琳除了通过戏剧化手段和意象凝聚达到客观化表达效果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营构诗歌意境。卞诗中着意表现境界的作品是不少的,如《一城雨》、《夜雨》、《雨珠》将主人公感情的抒泄与雨景描写相融而成诗的意境。《傍晚》虽客观地描摹了三幅暮色图,但它是通过主人公的视觉、听觉、内心感受投射出来的,其中透出的衰颓冷寂的色调正是主人公抑郁、荒芜心情的反映。这种意境营构方式在传统诗歌中是相当普遍的。卞诗虽然重视对中国古典诗歌意境营构方式的借鉴,但其意境营构方式又与古典诗歌有所不同。古典诗歌追求主体与客体交相融合的诗美境界,其中主体情感的投射相当强烈,即意境中有着浓厚的情绪氛围;而卞之琳在营构意境时,则力求生成思想,传达智慧。古典诗以和谐浑融的意境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和审美的愉悦;而卞诗则让人沉入其中,又能超脱其外,引起人们灵魂深层的颤动与思索。在古典诗歌中,其诗质元素主要是情绪,宛若水的流势或酒的香味,它以音乐的方式由内向外辐射,由我向物洋溢或弥漫,呈现出柔媚轻曼的幻动感。在卞诗中,其诗质元素富于金属性硬度,它也有情绪,但情绪渗透于智性思考与经验传达之中,使诗拥有内在的灵度与强度,仿佛雕塑凝聚的力,诗的情思由外向内,由物向我投射,在深处融为一体,其诗宛如雕刻的结晶的沉思的风景。
从卞之琳的代表作《断章》就可发现卞诗意境营构方式与传统的区别。《断章》是诗人巧妙地化解冯延巳的《蝶恋花》而得。冯诗云:“河畔青鞠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在“新月”、“小桥”烘托的意境里,诗人的别愁情绪得到渲染,其诗以写情为主,除了表现友人别后无法排遣的忧愁之外,再无更幽深的含义。《断章》在此诗基础之上,拓展成意境相联的两幅图画,画中的人物、桥头、楼上、风景、明月以及想象中的梦境,不仅比冯诗显得更丰富多彩,而且在这些景物的状写之中还寄托着一种深刻的哲理思考。自然景物与人物主体构图,达成一种象征暗示境界,传达出作者的哲学沉思:在宇宙与人生中,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而一切事物又是互为关联的,它包蕴着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整体性思考。冯诗意境以传情为主,卞诗则以致思为重,诗人将感情淘洗与升华,结晶为诗的经验,表现了极大的情感的克制,淡化了个人的情感色彩,增添了诗的智性化意味。
卞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意境综合于其它方法之中。他的无题诗表现相当明显,如《无题一》将男女主人公的柔情蜜意与“小水”、“春潮”联系在一起,情与景交相辉映,同时又在叙述与对话中表达溢于景外的欢乐与机智,使得爱情诗的传统意境增添了现代性的叙述意味。把意境综合于其它方法,使其营构的诗歌境界更好地通向客观化的智性表达层面,这也是达成卞诗智性建构的一个重要因素。
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是卞之琳艺术法则的突出表现,通过这些艺术法则的运用,最终使他的诗歌智性因素增强了,从而为中国现代诗歌园地贡献出了一株株新智慧诗的奇葩。应当说,在20世纪30年代新诗人中,卞之琳诗作的智性程度最高。就世界现代诗坛而言,大多数诗歌流派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在突出非理性因素的同时,往往更见出理性的思考,瓦雷里、里尔克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中都包含着哲理思辩的因素,而艾略特的成功,则标志着以《荒原》为代表的智性诗时代的到来。当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刚刚告别早期象征派而进入一个新的探索阶段的时候,卞之琳则在现代派诗歌中另辟蹊径,即在“五四”以来新诗主情传统之外努力于中国新诗的智性建构,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十分自觉地借鉴了西方波特莱尔、艾略特、瓦雷里、叶慈、奥登、阿拉贡等诗人的艺术经验,而且十分注重与自己民族传统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一种新智慧诗。卞之琳的新智慧诗虽然规模还不够大,数量还不够多,甚至有些诗的份量还较轻,有些诗的内蕴过于冷涩费解,但它在整体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经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需要。因为不管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还是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大多数诗人都偏重于颓废、绝望、忧郁、神秘的现代情绪的表达,而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心理变幻的哲理探寻,对于社会现实的冷峻解剖与理智批判,则关注不够,这就使现代派诗歌呈现出虚弱和贫乏、狭窄和单调的状态。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有待于哲学思想及其艺术表现的开拓,而卞之琳则顺应了这种历史的要求,他的新智慧诗给后起的现代派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20世纪40年代诗人对新诗现代化探索突出表现在主智传统的建设上,冯至的《十四行集》和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的创作在感性与智性的交汇中,在官能感觉与抽象观念的艺术整合中,表现出一种沉思的美、智性的美,由此开拓出新诗的崭新境界。应当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多种艺术的激烈竞争中,新智慧诗的生成和发展,不仅为中国新诗拓宽了疆域,而且对于民族灵魂和智慧的塑造,也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可以肯定,中国现代诗的主知传统的建立是与卞之琳的辛勤劳作分不开的。
收稿日期:2000—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