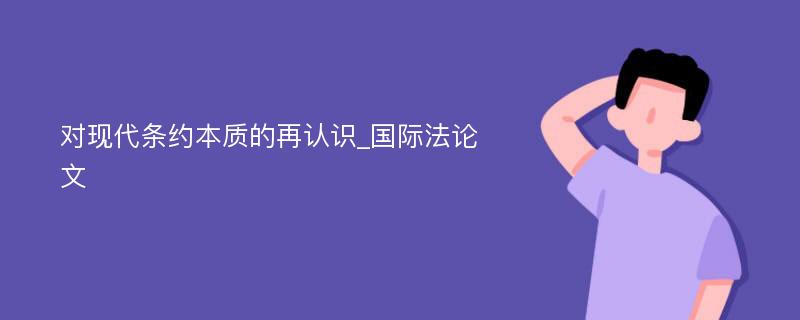
对现代条约本质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条约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多数学者认为条约就是国家之间的契约或合意。《奥本海国际法》对条约所下的定义是,“国际条约是国家间或国家组成的组织间订立的在缔约各方之间创设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契约性协定”①。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条第1项(甲)规定,“条约者,谓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公约》虽没有直接使用契约或合意的字样,但学者们关于该条的学术解释几乎都强调这种协定之“意思表示”或“意思表示一致”的特征。②条约定义借用私法契约的概念,反映或突出了条约的契约本质观点。考察各国国际法学者关于条约的定义,只是在条约主体、形式和定义详略方面有所差异,至于条约本质和定义路径则完全相同,即采用私法契约的定义方法与路径,揭示条约——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合意”或“意思表示一致”的本质。换言之,国际法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条约的本质就是国家之间(包括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际组织相互间)的“合意”或“意思表示一致”,亦即契约。③这种流行的“条约契约说”反映了条约与国家意思之间的密切联系,对条约缔结及其适用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不可否认,这种认识过于粗略,没有注意到国际条约本质发展变化的事实以及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之间细微而重大的区别。其实,条约并不完全都是契约,一部分多边国际条约与国际组织公约应该属于共同行为或决议的范畴。《公约》第9条第2项的规定就已经涉及多边条约多数决的问题。④以私法中法律行为之契约与共同行为或决议理论全面研究条约本质,⑤可以获得关于条约本质更加完整和清晰的认识:条约是国家以“意思表示”和“意思表决”为工具的国家间或国际组织间意思互动的结果。
一、“条约契约说”的成立与局限
著名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认为,“私法上的契约和国际法上的条约,其法律上的性质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契约和条约中,各个当事者的自治的意思,都是一个法律关系的构成的条件,而这个法律关系,从其产生之时起,就独立于当事者一方的自由处理的意思之外。私法上的契约,是由国家的法律赋予客观的效力,而国际条约,是由国际法上的一个基本规则,即条约必须履行的规则,予以客观的效力。”⑥李浩培先生在论述条约定义核心要素“一致的意思表示”时,引用了上述观点,并强调这些“一致的意思表示”必须意在产生、改变或废止在原则上按照国际法的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最终认为“条约是至少两个国际法主体在原则上按照国际法产生、改变或废止相互之间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的一致”。⑦显然,李先生关于条约性质的分析过程包含了丰富的契约思想(意思表示)和元素(权利义务关系等)。《公约》也秉承和贯穿了“条约契约说”理念。如其第9条第1项以及第40条第2项在涉及双边条约和部分多边条约议定、修正的相关规定中皆体现了缔约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契约理念。⑧纵观国际法学者有关条约的定义或成立要件的论述,皆一致地采用了类推私法契约原理的方法。1969年和1986年两个关于条约的《维也纳公约》之框架和方法明显继承了私法契约和契约法的基因。⑨
其实,在主权平等的国际社会里,国家之间的关系犹如市民社会私人之间的关系,地位平等和意思自由是二者共同的要求。所以,意思自治成为平等主体之间利益协调或权利义务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手段。“条约和契约”作为意思自治的基本法律形式,不可能因为国家和私主体(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法律属性和构造不同而产生本质差异。意思自由和意思表示必然是条约与契约共同的核心要素。条约理论对私法契约原理的借鉴不可避免。罗马法滋养现代民法的同时,也孕育了国际法。正如学者们指出的,尽管“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政治关系属于公法范畴,但是,它所适用的原则却完全是私法性质,即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个人’。‘个人’之间关系是平等、自由、独立的。这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特征。可以说,国际政治关系是国际政治化的民事关系。”⑩可见,条约法从罗马法中吸收和借鉴契约原理发展条约理论是人类理性的当然结果,这一点,如同格劳秀斯借用自然法原则论述海洋自由论题一样。“条约契约说”运用私法契约原理理解或解释国际条约而获得的关于条约本质的基本认识,反映了人类理性的共通性和一致性。它抓住了国家在签订条约时“意思自治”这个核心要素,强调条约是国家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11)这种学说或观点,既有利于人们利用对私法契约的“前理解”以接受和认识国际条约,提高利用条约处理国际事务的自觉性,也为“条约必须信守”——这一条约效力来源的客观规则提供了理解和认识的基础。“条约必须信守”在一定意义上是契约是当事人法律的推演和转换,私人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契约效力的认同证成了“条约必须信守”的绝对性和客观性(即不证自明的特点),为早期国际法提供了效力来源规则,大大降低了条约效力的说理成本,提高了条约的强制力和履约效率。
不仅如此,“条约契约说”满足了条约早期发展的现实和需要。从条约的起源来看,早期条约与战后恢复和平有关,主要内容包括缔结同盟和划定疆界。(12)公约前31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拉加什城邦和乌马城邦缔结的条约就是疆界条约。(13)公元前1280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同赫梯王哈土舒尔三世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14)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同盟条约在史书上也屡见不鲜。(15)这些条约以口头协定订立,通过交换各自的书面记载而达成。(16)不仅内容单一,而且都以双边条约的形式缔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15年的维也纳公会止。并且,集体条约出现早期,存在一个由双边条约向多边条约过渡的阶段。即便应当缔结的集体条约也通常由多个双边条约转换而来。如1713年英、法、普、萨、西、荷六国签订的《乌得勒支媾和条约》实际上是由法英、法萨、法普、法荷、西英和西萨六个内容完全相同的双边条约所构成。1814年法、奥、俄、英、普之间缔结的《巴黎媾和条约》,形式上是一个多边条约,实际上也是以四个双边条约的方式所缔结。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集体条约直至1856年缔结的《巴黎条约》才标志最后产生。(17)可见,直到19世纪中叶,国际条约实践还主要是双边条约,甚至在欧洲人的观念里,所有条约都应该是双边的。(18)这样一种条约理念和实践与私法契约行为完全吻合:双方平等主体之间关于产生、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可以推论,关于条约的早期认识本身就是契约理论认识迁移的结果。至此,在理论和实践上条约与契约达到了完美的一致。“条约契约说”适应了条约(主要是双边条约)早期实践和认识的需要,契约原理足以解决条约形式、效力及履行等理论问题,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可,也成为条约理论借鉴私法契约原理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国际社会对诸如环境、人权和反恐等公共利益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多边化和组织化趋势日益加强,不断产生的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互为推力,成为了影响和变革国际法的重要因素。(19)一般或综合性多边条约与国际组织宪章或规约的空前发展为传统条约法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强烈的现实要求。“条约契约说”理论在国际关系复杂化和条约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表现出一些理论上的局限性或困境。主要表现在:
1.对“条约——国家间意思表示一致”的违反。“国家间意思表示一致”是条约成立的核心要素,是“条约契约说”的理论基石,成为现代条约法的基本认识。但是,随着条约多边化、国际社会组织化及国际公共利益的发展,作为建立和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保护和文化交流等国际秩序主要方式的多边条约,其国际法影响和地位大大提升。为了降低条约签订成本,提高签约效率,某些领域和类型的多边条约突破了“国家意思表示一致”的程序和原则,变一致表决为简单或特别多数决,允许缔约国在一定条件下对条约提出保留,(20)甚至一些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条约改变了“一人一权”的计票方式,实现了“加权投票制”。如1944年7月制定的《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须有份额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0%的成员国交存批准书后,协定始发生效力;1948年3月制定的《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公约》,必须有21国批准,而且其中7国须各拥有100万吨以上的船舶总吨位,公约才正式生效。《国际劳工组织条约》是突破传统条约法较为典型的例子,它的各种决议,除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均以简单多数进行表决,经大会主席或国际劳工局长签署后,通知全体会员国批准。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宪章》、《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组织宪章》和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也都有类似的规定。(21)《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对传统条约法的突破较为实质性。其在第54条第12款和第90条中规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有权以2/3多数通过关于民用航空的一些标准,并决定把它们作为公约的附件,通知各缔约国,这种附件或其修正案在通知各缔约国后经过3个月或理事会规定的更长的期间,即发生效力,除非在这一期间内各缔约国过半数向理事会表示其不赞成的意思,这里公约附件的生效既不经过各缔约国的谈判,又无须它们的批准,条约订立的基本步骤所剩无几,各缔约国意思表示一致只体现在它们还保留着过半数的否决权。(22)可见,在多边条约的缔结过程中,特别是国际组织条约或宪章,条约之“国家间意思表示一致”原则的例外获得了较大发展。条约获得通过并不完全是所有缔约国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少数缔约国弃权甚至反对并不影响条约的缔结。
2.对“条约——产生、变更或废除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突破。双边条约是两个缔约国之间产生、变更或废除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定,主要用于解决两个国家或集团之间利益,一缔约国享有的权利是另一缔约国应当承担的义务。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相向性和对等性。多边条约弥补了双边条约不完全适合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调整的不足,更多地关注和协调多个国家之间的共同和整体利益,各缔约国之间的意思表示内容具有同一性,不同国家承担相同或自己接受的一定比例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权利义务关系直接指向条约缔约方整体的利益,而不是缔约方相互之间的个体利益。多边条约的这些特点突破了条约是产生、变更或废除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理念,导致完全用“条约契约说”无法加以解释。在一般情况下,国际组织公约主要是会员国关于国际组织及其机构设立、宗旨、职能以及程序等方面的约定,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等;专门性国际多边条约主要就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贸易、环保、外交等单一主题约定国际社会的共同权利和义务,如1947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这些多边条约并不约定缔约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就某一个主题约定所有缔约国的共同权利和义务。(23)
3.条约效力相对性原理之例外获得了发展。《公约》第34条规定:“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和权利。”条约是缔约国之间的合意,条约的效力只及于条约缔约方,未经第三国同意,不产生约束第三方的效力。但是,这一原则在多边条约中出现了例外。如《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6款规定:“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在涉及争端事项时,《联合国宪章》第32条、第35条为第三国规定了参与争端解决的权利。联合国是以发展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为宗旨的世界性组织,联合国本身的客观国际人格,第三国有承认的义务。(24)《联合国宪章》客观上对第三国施加了法律上的义务。(25)随着人类发展的依赖性加深,关于全人类最一般利益诸如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和极地保护等方面的新规则效力普遍化是可以想象的。可以预见,条约效力相对性原理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必将获得更大的突破。
所以,单一适用“条约契约说”解释和说明多边条约与国际组织宪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窘境。应该承认,“条约契约说”只是契合了早期条约发展,特别是双边条约发展的历史,为双边条约订立、履行、解释和争端解决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解释力,有力地促进了条约实践和学术研究。但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人类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出现了更多需要合作和关注的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关系多边化和国际社会组织化已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现状迫切需要现代条约法理论以更加创新的精神迎接和应对21世纪国际社会多边化和组织化的挑战。
二、“条约契约说”的补充与修正
如前所言,“我们讲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首先要从民法原理出发。脱离民法原理,研究国际法,就可能会感到吃力”(26)。“条约契约说”其实就是民法与国际法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抓住了条约与契约的共性——“意思表示一致”的特点,成为借鉴私法原理解释和说明国际条约的成功范例。但是,“条约契约说”忽略了现代条约“意思表示不完全一致”的情形。“意思表示一致”和“意思表示不完全一致”的差异在私法和国际法中都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并且深究这种差异可以带来理论上的进步。在私法上,德国学者将这两种意思表示过程和结果略有不同,但又完全统一于“意思表示”过程之中的私人意思自治行为上升概括为“法律行为”,并分别以契约和决议(或共同行为)来指称。(27)契约是双方法律行为;决议或共同行为是多方法律行为。在国际法上,私法契约理论可以解释双边条约的缔结过程及其效力来源,但如果将其适用于多边条约,则不免过于牵强,缺乏说服力。《公约》第9条关于约文议定的规定,作了明确区分,其中第1项要求“议定条约约文应以所有参加草拟约文国家之同意为之”;第2项“国际会议议定条约之约文应以出席及参加表决国家2/3多数之表决为之……”这一规定清楚表明: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所议定的条约约文并不是国家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国际会议对条约的表决程序,在一定意义上赋予了这种多边条约的决议性质。随着国际社会组织化和多边条约机构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公约》第9条第2项适用范围将会不断扩大。由此可见,条约法理论与实践证明,条约法需要引入法律行为决议(共同行为)理论。
但是,现代条约法与《公约》只是承袭了法律行为中的契约理论,并没有借鉴和吸收决议理论。(28)纵观国内外条约法文献,研究决议类国际条约性质和理论的文献十分少见。(29)究其原因:一是私法中法律行为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意思表示及其在契约中运用。契约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及意思瑕疵的研究相当深入,关于法律行为中的决议性质及其地位的研究相对不足;(30)二是现代条约法缺少条约类型化的深入研究,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以及一般意义的条约与国际组织决议等不同类型条约的本质差异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31)上述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共同导致了现代条约法对法律行为中决议理论借鉴的需求和动力不足。
严格地讲,契约和决议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行为。德国民法中的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32)根据参与法律行为当事人的数量(实质是意思表示的数量)以及他们参与的方式,将法律行为区分为单方和多方法律行为。(33)其中,多方法律行为主要由合同和决议等构成(在此合同之义与契约相同——笔者注)。(34)合同和决议都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统一于多方法律行为之下,但是决议不同于合同。合同是必须由多个人,通常是由两个人参与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两个人(或全体人)所期待的法律后果是因他们之间相互一致的意思表示而产生的。(35)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既是合同的本质,也是合同效力的来源。所以,合同通常只能约束表示同意受其约束的当事人。而决议不同于合同,它是多人(或法人集体机构)意思表决的结果。卡尔·拉伦茨指出,“决议是人合组织、合伙、法人或者由若干人组织的机构(如社团董事会)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意思形成的结果”,“应该将决议从合同中分离出来”(36)。这种“意思形成”,必须通过“意思表决”的程序。决议可以“一致通过”的方式作出,也可以“多数决”方式作出。通过的决议的效力不仅及于参与决议的人,而且也及于该团体的全体,且均不考虑是否同意该决议的意思。但是,决议不调整团体或法人与第三人的关系,也不调整团体成员之间的私人关系,而旨在构筑成员间共同的权利领域或法人的权利领域。(37)可见,合同(契约)是两个主体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决议则是团体组织或多个主体之间“意思表决”的结果。“意思表示一致”是对立意思之间的协调,而“意思表决”是团体或整体意思的形成。归纳起来,契约与决议主要具有如下区别:第一,意思表示的相向性与同向性之别。契约和决议都是意思表示的结果。但是,契约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和方向具有相向性,即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就是另一方当事人要承担的义务;反之亦然。而决议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和方向完全同一,所有当事人享有共同的权利和承担共同的义务。第二,法律效力的相对性与整体性之别。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其效力具有相对性,即契约效力仅及于当事人,对第三人无效。而决议的效力及于所有当事人,对未参加表决或表决时投反对票的相关当事人同样具有约束力。第三,共同意思形成方式的意思表示一致性与多数决之别。在一定意义上,契约和决议都是共同意思形成的结果。但是,契约必须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条件,而决议则以“一致通过”或“多数通过”的方式形成。特别是随着现代法人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张,多数决的方式将会被更多的运用。
如前所言,德国学者关于法律行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意思表示和契约行为,对于决议理论(共同行为)的研究明显不足。(38)国内民法学者关于法律行为理论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倾向,忽视法律行为中的决议(共同行为)理论的研究。(39)私法对决议(共同行为)理论的研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条约法对法律行为理论的整体引入,影响了现代多边条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商事组织的迅速扩张,决议(共同行为)理论开始引起国内外私法学者的高度关注。大多数德国学者在民法教程和专著中对契约与共同行为或决议的区别给予了关注。(40)国内也有学者具体论述了决议的独立性问题,甚至提出应当将决议从法律行为理论中独立出来,以便更好地研究决议这种意思形成的程序和商行为程序。(41)还有国内学者以公司行为为例,论述了共同行为与契约的区分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42)这些国内外私法学者关于决议(共同行为)研究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拓展了法律行为的研究领域和深度,为国际条约法更加全面地引入和借鉴法律行为决议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
决议理论引入条约法可以有效地解释和说明现代多边条约与双边条约缔约过程及其效力的差异,弥补了“条约契约说”的理论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契约和决议实质上都是主体之间的意思互动,是形成共同意思的过程和结果。契约是双方主体之间的意思互动,决议是三方以上主体之间的意思互动,但互动所形成的共同意思之组成不完全相同。契约之共同意思是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主体之间的个体意思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意思互动实现了与共同意思的同一;决议之共同意思,是意思表决的结果,主体之间的个体意思可能与共同意思存在差异或距离。契约之共同意思的形成以“意思自由”为原则,要约和承诺的内容不受对方个体意思的干扰或约束;决议之共同意思的形成以“意思民主”为原则(这种意思民主是以意思自由为基础的表决民主),个体意思相互制约或影响,最后湮没于共同意思之中。任何个人意思都不能左右或支配共同意思。并且,决议之共同意思的形成过程不是简单的要约和承诺,而是一个意思表示、协商、妥协和表决的过程。决议程序在决议行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决议的正义价值。
私法上决议法律行为的这些特点及其独立于契约的价值,为决议引入条约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决议理论不仅可以解释现代多边条约及其组织化趋势,而且有效地化解了前述“条约契约说”的三个理论难题(“意思表示一致的违反”、“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突破”以及“效力相对性例外”)。在本质上,现代多边条约不过是缔约国围绕某一共同目标或国际公共利益通过意思表示、协商、妥协和表决所形成的共同意思,这种国家之间的共同意思不是个别国家意思的简单相加,它一旦通过民主程序而形成,必须约束所有缔约国,个别国家意思只能消弭于国家共同意思之中,不能左右或支配国家共同意思。并且,这种事关国际公共利益的共同意思之履行经常需要一个组织化的常设机构来协调众多国家之间的行为。现代多边条约的这些特点完全不同于双边条约,如果简单地借鉴私法契约原理解释多边条约就会导致“条约契约说”面对丰富条约实践时的捉襟见肘。我们循着“条约契约说”以私法理论解释国际法问题的路径和方式,且将“国家”想象为私法中的“个人”,现代多边条约及其缔约行为,质言之,乃是私法决议行为在国际条约法中的迁移和“再生”。现代多边条约,特别是一些组织章程的多边条约,也就是一种关于国家共同利益或国际共同利益的决议。这种认识或学说为现代条约法引入私法法律行为决议理论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分析工具。
三、引入法律行为理论重新认识条约本质
法律行为理论是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理论精髓,条约法对私法理论的借鉴主要集中于法律行为理论。正如学者们所认为的,“学说汇纂体系的主要特征在于前置总则之体例,总则之核心则在法律行为理论”。(43)法律行为理论是“19世纪德意志法律科学的绝对主题,而当时德意志法律科学所获得的世界性声誉,正是建立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44)法律行为理论不仅凝练了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精神,而且彰显了国际法(包括条约法)强调国家主权平等和意思自由的理念。国际法与私法在主体地位和调整对象上具有法律性质的趋同——即都以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这一特点决定了私法和国际法在理论上必然具有相通性;(45)并且,充当二者相通媒介的就是法律行为理论。事实上,法律行为理论所关注的意思表示和意思表决内容,成为解释和说明条约订立与效力的主要理论工具。“条约契约说”解释了早期条约现象及双边条约实践;“条约决议说”揭示了多边条约的特殊性,化解了现代国际社会多边化和组织化背景下“条约契约说”的理论难题,为法律行为理论适用于国际法提供了依据。所以,在国际条约法理论和实践中全面引入私法法律行为理论,作为解释条约本质和研究条约程序的理论工具和学说,具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和丰富的实践基础。
“法律行为是现代体系的产物”,(46)“罗马人未曾有过与之相应的技术性术语”。(47)最早系统论述法律行为的学者,当推历史法学派法学家萨维尼,他在《当代罗马法体系》第3卷中,阐述了法律行为作为“个人意思的独立支配领域”的观念,使得法律行为成为当事人设立与变更法律关系的重要手段。(48)他强调,法律行为不仅是人的意思自由,而且是行为人的意志直接指向法律关系之产生或解除。普赫塔承继了萨维尼关于法律行为的基本见解,并以更具技术性的“法律上的行为”概念来表述萨氏所称“自由行为”,认为法律效果如系基于行为人意旨而发生,则称“法律行为”。(49)类似地,温德沙伊德也认为,法律行为作为法律事实之一类,是指向权利设立、消灭与变更的私人意思表示。(50)德国民法典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采纳了温德沙伊德的观点。(51)可以说,正是意思自治、意思表示与法律效力“三维一体”构筑起私法上法律行为的空间。其中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支柱。德国学者恩内克策鲁斯和尼佩代说:“任何法律行为均要求以意思表示为其根本成分”,但意思表示只是私人追求所欲法律效果的工具。他们写道:“在现行私法制度与宪法之下,人们被授予广泛的权力来根据自己(表达出来的)意志形成法律关系,并由此协调各自的需求与偏好。为之服务的手段,乃是意思表示——法律效果系于其上的私人意思表达——之作出。单方意思表示或与他方意思表示的结合,加之经由意志附设的其他构成要件,被承认为意欲法律效果之基础,所有这些意志行为或者另加经由意志附设的其他法律要件,我们称之为法律行为。”(52)冯·图尔亦如恩内克策鲁斯和尼佩代,明确表示,私法领域内的自由自决不妨称为私法自治,而法律行为则为实现私法自治的手段:“个人的法律关系由各自调整乃是最为合理的选择,并因此许可当事人在广泛的范围内为自己的法律关系作出决策,这一观念构成民法的出发点。为该目的服务的,是法律上的行为中最重要的类型:法律行为。因此,指向私法效果(法律关系或权利的创设、废止或变更)之私人意思表达实为法律行为构成中的本质因素。”(53)
可见,法律行为主要是私法自治的工具,反过来,又以意思表示作为自己的工具或手段。(54)它是以意思自治为前提、以意思表示为工具、以法律效果为目的的“三维法律构造”,整体彰显私法自治之精神。私法上法律行为的这些属性和构成,为国际法上的国家法律行为提供了恰当的理论注解。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本质乃是一种“对内至高无上,对外一律平等”的高度自治的权力。在国家主权平等的社会里,不存在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或权力机构,所谓国际法也不过是国家之间意思协调的产物。所以,如果将国家比拟为个人,国际社会则是一幅生动的市民社会图景。(55)国家行为是国家的“意思自治”,主权国家的意思是产生、变更或消灭国际法权利义务关系的唯一依据。以私法法律行为理论类推,国际法上指向国际法效果(法律关系或权利创设、废止或变更)的国家意思表达乃是“国际法律行为”。(56)这种“国际法律行为”完全符合“私法法律行为”的三维构造:意思自治、意思表示和法律效果。不同的是,意思主体转变为主权国家,法律效果产生于国际法,意思表示方式要符合国家外交习惯和法律规定而已。国际法上这种关于国家意思表示行为的认识,以及国际社会不存在“中央立法机关”的国家平权状况,赋予了国际法律行为在国际法领域中更加特殊的地位和广阔的适用空间。
条约行为是形成国家之间共同意思的国际法律行为。(57)它以国家意思自治为前提,以意思表示为工具,以改变国际法原有秩序为目的,是一个从单方国家意思到国家之间共同意思形成的过程。私法上主体意思的形成过程相对简单,特别是自然人的意思形成是人类有意识的内在心理过程,通常归属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长期被私法所忽略。关于意思(形成)能力,只是以法律行为能力加以替代(有法律行为能力者即有意思行为能力)。这种私法上学术思维的惰性,导致了人们忽视对私主体,特别是私组织的意思形成过程或程序的深入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了现代条约法理论关于国家共同意思形成过程的探讨。(58)私组织(团体)意思的形成过程,是组织成员按照一定程序和原则,成员之间意思相互碰撞、整合产生新的共同意思的过程。团体新的共同意思之形成不同于单一成员的意思形成。前者是成员之间的意思表示或表决;后者是成员的内心或组织内部的活动。私组织的(团体)意思形成过程和特点的研究可以为现代条约缔结过程中国家意思形成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作为条约缔结过程起点的“国家意思形成”,与经历“国家意思表示或意思表决”后最终形成的缔约方之间的共同意思(缔约国共同意思形成),同样也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意思形成过程。某一缔约方的国家意思形成,是内国法问题,与内国宪法之国家机构及其职能密切相关,现代条约法只是在条约缔约权及其代表资格等问题中有所涉及。(59)只有缔约方的共同意思形成才是条约法所关注的问题。这种共同意思以条约为载体,已经超越了单边国家意思和内国法,转化为国际法问题。所以,无论如何,条约离不开国家意思,条约本质上乃是缔约方之间共同意思形成的结果。国家之间的缔约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法律行为。
条约作为国际法律行为,仍然表现为国家意思表示和国家意思表决两种基本形式。国家意思自治只是国家缔结条约的前提,离开了国家意思自治,不会产生任何有效的国际法或条约。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就是限制国家意思自由的结果。但是,国家意思自治不是条约或条约行为的本身,条约的产生一般要经历意思表示或意思表决过程或程序。(60)在私法上,意思表示是“法律效果系于其上的私人意思表达”,是法律行为的工具。(61)德国学者对法律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成为观察法律行为本质的重要参数。(62)甚至,意思表示程序和意思表示效力可以等同于法律行为的程序和效力。(63)这些私法原理可以适用于条约法理论中国际法律行为的认识:国家意思本身不是国际法律行为,只有将附着国际法律效果的国家意思表达出来,国家意思才能转化为国际法律行为。没有意思表示或意思表决的媒介和工具,国家意思不可能产生条约法上的意义。可见,条约是国家意思表示或意思表决的结果。具体而言,双边条约是国家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多边条约是国家意思表决的产物。
“国家意思表示”和“国家意思表决”在意思表示方式上的差异:国家意思“表示一致”和国家意思“多数决”,决定了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在条约性质和条约程序上的不同。(64)两个国家之间通过约文议定、认证等包含要约和承诺私法要素的国家意思表示达成意思一致,产生双边条约,从而约束缔约方。这种简单的程序可以较好地保证双边条约订立的效率,但是,不能满足多边条约缔约方意思表示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要求。多边条约不是契约,三方以上缔约方共同意思的形成是一个包含意思表示的复杂的意思表决程序,类似于私法上的决议,包括意思协商、妥协、放弃和修正等。从理论上讲,国家意思表决是一个从国内到国际的复杂程序:各缔约方首先将按照国内法(主要是宪法)形成的国家原始意思表示出来,通过反复意思协商和妥协不断修正国家原始意思,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缔约方意思的接近或趋于一致,直至以多数决或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多边条约文本所承载的缔约方共同意思。多边条约所承载的共同意思不是缔约方意思的简单相加,其中包含缔约方对条约某些条款的反对或弃权意思。然而,多边条约共同意思一旦形成,即对所有缔约方产生约束力,甚至约束后来加入条约的缔约国。可见,这种“国家意思表示”与“国家意思表决”在表示方式和效力上的差异,决定了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不同的法律性质。
虽然前文中关于条约性质的表述——“条约契约说”和“条约决议说”,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私法法律行为理论适用于条约本质的认识结果,以及两类不同条约的性质差异,但是却忽视了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统一于国家意思互动的事实,没有揭示出两类不同条约的共性,即双边条约的“国家意思表示一致”与多边条约的“国家意思表决”只是“国家意思互动”的两种形式而已。条约的本质系于或统一于国家意思互动。通过意思互动,达到国家意思表示一致或意思多数决。传统法律行为理论没有提出意思互动概念,但其始终认为,契约是一个“要约和承诺”不断反复的过程,事实上也是承认了契约主体间的意思互动。私法特别强调,法律行为是法律效果系于其上的意思表达行为,这一观点也蕴含了法律行为中的意思互动思想。若没有意思互动,单纯的意思表示并不会产生或改变法律关系的效果。意思表示或表决,通过意思互动实现了法律效果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向法律行为的转化。所以,尽管传统法律行为理论没有直接研究意思表示和意思表决之中的意思互动,但从其产生之日起,即包含了主体间意思互动的思想,这一点是不用质疑的。以法律行为理论为工具,分析和揭示缔约方共同意思形成过程之中的国家意思互动,对于创新条约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言,条约是一个以意思表示或意思表决为工具,最终形成缔约方共同意思的过程,即由单边国家意思(某一缔约国意思)转化为不同国家之间(所有缔约国)共同意思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充满了国家意思互动。离开了国家意思互动,国家意思表示或表决就会成为空洞之物。与私法契约要约与承诺类似的约文议定、认证是双边条约之意思形成的意思互动形式;包含私法决议协商、妥协等因素的缔约国协商一致、多数决是多边条约之意思形成的意思互动方式。条约作为国际法律行为,仅凭形式上的国家意思表示或表决不可能实现其法律效力,必须依靠国家意思表示或表决背后的国家意思互动。没有国家意思互动,国家意思表示只是单方的国家声明,国家意思表决将无法进行,国际条约也无从缔结或产生。因为只有国家意思互动才能实现国家意思之间的沟通、协商、妥协和认同,才能将个别国家意思转化为国家之间新的共同意思。并且,国家意思互动不是对原始意思表示的简单认可或组合,而是一个动态的对原始意思表示进行“化合”产生新的意思的过程。@离开了国家意思互动的国家意思表示或意思表决不可能形成国家之间共同意思或条约。可见,条约是国家意思互动的结果。国家意思表示或表决只是国家意思互动的方式。条约本质“国家意思互动说”符合国际条约实践,统一了条约法理论关于条约本质的不同认识,是运用私法法律行为理论对条约本质进行高度理论概括的成果。反之,如果以国家意思表示或意思表决单独概括条约本质,不仅没有反映私法上法律行为的契约与决议分类,而且以偏概全,掩盖了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的区别,理论上未免显得片面和肤浅,不利于条约深入的研究;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分别概括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本质:以“条约契约说”强调国家意思表示一致,解释双边条约本质,以“条约决议说”主张国家意思表决,反映多边条约本质,似乎可以说明两类不同类型条约的本质,但是,这种方式无法揭示“国家意思表示”和“国家意思表决”二者统一的基础与方式,以及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作为条约之间的共性。一句话,只有深入国家意思表示和国家意思表决背后的国家意思互动,才能真正获得条约形成方式和条约本质两个方面的真理性认识。
四、条约本质再认识对我国缔约实践的意义
“条约契约说”解释了双边条约的缔结过程和效力来源,适应了传统条约实践对理论的需要。但是,“条约契约说”不能解释现代多边条约所秉承的国家意思民主和意思表决制度或原则,无法化解条约“意思表示一致之突破”和“效力相对性例外”等条约实践中的理论困惑。而“条约决议说”为解释上述理论难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揭示了现代多边条约意思民主和意思决议的内在特质。但是,“条约决议说”不能适用于双边条约,不能兼容条约法理论的传统认识,容易造成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条约契约说”与“条约决议说”的分离,不利于条约法的统一立法或解释。其实,不论是双边条约还是多边条约,不管是意思表示还是意思表决,都是国家意思自治条件下国家意思互动的结果,都是典型的国际法律行为。从国际法律行为与国家意思的关系来看,单边国际法律行为是纯粹的国家意思表示,双边国际法律行为和多边国际法律行为是典型的通过意思表示或表决的国家意思互动。国家意思表示、表决和互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统一于国家意思互动之中。双边条约中意思表示之目的在于意思互动,多边条约中意思表决包含了意思表示和意思互动。(66)只是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在国家意思互动的方式和复杂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传统私法法律行为理论专注于意思表示的研究,简单地将贯穿于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抽象为法律行为的本质或等同于法律行为,忽视了单方法律行为与多方法律行为(包括双边法律行为)的区别,忽视了多方法律行为(包括双方法律行为)意思互动的本质。(67)私法上法律行为理论的缺陷通过“条约契约说”传导到条约法之中。即在条约法研究中,简单地以契约概括条约本质,就是私法上以意思表示代替或等同法律行为之错误的理论翻版。条约本质既不是契约或决议,也不是意思表示,而是国家之间意思互动的结果。条约本质的这种崭新认识化解了“条约契约说”解释条约本质的理论窘境和矛盾,拓展了现代条约法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领域。同时,也更加突出了两类条约的异同点:一是实证和反映了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性质上的差异,将其分别归属于法律行为的契约和决议,为深入研究条约提供了适当的理论工具;二是揭示和创新了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的本质上的联系——不同类型的条约都是国家意思互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意思表示或表决。现代条约本质的“国家意思互动说”不仅丰富了条约法关于条约类型和本质的认识,而且对指导我国相关缔约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条约法的类型化研究,指导我国条约缔约方略
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是条约的基本分类。《公约》从内容来看,主要规定了多边条约的内容。多边条约缔约过程复杂、涉及缔约国多、更多地关系到国际共同利益,所以,为了更好地预防可能频发的多边条约争议,提高缔约效力,倾注足够的立法资源总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但是,条约法更多关注多边条约的事实,与学术上对多边条约理论研究的冷落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状况延续至今,使得“条约契约说”成为条约本质认识的唯一学说,而从没有受到学界的质疑成为可能。国际法委员会研究组2006年《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与扩展引起的困难》报告也曾经指出,“总的说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特殊类型的条约和可能用来解释和适用这些条约的特别规则未给予足够的承认……至少,下列主题应该成为此类努力的一部分:(a)应该在更大程度上承认双边和多边条约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同……”(68)条约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这种奇异现象表明:条约理论与实践严重脱离,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以指导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的立法实践。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在国家意思表示或意思表决原则、国际法律行为类型和性质、意思表示与意思表决程序以及条约效力来源上存在重大差异。运用“条约契约说”和“条约决议说”可以从理论上将这些差异分离开来,对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类型化研究给予具体指导;另一方面,条约本质之国家意思互动的论断,又将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统一在国际法律行为的理论之下,为“条约契约说”和“条约决议说”的统一与合作提供理论注解,从而在条约本质“国家意思互动说”的基础上改变条约法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实。比如,在国际多边投资体制缺乏的背景之下,为了保护规模日益庞大的海外投资,我国应当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坚持双边投资条约的契约本质,与海外投资东道国逐一签订个性化的双边投资条约,同时,关注双边条约的发展趋势,积极倡导投资自由化,推动与国际投资相关的多边条约的缔约活动。
(二)有利于提升条约法的程序理念,优化我国条约缔约过程
法律程序不仅有助于“好结果”的实现,而且自身具有和平、参与、自愿、公平、及时、人道、正统等独立性价值。(69)作为国际法主要渊源的条约,本质上是国家意思互动的产物,程序及其价值在条约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公约》第23条、第65~68条具体规定了条约保留与条约终止、退出等方面的程序,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形成条约内容的意思互动程序。《公约》第9条关于“条约议定”之规定十分简单,一般认为,第9条第1项适用于双边条约,即缔约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第2项适用于多边条约,即缔约方采取意思表决多数决。当然,不排除有些多边条约采用第1项“意思表示一致”的方式。从条文内容来看,与其说第9条是关于约文“议定”的规定,不如说是约文“通过”之规定。因为条文只有“定”,而没有“议”的内容。这种重“通过”,轻“商议”的规定不符合“条约是国家意思互动结果”的认识,没有反映条约之国家意思互动的程序要求和价值。不论是双边条约,还是多边条约,其缔结过程都是一个国家意思互动的过程。意思互动之步骤和方式的合理安排,乃是程序理性和价值的内在要求,也直接关系到条约“是否为好条约”以及公平正义价值之实现。否则,“条约议定”就可能演化为强势缔约方推销个体意思的过程。历史上,不平等条约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国际现实生活中,军事和经济霸权的存在,也赋予了条约法规定意思互动程序的意义。
具体来讲,国家意思互动程序,包括意思表示和意思表决程序。双边条约之意思互动比较简单,主要是双方意思表示,通过缔约方之间的要约和承诺的多次反复进行约文的议定和认证。特别是有些通过换文和口头等通过非正式形式缔结的条约,国家之间反映要约与承诺的文件和相关凭证具有证明条约内容的效力。条约法中明确规定双边条约约文议定程序有助于认定双边条约的成立和生效。多边条约之意思互动是一个复杂的意思表示和意思表决过程。在意思表决程序之中,各方应有机会以提案的方式进行意思表示,然后经过公开讨论、辩论、协商、妥协等程序,各种意思表示在合理的程序之中得到碰撞、磨合、选择和修正,各种新观念得以表达并吸收到条约文本之中,最后以表决方式形成缔约方共同意思,即条约约文,再进入约文认证、签署和批准程序。条约是复数意思互动,必须解决意思互动的有序性问题,以实现复数意思表示的整合。否则,杂乱无章的意思表示可能会为强权留下淫威的空间。可见,条约法中的程序,尤其是国家意思互动程序,具有鲜明的可以达到“好结果”的工具价值和实现参与、自愿和公平的“程序价值”,以双重保障缔约方真正共同意思的形成。(70)因此,我国在双边条约的缔结过程之中,应该重视要约和承诺的过程以及过程的证明材料;在多边条约缔约过程中,应当积极发挥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利益相近国家进行沟通与协调,形成有代表性的共同意思,赢得与其他利益相对方进行博弈的条件与优势,从而争取多边条约形成过程之中更多的国家利益。
(三)有利于区分条约解释的不同路径,提高我国条约适用水平
《公约》第31~33条作为条约解释通则,规定了条约解释的基本原则、条约上下文含义以及条约解释的法律渊源等问题,成为指导条约解释实践的基本规则,并得到系列国际法院案件的支持。(71)但是,条约相关规定忽视了不同类型条约之解释的差异。双边条约与多边条约法律行为性质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二者不同的解释路径。双边条约是缔约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条约所载之共同意思等同于缔约方各方的意思。如果相关条文的理解出现分歧,这种平衡或意思同一关系就可能会被打破。所以,恢复这种平衡或同一关系就成为条约解释的主要任务。换言之,就是要寻找条约中所载缔约双方之“原意”或缔约双方重新达成关于分歧的共同意思。这一目的和任务,实际决定了双边条约解释的方式——双方协商。只有在协商无果的条件下,才可以请求国际仲裁机构或国际法院协助完成寻找“条约原意”或达成新的共识的任务。与双边条约不同,多边条约缔结是以意思表决方式完成的。多边条约一旦缔结,则形成了不完全相同于条约缔约方单方或部分意思的共同意思。这种以单方意思为基础形成的共同意思,不是缔约方意思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复杂的意思“化学反应”,原单方意思消解于“化合物”之中。因此,多边条约的解释,不可能通过寻找缔约方各自原意的方式完成。为了实现解决条约争议的效率,节省司法资源,所有缔约方参加重新达成共同意思的方式,也不可能多用。所以,多边条约解释争议解决的理想方式,应当主要通过“条约机构”或国际组织自身解决。机构或组织作出的解释对缔约方全体产生约束力。(72)相应地,我国在条约实践中应该注意区分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不同的解释路径和方法,真正提高条约的履行和适用水平,以减少纠纷。
注释:
①《奥本海国际法》(第8版)对条约所下的定义是,国际条约是国家间或国家组成的组织间订立的在缔约各方之间创设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契约性协定(在詹宁斯和瓦茨第9版修订时,将条约的定义删除,原因没有具体解说,不得而知)。德国国际法学者菲德罗斯认为:“条约是指两个或几个国家之间根据国际法明示成立的或通过推断性行为成立的合意,这些国家在这种合意中承担一定的给付、不作为或容忍的义务,不论这种义务是单方的或相应的,同样的或不同的,一次的或反复的。”在苏联科学院编著的国际法教科书中,国际条约被界定为:“两个或更多国家关于建立、修订或终止其相互权利义务的正式表示合意。”日本国际法学者尾崎重义将广义的条约定义为:“国际法主体(国家、国际组织、交战团体)之间达成的、产生一定的国际法效果(国际法权利和义务的产生、修改和消灭)的国际协议。”李浩培先生认为:“条约是至少两个国际法主体在原则上按照国际法产生、改变或废止相互间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的一致。”王铁崖先生认为,条约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依据国际法确定其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一致的意思表示”。相关内容,可参见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版,第407~408页;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页;万鄂湘:《国际条约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2分册,石蒂、陈健译,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688页等。
②同上注,王铁崖书,第293页。
③私法契约定义来源于罗马法,基本上为大陆法系各国民法所继受。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规定:“契约,为一人或数人对另一人或数人承担给付某物、作或不作某事的义务的合意。”《意大利民法典》第1321条规定:“契约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关于他们之间财产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或者消灭的合意。”而英美法中,一般认为契约乃是一种“允诺”。美国《法律重述·合同》(第2版)第1条规定,契约是一个允诺或一系列允诺,违反该允诺将由法律给予救济,履行该允诺是法律所确认的义务。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契约所下的定义是:“契约是可以依法执行的诺言。这个诺言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④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仅引用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省略1986年《维也纳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间条约法公约》的相关条文。《公约》第9条规定:“一、除依第二项之规定外,议定条约约文应以所有参加草拟约文国家之同意为之。二、国际会议议定条约之约文应以出席及参加表决国家三分之二多数之表决为之,但此等国家以同样多数决定适用另一规则者不在此限。”
⑤德国学者弗卢梅(Flume)将法律行为分为两大类:单方法律行为与多方法律行为。梅迪库斯将法律行为分为四类: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多方法律行为以及决议(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167页)。贝克法律词典将法律行为划分为单方法律行为与多方法律行为,后者首推契约,次为共同行为。日本将法律行为分为单方行为、契约与合同行为,即共同行为(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因使用习惯不同,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习惯于用“合同行为”来指称“共同行为”(参见杨与龄:《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我国大陆学者通常将法律行为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161页)。这些分类,用语虽略有不同,但实质上大同小异,其大同者,在于所分的类型大体相似;其小异者,在于决议是否可归入共同行为,意见不一,多数主张区别开来。德国学者如拉伦茨、梅迪库斯以及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等认为应当将决议与共同行为区分开来。但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决议属于共同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因为是否采用多数决,只是形成最终的团体意思的方式有所不同,在多数人同向的意思表示方面,决议与共同行为没有本质区别(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本文在使用契约概念时,不区分契约与合同;在使用决议概念时,赞同王泽鉴先生的观点,不区分共同行为和决议。
⑥[英]劳特派特:《国际法的私法渊源和类比》,1927年版,第126页。
⑦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⑧第9条约文之议定:“一、除依第二项之规定外,议定条约约文应以所有参加草拟约文国家之同意为之……”;第40条多边条约之修正:“……二、在全体当事国间修正多边条约之任何提议必须通知全体缔约国,各该缔约国均应有权参加:(甲)关于对此种提议采取行动之决定;(乙)修正条约之任何协定之谈判及缔结。”
⑨1969年和1986年两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均将条约定义为协定,从整个条约法的结构:条约订立、条约生效、条约解释等,与国内合同法的结构也有相同之处。
⑩张乃根:《国际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我国国际法一代宗师李浩培先生也十分重视国际法的民法学基础,认为“民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
(11)为了分析和行文的方便,本文主要截取国家之间的条约作为研究对象,文中所称“国际法主体或国家”之处,都包含国际组织。文中关于国家之间条约本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所缔结的条约。
(12)这一点从拉丁语“pactus”、“pactum”(条约)的语源可见。“paetus”、“pactum”系由拉丁动词“paciscere”的过去分词pactus派生而来。“paciscere”的意思是达成一致、缔结契约或者条约,其字根pac源于pax。pax是指两个交战国缔结或达成一个协定的行为或事实,因此这个词也取得和平条约、和平女神的意义。同前注①,李浩培书,第32页。
(13)See Arthur Nusabaum,Concis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1947,p.7.
(14)参见陶伯:《论条约的不可侵犯性》,载《国际法学院演讲集》1930年第2册,第304页。
(15)公元前579年的晋楚同盟是双边条约,《左传》中载有该约的约文。公元前651年和公元前562年各诸侯的同盟条约,《左传》中也记载了其约文。
(16)这种形式一直沿用到12世纪,公元1122年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缔结的《沃尔姆斯友好条约》也通过此种形式订立。从1153年拜占廷帝国与匈牙利人缔结的《康斯坦条约》起开始采用新的方式:条约记载在以缔约双方的名义写成的一件文书中,每人各执一份,两份中所包含的条款完全相同。至中世纪以后,这种方式已一般化。
(17)同前注⑦,李浩培书,第34页。
(18)同前注⑦,李浩培书,第33页。
(19)根据UIA统计,2004年到2005年,包括其所有类型的各类国际组织共有58859个,比1991年多一倍以上,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数目为735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有51509个,分别比1991年多61%和109%。国际社会的日益组织化不仅表现在国际组织数目的增长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国际组织范围的扩大上,它早已冲破初创时期的地域、领域局限,活跃在当今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20)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节第19条、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规定了保留的权利、接受或反对、撤回及其相关程序。
(21)参见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国际劳工组织约章》在1953年国际劳工会议第三十六届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的修正案,规定此后该组织约章的修正案,经国际劳工会议出席代表2/3多数通过,并经该组织会员国三分之二,包括作为具有主要工业上重要性而有权邀请代表参加理事会的10个会员国中5个的同意,即发生效力,即使对于反对该修正的会员国,包括具有主要工业上重要性的5个会员国,也发生效力。当然,不同意修正的会员国有退出的权利。
(22)李浩培先生认为,这是条约和国际立法两者相接触的边缘地带(同前注⑦,李浩培书,第141页)。有学者认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的这种权力是准立法权(参见赵维田:《国际航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这里条约缔结的程序几乎完会被弱化,主要是由于这些附件相当大部分是技术性细节,细化为法律细则是为了确定国际标准以保证公约的实施,是与专门性国际组织的目的相适应而对条约法的特殊变通。
(23)关于专门性国际组织职能及其法律制度的论述,可参见前注(21),梁西书,第279~316页。
(24)“第三国有承认联合国人格的义务”这个原则是国际法院1949年4月11日“在为联合国服务中所受伤害的赔偿案”的咨询意见所宣示的。
(25)同前注①,李浩培书,第413~416页。
(26)同前注⑩,张乃根书。
(27)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中心,其构成要件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关于法律行为概念的沿革,可参见朱庆育:《法律行为概念疏证》,《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
(28)学界关于条约概念及特征的论述,除强调意思表示一致外,没有意思表决的论述。例如李浩培在《条约法概论》第13页的相关论述(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英]安托尼·奥斯特(Anthony Aust)在《现代条约法与实践》第14~26页关于条约定义的论述(江国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29)目前,笔者尚未查阅到专门研究决议类国际条约的文献。有些文献虽注意到了决议类条约,但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例如安托尼·奥斯特在《现代条约法与实践》第25页中提及到决议类条约问题。
(30)在[德]卡尔·拉伦茨所著的《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和[德]迪特尔·施瓦布所著的《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章节中皆没有对决议进行专门论述。
(31)Report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n 2006,Chapter 9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Difficulties Arising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p.156.
(32)同前注(30),迪特尔·施瓦布书,第294页。
(33)在国际法中,单方面法律行为主要表现为主权国家声明和处分等,涉及条约解除、撤销等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对不同种类条约的性质影响不大。鉴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在此不作进一步阐释。
(34)同前注(30),迪特尔·施瓦布书,第295页;同前注(30),卡尔·拉伦茨书,第431页。
(35)同上注,卡尔·拉伦茨书,第432页。
(36)同上注,第433页。
(37)同前注(35),卡尔·拉伦茨书。
(38)同前注(30)。
(39)我国主要民法学教程,如王利明主编的《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魏振瀛主编的《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都未涉及相关内容。
(40)同前注(35),卡尔·拉伦茨书。
(41)参见陈醇:《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的区别:决议独立性初探》,《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
(42)参见韩长印:《共同法律行为理论的初步构建——以公司设立为分析对象》,《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刘康复:《论股东决议与股东协议的区分》,《法学杂志》2009年第9期。
(43)Werner Flume,Allgemeiner Teil des Burgerlichen Rechts II,Das Rechtsgeschaft,4.Aufl.,Springer-Verlag,1992,S.28.
(44)Flume,a.a.0.,S.30.
(45)参见张文彬:《论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8页。
(46)同前注(43),Werner Flume书,第29节,弗卢梅却指出,学说汇纂法学创造的法律行为概念,并不是各种具体行为类型归纳抽象的产物,而是“人的行为”这一上位概念演绎而来。他列举的典型例证是时任哈勒大学法律正教授与法学院董事的达贝洛首版于1794年、再版于1796年的《当代民法大全体系》,该书第1卷初版第329节(再版第366节)在“论法律的行为”之标题下,作有如下说明:“人的行为有一主要类型,即所谓法律上的行为或称法律的行为,其含义为,以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为标的之合法的人的行为。”冯·图尔似较倾向于归纳,他认为,“法律行为概念产生于各种依当事人意志安排法律关系之法律上行为的概括”(Vgl.Andreas von Tuhr,Der Allgemeine Teil des Deutschen Biirgerlichen Rechts,zweiter Band,erste Halfte,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Miinchen and Leipzig,1914,S.143)。
(47)Heinrich Dernburg,Pandekten,erster Band,Berlin,1884,S.207.
(48)Vg.Friedrich Carl von Saviny,System des heutigen romischen Rechts,Band 3,Berlin,1840,S.5.萨维尼指出,法律事实包括当事人的自由行为与偶然事件,前者“指涉当事人(法律效果)之取得或丧失”,以行为人意志是否直接指向法律效果为标准,它又可分为两类,其中,“尽管一项行为也许不过是其他非法律目的的手段,只要它直接指向法律关系的产生或解除,此等法律事实就称为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
(49)Vgl.Georg Friedrich Puchta,Pandekten,9.verm.Aufl.,Nach d.Tode d.Verf.besorgt von A.F.Rudorff,Leipzig:Barth,1863,S.74.
(50)Vgl.Bernhard Windscheid,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Band 1,Diisseldorf:Verlagshandlung von Julius Buddens-1862.S.144.
(51)Mathias Schmoekel/Joachim Riickert/Reinhard Zimmermann(Hg.) Historisch-kritischer Kommentar zum BGB,Band I,Allgemeiner Teil,Mohr Siebeck,2003,S.358.德恩堡(Dernburg)亦将法律行为定义为“据以设立、变更或废止法律关系之人的意思表示”,并明确指出,“法律行为的特征在于法律效果对于意志的依附性”。同前注(47)。
(52)Ludwig Enneccerus/Hans Carl Nipperdey,Allgemeiner Teil des Burgerlichen Rechts; Ein Lehrbuch,zweiter halbband.15.Aufl.J.C.B.Mohr (Paul Siebeck) Turbingen,1960,S.896f.
(53)同前注(46),Andreas von Tuhr书,第105节。
(54)同前注(36),梅迪库斯书,第142页。
(55)这里借用市民社会概念,表达国际社会主权平等、国家意思独立和自由、没有超越国家主权的权力存在的国际社会的平权结构。
(56)国际法律行为是指国家意欲发生国际法效力的意思表示行为,不同于国家法律行为。国家作为私法主体,在国内法上也可以为法律行为,为了区别起见,称之为国家法律行为。
(57)这种国家意思表示行为完全符合私法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可以称之为法律行为。为了区别之便,当国家作为国内私法主体,与其他主体从事民事交往,受国内法调整时,这种国家意思表示行为,直接称之为法律行为;当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与他国订立有关领土、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条约,受国际法和条约法调整时,称之为国家或国际法律行为。
(58)公司章程、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等实质上是公司意思形成的结果,公司法中关于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通过的程序就是公司意思形成的程序,包括公司意思产生、变更或废除等方面的程序。公司团体意思形成从法律行为类型划分来看,应当属于决议或共同行为一类。
(59)西方国家议会的决议和总统命令属于国家意思,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以及国务院的决定属于国家意思。这些国家机关的意思形成过程和程序是国家意思的形成过程和程序。
(60)任何行为都有一个过程,对行为的步骤、方式的理性安排就是程序。程序与过程的区别在于,程序是人工设计的产物,是经过人工设计的过程,其中注入了人工理性,即程序理性。
(61)同前注(30),卡尔·拉伦茨书,第492页。意思表示程序和意思表示效力是意思表示的主要内容。意思表示程序包括要约和承诺;意思效力主要是意思瑕疵,包括意思形成阶段的瑕疵与意思表示阶段的瑕疵,后者包括五种形态:心意保留、戏谑表示、虚假行为、错误、恶意诈欺和非法胁迫。
(62)在对“法律上的行为”进行分类时,恩内克策鲁斯/尼佩代将意思表示与违法行为划作一组,并认为:“之前的理论通常在这两类行为中只考虑法律行为与侵权行为,此等认识并不完全正确。法律上的行为之下位概念并不是法律行为——它经常由数项行为构成甚至还包括其他成分,而是意思表示。”同前注(52),第863页。
(63)《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书》写道:“就常规言,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为同义之表达方式。使用意思表示者,乃侧重于意思表达之本身过程,或者乃由于某项意思表示仅是某项法律行为事实构成之组成部分而已。”转引自前注(36),梅迪库斯书,第190页。
(64)遗憾的是,这种差异被现代条约法理论所忽略,影响了现代多边条约的深入研究。本文第1、2部分已经作了细致论述,在此不作赘述。
(65)关于私法中决议的意思互动,可参见陈醇:《论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和决议之间的区别——以意思互动为视角》,《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66)意思表决与意思表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意思互动的程序不同,文中分开称谓的根据和意义也在于此。意思表示的意思互动是要约和承诺的过程;意思表决的意思互动包括意思表示、意思协商、意思妥协和决议等程序。二者相互联系之处,主要在于都是意思自治的体现,都离不开意思表示。将意思表示完全从意思表决中分离出来的观点有待商榷之处。
(67)关于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决议的区别以及传统法律行为意思表示说不足的论述,可参见前注(65),陈醇文。
(68)同前注(31)。
(69)See Robert S.Summers,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Legal Processes-A Plea for "Process Values",60 Cornell Law Review,1,23(1974).
(70)对于这种程序价值。也有人译为“过程价值”。参见陈端洪:《法律程序价值观》,《中外法学》1997年第6期。
(71)第31条解释之通则:“一、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二、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指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并应包括:(甲)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乙)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三、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甲)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乙)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丙)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四、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
(72)条约机构是指由非以创设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要目的的多边条约建立的机构,包括条约规定建立的机构,以及这些机构根据条约授权而建立的其他机构。条约机构又被学者称为“条约机体”甚至“条约组织”。它们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Alan Boyle and Christnie Chinkin,The Making of Inte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51;) Philippe Sands and Pierre Klein(eds),Bowetts Law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5th ed.,Sweet & Maxwell,2001,p.115)。条约机构现象在多边环境条约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