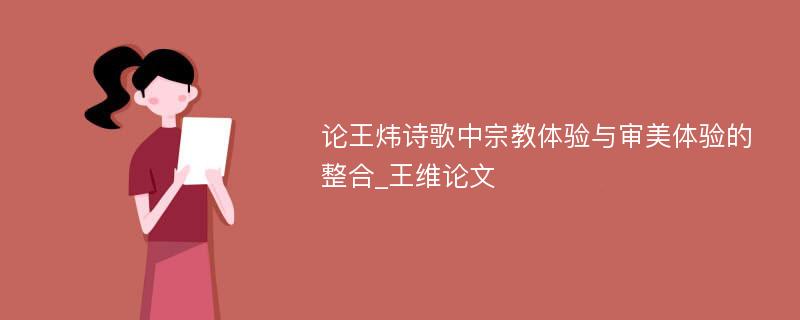
论王维诗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之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王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0)01-0107-06
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了“诗佛”之称誉的诗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佛学理论修养非常精深,历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能坚持较为严格的宗教实践,通过对禅门妙法的透彻参悟,深得禅家三昧,以至有些诗达到了“字字入禅”的境地。因此,按照禅宗“顿悟成佛”、“彻悟即佛”的说法,称王维为“诗中之佛”当是不过分的。
在王维生活的盛唐时代,中国佛学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关系当然最为密切,据其所撰的《请施庄为寺表》说,他的母亲“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据考证,这位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嫡传高足弟子,北宗禅七祖普寂。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的诗人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这位道光禅师也是一位北宗中人。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禅大师神会相遇于南阳临湍驿,这次会见,对王维影响极大,据《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记载:“于时王侍御(指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乃为寇太守、张别驾、袁司马等曰: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寇太守云:此二大德(指神会与北宗禅僧惠澄)见解并不同。王侍御问和尚,何故得不同?答曰:今言不同者,为澄禅师要先修定以后,定后发慧,即知不然。今正共侍御语时,即定慧俱等。……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2]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在孤独与寂寞中,他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就在这种禅境之中,宗教体验竟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而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作为宗教实践、宗教体验而言,王维的“以寂为乐”、“知悟胜事”,是与禅观修习法门联系在一起的。全部佛学即包括戒、定、慧三学,修持者必须三学齐修,缺一不可。其中定学一门,多强调止观双修,即在修定之时,必须辅之以观想,方可达到目的。早期传入中国的安世高禅学倡导的多半是小乘禅观,主要在于观空、观苦、观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具体有修“不净观”、“数息观”等法门,如不净观想象众生身体各处的秽污不洁;数息观则闭目凝神,端坐不动,心如止水,默数自己的呼吸出入;还有修“四念处”禅观的,即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些禅观,由于有导致修行者悲观厌世,停息一切心识活动的倾向,所以被大乘禅学斥之为“沉空守寂”,非是至道。与小乘禅学不同,大乘禅观强调五蕴本空,六尘非有,真空妙有,实为不二。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便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3]中国佛学主要是沿着印度大乘一派发展的,所以在禅观方面也不主张一心唯作苦空观想,而是真有两边,双遮双照。如天台宗提出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三论宗提出的“八不中道”“二谛圆融”,禅宗提倡的“定慧等学”,都有强调禅观不能脱离世相,不能脱离实际生活本身的意思。王维作为一位虔诚奉佛者,对中国佛学尤其是禅宗南北二宗的禅法,不但有很深的领会,而且也有认真的践行。他早年与北宗禅有较多的接触,对那些“闲居净坐,守本归心”(净觉《楞伽师资记》卷一)的禅法很是倾心,在为北宗禅大师净觉撰写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中还盛赞净觉安居坐禅能达到“猛虎舐足,毒蛇熏体,山神献果,天女散女,澹尔宴安,曾无喜惧”的境界。以后,他接触到南宗禅,对那种真空妙有两不相妨,“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禅法更为佩服。如由他撰写的《六祖能禅师碑铭》就说道:“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乘化用常。……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爱。……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不着三界,徒劳八风,以兹利智,遂与宗通。……”在这里,王维主要是谈了“空”与“有”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看来,王维的禅学观是既包含了“闲居净坐”的北宗禅法,也包括了“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的南宗禅法。将这两种禅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王维特有的“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禅观修习方式。
《旧唐书·王维传》曾提到王维“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王维在自己的诗中也多次写到“闲居净坐”的乐趣。如:
竹径从初地,蓬峰出化城。窗中三楚尽,林上九江平。软草承趺坐,长松响梵声。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秋夜独坐》)
暮持筇竹杖,相待虎蹊头。催客闻山响,归房逐水流。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
从上述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维的“闲居净坐”一般都带有禅定禅观的目的,但在“净坐”之时,又并非枯寂息念,而是耳有所闻、眼有所见、心有所感、思有所悟的。当然,在更多的时候,王维的禅观修习并非采取净坐的方式,而是如南宗禅师们常说的“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永嘉玄觉《证道歌》)采取的是一种“山林优游禅”的修习方式,就在这种“境静林间独自游”(同上)的生活中,诗人既获得了“心法双忘性即真”(同上)的证语,也获得了无人干扰、心清境静的静美享受,一首首意境优美、含蕴深邃的山水诗也就在这种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高度融合之中诞生了。
我们认为,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其所以能在王维这里得到高度融合,除了宗教体验本身就具有审美体验的内涵这一因素之外,还与王维本人对解脱方式的认识有关。他在《叹白发》诗中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又在《山中示弟》诗中说:“山林吾丧我。”而《饭覆釜山僧》诗更明确地说:“一悟寂为乐,此身闲有余。”可见他是有意将自己一生的烦恼痛苦消除泯灭于佛教这个精神王国和幽寂净静的山林自然境界之中的。换言之,空门、山林、寂静之乐就是他解脱烦恼痛苦的最好方式,这样,他就必然要通过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知道,无论在宗教体验还是审美体验中,主体都能获得一种解脱、自由、轻松、愉悦、和谐的感受,都能消除心中的矛盾、痛苦。禅悟这种中国特有的宗教体验的目的即是为了明心见性,而中国文人徜徉于大自然中优游山水之审美体验也往往是为了得到一种“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和洽之境界。所谓“明心见性”的“性”即是谢灵运曾经说过的“性灵真奥”,(见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引谢灵运语:“必求性灵之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在佛家而言,此性即是万物所共具的本体——真如佛性,因此,性即是真,见性也就是即真。那么,王维认为只有什么才是性,只有什么才是真呢?他说:“浮名寄缨佩,空性无羁鞅。”(《谒璿上人》)又说:“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也就是说,性者,即空也。虚空即是我性;真者,浮也,浮幻即是我心之真。总之,我之心性即是虚空不实的。王维这种认识无疑是符合佛教教义的。慧能《坛经》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空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4]又说:“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4]慧能认为,由于心性虚空,所以广大无边,因此一切世间万物皆可包容于内。而世间万物在其本性上也只是虚空。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5]这就是所谓“诸法性空”、“万法皆空”。即无论物、我,无论内在之心性,还是外在之境象,在本体上都是虚空不实的。由此出发,禅宗认为,若要明心见性,体认自己性空之本体,必须“即事而真”,即通过内在之心性与外在之物境的契合交彻而获得一种对于“空”的证悟,这种证* 悟即是解脱,即是涅槃境界。
当诗人王维具备了“空性无羁鞅”、“浮幻即吾真”的认识之后,便自觉地去除因为执虚为实而带来的种种世俗缚累,“无羁鞅”的诗人在自然山水境界中常常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他是那样既无心而又有意地观照着自然界云生云起、花开花落种种纷纭变幻的色相,他说:“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寒空法云地,秋色净居天。”(《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外在的一切物境都是生灭无常的,而诗人的心性也是虚空无常的。概言之,变幻莫测,虚空无常既是诗人之真性,也是自然界万物之真性。在已复其真的诗人那里,即自然万物之真,便是见自然万物之性。所谓:
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木兰柴》)
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文杏馆》)
逶迤南端水,明灭青林端。(《北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辛夷坞》)
大自然的一切都是那样清寂、静谧,既生灭无常但又充满生机,无牵无挂,无缚无碍,一任自然,自由兴作,诗人王维便正是通过这种即自然之真,悟自然之性理来回归自然的。在与大自然之真的融和契合之中,诗人感到了愉悦,也得到了解脱。然而,当他沉浸在那由彩翠、白云、青林、红萼组成的大自然境界中时,他能不感到美吗?何况佛教之色空观还一再强调要因色悟空,因空见色呢?可以说,不知大自然纷繁变幻的妙有之美,便不可能悟得世界万物虚幻无常的真空之理,因此,像王维这样一位有着对美的敏锐感受力的艺术家兼诗人,是应该比一般人更具备体悟佛理的灵心慧性的。当他徜徉在大自然境界中时,自己那“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虚空寂静而自由自在的空性便与“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偶成》)的自然山水有了亲密的契合,就在这朗然见物之性(变幻无常之性)与物之境(奇妙变化之境)的同时,也见出了我之性(性空无碍之性)与我之境(澄明如镜,虚空能含万法之境)。正因为“我”之性已去除了一切对于世俗妄念的执著,所以在已复其本真的诗人王维那里,当他与各得其所、自由兴作的自然万物相遇的时候,便能以己之性空之真去与万物生灭变幻之真相契合,此时诗人心中鸟飞鸟鸣,花开花落,一片化机,天真自露,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归一,诗人的生命存在便在此中得到了自由解脱,他的本真也在此澄明朗现。正因为“我”之境已去除了一切来自世俗浮华的遮蔽,所以它朗然澄澈如天地之鉴,一切万物可以在此光明晶洁的虚空中自由来往,万物得以历历朗现,它们变幻无时但又生生不息,虽虚空无常但又一任自然,诗人在清晰地感受着它们的同时,也在清晰地感受着自己。可以说,王维正是通过这种见物之性、物之境的审美体验,从而体悟自己内心中澄明敞亮、无挂无牵、无缚无累的自我之性的。按照佛教的说法,这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即事而真。诗人就在这种将自性、物性、佛性都融合到澄明寂静之美之特性的体验中,实现了解脱与超越,进入了涅槃寂静的境界。
其次,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之所以能在王维的山水诗中得到融合统一,也是因为二者之间可以互为作用。就宗教体验而言,如前所述,佛教强调因色悟空,因空见色,尤其是大乘般若空宗所倡导的“实相禅”是以观照诸法性空的实相、体证真如佛性为究竟的。他们认为,观万物为空并不难,而应从空入假,即观真如本体虽空,但却依诸因缘而生起万法,故万象森罗,宛然是有。然此有并非真有,而是一种“无常”“无我”的幻有。而幻有虽不可执虚为实,但修行人却必须通过对“幻有”“假有”的观照,才能体悟万象“无常”“无我”虚幻不实的真性。这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3]真空妙有,一则为体,一则为用,修行人如果偏执任何一方,就不可能悟得真如佛法。
王维是深谙“真空妙有,无异无碍”之禅家三昧的。他说:“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所以他十分注意观有悟空,双遮双照。所谓“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摘露葵”,(《积雨辋川庄作》)“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终南别业》)就是他借对大自然物象的观照而得以进行宗教修习的一种体验。在他的不少山水诗中,也常常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观照,表现出深邃精致的“色空一如”思想。如《木兰柴》:“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又如《北垞》:“北垞湖水北,杂树映朱阑。逶迤南端水,明灭青林端。”这两首诗都是眺望远景所作。我们可以看出,王维在观照景物时,特别注意对景物的光与色彩的捕捉,他正是通过夕照中的飞鸟、山岚和彩翠的明灭闪烁、瞬息变幻的奇妙景色的表现,通过对湖对岸青翠的树林后面,北垞水波光如同一条银白色的缎带时隐时现、变幻不定的现象的描绘,来表达出事物都是刹那生灭、无常无我、虚幻不实的深深禅意的。与上述两诗表达出相同“色空”、“无常”思想的还有《华子冈》诗:“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这首诗则直接写出了诗人登上华子冈眺望远景的深沉感触:飞鸟向无尽头的天边飞去,只在转瞬之间就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仅留下一片绵延起伏的群山,在秋空下默默地无言地伫立。这一切令深知空寂禅理而又多愁善感的诗人惆怅万分,人生、世事难道不也是这样幻灭无常的吗?正如陈允吉先生在《唐音佛教辨思录》中指出的那样,王维的山水诗“的确是处心积虑,借助于艺术形象来寓托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在描绘自然美的生动画面中包含着禅理的意蕴”。[2]如前所述,王维作为一位具有音乐、绘画才能的艺术家,对于自然美有着远过常人的敏锐感受力,同样,他也常常利用这些艺术才能特别着力于对自然景物声、光、色、态的表现,通过自然物象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所呈现出的种种变幻不定的色相显现,使“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理禅意得到了极为生动形象的演示。
如果说,王维的宗教体验常常必须借助审美体验才能实现,那么,当王维沉浸于山水自然境界进入极深层的审美体验的时候,这种审美体验也往往到达了宗教体验或哲学体验的层次。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一文中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6]他还说,艺术境界是介于学术境界与哲学境界之间的。他认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受的模写,到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个层次。他引用冠九《都转心庵词序》中的话说:
是故词之为境也,空潭印月,上下一澈,屏知识也。清馨出尘,妙香远闻,参净因也。鸟鸣珠箔,群花自落,超圆觉也。
综合宗先生的种种说法,我们可以知道,人们对于宇宙、自然、人生种种色相美的体验只有深入到了宗教或哲学的层次,才能使自己所写的一切形象都具有了象征意味,才能借有限以表现无限,由对丰富复杂的色相描写到达最高最深的玄冥境界。试看王维的小诗: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文杏馆》)
这一切的一切,既是诗人片刻之间的审美体验,然而又担荷无边的深意,多么精致,多么深邃,这就是从刹那见永恒的超圆觉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禅既在刹那,又在永恒,变幻无常,生生不息,虚空中有妙有,妙有即是虚空,空寂中见流行,流行中见空寂,这究竟是审美体验还是宗教体验?究竟是艺术境界还是哲学境界?这就是禅,是“诗佛”王维将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融合为一的最高艺术意境。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的心灵深处而灿烂的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二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6]胡应麟说王维的辋川诸作“字字入禅”,读后使人“名言两忘,色相俱泯”。[7]王士祯说王维的五言绝句“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带经堂诗话》卷三)王维的这些山水小诗为什么能形成如此深邃玄冥的境界?因为诗人对山水自然美的体验已经进入佛教空幻寂灭义理层次了。歌德说:“在璀灿的反光里面我们把握到生命”,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就是说,当人觉悟到生命无常的时候,也就证悟到了自己的本性不过是虚空,由此而产生的对纷浮世事不粘不滞、无执无求的态度便是一种解脱,经由解脱而达到自由之后,人就彻底去蔽了,在澄明无蔽的境界中,人也就返回到了本真,获得了清净无染的自性,把握到了生命。所谓“一切生灭者,象征着永恒”,[7]在宇宙自然之中,无论是人是物,是一花一草,一鸟一石,还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时时处在生灭无常、变动不居中。无常便是事物的本质,刹那便是世界的永恒。王维诗中那时明时灭的彩翠,合而复开的绿萍,转瞬即逝的夕阳,若隐若现的湖水,都是诗人“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王船山语)[6]的杰作,是他对大自然的审美体验已经到达哲学层次或宗教层次的产物。在这样的艺术意境之中,理即是事,事即是理,一切都如同天珠交涉,互映互证,融彻贯注。这,就是璀灿的反光,在这种璀灿的反光里,人与物,事与理,无限的时间与无穷的空间,一切都在对刹那永恒这一本真之美的体验中高度融合统一了,而我们的诗人于其中所领悟到的也不仅是大自然的物态天趣,而是一种宇宙的哲理、生命的哲理了。
庄子在其《天道篇》中曾经说道:“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境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他在这里所讲的是“虚静纳物”、“澄怀观道”的问题。我们知道,主体在进入宗教体验或审美体验时,都必须摒弃尘念,清除浮躁,宁神息心,才能见性,才能见美。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诗品·冲淡》)只有当诗人心境极为淡泊、虚静的时候,才能可能对大自然最神奇而又最微妙的动人之美,有一种会心的感受与体悟。苏轼在写给参寥禅师的诗中说:“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今诗语妙,无厌空与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寄参廖师》)他认为,浮屠佛子之所以能写出绝妙的诗篇,其原因就是因为心如丘井,意绪淡泊,故才能“了群动”,才能“纳万境”,这也就是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如前所述,诗人只有在彻底去蔽的澄明敞亮的心境中,大自然的一切才能历历如在镜中朗现出它们本来生机活泼、自由兴作的飞跃生命,正如王维在诗中所写的那样: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昙兴上人院》)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
只有在“人闲”“夜静”“山空”时,诗人才能感受到月出鸟鸣,觉察到细小桂花的轻轻落地;只有在“夜坐空林寂”时,诗人才能感觉到“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由于心境之特别虚静,他甚至可以感受到阶下院中那青苔绿幽幽的颜色,正在静悄悄地向自己衣襟上爬来。如此奇妙得不可思议的幻觉通感,如果不是心境极其虚静的诗人,又有谁能做得到呢?这就是“静穆观照与飞跃生命构成的艺术二元”,而王维也正是在这种二元的艺术境界中与大自然和光同尘,从而获得寂静、圆满、和谐、自足的本真之性的。
如前所述,对大自然最深层次的审美体验即近乎宗教体验,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像王维这样具有觉心、灵性、慧眼的诗人才能更好地进入到自然美的最深层之处,深入造化的核心,表现出自然物象最具魅力的神理。换言之,只有具备虚静淡泊之心性的诗人,才能对自然物象遗貌取神,创构出空灵清妙的意境。因为这种深层次的体验往往能使作者既不拘滞于对“我”的主观意念的表现,也不拘滞于对“物”之形貌的逼真刻划了。试比较王维与裴迪在《辋川集》中的同题唱和诗即可知道。如《文杏馆》,裴迪的诗是:“迢迢文杏馆,跻攀日已屡,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后顾。”王维的诗则是:“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又如《木兰柴》,裴迪的诗是:“苍苍落日里,鸟声乱溪水。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王维的诗是:“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再如《辛夷坞》,裴迪的诗是:“绿堤春草合,王孙自留玩。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王维的诗则是:“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裴迪的诗总是写自己在跻攀、缘路、留玩,看不到对自然物象深层的审美体验,而王维的诗虽然没有诗人自我形象、行为、主观意图甚至情感的表现,只有大自然物象本身声、光、色、态的纯然呈现,而物象之神理却因其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深入细致而得以有极为清楚动人的表现。这一切当然也是因为其心境极为澄明空寂,所以才能使物色自映照于心而不必再着意去寻幽访胜了。苏轼在《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是“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一篇神气都索然矣”。盖渊明也好,王维也好,他们都是自性圆满具足,无待无求,亦不着意之人,他们的精神已近乎庄子所说的“圣人”境界,因此心明如镜,览照万物,万物自现于心而无待其去望了。
综上所述,在王维的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之中,都包含有理性的愉悦与感性的满足的成分,诗人正是通过这二者的结合,获得解脱与自由,从而使生命得以超越的。因此,在王维那里,无论宗教体验还是审美体验,都包涵有生命体验之内涵。19世纪中叶,美国思想家梭罗为了体验自己真实无误的生命,曾告别城市,来到森林湖畔,寻求与大自然最亲密的结合。他认为人应该回归大自然,才是最高的善与美。我们认为,人的生命源泉就是来自大自然的生命,人虽然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人也毕竟是大自然的产物,和大自然中所有的生命一样,在本体上是相同的。即无论天地也好,自然也好,人类也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前赤壁赋》)生生不息,周而复始,不断变化而又实无有变,这就是宇宙自然中一切事物的法则。因此,人要体验自己的生命本真,必须与大自然有最深层的和谐契合。王维之所以在发掘自然美与表现自然美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就是因为他在其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融合中,能以静穆的观照感受到宇宙万物与自己那清寂而又灵动的生命。因此,他诗中的山水景物表现,既构成了一种‘禅’的状态,也形成了极为优美深邃的意境,无论从哲学境界还是艺术境界而言,都达到了一个极灿烂极澄明的层次。
收稿日期:1999-0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