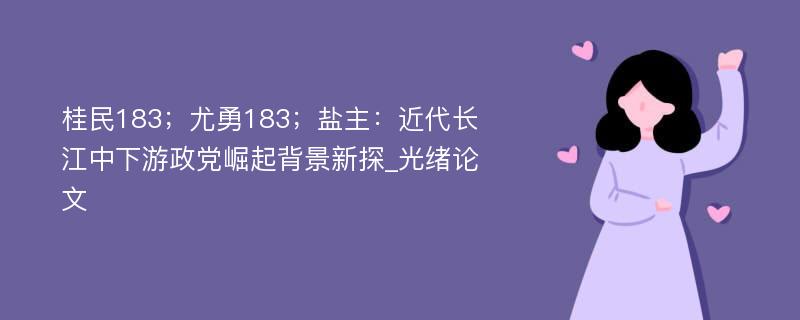
客民#183;游勇#183;盐枭——近代长江中下游、运河流域会党崛起背景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盐枭论文,会党论文,游勇论文,中下游论文,长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下半叶,以哥老会、青帮为主体的秘密会党在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流域蔓延发展并迅速崛起,成为这一区域最有势力和影响的秘密结社。对这一区域哥老会、青帮崛起的社会历史背景,前辈学者归结为: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化,近代长江、运河流域旧式航运业的衰落造成这一区域大量人口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游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于传统的“四民”之外的一个过剩的社会群体——流民、游民集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不能从事正常的职业,其中大部分最终不得不投入秘密社会,从而造成了哥老会和青帮势力的膨胀。本文试图另辟蹊径,从长江、运河流域在在皆有的客民、游勇、盐枭入手,探讨近代长江运河流域会党崛起的背景。
一
太平天国失败后,苏、浙、皖三省人口耗减,田野荒芜,荆榛塞路,大批外来客民流迁这三省,哥老会为主体的秘密社会也随之在这一地区发展起来。
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苏、浙、皖三省是太平军与清军及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常胜军”长期交战、厮杀的地区,人口因逃离、战死、饿死或其他因素而锐减。据清方统计,浙江人口到1866年减少为637.8万人,净减23728857人,占战前人口的72.8%;1874年江苏人口减少为1982.3万人,净减24679621人,占战前人口总数的55.7%;安徽人口直到1892年也仅206万人,净减16034012人,占战前人口的42%。 (注:这些统计数字,参见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这些统计数字可能有缺漏或不精确之处,但人口数量的大量耗减则是肯定的。战后,清政府面对人口锐减、耕地荒芜的现状,认为“善后要政、莫急于垦荒”,各主要荒废省区先后拟定出垦荒章程,各垦荒州县先后设立“劝农局”、“招垦局”、“招耕局”之类的机构,从事荒地的招垦事宜。如安徽在同治初年于临淮设立“善后屯垦总局”,在凤阳、定远设立分局,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保结,……一律借与耕牛籽种,准其开垦,其续价收租,较土著之民一律办理”(注:唐训方《唐中丞遗集》,《兴办屯垦告示》。)。结果,“客籍农民迁入垦荒者,接踵而至”(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第7 页。)。苏、浙两省也大体如此。在迁入三省的“客民”当中,两湖人占有相当的比例。战后安徽广德州:“土著不及十分之一,田地荒芜,招徕客民开垦入籍,湖北人居其四,河南人居其三,江北人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注:光绪《广德州志》卷16。);南陵:“湘、鄂及江北等处客民流寓此者亦十之五焉”;南陵县城还有湖南街;(注:民国《南陵县志》卷41。)宣城:“客民约占十分之九,其中以两湖籍居多数,皖北次之”(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2页。)。在江苏宜兴,“赵、豫、淮海人民蜂至”,两湖农民亦“争来垦治”;(注: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5。)光绪中后期, 外来客民仍迁往苏南,“以两湖人为多”(注:丛刊本《辛亥革命》(三)第69页。)。浙江也有不少两湖籍客民迁入,如安吉县同治时期有“宁绍湖广安庆”等地客民10848户,接近全县民户总数的一半。 (注:同治《安吉县志》卷4,“户口”。)
在客民当中,还有一部分湘、淮军的裁撤勇丁。清代后期,湘、淮军大量裁撤,不少散兵游勇流散于江南地区。如曾国藩攻据南京后,所辖部分湘军在苏南领垦荒地;左宗棠则在浙江创行“撤勇归农之法”(注:《申报》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就地安置了部分“老湘营”勇丁。另外,“遣撤之勇流落不归者,亦改而务农”(注:《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淮勇也“虽遣不归,盘踞于浙湖郡县,而以贩盐为生”(注:《论江浙枭匪》,《东方杂志》1906年第1期。)。
两湖地区是哥老会十分活跃的省份,随着湖广籍客民大量流向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以及部分湘、淮勇在这些地区逗留或落户,哥老会不可避免地随这些“客民”的到来而扩散开来。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安徽巡抚陈彝奏称:宁国府拿获熊海楼、熊之到、陶桂有等12名哥老会分子,他们“分隶湖南长沙、临湘、善化、宁乡及湖北黄陂各县,均寄居(宁国府)南陵县,以垦荒为名”,是一批从两湖移居安徽的“客民”。光绪十三年正月,原本就是“积匪”的熊海楼在南陵县会遇何淋、王南山,商同结会,旋“秘造伪印、阵图、序规、执事”,“立会名系戴公山龙泉水金兰香结义堂”,纠邀会众数百人,迭次抢劫。(注: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十日安徽巡抚陈彝《会匪勾结谋逆折》,见徐安琨《哥老会的起源与发展》附件奏折。)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十二日刘坤一《复李中堂》说:“皖南地处万山,半山半客,哥匪、盗匪混迹其中。”光绪三年(1877)浙江杭州府拿获哥老会分子崔华云,供认系湖南常宁县人,本在严州湘营中充勇,遣撤后在仁和县塘栖地方,开设洋烟馆,“时有游勇钟景光、黄发洋、胡镜卿、彭受辉往来吸食”,遂起意纠众结拜哥老会,崔自任为“浙省集贤龙头总坐总理合办各军帅”,并放票(每票600文)招邀会徒。 (注: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浙江巡抚梅启照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26。)湖南客民和湖南籍的散兵游勇还在江南一带结成“湖南帮”,声势和规模仅次于安徽人结成的“巢湖帮”,著名的湖南帮帮首有曾国漳、朱鸿贵、曹新甫等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曾国漳在常州、江阴等属内河,“开堂立会,诱约多人,遣党分路肆行抢劫”。并与“匪目”崔得沅、李金标、熊满堂“结成死党”,各踞地段;(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266—268页;曹仲道《清末沙洲帮会的活动情况》,载《常熟文史资料辑存》(三)。)朱鸿贵、曹新甫等人是太湖周围湘籍客民领袖,“释兵则民,执兵则盗”。两湖客民在哥老会领导下还屡屡进行抗租斗争,如“常州府属之武进县,先因楚民初到开垦,其时本地人少耕作,及至楚民渐多,声势渐横,每届收租,类多抗欠,甚有收获后饱载远扬”(注:《光绪朝东华录》(二)第1654页。)。
太平天国失败前后,太平军将士大多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杀害,但也有部分太平军被湘军纳降收编,如同治年间,张遇春部万余人投降,被挑留3000人,立为春字营,由张自统;李昭寿部立为豫胜营,由李自统;童容海部立为启化营,令童自统。再如同治四年(1865)杭州城共存兵勇“八千名,内有长毛投诚者三千名”,湘兵5000名;(注:《吴煦档案选编》(四)第154页。)70 年代随左宗棠进兵陕甘的高连升果营,“名虽楚军,实则剿平广西、江西、闽浙、粤东发逆收降人居多”(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3—24页。)。还有一部太平军将士被遣回广西原籍,或被清政府在江南等地就地分散安置以辟垦荒地。据记载,江苏无锡、宜兴以至浙江长兴、余杭一带“种田者无数”,其中“内多散贼”。(注: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312页。)如被遣回广西、广东原籍的太平军成批“转红”(注:《玉林州志》卷18,《堂匪总录》卷4, 转引自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178页。)加入天地会反清队伍一样, 被收编“纳降”的太平军,就地安置的“散贼”也有不少加入了哥老会。同治四年(1865)杭州蒋益澧湘营抓获30余名哥老会分子,其中太平军“投诚赏职之人不少(有10余名),又有贼中师爷数名”(注:《吴煦档案选编》(四)第149页。);光绪十二年(1886 )浙江巡抚刘秉璋的亲兵中营拿获哥老会头目杨玉松、王葱五2名,起出会簿等件, “杨玉松呼为杭州主将、王葱五呼为温州主将,纠结党羽,欲图举事”。主将,原为太平天国后期职官名称,杨、王自称主将,可能原本是太平军中人。(注: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刘秉璋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27。)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江西巡抚德馨奏报拿获黄咸礼,“为哥老会正头目,授有左营旅帅伪职”(注:宫中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686。), 这个“左营旅帅”官名,显然也来自太平天国官制。当然,也有部分太平军将士投入秘密宗教组织的,如同治五年(1866)底江西永新县拿获斋教教首李合其、吴宾官等,李“先在原籍(江西)信丰县被石达开股匪掳去,曾受刑审伪职”,嗣为清军击败,携带“大军略统戎巡察刑审伪印四颗潜逃回江”,次年与同在“贼营”的涂观生用“洋布蜡光纸造有伪官执照并保家凭据多张”售卖。后与吴宾官、金生亮等斋教徒合伙,围攻永新县城。(注:《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3第65—66页。)在19世纪70 年代长江流域发生的“其字派大抵出自白莲教、其头目大抵出自哥老会”(注:沈葆桢《匪徒散播流言民情惊扰现筹查办情形折》,《沈文肃公政书》卷6。)的“纸人剪辫”事件中,也有太平军余党参加——因为事件发起者虚构的圣地“九龙山”上有都旗、主旗、丞相、豫、燕王等名目,(注:光绪二年六月初一裕禄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26。)这些,均来自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失败后,一些太平军将士转而加入哥老会或斋教等秘密团体,这是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各种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而这时期秘密社会却能够从事组织群众自卫抗暴、劫富济贫、扶弱抑强以及反封建统治、组织农民起义等集合“反叛”的活动。光绪八年(1882)初贵州巡抚林肇元慨叹:“洪秀全结上帝之会为滔天之逆,其已事也;乃洪逆方平,而哥弟会又起,……声息气势较洪逆秀全之上帝会尤远且宏也。奸民伙乱一至如此,万一有稍雄桀者出而号召其间,远近响应”,则大局不可收拾。并认为哥老会这一“内患”较“外夷(之患)尤急”。(注:光绪八年一月廿一日林肇元《密陈各省会匪情形由》,徐安琨《哥老会的起源和发展》附件。)应该说,林肇元的这一看法是有“先见之明”的。正是哥老会继承了太平天国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传统,最终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组织“号召”下,参加了推翻满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斗争。
二
太平天国失败前后,长江流域充斥着大量的散兵游勇,对这一区域的秘密社会势力的发展与壮大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清朝统治者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面临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上无处不在的散兵游勇。大批散兵游勇主要出自两途:一是战败后大批太平军和各地起义军的幸存者,出于躲避清政府的政治迫害等原因,并没有全部返回原籍或就地务农,而是隐姓埋名,浪迹四方。如“皖北各处半为捻逆旧巢,皖南尤为客民麇集。……自肃清后,虽著名漏网匪首陆续捕除,而降众散勇当不一而足,……此等游手之徒,势不能悉安耕凿。”(注:《光绪朝东华录》(一)第1251—1252页。)二是大量被裁撤的清军营伍勇丁,这是散兵游勇的最主要的来源。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先后遣撤湘军数十万;淮军在镇压捻军起义之后,被裁98营,共5万人, 几达淮军半数。此后,又陆续裁撤,到本世纪初,被裁殆尽。绿营也大规模裁撤。自同治二年(1863)至光绪十九年(1893),有明文可考的共裁绿营兵17.3万多人,实际情况远不止此数。(注:罗尔纲《绿营兵志》第8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甲午战后,绿营又被裁6 万名左右, (注:周育民《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省绿营被基本裁尽。 新兴的“练军”也有被裁的情况,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江总督刘坤一裁江苏练兵1981名、安徽1296名、江西822名。 (注:《刘坤一遗集》(三)第991页。)这些勇丁被遣散之后,生活无着,纷纷流向秘密社会。 刘坤一指出:沿江各省哥老会“半系军营遣撤弁勇”(注:《刘坤一遗集》(一)第381—382页。),黄翼升也奏称:“查外间所称哥老会,多是游勇相率为匪”(注:《光绪朝东华录》(三)第3207页。)。笔者曾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列出过《光绪年间哥老会成员出身背景简表》,通过此表可知,在所列217名有明确出身背景或职业的哥老会成员中, 其充当各营弁员、营兵、勇丁及武举、武生出身者,占121名,几近60 %,(注:参见拙文《湘军与哥老会的蔓延及其崛起》,载《曾国藩学刊》总第6期。 )充分说明了哥老会的盛行与社会上大量充斥着的散兵游勇的关系。此表还反映出一个现象,哥老会成员中有明确籍贯者为180 人,其中湖南、湖北籍占92名,占一半稍强;而湖南、湖北籍的哥老会员其“结会地点”却大多不在本籍,而在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并且,光绪中后期以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一方面说明,湘军兴起后,两湖地区投营充勇者特别多,因而哥老会成员也相应增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湖哥老会沿江向中下游、运河地区伸展势力的趋势。
游兵散勇的大量存在并且纷纷结拜哥老会,引起了各省督抚的焦虑和惊恐。光绪十七年(1891)两江总督刘坤一奏称:“江苏自兵燹以后,伏莽未靖,游勇会匪到处勾结为患,以致盗风日炽,剽劫频仍”(注:《刘坤一遗集》(二)第689页。);二十四年(1898)七月, 刘坤一又奏称:“沿江之九江、安庆、芜湖、大通、金陵、镇江、仪征、瓜扬一带,五方杂处,往往藏垢纳污。……至游勇中每有哥老会匪、安清道友,踪迹诡秘,支党蔓延”(注:《刘坤一遗集》(三)第1051页。);光绪八年(1882)四月刑部奏折中曾详细地描述了各省游勇、会党的猖獗情形:“直隶称西北临边,东路滨海,时有马贼海盗勾结为患,张、独、多三厅,广袤千数百里,匪徒肆行无忌,西南为枭匪出没之区,……奉天称海疆大定,腹地有遣散未尽之游勇;……黑龙江称有马贼什伯为群,陕西称抚回罔知法纪,江湖等会党羽动至数百人之众。湖南、北称遣散勇丁抢劫为生,刀哥会层见叠出;山西称口外界连新疆,为马贼游勇出没之所;……山东称西南为捻、幅渊薮,东北滨海,时有马贼、枭匪出没;安徽称降众散处不一而足,各处撤勇纷至沓来,哥会斋匪等项,靡地蔑有。……四川称瑱匪、会匪、枭匪实繁有徒,加以游勇散练,动多勾聚。江苏省称滨江临海,口岸繁多,华洋辐辏、奸宄溷迹。河南省称,陈、南、汝、光各属,逃捻余孽尚多,河、陕、汝一带,山径丛杂,游勇劫夺,所在皆有。河北情形亦然。江西省称教、斋土匪焚劫杀人,遣散游勇聚众抢劫之案,尚未尽绝。”(注:《光绪朝东华录》,总1317—1318页。)
最初,对待日益严重的游勇问题,清政府并未制定一个统一的政策。光绪元年(1875)署理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政府建议对遣撤勇兵“宽为收标”:
又查该哥匪等半系军营遣撤弁勇,其中竟有二三品武职人员,前曾充当偏裨,易于招呼丑类,且系久经战阵,尤恐猝为厉阶,此辈甘为游荡者固多,其迫于饥寒者亦复不少,可否仰恳饬下湘鄂等省宽为收标,仍照江西奏准章程,给予半俸,既得升斗以养身家,且冀补署有期,不至自甘暴弃。(注:光绪元年十月《密陈会匪情形设法钳制片》,《刘坤一遗集》(一)第381—382页。)
所谓“收标”,就是以遣散勇丁、游勇来挑补绿营的兵额。经过多年的战争,长江流域的绿营几乎荡然无存、毁弃殆尽。战后,清廷念念不忘恢复绿营制度,以收归业已旁落于地方督抚手中的兵权,并曾建议以湘军来挑补绿营,但此举遭到了曾国藩等的反对:“挑补兵额之说,近多建此议者。臣窃不以为然。盖勇丁之口粮,一倍于马兵,三倍于守兵。马兵之缺极少。守粮月支一两,断不足供衣食之需,谁肯于数千里之外补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朴实之勇,补之以绿营之缺,必不情愿,其愿补者,皆游惰无归者也。”(注:同治三年七月廿九日《裁撤湘勇查洪福嘓下落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5。)李鸿章、张之洞对“挑补绿营兵额”、规复绿营旧制,也甚不以为然。同治年间,在江西巡抚任内的刘坤一“因盗案多有武职人员,曾以收标给俸为请”,即对曾国藩所说的那些“游惰无归”之辈给予半俸收标,由于这一做法与清廷欲恢复绿营旧制的意图若合符节,很快得到了清廷的俞允。这次,刘坤一又欲将他的收标办法推行到散兵游勇众多的湘鄂等省。就此,清廷谕令各省督抚复议。结果,除江西巡抚刘秉璋秉刘坤一之意于光绪二年(1876)三月初二日上《严办会匪、武职收标章程现无流弊折》表示赞同外,(注: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26。)其他地方督抚特别是那些湘淮实力派纷纷表示反对。湖广总督李瀚章首先表达意见:对撤遣勇丁,“至虑其为匪,遂谋所以赡恤之,此举则似是而非。……此等会匪有已保官职有系属平民,既难尽予收标,即给俸岂能遂戢奸志。若照江西办法概给半俸,不特度支难继,甚至良莠不分,若辈将以食俸为护符,更恐肆行无忌。是会匪本属散处,反令招聚省城,关系实非浅鲜。江西所定章程,本非良法,倘再推及各省一律仿照,转长奸邪之志,殊于政体未合”(注:李瀚章《合肥李恪勤公政书》卷6,转引自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254页。);三月二十二日,安徽巡抚裕禄上《拟武职收标人员仍直循旧办理毋庸另议章程》,也表示反对。(注: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26。)三月二十七日,贵州巡抚黎培敬《遵议办理会匪情形由》折中表示赞同李瀚章所议,“无庸另议章程”(注: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26。);七月二十五日,暂护四川总督、云南巡抚文格指出:“会匪多嗜乱之徒,如裁撤之将弁负其犷悍之性,甘与为伍,亦就区区半俸,所能束其野心?是收标徒自收标,而入会依然入会,且招聚一处,后患甚误,至虚縻经费……”(注: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26。);光绪二年春,新任两江总督沈葆桢以“巨款难筹”,收标后“内外匪声气潜通”,反对收标,认为处理游勇、哥老会、青帮只有按照曾国藩的“不问其会不会、只问其匪不匪”,以惩“首恶”,散“胁从”。(注:《设法严拿哥老会匪片》,见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6。)
“收标”之议,由于遭到普遍的反对,最后不了了之,地方督抚对待游勇、会党问题,仍重弹曾国藩所定的“外宽内严”、“刚柔并济”的老调。这次争议,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社会上大量充斥的散兵游勇问题,而实质上涉及到是恢复还是废除腐朽的绿营制度这一关系到清政府统治命运的重大问题。清廷欲借“收标”,重建绿营以替换非国家“经制”的湘、淮军,以重新掌握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必然遭到湘淮地方督抚的强烈抵制。众所周知,湘、淮军兴起后,虽暂时挽救了清王朝的灭亡,但同时削弱了清朝中央政权的军事基础,使军、政实权由满族皇室为首的贵族手中转移到湘、淮系的地方督、抚实力派手中,形成了晚清政治、军事生活中“兵为将有、督抚专政”的独特格局。这次“收标”之争,仅是地方督抚权势日盛、清政府中央集权日益削弱的一次具体显现。
“收标之争”最后没有结果,散兵游勇仍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在这一问题上清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各怀私利、勾心斗角,但为了清封建统治能够维持下去,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的确又都在殚精竭虑地试图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无奈当时的中国已经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战争连年,国弱民穷,已难以从根本上铲除散兵游勇产生的社会土壤,同时缺乏解决日趋恶化的散兵游勇问题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
三
盐枭,自古即充斥于长江、两淮地区。如康熙后期,“淮阳一带地方,有山东、河南流棍,聚集甚多,兴贩私盐。其中各有头目,或率党数十人,或率党一二百人,横行白昼”(注:《李煦奏折》第129 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他们之所以被官吏称为“盐枭”,是因为“枭私者出于所在之私贩,以其剽鸷,而谓之枭”(注:《两淮盐法志稿》卷155,“杂纪门·艺文”(一),转引自萧国亮《清代盐业制度论》,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2期。)。近代以降, 江淮地区的盐枭更形充斥,活动规模、组织形态、活动方式等较过去相比,都显现出一些新特点。
第一,盐枭在太平军与清军的军事政治大搏斗的夹缝中壮大了自身的实力。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转战大半个中国。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广、江西、安徽、江苏等淮盐引地,清湘、淮军与太平军、捻军长期争夺、激战或对峙,致使淮盐运道梗阻,引岸丧失、运商星散。因盐销不畅,使得场盐堆积,一些灶户被迫停煎,大量的运丁、灶丁纷纷失业;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又恰是清政府的漕运要地,这里成为军事上角逐的场所,漕粮河运无法进行,数以万计的水手、舵工、纤夫与盐船运丁、盐场灶丁一样,也失掉了赖以活命的饭碗,他们一部分加入了太平军或捻军,也有部分“追随曾国藩的军队,屡建功勋”(注:长野郎《中国社会组织》(中译本)第274页,光明书局1930 年版。),相当一部分却聚集到两准盐场,组成了安清道友(青帮)。就在太平军与湘军展开殊死搏斗的同治六年(1867)底,卞宝第奏:
闻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其先数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带把持村市,名曰站码头,借查街查河为名,骚扰商旅,抢夺民财,近更加以各处土匪附和,窝主容留,结党盈万,散布愈多,并有李世忠营弁庇护。(注:卞宝第《卞制军奏议》卷1第66页。)
以贩私劫掠为生的“安清道友”出笼后,盐枭的活动空前猖獗,他们的队伍急剧膨胀,与数以万计的失业水手、纤夫、土匪人等,在辽阔的淮盐引地,以及运河、长江中下游一带从事贩卖私盐、劫掠抢夺的勾当,活动更具寄生性,对社会的侵蚀日趋深重。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两淮长期处于李昭寿等封建割据势力的控制之下,盐枭在这一带的兴盛,臭名昭著的李昭寿及其所部“豫胜营”起了不小的作用。李昭寿,河南固始人,又作兆受、昭受、长寿,降清后赐名李世忠,“幼贫贱,秃而黠”,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痞流氓。1853年初,河南、安徽捻军兴起,李昭寿也于霍山一带聚众响应,揭竿举事。咸丰五年(1855)十月,李昭寿势穷降清,但一月后再次起义,投入太平军李秀成麾下;咸丰八年(1858)七月,再降于清将胜保,献其所据滁州、来安、天长等城,与太平军对抗,并在淮阳一带拥兵自重,割据称王(“寿王”),其所部经裁撤,最初留1.7万人,称“豫胜营”, 后来又发展到六七万人。由于豫胜营是“月给饷盐”,从此,李昭寿便和两淮盐场结下了不解之缘。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政府因军饷难筹,曾在两淮实行“以盐抵饷”办法,让清军每月提取盐包,规定“袁甲山每月提饷盐二万包,皖抚营一万包,李世忠(昭寿)营二万包”(注:《光绪两淮盐法志》卷170,“淮北饷盐”第1页。),但李昭寿野心勃勃,并不满足于区区2万包,而是力图独霸两淮盐场。在他的授意下, 豫胜营特意疏通会通河道,以利贩济私盐;他“据有城池,自为风气,于长、淮、五河等设厘卡数处,于长江河口设厘卡一处,各县亦有卡局,所获颇厚。又广运盐斤,自捆自卖,上侵公家之利,下为商民之害”;“李世忠颇骄亢任性,其部下尤恣横无状,捆盐自售,场坝避其凶焰”(注:王定安《求阙斋子弟记》卷14“抚降”。)。同治二年(1863)初,为争盐船,豫胜营与苗沛霖大战于洪泽湖;其部将杨玉珍率洋枪队突赴西坝,将各栈饷盐、商盐封锢,有运盐出栈者即斩,查封西坝盐达数十万包。(注:王定安《求阙斋子弟记》卷14“抚降”。)清廷严令禁止,但他“垄断自如”。李世忠在两淮盘踞7年之久, 在他的羽翼下,安清道友得以出笼并迅速壮大。青帮盐枭、杀人亡命之徒“有李世忠营弁庇护,官吏畏势,莫敢奈何”(注:卞宝第《卞制军奏议》卷1 第66页。)。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两淮引地的湖广、安徽、江苏以及食浙盐的浙江,遣散勇丁和在役兵丁,也投入贩私活动。周庆云《盐法通志》记载:“兵燹之后,盐船盐户多系湘楚各军官哨,大则提镇,小则参游,所用水手,皆属百战之余,犷悍强暴,最难驾驭”(注:周庆云《盐法通志》卷86,“辑私”(二),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44页。),在江浙一带,遣散淮勇多以“贩盐为生”。 一些现役兵丁也走贩私盐。如清末淮北盐场有13个缉私营,大都以缉私为名,对来往客商敲诈勒索,而对于大股盐枭,则进行勾结。如驻淮南新兴盐场的定子营,直接与盐枭勾通贩私,白日为警,夜里为匪。(注:见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第305页。)在安徽一带, 散兵游勇勾结军营炮船,“往来长江,夹带私盐,沿途洒卖,(注:光绪元年七月《禁止炮船带私示》,《刘坤一遗集》(六)第2796—2997页。)为此,光绪六年(1880)刘坤一出示“仰营哨各官及弁勇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有炮船在长江行驶,均不准颗粒夹私”(注:光绪元年七月《禁止炮船带私示》,《刘坤一遗集》(六)第2796—2997页。)。散兵游勇、在役兵丁加入盐枭队伍,不仅壮大了盐枭的声势,也使盐枭的成员背景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二,盐枭已与“青、红二帮、会、票各匪连成一气”,“如虎傅翼,莫敢谁何”。(注:《论江浙枭匪》,《东方杂志》1906年第1 期。)盐枭、青帮、哥老会(红帮)相互勾串,纠缠难分。
李昭寿豫胜营在淮场、皖北割据7年间,盐枭、 青帮势力得以坐大,在里下河一带,“抢夺民财”、“结党盈万”。豫胜营解散后,两淮盐场仍是他们的天下,如光绪三年(1877)“淮北海州一带小民,以拜安清道友,仍以伙运私盐为业”(注:转引自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302页。);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十五日, 上谕曰:“江南枭匪横行,……淮北、淮南透私之地甚多,侵灌皖岸,各关卡不查私盐,以致枭风日炽,劫抢之案,层见叠出”,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将情况奏明。刘坤一奏复中承认:“枭匪以安徽凤阳、寿州人最为强横,均住江宁之江都、甘泉县境,初仅贩私,继有抢掠、讹诈等事,乡民畏与结仇,不敢报案”(注:光绪十九年三月廿九日《复陈严缉私枭事宜折》,《刘坤一遗集》(二)第775—776页。)。两淮盐枭活动范围不只局限于里下河一带,还沿长江向安徽、湖广腹地以及苏南太湖地区伸展。光绪二十六年(1900)安徽巡抚邓华熙奏:“长江北岸和州所属无为、含山等县、南岸宣城县各乡村镇,突有私枭连樯私运,不服盘查,逞强闯关,在市上陈列凶器,公然售销,强民购买”(注:光绪廿六年正月十三日安徽巡抚邓华熙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34。)。同年六月十五日,江苏候补道韩庆云,因事乘船经过常州三官塘,天甫破晓,与枭船相遇,倒争纤路,韩庆云家丁漫骂,盐枭们即过船将韩庆云拉去,后经武进知县施沛霖率勇追回。(注:光绪廿八年五月廿日《查明部内枭匪幕丁情实折》,《刘坤一遗集》(三)第1354—1357页。)盐枭的猖獗可见一斑。在活动范围日见扩大、队伍日益膨胀的同时,某些盐枭的组织也日趋完善:
枭徒之首名大仗头,其副名副仗头,下则有秤手、书手,总名曰青皮,各站码头。私盐过其地则输钱,故曰盐关;为私盐过秤、主交易,故又曰盐行。争夺码头,打仗过于战阵,有乘夜率众贼杀者,名曰放黑刀;遣人探听,名曰把沟。巨枭必防黑刀,是以常聚数百人,筑土开壕,四面设炮位、鸟枪、长矛、大刀、鞭锤之器毕具。……大伙常带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为辈,皆强狠有技能。(注:包世臣《庚辰杂著五》,《安吴四种》卷3“中衢一勺”。)
这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这真是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完整的黑社会的写照”(注: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史》第300页。)。
盐枭队伍的壮大、组织结构的渐臻严密、活动日烈一日,与其在这一阶段和青、红帮的联手合流、交通融合有莫大关系。虽然,由于各自集团利益的驱使,他们之间也时有争夺和仇杀,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有人探得:“向来枭贩有清帮、围帮两种:清即安清道友,半东皖、徐、海青皮光棍;围帮俗号红帮,即哥老会匪,多两湖三江散勇在内。两帮争夺码头,时相仇杀。”(注:《查探徐怀礼报告》,载丛刊《辛亥革命》(三)第403—404页。)但为了对付清政府的剿杀,求得各自的生存,盐枭、青帮、红帮关系的主导方面则是更多地趋向合作和融合。这种情况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以哥老会为斗争主力的长江教案中就得到充分的反映。张之洞曾奏称这一年“沿江口岸,匪党布满,……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一处蠢动,处处响应”(注:《张文襄公全集》卷31第9页。),这里的“匪党”指的就是盐枭、 青帮和哥老会。在这次教案中被捕的一些头目,既是哥老会成员,又是青帮盐枭分子,如苏松太道聂缉规派人在上海抓获“陈金龙即陈殿魁系属红会(帮),……并自认为安清道友通字辈”(注:光绪十七年,佚名奏片,见宫中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762—1。);扬州保甲局会同营讯拿获“曾同即曾老五,……供认先入安清帮,拜张五痂子为师,排行通字辈,后又入高德华五华山哥老会”(注:光绪十八年四月初四日安徽巡抚沈秉成片,宫中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692—5。)。后来,在走私贩私、往来溷聚的过程中,这种合作融合更趋明显,特别是在著名盐枭徐宝山登台亮相成为“匪首”之后。徐宝山(1862—1913),字怀礼,江苏丹徒人,绰号徐老虎,“自幼不安本分,在外勾结无赖,种种不法”。光绪十九年(1893)在江都仙女庙犯抢劫之案被发配甘肃,但他中途脱逃,投入丹徒高资乡盐枭陶龙雨家。后来与活动于苏北沿长江的一些著名码头如七濠、口岸等处的盐枭几经火并与勾结,立稳了脚跟,领导私盐船队“往来口岸、三江口、西马、大桥、七濠、十二圩等处”,并“上至大通、芜湖、汉口、江西、下抵江阴等处,长江千余里,时有该匪私盐船出没其间”,他拥有的私盐船队多至700余号,党众万余,淮河两岸到沿江一线, 均为其势力范围。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十三日,盐枭徐宝山模仿哥老会的山堂组织及散卖飘布制度,在“七濠口演剧数日,设立春宝山堂名目,入会者人给一票”,上写口号,监读三日,旋即焚毁灭迹。由于徐宝山身兼盐枭、青帮、红帮诸多角色,加之“其狼鸷之性,狡悍之才,足以慑震群匪,时假仁义,煽结人心,赈济贫民,收纳亡命”(注:以上关于徐宝山活动的叙述,根据《查探徐怀礼报告》。),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盐枭、青帮、红帮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从组织上行动上更趋融和或合作。徐宝山接受刘坤一廷招抚后,这种融和、合作并未就此停止。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六日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军机处:“接英领事函:近日确闻票匪、盐匪、游勇及各会,拟在长江合伙,定期起事等语”(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265页。 )。二十九年(1903)两江总督魏光焘奏称:“江淮一带伏莽滋多,盐枭会匪互相勾煽,往往乘间窃发,为害地方”,并指示其部属抓捕了著名盐枭曾国漳、熊满堂。曾、熊既是盐枭头目,同时又开“天目山聚众堂”,“纠人入会”;(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266—268页。)在苏南武进阳湖一带,“自光绪廿六年北方拳匪事起,各处莠民,闻风蠢动,即有外口匪船,装载私盐,携带军械,由武进小河等口连樯入内,暗地洒卖。始尚不敢生事,继则聚赌抽头,开堂放飘,入其会者,伪诈横行,无所不至。……内有红帮、青帮匪党名目。青帮专重贩私,红帮兼行劫掠”(注:《刘坤一遗集》(三)第1354页。)。到了清末,由于行动与利益上的一致性,两淮地区及运河、太湖一带的盐枭、青帮、红帮之间渗透合流、纠缠相混更加普遍。光绪三十三年(1907)署邮传部右丞蔡乃煌指出:浙西之青帮、红帮,浙东之会匪、枭匪以及宁、绍、台之海盗,丰、沛、萧、砀之刀匪,太湖之盐贩,苏、松一带之青皮光蛋,“久已结党联盟,肆行无忌”(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279页。)。光绪三十年(1904 )八月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江苏省枭匪、会匪,“内河以董道富为首,沿海以范高头为首”,董被清兵追捕负创而毙,范“投入枭党,身充头目,贩私行劫,又为青龙山会首,……结纳亡命,沿海各属满布爪牙”(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271—272页。)。尤须指出,这时期“沿江枭会匪棍,党众势强,多以贩私为名,肆行不法,并仿哥老会恶迹,纷立会党,散放飘布,派费入伙”(注:光绪廿六年正月十三日安徽巡抚邓华熙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34。)。盐枭、青帮也自行开立山堂。不仅如此,他们也仿照、抄袭哥老会的会簿《海底簿》,结合一些漕运方面知识,杜撰出诸如《三庵宝鉴》、《家礼问答》、《安庆粗成》之类的“青帮秘籍”,使人难以准确分清谁是盐枭、青帮,谁是哥老会(红帮)。
当然,近代盐枭还具有其他某些新特点,如与清政府的武装对抗加强,更具社会寄生性与破坏性,更多地以黑社会面目出现以及日益为外来侵略势力所利用,等等,由于这些方面与本文的主题关系不大,故不再详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在长江中下游、运河流域这一特定的区域内,在在充斥的客民、游勇、盐枭,对哥老会、青帮为主体的秘密会党势力的壮大与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是这一区域会党崛起的最直接原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江、运河流域以哥老会、青帮为主体的会党,在新的地区以新的时代风貌以及其自身组织的开放性后来居上,成为近代中国最为活跃、势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无业游民的秘密结社。
标签:光绪论文; 太平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长江论文; 清代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刘坤一论文; 历史论文; 光绪朝东华录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李昭寿论文; 哥老会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历史学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